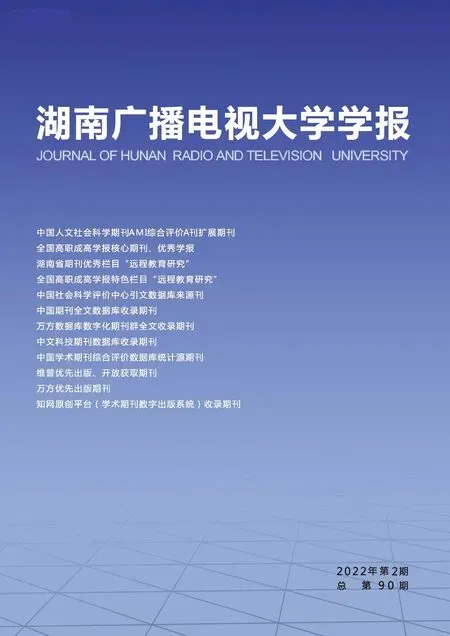新时期以来我国生态小说的复魅书写
2022-11-24杨静慧
杨静慧
(闽南师范大学,福建漳州 363000)
随着工业革命以来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引发了生态失衡,人与自然的关系走向人类中心主义,生态危机随之爆发。生态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类型,表面上呈现的是生态危机,实则揭示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以及人的精神和现代文化所面临的困境,批判以人类为中心的生态模式。人们通过工具理性为世界祛魅,祛魅意味着反对权威、驱逐神秘,使人们失去了对大自然的敬畏。随着全球气候变暖、自然资源紧缺等问题日益凸显,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新时期以来我国生态小说以其特定的艺术叙事为自然复魅,打破了以人为中心的现代话语体系,为人们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促进文学发展开辟了全新的价值向度。
一、祛魅与生态文学
祛魅一词出自马克斯·韦伯题为“以学术为业”的演讲。在韦伯看来,由于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人们产生了依靠科学就能揭开自然的神秘面纱、没有什么是不能通过理性的方法推断和演绎出来的认知,认为借助科学技术可以控制一切。理性成为人们为世界祛魅的工具,人化自然被践行,人们大肆开发、改造自然,迫使自然服务于人类。进入后工业时代,随着全球生态问题加剧,崇尚工具理性的现代社会被抛向一个不可知的未来,生态文学在时代的焦灼中应运而生。
(一)祛魅以工具理性为核心
魅原指古代传说中住在深山老林的鬼怪,释意为魑魅、古怪,后引申为神秘、令人迷惑之意,是远古时期人类对自然的初步感知,带有强烈的迷信色彩。从《山海经》《楚辞》到《搜神记》《西游记》《聊斋志异》,鬼神文化作为我国古代民众的深层文化认同,在诗歌、散文、小说、戏曲等文学形式中均有所体现。至“五四”时期,这些传统的怪力乱神与现代科学知识格格不入,新文化倡导者们在全国开展了一系列扫除封建迷信、祛除愚昧的运动,魅受到严厉的批判。胡适曾言:“吾尝持无鬼之说,……且处兹思想竞争时代,不去此种种魔障,思想又乌从而生耶?”[1]鲁迅也以“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2]来批驳讲鬼道神之徒的迷信思想。以迷信鬼怪为代表的自然之魅成为理性主义祛除的对象,遭到现代科学的强力消解。在西方社会,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使人文主义取代封建神学成为价值标准,科学理性把人性从宗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以宗教为核心的话语体系受到强烈冲击。“从原则上说,再也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而这就意味着为世界除魅。人们不必再像相信这种神秘力量存在的野蛮人那样,为了控制或祈求神灵而求助于巫术手段。技术和计算在发挥着这样的功效,而这比其他任何事情更明确地意味着理智化。”[3]自此,以理性为基本特征的科学话语取代了以信仰为核心的宗教话语,工具理性的功利化造就了祛魅,长期以来被赋魅的自然作为工具理性的对立面被拉下神坛,“一个无神的和没有预言者的时代”[4]到来。
(二)生态文学的要义是去人类中心主义
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下,自然之魅被彻底解构,大自然在人们一味追逐经济效益的活动中逐渐失去神性,被矮化为有利可图的生态资源。人们在物质和欲望的冲击下失去了对自然和生命的敬畏,人与自然的关系日渐紧张,甚至出现了人与自然的对立与冲突。在20世纪,生态文学作为一种先于其命名而存在的写作现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称为环境文学、绿色文学、自然文学等,生态文学的本质模糊。生态文学作为一种价值立场,不仅是对自然环境、绿色家园的书写,更超越了对外部生态的表层关注,侧重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表现为一种现代思维观念和生活方式。从梭罗的《瓦尔登湖》、雷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等生态力作,到我国新时期以来徐刚的《伐木者,醒来!》、何建明的《共和国告急》、李林樱的《生存与毁灭》等生态报告文学,以及贾平凹的《怀念狼》、姜戎的《狼图腾》、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等生态小说,一系列生态文学作品不仅反映了生态环境问题,更揭示了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是作家生态之思的诗意昭示。生态文学不是环境文学,因为环境这个词带有人类中心主义色彩[5]3,而以去人类中心主义来反思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才是生态文学的要义。随着生态危机的加剧,生态文学在科学至上与物欲膨胀的现实之下,对社会发展与人类生存等问题进行追问与反思,其实质是对因人本主义的过度张扬而催生的功利主义和利己主义的批判,是对现代工业文明的重新检视。
(三)祛魅成为生态文学创作的对立面
生态文学诞生于现代工业社会,这一时期祛魅随着工具理性的演变而不断发展,自然权威、神学信仰消解于科学思想和理性精神之中。生态灾难的恶果和生态危机的现实使生态文学家认识到,只有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根本前提和最高价值[5]8,才是生态文学创作的核心要义。生态文学以生态整体主义为宗旨的创作取向明显与人类中心主义对立,复魅成为生态文学反思现代化的叙事策略。人类中心主义是祛魅这一功利思维作用下的产物,生态文学的去人类中心主义实质上是对祛魅的反拨,呼吁生态整体主义的复归。生态文学创作的现实需求及思想基础在现实的自然生态危机、传统的生态智慧以及当代生态科学、生态哲学和生态伦理学[6]18的综合作用下逐渐成熟,祛魅带来的生态危机和信仰失根成为生态文学创作中的重要议题。祛魅祛除了鬼怪之魅,但也在引发生态危机的同时催生了人的精神危机与文化危机,“它不仅是一个环境事件,更是一个文化现象”[6]12。
二、新时期以来生态小说创作的复魅
吴秀明认为“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文学是源于现代的资本主义”[7]。雷鸣认为“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文学产生在新时期以后,即1980年代以后”[8]。这一时期的生态小说书写着祛魅和为自然复魅,促使人们重视生态危机,对现代人的精神与文化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一)走出祛魅:新时期小说创作的转向
改革开放以后,在我国社会建设卓有成效的同时,也出现了生态环境被破坏、人的物质欲望膨胀、人的主体性被消磨等问题。在新时期,面对祛魅带来的潜伏于现代社会中的各种问题,首先拉开现代文学发展序幕的是寻求思想解放的伤痕文学与揭示社会问题和个人伤痛的反思文学,后来致力于挖掘传统意识、民族心理的寻根文学热潮随之而来,走出祛魅成为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走向,人们越发重视对人的生存价值以及国家、民族的存在意义的探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先锋文学为代表的现代派用新奇的文学笔法批判社会秩序对人的压抑,着眼于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新写实小说则哀叹人的主体性被消磨,诸如《虚构》《透明的红萝卜》《来来往往》等揭示现代性精神困境的小说层出不穷。进入90年代,莫言、阎连科、陈忠实等作家的新历史主义小说创作从个人化的视角表现历史,用个人的生存欲、情欲、物欲阐释历史,人成为文学话题的中心。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市场的催化,私人化小说、网络文学、青春小说等个性化创作接连出现,元叙事、零度写作、身体写作等叙事方式令人应接不暇。小说创作不断追求新奇,急于求新求变,但整体上却不断衰落,其中所反映出来的创作困境与走出祛魅的后现代思潮紧密相关。
新时期生态文学揭示了祛魅背后工具理性、人类中心主义盛行的真相,看到了生态危机与人的精神危机、文化危机之间的联系。生态文学通过重新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力图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束缚,重建人们的生态良知。
(二)新时期以来生态小说的流行与复魅
马克斯·韦伯将理性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关注的是理性的功利化和实用化,价值理性则指向对人的命运、尊严和价值的关怀,其功能在于反思性、批判性和否定性[9]。生态小说的流行伴随着对工具理性的反拨,打破文学中的人类中心主义。随着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的不断发展,生态小说逐渐解构文学世界里的祛魅,使自然回归附魅的状态,从而为自然复魅。以贾平凹的《怀念狼》、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阿来的“山珍三部”(《三只虫草》《蘑菇圈》《河上柏影》)等为代表的生态小说将复魅作为叙述策略,塑造了万物有灵的文学生态,复魅后的大自然不再只是客观存在的环境,还是人的精神力量的反映。生态小说采取人与动物、植物共生共荣的叙事模式来反观人与自然的生存境况。在《怀念狼》中,狼被人格化,在真实与虚幻之间展现了商州地区人与狼相互斗争、相互依存的生存关系;《额尔古纳河右岸》中描写了鄂温克族的百年历史,通过对萨满、瘟疫、灾难等象征自然神性的神秘力量的渲染,重现少数民族原始的自然崇拜;在阿来的“山珍三部”中,藏族万物有灵的文化理念与现代物欲的贪婪形成鲜明对比,反映出人类中心主义带来的文化隔阂和精神危机。生态小说复魅的叙事方式是作家在文学世界对生态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工具理性对自然祛魅,科学技术成为人主宰世界的工具,以人类为中心来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文学的发展与社会的变化密切相关,生态小说中的复魅是文学对祛魅的反思,是为祛除人类中心主义开出的处方。
正如韦伯所言:“可见理智化和理性化的增进,并不意味着人对生存条件的一般知识也随之增加。”[10]随着理性对崇高与权威的消解,怀疑主义、价值虚无主义随之而来,现代人的精神世界和文化认同面临重构。现代社会的生态危机、信仰混乱激发了复魅的产生,无论是自然的复魅还是信仰的重建,都是人对祛魅的反拨。值得注意的是,复魅并不是重新寻找神灵的庇护或臣服于自然的怪力,而是改变祛魅造成的混乱状态,通过对敬畏自然、尊重生态的呼吁,为未来的社会发展和文化生活指明方向。
三、新时期以来生态小说复魅书写策略的反思
祛魅以工具理性为核心,改变了个体的思维模式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形成了一种主体与他者的关系[11],人是主体而自然是他者。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使人们反思人类中心主义,以生态小说为代表的文学艺术开始为自然复魅。复魅与返魅异曲同工,返魅来源于以格里芬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强调宇宙自然中存在价值、经验、目的、理性、创造性与神性[12]。新时期以来我国生态小说以复魅为叙事策略,通过文学的审美张力催发人们对现代生态危机的反思。
(一)反思现代性: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
我国传统文化历来重视人与自然关系和谐。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现代化、城市化节奏加快,生态问题日益突出。当代作家纷纷进军生态写作领域,如迟子建、张炜、贾平凹等在小说中重塑自然的神性、灵性,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姜戎、阿来、乌热尔图等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生态小说更是充满神秘色彩。生态小说的复魅主要体现在自然人格化、人物神灵化等方面,强调人与自然共生共存,表达了深切的生态关怀和人文反思。
首先,生态小说的复魅表现在自然的人格化。在迟子建笔下,自然万物皆有灵性,《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鄂温克族人对火种、山神、雷神、驯鹿等生灵充满崇拜,人们通过各种祭祀仪式表达对自然的敬畏。贾平凹在《怀念狼》中赋予动物说话的权利,狼作为正义的化身审判光棍、郭财、成义等人的罪恶,动物知恩图报的形象被刻画和强调:野狼衔金香玉报道士之恩,金丝猴变成女人向舅舅报恩。陈应松在《豹子最后的舞蹈》中从动物视角讲述了湖北神农架最后一只豹子的孤独,以寓言体的方式表达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复魅的生态小说以动物、植物的人格化为叙事逻辑,呼吁人们重视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
其次,生态写作通过人物的神灵化来实现对传统神秘力量的复魅。在迟子建作品中,《群山之巅》里的安雪儿身为侏儒却能预测占卜,《额尔古纳河右岸》中鄂温克族的保护神萨满妮浩拥有超人的神异力量,《候鸟的勇敢》中的张黑脸可以预知自然灾害的发生。生态小说中的边地系列更是通过对少数民族神秘仪式的描写来强化大自然的神性。如阿来《随风飘散》里的兔子火葬,杨志军《巴颜喀拉山的孩子》中人去世后的天葬等。
再次,生态小说复魅强调人与自然的共生。以《怀念狼》《狼孩》《狼图腾》为代表的狼文化小说打破了人类中心主义,体现出新的生态伦理关系,通过对人与狼密不可分及关系异化的书写,暗示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关系。《蘑菇圈》中斯炯的命运与蘑菇圈同频共振,《河上柏影》中柏树的生长、衰落与人物的命运、村庄的兴衰息息相关,人和自然荣辱与共。生态小说以复魅为写作策略,形成了对祛魅的反拨,以此来呼吁人们尊重自然万物,凸显生态文学反思现代性的立场和使命。
(二)批判人类中心主义:确认生态小说的复魅价值
主客体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在工具理性的烛照下泛滥,人类中心主义打破了人与自然的有机统一。现代工业的发展以生态失衡为代价,科学技术和工具理性的力量弱化了价值理性的意义和伦理道德的内涵,工业革命以来的现代性问题层出不穷。面对生态困境与文化塌方,新时期众多作家致力于生态写作。张炜认识到现代社会“对大自然的生物多样性不感兴趣也不关心,对文明的多样性更是缺乏耐心,结果导致世界的单调和沉闷”[13],他的生态小说对现代工业革命进行了深入反思,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分析鞭辟入里。《古船》描写了工业化对洼狸镇的冲击,实现机械化之后镇上的粉丝磨坊从兴盛走向了衰亡,现代化和工业化就如潜伏在村庄里的铅筒,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传统的生活方式、自然的生态环境、单纯的精神世界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张炜不像古人用古船“来抒写个人的羁旅哀愁、漂泊流浪与离怀别恨,而是用它来抒写民族和国家的苦难”[14],而是对现代工业文明进行严厉审视。阿来的《三只虫草》《蘑菇圈》《河上柏影》等作品则表现了现代消费社会对边地物产的大肆掠夺,现代人以自我为中心,为满足一己私欲疯狂垦殖土地、残忍猎杀野生动物,甚至连被封为“树神”的千年古柏都难逃此劫。莫言在《天下太平》中尖锐地批判了现代社会中人的主体性的膨胀:太平村村民袁武为一己私欲,将养猪场的废水直接排入原本清澈见底的大湾。《哦,我的可可西里》中的王勇刚为了发财,在可可西里疯狂开采金矿、猎取藏羚羊。在利益的驱动下,人们以自我为中心大肆开发利用自然,破坏了大自然原有的生态平衡。人类中心主义支配下的现代化不仅滋生了生态问题,更使得人类对自然的敬畏完全被解构。生态小说的复魅在揭示生态危机的同时,表达了对现代化的反思与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是人们对现代性的重新检视。
(三)辨析生态整体主义:正确看待生态小说的复魅书写
复魅书写使人们重新认识工业化,万物有灵等原始观念复归。部分生态小说为反拨现代性的祛魅,不可避免地走向对原始神话、宗教迷信、奇风异俗等神秘文化的认同。如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中为人送葬的狐狸、贾平凹《怀念狼》里幻化为女人的金丝猴以及郭雪波《银狐》中“白娘子”再世般的银狐等,均具有迷信色彩,这也是此类小说不可取之处。科学理性将人从宗教神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现代性的祛魅虽然带来了生态危机等问题,但正如韦伯对理性和人的价值的肯定,科学与祛魅的存在具有历史合理性,应当辩证看待,而非全盘抹杀。生态小说的复魅虽致力于构建人与自然的平等关系,力图探寻解决生态危机的文化途径,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必须重新返回过往时代对神秘力量的盲从。
正如王诺对生态文学的定义:“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的,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的文学。”[5]11生态作为一个有机的系统,包含了人与自然万物,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才是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最佳方式。现代工业文明唤醒了人们对生态危机的重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既要避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追捧,又要防止倒退到对自然之魅的盲目崇拜,而应牢牢把握生态整体主义,正确看待生态小说中的复魅书写。应该注意的是,尽管科学理性逐渐深入人心,但由于现代文化发展不平衡等因素,诸多愚昧、落后的顽疾并没有得到根除。由此,在警惕陷入现代性祛魅困境的同时,还要重视科学和理性启蒙不够彻底的现实问题,生态小说创作应立足于我国现实和历史语境,更加旗帜鲜明地揭示现代性危机,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及现代人的诗意栖居提供独特的视角和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