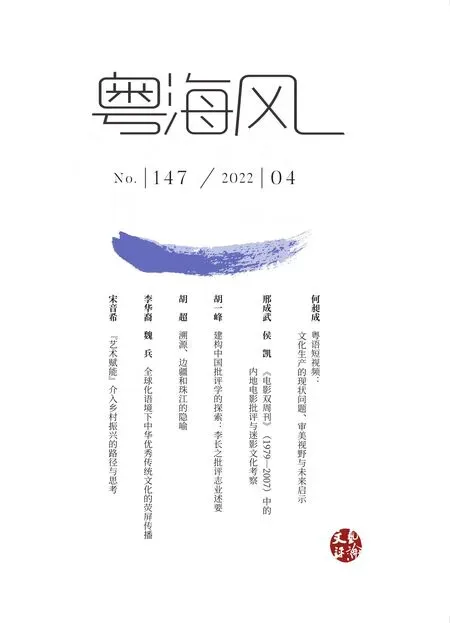粤语短视频:文化生产的现状问题、审美视野与未来启示
2022-11-24何昶成
文/何昶成
粤语短视频,是指以粤语作为创作载体或主要表现形式的短片视频。近年来,一些极具特色的地方语言如东北话、粤语、沪语等频繁地出现新媒体平台上,而由这些方言所延伸出的短视频影像也越来越受到观众的关注、讨论及使用。实质上,作为一定区域内集聚群体之间且相对小众的日常用语,方言更多承载为交流功能;而通过短视频创作,兼具生产与传播双向技能的创作者/观众们既享受着由方言带来的语义快感,同时也能借助方言将地方文化融合为影像资源,以此探索方言从私人语域到公共空间的传播可能,推动地域文化的沟通交流与传承发展。
作为推广、传播广府文化的重要载体,粤语短视频以多元的姿态、丰富的内容迅猛发展,并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体量;但深入来看,粤语短视频适用场景与影响范畴相对局限,其在艺术审美、文化传播等层面仍相对不足。为进一步推动广府文化传承发展,推动跨地域文化交流,丰富广府文化表现类型,提升粤语短视频创作艺术审美层次与文化传播能力,本文将从粤语短视频创作特点出发,探讨其现状问题、文化审美内涵及其未来的发展可能。
一、创作特点:多类型粤语短视频百花齐放
当下,粤语短视频创作内容丰富、形态多元,从类型上看,不仅有“闹腾男孩KC”、“粤知一二”等脱口秀类的短视频创作,也有“顺德美食”等探店美食类,当然还不乏有“亮声open”、“李泳希”、“许靖韵Angela”等才艺展示类;从功能上看,其类型涵盖有“罗记话安全”等新闻资讯类,“粤讲越好玩”“粤语一点通”等知识传播类,“郑建鹏&言真夫妇”“ON仔”等文化娱乐类,以及“伊利额”等生活服务类。概括来说,粤语短视频创作主要呈现为以下三方面的现状特征。
一是彰显文化特色。作为一种独特的语言短视频创作类型,粤语短视频融合了粤语与短视频的质素特征,借助于新媒体视听语言声情并茂地展现出独特的广府文化,这不论是站在粤语还是短视频创作层面来看都是极具特色的。特别是以“粤知一二”等为代表的脱口秀类粤语短视频创作,利用所处的广府文化优势,从垂直领域打造了一档接地气的短视频节目——由最初的单一口播新闻的样态逐渐转向到当下的小剧场模式,形成了独特的粤语单口喜剧。分饰多角的主持人郭嘉峰,给观众们带来恶搞、滑稽的口技演绎,其中题材内容更具地域文化特色,譬如由节气所蔓延的南北方争论等等,可以说是拉近了不同地域观众的文化距离,达到了文化传播的效果。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以“粤知一二”为代表的粤语短视频不仅满足了人们对于单口喜剧或情境喜剧的巨大需求,同时也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景观,即通过短片影像有效传播了广府文化。
二是浸润情感深处。粤语短视频创作题材内容与两广人民的日常生活紧密关联,而通过粤语来对地域生活进行策划与展示,在呈现独特魅力的同时也散发出审美的温情,似乎扮演着一位“熟悉的陌生人”,在耳濡目染中环抱着粤语区的观众们。譬如美食类的粤语短视频创作者“花师奶(吃货顺德)”,即是以“师奶”(广府地区对家庭主妇的称谓)作为名字,来进行美食制作分享,而其中所穿插的广府家庭故事,则大大增强了与观众们的习俗共情。
三是探寻创新可能。粤语短视频创作与时俱进,不断从新语境中寻求创作的可能性,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融合创新,尽管粤语短视频创作是以粤语作为母语来进行影像生产,但随着新媒体传播力和粤语影响力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非粤语区观众也开始接受并逐渐喜欢上这种短片内容,而有的创作者则开始融入普通话来进行共同生产,其中不乏有粤语教学、文化对照等影像类型,大大提升了非粤语区观众的接受度;另一方面是制作创新,较于最初以草根创作者为主的日常记录,当前有的粤语短视频创作已逐渐走向了专业化,特别是在MCN机构或专业技术团队的运营下,这部分的影像生产开始注重审美品质,提升表达水准,实现互动交流等,不断给观众带来新的感官体验。
二、困境问题:粤语短视频创作的多维度审视
从文化生产的角度来看,笔者认为,当前粤语短视频创作仍存在以下四方面的困境及问题。
一是定位固化,想象力相对不足。目前粤语短视频创作的定位大多数是以vlog、脱口秀、采访、新闻等为主,其中段子类短视频创作更为占据多数且有不断推陈出新。但整体来看,粤语短视频创作的定位仍相对固化,创作者们更多囿于成功经验,缺乏具有想象力的创作创新——尽管有其他的内容定位如纪录影像等崭露头角,但却未能更深入发展且形成创作习惯,创作者们更青睐于眼前的红利,急于求成的状态也使他们难以再去探索或深入其他的可能性定位,这也将导致当前粤语短视频给观众带来一种固化的印象,陷入只有段子文化的创作局限中。
二是选题局限,影响力相对不足。从粤语短视频创作题材来看,尽管近年来有较大的融合创新,但实质上仍处于围困状态。一方面,当前粤语短视频创作选题挖掘相对不多,更多是基于广府地区的生活文化来进行策划,其内容不乏饮食、音乐等题材,而实质上,粤语所承载的广府文化博大精深,诸如历史、地理等文化内容的挖掘,有的甚至在电视节目、纪录片、电影等经典影像中均有呈现,具有强大的文化性与感染力,这些都能作为短视频创作题材的重要来源;另一方面,当前粤语短视频创作选题挖掘不够深入,诸如有的新闻采访、文化现象、历史典故等选题仅停留在表面上,这就使得观众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其中所蕴含的更深入的内容尚待创作者们挖掘。
三是制作欠佳,审美力相对不足。在机构与专业化的共同运营下,短视频影像质量已获得了飞跃般的提升,但相对于电影、电视等传统影视,多数的粤语短视频制作水准仍相对不高,审美力相对不强。一方面,粤语短视频创作存在影像失真的问题,拼凑、拼贴现象时常出现,诸如加入其他影像、声效等对原生内容进行弥补,而其中关联度不大的内容则容易混淆视听,甚至会发生新的逻辑关系,譬如在某些粤语剧情短剧中,有的创作者则加入其他视频的爆笑声来增加气氛,但实质上却产生突兀的视听效果;另一方面,粤语短视频创作仍存有制作粗糙的问题,由于多数的粤语短视频创作仍处于快速探索阶段,加上有的制作人员未接受过专业训练,使得短视频创作呈现出质量不佳的情况,诸如镜头不稳、构图不协调、色彩平淡、声画不同步、配音生硬、环境简陋、表演生硬等问题,整体还缺乏打磨相对于较为成熟的“蜀中桃子姐”“李子柒”等方言短视频影像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四是宣推贫乏,传播力相对不足。尽管部分粤语短视频创作在宣传推广上呈现出了跨屏联动、多平台分发等特点,但从整体上看,其宣推的效果仍相对不佳,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粤语短视频创作的投放仍不够精准,当前粤语短视频创作覆盖面相对局限,尽管有的粤语表达能给非粤语区的观众带来一定的新鲜感,但存在文化差异的部分也会带来陌生化体验,诸如语义上的笑梗、美食上的甜咸等等,非粤语区的观众也许会难以理解和接受;二是粤语短视频创作的反馈机制不够成熟,尽管非粤语区的观众会对粤语影像内容产生兴趣,但由于语言、文化等差异性问题,当前粤语短视频创作仍未能激发更多话题性的探讨,缺乏与观众的良好互动,而由此局限所形成的单向传播,则难以推动再创作创新、进行更广泛地传播。
三、审美视野:粤语短视频创作的文化记忆
粤语短视频的创作基础离不开流传于广府地区的粤语符号,而这些平实生动且富有韵律美感的语言内容,深受广府地区的文化滋养。可以说,这些历经时代岁月的民间语言,凝结了广府人的生活习俗与乡土情结,是粤语短视频创作中不可或缺的文化记忆。
(一)多元粤语文化的符号呈现
粤语方言历史悠久,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而其所生成或延伸出的文化符号包括粤语童谣/粤曲/粤语歌、歇后语/俚语、粤剧/粤语片等等。
粤语童谣/粤曲/粤语歌是以音乐为媒的粤语文化,可统称为粤乐。其中粤语童谣属吟唱性的民间文化艺术,人们耳熟能详的包括《月光光》《落雨大》《鸡公仔》等,而与其他童谣不同的是,“问字攞腔”式的表达方式使得同一首粤语童谣有着众多的版本[1],并根据地域和创造时期出现语言或情感的变化,其中词语、语调等也有所变迁,诸如收录于《广州民间歌谣》中的童谣,《氹氹转(团团转)》有 9 个版本、《打掌仔(打手掌)》有 7 个版本、《排排坐》有 6 个版本等等。粤曲则属于歌唱性的粤语文化,粤曲是粤语方言区广为流行的曲艺形式,有着一百八十多年的发展历史,形成由曲牌体、梆子腔、二黄腔和歌谣体四大部分组成的音乐体[2],经典曲目包括《百里奚会妻》《黛玉葬花》《弃楚归汉》等等。粤语歌也属于歌唱性的粤语文化,初期粤语歌曲创作是从广东小曲发展而来,粤语歌的繁荣则还得回溯到香港流行乐坛的发迹,如《海阔天空》(Beyond)、《迟来的春天》(谭咏麟)、《Monica》(张国荣)、《偏偏喜欢你》(陈百强)、《千千阙歌》(陈慧娴)、《月半小夜曲》(李克勤)等歌手的经典粤语歌曲作品仍为当下大众所传唱。
粤语歇后语/俚语可以说是一种在生活实践中凝结的文化符号。在粤语歇后语中,不论是由外来文化所形成的“番鬼佬月饼——闷极”,还是基于祭祀、庙会文化所形成的“年三十晚谢灶——好做唔做”,又或是源于饮食文化中所生成的“番薯跌落灶——该烩(煨)”等,都是广府人在长期的生活体验和不断增加的认知经历中总结而成;而从工作、生活日常中所延伸的“煲电话粥”“炖冬菇”“炒鱿鱼”“菠萝鸡”“冻过水”“撑抬脚”等等粤语俚语,更是作为广府人交流的语言习惯,其中蕴含深厚地域和民族文化。
粤剧/粤语片则是以一种综合艺术的形式所形成的独特的文化符号。粤剧是指广东地区以粤语为语言媒介的戏剧形式,在民国前被称为“广府大戏”,在经历时代磨合后逐渐形成当下的艺术形态,经典的粤剧包括《祭玉河》《锦江诗侣》《客途秋恨》《帝女花》等,而粤剧与上文所谈及到的粤乐(粤曲、粤语歌等)有着紧密的联系,二者间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粤语片是指以粤语发音的影像内容,其中经典作品包括粤语电视剧《七十二家房客》《外来媳妇本地郎》等和粤语电影《英雄本色》《秋天的童话》《大话西游》《无间道》《叶问》等等,不同类型的影视作品更是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独特粤语文化符号。
(二)文化记忆的审美路径与影像书写
可以说,粤语短视频正是以粤乐、粤语歇后语/俚语、粤剧/粤语片等文化符号为基础,通过熟识的文字、音色、节奏等不断地呼唤着广府人内心深处的文化记忆,并由这种情感认同营造出一种共同体美学,从而实现粤语短视频的圈层生产与破圈传播。
结合艺术创作的角度来看,粤语短视频的影像书写,首先是文化体验的发生。粤语短视频创作源自于创作者对文化记忆的感通,这就需要从粤语的口传历史中探索文化质素,当然也包括在粤乐、粤语歇后语/俚语、粤剧/粤语片等文化符号的审视中挖掘其形式美、内容美、意境美,以此生成对粤语文化的理解及认同。
第二是创作构思的碰撞。当获得了一定的审美储备,由地域所形成的文化差异以及个人记忆深处的文化基因则开始发生碰撞,观念与情感在较量中“跃跃欲试”。一方面是文化记忆形成了强烈的观念认同,这主要表现在南北地区所形成的文化差异中,其内容涵盖节气习俗、饮食习惯等方面,是观念表达的主要范畴;另一方面则是由文化记忆所形成的情感力量,这主要表现为创伤性文化情感和稳固性文化情感,而短视频创作则不会涵盖过多悲伤欲绝的内容,但一些来自于粤语家庭的“谩骂式”称谓却成为创伤性文化情感的主要来源,诸如“衰仔”“叉烧”等称呼,往往是一种既亲密又带有恨铁不成钢的代际表达,而稳固性文化情感则是由地点、物体等产生的情感支撑,结合皮埃尔·诺拉所提出“记忆之场”来看,诸如粤语地区的骑楼、喝茶、舞狮等固有的文化内容,为创作者营造了熟悉的情感场域,从而激发情感的宣泄。
第三是审美影像的形成。植根于文化记忆深处的影像生成涵盖着知识内容的呈现、观念习俗的彰显以及情感记忆的表达。诚如扬·阿斯曼所言,“文化记忆包括了一个社会或一个时代不可或缺的表现为文本、图画和仪式的知识体系”[3],知识内容作为文化记忆所形成的一种范式体系,在粤语短视频创作中较为丰富,其中包涵对粤语地区生活常识、文化知识的普及,具体见于“如何快速融入广东”“广东啥都吃吗”等话题表达当中;观念习俗则是文化记忆所形成的一种风格惯性,在短视频创作中更多呈现于对非粤语或广东以外地区的风俗人情、生活习惯等进行对比,如“广东人怎么买菜”“广东的压岁钱”等话题的影像创作;情感记忆则是来自于文化记忆中的感性力量,情感的张力涵盖着对粤语文化及其所形成的文化符号的体认,具体的表达则可以是对经典戏剧、影视作品的剪辑等等。
由粤语所凝聚的广府文化记忆,为短视频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审美质素;而创作者们正是通过文化记忆深处中的观念认同与情感力量,将粤语文化从口述历史延伸至影像艺术中,形成新美学符号予以呈现。
四、未来展望:粤语短视频创作的创新思考
粤语文化传承的路很长,如何继承与创新,如何培育粤语文化认同,如何切实地进行粤语文化的生产传播等等,都需要我们不断探索与实践。当下,粤语短视频的快速发展,为广府文化从粤港澳大湾区走向全国乃至全球提供了主流渠道和快捷方式,而创新则是推动文化发展的主要动力。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笔者认为,粤语短视频创作应注重以下四个方面的创新思考。
一是更精准化的定位。粤语短视频创作从最初的用户vlog开始,到当下脱口秀、采访、新闻等类别内容的层见叠出,可以说,正是技术与时代的发展赋予了粤语短视频创作无限可能。但从整体来看,当前大多数的粤语短视频创作仍处于扁平的、广撒网式的探索状态,而垂直的、有深度性的短视频创作仍相对较少,当然,处于探索状态的粤语短视频内容也许会产生一定的关注与流量,但这种状态却常以昙花一现而告终,散兵游勇式的创作且很难产生深远的影响力。因此,从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未来粤语短视频创作还需回归本体进行精准定位,譬如要计划做什么类别的粤语短视频?怎么去做?做成什么样?等等,同时还需立足于文化本身,以此打造独特的文化影像符号。
二是更多元化的选题。选题的纠葛将限制影像的创新表达,多元化的选题则有助于挖掘粤语影像的无限可能。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粤语短视频创作者应合理利用丰富的广府文化资源,从中探索选题的可能性。一方面是传承,即创作者可基于某些已具备现象级影响力或具备一定潜质的选题中继续深入,譬如在某些影响力较大的新闻采访中继续深入,做深度采访;另一方面是创新,创作选题不能以流量为标准,在原有选题基础上继续深入的同时也要注重选题创新,譬如可以从历史文化、好人好事、习俗风俗等方面建构新的文化选题,并以此引导更多观众接受,传播正能量,生成正向价值观等。
三是更规范化的制作。尽管当前有部分粤语短视频在MCN公司、专业化团队的运营下,其创作质量、内容呈现等方面都接近于传统电影、电视的标准,但多数粤语短视频仍是以直接、简单的制作方式为主,其质量短板较为凸显,且难以满足观众愈来愈高的审美要求。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更为规范化的制作需求呼之欲出——一是组建团队,即建立专业化的制作团队,从策划、拍摄、后期等方面建立较为标准的创作流程;二是规范管理,即建立管理标准,整治抄袭、挪用等失德乱象;三是注重审美,在规范化制作的基础上,要注重美的探索与美的塑造,破除短平快语境下唯审丑、唯恶搞的内容呈现。
四是更联动化的宣推。由于语言及地域文化屏障,当前粤语短视频创作在宣传和推广方面仍相对较弱,难以与内容生产形成再生产的回馈机制。于此,面向粤语短视频创作的发展未来,笔者认为仍需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开展宣推。一是借助优质媒体,形成多渠道创传矩阵,当前,诸如“粤知一二”等粤语短视频在抖音、微信等平台进行了较好的推广,这种媒体联动的方式值得借鉴效仿,利用多媒体拥有不同用户群体的优势来进行多角度传播,有助于提升传播力,增加关注度和反馈度,以此推动更多热门话题的内容生产;二是创造条件机会,探寻多元合作可能,诸如可加强政企合作、校企合作,开创粤语短视频创作竞赛、设立相关奖项等等,由此激发创作创新活力,推动粤语短视频影像传播;三是打造热点话题,寻求价值认同,诸如可借鉴“大唐不夜城”等宣推形式,借助热门话题或设定话题来进行对粤语短视频创作的引导,这不仅有助于吸引更多短视频创作者进行影像生产,同时也能有效推动粤语文化传播。
列夫·曼诺维奇(Lev Manovich,L)在《新媒体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New Media)中谈到自小说之后影视成为当下文化表达的主要方式,还指出网络时代下的新媒体文化是以更小的单位进行任意组合、解构、提取[4],而短视频恰是当前影视表达的一种新媒体方式,通过碎片化的方式来书写创作者的文化记忆。作为方言短视频的显著代表,粤语短视频以多元的姿态,给观众带来了丰富的文化意味与强烈的审美乐趣。诚然,粤语短视频创作不仅承担文化娱乐功能,同时也是广府文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在发展中面临着诸多问题与挑战,仍需不断改良、探索与完善。面向未来,如何通过粤语短视频创作来推动广府文化的传承创新与“走出去”,仍是值得我们继续深入思考和探索的话题。
注释:
[1]曾应枫:《广府文化记忆中的民间吟唱——论粤语童谣的传承与发展》,《探求》,2018年,第5期。
[2]李日星:《粤曲的历史与艺术文化品格》,《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3]金寿福:《扬·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外国语文》,2017年,第2期。
[4]Lev Manovich,L :The Language of New Media,MIT press,2001,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