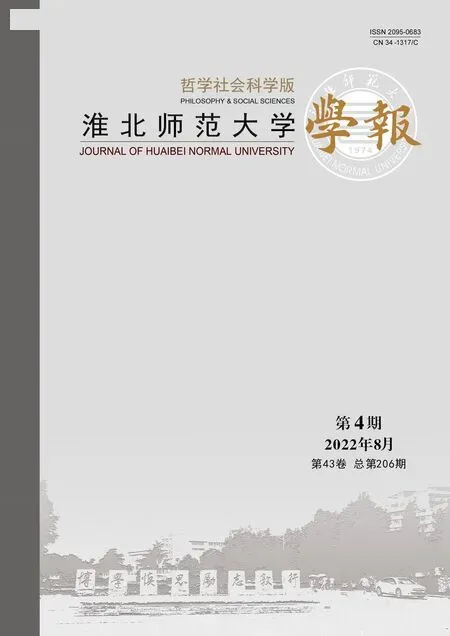伦理学视域中研究生和导师关系的重构
2022-11-24孙艺铭
孙艺铭
(安庆师范大学 音乐学院,安徽 安庆 246011)
正如哲学家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所言,大学存在的理由在于:它联合青年人和老年人共同对学问进行富有想象的研究,以保持知识和火热的生活之间的联系。大学是一个充满文生情调的意义之域,大学师生关系应当体现伦理的精神。然而近些年来,大学师生关系已出现种种不良现象,这已招致社会的广泛诟病,更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忧思。研究生作为大学校园的特殊群体,他们和导师间的关系不仅具有大学师生关系的一般共性,而且其异化程度、异化形式均有自身的特点。然而,已有的研究鲜有能聚焦于差异性对研究生和导师间的关系进行专门研究。另一方面,伦理是教育的本质属性,教育本身就应当是伦理性的。伦理意识的淡薄意味着教育失去它的本质规定性。同样,伦理是研究生和导师关系重构的一个重要向度。
一、从传统到现代:研究生和导师关系的嬗变
当前,随着大学外部环境及其自身的变化,与我国古代大学进行纵向比较,我国研究生与导师关系正发生着重大的嬗变。这种嬗变虽然使师生关系多了一些民主、平等、自由等时代特征,但却也带来一些消极作用。
(一)从“向善”转向“功利”
我国传统社会中的师生关系有着鲜明的伦理意蕴。在倡导“师道尊严”的传统社会中,学生对教师“事师若父”。“师”是社会伦理意义上的“父”。汉代马融曰:“先生谓父兄”,传统社会中,学生不仅日常饮食起居方面,待老师要像侍奉父亲一样,事无巨细,无怨无悔,而且弟子的“事师若父”还体现在老师的丧礼上。孔子弟子为孔子守丧三年,而子贡守墓六年。另一方面,传统社会中,老师对弟子也同样有着“视如父子”般的父爱情怀。譬如,《论语·先进》:颜渊去世,孔子“哭之恸”。这可谓是传统社会师生关系的典范。传统社会中的师生关系之所以充盈着伦理意蕴。《大学》开宗明义地指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对于“至善”,《大学》解释:“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意即每个人如果能尽到自己的伦理义务,这就是“至善”。“学界多用‘以道相交’‘感情笃厚’‘以爱相济’‘互相砥砺’等词汇诠释传统书院师生关系的特质。”[1]我国传统书院之所以有这样优良的师生关系,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师生之间双向选择,“以道相交”。对于书院中的教师而言,山长在招生环节拥有一定的话语权,“道相同,方为谋”,他们择生的主要依据是生徒的举业潜力、治学能力,以及道德志向;对于学生而言,“求道而聚合”,他们选择书院主要是依据书院能否提供道德、学术上的优良资源。除了入学环节,传统书院中的师生关系主要是依托在考课、讲学、交游酬唱等教学环节,师生双方都本着至善追求,进行情感上的充分互动。
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制度虽然直到民国时期才真正成型,但它深深扎根于我国传统教育的土壤中,在最初发展阶段仍能固守我国大学教育的“向善”传统。研究生和导师之间,以道义和学问相期许、相砥砺,形成了一个美善相偕的“道义共同体”,留下许多佳话。而当前,我国大学逐渐遗忘了其“向善”初心,日渐呈现功利化倾向。在此整体背景下,研究生与导师间的关系也较为普遍地由“向善”转向“功利主义”。这通常有以下典型表现:第一,论文发表与课题申报等学术成果成了研究生与导师合作的主要目标,甚至成为唯一的追求。功利化的师生关系使师生由“道义共同体”蜕变为“利益共同体”,因而严重偏离了大学的“向善”传统。第二,因研究生与导师的关系建立在“功利”而非“善性”的基础上,又由于导师在学术水平及学术资源上的强势地位,研究生通常受导师操控,导师辱骂、“奴役”、性骚扰学生等现象近年来频频曝光。第三,随着近些年来的研究生扩招,特别是自2009年我国专业硕士研究生项目扩招以来,研究生生源质量良莠不齐,有不少学生(特别是专业硕士)的学术基础相当薄弱,他们难以和导师合作取得学术成果。出于功利的计算,一些导师对待这些研究生消极、冷漠,仅仅完成毕业论文指导等基本的指导任务。
(二)从“亲密”转向“疏离”
古代大学中,师生间形成了亲密、友爱的师生关系。当代大学中,师生关系主要以功利和契约为基础。功利只能带来师生间短暂的、形式上的亲密,而非长久的、实质的亲密。正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师生间交往的基础如果仅是功利,那么功利一旦不在,师生间就缺少长久交往的必要性;师生间交往的基础如果仅是功利,那么这种“亲密”仅是形式上的,它不是源于因向往教师学识和德行而产生的真正的、内在的亲密。契约也可能导致使师生关系由“亲密”向“疏离”的嬗变。卢梭在《爱弥儿》中批评教育契约时指出:“……一旦他们觉察到他们以后会分离,一旦他们预见到他们有彼此成为陌路人的一天,他们就已经成为陌路人了。每个人都建立了自己小小的隔离体系;两个人一心想着将来不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只是勉强待在一起。”[2]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曾将人际关系分为三种类型:偶遇、相处、相依。[3]在偶遇(being-aside)的关系中,双方如同陌生人一样偶然相逢,双方见到的都是对方的一个碎片,多数偶遇没有过去和将来,也不产生结果。相处(being-with)是一个话题式的关系,双方的相关性由话题赋予,而且通常是,手头的话题和限于此时此地的“专门”的兴趣,产生和限制着这种相关性。主题性的限制性影响使双方不愿意在相处中展开超过话题的内容。因此,在相处的关系中,双方虽然相互注意,但仍然是不完全的自我的一场相会。事实上,当前研究生和导师之间更多的是“偶遇和相处”的疏离关系。研究生和导师不熟悉对方的过去,不关心对方的未来;双方交谈的主题通常局限在论文发表等有限的学业领域,超出学业领域的任何话题或被导师认为并非自己职责,或被研究生认为是导师的“越权”,或“别有用心”。
(三)从“平等中的敬畏”转向“无敬畏的平等”
古代大学中,师生间是一种平等的师生关系,但这种平等又蕴含学生对教师的敬畏。教师之所以值得学生敬畏,在于他的道德和学问,以及让学生既爱又惧的人格魅力。在孔子的教育世界里,孔子是温和的,他坚信学生都是有着向善之心的平等主体;同时,孔子又凭借其道德、学问以及人格的力量使学生对其怀有深深的敬畏之情,“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论语·述而》)另一方面,学生需要敬畏教师,是因为他虽有向善之心,但他必须在教师的导引下才能由可能变成现实。而当代大学中,师生间通常是建立在欲望和契约基础上的缺失教育性的“平等”关系。这正如柏拉图所批评的那样:“教师害怕学生,迎合学生,学生反而漠视教师和保育员。普遍地年轻人充老资格,分庭抗礼,侃侃而谈,而老一辈的则顺着年轻人,说说笑笑,态度谦和,像年轻人一样行事,担心被他们认为可恨可怕……同样,驴马也惯于十分自由地在大街上到处撞人,如果你碰上它们而不让路的话。什么东西都充满了自由精神。”[4]研究生和导师在人格尊严、价值观念等方面虽然处于平等的地位,但建立在功利和契约基础上的平等实质上消弭了研究生对导师应有的敬畏;一些导师放任这种“形式上的平等”,而未能将师生间的平等建立于道义和学问的相互砥砺上,并且通过道德、学问的日益增进,以及人格的力量赢得研究生的敬畏。
二、传统与现代的融合:研究生和导师关系重构的基本向度
传统与现代的融合是社会发展伦理的基本要求和发展趋势。大学中,研究生与导师间的关系虽然有自己的特殊性,但大学毕竟不是“象牙塔”,它在某种程度上也一定要顺应社会伦理发展的总体趋势,也要遵循传统与现代融合这一基本向度。
(一)传统向度:复归传统伦理的“情谊之理”
诚如牟宗三所言:“陈迹不可为统,意义乃可为统。”[5]对传统伦理精粹的继承和弘扬并非是照搬其固定做法,而是要把握住其“真精神”。我国传统的儒家伦理即“情义之理”。梁漱溟对此指出:“伦理关系,即是情谊关系,亦即是其相互间的一种义务关系。伦理之‘理’,盖即于此情与义上见之。”[6]传统儒家伦理中的“五伦”均体现着一方对另一方的“情感义务”。传统社会,以父子伦理来类比师生伦理,即教师要爱生,甚至要达到视生如子;学生要尊师,甚至“事师之犹事父”。“爱生”和“尊师”是师生双方“绝对的责任”。以传统伦理观之,当前研究生与导师间关系的重构也需要师生“重情”,即重视自己对对方的情感义务,而不是单方面的“讲理”。首先,导师对研究生要真正地关爱,关注学生的过去、当下及未来;不仅学生的学业,而且学生的交友、恋爱、家庭及未来职业选择等,都与导师的心紧密相关;导师与研究生并非仅是由话题而引起的“相处”关系,而应当是类似于家庭成员的“相依”关系。其次,研究生对待导师虽然不能完全因袭“事师之犹事父”的传统做法,但仍然要将“尊师”视为自己的责任。不能因为导师学术水平及职称的高低、学术资源占有的多少,以及有无“官衔”等有所区别;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自觉自愿地协助导师处理教学、科研甚至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事情等等。传统“情谊之理”的复归,并非必定导致学生独立人格的丧失及合法权益的损害,相反,双方对自己情感义务的自觉履行,可以为师生关系的优化构建一个良性互动机制。
(二)现代向度:彰显现代伦理“平等的自由精神”
现代伦理以“平等的自由”作为其伦理精神的核心——“社会正义唯一被规定为公民平等的基本自由权力,公民间没有任何特权、身份、价值上的优先性。”[7]因此,研究生与导师关系重建的现代向度也必须彰显“平等的自由精神”。具体而言,首先,研究生与导师都是平等的公民主体,都是权利与义务相对等的复合体。导师和研究生双方在行使权利的时候,都必须恪守权利的边界,遵循权利的法律和制度依据,而不能将权利当作谋取私利的手段。其次,研究生与导师都是平等的价值主体。由于年龄、性别、经历、学术水平、所处环境等方面存在的差异,研究生和导师之间的价值冲突广泛存在于学业指导、未来职业规划、日常交往等多个方面,并且有时会达到尖锐的程度。导师应当承认、尊重研究生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自觉防范自己对研究生的诸种精神操控。再次,导师要通过和研究生的“商谈”,积极进行价值阐释和引导。因为,真正的自由需要把握人、自然、社会的各种规律,需要摆脱来自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种种束缚。当前,一方面,研究生一般而言较之本科生面临更多的选择自由。他们会有更高的进一步深造平台,但同时也面临更大的经济和恋爱婚姻压力;当被导师凌辱、奴役、学术成果侵占,甚至是性骚扰时,他们可以选择沉默,也可以选择以不同的形式反抗;既可以选择坚守学术良知,也可以为了功利的目的,选择急功近利,甚至不择手段……但另一方面,在价值多元甚至是价值无序的当今时代,人们往往容易陷入价值选择的迷茫。又由于年龄、学识和阅历的因素,研究生较之本科生个性倾向“定型化”程度较高,在思想观念上也容易陷入自我而浑然不觉。因此,导师更应当通过商谈和积极对话,引导研究生们在选择时如何坚守学术良知以及道德立场;如何以一个积极公民的姿态,捍卫个人及他人的合法权益;如何摆脱主观的任意和偏好,在尊重规律的基础上,对学业、生活等进行理性的权衡和选择。
在传统社会,教师虽然对学生“视如父子”,但往往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学生身上;而在现代社会,导师除了要充分借鉴传统社会“视如父子”所体现的对学生的关爱精神,还要和研究生进行商谈和价值引导。这种“平等的自由”是授业与受业的知性氛围中共享的自由,它又是知性的、导引的、对话性的、启发性的、富有教育意义的,因此也是真正的自由。另一方面,导师和研究生间的积极商谈和孜孜不倦的价值引导也正是导师将研究生“视如己出”的体现,这即传统伦理和现代伦理的充分融合。
三、伦理自觉与制度优化:研究生与导师关系重构的基本路径
研究生与导师关系的重构是一个社会、大学、研究生、导师等多方协作、良性互动的过程。为此,利益相关方必须探索研究生与导师关系重构的立体路径。
(一)主体自觉:导师伦理自觉的提升
1.心上体会,加强省察克治
明代哲学家王阳明在《传习录》中指出,“心上体会”,也就是“在思虑萌动处,省察克治”。“心上体会”首先强调通过内省,寻找每个“思虑”的深层根源。王阳明的这一主张对导师伦理自觉大有裨益。譬如,研究生违背导师意愿时,导师需要反思的是自己为何要强迫学生接受自己的意见?是为了维护自己的个人权威、个人利益,还是真心为了学生的进步着想?有无站在学生的立场去思考问题?对于学术基础薄弱、学术发展空间不大的研究生,除了认真指导其学业之外,还有哪些指导职责?如此等等。“心上体会”其次强调的是通过道德理性和道德意志的作用,抑制“恶情”的泛滥,以及“恶念”向“恶行”的转变。因为,较之本科生而言,研究生与导师接触的时间更为频繁,个别接触的时间更多,空间更为自由;研究生可与导师进行“交易”的方面更多;再加上当前研究生培养模式及管理制度等存在的疏漏,导师更多的是需要“慎独”和道德自制。
2.“爱的斗争”
王阳明极为重视“事上磨炼”,王阳明的思想是心物一体,即格物致良知。所以,无论是“心上体验”还是“事上磨练”,都是包含对象性的结构一体,主张在不厌外物的前提下,复于静处涵养。同样,在诸种影响因素的影响下,导师在和研究生的交往中,有时体验的不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孟子)的职业快乐,相反是很多的忧烦和无奈,甚至还面临着种种因诱惑而带来的道德风险。但导师绝不能厌弃这些“外物”,相反,只有在复杂的研究生培养实践中,才能真正提升自己的学术水平和道德修养。
面对研究生和导师间关系的冷漠和疏离,导师要如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所倡导的那样,积极进行“爱的斗争”。首先,导师需要深刻体认“责任”的伦理意蕴。这实质上是与自己道德上的有限性做斗争。康德曾将爱区分为“病理型的爱”和“实践的爱”。前者是基于本能需要及感官愉悦需求满足的爱,没有道德的意蕴;而后者是出于责任的爱,是有道德内涵的爱。无论研究生的外表、个性等外在因素是否能引起人感官上的愉悦,导师都要出于责任,给予其“视如父子”般的爱。其次,导师要通过说理、以身示范等多种方式积极引导学生,使其继承传统优良的学统及尊师传统。这实质上是与学生作“斗争”。除此之外,从“视如己出”的伦理观念出发,学术是导师和研究生的重要话题,但不应当是全部话题。导师还要深入到研究生的生活世界,展开指向生存的实践,特别是共同经历一些“临界体验”(如灾难,疾病等)。惟有此,研究生和导师才能逐渐建立起“相依”的生存关系。
3.书上考究,汲取伦理智慧
王阳明还特别强调“书上考究”,也即通过一些圣贤之书,来发明心中之理,作为“致良知”工夫中的重要环节。同样,导师应当自觉摒弃专业的局限性,从人文社会科学中广泛汲取伦理素养。譬如,“未经省察的生活不值得过”(苏格拉底)、“合乎德性的思辨生活是最幸福的生活”(亚里士多德)这些伦理思想虽然没有实际功用,但它们是“无用之大用”,它们对个体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建构起着深层的支撑作用。又如,当代德国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在其商谈伦理学中认为,“人们进行话语商谈的前提条件在于人们有着进行话语商谈的语言资质和道德资质。”[8]语言资质指的是运用语言正确表达自己思想或意向并被听众理解的能力,即语言具有“可理解性”;而道德资质指的是语言要有“真实性”(客观反映外部世界)、“真诚性”(真实反映内部心理世界)、合规范性(语言具有教育性)。当前,导师需要和研究生进行积极的商谈和价值引导,它同样需要导师的语言资质和道德资质。因此,商谈伦理可以为导师提供有益的伦理智慧。
(二)环境优化:制度伦理的系统设计
“‘制度伦理’就是指社会制度的合乎伦理性。”[9]230“制度伦理既包括对制度主体的伦理规定,也包括对道德规范体系和运行机制的合理安排;既包括对制度本身的合理秩序的探求,也包括对制度运行中一系列环节的道德评判和价值判断。”[9]231因制度伦理所具有的规范、导引和激励功能,研究生和导师关系的重构还要着力于制度伦理的系统设计。
1.学校中的平等公民:提升制度设计程序和运行的伦理性
在以“平等的自由精神”为现代伦理精神核心的当今时代,制度设计通常是众多利益相关者平等参与、重叠共识的过程。这即程序正义,是制度伦理在程序上的伦理要求。现代大学要赋予研究生真实的公民身份,平等地参与学校公共生活。而在实然状况上,研究生在学校的制度设计和制度运行过程中通常处于边缘化和缺场的状态。譬如,在导师分配上,虽然也有不少学校实行“双向选择”制度,但具体如何双选则由校方制订,而且其中有时有暗箱操作的成份。在研究生开题答辩、论文预答辩及论文终期答辩等研究生培养环节,论文评价的权力被导师及导师组垄断,研究生即使能参与其中,他们仅能当听众。在研究生综合测评活动中,虽有不少学校也在制度上规定了包括思想道德素质、学业成绩等多元化的评价内容,以及包括导师组、研究生代表等多元的评价主体,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除学业成绩外的很多评价内容都处于形式化的状态,评价的主体也通常局限于学院领导和导师,研究生本人难以公平、充分地参与其中。
2.促进“相遇”:提升制度设计内容的伦理性
大学的制度设计既要讲“理”,即体现权利和义务上的公平、正义。但基于理性(主要是工具理性)的制度设计只能使人处于“原子式”的存在状态,而不是伦理式的存在。因此,大学的制度设计又要讲“情”,使制度充盈伦理的内涵,并且情理交融。为了促进研究生和导师关系的重构,当前可以着力于以下的制度设计。
首先,通过制度设计促进研究生和导师的“相遇”。犹太裔法国哲学家埃曼纽尔·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的“他者”伦理指出,相遇是伦理的起点,没有相遇就没有伦理。“当我面对他者时,我与他是脸对脸、面对面;面孔对面孔是一种交流,而且是一个双向交流的过程;他人的存在以面孔显示,面孔的在场就预示着他人无法被我占有;他人的面孔一直在抵制我的占有企图,突破我的同一化;我注视着他人之‘面孔’,不仅仅是一种‘注视’,也是对他人的‘回应’;对他人之‘面孔’的‘回应’具有原初的伦理性。”[10]为了促进研究生和导师的相遇,学校应当不断丰富和完善研究生教育和管理的制度体系。譬如,建立相关制度,规定由学院领导或学位点负责人定期召集导师组会议,交流汇报研究生的经历、学习及生活状况,以及职业发展规划;通过制度明确导师约谈、研究生参加学术会议、导师参加研究生团体活动(包括学术活动和文体活动等)等活动的时间、次数及具体要求。这些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导师和研究生的联系。其次,建立和完善防范与问责制度。当前,不少大学导师评价制度在评价内容上较为褊狭,仅关注导师对研究生的学业指导;在评价主体上比较单一,通常由学院领导、学位点负责人、导师组作为评价主体,研究生很少有机会对导师进行公正评价;在评价类型上比较单一,仅有终结性评价,而很少有形成性评价。这些制度都不利于积极防范导师的道德风险,也难以对导师的过错进行及时问责。因此,大学导师评价制度应包括德、能、勤、绩、廉多元内容;可以由学院领导、学位点负责人、研究生教学秘书、研究生辅导员、研究生代表组成导师多元评价主体的评价小组;不仅注重终结性评价,更要注重形成性评价的次数和实效,从而对导师的过错及时问责,并发现潜在的问题,积极防范。以上制度的实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导师能及时发现和改正错误,从而更好地和研究生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