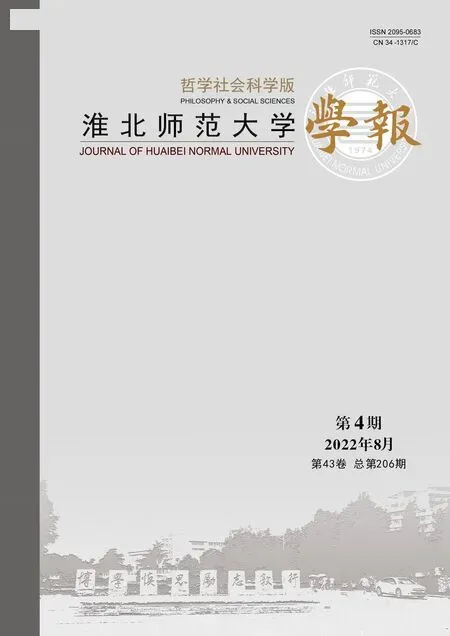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反巫神运动的历时性考察
2022-11-24吴承望
吴承望,魏 苗
(1.华中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2.武汉华夏理工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223)
抗战爆发以后,中国共产党为了打造稳固的抗日根据地,实现更大程度上的社会动员,不得不对乡村社会加以改造。巫神作为旧社会的荼毒,长期以来受到陕北民间的崇拜,他们攫取了边区社会的大量财富,威胁着边区政权的稳定,是乡村社会的“寄生虫”,也是中国共产党开展乡村社会改造和社会动员的“绊脚石”。因此,为了扭转乡村社会的风气,争取社会民心,将群众更好地组织起来,反对和改造巫神必然成为中国共产党逐步面对的问题。
以往对于巫神的研究重点集中于以下两点内容:一是探究巫神角色的归属问题。如王建华认为巫神就是二流子的一种,反巫神运动与改造二流子运动具有内在的一致性。[1]除了将巫神视为二流子以外,温金童认为巫神分为懂一定医术的巫医,和完全不懂的巫神。[2]二是关于反巫神运动的过程与作用研究。李旭东从社会控制这一视角出发,认为中国共产党从社会舆论、医疗和强力三个方面对巫神展开围剿,扭转了边区社会的迷信风气,强化了边区对乡村的社会控制。[3]李瑞芳从无神论教育和医疗卫生观念的变革入手,认为边区反巫神运动在预防为主思想和群众性卫生运动的广泛开展之下,实现了医疗卫生观念的变革。[4]总体来看,目前对于反巫神运动的研究取得了较为可观的成果,多集中于反巫神运动兴起的原因及运动后所产生的影响,但对反巫神运动展开历史性脉络的梳理少有论及。因此,笔者在前人的基础上,以《解放日报》为主要资料来源,试图以长时段的历史视野,系统回顾边区反巫神运动兴起的历史过程,力图丰富和补充此项研究。
一、萌芽初显:大生产运动的兴起与反巫神运动的发轫
抗战初期,为了获取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中国共产党并未将发展的中心置于边区生产上,更多考虑的是从国民党方面争取外援,所以边区财政收入起初格外依赖外援。然而,伴随着国共关系的日益紧张,国民党于1939 年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对边区展开了经济封锁,外援由此基本断绝。此外,由于陕甘宁地区本身的粮食负载能力极为有限,无法承载如此众多的人口,所以外援断绝以后,如何走出财政的困境成为当时边区党和政府所面临的重要问题。面对这样的严峻形势,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经济自给动员大会上强调:“我们遇到了抗战以来空前的困难,要求我们用自己的力量摆脱一切的困难与压迫”。[5]毛泽东在1939年延安干部生产动员大会上更是尖锐地指出:“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呢”。[6]所以他向全边区的党政军各级组织发出了“自己动手”的号召,部队实行大规模的屯田生产,党政军民也由此开始了大规模的大生产运动。
边区大生产运动的兴起,要求将整个边区的社会力量都组织动员起来,处于乡村社会边缘的巫神也不可避免。因而,反巫神运动发轫于大生产运动,并在整个大生产运动背景之下不断得以推进。其一,大生产运动不断塑造着农民积极进步的思想观念。马克思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即只要改变人们的社会存在方式,就能为改变人们的社会意识创造基本的物质条件,所谓劳动改造思想,也正是以此作为逻辑起点。在边区强大的群众动员和严密的组织生产之下,边区人民不仅物质生活得到了改善,精神世界更得到了荡涤与洗礼。对边区群众而言,近代以来的天灾人祸让他们几乎难以看到生存的希望,中国共产党到来以后积极组织他们参与生产,不断重塑边区的乡村社会结构,并且营造出“劳动光荣”的氛围,使边区群众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和勇气。尤其是边区政府大张旗鼓地奖励那些勤恳工作的受苦农民,坚定了他们在政府领导下劳动生产的信心。所以以迷信作为谋生手段的巫神,也由此遭受剧烈的冲击,许多巫神在生产过程中得到改造。
其二,大生产运动要求边区将包括巫神在内的所有群体组织起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发表的《组织起来》就号召:“把群众组织起来,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队机关学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劳动力半劳动力,只要是可能的,就要毫无例外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7]928尽管巫神是处于边区乡村社会的边缘群体,但毫无疑问他们也是被组织起来的对象,边区政府不可能对这一群体置若罔闻,熟视无睹。具体而言,边区政府依靠“利益诱导—宣传教育—典型示范”[8]等方式构建起“组织起来”革命话语,并以此作为之后开展反巫神运动的重要依据。许多巫神就是在制定生产计划和努力生产后逐步实现了改造。“在安塞四区的一次反巫神斗争大会上,有好几个巫神宣布制定生产计划,一个到会的巫神还将他的三山刀(巫具)打成了一把菜刀。”[9]不难想象,凭借“组织起来”这一特殊的革命话语,包括巫神在内的边区许多群体都要求加入到各种形式的劳动互助组织,并以扎工队或变工队作为载体,在组织化中接受着改造。许多巫神正是在加入这些组织后,才逐步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摆脱了对鬼神的依赖,脚踏实地地从事劳动生产。正如毛泽东指出:“这种生产团体,一经成为习惯,不但生产量大增,各种创造都出来了,政治也会进步,文化也会提高,卫生也会讲究,流氓也会改造,风俗也会改变;不要很久,生产工具也会有所改良。到了那时,我们的农村社会,就会一步一步地建立在新的基础的上面了”。[10]
二、初步形成:改造二流子运动的开展
反巫神运动虽然发轫于大生产运动,但更多是在改造二流子运动中不断深化。尤其边区将巫神定义为最坏的二流子,剥夺其存在的社会基础,赋予了边区改造巫神的正当性。
乡村无赖或游民,作为游离在正统乡村权力之外的不稳定势力,长期以来一直是传统国家治理建设过程中的痼疾,不受到正统权力所承认。不同政权实体都对其展开了治理和控制,却都未曾有效得以解决。20 世纪30 年代左右,由于战乱、灾荒等原因,导致了大量游民涌现,尤其是在共产党政权扎根的陕甘宁边区。据统计,中共中央于1935 年来到边区时,无赖游民就已有七万多人。[11]如何处理这些游民所带来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成为这一时期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当时,这一工作最早开始于延安县和华池县,1939年大生产运动提出以后,延安和华池就已着手开展改造二流子运动,随后党政机关虽提出要全边区开展改造二流子运动,但远没有形成热潮。直到1942 年西北局高干会议后,为配合大生产运动,边区开始决定发动改造二流子运动,自此以后,这项运动得以如火如荼地开展。
1943年2月14日,《解放日报》发表《改造二流子》社论后,掀起了全边区改造二流子运动的高潮,巫神在该社论中就被视为二流子。该社论称:“延安县在改造二流子时出现了很多动人的例子,其中蟠龙区某巫神,把三山刀打成了䦆头,向群众宣布,再不骗人,从此努力生产”。[12]巫神与二流子基本上划上了等号,被认为是农村里的“耗子”。而且以社论的形式对巫神加以定性,也表明了中央的态度。同年5月,延属分区政府指示边区分区要组织另一种二流子,即组织巫神参加生产,强制巫神放弃过去骗人的职业,采用对待二流子的方法让他们选择一种正常的生活方式(农业、工业、商业)等,并且明确提出“巫神是一种最坏的二流子”。[13]
为何说巫神是最坏的二流子?其一,巫神的危害性要远高于二流子。二流子更多指那些无业游民和地痞流氓,而巫神更多是迷信职业者,他们不仅同普通二流子一样,没有正当职业到处闲逛,而且他们还骗人钱财,危害着群众生命健康。当时边区政府就称巫神肆意无忌,浪费了人民大量金钱,杀害了不少边区公民,婴儿死亡率相当惊人。[14]
其二,剥夺巫神神圣的外衣。许多群众对于巫神极为崇拜和信仰,但对二流子却极为厌恶。尤其是群众每次耕作时,二流子总在旁边说风凉话,像“你们生产了,吃的穿的还不如我”。[15]而且由于政府在征收公粮时实行分摊制,要求每个村出一定比例的公粮。二流子没有粮食上缴,公粮负担也会被分摊至其他农户身上,也引发农户极大不满,有农户就说道:“勤户种地多吃亏,二流子不种地占便宜”。[16]另外,二流子本身或多或少带有好吃懒做、挑拨是非等不良社会风气,使群众对其十分厌恶,而若将巫神贴上二流子的标签,并且以“最坏”加以定性,就会使群众所倚赖的巫神身份失去了本身的神圣意义,减少改造过程中所遇到的阻力,并同时赋予边区政府改造巫神的正当性。
其三,考虑到群众心理接受的需要。巫神在群众心中一直是降妖除魔,治病救人的“布道者”,若是直接开展对巫神的改造,不仅收效甚微,而且还会招致一些群众的反对,但若将二流子与巫神划为等号,群众在心理上也更容易接受。
饶是如此,巫神与二流子仍有所区分。改造二流子一般来说只是改造他本人,而反巫神还涉及到群众思想改造的问题。[17]这侧面说明了改造巫神的难度要远高于改造二流子。禹居区三乡李家沟的田宝成本人是个巫神,还曾种过12垧庄稼,在群众大会上定义他为二流子,不但他本人不满意,就是一般的群众都不满意。[17]从该个案可以看出,尽管田宝成是个巫神,但他也从事生产,若是将从事生产的人也定位于二流子,群众的心理难以接受,甚至于产生不服气、难以理解的心理。所以在开展反巫神斗争时,政府有时也无法在改造二流子运动中精准实施巫神改造。深究其原因可知,由于边区政府倡导的诸多社会改造运动都服务于发展生产这样的背景之下,巫神作为二流子的一部分,在改造过程中所强调的经济属性大于其社会属性。换言之,只要巫神能够不再骗人,安心从事生产,即认为改造成功。这样也使得许多巫神鱼目混珠,仍以秘密或者不公开的方式从事迷信骗人。在安塞二区就发现农村中仍然有许多传播迷信和骗取群众财物者活跃各地。[18]因此,伴随着二流子改造的巫神改造,在改造时并不彻底,许多巫神仍然逍遥法外,极为猖獗。但在改造二流子中的经验和教训,也为之后开展反巫神运动奠定了前提和基础。
另外,二者在工作方式上也应有所区分。有报道称:“除职业巫神外,在银川有一部分巫神还参加生产劳动,他们对于二流子的好吃懒做的习惯还是反对的。同样的,在二流子中,有一部分是不迷信的,对巫神也是反对的。如果在工作方式上不加以区别,不但不能利用二者之间的矛盾,反而还会促成二者的相互结合”。[17]可见,将巫神定义为最坏的二流子后,如何更好地避免巫神与二流子的混同,实现精准改造,也是边区政府不得不面临的重大问题。
三、高潮迭起:崔岳舜运动和巫神坦白运动的并举
尽管边区通过改造二流子运动使一部分巫神得到改造,但仍有许多顽固的巫神未曾改造。只有发起群众性的反巫神斗争运动,取缔巫神的活动,同巫神展开坚决的斗争,才能推进反巫神斗争的深入和扩大化。为此,1944年4月29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开展反巫神的斗争》,正式掀起了全边区反对巫神的热潮。社论称:“巫神最大部分是二流子,是鸦片鬼……希望各地党政军民、西医、中医、小学教员和有知识的人都联合起来,劝说人家,不信巫神,相信医药”。[19]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希望将巫神改造转变为全边区的一场群众运动。在具体实践中,边区政府通过典型引领和“巫神坦白”的方式,推进反巫神运动不断深化。
1943年11月,毛泽东在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强调:“‘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就是说,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7]933毛泽东所说的寻找诸葛亮,实际上指的是寻找和确立典型,促成群众性的运动。三边分区的老中医崔岳舜就在此次破除迷信的反巫神斗争运动中脱颖而出,成为了毛泽东所说的“诸葛亮”。
崔岳舜是个医生也是定边县的参议员。崔岳舜为了破除卜掌村的迷信,不仅经常去给群众治好病,同时不停地向老百姓做破除迷信的宣传。“他说:神是哄人的。老百姓说:没神,怎么会生病呢?崔说:因为五脏受冷受热,不信就治治看。老百姓还问:没神,为啥会刮风、下雨、打雷呢?为啥日月东出西落?等,崔岳舜一一用科学知识进行了解答。”[20]
此外,崔岳舜还从确凿的事实进一步揭露巫神骗人的伎俩。尤其他通过医药治好病人,让此人不再信鬼神,然后此人又影响其全家人不迷信,一家又影响一村,从而实现全村迷信的破除。崔岳舜所医治的病人,大多经过了巫神和阴阳医治后无效才去崔岳舜那治好。许多群众经过实际的比较,并配合边区医药卫生的宣传逐步相信了医药。崔岳舜的这种救治方法不仅教育了一般群众,而且一些巫神甚至由此转变过来。“石锡三曾是四代的阴阳,前年患腹泻病,请阴阳安砖吊瓦,都没效用,最后请崔岳舜医治后,一剂药见效,于是他便利用这一事实到处宣传。群众中也逐步流传道:‘阴阳到处给人治病,自己有病却没法治’,由此阴阳在群众中影响大大削弱,石锡三一家四个阴阳也逐渐从事了生产。”[21]
崔岳舜破除迷信的事迹被报道后,边区政府即将崔岳舜和卜掌村树立为卫生运动的模范,三边分区的罗专员、孙县长、丁县长亲自授予崔岳舜奖品。从整个授奖仪式编排即可看出整件事的教育宣传意义要远大于其事情本身。无论是三边分区领导颁奖,乡长提前一天准备会场,颁奖会上附近各村群众代表的广泛参与,还是刻有毛主席像的模范奖章以及刻在正房上的英雄匾都无疑体现了政府的重视。议程最后,崔岳舜还向边区群众承诺五件事情,不仅要办好清洁卫生、成立药铺、组织成立医生研究会、下乡看病,还要负责全区人民的身体健康,疾病治疗。[22]
总之,边区政府通过确立典型,以表彰先进的方式实现了权力的下乡,并以崔岳舜作为符号,掀起了全区破除迷信,反对巫神的热潮。尤其是三边分区地处整个边区的边缘地带,巫神势力相比延安周边地区更为猖獗,在此地确立典型,也昭示着中国共产党改造巫神的决心。崔岳舜和卜掌村获奖后,许多村庄的人相继学习崔岳舜。“单是黄儿庄的人回来后即有十九户人家烧了神像,这一消息传到城区四乡后,有两户村民还比赛烧神像,不到十天就有三十二家烧了神像。这一系列的事件不久后刊登在区政府的黑板报上,各地随即传开了崔岳舜反迷信的故事,相继展开了崔岳舜运动。”[21]
另外,边区开展反巫神斗争一开始基本上采取一味打倒的原则,即依靠政府的强权,采取严惩的方式“打倒”巫神。然而,边区党和政府逐渐发现这种单纯的打倒不仅收效甚微,而且还引发了一些新的问题。特别是迫于巫神在乡村的崇高地位,采取单纯打倒的方式极易引起群众的反感。毛泽东较早就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他认为“我们反对群众脑子里的敌人,常常比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还要困难些”。[23]毛泽东的这一看法在实践中得到了印证,许多巫神在改造之后,经常又“起死回生”,继续秘密从事巫神的行业。在这种情况之下,边区党和政府逐渐认识到“在群众文化战线上,即使是应该反对的东西,也不是简单的打倒,巫神及各种封建迷信是敌人,不发生联合问题,但也不是用简单打倒的方法所能解决的,要经过群众与本人的自觉才会被消灭”。[24]
由此,边区政府乘着改造二流子运动的“东风”,号召广大干部群众改造巫神,破除迷信,“唤起群众自觉地参与反巫神运动和巫神坦白运动”[25]。所谓“巫神坦白”即经过改造后的巫神在群众大会、庙会等场所,向群众公开揭露其骗术,以求达到宣传教化之效果。巫神坦白运动之所以能够推动反巫神运动的深化和群众旧有观念的荡涤,其关键就在于“通过巫术的制造者来揭破超验的观念世界,无疑具有颠覆传统的教育意义。”[1]具体来说,巫神坦白运动大致遵循巫神显露、政府谈话和群众集会三个阶段。
首先,巫神显露是巫神坦白的基础和前提。许多巫神擅长东躲西藏,极为隐蔽,再加上民间刻意隐瞒,致使边区政府难以发现巫神的踪迹。因此巫神显露的关键还是在于群众能够自觉地举报巫神害人事件。吴旗县有一个名为李九滋的巫神,由于到处骗人,将自己吐的污水给村里一名妇女喝下,结果几月后,该妇女疼得饭也吃不了。有人将这一消息报告区政府后,区书记亲自前往村庄同该巫神进行谈话,并要求召集村民大会,戳穿李巫神的骗术,让李巫神能够当众坦白。[26]此外,除了群众自发举报外,许多巫神也可能在边区崇尚生产的氛围之下,自觉改造。像做了二十多年巫神的聂志秀,就是在村民紧张劳动的感动下,积极生产。[27]再如中区一乡的张贺思,是个巫神又是个二流子,在政府的生产号召下,经过群众的劝说后,决心改邪归正,自动跑到乡政府声明参加生产。[28]
其次,政府谈话是实现个别巫神转变的关键。在巫神显露之后,边区党和政府就会积极开展一系列手段使他们转变。其中谈话是政府最常用的手段,这种谈话隐含着一种教化性的权力。即这种谈话并非是压制、横暴和冷酷的,而是鼓动、动情和引诱的,它体现的是教化者与被教化者之间的有效互动,其目的是能够引导受教化者思想的觉悟,形成教化权力的运作空间。政府谈话显然就带有这种教化性的权力,如以下个案:
史月详率领自卫军一个班,到四乡巫神薛桂开家去,薛桂开看到进来了几个自卫军,便慌了,坐在炕上说不出一句话。史月详看出了这一点,便也坐到炕上去,先和他拉了一阵家常话,往下才慢慢转到正题上去,史月详很严正却又很亲切地说:老薛,你这事儿可以抛开啦!依我看来,倒不如学学扎针,学学开药方有用些。开头薛桂开没做声,史月详想:要巫神抛掉三山刀、铜爷爷,就像地主要抛掉地租契约一样,是件难事儿。所以他和自卫军的弟兄们一点也不着急,耐心地给他讲道理:“这个不是十年前的旧社会了,三山刀、铜爷爷吃不开了,今儿下个决心,重新做个正派人,务生产还来得及。”史月详还知道对方在担心另一个问题,就诚意地告诉他:“只要你愿意改好,政府不为难你,还欢迎你哩。”大家在旁边也帮着劝,就在当夜把薛桂开劝过来了。[29]
可见,此次谈话并未使用强制性的刑罚手段,更多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凭借教化权力所构建的权力空间,使得该谈话也带有一种不由分说的强制性。尤其是谈话者史月详自卫军的身份足以给薛巫神形成一种震慑力,再加上谈话者动情的劝说方式,个别巫神由此得以转变和改造。
最后,群众集会是巫神坦白运动的重要载体。个别巫神转变后,要使其达到教化人心,破除迷信的效果,还需借助群众集会来扩大影响力,并且通过群众之间的相互感染、相互激励,将边区政府破除迷信的意志传递和辐射到更大范围的对象中去,从而凭借这种渗透力影响到群众基础较为薄弱的地区。为此,边区政府召开各种群众大会,许多巫神在会上宣布转变,向群众坦白巫神的骗术。延县召开反巫神大会时,很多巫神将骗人的假把戏痛快地说了出来。盘龙区的巫神赵某就说:“下阴就有神?毬!谁在里边还会舒服,除了夏天地下凉凉的,我就在里面美美地睡一觉,出来可就要赚钱咯”。[30]当然除了专门性的反巫神大会,边区政府还借助其他形式的集会开展巫神坦白运动。“延市召开卫生展览会时,延安县委书记王丕年亲自率领30 多名的坦白的巫神前往展览会,巫神赵桂璋当时就以自己巫神骗人害人的事实向大家报告,并号召在座的巫神坦白后,应好好生产,讲究卫生”。[31]总之,反巫神运动凭借着崔岳舜运动和巫神坦白运动,掀起了全边区反巫神的高潮。
结语
通过对反巫神运动的历史脉络进行梳理,可见反巫神运动并非是中共中央初到陕北就着手开展,它是在特殊背景之下所展开的一项运动。乡村文化建设固然重要,但在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一切服务于战争”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价值诉求。而且战争的不断扩大也考验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资源汲取能力,为了有效动员群众,最大程度上满足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后勤补给需要,以大生产运动为核心的一系列运动随之出场,反巫神运动亦是如此。它发轫于大生产运动,初步形成于改造二流子运动,并以此为基础,借助崔岳舜运动为典型引领,巫神坦白运动为导向,掀起了边区反巫神斗争的热潮。
1945 年以后,随着边区各县绝大部分巫神受到不同程度的改造,反巫神运动取得了显著成效。王春在《继续向封建文化夺取阵地》中提出:“我们有了由巫神转过来的劳动英雄。有了自动上门替人治病的农村医生。签筒不见了,泥老爷也不见了。因为蝗虫可以打绝,所以蝗神庙没香火,因为旱灾真能渡过,所以再不见祈雨的行列,人们要参加的是农会、工会,没了枪会、佛会的阵地。要学的是时事政治,所以《推背图》、《东方朔》再不上场……家里的《诸神同堂图》撕了,换了毛主席”。[32]但迷信思想并非仅是凭借反对巫神,破除迷信就能够简单消弭的,群众观念的转变也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因此,巫神一类的迷信职业者仍有活动的生存空间。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对于乡村迷信的治理有着长期和复杂性的考量,《解放日报》评论中就称:“我们应当了解和迷信思想斗争是长期和艰苦的教育过程,几千年来旧社会所遗留下来的东西绝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肃清的”。[33]然而,在边区反巫神运动的运行实践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反巫神运动融入乡村社会改造之中,重塑社会新人、重构群众认同、重树社会新风、重建社会秩序,使乡村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尤其是反巫神运动同边区卫生防疫运动、反迷信运动等一系列运动交织一起,勾勒出了乡村社会蝶变的亮丽图景。而且以改造巫神为代表的反巫神运动,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新式公民的角色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