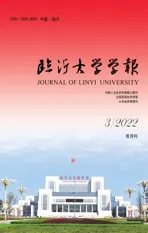从符号学看王尔德《莎乐美》中月亮意象的重复性修辞
2022-11-23杨利亭
杨利亭
(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2)
重复,是文学活动中常见的现象。 “任何一部小说都是重复现象的复合组织,都是重复中的重复,或者是与其他重复形成链形联系的复合组织。”[1]3文学一再地揭示着一个真相:人的意识驱使人不断地选择当下的生活,并因循此选择去理解生活,构建对未来生活与世界的想象。 “意识如何辨别时间与空间中的世界? 靠辨别重复,重复是意义的符号存在方式,变异也必须靠重复才能辨认:重复与以它为基础产生的变异,使意义能延续与拓展,成为意义世界的基本构成方式。 ”[2]120与此同时,随着生活本身的持续性流变,相应的重复性选择及其相关叙述,也必然处于动态的流变中。事实上并不存在完全的重复,而总是差异性的重复:每个人、每件事和每个事物,既在当下适度敞开自我,又保持着各自过去和未来的独特性。
就现实经验而言,重复是同一事物、人物、情景和记忆的变相性再现。实际上,借助主观意识,文本中符号表意过程中的任一元素,都能成为重复所获取的材料印记。 “重复是一种解释行为,每次重复只留下上一次重复的东西,略去了无关的变异因素。因此重复可以逐渐创立一个模式。”[2]121就文学修辞传统而言,重复是对传统的辩证式延续,整个西方文学的延续性继承与流变正是源于对二希传统(《圣经》和《荷马史诗》)与苏格拉底、柏拉图哲学的差异性重复。[1]5
就阅读认知而言,重复是缝缀现实与虚构的丝线。 读者之所以能将《奥德修斯》中珀涅罗珀白天织布、晚上拆布的重复行为理解成她对奥德修斯忠贞不渝的表现,恰恰在于读者辨认出了珀涅罗珀这种看似重复的无效编织与拆解行为背后的执著与坚韧。 同样,对狄更斯小说《双城记》的经典性确认,源于读者对作者小说中重复性修辞的辨认。 读者对德伐日太太之所以印象深刻,在于狄更斯对德伐日太太这一底层革命者形象的单一行为的重复性强化——对其编织行为的重复叙述,正是编织行为塑造了她立体的形象,暗示了她苦心经营的复仇大计,刻画了她苦大仇深的革命形象,揭示了她被仇恨扭曲的人性。对德伐日太太编织行为的重复性叙述,逐步强化了读者对暴力革命和私人恩怨之间关系的思考。
美只在重逢与重识中发生,“美是慢箭”[3]100。 面对文本中的重复现象,读者可能会根据自身的阅历做出不同的反应:或者对叙述形式密切关注,进而对重复性修辞加以推敲;或者有意忽略形式而将注意力集中在故事层面。因此,“读者对重复现象的识别可能是深思熟虑的,也可能是自发的;既可能是自觉的,也可能是没有思考成分的”[1]3。 王尔德的《莎乐美》是运用重复现象的集大成者。 该戏剧的整个形式图景都建立在对多个意象的重复运用上。 该剧中常见的意象有“白玫瑰”“水仙花””百合花““月亮”“白蝴蝶”“小鸽子”“酒”(凯撒的紫袍色、黄金色和血红色三种)……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月亮”,它是贯穿《莎乐美》全剧的核心意象。王尔德对月亮意象的重复性运用,充分体现了差异性重复的生成力量。《莎乐美》的释义多元性恰恰在于不同人物对同一个月亮的“互不相容的解释的同时并存”[1]146。
在《莎乐美》中,月亮意象不仅是一种审美上的修辞性重复,而且还使该剧的整个唯美式叙述拥有了一个潜在的深层结构,不同的人物重复提及的三种月亮隐喻均扎根在月亮的女性化层面:月亮的爱情隐喻、月亮的贞洁隐喻和月亮的死亡隐喻。三种隐喻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既是相辅相成的,又是各自独立的。 月亮女性化的三种隐喻,让原本停留在表层形式的月亮逐步渗入到叙述内容之中,进而成为破解意义之谜的密钥。
一、月亮意象:爱情的隐喻
重复性修辞会对文学风格的形成产生极大影响。 重复叙述同一件事,会使文学艺术达到一种重复性的修辞效果——“事件的多样性和风格的丰富性”[4]。
月亮意象是剧中重复出现的爱情隐喻,正是它印证了作者的重复性修辞给读者带来的累加式语义认知。 重复出现的月亮(爱情符号),不仅强化了叙述者对月亮与爱情之间关系的同一性释义,而且还深化了读者对莎乐美爱情悲剧主题的思考。月亮既是爱情的隐喻,也是死亡的征兆。被云纱遮住面庞的月亮,正如戴着七层面纱的莎乐美,面纱之下是不可遏制的激情和迫切毁灭一切的冲动。 因此,爱情既是美的幻觉,也是死的凶兆。
爱是欲求自己从未拥有和早已丧失之物,源于一种对自身匮乏的心理补偿。 一个人之所以爱另一个人,在于他/她缺乏的正是他/她欲求的对象所具备之物。 人总是欲望他者,他者越是不可企及,就越是魅力非凡。 在《莎乐美》中,月亮意象作为爱情的隐喻,主要与两种单向度的爱情欲求相关:一是叙利亚青年对莎乐美的爱情;二是莎乐美对先知约翰的爱情。莎乐美是叙利亚青年眼中的月亮女神, 先知约翰是莎乐美眼中的高冷而又圣洁的月亮化身。 “人所爱的并不是属于自己的东西,除非他把好的都看成属于自己的,把坏的都看成不属于自己的。 ”[5]60不幸的是,无论是叙利亚青年对莎乐美的一厢情愿的膜拜式恋慕,还是莎乐美对先知约翰的不可遏制的占有式激情,最终都悲剧性地证明了单向度的爱情注定是自食苦果。
叙利亚青年和莎乐美是两个既平行对照又异质同构的镜像。他们追逐圣洁的“月亮”恋人的爱情悲剧,均源于一意孤行的毁灭式激情,但二者又有形式上的区分——叙利亚青年以自杀的方式,毁灭自我、终结爱情;莎乐美以杀死他者(先知约翰)的方式,毁灭爱情、终结自我。 然而,从悲剧的根源上来看,导致二者毁灭自我和终结爱情的并不是他们自身的性格,而是悲剧的始作俑者——贪恋权力、金钱和美色的弑兄篡位者希律王。叙利亚青年作为被希律王俘虏的他国王子,莎乐美作为被希律王觊觎的受辱女性,形成了两个受辱形象的平行对照。 叙利亚青年的命运和莎乐美的命运极为相似,他们各自的父亲均被希律王所打压,叙利亚青年之父被希律王流放他国,莎乐美之父被希律王先囚禁后杀害。
“爱神首先是对某某东西的爱,其次是对他所欠缺的东西的爱。 ”[5]50然而,这种源于自身匮乏并欲求借助他者的丰盈——以完善自身的爱之主体, 通常并不能得到另一方的回应。凡人爱上月亮,这是一种非尘世而又不可企及的爱情理想。被希律王俘虏的叙利亚青年原本是一个王子,现在却沦为朱迪亚王国的仆从(“囚徒”),仆从爱上公主,这种爱注定了无法得到公主莎乐美的回应。 同样,莎乐美是尘世王国的公主,但她欲求的却是神的化身(代言人)——先知约翰,这就变相重复了叙利亚青年对莎乐美的单相思的爱情欲求,即尘世之人对非尘世“月亮”神的爱情想象。
爱的产生,是对美的自愿臣服,是将自我退出中心位置,自愿让位给他者的一种自我收回。“因为美的存在,主体退居侧位,它走向一边,而不是向前突出自己。主体变成侧面角色。为了他者,主体收回了自我。 ”[3]81在恋慕莎乐美的叙利亚青年眼中,莎乐美是他聚焦的中心,月亮是莎乐美的象征。 在他眼中,莎乐美既娇美动人又洁白无暇,他将莎乐美视为他生命存在的轴心。他就像一个单方面坠入爱河的情痴,以恋人的眼光打量隐喻爱情(爱情对象莎乐美)的月亮。 在他看来,月亮“像一个小公主披上了黄纱,那双脚却是银色的。 它像一个公主长了一双白鸽般的纤脚。 你看它的样子就是在翩翩起舞”[6]5。
当一个人将自身全部的精力投射到另一个人身上时,他就不再是一个独立而完整的主体,反过来说,他的独立和完整已经不可能从自身获取,而必须仰仗于另一个人的帮助。 叙利亚青年将莎乐美的形象抽象化为绝对的美与爱的理想,但莎乐美本身却不具有抽象的绝对性。 “爱主要不是由某一特殊对象‘引起’的东西,而是人内在的一种缠绵之情,只有靠某一‘对象’才能实现。 ”[7]当叙利亚青年将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莎乐美身上时,当他对莎乐美微妙的表情变化都能产生共情时,他的主体性便不再独立而完整。 当莎乐美是他生命中所寄托的一切时,之后他所知所见的关于莎乐美的一切也都是莎乐美的隐喻。
月亮是一个集中隐喻了莎乐美形象的核心意象。 叙利亚青年最初用鸽子、白蝴蝶和小公主来描述月亮的形貌,在见到莎乐美之后,他又用描述月亮的语汇“鸽子”和“白蝴蝶”来形容莎乐美:“公主把脸藏在她的扇子后面了! 她的小手扑棱棱得多欢,像鸽子飞向它们的窝里。 她的手跟白色的蝴蝶一样。 它们简直就是白色的蝴蝶呀。 ”[6]8
不难发现,在叙利亚青年眼中,“鸽子+白蝴蝶+小公主=月亮”与“鸽子+白蝴蝶+月亮=小公主”是一致的,如果两个公式都去掉“鸽子+白蝴蝶”的成分,便能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月亮=小公主”或“小公主=月亮”,这就将月亮的隐喻和莎乐美的形貌合一了,正是人的隐喻符号和人的意义同一性,逐步强化了读者对月亮即莎乐美、莎乐美即月亮的同一性认知。之后,叙利亚青年谈及的所有意象,如琥珀眼睛、轻纱后的小公主、小鸽子、水仙花、白玫瑰,都与莎乐美在他心中投下的影像具有认知的同一化关联。
同样,莎乐美对先知约翰的占有式爱情,最初也定格于她对先知约翰高冷而圣洁如月亮的身心的欲求。之后,莎乐美又运用了大量的意象来描述先知约翰的形貌和气质,这些意象如 “憔悴的象牙雕塑”“银色肖像”“银色的箭杆”“冰冷的象牙”“晶莹的积雪”“洁白的玫瑰”“黎明的光”……这些意象均是对月亮意象的进一步诠释——对月亮那清冷又高洁品质的延展。 正如叙利亚青年最终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了他心中的月亮女神——莎乐美,莎乐美最终也因不可遏制的毁灭式激情殉葬了她的爱情——把自己的生命献祭给了先知约翰的亡灵。
二、月亮意象:贞洁的隐喻
在《莎乐美》中,贞洁指的是处女贞洁和隐喻处女贞洁的月亮,二者均指的是一种不受玷污的圣洁。确切地说,《莎乐美》中的贞洁,指的是莎乐美的处女贞洁和隐喻莎乐美处女贞洁的月亮。
对莎乐美而言,莎乐美最初的贞洁代表着她未被玷污的自尊和未被羞辱的人格。 对恋慕莎乐美的叙利亚青年而言, 莎乐美的贞洁是他不再拥有的王子身份的心理补偿和他对爱情理想的完美隐喻。 对以希律王为代表的男性而言,莎乐美的贞洁是富有情色诱惑的强力催化剂。 对莎乐美之母希罗底而言,莎乐美的贞洁是制衡第二任丈夫希律王的棋子。 对先知约翰而言,莎乐美的贞洁早已被父辈的恶行所玷污——被她叔父与母亲的乱伦之罪所浸染。
在《莎乐美》的语境中,不仅男性将月亮理解为女性的隐喻,而且连女性自身也将月亮理解为女性自身的隐喻。 如果说叙利亚青年将月亮和莎乐美相等同是前者的一厢情愿,那么莎乐美自比为月亮就不再是无稽之谈了。 被不怀好意的希律王频频窥视,让莎乐美感到倍受侮辱,她认为自身的处女贞洁和人格尊严受到了冒犯,因此欣羡于月亮的圣洁和自爱。
希律王:月亮看上去不是很怪吗? 它像一个疯女人,一个到处寻找情人的疯女人。 它还裸露着身体。 它简直一丝不挂。 云彩在追着给它往身上披衣服,可是它还不让云彩给它披。它让自己赤裸裸地展露在天空。 它在云彩里打着滚儿,像一个喝醉酒的女人……我敢保证它在寻找情人儿。 它难道不像一个醉酒的女人? 它像一个疯女人,难道不是吗?[6]21
莎乐美:看见月亮多好啊。 她像一枚小硬币,你会以为她就是一朵银色的花朵。 月亮清冷,娴静。我敢说她是一个处女,具有处女的美。是的,她是一位处女。她永远不会糟蹋自己。她永远不会像别的仙子那样,心甘情愿地委身于那些臭男人。[6]11
通过对比希律王和莎乐美各自理解的月亮意象可知,莎乐美之所以将月亮作为处子的隐喻,在于她受到冒犯的尊严让她自认为她原本的处女纯洁已经丧失。同时,莎乐美将月亮等同于处女,也是对希律王将月亮视为疯女人、醉酒的女人和寻找情人的疯女人的一种修辞性反击。 王尔德对月亮意象的悖论式重复,使得莎乐美和希律王两个人的月亮隐喻形成了尖锐的对立。
莎乐美对先知约翰的毁灭式占有欲,很大程度上也是对叔父希律王的反相复仇——希律王杀了她的父亲、娶了她的母亲,还时时垂涎于她的美貌和舞姿。当她得知希律王忌惮于上帝的代言人先知约翰时,她那原本受到损害的自尊心和杀父之仇便再次被强烈地激发了出来——她要利用先知约翰的震慑力作为反击和报复叔父希律王的一把利剑。
莎乐美不仅以月亮自比,还用月亮来形容和赞颂先知约翰的高冷和圣洁,似乎先知约翰的高冷和圣洁,在提示着她早已丧失的精神“贞洁”:“他像一幅银色肖像。 我敢说他像月亮一样高洁。 他像一缕月光,又像一支银色的箭杆。 他的肉体一定像象牙一样冰冷。 ”[6]16以月亮意象来界定先知约翰的形象之后,莎乐美又运用诸多具体的意象(百合花、玫瑰、白雪、白色墓地、黑葡萄串儿、黎巴嫩的雪松、黑蛇、石榴花、鸽子爪、红珊瑚、朱砂、)来赞颂和否定先知约翰的品格、声音、肉身、头发、嘴唇,也即在是与否中表达对约翰步步紧逼的占有欲。
爱是一个人欲求他者身上所拥有的那些自己早已丧失的东西。 觉察到受到希律王对自己贞洁之身羞辱的莎乐美,将贞洁的品质赋予月亮,继而又赋予了高冷又圣洁的先知约翰。然而,莎乐美非但没有在先知约翰那里得到自己贞洁丧失的心理补偿,还再次受到了男性(先知约翰)对她贞洁的话语性羞辱。先知约翰不断以蔑视和诅咒的犀利话语,来贬低和否定莎乐美母亲和莎乐美本人。约翰以“巴比伦之女”“罪恶之地之女”“通奸之女”来形容莎乐美,这让原本就受到希律王眼神羞辱的莎乐美再次受到了先知约翰诅咒话语的毁灭式打击。
无论洪流还是大水,都不能平息我的激情。 我本是一个公主,你却敢责骂我。 我是一个处女,你却把我的贞洁剥夺了。 我静若处子,你却往我的血管里填塞了火焰……啊! 啊! 为什么你不看我,乔卡南?你如果看看我,你准会爱上我,爱之神秘远比死之神秘更神秘啊。爱才是唯一应该考虑的。[6]16
莎乐美对约翰的毁灭式占有,源于对自身贞洁再次受到侮辱的一种激情报复,她借杀死约翰同时报复了希律王对她的眼神侮辱和约翰对她的话语羞辱,尽管她对约翰的报复源于一种被扭曲的爱。
三、月亮意象:死亡的隐喻
王尔德借助多义的月亮意象为《莎乐美》中的各个人物赋形。 不同的人物,因对同一事物的不同理解而拥有了自己的形貌。 “意象常常是外在客观物象和储存在记忆中的物象印象共同感发主体的情怀,由主体通过想象力,取法天地,‘类万物之情’而创造”[8],主体又因对万物的情感投射而形塑自身。
在《莎乐美》中,月亮意象的重复运用,在塑造了立体化人格的同时,也引导着情节在何处分叉演绎,继而营造了阴森的死亡氛围,最终还影响了故事的走向。就出现频率最高的月亮意象而言,虽然剧中各个人物看到的是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的同一个“月亮”,但是每个人对月亮含意的理解却大相径庭。 然而,正是这种对同一月亮的差异性理解形塑了形色各异的人格类型,进而也影响了故事的发展走向。
月亮意象不断寄身在不同的人物话语中,而恰是这些有关月亮的重复性话语给予叙述以意义,同时,也促使文本外的读者赋予月亮及谈及月亮的人以相应的意义。 故事一开篇,希罗底的小童就看出了月亮蕴含的死亡意义:“快看月亮! 快看月亮多么古怪啊! 它像一个女子从墓中缓缓而起。它像死去的女人。你会觉得它在寻找自己的东西。”[6]5随着剧情的不断推进,月亮意象作为死亡的预言者,在希罗底的小童眼中变得愈加离奇古怪和阴森可怕:“你会以为它是死女人的手,正在寻找裹尸布把自己覆盖上。 ”[6]14
具象的月亮和抽象的死亡,总是被看出月亮和死亡之间的关联的见证者(剧中人)理解成具象的月亮和个体的死亡,尽管见证者并不知道是哪一个体的死亡。 在希罗底的小童表达对叙利亚青年之死的悲痛和悔恨时,便可看出月亮的死亡隐喻,总是关乎见证者对个体悲剧的喟叹:
年轻叙利亚人杀死自己了!年轻叙利亚人杀死自己了!我的好朋友把自己杀死了!……啊,他不是早说过会发生不测之祸吗?我不是也早说过有横祸,而且横祸果然发生了吗?哦,我早知道月亮在寻找死物,可我万万没想到月亮是在寻找他啊。唉,我为什么不把他藏在月亮找不到的地方? 如果我把他藏在月亮找不到的洞穴里,那该多好啊。[6]19
当死亡真的降临到某一个体身上,看出月亮即死亡隐喻的见证者,总是局限在某一个端点。 一方面,通过死亡隐喻,见证者只能看到某一个体的死亡。 把这隐喻只与当下的死亡事件相联系,而并不将其与过去和未来之死,甚至更普遍的死相关联。
将月亮理解成是死亡隐喻的见证者,通常只将目光牢牢地投射在当下个别含意的而非更具普遍意义的死亡语境中,如希罗底的小童由月亮洞察的死亡寓意。另一方面,见证者只看到普遍的死亡隐喻,而拒绝将这种灾祸与自己相连接,如先知约翰就将月亮的死亡隐喻仅仅视为对暴君命运的预言。 虽然希罗底的小童看出月亮是死亡的象征,但他却不知道月亮隐喻的究竟是谁的死亡,正如先知约翰也看到血色的月亮背后隐含的死亡暴力,但他并未意识到这死亡暴力是否与自己相关:
到了那天,太阳会变成漆黑一团的,像头发上的黑丧步;月亮会变得像浓血,天上的星星会像无花果树上长熟的无花果那样,纷纷从天上掉到大地上,地上的国王都会吓得胆战心惊。[6]32
希罗底的小童和先知约翰所理解的月亮,实际上隐喻了整个戏剧中的所有死亡——莎乐美父亲之死、叙利亚青年之死、先知约翰之死和莎乐美之死。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死亡都与月亮有着直接的隐喻关联,比如莎乐美父亲之死,便是通过其他三人的死亡一步步被揭示出来的。 这一系列的死亡悲剧均源于希律王不可遏制的权力欲:朱迪亚王国的上一任国君是莎乐美的父亲,希律王是莎乐美的叔父,为了攫取权力、渔猎金钱和美色,希律王不惜弑兄篡权。 希律王将兄长囚禁在古井十四年后又派人将其勒死,之后迎娶了兄长的遗孀即莎乐美之母希罗底,并觊觎莎乐美的美貌和舞姿;俘虏了他国王子(即叙利亚青年)并将其父王驱逐出国、将其母贬为奴隶;因迷恋莎乐美的舞姿而兑现了许给莎乐美的诺言——杀死先知约翰;因忌惮于神的报复而杀死莎乐美祭神。
当文本中的重复性修辞——月亮意象成为指涉故事深层意义的符码,这个符码就架起了一座连接月亮及月亮所代指的意义之间的桥梁。《莎乐美》正是借由多个人物口中的月亮意象,来逐步揭示出死亡悲剧的始作俑者——希律王。
结语
王尔德深谙作者的重复性修辞给读者带来的强烈认知效果。读者通过阅读具有大量重复性修辞的文本,会习得一种记忆式审美经验——源自其不断地重复观察和记忆反复再现的事物。在《莎乐美》中,王尔德正是重复运用月亮这一意象,从而重新激活读者的前阅读记忆——暂时忘却的前文中关于“月亮”的叙述。王尔德《莎乐美》中重复回现的三种月亮隐喻均扎根在对莎乐美多元形象的塑造中,也即月亮的女性化层面:月亮的爱情隐喻、月亮的贞洁隐喻和月亮的死亡隐喻。
在对月亮意象的不同理解中, 每个人都间接地通过谈论莎乐美与月亮之间的隐喻关联,既勾勒了自己的形貌,也推进了情节的发展进程,最终引领读者逐步洞见莎乐美悲剧的真相。 对以男性欲望视角来观察莎乐美的希律王而言,莎乐美是带着七层面纱跳舞的性感精灵和男性爱欲投射的对象;对以恋人的眼光打量莎乐美的叙利亚青年而言,莎乐美是娇柔可爱的、超凡脱俗的月亮仙子,是美和纯洁的隐喻,是理想爱情的象征;对王后希罗底而言,女儿莎乐美是她挟制希律王的一枚棋子;对先知约翰而言,莎乐美是背负着父辈乱伦之恶的不洁后裔。
月亮意象的重复性叙述成为推进故事进程和控制叙述节奏的遥控器,最终也迫使读者进入主题阐释的语境。 修辞性重复不仅锻炼了读者的审美力,而且还影响着读者的判断力和对文本主题的阐释欲。 王尔德提示读者,作为解释主体的读者不是在阅读文本之前就有稳固不变的价值立场。相反,读者的思想很可能来自于重复性的修辞艺术,甚至读者的思想会因一个意象的无限重复而持续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