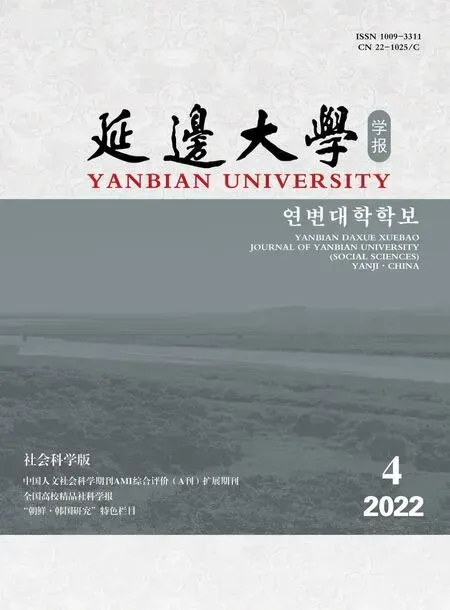论钱穆对中国传统经学的研究
2022-11-23迟浩然
迟 浩 然
钱穆认为,“欲考较一国家一民族之文化,上层首当注意其‘学术’,下层则当注意其‘风俗’。学术为文化导先路”。(1)钱穆:《中国学术通义·序》,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1页。想要考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内涵,探究其学术根源是为上,注意风俗是为下,盖因学术乃是文化的先导,只有了解中国学术的独特性,才能继续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的独特性。经学是中国古代学术研究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域。最初,中国古代典籍分为《诗》《书》《礼》《乐》《易》《春秋》,即“六经”,后《乐》逐渐失传,便成为“五经”。据钱穆推测“五经”概集结于秦末汉初,汉时人们将“六经”称作“六艺”。钱穆指出,汉代并不曾有“乐经”,则“六经”“六艺”之说只是虚设。“五经”之后又有“七经”“九经”“十三经”等汇集,至南宋形成“十三经”之后中国经书再也没有增加。钱穆认为,经学是中国传统学问中最重要的部分,甚至可以称之为“中国学问之主要中心”。(2)钱穆:《中国学术通义·序》,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2页。
同时,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经学几乎成了中国历朝历代统治阶级追捧的主流学问,探究经学的渊源及其发展史不仅对我们认识中国传统学术和传统文化具有重要作用,也对我们进行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钱穆的经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其著作《中国学术通义》《四书释义》《国学概论》《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本文拟以上述几本钱穆的著作为中心,对钱穆经学研究进行梳理,管窥其学术思想。
一、钱穆对经学渊源的考证与研究
钱穆十分注重采用历史研究方法,不论是研究文学、政治,还是思想等问题,追根溯源是研究任何问题的第一步。钱穆指出:“中国经学应自儒家兴起后才开始。”(3)钱穆:《中国学术通义》,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7页。我们探讨中国经学渊源问题,不可避免地首先触及孔子与“六经”的关系问题以及中国古代典籍的分类和“经”称谓的沿革问题。
(一)孔子与“六经”的关系
钱穆指出,“然于中国学术具最大权威者凡二:一曰孔子,一曰六经。孔子者,中国学术史上人格最高之标准,而六经则中国学术史上著述最高之标准也”。(4)钱穆:《国学概论》,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2页。自孔子之后的两千余年,大凡研究中国古代学术思想者,在研究孔子之时,皆会提及“六经”;同理,凡钻研“六经”者,亦必然论及孔子。故而钱穆认为,“六经之内容,及孔子与六经之关系,终不可不一先论也”。(5)钱穆:《国学概论》,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2页。我们必须先研究“六经”到底写了什么,以及孔子与“六经”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
司马迁对孔子与“六经”关系的看法,深受董仲舒的影响。司马迁指出:“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故《书传》、《礼记》自孔氏。”(6)司马迁著,文天译注:《史记·孔子世家》,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61页。“孔子语鲁大师……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7)司马迁著,文天译注:《史记·孔子世家》,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62页。“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8)司马迁著,文天译注:《史记·孔子世家》,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63页。“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9)司马迁著,文天译注:《史记·孔子世家》,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65页。“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10)司马迁著,文天译注:《史记·孔子世家》,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68页。即,司马迁认为是孔子编辑《书》,删订《诗》,撰修《礼》和《乐》,作《易》《春秋》的。然而,后来之经学者也并非悉数赞成司马迁的观点。时至清末,对孔子与“六经”之关系,学界已然分成两派,一派认为“五经”皆为孔子所作,另一派则认为“六经”与孔子无关。钱穆并不赞同“六经”皆孔子所为的观点。钱穆或多或少受新文化运动以后产生的“疑古辨伪”为特征的古史辨学派的影响,观点倾向于古文经学派。
钱穆在谈及“六经”之时,将其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易》与《春秋》,第二部分为《诗》与《书》,第三部分则为《礼》和《乐》。
1.《易》与《春秋》
《易》的成书,本是源于八卦,犹如文字有会意、有假借,古人卜卦、卜问吉凶则是拆字占卦,系辞就像寺庙中卜问吉凶的诗句。周易出现于殷周之际,这说明周天子能统治天下皆因其天命之故。顾炎武谈及此处时指出:“孔子论《易》,见于《论语》者二章而已,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见《述而》。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见《子路》。”(11)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栾保群点校:《日知录集释》(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45页。顾炎武认为孔子在其《论语》中对周易也有所论及,不过只有上述两章。
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12)张燕婴译注:《论语·述而第十七》,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93页。顾炎武指出:“圣人之所以学《易》者,不过‘庸言庸行’之间,而不在乎图书象数也……记者于夫子学《易》之言而即继之曰:‘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见《论语·述而》。是知夫子平日不言《易》,而其言《诗》、《书》、执礼者,皆言《易》也。”(13)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栾保群点校:《日知录集释》(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45页。顾炎武认为先贤圣人们学习《周易》都是在平常的言行中,而不是只在于图书象数之中……孔子虽然平时不会提及《易》,但是孔子会谈及《诗》、《书》、礼等,其实都是言《易》。说明顾炎武认为此处应该译作“孔子学《易》”,即顾炎武赞成“孔子作《易》”的观点。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14)杨天才译注:《周易·恒卦·九三爻辞》,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79页。子曰:“不占而已矣。”(15)张燕婴译注:《论语·子路第二十二》,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98页。意即,《周易》中记载:“立心勿恒,凶。”(16)杨天才译注:《周易·益卦·上九爻辞》,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226页。古人认为没有恒心是不吉利的,《论语》中这段记录是说南方人有一个说法,没有恒心的人不能做巫医给人卜卦,孔子认为说得很好;《易经》中有一句“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表示没有恒心、不能恒常地坚守自己品德的人,将来或因此蒙受羞辱。孔子表示连恒心、恒德都没有的人也用不着去占卦了。
钱穆考证到,“五十以学易”的“易”,《古论语》写作“易”,但是《鲁论语》写作“亦”,而联系上下的文义,比较得出应是《鲁论语》写作“亦”才是正确的,故而此处不能理解为“孔子五十学《易》”,这与顾炎武的结论大相径庭。钱穆表示:“顾氏谓孔子平日不言《易》是矣,而曰其言《诗》、《书》执礼者皆言《易》,则不得其意而强说之也。”(17)钱穆:《国学概论》,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6页。至于《十翼》不是孔子所作一事,在钱穆之前已经有了很多论证。钱穆据此总结:“易与孔子无涉也。”(18)钱穆:《国学概论》,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6页。即,钱穆不认同顾炎武“孔子作《易》”的结论,而认为《易》非孔子所作。
孟子言:“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19)万丽华、杨旭译注:《孟子·滕文公下》,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38页。钱穆认为孔子作《春秋》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它不同于孔子的弟子记录其言行的《论语》。钱穆承认孔子所作《春秋》在历史文化、政治文化、民族精神等方面都有着显著的价值。章太炎也认为,比起《春秋》,《尚书》则显得有所缺漏、简省,并且还没有年次之分:“然《春秋》所以独贵者,自仲尼以上,《尚书》则阔略无年次,百国《春秋》之志,复散乱不循凡例”。(20)章太炎:《章太炎全集:国故论衡先校本、校定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34页。至于后来的《春秋》三传的门派之争,钱穆对此则采取了批评的态度,认为《春秋》三传皆不具备孔子《春秋》的精神,有失于孔子的本义:“捨后世三传之纷纷,则孔子春秋之精神,亦若是而止耳”。(21)钱穆:《国学概论》,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12页。
2.《诗》与《书》
《论语》中记载:“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22)张燕婴译注:《论语·述而第十八》,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93页。于是《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并无问题。但是此处并没有证据表明孔子删减《诗》《书》的内容。而且现今流传下来的《诗》《书》,都是秦焚书之后的,也不是孔子曾经咏诵过的古本。钱穆还进一步表明:“纵复睹孔门之旧,而《书》乃当时之官书,《诗》乃昔人之歌咏,亦不足为万世之经典,千祀之常法也。”(23)钱穆:《国学概论》,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16页。即便是孔子曾经咏诵过的古本,当时的《书》乃是那时的官书,《诗》也不过是过去百姓的歌咏,不过是那个时代特有的产物罢了,已不足以当成万世经典,不能被当作万世不变的法则。故而,钱穆认为并无证据表明《诗》《书》乃孔子作。
3.《礼》与《乐》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礼》“自孔子时而不具,至秦大坏”。(24)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61页。意即,《礼》在孔子时还没有,而到了秦焚书时已经崩坏。钱穆认为,孔子当时虽然没有《礼》可观,但是孔子言礼,深明礼义,且孔子之礼不是浅显地体现在言语中,而是著于行事中。至于《汉书》中所说的礼经,也就是现在的《仪礼》十七篇。至于春秋时期的列国国君大夫之礼的记载,在其中未有一言。钱穆指出:“且其书与孔子之意多违,盖出周末战国之际。”(25)钱穆:《国学概论》,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18页。意即,钱穆认为《礼》非孔子作,且很有可能出自周末战国之际。
至于《乐》,本没有经。“乐”者应时而变,固孔子不可能作《乐》。
综上所述,钱穆得出结论:“孔子以前未尝有‘六经’,孔子亦未尝造‘六经’。言孔子者,固不必专一注重于后世之所谓‘六经’也”。(26)钱穆:《国学概论》,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19页。
(二)古籍的分类与“经”称谓的沿革
1.古籍的分类
钱穆通过考证古籍的分类,进一步明确了孔子与“六经”无关。钱穆考证到,《国语·楚语》中记载,申叔时在论教太子时,详细地列举了古代典籍为《春秋》《世》《诗》《礼》《乐》《令》《语》《故志》《训典》九类。钱穆将这九类古籍,直接归为《书》《诗》二类。其中,《春秋》《世》《礼》《令》《语》《故志》《训典》属于《书》一类,只有《诗》《乐》属于《诗》一类。钱穆指出:“《诗》《书》言其体,‘礼乐’言其用。”(27)钱穆:《国学概论》,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21页。这样的体用关系即可表明,《诗》与《书》重在知识上,而礼、乐却是重在行与实践上,而非言策。
此外,礼有先例之礼、成文之礼。先例之礼本是来源于历史,也就是《春秋》《世》《语》《故志》《训典》这类《书》。而成文之礼则是来源于制度,也就是《礼》《令》这类。因为前人都尊古笃旧,制成的法令遗制都要世代遵守不可更替,这便是所谓的礼。离开礼就没有法令可谈,离开礼也就没有历史。因此,古人将历史、礼、法令看成一个整体。同样,随着历史的更迭,制定了新例,礼法也会随之更改。前人也许因为一时的特殊情况,会开创一项新例,后人会学习沿用下来成为他们礼法制度。一旦违反了礼,也就是违反了法,历史就是制度,而《诗》和《乐》本就属于礼制之中。故而,古人们所学的学问若用一个字来概括便是“礼”。因此,钱穆指出,“古人言学,皆指‘《诗》《书》礼乐’。此即求之《论语》可证”。(28)钱穆:《国学概论》,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22页。所以并没有后人所说的“五经”“六经”。
后来添加孔子的《春秋》与《诗》《书》《礼》《乐》合而成五,又增添卜筮之《易》为六,将其合称为“六经”,并不是孔子以前就有的。《论语》和《孟子》中并没有提到《春秋》《诗》《书》《礼》《乐》与《易》。古人学问本为《诗》《书》《礼》《乐》,至于《春秋》和《易》,则是汉代儒学家添加到“经”里的。钱穆从先秦史逐字逐句考证,驳斥今文经学家的观点,复原了孔子之前的历史古籍的类别,为后世经学家们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2.“经”的称谓
据钱穆考证,“经”这一称谓是仿照了《墨子》,《墨子》分上下篇经。儒家孔子、孟子均无言《春秋》《诗》《书》《礼》《乐》《易》为“经”者。《孟子》中虽有“经”的字眼,如“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慝矣”,(29)万丽华、杨旭译注:《孟子·尽心下》,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341页。但是此“经”非彼经,孟子所云之“经”乃指法统正道。钱穆认为,“荀子儒家,始称‘经’,始以《春秋》与《诗》、《书》、礼、乐连称。然尤不知‘六经’,又不以《易》为‘经’。”(30)钱穆:《国学概论》,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23页。儒家到了荀子才提到“经”。
“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31)安小兰译注:《荀子·劝学》,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1页。荀子认为,学习要从诵读钻研“经”(此处指的是《诗》《书》)开始入手,再到诵读研究《礼》结束。不难看出,在这里荀子只把《诗》《书》称之为《经》,并与《礼》并列。在这里并没有提到所谓的“六经”。荀子又说:“《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32)安小兰译注:《荀子·劝学》,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1页。在此,荀子将《礼》《乐》《诗》《书》《春秋》并举,却并未提及卜筮的《易》,这说明荀子尚不知有“六经”,否则不会只谈到《礼》《乐》《诗》《书》《春秋》便认为它们已经将天地间的大学问都囊括其中了。足见,荀子之时并无“六经”。
至秦始皇焚书坑儒之时,所焚之书乃是“诗书百家语”,《易》作为卜筮之书则不在所焚行列。被焚之所谓“诗书”,皆为孔子、墨子之前之典册;“百家语”则指儒家、墨家以下私撰之册。秦朝时人人皆知《易》乃卜筮之说,非儒家之经典。此外,《孟子》七篇未言及《易》,荀子只云《礼》《乐》《诗》《书》《春秋》,却独独未言及《易》。将《易》与《诗》《书》《礼》《乐》《春秋》并列者,应为汉时将儒、道、阴阳合糅之人。
钱穆进一步提出,汉代儒学家也未言及“六经”。《淮南子·主术训》将《易》与《诗》《书》《礼》《乐》《春秋》统称为“六艺”;贾谊所作《新书》亦称其为“六艺”;司马谈认为先秦时期不存在《易传》;司马迁也将《易》和《诗》《书》《礼》《乐》《春秋》称之为“六艺”。总之,没有称其为“六经”者。钱穆认为,自墨家开始才将典册称为“经”,而后世沿用此称谓。至于“六经”之称谓,则由《庄子·天下篇》首次提及。此后,《汉书·王莽传》中亦有“六经”之说。
孔子与“经”的关系的争论自汉代便有,但因史料所限,一直未能形成统一的观点。学界对孔子与“经”的关系,存有多种不同的观点。钱穆考证的是古籍的分类与“经”的称谓沿革,他并不否认“经”作为古代典籍的存在。钱穆只是想表达,在先秦时期,无论是孔子之前还是之后,都未曾有过将儒家典籍称作“经”的情况,被称为“经”的也并非儒家典籍。且当时之“经”与其后期汉代之“经”亦非同一内容。钱穆在这一问题上没有受到之前传统经学家研究范式的束缚,而是选择从史学的角度、用历史发展的观点考证古籍的分类与“经”的称谓沿革之间的关系,将经学的研究还原到史学文献研究之中,为后世的经学研究开辟了另一种路径,这对后世经学研究的深入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二、钱穆对经学发展的五个分期
前文已指出,钱穆认为先秦时期的儒家典籍并不被称为“经”,将儒家之典籍称为“经”乃是汉代儒学家之所为。我国汉代应该是经学的奠基时期。自汉代以来经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历程。钱穆将这一漫长的历程按朝代更替顺序划分为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和清代五个时期,并分别阐述了每个历史时期经学发展的不同特点、精神及其得失。
(一)两汉时期学以致用之经学
钱穆认为,“直到西汉初年,经学传统始正式成立”。(33)钱穆:《中国学术通义》,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7页。西汉的经学家们,在最初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兼通“五经”的。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立《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博士之后,经学的研究才得以繁荣起来。到了汉宣帝时期,经学家们开始渐渐走上专治其中一经的精细研究道路。汉代的“今文博士”便是属于这一类的经学家。至东汉古文经学兴起,经学家又渐重回兼通诸经之旧路。
钱穆认为,两汉经学研究注重政治上的学以致用。“一、当时的政治理论,不依托在神权或君权上,而别有一套合于人文社会历史演进的大理论。此套理论,皆从古代经书中推演出来,即是从周公、孔子的教训中推衍出来。二、政治措施不倚重在当朝之法律,或帝王宰相大臣等之私人意见,而必根据在古经书中推衍出来的理论上作决夺。”(34)钱穆:《中国学术通义》,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7页。这也直接表明了经学在两汉时期的独特贡献。中国历史上以文治国的政治传统,也是在两汉时期奠定基础的。
两汉时期,把修读经学之人称为“儒”或“儒生”,后来修读经学的儒者皆以儒家为正统,以“修身治国平天下”为其人生主要目标。在汉代,孔子被誉为“素王”,并称孔子是“为汉制法”。儒家此举概因面对大一统政治初创,王权借机扩张,试图抬高孔子与经学,冀此限制和牵制王权,进而渐次形成能够接受儒家思想指导的王权国家。这是汉代儒家的一大功绩。
汉代儒家认为,孔子上承周公之学,下启儒家思想。东汉班固所著《汉书·艺文志》据刘向、刘歆二人之《七略》,将《七略》分为“六艺”和“诸子”两列,并将儒家位列诸子之首,孔子之《论语》被列入《六艺略》中,孔子却未被列入儒家。汉“六艺”乃“王官之学”,儒家仅为“百家之言”之一。汉代儒学将孔子与周公并举、将五经尊为“王官之学”乃是两汉时期经学的主要发展特点。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训诂疏义之经学
不少经学家认为,经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整体上呈现出一种衰弱的景象,但是钱穆并不完全赞同这一观点。钱穆认为,尽管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在政治上逐渐失去了两汉时期“王官之学”的地位,但这只能说是儒学之衰。与之相反,经学研究在此时还是有了很大的发展,后来中国经学之一大集成《十三经注疏》中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完成的。比如,魏时王弼、晋时韩康伯注《易经》,晋时杜预集解《左传》,晋时范宁集解《榖梁》,晋时郭璞注《尔雅》,魏时何晏集解《论语》等。当时的经学家们又创立了“义疏之学”,现在还存有梁时黄侃的《论语义疏》。因此,在《十三经注疏》中有关“注”的部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已经完成了一半,而“疏”的部分则完成了十之八九。
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朝在建制上大致承袭了两汉时期,并依然以儒家经学的礼法维系着门第等级,但是自西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佛教思想得到快速传播,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动荡,佛、道思想开始盛行,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传统儒学,并发展成儒、道、佛几乎三足鼎立之势。钱穆指出:“经学上义疏之学,也与当时佛教中人解释佛教经典的工作有关系。”(35)钱穆:《中国学术通义》,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8页。钱穆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训诂义疏之学的兴起与当时佛教徒阐释佛教经典有一定的关系。钱穆还强调,同一时期南北的经学也有所不同,尤其表现在礼学方面。南方门第等级制度盛行,各个姓氏家族在一定程度上依靠丧服识别维系门第和亲疏关系,这使得南方格外重视《仪礼·丧服》。另外,南方也相对重文轻武,重视王宫朝廷的礼乐制度,认为礼乐可以激发民族自信心,从而弥补武力不足的缺陷。然而到了唐代,随着门第的逐渐消失,丧服制度也渐渐不为人们所重视。钱穆认为,相比较而言,北朝虽然也重礼,但“北人研究主要尤重《周官》”。(36)钱穆:《中国学术通义》,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65页。钱穆指出,由于北方民族血统多样,胡汉混杂,政治不上轨道,故而《周官》就成了北朝经生们试图改进政治体制的一项重要依据,并且这一特点对后期隋唐的政治体制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尽管魏晋南北朝时期多讲究“出世”的佛学或庄老之学,但在钱穆看来,“论中国文化存亡绝续之命脉所系,则主要仍在此辈儒生手中”。(37)钱穆:《中国学术通义》,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66页。
(三)隋唐时期科举考试之经学
钱穆指出,隋唐时期的经学总体上延续了魏晋南北朝的经学发展之路,并与佛、道合流。到了唐代,经学家将魏晋南北朝各家义疏之学加以糅合,孔颖达等作《五经正义》,后来《五经正义》又作为唐代科举考试的标准。值得一提的是,唐代儒学与文学会合,使唐代科举考试更加重视文辞诗赋,在人生哲理方面,人们则更加倾向佛学。“唐代经学,依然是在衰微时代,并可说更比不上魏晋南北朝。”(38)钱穆:《中国学术通义》,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8页。但是钱穆强调,由于唐代政治上的稳定和经济上的繁荣发达,远远超过南北朝时期,人们讨论政治依靠经学,因此经学的地位在唐代依旧重要。然而,人们对政治与人生的选择却走向两条道路,“从事政治事业,在人生理想中只认为是次要者,若论人生最高向往及其终极理想,则不在孔子与五经,而必从佛教经典中去探求”。(39)钱穆:《中国学术通义》,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9页。
(四)宋元明时期之“新经学”
宋代兴起的“新儒学”,主要目的在于将先前儒家思想家的人生哲理重新发扬、传承和光大,再使其与国家政治思想结合起来,并希望依靠孔子的哲学思想来排斥佛教思想。而有了新儒学,自然也就有了“新经学”。宋代儒学家有很多都是新经学的运动倡导者,主要代表人物有北宋的王安石和南宋的朱熹。
钱穆指出,王安石意识到唐代的科举考试侧重于诗词文学,于是他重新将其重点调整到经学方面。此外,王安石还试图将六朝之后的经学义疏简单化,只举《诗》《书》与《周官》三经作为新注,这在当时被称作《三经新义》,也被称作“王氏新学”。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王氏新学”的内容并不被当时的新儒家所认可。新儒家认为,王安石之新学对古代儒家人生最高理想的阐释不足,重视不够,在当时的新儒家看来,这样的“王氏新学”并不能与佛学抗衡,故而后来又有了以关学、洛学为代表的理学四大派的出现。
虽然北宋的理学家创立了一套新的理学思想,并试图以此与佛学抗争,但是钱穆认为“北宋理学家未能完成一套新的经学来直接先秦与两汉之旧传统”。(40)钱穆:《中国学术通义》,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9页。直到南宋朱熹才承接了先秦与两汉时期的经学旧传统,完成了一套新经学理论,才“在中国经学史上掀起了绝大波澜”。(41)钱穆:《中国学术通义》,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9页。朱熹新作了《诗》和《易》的注释,又另择《论语》《大学》《孟子》《中庸》为“四书”,以此取代此前《诗》《书》《礼》《易》《春秋》五经的地位。
钱穆考证到,朱熹所作“四书”新注,在其身死百年、南宋亦亡国后,还传到了北方,并且“在当时社会上已有了广遍深厚的基础”。(42)钱穆:《中国学术通义》,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10页。元代也承认并接受朱熹的“四书”,将其确定为元代科举考试的新标准。明朝在这方面基本承袭元制,此后直到清末,都没有大的改变。
(五)清朝时期的经学与“小学”
钱穆指出:“明亡后,学术重心又变。”(43)钱穆:《中国学术通义》,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11页。明朝灭亡后,清朝的学术重心也发生了改变。钱穆在此指出了清代经学所经历的几次转变:
清朝初期的儒学家希望将经学回到两汉以来的旧经学,拒斥两宋以来的新经学传统,不再承袭宋时过分注重的个人心性修养方面的理论,而是使其回归到两汉以来注重“学以致用”的政治传统。顾炎武则是这一经学复归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
后来,由于清朝统治者的身份以及随之带来的政治高压、“文字狱”等,使清代儒学者难以施展其政治抱负,逐渐厌恶清朝统治阶级,继而厌恶科举制度,最后发展到反对宋学,甚至反对朱熹。同样地,清代的经学也逐渐发展成了只重视校勘、训诂、声韵、考据之“小学”。(44)小学即指研究文字字形、字义及字音的学问,包括文字学、声韵学及训诂学等。但是钱穆在此强调,“他们虽自称为汉学,其实和两汉经学精神甚不同”。(45)钱穆:《中国学术通义》,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12页。可以说,两汉经学注重的是政治上“学以致用”,而清代经学则专注于对于儒家古典的校勘、训诂、考证和整理,二者大为不同。到了道光、咸丰时期,由于清朝政权的逐渐衰落,儒学者又开始注重政治上“入世”和有所作为。这一时期的经学研究又以龚自珍、魏源等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学派的崛起为代表。及至清末废科举,经学亦中绝。
从上述五个历史阶段来看,经学在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体系历久传承中具有重要意义。经学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朝代的更迭、社会的变革、政治统治思想的转换,也在发生演化、更迭和发展。我们可以根据经学发展过程中的明显转变,将之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汉唐时期,也就是“五经”时期;第二阶段是宋元明清时期,也就是“四书”时期。前期经学注重“学以致用”,强调经学的政治功能,强调“治国平天下”,同时兼顾考据之学与义理之学。后期新经学注重“修身”,重心逐渐从政治思想倾斜向了教育思想、文学思想等方面,新经学与旧经学进行了新的融合,以“四书”取代“五经”,这一明显的更迭标志着经学发展史上经历了一次重大变革。
三、钱穆经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钱穆认为,中国此下要复兴新儒家与新经学,至少要先了解中国以往经学的大传统,才能了解中国的文化与中国的学术。中国人爱说“通经致用”,中国人看重经学,认为人们可以通过经学塑造自己,再由此去贡献社会,而所贡献的对象则是“政治”和“教育”。因此,中国经学一向被看作“做人”的学问,一种“成圣”之学。中国经学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乃是对自然与人生知识的会通合一,并由此探寻出实用的学问,贡献于社会。
钱穆概括了中国经学的主要精神:其一,天人合一的观念。钱穆认为,天人合一的观念是宇宙真理与人生真理合一的一种崇高信仰,这一观念在“五经”之中最为显著,也最受重视,经学也成了天人合一信仰的主要渊源。其二,经学的精神是一种以历史为基础的人文精神。这种以历史为基础的人文精神使学者能够深切认识到人类历史的演进是有着其内在的一以贯之的真理的。我们在历史繁复演变的过程之中可以举例出很多可以代表这种真理的人物、事业及其相关的教训,使我们保持尊敬、信任与向往的心情。其三,经学中蕴含的一切学术宗旨,是可以创造出一定的人物与时代来为这一真理进行实证的。其四,一切学术都应在这最高真理之下会通合一,不应有什么过分的门户壁垒。这四点不仅是钱穆指出的中国经学的主要精神,也可以说是中国儒家精神与理想之所在。
客观地说,钱穆对于经学的渊源与发展史的考察是十分详细且包罗万象的。不论是考据方面,还是义理方面,甚至政治思想方面、文学方面、心性修养方面等都包含其中,较为全面。这种包容的格局突破了以往只以今文经与古文经流变为线索梳理经学史的传统经学研究方法,对后世进行经学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钱穆还注意到,现如今的经学早已不复往日地位与辉煌,不论是政治理论方面还是人生信仰方面,都失去了与以往经学的关联,经学也失去了在政治理论方面和人们信仰方面的中心地位。尽管如此,钱穆依然认为,倘若忽略经学的重要性,我们就会失去自己文化传统的历史血脉。
钱穆对传统经学渊源的考证与经学发展史的研究,体现其不论门户只求会通的学术特质,站在以史治经的立场上,将考据、义理与辞章相结合,将经学家们从旧有的研究方法中解放出来,为中国传统学术的研究开启了新的学术风气。
四、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46)《(授权发布)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0/14/c_1116825558.htm。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自知是我们树立文化自信的必然要求,经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势必不能忽略经学的重要地位。国学大师钱穆对经学乃至其他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在当下依然具有重要意义。诚然,不同时代的研究都有其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我们不能原封照搬,而要根据新时代的文化精神对其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和发展,这也是我们今天探析钱穆的经学研究甚至其他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