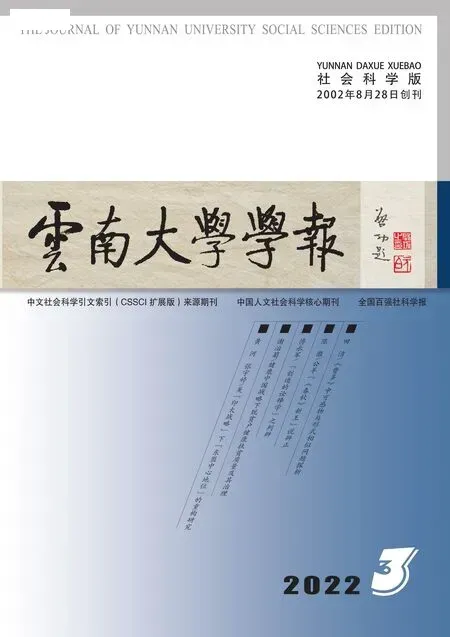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学术史考察及其新时代的范式转换
2022-11-23李艳峰
李艳峰
[昆明学院,昆明 650214]
对于民族现象进行叙述、研究是我国自古以来就有的文化传统,以之为关照对象的中国民族史研究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各自的时代面貌和鲜明特点,其结构范式表达了与当时历史阶段相适应的书写意图和叙述重点,亦关涉中华民族的凝聚品质与建设质量。中国共产党“十八大”召开后“新时代”的到来,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面临一个迥异于前的时局形势。为此,以习近平“四个共同”重要论述(1)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提出中国各民族在“疆域”“历史”“文化”“精神”方面的“四个共同”,详后。为方法论指导,实现中国民族史研究的范式转换,多角度真实还原中国各民族“四个共同”的历史发展主线,发挥范式优化对于深化民族发展规律认知、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质量的积极促进作用,是新时代中国民族史研究者需要认真面对的。
一、王朝时期的中国民族史研究与“天下观”统摄下的华夷共同体
在古代中国,有关民族现象的记载最早见于先秦时期的甲骨文、金文、诸子散文等,而其主体部分则载录于《二十四史》、非汉世居地域的方志,以及相关舆地著作、类书、杂史、游记、笔记等多种古籍构成的文献体系当中。相关舆地著作、类书等固然也都集中体现了民族史叙述的为文意识,反映了当时的文化观念和社会风貌,但是相比前两类较为全面、系统的民族史叙述而言,更多表现出风格上的片段、点滴特征,且总体上影响不彰,所以我们主要讨论前两种文献类型。
司马迁《史记》“四裔传”(2)有关“蛮夷”的记载也大量散见于其人物纪传、各种相关志表等。之后,各种史书便有了对民族现象进行叙述的著史习惯。因为所载“蛮夷”群类齐全、历史完整、谱系赅备,后世所谓二十四正史成为承载王朝时期中国民族史叙述系统最基本、最主要的文献。(3)对于二十四正史民族撰述的研究,具有代表性的学者主要有王文光、汪高鑫等诸位。王文光等《先秦、秦汉时期的东夷研究——以〈后汉书·东夷列传〉为中心》(《学术探索》2016年第12期)和王文光等《汉代边疆民族与国家发展关系研究——以民族历史文本书写的视角》(《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9年第4期)二文深刻论述了《史记》《汉书》《后汉书》所见各民族群体对于统一多民族中国发展内涵的巨大贡献。汪高鑫《二十四史的民族史撰述研究》(黄山书社,2016年)一书的相关章节,从传统历史学、史学思想层面梳理了二十四正史民族史撰述对于统一多民族中国历史构建的记载,分析了其中的历史文化认同意识。相关论述也见于此前其系列论文,如《两汉正史民族史撰述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求是学刊》2012年第2期)、《二十四史民族史撰述与中国多民族国家历史的构建》(《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以区域史地、地方社会为主要内容的方志也深受史书影响,辟有专卷或详或略地记载当地的殊风异俗,内容丰富多样、炫彩斑斓,(4)方志对此着力颇勤,亦多辗转猎奇、舛误相累的情况。进一步完备了正史民族传的叙述策略。例如东晋常璩所撰《华阳国志》就参考了《汉书》《三国志》等历史著作,为“处邛、笮、五夷之表,不毛闽濮之乡”的“南中”立有专传,并附志“交趾之蛮”;(5)〔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第3、468页。唐人樊绰于唐懿宗咸通年间所作《云南志》亦载有“蛮事”三卷,编次于全书之尾;南宋范成大成书于南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的《桂海虞衡志》列有“志蛮”专条于文后;明清之后各边省通志更是专记“蛮夷种人”之事,并将之列于志末。
王朝时期的民族史叙述系统并不十分严格,有时显得凌乱杂芜。如《新唐书·南蛮传下》记录了南方、西南方的蛮僚夷类,行文顺序似显混乱,旨义不甚清晰,所涉地域的排列也往来飘忽,跨度很大。加之以古文言写就,在文本的分析解读方面容易引起分歧。在内容结构上,其基本按照空间方位(包括自然位置、行政区划、分布四至)来撰写,可以分为社会发展和关系往来两大部分。社会发展部分所占篇幅一般很小,包括族称由来、社会组织、自然物产、生态环境、生计方式、语言性情、支系分部、生活俗尚(如饮食居住、服饰艺术、日常器用、丧葬婚俗、宗教信仰)、农业生产、手工商贸等;间有社会变迁(包括分化、融合、迁徙流动)之内容。关系往来部分则往往占据大量篇幅,主要是对于王朝统治的服叛来去以及相应招捕征抚的军政关系,例如归附内属、纳贡朝觐、反抗斗争、军事弹压;间有夷人不同系部之间的政治、军事争斗,以及王朝的羁縻治理、郡县设置、行政措施、赋税征收等。对于有持续影响、甚至一度建有地方政权的“蛮夷”,如秦汉时期《史记》《汉书》《后汉书》中的南越、匈奴、西域,新旧《唐书》中的突厥、南诏、吐蕃,《宋史》中的大理等,则重点记述其先祖所自,尤其是与华夏同源共祖的深远历史渊源,以及君主酋领的传承世系,注重记载其起源、发展与兴衰。
《二十四史》“四裔传”和众方志的相关叙述自古相延、代有增益,基本以对于正统王朝有军政意义作为民族群体入史、存传之标准,以文化差异为据对其进行分类、指称,总体而言叙述了以中原华夏为中心的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并统称为“天下”“五方之民”;多站在“非我族类”的他观视角来记录,杂有猎奇、夸饰的成分,多表层观感的采撷展示,少内里深入的因果探究。古代这种民族史叙述系统认为四方“夷戎蛮狄”是王朝历史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将自身置于王朝历史书写体系的“末处”,是大一统王朝文化建设的重点领域,其认知基点和阐述中心为所谓的正统王朝,为王朝政治服务,(6)辽、金、元、清时期的民族史与王朝史很大程度上是重合的。行文书写上尤其强调朝廷对于边疆各民族群体的辖领和治理。
王朝视野下的民族史叙述系统生动描绘了统一多民族王朝历史发展的时代风貌,明确表达了王朝国家“天下一统”的社会格局与历史发展大势;其结构和特点,与中国皇权—官僚的政治治理体系、商周“五服”“九服”之说以来华夷五方的等第制度、(7)李艳峰等:《商周时期华夏族的民族观、地理观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天下观”(8)在中国古人的世界观里,“天下”是一个兼有政治、地理和哲学多重意涵的词语,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别。狭义的天下主要指皇帝政令可以直接实施的范围,广义天下则指分布有华夏和非华夏的全部空间,即“普天之下”。统摄下“华夷之辨”的文化心理相辅相成,大民族主义为其显著特点。这无疑决定了其对于自在中华民族共同体(9)根据王文光的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虽然提出的时间不长,但是‘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孕育却是从商周时期就开始的。从多民族中国发展历史长时段的角度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具有‘自在’与‘自觉’两个阶段性特征。”参见王文光等《二十四史的边疆民族记述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论纲》,《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凝聚品质与建设质量的理论效能,(10)我们认为一种社会理论的表达效能主要可以有以下两个方面:对于各种社会现象所蕴含的人类发展真相、规律的揭示和呈现程度,以及对于当下人类社会走向进步的引领和促进程度,即经世致用的功能价值。这一问题需要到下个历史时期来推进并完善。
二、近代的中国民族史研究与中华现代国家构建
欧洲殖民主义浪潮之下,曾经一直自视居于“天下”中心位置的“天朝上国”在近代开始成为新世界的列国之一,而共同抵抗西方列强的斗争也是参照“他者”再塑“我者”形象的过程,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开始走向自觉、自为。而传统“华夷之辨”视野下以“蛮夷”为对象的叙述系统的概念、立意与结构范式显然不能适应“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大背景下“统一多民族中国”国家建设的时代需要。如何呈现由历史和文化延续性形成的各民族群体的过往经历,凝聚曾经的华夷五方之民,使之成为与“国家”相匹配的一个“民族(共同体)”,实现由“王朝”向中华现代国家转型,从而摆脱时代嬗变所带来的理论困境和现实危局,是近代中国知识精英面临的重大理论课题。(11)参与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梁启超、李济、王桐龄、吕思勉、林惠祥及范文澜、吕振羽等。参见李济:《中国民族的形成》,美国:哈佛大学,1920-1923年;王桐龄:《中国民族史》(上编),北平:文化学社,1928年;吕思勉:《中国民族史》,上海:世界书局,1934年;宋文炳:《中国民族史》,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缪凤林:《中国民族史》,南京:国立中央大学,1935年;吕思勉:《中国民族演进史》,上海:亚细亚书局,1935年;林惠祥:《中国民族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吕振羽:《中国民族简史》,哈尔滨:光华书店,1948年,等。
近代梁启超的相关研究无疑是具有开创性和奠基性的,使得此前被置于王朝历史书写体系“末处”的“蛮夷”载录开始成为一门具有现代性的独立学科。梁启超不仅引入日制汉词“民族”,(12)1899年梁启超《东籍月旦》一文使用了具有现代意义的“民族”一词。他在评介当时有影响的世界史著作时称其“于民族之变迁,社会之情状,政治之异同得失……乃能言之详尽焉”。又云“著最近世史者,往往专叙其民族争竞变迁,政策之烦扰错杂”。参见梁启超《东籍月旦》,收于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另外,郝时远对“民族”一词由来的观点与此稍有不同,参见郝时远《中文“民族”一词源流考辨》,《民族研究》2004年第6期。提出“中华民族”概念,(13)1901年梁启超《中国史叙论》一文首次提出“中国民族”概念,参见梁启超《中国史叙论》,收于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页。1902年梁启超在其《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首次提出“中华民族”一称:“齐,海国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惟齐。”见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收于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1页。在梁启超、孙中山等人的使用实践中,“中华民族”的内涵和外延有一个不断完善发展的过程。一百多年后的2018年,“中华民族”表述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特别是针对以日人桑原骘藏《中等东洋史》(14)〔日〕桑原骘藏著:《东洋史要》,樊炳清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08年。桑原骘藏于1898年出版《中等东洋史》,中译本名为《东洋史要》。等为代表的、否认王朝中国“华夷一体”不可分割的共同体属性、有意建构出中华大地上多“民族”竞争的历史景象、从而否定中国历史主体性和连续性的研究倾向,先后提出将“混合”“同化”作为理解历史上中国民族的线索。(15)“混合”见于1906年梁启超所作《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收于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4页。“同化”见于1922年梁启超所作《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收于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1页。关于近代中国民族史研究中的民族关系这个重大理论问题,顾颉刚、费孝通另有“中华民族是一个”还是“多元并存”的争论(1939年顾颉刚和费孝通在《益世报·边疆周刊》发表多篇文章进行讨论),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书又提出“中华民族宗族论”之谬说,参见蒋介石:《中国之命运》,重庆:正中书局,1943年。1922年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一文提出了较为系统的中国民族史研究的范式框架,将春秋中期的民族群体分为“诸夏”“荆吴”“东夷”“苗蛮”“百越”“氐羌”“群狄”“群貊”等八组,详细论述了各组所包含的多个民族单元的起源与历史流变,并明确了居处于“现在中国境内及边徼”的中华、蒙古、突厥、东胡、氐羌、蛮越等六个族别。(16)参见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收于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6-9页。
1928年王桐龄《中国民族史》(上编)一书秉承梁启超“同化”而非“竞争”“嬗代”之思想,又将其《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一文的思想理路具体化,以所分中国历史之八期为结构框架,逐章叙述每个时期汉族群体同化他族的方式与成果。随之罗香林发表了一篇书评,对于王著“喜慰”之际,更“兴悲”有三,其第一条即源于“重汉族,轻四夷之传统观念”的“编法之不善”。并提出了关于中国民族史研究的结构主张:“第一当探究各族之来源。一元乎,抑多元乎?必为之审慎辨证。……其次则宜于汉满蒙回藏苗诸族,各为专传,一以探究其各代递演嬗变之迹,一以探讨其盛衰存亡之理,务必使各族之个性一一活现于卷中。凡此二端为民族史中之纵的叙述。……又次,则当从事横的叙述。……就过去事迹,划分若干时期,择各时期中,各民族间之要事,汇而述之,以见其交互之关系。”(17)罗元一:《试评王著中国民族史》,《清华周刊》1928年第30卷之第5期。在继续坚持“混合”“同化”的民族关系处理原则下,1934—1936年间吕思勉、宋文炳、林惠祥各作一部题名为《中国民族史》的通史体民族史论著,之后的1948年吕振羽又做《中国民族简史》一书,他们均以历史分期和民族类别为结构框架,采用“各为专传”的体例形式,分章节叙述每个民族群体的历史渊源、演化流变、社会发展、关系往来。这与罗香林所提出的“纵”“横”结合、以“纵”为主的民族史研究范式基本一致。还有,1936年郭维屏编著出版了本意用作中央军校成都分校政治课程教材的小书《中华民族发展史》,除赅备以上特点外,此书特以“中华民族”为意,并增以结构上的“地理区域”一项,述其发展壮大,(18)参见郭维屏:《中华民族发展史》,成都:球新印刷厂,1936年。该书编排上贯彻民族“大混合”主张,目的是使国人“对中华民族有个整个的概念……因而能更有效的努力于中华民族的复兴运动”。参见该书前言各序及“编者的话”。很值得注意。
近代对于王朝时期民族现象的分析研究,开始体现出民族平等和民族交融的为史原则,注意开掘、揭示出中国统一多民族格局形成与发展的内在机制和历史逻辑。近代中国民族史研究范式的变化,既是中华现代国家建构的理论需要,更是团结御侮、保种救亡的时局所迫,反映了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自为的历史转变,发挥了重塑自我、凝聚国人的巨大社会作用。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民族史研究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普遍规律性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政府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所揭示的普遍规律与中国民族问题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贯彻民族平等、民族自治的政治原则,持续开展了大规模的民族调查和民族识别工作,(19)参见黄光学等:《中国的民族识别——56个民族的来历》,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年。至1979年最终确认了包括汉族在内的56个民族,确定了若干民族区域自治的行政区划,完成了这一在当时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存在的制度体系安排。而对于由历史和文化延续性而来的56个民族之间的历史交往及其关系定性问题,1960年前后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等人,特别是1981年翁独健、白寿彝等倡议召开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中国民族研究学会联合举办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学术座谈会”等,进行了持续地深入讨论,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民族理论指引下创建了一套自洽的理论体系,并为“统一多民族”新中国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20)王娟:《重建“多民族中国”的历史叙事——20世纪中国民族史观的形成、演变与竞争》,《社会》2021年第1期。需要注意的是,早在1963年方国瑜便强调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21)参见方国瑜:《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学术研究》1963年第9期;潘先林等:《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是现代中华民族建设与认同的基石——方国瑜〈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研究之一》,《思想战线》2019年第2期。尤其是1988年费孝通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22)参见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在民族平等原则下推动了以“中华民族”概念为核心的民族思想继续发展,学术界围绕这一理论展开了广泛而热烈的探讨。(23)参见徐杰舜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研究述评》,《民族研究》2008年第2期。这些大事件都直接影响了这一时期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内容特点和结构范式。
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大规模民族调查基础上,中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编辑出齐了“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以识别后确定的55个少数民族为叙述基点介绍相关情况。《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更是分专册逐个介绍其历史由来和发展演变,主要的叙述结构为族源、族称、历史发展、社会形态、文化艺术、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以及为缔造统一多民族中国所做出的历史贡献。
这一时期的中国民族史研究在理论方法上更加综合细密,在学科开掘上日益全面深入,成果数量庞大、风格多样;遵循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民族发展变化的普遍规律和科学研究的内在逻辑,以现代学科理论为工具、为指导,对于历史上缤纷多彩、繁芜浩瀚的民族材料进行摘引裒聚、归类梳理和分析探究,描绘出包括汉族在内的56个民族丰满充实的历史形象;突出清晰明确的古今演化脉络,重视机制规律的揭示和阐明,强调现代意义的联系和挖掘。在结构上基本以时代分期、地域空间为框架,以一个或者多个民族群体为关照对象。根据对以上要素的选择、裁取程度,可以大体分为四类。一为通史体的民族史研究,以时间上纵贯、地域上兼覆、族别上齐全为显著特点,如江应梁《中国民族史》、王钟翰《中国民族史》、尤中《中华民族发展史》、徐杰舜《中国民族史新编》、田晓岫《中华民族发展史》、王文光《中国民族发展史》等。(24)参见江应樑:《中国民族史》,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年;王钟翰:《中国民族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尤中:《中华民族发展史》,昆明:晨光出版社,2007年;徐杰舜:《中国民族史新编》,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89年;田晓岫:《中华民族发展史》,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王文光:《中国民族发展史》,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年。其中田晓岫《中华民族发展史》以中华民族之名,突出了各民族在文字、科技方面的汇聚、融合。二为断代民族史研究,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的“中国历代民族史”系列,从《先秦民族史》至《清代民族史》共有所分八个历史时期相应的八册等。(25)参见谢寿光:《中国历代民族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三为区域民族史研究,如尤中《云南民族史》《中国西南民族史》、周伟洲《西北民族史研究》、杨建新《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姜维公《中国东北民族史》、杨兆钧《云南回族史》、喇秉德《青海回族史》、吴丕清《河北回族史》、段丽波《中国西南氐羌民族源流史》、李艳峰《中国古代南方僚人源流史》等。(26)参见尤中:《云南民族史》,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尤中:《中国西南民族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周伟洲:《西北民族史研究》,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杨建新:《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姜维公:《中国东北民族史》,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4年;杨兆钧:《云南回族史》,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年;喇秉德等:《青海回族史》,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年;吴丕清:《河北回族史》,北京:民族出版社,2018年;段丽波:《中国西南氐羌民族源流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李艳峰:《中国古代南方僚人源流史》,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等。四为系于“民族”的专题研究,其中尤以关系史和文化史两个方面的影响为著,如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蒋炳钊等《中国东南民族关系史》、龙晓燕等《中国西南民族关系史纲要》、莫俊卿《壮侗语民族历史文化研究》等,另有周伟洲《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开发史》、林永匡等《清代西北民族贸易史》等。(27)参见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蒋炳钊等:《中国东南民族关系史》,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年;龙晓燕等:《中国西南民族关系史纲要》,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莫俊卿:《壮侗语民族历史文化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年;周伟洲:《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开发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林永匡等:《清代西北民族贸易史》,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年,等。
数量众多的现代研究在具体内容的构成上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第一为王朝治理背景,包括羁縻政策、郡县设置、行政措施等;第二为族称、族源;第三为分布;第四为社会发展,包括自然环境、支系分部、生计方式、社会组织、分化流变、迁徙移居、农业、手工业、商业贸易、语言文字、吃穿住用、婚丧俗尚、宗教信仰、艺术审美等;第五为民族关系,包括归附向化、纳贡置藩、服叛抚征,以及“蛮夷”内部不同支系群落间的政治争斗。对于一度建立有地方性民族政权的情况,如汉唐时期的匈奴、南诏,两宋时期的辽、夏、金等,则重点记述其政权首领的世系承替、政治运转、经济生产、风土地理、域内外交往,以及辖境内的各个民族群体等。并且不仅长篇宏论的民族史著作,数量庞大的专题性文章类成果也多遵循以上研究理解和叙述策略。
该阶段的中国民族史研究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认识:以科学研究之名摒弃王朝时期同源共祖的民族史叙述原则,具有强烈而鲜明的族体意识与地域分割特点;无论居今溯古或是以古俯今,均族别清晰、源远流长、演变过程完整,突出了民族识别后各个民族单元的主体性、特殊性;总的来看,对于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整体关注被稀释于“具体而微”层面的各种碎片化研究之中,“中国民族”的“戏份”明显多于“中华民族”。
四、“新时代”中国民族史研究的范式转换与习近平“四个共同”重要论述的提出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召开后,“新时代”的时局论断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将面临一个迥异于前的复杂的内外部发展环境。作为基础性战略资源,将中华民族建设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对于中国胜利实现破局再前进、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意义重大。新时代背景下,随着中国民族实践发展与理论研究深入,作为指导人们观察、理解中国民族历史现象的框架、模式,中国民族史的研究范式也应不断优化,以使中国民族史研究在体现自身时代价值的同时,深化对于中国民族历史结构本质、运动机制的认知,进而体现出其一直以来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2019年9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指出:祖国“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28)参见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9年9月28日第2版。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中国历史实践的“四个共同”重要论述强调了由各族先民联结共生而形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一致性、一体性,体现了当前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国家建设事业的深层需要,为新形势下中国民族史研究的范式转换提供了方向指引,是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后中国民族史研究求突破、有创新必须重点关注并自觉引以为纲的。
为此,秉持中国史家自古以来积极回应时代诉求的理论自觉,以习近平“四个共同”重要论述为方法论指导,发挥民族史研究的范式优化对于深化民族发展规律认知、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质量的积极促进作用,是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民族史研究者需要勇敢面对并认真思考的。
我们认为,新时代中国民族史研究的结构范式需要继续坚持以时间、空间、民族单元为基本的叙述要素,在内容结构上则要以“四个共同”为研究实践的旨趣方向和展开纲要,将中国各民族的“四个共同”历史置于学术研究的聚光灯下,使之成为新时代中国民族史研究的主要议题,坚持围绕“四个共同”来提出问题、组织问题、阐释问题。新范式指导下的中国民族史研究将关注重点由此前单个族体的源流发展、平实的族际联系转向中国各民族“四个共同”的历史内容和脉络过程,通过问题设置、案例择取、策略选配,深刻揭示中国各民族以内在认同和外在凝聚为主要特征的民族共同体属性逐渐萌生并不断增强的历史客观性,深刻揭示中国各民族演化流变过程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内在同一性,充分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历久而来的“大同”之质、“大同”之势。
以习近平“四个共同”重要论述为方法论来指导探讨中国民族史研究范式的转换,重新构建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叙述重点和展开主线,将有助于实现对于中国民族发展规律的认知再深化,将能够促进中国民族史研究的知识创新,实现并促进中国民族史学科的知识增量和创新发展;有助于进一步提高中国民族史研究的理论阐释力、学术传播力和话语影响力,提升新时代中国民族史研究对于现实关照的理论效能。在实践应用层面,对于中国各民族“四个共同”历史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分析探究,将有助于实现对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实体”的地位肯定;通过使相关研究的成果体系成为新时代各族民众理解自身历史的话题资源,实现中华民族共同性、一体性的增进,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凝聚力的不断再生产,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品质和建设质量;有助于我国各民族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并可以通过为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伟大民族实践提供经验参考,助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29)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8月27至28日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概括了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其中“四是必须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特别强调“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参见《人民日报》2021年8月29日第1版。
关于习近平“四个共同”重要论述对于中国民族史研究范式转换的方法论指导价值的核心要义与宏富内涵,笔者将另文专论。
结 语
纵观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学术发展历程,古代对于“蛮夷”的载录被置于王朝历史书写体系的“末处”,其研究范式与“天下观”统摄下的华夷共同体相适应,为王朝的皇权统治服务。近代的中国民族史研究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现代学科,其研究范式与中华现代国家构建、实现从“华夷”到“民族”的话语体系转换相适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中国民族史研究则遵循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所揭示的普遍规律的指引,与实现民族平等、扩大政治参与,维护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相适应,目的是保障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顺利推进。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民族史研究的面貌风格、范式结构都是在一定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具有不同的时代特征和学术使命,但又具有内在的联系性、一致性。贯穿于古今中国民族史研究学术发展历程的共同旨意,是促进团结,维护稳定,建设一个基于认同、具有强大凝聚力的民族共同体,以维护我们这个民族共同体与其赖以生存的物理空间和内外秩序。
“统一多民族”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其过往历史是先人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我们不断进取的力量源泉。与时俱进,积极回应时代诉求,以习近平“四个共同”重要论述为方法论指导,实现中国民族史研究的范式转换,细致勾勒中国各民族“四个共同”的历史发展主线,细致辨明中国各民族“四个共同”的历史内容脉络,充分彰显贯穿其间的民族共同体属性逐渐形成并不断增强的历史客观性,积极助力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既是对于中国民族发展规律认知再深化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新历史时期的时局变化赋予中国民族史研究的时代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