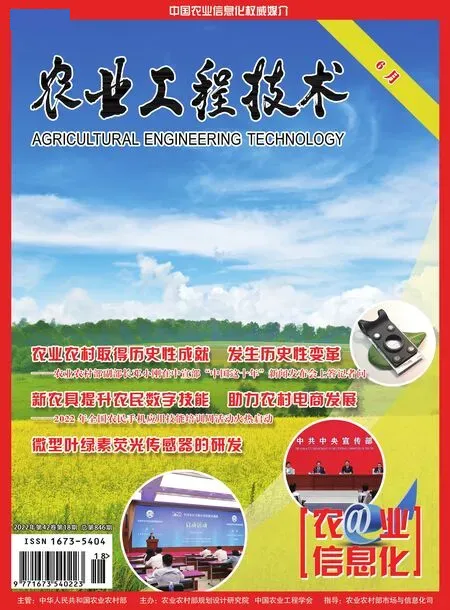贫困村党支部推动乡村振兴战略能力的研究
2022-11-23李文芳
李文芳
(中共迭部县委党校,甘肃 迭部 747400)
“三农”问题始终都是影响甚至决定社会主义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稳定,乃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点、难点、痛点问题。贫困问题更是“三农”问题中的重中之重、难中之难、痛中之痛。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最后阶段,“贫困县”“贫困村”等所映射的“整体性贫困”必将得到解决。但是,造成“整体性贫困”根源性因素是“制度的贫穷和落后”,在反贫困过程中,必须“重新思考公共治理的价值”[1]。也就是说,只要“制度的贫穷和落后”依然存在且“公共治理”的价值和能力不能有效应对和解决这一问题,贫困问题就不能得到彻底解决。这正是在解决“绝对贫困”之后,仍然必须缓解“相对贫困”而继续减贫、反贫的原因所在,也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为何要以“治理有效”为基础的原因所在。
1 贫困村党支部推动乡村振兴战略治理能力提升的困境
1.1 对外连接机制失常:治理体系被简约化
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采取了“超常规举措”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脱贫攻坚战,在“取得决定性进展,创造了中国减贫史上的最好成绩”的同时[2],几乎重置了贫困农村治理的格局。最重要的就是贫困村党支部与政府、基层自治组织、群众之间连接机制的超常规运转。在社会治理中,连接机制“负责社会成员诉求的‘有组织上达’”[3],强调村级治理与国家治理体系的内外联通。在超常规的贫困治理过程中,作为党和政府、基层自治组织、群众之间重要桥梁纽带的贫困村党支部的作用发挥也是“超常规”的,即“失常”的,村党支部几乎成为推动贫困村治理的绝对强势主体,包括治理主体、治理机制在内的整个治理体系都被简约化了,甚至基层党组织被局限在“行政”层面而放弃了治理体系的系统性和整体性。
1.2 对内协调机能失效:主体利益诉求被压制
贫困村党支部的“连接”功能是通过“协调”功能发生作用的。利益协调机能失效,不仅非贫困与贫困群众之间的矛盾疏于解决,而且贫困群众的个人利益也表达不畅,村民的利益诉求实际上受到了极大的压制。在共建共治共享理念下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要求农民的主体地位充分显现。主体利益诉求被压制,农民就无法转化为建设主体,也就无法成为治理主体,基层干部工作量和工作压力徒增,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成效却只会事倍而功半。
2 制约贫困村党支部治理能力提升的三大因素
2.1 “超常规”的治理环境
一是农村常住人口的“老龄化”,青壮劳动力外出务工有的举家进入城镇,60岁以上人口成为贫困村的主要劳动力,“空巢”困境延伸出来的“养老”“赡养”“健康”等问题,与贫困问题相互交织、交融;二是农村社会关系的极端化,包括人口结构的极端化、乡村社会心理的极端化和村民经济结构的极端化,在贫困村利益协调机制失效的现实中,村民利益表达的情绪化与无声化,加速了贫困村社会结构的分化;三是农村居民的综合技能有待提高,不仅包括生存生产技能的提高,而且包括村民对生产发展的态度和情绪的提高。
2.2 “派出性”的治理结构
在“五级书记一起抓”和“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扶贫工作机制下,由组织部统一下派“驻村工作队”,“尽锐出战、精准施策”,使得贫困村治理在面对分散化的社会结构时,能够借助党的组织体系自上而下地层层转导压力,贫困村党支部书记作为“实质性的领路者”,“当选者”则仅仅具有“应然性”的“象征意义”;同时,为了统一调配资源和保持标准尽可能地一致,各项政策的设计和执行落实方案在县级及以上机构已经总体完成,且规范性强、约束力大,贫困村甚至乡镇都没有很大的自主裁量权。
2.3 “行政性”的治理机制
新中国成立之后,地方自治权威就已经“逐渐转为服务于国家目标”的角色,开始了为“民服务转化的进程”[4]。超常规的脱贫攻坚战中的超常规贫困治理显然加速了这一过程,不仅触及甚至改变了原有的贫困村治理基础框架,而且“基层治理者的权力基础”逐渐转变为“基层党组织为民服务体系建设”[5],二者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被行政化了的压力关系所取代。基层权力结构从服务自治和服务大众相互补充、相互依赖中脱离而转向服务于大众时,其利益倾向也将服务于主体的利益实现而非基层群众的利益实现。
3 贫困村党支部提升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治理能力的路径
3.1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夯实治理基础
当前,脱贫攻坚战已全面完成,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使命在肩、任务在前,这就要求党员干部必须以奋发有为、勇往直前的斗争精神,主动聚焦乡村发展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首先,立足县域、依托脱贫政策落实稳定化,综合评判政策落实过程中的问题、短板,厘清问题体制原因和短板制约因素,平衡措施针对性、改进策略性、机制系统性,强化政策主体部门协同能力;其次,抓稳抓牢、高质量突破剩余脱贫攻坚任务,尤其关注“三保障”问题,扎实做好“控辍保学”、乡村医疗服务、农村危旧房改造、特殊困难群体(老年人、患病者、残疾人)社会保障等工作;再次,克服疫情、加快扶贫工程的复工复产复能,稳定受疫情影响的贫困劳动力群体情绪,创造性保障贫困劳动力群体务工就业。
3.2 加强基层民主法治,创新治理机制
首先,增强乡村干部法治观念、法治为民意识,实现民主自治与依法治理互助互进,强调自治的本质就是民主治理,民主治理的基础是依法治理,以法治精神贯穿民主自治,以法治民主建设为村级治理提供法治保障,充分保障农村基层“权财事”的结构均衡和运行有序,在推动乡村治理重心下移,尽可能把资源、服务、管理下放到基层的同时,把各项农村各项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其次,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将精准脱贫中的“两评议两公示”民主程序制度化、广泛化、实质化,加快加强各类村务工作民主化程序、制度、机制、方式改造,使脱贫攻坚的民主成果和民主经验推广到涉农工作的各个方面.乡村干部作为乡村发展的“第一责任人”,应当自觉强化“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的责任意识,积极谋划新方法、寻找新出路,敢于接“最烫手的山芋”、挑“最沉重的担子”,以“钉钉子”精神稳扎稳打向前走,投身到急难险重的任务中去,争做致富带头的“排头兵”、改革发展的“先锋队”,在经历风雨中练就担当的“铁肩膀”,在实践磨炼中挺起实干的“硬脊梁”,实现农村各项工作创新推进、快速发展。
3.3 提升乡村德治水平,改进治理方式
首先,要深入推进农村基层减负工作,在整合优化乡村公共服务的同时,打造“一门式办理”、“一站式服务”的综合服务平台,推进和完善农村基层便民服务体系的规范化标准化;其次,以深入挖掘乡村熟人社会蕴含的道德规范,配合各类村级自治组织、社会组织的培育发展,建立健全乡村道德激励约束机制和乡村内部矛盾调解处理机制,为强化道德教化作用、引导村民“知礼”“守规”提供有效路径;再次,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核心,以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为载体,开展专项文明行动,稳步推进移风易俗,抵制封建迷信活动,深化农村殡葬改革,坚决遏制大操大办、相互攀比、“天价彩礼”、厚葬薄养等陈规陋习,积极倡导向善向善、孝老爱亲、重义守信、勤俭持家的优良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