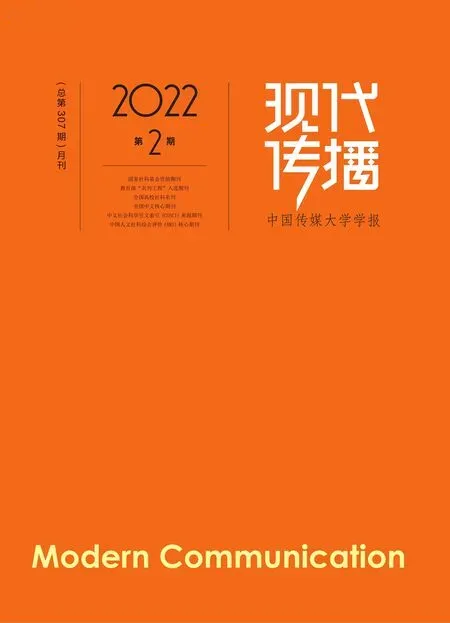智能触控媒介实践的生产、操演与反思*
2022-11-23段鹏张倩
段 鹏 张 倩
一、数字化语境下的智能触控媒介实践
当下,移动通信网络技术的迭代升级和具身性智能装置的发展为触屏信息流的生产与消费提供了前提条件,尤其是5G技术以其高流量密度、高连接数密度、高移动性等特点,使高清视频、虚拟现实等所需的大数据量传输效率大幅提升,带来了智能触控数字媒介使用的体验感、具身性、灵活性的极大升级,使人与数字媒介之间的互构关系发生着更为深刻的变迁。自2007年首款iphone诞生以来,“触屏”功能的出现便引发了人与技术互动方式的极大变革。这种触控操作基于硬件和软件的可供性与手部智能的互动关系①,为人的“知觉—动作”这一技术连结的适应性过程开辟了初始起点。随着智能设备技术具身性、可操作性的迭代升级,实践者身体与智能平面的互动连续性不断增强,“触”的点击式互动方式逐步演变为更具连贯性的“触控式”操作模式——“刷屏”,智能手机的触控媒介实践将手指的点、按、滑等操作姿势自然化为语汇。②如今,随时随地“刷屏”成为了具身性、泛在性的新型数字生存方式,深度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一个‘刷’字,集中体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人类的生活和精神状态”③。
“刷屏”不仅仅以一种扁平化的行为方式存在,还在更大程度上贯穿了信息的形成、知化、流动、使用、共享、过滤与互动等价值实现的全过程④,在虚拟、现实双重层面均隐含着极为深刻和丰富的内涵,描摹了人的技术化存在方式的立体画像。在数字场域中,“刷屏”的行为方式从经验习得逐步发展为数字化的生存习性,它集合了信息消费的知觉面向和进行反复身体操演的行为面向,是一种典型的数字化媒介实践。
21世纪初,库尔德利(Couldry)、布劳克勒(Brauchler)和波斯蒂尔(Postill)等学者开始对日益兴起的数字媒介进行关注,并在传统的社会实践研究基础上对既有理论不断扬弃和改造,针对数字媒介实践的研究也由此逐步兴起。具体而言,数字媒介实践的理论阐释是基于物质性的技术媒介环境与人的精神活动、身体活动之间的结构性互动,以技术化的日常生活研究为聚焦点,既关注具体媒介情境之中人的微观能动性,又关注技术对人的规约,以及由资本、制度、技术专家和用户自身共同形塑而成的思维与行为结构性。⑤除了探究媒介技术与行为模式之间的互动机理,数字媒介实践研究的落脚点还关注数字场域中习性的养成及其如何建构个体的生存样态和存在方式,这为批判性地观察日常生活中的数字媒介使用行为、人的能动性与技术结构性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种绝好的视角。
库尔德利认为,媒介研究的“实践范式”转向应关注四大问题:一是关心与媒介相关的行为规律及其语境和资源的规律;二是关心媒介行为习惯问题;三是应探索与媒介相关的习惯如何由基本需求形塑的问题;四是应追问人类如何靠媒介生活的问题。⑥他的观点引导我们关注现代人的数字媒介实践的规律与症候,从其生产语境出发探求其源起与操演过程,并启发我们思索这一媒介实践所建构的社会后果及实践主体的数字生活问题。
二、智能触控媒介实践的生产语境:社会加速下的媒介时间消费
从农业社会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到工业社会的“速度之美”,再到媒介化社会的“见屏如面,即传即达”,基于发展需求,人类社会对速度的追寻是永恒不变的。从报刊媒介时代的“深度阅读”,到电视时代的“观看”,再到具身手机媒介时代的“浅度浏览”——“刷屏”,我们发现,媒介技术现代化的更迭历程始终伴随着媒介观看方式、观看速度的变革,呈现出媒介观看的浅层化和媒介时间消费的加速化倾向。在数字时代,人们对速度的追求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当信息量的无限性与认知有限性之间产生矛盾时,人们总是倾向于花最少的时间看到最多的内容,“刷屏”便成为数字化时代一种典型的媒介实践,集中体现了赛博人“速度至上”的数字生活状态。媒介化世界中,信息碎片化、海量化、浅层化的物质和符号形态构建了加速化的媒介时间认知偏向,媒介逻辑深刻嵌入人的日常时间消费之中,从而型塑了人们加速化的媒介实践惯习。
在数字环境下,媒介实践深刻嵌入人们的日常时间消费之中,与其相应的媒介实践实质上就是一种对自由时间的消费实践:在移动时代,由于手机媒体的具身化及其使用成本的无限降低,媒介的时间使用趋于私人化,人们在信息消费中可实现对媒介时间的自由操纵。与以往的自然时间、时钟时间相比,在媒介时间阶段,人类对于时间的认知、感受、体验、测量、使用都被媒介化了,这构成了作为存在处境的新的“时间性”,在“社会加速”的表面领会之下⑦,媒介化沉浸式、虚拟式的时间消费改变着日常生活的时间感知及其结构秩序。
从马歇尔·伯曼(Marshall Berman)、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对现代性及社会流动速度的讨论开始,聚焦于媒介化社会时间维度的“社会加速”日益进入学界视野。社会加速理论的代表学者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认为,社会变迁加速、科技加速、日常生活节奏的加速是社会加速的重要特征⑧,而智能触控的媒介实践行为,生动体现了科技加速和日常生活加速作用下信息消费和时间消费的双重逻辑,是社会加速下的典型媒介行为表征。单位时间内,在技术可供性基础上,能被“刷”到的信息量呈几何倍增,是通信加速与效率提升的结果;同时,生活节奏的加速体现在传播领域,例如传播行动效率的极速提升,同时还伴随着媒介内容消费的加速化认知与体验;而社会变迁的加速意指社会各个事物、信息的时效性已经越来越短,即罗萨所说的“当下时态的萎缩”,不断“刷”新信息,追求新鲜和时效,是社会变迁所带来的适应性认知反应。
由此而生的是,在社会加速背景下,源于媒介时间消费的智能触控媒介实践——“刷屏”,其“刷”的动作模式内涵在继承其本源意义的基础上,又衍生、抽象出数字化的新意涵,深刻体现和印证了这种加速化逻辑。
首先,“刷屏”的媒介实践来源于媒介时间使用机制的进化。《尔雅·释诂》有言:“刷,清也”,《说文》注解“刷,刮也”,“刷”原表示行动主体作用于物理客体使之发生变化的过程,有清扫、剔除、淘汰、更新之意。罗萨认为,社会加速的后果是“快速建立起新事物,必须快速扫除和摧毁既有的事物”⑨,这对行动者的认知更新速度提出了新的要求。彭兰指出,面对互联网的海量信息,人的认知衍生出自我防御机制,随时清理大脑“内存”使新的信息流入。⑩在数字化的日常生活中,有限时间、有限注意力与无限信息规模之间形成的矛盾,伴随着“刷屏”的数字实践而产生的“认知滤网”使旧信息下沉而不断让位于新信息,这是数字时代泛化的媒介时间使用机制得以迭代升级的表现,改进媒介时间使用策略、及时进行信息认知的更新换代显然更为适应数字化的生存方式。
另外,这一媒介实践的生产与当下媒介时间消费密度的压缩有关。颜延之的《赫白马赋》描述骏马“旦刷幽燕,昼秣荆越”,以形容主体行动速度迅疾,而数字语境中,“刷”的概念由以往的“行动加速”衍生出“认知加速”的新意涵,即认知量的无限叠加与速率的升级,印证了罗萨对“加速”的阐释,即“单位时间内数量的增长(逻辑上等同于某一数量所耗用的时间的减少)”。英国柯林斯词典将“刷剧”定义为“在较短且集中的时间里一口气看完许多剧集”,刷剧时,我们常常关注整体剧情,而跳过我们不想看的桥段,行动者通过自由选择式、跳跃式的内容消费方式来压缩媒介使用密度,从而提升单位时间内的内容认知规模。因而,“刷屏”作为媒介实践,意味着追求内容认知效率的最大阈限,使“一目十行”“日阅千章”的媒介内容消费成为现实。
其次,“刷屏”的出现还涉及数字环境下媒介时间消费的去目的化。宋代杨万里《发银树林》一诗有云:“淡天刷墨晓来阴”,传统字义中,“刷”有大面积涂抹之意,强调行动的无重点、不聚焦及其作用效果的弥散性和去中心化。在数字化的时间加速环境下,智能手机对日常生活的深度嵌入改变了人对媒介的交互主体性,传统含义中行为效果的去中心化转变为认知的非聚焦和去中心化,即人们的认知很难集中在同一个媒介产品之上,从而导致时间消费的“漫无目的”。保罗·维利里奥(Paul Virilio)认为,在绝对速度阶段,时间的压缩消弭了空间隔阂,这使得人们的注意力集中于“当下”。当媒介时间消费的速度超出认知速度时,原子化的媒介使用主体在“无意识”状态下生产和消费媒介内容,意味着媒介时间的消费不再具备明晰的认知目标,不关注“获得什么”而关注“正在做什么”,打破了以往线性的媒介时间运作规律,媒介时间的使用从以往阅读、收听、观看等行为的目的指向转为浅度浏览的过程指向。
最后,“刷屏”的进程还伴随着媒介时间消费感知的非秩序化,这一连续性、无意识性数字媒介实践改变了人的时间认知结构与趋向。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认为,数字媒介既破坏了我们的“逻辑时间序列”,又破坏了我们的“生物时间感知”。数字媒介实践中,时间消费的逻辑性、秩序性、结构性被解构,这便造成了“抖音5分钟,人间1小时”的时间认知失调倾向。
基于对智能触控的数字媒介实践——“刷屏”的生产语境的剖析,笔者将其内涵概括为“一种社会加速下的媒介时间消费实践”,它既是社会加速在数字场域中的微观表征,也是加速化的媒介技术环境与人的意识和行为方式进行互动建构的结果。那么,“刷屏”的行为实践被“生产”出来后,又是如何进行操演的?这一行为规律是如何维系的?笔者将从实践的两个内在层面——行为层面、认知层面展开分析。
三、智能触控媒介实践的操演机制:“身—心”演绎与身份建构的双重实践
数字媒介实践研究关心媒介行为习惯问题,探索与媒介相关的习惯如何由基本需求形塑的问题,强调我们既要关注数字媒介实践的行为层面的惯习表征,又要关注其认知层面的需求动因。从行为层面看,智能触控媒介实践建立在技术化的“身—心”操演基础之上;从认知层面而言,它又是通过数字身份的建构来进行演绎的。
(一)“身在牢笼,心在四野”:“极惯性”的“身—心”演绎实践
“在信息加速流通和万能文化遥控的情况下,万能遥控空间变成了我们动物性身体的一种功能,从内部控制着这一文化中的栖息者。”社会加速下媒介实践行为的发生源便是身体,技术的身体操演是“刷屏”这一数字实践的基础。从行为层面来看,“刷屏”的实践模式是由身体与手机屏幕的持续互动来构建的,通过眼动和手指连续滑动的配合式作业,“刷屏”的暂时性动作内化为持久性惯习,正如保罗·康纳顿(Paul Connerton)所言:“通过练习,身体开始能协调越来越大范围的肌肉活动,越来越变得自然而然,直到无意识,动作‘不由自主地’发生,于是出现了一套从头到尾流畅进行的固定习惯动作。”维利里奥运用“极惯性”(Polar Inertia)的概念完美地描述了具身媒介塑造下的身体状态:媒介所创设的环境场所使置于其中的人的身体不再移动,所有变化均在原点发生,即刻的行动惯性代替了持续的身体运动。“刷屏”的身体惯习构筑于一个由身体和媒介组成的相对固定的动作空间中,人在操作时的身体并未发生位移,以手肘为支点,视线和屏幕之间构成一定的平面夹角,可通过单纯的手指运动完成数字实践过程。这种身体与媒介的互动性惯习发展成一种病理表征,彰显出身体尤其是手部连续性动作的生产性功能,构成新的视听意指实践。
人类起源的“沼泽地学说”认为,人为了适应沼泽环境而学会直立行走,是一种对生存环境的适应性身体演化过程。在这种现实的生产性生存环境中,人对生产工具的创造和使用的目的是满足自身对物质资料的需求,这一过程实现了手的功能延伸。而具身媒介的出现使直立姿势演变为颈椎前倾甚至弯曲变形的惯性姿态,从而适应数字化的生存样态,同时,手对媒介的操作不再是生产性和创造性的,而演变为强迫性、重复性、流程化、格式化的一系列身体动作模式,是以媒介为核心、被媒介生产和塑造的。“刷屏”形成固定化的行为模式后,人的身体被动接受、服从媒介的结构、逻辑和规则,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它的“伺服机制”(servomechanism),以往人对自然环境的“伺服”演变为对技术环境的“伺服”,从而实现身体及惯性实践的运作。
同时,身体的技术操演与知觉运作相伴相生。维利里奥提出“阈下舒适的技术假体”来指代技术化的身体补充物,此种文化技术作为感知形式来影响人的心理结构与情感状态。智能触控的媒介实践建构了其相应的技术性文化,在身体伺服机制运作的基础上,“刷屏”的视觉移动以跳读和扫描为特征,这种“浅度浏览”方式使得信息内容的重要性让位于行为本身带来的心理舒适感和体验感。正如维利里奥预测的那样,“一个普通行人变成了具有某种标志性神经疾病的残疾人或不由自主的编舞者”,最终“完全沉浸在一个可视听的‘遥远世界’的集体化想象之中”。技术媒介开辟的想象空间满足了人的求新欲、窥私欲和好奇心,创造了一种狂欢化的知觉快感。由此,身体的伺服机制与心理的沉浸机制合而为一,共同描摹了一幅“身处牢笼,心在四野”的数字化生存图景。
(二)“我刷故我在”:“数字自我”的身份建构实践
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在《第二媒介》中说过:“技术革新最关键的并不是信息交换效率的增加,而是造成了身份建构方式以及文化更广泛而全面的变化。”在行为层面“极惯性”的身体操演背后,现代人的智能触控媒介实践有其认知面向上的深刻动因,随着数字媒介在日常生活的深度嵌入,它不仅仅是一种行为方式的表征,更建构了一种普遍的、共同的数字身份——“刷屏人”,是由手机媒介建构的数字化生存的符号表征以及数字化的思维、形象、态度的意义系统。
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的“我思故我在”浓缩了他对自我存在和身份建构的看法。他认为,自我身份的建构来源于对事物的理性思考,主张向内、向心探寻。而数字环境中,人的存在方式、认知方式均发生了变化,对事物的思考在数字场域中进行,数据信息已成为最重要的认知资源,而“刷屏”的行为实践以扩大认知容量、提升认知效率为目的,是人们认知世界的新型方式与路径表现。人们通过“刷屏”向外探寻,来达到认知世界、认知自我的目的,“我刷故我在”的价值体认成为“数字自我”的身份建构的开端。凯思林·伍德沃德(Katherine Woodward)认为,身份问题关涉对自我、他者及各自归属社群的认知、态度、情感,自我和他者成为个体身份建构的来源,因而,社群中个体的数字身份是通过自我建构和社群互动中的他者建构两种方式形成和塑造的。
一方面,“刷屏”的行为个体保持着“永久在线、永久连接”的数字生存状态,通过随时随地刷朋友圈、刷微博、刷视频来维系自身的“数字身份”,以防止与既有网络圈层断联或无法第一时间获取新信息。通过“刷屏”,我们感知到自身与世界保持联结的状态、确认自己未曾被信息社会孤立与隔离,从而获得对自我存在价值的认知与确证,并实现对自我“数字身份”的认同。如“每次看到app上的小红点,就像看到脸上长了痘痘一样,不消除它就浑身不自在。不停的拿出手机,生怕错过了一条信息,一次更新”。由英国作家阿兰·德波顿(Alain de Botton)在《身份的焦虑》一书中提出的“身份焦虑”(status anxiety),是指担忧我们处在无法与社会设定的成功典范保持一致的危险之中,害怕被夺去尊严和尊重,这种担忧的破坏力足以摧毁我们生活的松紧度。而数字媒介营造了欣欣向荣的线上世界,改变了现实生活中个体的身份隐喻:若无法跟随虚拟世界的发展步伐,便无法获得身份的确证。因而,“数字身份焦虑”成为“刷屏”的心理根源与动机,个体通过延续和维系“刷屏”的实践惯习来实现对“数字自我”身份的建构,并缓解数字身份焦虑。
另一方面,个体通过“刷屏”的行为实践在人际、群体互动中建构着自我的“数字身份”。现实社会中,米德(Mead)的角色扮演理论强调个体在社会化互动中站在他人的角度来理解经验自我,从而形成对自我的观察与评价。在日常人际交往中,“刷屏”的数字实践在虚拟与现实世界之间标记了界线,“刷屏”的动作可使他人明确认知到行动者由现实交往身份向虚拟数字身份的切换,从而达成行动者对自我“数字身份”的重新理解与再次确认。有研究表明,社交尴尬是刷手机最常见的诱因之一,譬如“和认识的人顺路,只有刷手机才能缓解尴尬”“当别人试图跟你说话的时候,你可以拿起手机假装有事在忙”。在这些情境下,“刷屏”作为一种数字身份的标识,可使他人理解行动者“在线上,请勿扰”的状态,使行动者再次确证自我进入数字身份实践的个人化时间与空间状态,为规避现实的人际互动提供了正当性与合理性,从而缓解社交焦虑和人际尴尬。
四、智能触控媒介实践的社会后果及反思
数字媒介实践研究的落脚点在于思考“人类如何靠媒介生活”的问题,这成为其研究的终极关怀。从媒介实践视角来看,媒介技术的结构性对人的主体能动性发挥着建构作用,数字技术的可供性在促动着人效率化地追求自由时间、形成数字化身体惯习和数字身份的同时,又产生了与此生存方式有关的后果。
(一)“刷屏”是真休闲还是假休闲:自由时间消费异化
休闲是工作时间之外的自由时间,是人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内容。日常生活中,“刷屏”的目的是更有效率地追求休闲的自由时间,本质上源于加速化的数字媒介时间消费实践,但手机媒介在为人们提供了休闲的消费渠道的同时,也通过时间的权力机制运作来实现对人的休闲时间的支配。
由于时间是一种具体的社会制度,时间单位的划分被赋予实践意义,由时间所建构的制度会形成一种行动参考框架而影响行动。在社会资本和权力主导对线性时间管理机制的建立与维护的当下,社会个体渴望在一些瞬间,通过使用一些策略,例如时间逃离、时间中断等,来获得个体意义上的时间。赫尔嘉·诺沃特尼(Helga Nowotny)认为,“瞬间”的个人时间是一种对抗集体时间、逃避时间统治的游戏——创意策略和斗争方式。以自由主义为目标的个人时间与支配性的社会时间规范体系之间存在冲突性,而随时随地的智能触控媒介实践恰恰为行动个体提供了获取“时间逃逸”的可能性,实质上是行动者对资本化的时间运作规则及其意识形态性的微观抵抗。如日常生活中“工作累了刷会儿视频”“葛优瘫刷手机”等等,生动描摹了数字媒介环境下人的休闲景观。通过这一媒介实践,社会成员获得了在时间观念和感官上的即时性满足,但也正是通过这种可供性,个体化的自由时间被技术合理化操纵。
马克思的休闲理论主张人最终应实现休闲的自主性,使休闲成为发展人自身的一种手段,当休闲与主体相对立、脱离主体掌控时,就产生了“休闲异化”。而具身化的媒介使用空间中,主体获得部分休闲满足的同时,更让渡了对休闲时间的自我掌控。更为显著的表现是,智能触控媒介实践还通过休闲的“工作化”加速了休闲异化危机,使个人时间又落入消费主义的窠臼。如短视频、游戏APP通过有偿鼓励用户做任务、增加刷屏时长来增加其广告的曝光率,从而获得更高的分成收益,通过提供娱乐内容、设置进阶激励机制将个体休闲时间转化为数据化的经济效能。休闲是人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的内容,数字场域的劳动力再繁殖使休闲本身以异化休闲的方式存在,必然难以达到它本该具有的对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效能。
(二)“刷屏”的“准他者化”:技术中介作用下身体实践与知觉运转的分化
数字媒介实践是通过身体与知觉之间的互动关系运作来展开的,是数字化的“身—心”系统持续运作的结果。与现实实践相比,数字领域中的技术力量中介化了实践的“身—心”系统,在技术对人的“意图—行动”的影响下,人也正在通过媒介将自身的身心技术化。这一技术的中介化过程体现出人性化的媒介作为行动者,在与人融合与交互中,利用强黏性对人进行驯化、形塑与操控,从而形成对人身体实践和感知模式的控制力。
数字媒介实践理论关注技术影响下“身—心”二元的结构性互动。“身心合一”“知行合一”的身心关系是传统现实实践所追求的目标,此种状态下,身体是人进行数字实践的中介,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得以发挥的装置,而知觉则是由身体的物质性实践决定的意识产品,同时又对身体能动性发挥着结构性的指导作用。而在智能触控媒介实践中,技术的中介性重塑着个体的身体实践和感知模式,改变了“身—心”的互动关系。人在“刷屏”这一智能触控媒介实践中,虚拟与现实的融合成为人感知到的自然状态,人更加难以辨别二者之间的界线,从而产生意识可以脱离现实的物理身体而沉浸在虚拟时空中的知觉,导致了人的思维知觉与身体实践的分化。
美国技术哲学家唐·伊德(Don Ihde)提出“意象的身体”(image-body)概念,认为人在虚拟世界中获得了非实体的身体体验,使意识与现实的肉身分离,个体成为以旁观者视角观察自己的“准他者”(quasi-other)。在“刷屏”的数字实践中,这种身体与知觉的分化表现在心理层面的“无实体身体”,虽附着在实体身体的技术操演之上,但知觉在一定程度上处于闭锁状态而无法感知身体与媒介的互动行为,形成“身—心”的联动障碍。“我们迷茫、焦虑,于是拿起手机,继续刷屏,缓解焦虑。最后,陷入了越刷屏越焦虑,越焦虑越刷屏的恶性循环之中,无法自拔。”这种状态便是身心二元分化的真实场景描摹。当技术的身体操演流程化、机械化后,人们开始用第三人视角看待自身“刷屏”的实践行为,意象与身体的分离使身体动作系统无法对大脑指令作出即刻反应,正如麦克卢汉所指出的,“媒介在形成的新的环境和媒介延伸人类身体的同时,反过来对人类自身形成新的‘压力’和自我截除,使人产生麻木和不自知的状态”。
(三)“刷屏”作为一种存在维度:数字身份建构实践与“游牧”的生存体验
罗杰·西尔弗斯通(Roger Silverstone)认为,“驯化”是个体主体性卷入并改变媒介及其意义的复杂过程,“它是一种过程,我们在其中使某物隶属于我们,受我们的控制并能印染上、表达出我们的身份”。在技术对身心的“驯化”状态下,数字媒介实践主体并不关注自身在互联网上的存在意义即为何而存在,而是关注自己以何种身份、何种方式存在。沉浸式传播环境给予参与者身份建构的机会,当虚拟与现实的界限被模糊之后,参与者自身的认知也随周遭环境的变更发生震动。身份是主体存在的表征,“刷屏”作为一种数字身份建构实践,标识了一种数字生存的存在维度。
由于“媒介是能够孕育文化的技术……媒介构成了文化的政治、社会组织和习惯性思维方式”,数字媒介技术通过智能触控的媒介实践过程使其相应的媒介文化得以建构和维系,从而塑造了其中人的意识结构和生存状态。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提出,与现实中规则有序、静态封闭、等级森严、线性的“条纹空间”不同,网络虚拟世界是一种开放无界、散漫自由、多元并存、块茎式的“光滑空间”。建立在个体自由时间基础上的“刷屏”的过程,实质上是从现实的“条纹空间”逃离,从而转向沉浸于“光滑空间”的自由主义行动。通过不断地“刷屏”,主体的数字身份得到凸显,不断追求“永久连接、永久在线”的状态,这反映了数字化主体的意识系统从现实到虚拟世界的切换和对现实秩序和制度主义的逃避。相应地,通过“刷屏”的数字媒介实践,主体身份特征由现实世界中固定化、秩序化转变为暂时性、流动性、非单一、去中心化,与之相应的空间观和时间观也不复存在,现实社会时间、空间框架下的“秩序”式生存体验转向“游牧”式的生存体验。
然而,这并非意味着主体对新身份和新生存状态的完全适应,智能触控数字媒介实践虽建立在消费自由时间的基础上,但主体的身心操演又受到技术框架的结构性影响,因而形成了一种“被自由所束缚”的数字身份状态和生存状态。人们因对速度的掌握而失去思维和行动的能动性,原有的秩序化生产生活体验让渡于“游牧”体验,而个体“刷屏”的技术易得性和介入性正是虚拟“游牧空间”对现实“条纹空间”的入侵通道。如“生怕错过每一场朋友圈刷屏活动、明明知道99+的群聊消息没有营养也要点开查看”“没刷手机的一天过去,我可能又错过了一个亿”等错失焦虑的出现,反映了“游牧”式的生存体验是在技术“驯化”下“假性自由”的状态,在主体建构自身数字身份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对数字身份被剥夺、被线上世界忘却、与虚拟视像隔绝的身份焦虑。
五、结语
数字媒介实践研究关注人与数字媒介的复杂关系,目的是真实、深刻认知当代信息社会人的生存状况。智能触控媒介实践是反映当下人与具身媒介关系的典型表征,又是技术环境下人的新型数字生存方式。在技术所创生的媒介化的日常生活中,智能触控的连贯性媒介实践生产于数字环境下加速化的时间消费实践,又通过行为层面技术化的“身—心”演绎、认知层面数字化的身份建构进行操演。同时,这一数字媒介实践源起于人对休闲的基本需求,又反向导致了自由时间消费的异化;数字媒体将人类理想中的情境带到眼前的同时,也可能导致人类的理性在现实与虚拟的重叠中逐渐迷失。在技术的中介作用下,智能触控的媒介实践惯习使人的身体实践与知觉运转出现分化,使“身心合一”的朴素理想渐行渐远。最终,智能触控的媒介实践成为了赛博人的数字身份标识和存在维度,是人从现实社会秩序和线下世界规则中“逃逸”的实践通路,建构了去中心化、离散化、永恒流动的“游牧”式的生存体验,随之带来了“被线上世界忘却”的恐惧和对自我数字身份的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