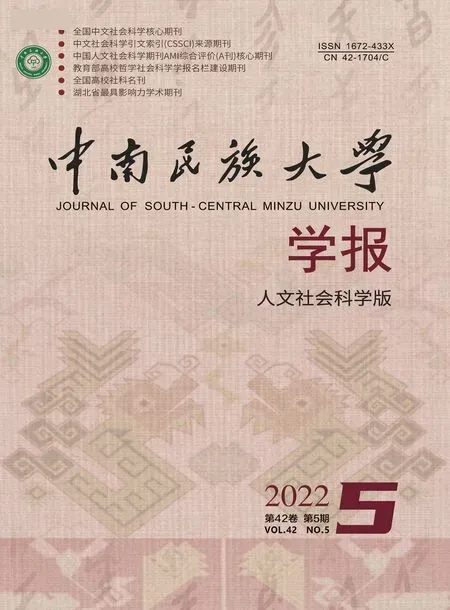祖先崇拜与竹图腾的交融互渗
----汉族与南方少数民族族源传说的比较
2022-11-22叶远飘
叶远飘
(广东医科大学 生命文化研究院,广东 东莞 523808)
中国许多地区的民间族谱都有“祖先来自珠玑巷”的说法,这一现象令人困惑不已。20世纪90年代,在青海举行的一场关于民间族谱的学术讨论会上,学者们普遍猜测“珠玑巷”不是一个真实的地理名字,仅是一个文化符号。但它究竟是什么符号,该符号如何产生的,却苦于没有证据而语焉不详。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受法国年鉴学派影响甚深,历来重视实证研究,那场讨论会上的“猜测”并没有改变这一风格。事后,学者们仍然热衷到南京、福建等地考证族谱所载的“珠玑巷”之地理位置,但结果都是无功而返。近年来,笔者注意到“珠玑巷”与古越人的“竹崇拜”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尝试避开传统研究路线,从神话学的角度揭开这一谜团,旨在抛砖引玉。
现实世界中的“珠玑巷”是广东省韶关市南雄县城北部偏东的一条巷子,全长1500米,宽4米,为古代中原和江南通往岭南的古驿道,但已经被今天珠江三角洲地区操粤语群体的广府人视为祖先发源之地。2021年6月国务院批准的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广东“南雄珠玑巷人南迁传说”赫然在册。“珠玑巷人南迁传说”主要以粤语为载体口头传承,讲述了南宋时期(各家族谱记载的时间不同),罗贵带领珠玑巷人33姓97户为了躲避官府杀戮,在胡贵妃(另有族谱记为“苏贵妃”)的掩护下,逃亡南迁到广东南雄珠玑巷,之后辗转落户珠江三角洲,从而开拓岭南疆域的故事。该传说最早出自珠江三角洲地区以粤语为母语的广府人的族谱,后由历代方志、笔记和诗文转述,又一度被改编为章回小说、粤剧和电视纪录片等,以多种艺术形式传播,对粤语族群后裔形成强大的凝聚力,数百年来吸引着海内外几千万粤语族裔到珠玑巷寻根问祖,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一、研究综述
以往学术界关于“珠玑巷人南迁”的研究主要聚焦三个层面的问题:一是故事的真实性问题。现有研究的共识是,“南雄珠玑巷人南迁”只是一个传说,但传说有其蓝本----北宋末年和南宋末年,中原士人的确经历过两次大的迁徙,而族谱的记载将这两次迁徙合二为一[1]。二是关于传说产生的年代。现有研究的主流观点认为传说产生于明代早期,但民间广泛流传并被众多族谱采纳的是明代中叶以后。既然如此,就引出了第三个问题,即明代为何会流传这样一个传说?是什么人编造出来的?目的是什么?以井上彻为代表的多数学者提出“汉化说”,认为这是明代珠三角地区的少数民族融入汉族,取得汉族身份的策略[2]。曾祥委提出“隐瞒身份说”,认为是宋末元初原宋朝广州府的勤王义民应对元朝政府编户齐民所采取的策略[3]。仲红卫提出“宗族建设需求说”,并认为珠玑巷传说体现的是儒家文化,而不是羼杂着“摆夷”色彩的岭南文化[4]。
以上研究丰富了学术界对该传说的认识,权且参考。在笔者看来,它至少能给后来的研究者两点启发:一是这些研究都承认了“珠玑巷人南迁”是一个传说。有了这个共识,便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讨论问题。二是从研究的视角来看,前述成果皆立足于该传说流行的中心地区----珠江三角洲,忽视了珠江三角洲地区之外的相关类似传说,或者仅仅把珠三角地区之外的类似传说视为珠三角传说的版本在外地的变形,即所谓“珠玑巷传说或者类似的故事,与黄萧养之乱以后重新整顿和编制里甲户籍有关”[5]。但从学术视野出发,所谓“中心”与“周边”是可以转换的。早在20世纪30年代,台湾知名人类学家王松兴就提出过从“周边”看“中心”的学术路径,他还特别指出,从“周边”看“中心”,容易看到一些在中心地区已经消失的文化,或者被中心忽略的经验[6]。这一论断至今已被许多研究证实,例如“宗族”这一缘起于中原汉族宗法制度的家庭结构至今保存其较原始形态的并不是北方,而是华南。假如立足这一视角,将其引入“南雄珠玑巷人南迁传说”的研究,那么这个传说会呈现出什么样的图景?是否更有利于我们接近理解该传说的本质呢?
二、珠玑巷:汉越祖先信仰交融的精神空间
关于祖先来自珠玑巷的民间族谱除了珠三角地区有保存以外,全国至少还有两个地区有发现:一是毗邻珠三角的粤西南,范围包括广西的梧州、贵港、玉林、钦州,广东的茂名、湛江,并跨越琼州海峡覆盖海南岛西线的部分沿海城市,尤其是海南省的儋州市和临高县;二是离珠三角更远的青海河湟地区,包括青海的西宁、大通、乐都、化隆、湟中、湟源、门源、民和、贵德和甘肃的部分地区。借用“差序格局”[7]的概念,可以把珠三角视为传说的核心区,粤西南为传说的辐射区,青海河湟为该传说的扩散区。由于该传说的传承主要靠文字的书写、语言的口述和仪式的展演,因此,笔者重点考察上述三方面的内容。
据广西玉林市容县黄泥塘的《彭氏族谱》所载,弘公、应宵公、益公三兄弟与母亲始迁自福建汀州府上杭县珠玑巷百石社画井村;《兴业泉江村彭氏家谱》说,远祖彭真一郎来自福建汀州府武平县朱基巷;钦州、廉江《彭氏本宗支情况》言,念一公自福建汀州上杭县朱紫街瓦子巷迁来;从桂东南的情况来看,说自己的祖先明朝始迁“珠玑巷”的涉及李、王、刘、郑、廖、邓、丘、万、林多个姓氏[8]。但族谱对“珠玑巷”的写法有差异,分别有“朱基巷”“朱紫巷”“朱衣巷”等,但无论如何,该地的人认为“珠玑巷”在福建莆田,而不是广东的南雄。粤西南民间族谱大多把“珠玑巷”记为“猪屎巷”,如广东湛江雷州地区的《朱氏族谱》写道:迁始祖朱发公,字思本,祖籍福建省莆田县朱史巷村猪屎巷,明洪武年间钦赐进士,授职雷琼兵备道,卸任后卜居雷州朱家村(古称周家村)[9]。语言方面,该地流行的多是“土白话”,属于粤语系的一种方言。海南的情况与粤西南类似,认为自己祖先由福建莆田县甘蔗园村猪屎巷迁至海南,姓氏有王、孙、李、沈、周、黄、马、陈、张、罗等十多个,大多数集中在儋州市和临高县。海南的“儋州人”与“临高人”在语言上是比较特殊的群体。“儋州人”说的语言被称为“乡话”,民国《儋县志》记载:“‘乡话’,字平声,言则仄,字仄声,言则平,惟入声字,仍照仄言;此乃由高州、梧州传来,放今声调颇异,而与高梧人言通,盖外人来儋,惟高、梧人为先且多,故其言传遍乡间也。”[10]说明“儋州人”的主体主要来自今粤西南的高州、化州一带。临高人的语言被称为“村话”,经语言学家鉴定,属于壮侗语系壮语支方言,在血统上是地地道道的百越种系。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府开展民族识别工作时,曾经一度认定他们为壮族,但该群体的知识分子却坚决认为自己是汉族,列举的证据就是所谓“猪屎巷”的族谱。
再看青海河湟,乐都峰堆瞿县的李姓、老鸦的谢姓、亲仁的张姓、马营大仓的李姓,其族谱都记载祖上来自南京珠玑巷[11]。《化隆县志》说今化隆境内大部分汉族自称祖籍南京珠玑巷或山西洪洞(桐)县[12]。《石氏源流》说石氏祖籍南京主司巷人,洪武年间来西域[13]。《平安县志》道:“民间多传南京竺丝巷。”[14]西宁《城西区志》言明朝时有从陕西凤翔、宝鸡迁入河湟的汉民和来自南京珠玑巷的汉民[15]。可见,在青海河湟地区,“珠玑巷”也有许多种写法,如“主司巷”“竺丝巷”“朱子巷”“竹子巷”等。语言方面,青海河湟人说的是青海地方方言,属汉语系,但与江苏南京的方言有一定联系,至今,有些江苏籍木匠用方言交谈时,青海人都能听得懂[16]。明朝定都南京,为防范西北少数民族政权,将军户和屯户自南京迁往西北并不奇怪。因此,青海河湟地区的老百姓认为珠玑巷在江苏南京市,而不是广东韶关的南雄市。
那么,广东韶关南雄的珠玑巷是什么时候得名的呢?目前能看到的最早记录是明末清初屈大均写的《广东新语》,屈氏给出了两种说法:其一,珠玑巷得名来源于宋代中原南迁之汉人对宋朝京都开封珠玑巷的思念----“吾广故家望族,其先多从南雄珠玑巷而来。盖祥符有珠玑巷,宋南渡时诸朝臣从驾入岭,至止南雄,不忘枌榆所自,亦号其地为珠玑巷。如汉之新丰,以志故乡之思也。”[17]49这段记录中谈到由中原入岭南止于南雄是事实。唐代以前,岭南与中原的交通在广东南雄一带受阻于由西到东延伸的五岭(越城岭、都庞岭、萌渚岭、骑田岭、大庾岭),其后,张九龄在距离今南雄珠玑巷15公里的大庾岭一侧开凿了梅关古道,宽约17米,路面平整,从此密切了岭南与中原地区的交流,南雄成了岭南与中原沟通的中转站。但是,这条记录说“开封有珠玑巷”却查无实据。屈大均是广东番禺人,他明确表示自己是珠玑巷移民的后裔,而且《广东新语》成书的时候关于南雄珠玑巷人南迁的传说已经在社会大面积流行,他显然采信了民间族谱的说法。其二,“珠玑巷”由唐代的敬宗巷改名而来,言“珠玑巷名,始于唐张昌。昌之先,为南雄敬宗巷孝义门人。其始祖辙,生子兴,七世同居。敬宗宝历元年,朝闻其孝义,赐予珠玑绦环以旌之,避敬宗庙讳,改所居为珠玑巷”[17]59。但这条史料到目前为止还是孤证。其实,从神话学的角度分析,《广东新语》给出的两种解释在神话的母体上并无区别,体现的都是儒家对祖先“慎终追远”的意识,特别是第二种解释所说的“敬宗”“孝”“义”等尤为明显,因此,有理由推断这是“南雄珠玑巷人南迁传说”流行以后的文化再生产(下文提到一部编于清康熙三十三年的族谱可以印证此推论)。
由此可见,迟至明代,在珠三角有一批说粤语的人声称自己的祖先来自河南开封一个叫“珠玑巷”的地方;在桂东、粤西,有一批说土白话的人声称自己的祖先来自福建莆田一个叫“珠玑巷”的地方;在海南,有一批说着“乡话”“村话”的人也声称自己的祖先来自福建莆田一个叫“珠玑巷”的地方;在青海河湟,又有一批说汉语但夹杂着吴越词汇的人声称自己的祖先来自南京一个叫“珠玑巷”的地方。根据学界目前的研究,不管是河南开封,还是福建莆田,亦或江苏南京历代都没有“珠玑巷”(包括谐音)这样的地名。很显然,族谱所说的“珠玑巷”不是一个真实的地名,其实仔细分析各个地区所谓的“珠玑巷后裔”的身份,虽然他们都是汉族,但所操的语言都有共同特点----都保存了古越语的成分。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交趾”在今天的广东广西南部和越南北部交界一带;“会稽”位于长江下游的江南一带,郡治在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城区)。这一地理范围的底层文化是百越文化,因此,有理由推断“珠玑巷”仅仅是汉文化与越文化交融后人们创造出的一个精神家园,类似于“天堂”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珠玑巷”是一种关于祖先信仰的隐喻,是尊祖敬宗文化的象征符号,而广东南雄因地处汉越交界区,在以后的文化再生产过程中成为这个精神空间在现实世界的投射地。那么,“珠玑巷”这种关于祖先信仰的隐喻究竟隐喻什么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必须回到“珠玑巷后裔”们的祭祖礼。
三、珠玑巷子民的祖先崇拜:尊“竹”与敬宗
在中国,有关祖先的仪式最核心的部分就是祭祖礼,特别是古老的祭祖礼。由于它关系到祖先来源的说法,即便在历史长河的发展中出现变迁,相比其他礼仪也会相对稳固。以下,笔者继续立足于珠玑巷人南迁的“传说”本质,描绘“珠玑巷子民”的祭祖仪式,从中将看到一幅有别于现有研究展现的知识图景。
在青海河湟地区,虽然族谱和方志对“珠玑巷”的写法多种多样,但在民间最普遍的说法还是“竹子巷”。至今,在青海湟中县共和镇的南村,凡是认为自己的祖先是由南京竹子巷迁过去的家庭都在院子里种有一支特别的竹子,表示不忘祖先来源于竹子巷[18]。过去,有的家庭在逢年过节的时候还会在竹子面前祭祀,给竹子贴红色的金箔。显然,从青海河湟地区“珠玑巷子民”展演的仪式来看,珠玑巷这个名字与竹崇拜存在着某种关联。当然,如果这种现象仅仅在青海河湟地区存在,确实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因为历史学有所谓“孤证不立”之原则。令人惊讶的是,相关仪式竟然也在粤西南所谓的“珠玑巷子民”中存在。
2021年6月,笔者在广东省湛江市廉江县的车山村收集到一部编写于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的《符氏族谱》,言其迁始祖、太上祖符敬宗,原籍福建莆田县,于元末明初在福建莆田起义反抗元朝暴政,兵败以后逃到广东南雄的珠玑巷生活并终老。符敬宗育有一子符芳,从珠玑巷迁徙到广西的博白,生有六子,明成化年间除一子留守广西博白,其他五子分别迁往茂名、吴川、廉江、雷州和海南,是为各地的开基祖。该族谱说自己的迁始祖名字叫“敬宗”,而且还说符敬宗在珠玑巷终老,与社会流传的珠玑巷由敬宗巷改名而来不谋而合。但据笔者调查,被称为同出一支的茂名、吴川、雷州、海南等地的符氏族谱都没有提到符敬宗。至今广东省韶关市南雄珠玑巷立有一块碑文,罗列出了据说从珠玑巷迁出的所有姓氏,也没有“符”姓。由此可见,该族谱的撰写具有攀附儒家尊祖敬宗的意识,符氏宗族内部流传的祖先在珠玑巷南迁过程中改姓的故事,则体现了该宗族底层的祖先观念。符氏后裔讲述道:
20世纪80年代,没有听说过什么族谱,很多关于符氏祖先的故事都是老人家口头相传的。基本上当时都流行这一说法:我村始祖来自福建莆田,兄弟六人。元末明初,因为在当地犯法,另有一说因为反抗元朝暴政,被官兵追杀,所以六兄弟向南方迁移,怕路上危险,只能走水路。由于水流太急,各兄弟不知所踪,我村始祖慌乱中抓住一根竹子,顺流而下安全登岸。为了感谢竹子的救命之恩,将自己原来的胡姓改为竹字头的符姓。[19]
该故事至今在广东廉江符氏宗族10万后裔中流传,当地30岁以上的符姓后人基本上都表示听过,说明它是该宗族大规模的历史记忆。在此历史记忆中,符氏祖先落水后因为竹子获救而改姓,凸显了该宗族在历史上有过非常强烈的竹崇拜。其实,粤西南符氏宗族的历史记忆并不是孤立的,它与珠三角广府人的历史记忆存在密切的互动。从广府人的族谱考察南雄珠玑巷人南迁的路线,未见有目的地的具体地点,但总的路程是结竹排随浈水南飘,经韶关、连江口、英德入清远而达珠三角地区。也就是说,他们南迁时所使用的交通工具是竹筏。广东南海鹤园《陈氏族谱》云:“各挈家逃窜荔枝山下者万余人,遂结竹为牌,顺水漂流,乃狂风大作,牌散,溺水死甚多。”佛山西樵《黎氏族谱》道:“山溪水涨,大家共扎竹排逃出,直下连州水口,各散其居。”何大佐在《揽屑》也说:“举族奔逃,时无舟楫。我祖兄弟砍竹为插,乘流漂泊。夜半,突至连江口,潦水冲散。”今广东佛山市南海区九江境大洋湾畔有一个叫“破排角”的地方,据民间说法,就是当年祖先从珠玑巷南迁时竹排被狂风吹散的地方[20]。
该传说在神话母体上与粤西南竹救祖先的传说并无不同----“乘竹筏逃跑避免被杀”实际上就是竹救祖先的表达。因此,珠三角的广府人也有强烈的竹崇拜意识,反映在仪式中,广府人至今在清明祭祖的时候必须使用甘蔗----他们把甘蔗砍成一段段,类似竹排排在祖先坟前祭拜,并要求祭拜子孙务必要把甘蔗吃完才能离开。对珠三角民俗颇有研究的民俗学家、原广东省肇庆市博物馆馆长谢子熊,肯定了广府人甘蔗祭祖仪式隐含竹崇拜的文化内涵[21]。甘蔗祭祖不仅因为竹子与甘蔗都属于禾本科,外形相像,而且甘蔗可以食用。因为儒家祭祖的意义在于“俊”,《礼祭·祭统》言: “夫祭有俊,俊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人有言曰: ‘善终者如始,俊其是也。’”所谓“俊”,指在祭祀后将神灵品尝过的食品赐给子孙后代,子孙后代吃下祖先品尝过的食品,吃下去的是一种信仰----他们认定由此获得了祖先的道德、智慧和福气。因此,儒家的丧祭礼体现的意义在于通过祭祖而达到凝聚“宗”的目标。值得注意的是,广东有三大族群:操粤语的广府人、操客家话的客家人和操闽语方言的福佬人,广府人与其他族群最明显的区别除了语言以外,就是甘蔗祭祖。众所周知,岭南的客家人主体才是真正从中原迁徙而来的,他们的祖先也一定路过广东南雄,然而他们并没有甘蔗祭祖的风俗。广府人使用的粤语是古越语和汉语融合而成的,其使用甘蔗祭祖的风俗当来源于古越人的竹崇拜。谈及此,不得不提及前文所述的海南临高县的“临高人”。历史文献曾将临高人使用的“村话”称为“西江黎语”[22],指这种语言来源于今广西梧州、广东肇庆一带的西江流域,而这一带恰恰也是广府文化的发源地。临高人很早就迁往海南岛,与广府人一样,至今仍然保留甘蔗祭祖的风俗。临高县广播电视台记者WJ这样讲述道:
祖祖辈辈都这样传下来,说我们临高人的祖先是从福建甘蔗园村猪屎巷迁来的。我们过年或者清明祭祖其它的可以没有,但一定要用甘蔗,这是临高人的规矩。父辈们都说因为我们的祖先从福建迁到海南的时候被官兵追杀,祖先躲进甘蔗园逃过灾难,现在祭祖用甘蔗就是纪念甘蔗救了祖先。(1)讲述者:WJ,男,海南临高人。讲述时间:2020年3月5日。地点:海南省临高县多文村。
“竹崇拜”不只反映在临高人用甘蔗祭祖的仪式上,还反映在给逝者做的安魂仪式上。按照临高人的丧葬风俗,老人去世埋葬以后要经过至少21天甚至更久的时间并专门举行一定的法事后灵魂才能进入宗祠。在此之前,死者的灵魂(写有死者生辰八字的纸牌)被装入一截竹筒,外包一块红布或者缠绕红线挂在客厅的角落处单独祭拜。
从青海河湟的“珠玑巷后裔”种竹子,到粤西南的“珠玑巷后裔”改姓,再到广府人与海南临高人使用甘蔗祭祖,皆说明“珠玑巷人南迁传说”的信仰核心是竹崇拜。而且,从“竹筒装灵魂(临高人)→甘蔗祭祖(临高人、广府人)→崇竹起‘符’(粤西南土白话人)→种竹子(青海河湟人)”,显示出了从越人到汉人祖先崇拜的进化路线:保留原始竹崇拜形态越多,其对应人群所使用的语言往往保留古越语的成分也越多。当然,竹崇拜文化的进化线路之成立还需要确认一个关键的环节,即古越人到底有没有竹崇拜?
四、“珠玑巷人南迁传说”的文化底色:古越人的竹崇拜
越人是华南的土著,史称“百越”,在历经长期的演变后,形成了今天华南地区的八个壮侗语族少数民族,即壮傣语支的壮族、傣族和布依族,侗水语支的侗族、水族、仫佬族和毛南族以及黎语支的黎族。越人对竹的崇拜显示出一种图腾,相信竹与本民族存在血缘关系,这一点在海南岛的黎族当中表现最为明显。如海南西南部地区的黎族,每当有人去世时会举行大型丧祭仪式,黎族巫师则念颂《黎族祖先歌》,第一句就明确提到“人类孕育在竹筒,竹筒破裂人类生”[23]。黎族今天跳的竹竿舞、做的竹筒饭在早期都是用于祭祀祖先的。黎族至今在丧葬活动中还保留砍竹条编织灵床的风俗----“净身洗尸后,亲属把用竹条编织好的灵床(黎语称[zya])放在堂屋中央的凳子上,灵床上铺一张露兜叶席,席上横放 3 条白线,再把遗体置于上面,头朝里。”[24]黎族对死者的忌日看得很重,每逢忌日,禁忌下种和犁耙田,七八年之后,在忌日种植芭蕉和竹子,等芭蕉和竹子成林时,才解除忌日里的禁忌。侗族在生育、丧葬、婚嫁等仪式中,历来都有“陪竹”“祭竹”“葬竹”“隔竹”的仪式。而布依族为老人做超度仪式时,“布摩”要诵《祭祖经》,经文强调祖先来自竹灵----“请你从那水竹口,你从水竹来;你从那楠竹口,你从楠竹来;来享儿孙酒,来享儿孙鱼。”布依族的丧葬仪式用大楠竹作灵幡,出丧时孝子肩扛金竹走在棺材前,此习俗意为“神竹引路”。安葬完毕后将竹尖留有竹叶的大楠竹插在坟头,以象征死者灵魂回归祖地[25]。壮族的传统丧葬仪式中在人去世的那一刻,需要用竹竿捅去一片瓦, 开一个天窗,使死者的鬼魂有处升天,免得留下来扰得家里不宁[26]。由此可见,竹崇拜在百越民族当中是很普遍的,而且这种崇拜涉及祖先灵魂的信仰。
正史对南方少数民族竹崇拜的记载最早见于东晋常璩撰写的《华阳国志·南中志》,曰:“有竹王者,兴于遁水,有一女子,浣于水滨,有三节大竹,流入女子足间,推之不肯去。闻有儿声,取持归,破之,得一男儿,长养有才武,遂雄夷狄。氏以竹为姓。捐所破竹于野,成竹林,今竹王祠竹林是也。”[27]其后,《后汉书》《蜀王本纪》《水经注》《述异记》《搜神记》等相关文献均有引述。《后汉书》还明确了“遁水”所在的地理位置和分布的民族,曰“夜郎者,初有女子浣于遁水,有三节大竹流入足间,闻其中有号声,剖竹视之,得一男儿,归而养之。及长,有才武,自立为夜郎侯,以竹为姓”[28]。夜郎,即现在居住于贵州南部的仡佬族。汉朝时期的夜郎国与华南地区的南越国毗邻,仡佬族与百越具有亲缘关系[29]。从这个传说还可以看出,竹与女子的结合生下了男祖先。很显然,竹带有男性的气质,而且具有生育的功能。竹生小孩就等于男人生小孩,其实已经隐喻了血缘关系对父权的确认,与20世纪50年代广西壮族部分地区存在的“产翁”习俗异曲同工。按照迪尔凯姆关于宗教来源于“社会事实”[30]的观点,不难解读出南方少数民族中竹图腾的这一支系至少在东晋时就开始由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了。而迟至明代,随着王朝礼教在南越大地的推广,编户齐民、里甲制度的推进以及和中原移民的交往交流交融,大多有竹图腾崇拜的越人完成了由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的过渡,编写了族谱并成立了宗族。
五、结论
行文至此,笔者希望能从理论和方法层面对前人的研究做出三点回应。首先,无论是“汉化说”,还是“隐瞒身份说”“宗族建设需求说”,其潜在逻辑都把“珠玑巷子民”视为“理性人”,认为“珠玑巷人南迁传说”是“珠玑巷子民”为了应付某种情势有目的地编造出来的,但笔者的研究恰恰显示,“珠玑巷子民”呈现的不是理性,而是信仰。这一信仰的形成是随着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加深自然产生的,假如说它恰好能够应对某种情势,也只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其次,少数民族与汉族的交融不等同于“汉化”,珠玑巷个案清楚地显示:越人的祖先(竹)信仰与汉人儒家的宗族观念交融所营造出的精神空间,既让越人的祖先(竹)崇拜得到充分的表达,也使汉人的“孝”“义”等宗族意识得以充分释放。而且“竹筒装灵魂→甘蔗祭祖→崇竹起‘符’→种竹子”的仪式特征显示出了一个关于竹图腾的连续体,少数民族的文化并没有消失,它只是以一种隐性的方式存在,并与汉文化以显性的方式构成了事件的一体两面,而脱离任何一面去理解事件都是不完整的。最后,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频繁交往交流交融的国度而言,阐释一种单纯的民族文化是困难的,因此,既需要有从“中心”看“周边”的学术视角,更需要有从“周边”看“中心”的学术情怀。就珠玑巷个案而言,从“中心”看“周边”,容易陷入实证主义路线,即认为广府人族谱中的“珠玑巷”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地名,其他地方族谱所写的“珠玑巷”(谐音)不过是受珠三角影响而已,于是热衷到河南开封、江苏南京、福建莆田等地去考证族谱中所谓“珠玑巷”的地理位置,结果是无功而返。假如我们从“周边”看“中心”,则发现“珠玑巷”并不是一个真实的地名,与其说“祖先来自珠玑巷”,毋宁说“祖先来自竹子巷”。在这个意义上,“珠玑巷”同样超越了地理概念,具有方法论的意义,而且凝聚着汉越人民共铸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