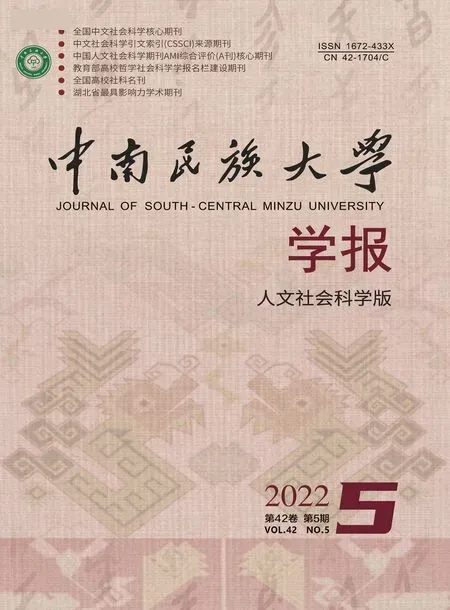中西传统性别差等及其文学表征
2022-11-22任现品
任现品
(烟台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烟台 264005)
性别差等即社会性别的不平等,常表述为“男主女从”或“男优女劣”。这种性别等级在世界各民族文化中普遍存在,而由于社会文化结构不同,中西传统性别差等呈现出迥异形态:中国因受一体性思维的影响,倾向于“先把世界看成是混沌未分的世界——太极,再看成混沌中有显隐、动静、刚柔、虚实的差别”[1]198的阴阳两极,在一体性思维与儒家意识形态的合力作用下,传统的性别差等是家族一元体内两性阴阳互动的男尊女卑,又通过男尊女卑的方式实现阴阳和合的一体性目的[2];西方则在两离性思维、本体论的引导下,将两性关系认定为差异对立的二元结构,“就西方文化总体而言,男性和女性的性差异倾向于建立在二元分类的基础上,而且这种差异被认为决定了性别差异”[3]263,这种性别关系与基督教意识形态的融合,表现为上帝旨意下男性压制女性的二元对立。中西传统性别差等的这种差异映射在虚实相生的文学作品中,呈现出形态各异的性别关系书写。笔者从性别差等入手,比较中西两性归属对象、女性卑从性质及两性关系格局等层面的差异及其文学表征,以揭示中西异质文化对社会性别观念的深层规约及多重影响。
一、两性归属对象不同:从属于家族一元体和皈依于上帝
性别差等作为性别不平等关系,是父权制性别定位的核心内容,与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既密切相关又交错叠合,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56性别关系自然蕴含着社会历史文化的多重元素。中国传统的性别观念深受儒家意识形态影响,两性关系形成于家族内部,并因“家国同构”的思想延伸到社会政治层面,“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5]161。男女都从属于家族,都不是独立的个体,性别关系是家族一元体内两性阴阳互动的男尊女卑,并与阳尊阴卑的自然秩序、君尊臣卑的社会秩序交错互证[6]。不同于中国,西方的性别观念有两种文化渊源——希腊文化与希伯来文化,二者都持男权中心观念。希腊神话中“潘多拉的盒子”将女性指认为灾难的来源,亚里士多德也说:“女人之所以是女人,是因为她们身体缺少某些品质,也因为这些天然的缺憾而遭受痛苦。”[7]15希伯来文化对女性的歧视与厌恶无不体现在《圣经》中,正是女人夏娃偷食禁果,人类才被逐出伊甸园,并用一生来赎罪。两希文化中的性别关系都突破了血缘家族,并随着历史演进拓展到基督教信仰领域,两性都作为犯有原罪的个体信奉至高无上的上帝,如“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8]3可见,西方的性别定位是上帝旨意下的男优女劣,男权社会文化借助于基督教将性别差等加以神圣化,拥有了更强大的思想控制力。
与上帝旨意下的男优女劣相比,中国家族一元体内的男尊女卑具有中国父权制的独特内涵。概言之,西方的父权制是男权制,女性是其压制对象。“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8]2女性作为男人的一根肋骨,要永远服从于男人。男性按照上帝旨令管制女性,女性因听命上帝而服从男性,不存在制约两性的家族利益实体,“丈夫在家中居于统治地位,以及生育只可能是他自己的并且应当继承他的财产的子女”[9];中国的父权制则是父系族权制,常由父家长作为家族代理人管理所有成员,因而中国女性不是直接服从于作为个体的父或夫,而是在两性都从属于父权家族的前提下再服从相关男性。犹如阴阳两仪从属于太极,男女共同从属于父系家族。“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10]541两性只是家族一元体的阴阳两仪,并不具有个体独立性,家族一元体始终制约着他们,使之以家族为核心,从而化解了两性间的直接对抗。因此,中国的两性关系不同于西方式的二元对立,而是相异互依的共同体。在西方,两性作为个体共同皈依于上帝,服从于上帝的旨意。上帝旨意虽存在着男优女劣的性别差等,但男女都作为个人直接接受上帝的奖惩。在个人与上帝之间、男人与女人之间不存在从属关系,只存在服从关系。上帝、男性、女性之间是分离的,这和中国所强调的个人从属于家族、没有个人独立性、只能作为家族一员而存在的思想有着本质不同。
这种归属对象的差异造成中西方不同的男女生活状态,构成文学想象的生活基础,并以感性生命的形式融入作家的艺术构思,反映到文学作品的两性关系书写中。因此,中国文学多表现父权制对男女个人的共同压制,即便是男性,也受家族代理人的掌控。而西方文学则多描写男性遵从上帝旨意管制女性的内容。如《孔雀东南飞》中恩爱夫妻最终命归黄泉,其悲剧根源不是男性压制女性,而是双方家长(焦母、刘兄)强行拆散,主人公男女却都无力抗拒家族代理人的权力。唐传奇《霍小玉传》中的李益,正是在家族一元体的强大规约之下,辜负了痴情的小玉,作品着力描写了他在个人情感和家长意愿对立中的纠结,最终他因屈从母命而背盟负义。相比于伊阿宋为获取权势、财富而主动抛弃美狄亚,李益则表现出更多的被动与无奈。陆游《钗头凤》中,作者与爱妻被迫分离,内心遭受持久的折磨,其中“东风恶”三字,暗示了作者难言痛苦的根源,即“不敢逆尊者意”而终“与妇诀”。《红楼梦》中的贾母既疼爱宝玉又爱怜黛玉,对宝黛的感情之真切也甚是明了,之所以同意实施调包计,不是出于作为祖母的情感意愿,而是作为家族代理人的理性选择。即便被宠溺的贾宝玉也不能自主选妻,家族一元体对所有成员的规约可见一斑。
西方文学中,因男权制的管制对象限于女性,其压制力量主要来自男性。从《荷马史诗》开始,女性就被作为财富、荣誉的象征,成为男人们征服、抢夺的对象,如对海伦的争夺成为特洛伊战争的导火索。《圣经》“摩西十诫”就告诫男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8]72女性与房屋、牛驴等相提并论,意味着女性只是男性的所有物。后来的文学延续了这一思维模式,并注入作家个体生命体验和社会时代内涵,如《卡斯特桥市长》中的苏珊,不仅日常要忍受丈夫亨查德的酗酒、偏执,还要被他强行卖给水手,苏珊悲剧的直接制造者是其丈夫;《德伯家的苔丝》中苔丝的悲剧命运是由亚雷·德伯、安吉·克莱尔等男性直接造成的;《欧也妮·葛朗台》中葛朗台夫人及女儿欧也妮都生活在老葛朗台的经济控制与生活管束之下,直到他死才得以自由;德莱塞的《美国悲剧》《嘉莉妹妹》等,也都有男性为实现发财梦而以女性为垫脚石的情节。这些作品中男性形象压制女性,除其生理优势和男权社会的制度保障外,更仰仗上帝旨意下的神授权力。
由此,中西文学中男性形象的生命状态明显不同,只因各种原因未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概言之,西方传统文学中的男性,因承接上帝在人间的权力又不受家族的制约,具有较强的自主意识与决断能力。如《伊利亚特》中因荣誉礼物被阿伽门农剥夺而愤怒罢战的阿喀琉斯;《浮士德》中因不满现状与魔鬼签约而竭力探求社会理想、人生意义的浮士德;《红与黑》中的于连,为个人前途不惜利用市长夫人、侯爵小姐的感情向上流社会进军;《呼啸山庄》中的希斯克利夫,因早年的不公正待遇疯狂地复仇;还有《鲁滨逊漂流记》中的鲁滨逊,他既热衷冒险又不断积累财富;等等。这些作品中的男性形象都表现出强烈的征服欲望与个人权益意识。中国传统文学中的男性形象因受制于家族,带有比较明显的依附性。他们不仅自身从属于家族无法生成明确的个人权益意识,而且由于自我权益与家族利益的交叠,又无法产生激烈的抗争念头与决裂行为,因而呈现出两种男性形象:一种是屈从家族需要、违背自我意愿的男性,如焦仲卿、李益等;另一种是为家国利益舍生忘死的男性,如杨家将、岳飞等。这两种形象都凸显了个人对家族的从属与牺牲的特征。
西方文学中两性共同皈依于上帝,其中男性因听命上帝而拥有土地、财富,并管制着妻子,具有相当的自主性。女性因听命上帝而服从丈夫,承受着生活的苦难与丈夫的压制。但是,两性都渴望成为上帝的选民,以回归天国,其听命行为的背后隐藏着一个至高权威——上帝。中国文学中男女共同从属于家族一元体,双方都借助家族将对方包含于自身成为一个无法分割的整体,并始终围绕着家族利益的轴心运转,都没有个人独立自主性,即使皇帝也不能因个人情感而违逆家国利益的需要。如洪昇《长生殿》中的唐明皇忍痛赐死杨贵妃,与莎士比亚《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中的安东尼为爱情蔑视死亡、舍弃一切构成了鲜明对比。总之,两性归属对象的差异,造成了中西文学中人物形象内涵及自主意识强弱的不同,是中西文学中性别差等最为显著的特征。
二、女性卑从性质不同:双重从属的男尊女卑与双重服从的男优女劣
家族一元体内,女性在两性共同从属于父系家族的前提下又从属于相关男性。“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11]355“三从”确保了女性终生处于从属位置,因而中国女性的卑从是一种双重从属,既从属于父系家族又从属于家族代理人,这种双重从属的生活和精神状态,使女性彻底丧失了萌生个人权益意识的可能。上帝旨意下的男优女劣,则使西方女性因听命上帝而服从丈夫。上帝认为女人是邪恶的,其月经与生育都是污秽的,生女孩尤其污秽。“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若有妇人怀孕生男孩,她就不洁净七天,像在月经污秽的日子不洁净一样。……她若生女孩,就不洁净两个七天。’”[8]103-104女性不仅忍受怀孕、生育之痛,还要被丈夫管辖。西方女性因服从神的命令而服从丈夫,这是一种双重服从,并且女性的服从地位被神圣化,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女性的反抗意识。
无论双重从属的男尊女卑,还是双重服从的男优女劣,都将女性定为“第二性”。中西传统性别差等观念可谓殊途同归,集中体现了二者社会文化的男权本质。中西女性的卑从地位首先表现为贞节标准的单向化,即贞节只针对女性,又因文化取向的差异,中国带有浓郁的世俗色彩,西方则弥漫着强烈的宗教意味。在中国,女性以“贞节”为吉,男性反而以“贞节”为凶。“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10]506正是家族一元体的利益诉求,男女婚姻成为合两姓之好的纽带,“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11]456。男女都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伦理规范,而父兄掌控个人婚配对象的选择权,用以结交强援、扩大家族势力。现实存在的婚姻模式为文学想象提供了感性材料,如《三国演义》中的二乔与孙尚香、《红楼梦》中的元春与探春等,其婚姻对象的选择都是出于对家族一元体的利益考量。但是,女子只有一嫁,男性却可多娶。如《红楼梦》中的贾琏瞒着王熙凤为尤二姐另立别宅、贾赦欲纳鸳鸯为妾,《三国演义》中的吕布在正室之外又纳貂蝉为妾,《金瓶梅》中的西门庆更是妻妾成群,等等。虽然维护父系家族血缘的纯粹性与人丁兴旺是单向贞节标准的目的所在,但实质上却呈现出男尊女卑的性别等级。在西方,婚姻是当事人在神坛面前缔结的契约关系,家族和他人都无权干涉,因而其对女性的贞节要求不是基于中国式的家族需要,而是被赋予神意的权威,如《希腊神话》中的贞节女神阿尔忒弥斯、圣母玛利亚等都强化了贞节的神圣性与合理性。此后,在基督教教义的影响下,又将女性贞节视为一种虔诚崇敬的赎罪行为,许以幸福的彼岸世界,被涂抹上了一层神性色彩,充分体现了男权社会世俗权力与基督教之间的合谋。至于世俗女性常因贞节而命运多舛,如哈代笔下的苔丝、德莱塞塑造的嘉莉妹妹与珍妮姑娘,其不幸遭际都源于身体的失贞,可谓女性现实处境在文学艺术中的反映。“国家意识形态永远都是与男性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同谋的,它自身就是一个父权制的象征秩序与权力结构。”[12]75在这方面,中西方皆如此。
中西女性的卑从地位还表现为个人价值实现方式的间接化,即都通过维护男权社会来实现自我价值。在中国传统“家国同构”的社会组织中,女性无法像男性那样通过“修齐治平”的途径来实现个人价值,唯有借助家族一元体间接实现自我,即通过做“孝妇”“贤妻”“良母”,在实现夫家兴旺、儿孙发达中,借助“妻以夫荣”“母以子贵”的途径间接实现自身价值,提高个人社会地位。受基督教影响,西方男女个人价值的实现方式都来自于上帝约定,表面看似没有区别,但上帝与男女两性的约定内容不同:耶和华与亚当(男性)约定的是“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8]3,把土地所有权交给了他;耶和华与夏娃(女性)约定的是“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8]3。可见,男性通过辛苦劳作、获取财富、掌管女性来实现自我价值,女性则借助于生育后代、服从丈夫获取自身价值。男女个人价值的实现方式都意在维护男权社会的利益,这与中国两性价值实现方式异曲同工,都体现了男权社会的本质。
贞节标准的单向化与女性实现自我方式的间接化,使中西方的两性生活状态全然不同。男性凭借个人努力获取权力、财富,只是中国男人以此光宗耀祖,西方男性用以体现上帝荣耀、彰显自我能力,只要前者不危及家族利益,后者不违逆宗教教义,个人生活无论怎样落拓不羁,都不会招致自我良心的拷问或社会舆论的谴责,因为男性在个人欲望、自我价值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要求是一致的。女性则不同,她们在单向化的贞节标准、间接化的价值实现方式的合力下,中国女性被分化为家族内、外两类,西方女性被分化为“天使”与“妖妇”。分类虽有不同,但都蕴含着男权文化贬低、利用女性的核心思想。对女性群体的分化,为作家展示人物命运、拷问人性内涵提供了现实生活依据。由此,中国文学中的家族内女性形象,常以维护父系家族利益来获取地位、价值等,以致背离了自身存在目的而被异化为维护父系家族利益的工具。例如,家族内女性为了延续家族香火,抬高自己地位与身价,产生了不同版本的“狸猫换太子”,直到莫言《丰乳肥臀》中上官鲁氏不惜代价的借种;家族内女性即使已开枝散叶,仍可能遭遇丈夫收婢纳妾,承受一夫多妻制的畸形婚姻所带来的痛苦,于是展开争斗,由此背负“妒妇”的恶名,如《金瓶梅》《红楼梦》中妻妾明争暗斗的情节一直延续到苏童的《妻妾成群》而未有停止的趋向。西方文学中的“天使”类女性形象,为了救赎自己作为人类原罪主犯的罪孽,虔诚地信奉上帝,遵从世俗的男性权威,作为温顺贞节的妻子,既要忍受人间苦难的煎熬,又要为丈夫、子女默默奉献,以洗清自身的罪孽,最后进入天国。如《奥赛罗》里的苔丝狄蒙娜,美丽柔顺,崇拜并听命于丈夫奥赛罗,最后竟被听信谗言的丈夫残忍地杀死;《少年维特的烦恼》中的绿蒂,听命于父亲的婚姻安排,婉拒维特的狂热追求;《贵族之家》中的丽莎,爱上了有妇之夫,为救赎这一“罪孽”而进了修道院;《一生》中的约娜,忍受丈夫背叛、儿子欺诈以完成此岸人生的救赎等,此类女性已成为西方小说的一种典型形象。基督教所赋予的宗教神圣性使西方婚姻超离了家族子嗣需要,因而“天使”类女性形象的子嗣生育并不影响其婚姻状况,这和中国女性千方百计地延续家族香火迥然不同。
另外,中西文学中的妓女形象也存在着类似差异。在具体生活形态上,中西妓女形象或许相距甚远,但在生存方式上并无根本区别,即都靠肉体取悦男性来获取生活资料,从而沦为男性玩物或流动性商品,丧失了做人尊严。她们若想要正常人的生活,中国妓女的唯一出路是回归家庭;西方妓女的不二选择则是皈依上帝,以洗清自身罪孽、死后进入天国。因此,中国传统文学中的名妓,如杜十娘、李娃、霍小玉、陈圆圆等,作为家族外女性形象,常为回归家庭而不惜代价,这种行为选择看似对不公命运的抗争,实则是她们竭力向父系家族伦理的就范,即使父系家族已将她们拒之门外,她们也要尽其所能力图从门缝中挤进去。西方妓女形象则不注重寻求现世生活状态的改变,而注重死后能否回到天国,因而她们选择虔诚地敬奉上帝,以化解自己的生命苦难,如《羊脂球》中的羊脂球、《茶花女》中的玛格丽特、《悲惨世界》中的芳汀、《复活》中的玛斯洛娃、《罪与罚》中的索菲亚等,作为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她们以身体的堕落完成献祭般的殉难,以宗教信仰的力量进行自我心灵的救赎。由于基督教的普救性,妓女也在可救赎之列,只是其精神救赎之路比常人更艰辛漫长而已。相比中国妓女欲挤进父系家族而不得的悲苦,西方妓女那种凭借生前忍耐换得死后的救赎,至少在精神上还有些慰藉。诚如阿尔都塞所说:“意识形态是以一种在个体中‘招募’主体(它包括所有个体)或把个体‘改造成’主体(它改造所有个体)的方式并运用非常准确的操作‘产生效果’或‘发挥功能作用’。”[13]中西妓女或回归家庭、或皈依上帝,她们的人生出路看似主体的主动选择,其实是意识形态把个体召唤为想象的主体,显示了父系家族伦理与男权宗教伦理所占据的统治地位。
三、两性关系格局不同:两性阴阳对反与男性单方面压制女性
家族一元体内的男尊女卑和上帝旨意下的男优女劣,都将女性定为“第二性”,体现了中西文化对两性关系的相同认定,这是男权社会本质的表征。但因中西两性的归属对象不同,两性关系格局也存在着很大差异。中国的家族一元体,使两性既共同从属于家族,又使女性从属于家族代理人,女性因而处于双重从属的地位,承受着父系家族及其代理人的双重管制。但家族的兴旺发达需要男女双方的共同经营,为激发被置于卑从地位的女性对家族利益的责任,规避男性彻底压制女性的倾斜状态,家族一元体的调节机制又补偿女性一定的家族事务参与权,即女性有权规劝或制止那些有损家族利益的男性,就像臣子为国家兴亡而进谏君王那样,起着辅助男性去振兴家族的功能。这就构成了家族一元体内的两性阴阳对反,整个性别差等结构也得以接榫成为一个循环系统,犹如那个富有包孕性的太极图。而在西方,上帝旨意下的男优女劣使两性共同服从上帝,而上帝的命令就是男人掌管女人,女人服从男人,不存在需要男女两性共同维护的更高利益实体,双方都听命于上帝即可。因而,西方女性卑从于男性是绝对的,是上帝的命令,即人神契约下的女性服从男性。“因为西方父权制社会对女性实施的是男性单级中心二元化的不对等统治,女性最重要的就是在这种不对等的权力模式中失去了平等权。”[14]这一男性掌管女性的二元对立,构成了男性单方面地压制女性的两性关系格局。可知,家族一元体内男尊女卑的阴阳互动与上帝旨意下男优女劣的二元对立,既构成鲜明对照又遥相呼应。
现实世界的两性关系格局通过作家生命体验、情感记忆的发酵,凝化为文学中的人物形象内涵。中国文学中,两性关系在男女阴阳对反的机制下,不再是不可变更的男尊女卑,而是交错变换的尊卑互动。西方女性因听命于上帝而服从于丈夫,无法获得制约男性的价值基点,因而始终处于卑从位置。因此,西方文学中的两性关系则是女性单方面地受制于男性,是固定不变的男优女劣,不存在尊卑交错的情形。虽然,家族一元体内的男女尊卑在阴阳对反中能互相转化,但是这种尊卑转换是有条件的,即以女性维护家族利益为前提。中国女性获得制约男性的权力依据不在自身,而在她们对父系家族的奉献大小与认同程度,所以,拥有这一权力的并非所有女性,而只是少数维护家族利益并被认可的女性,大致可分为下列三类。
1.恪守父权文化规范的女性形象。她们既以自己的贞静贤淑维护着家族名声,又能在男性违背礼制、危及家国秩序稳定时,适时恰当地给予劝导。例如,乐羊子妻与长孙皇后就被作为教夫模范,不断地出现在各种文学叙事中。这类形象与西方文学中的“天使”类女性形象比较相近,如《大卫·科波菲尔》中的朵拉、《双城记》中的露丝与《贵族之家》中的丽莎等。但“天使”只是美丽、纯洁、无私,虔诚地信奉上帝,听命丈夫,全方位地满足着男性对女性的审美期许,而根本无法制约男性。
2.拯救家族于颓败之际的“女中丈夫”形象。妓女欲回归家庭而不得的悲剧固然时有发生,但也并非绝对没有华丽转身的妓女形象,其关键在于妓女对家族一元体的贡献能否抵消其身份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如唐传奇中的《李娃传》和《警世通言》中的《赵春儿重旺曹家庄》,重视女性贞节、家族声誉的父系家族之所以能接纳妓女出身的李娃、赵春儿,根源在于她们扭转了家族趋于败落的走势而使其复兴。这在西方文学中是比较少见的,因为西方妓女多以肉身殉难来赎清罪孽、皈依上帝,而非借助于奉献父系家族获得世俗认可。
3.为家族的人丁兴旺与秩序稳定而辛勤操劳的母亲形象。相比照于西方文学,中国的母亲形象无疑是最为特殊的“他者”[15],其最具迷惑性的是母子关系,如《孔雀东南飞》中的焦母与焦仲卿、《霍小玉传》中的李母与李益、《红楼梦》中的贾母与贾政等,母亲在儿子面前都有一种不可侵犯的威严,她们掌管着教导儿子、决定儿子命运的话语权。还有《岳飞传》中的岳飞母亲、《三国演义》中的徐庶母亲、《杨家将》中的佘太君等,都因坚守伦理规范、超越个人生死,赢得晚辈的崇敬并扬名后世。西方文学中的母亲形象,如俄狄浦斯的母亲、哈姆莱特的母亲等,对儿子也表现出对男性的服从,全没有母亲的权威。即使希腊神话中的女神们,也都有嫉妒、贪图“最美”赞誉的弱点,如金苹果的故事,根本没有女娲抟土造人、炼石补天等保护族类的“母性品格”。希腊神话中的普洛克涅和《美狄亚》中的美狄亚,虽身为母亲,却更多是作为女性个人而存在,因而她们在反抗男权时,不惜杀死儿女以报复负心的丈夫。从更深层次来讲,中国母亲形象在儿子面前看似反卑为尊,其实已蜕化为父权制的维护者。在父系家族社会,母亲形象因将父权的家国之事优先考虑而被不断颂扬,不自觉中已演化为放弃个人主体性、承载父权文化的符号。而西方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单方面地受制于男性,即使母子之间也不例外,这种固定不变的男优女劣,看似女性始终处于卑从位置,其实质乃是男权文化尚未彻底分化、收编女性的明证,因而女性始终不曾放弃为追求自身性别权益的可能反抗,男性也一直未敢放松对这一反抗可能的打压。
家族一元体内的两性阴阳对反,最大程度地调动了女性投入父系家族事业的积极性,在有力维护家族制稳定延续的同时,也使女性由此掌握了制衡男性的某些权力,并以其独特方式实现个人社会价值。这看似女性反卑为尊的成功逆袭,其本质乃是女性完全放弃自我存在依据的表现,意味着父系族权在彻底分化女性的基础上,又成功收编了家族内女性,使其转化为父系家族的捍卫者。这是家族一元体制约性别关系的结果,其灵动交错的循环结构使男尊女卑的性别差等走向背反。“儒家伦理道德在女性身上体现的二律背反现象,使中国女性在自我意识的觉醒、自我解放的自觉性方面整体性地迟钝于西方女性。”[16]两性阴阳对反机制使中国女性走向了一条不归之路。而在西方,女性在基督教教义的规训下,虽单方面地受制于男性,始终处于卑从位置,却因此得以洞悉自身与男权社会文化的对立。另外,在“上帝的儿女都有翅膀”的基督教观念下,男女生而灵魂平等,这为女性争取自身权益、获得解放预留了可能性,只是在男权社会的持续打压下未能取得明显的进展。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对理性中心、人类中心等传统权威的反叛中脱颖而出,才真正拉开了对性别差等的社会批判与文化分析的序幕。
综上,中西传统性别差等的内涵、层次等存在着明显差异,其投射在虚实相生的文学叙事话语中,积淀为各具特色的叙事话语系统,成为性别意识形态的有机部分。中国传统性别差等比较隐蔽稳固,业已构成一个交错灵动的循环结构,很难被察觉,即使为某些先觉者发现也不易反抗。这是因压制男女个人的力量并非外在因素,而是与自我利益不可剥离的家族。内置性的压制力量使人们因压抑而产生的反抗冲动无从向外释放,只能向内反刍,从而形成一种向内用力的行为模式,造就了中国社会文化的超稳定与文学书写中“怨而不怒”的情感模式。而西方传统性别差等则比较直接明显,其性别压制易被发现,也易激起被压制者女性的反抗意识。因此,消除家族对男女两性的压制成为中国社会文化现代变革的关键,也使中国女性的解放路径不同于西方式的女性直接反抗男权,而是两性联手打破家族壁垒。五四以来的文学集中揭露家族制对个人主体性的泯灭,即“礼教吃人”,借此挣脱父系族权对男女个人的身心控制,使原有的性别差等结构应时代之变而调整组成元素。西方女性的解放路径则是女性凭借自身力量直接对抗男权社会文化,并孕育出了丰富的女性主义理论。这些理论如《第二性》《性政治》等,不仅详尽剖析了性别差等生成的内在机制及社会根源,而且与女性主义神学、生态女性主义等其他理论互渗融合,深化了自身观点,纠正了一向存在的性别偏见,以最终恢复女性的地位与权利为宗旨。
诚然,文学作为把握世界的一种艺术方式,对人的行为和心灵给予整体观照,比其他意识形态更具有含混性与复杂性。因此,中西传统文学并非单纯地依据各自社会的性别差等塑造人物,而是融合了作家个人生命体验、时代生活的主流态势与民族文化心理等,使艺术世界的两性关系呈现出形态各异的复杂特征。例如,中国文学作品中《李娃传》《金瓶梅》《红楼梦》等虽有类似的性别关系模式,但人物设置、情感倾向与叙事旨归又都各有特色。西方文学的复杂多变也是有目共睹的,不必说《悲惨世界》与《巴黎圣母院》、《罪与罚》与《战争与和平》的差异,即便法国同时代描写妓女生活的《娜娜》与《羊脂球》也各有千秋:前者更多地把妓女娜娜的悲苦命运与遗传生理因素相关联,带有自然主义的倾向;后者则更多地借助于妓女羊脂球的选择反衬法国上流社会的可耻,蕴含着时代反思的意味。但是,二者都塑造了鲜活的人物形象,并融入作家的情感判断与价值思考。由此,本文只是对中西民族性别差等及其文学表征的总体勾勒与宏观对照,并不否定其内在的复杂多样性。笔者也相信,随着中西文化、文学比较的不断深入,对二者的相似层面与丰富差异会有更多新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