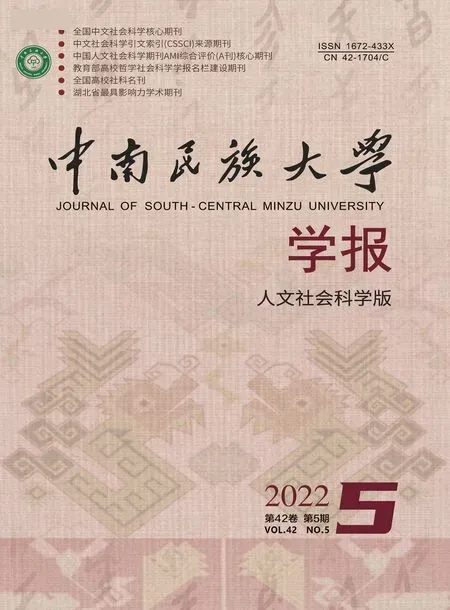国有企业在ICSID管辖权中的仲裁资格
2022-11-22伍穗龙
伍穗龙
(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上海 200336)
一、引言
理查德·鲍德温在《大融合》一书中曾将全球化进程比喻为三次不同阶段的松绑。得益于信息与通讯技术革命的发展,第二阶段松绑下的贸易-投资-服务一体化纽带已经在全球形成[1]。伴随而来的是国际投资重要性逐步超越国际贸易、且金额及数量日渐增多的局面,其中,国有企业功不可没。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统计数据,当前全球至少有500家跨国国有企业,把控超过2万亿美元资产(1)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4: Investing in the SDGs: An Action Plan, Geneva, 2014.。与所掌握的大量资金及资源相对应,2010年以来,国有企业由于海外投资而引发的法律争端数量也呈现上升趋势[2]615-616。
经济性的国际争端,大致有政治解决和法律解决两种方式。投资争端通过一国国内司法体系获得救济,难免有政治化之嫌。作为以去政治化、促进国际私人投资为设立宗旨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 ICSID),自1965年建立以来,被诸多国际投资协定甄别为解决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的国际投资仲裁平台之一[3],渐次随着国际投资的快速增长而成为最为重要的解决投资者-国家争端第三方机构。中国于1990年签署《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投资争端公约》(《ICSID公约》),并于1993年成为缔约方。根据该公约规定,中国企业(包括国有企业)与其他缔约国由于投资而引发的争议可以诉诸依该公约要求设立的ICSID机构予以解决。
但在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案件中,投资者仲裁资格又是必须明确的先决问题,就此产生的属人管辖权异议成为诸多案件无法进入实体审理阶段的重要原因。特别对于国有企业而言,其在公约允许下的投资仲裁资格并非直接适用。一方面,现有公约并未就国有企业的仲裁适格资格做出明确界定。同时,由于国有企业可能兼具公共职能及经济职能双重身份,国有企业投资者的仲裁适格资格问题较私人投资者复杂。已有国内学者的研究及仲裁庭在实践中形成的观点存在一定偏差[4]。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也是中国海外投资主力军。随着中国经济体量增大,国有企业海外投资已经呈现快速增长趋势。中国国有企业必将面临更多通过ICSID项下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进行仲裁以解决海外投资纠纷的情况。因此,清楚把握国有企业在ICSID中的仲裁申请门槛,从而在管辖权阶段保障中国国有企业的ICSID仲裁申请资格就构成本文的初衷。下文将分别从规范分析、案例实践及理论重构三个维度,明晰国有企业ICSID仲裁申请资格。
二、《ICSID公约》文本对国有企业作为适格仲裁申请人的判断(2)本研究不讨论双边投资协定中影响国有企业能否成为ICSID适格仲裁申请人的情形,默认国有企业满足双边投资协定对“投资者”内涵与外延之界定。关于双边投资协定对“投资者”界定,可参见梁一新:《 论国有企业在ICSID的仲裁申请资格》,《法学杂志》,2017年第10期。
《ICSID公约》缔结于20世纪60年代,正是发达国家在第三世界资本投入蜂拥之时,也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的跨国公司向全球投资逐渐激增之期[5]。出于对其国内海外投资者的保护需求,国际上迫切需要在既有国家与国家、私人与私人投资争端解决外建立一个第三方机构,以解决私人投资在东道国激增而引起的法律纠纷。在上述背景下,《ICSID公约》于1965年在华盛顿缔结,公约下的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应运而生。
作为国际投资争端去政治化的产物,该公约反映了当时对国际私人投资的保护倾向[6]。其仅调整私人投资者(一国国民)与国家就投资而起的法律争议,而不调整国家与国家之间由于投资而起的纠纷。该公约第25条就ICSID机构管辖权做出明确:“(ICSID)中心的管辖适用于缔约国(或缔约国指派到中心的该国的任何组成部分或机构)和另一缔约国国民之间直接因投资而产生的任何法律争端。”(3)Convention on the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 between States and Nationals of Other States, Article 25.1.但是,对国有企业能否作为适格仲裁申请人,《ICSID公约》却语焉不详。因此,国有企业能否作为适格仲裁申请人,关键在于理解国有企业是否属于上述条款中界定的“国民”(私人投资者)。按照国际条约解释的通行方法,需要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4)See 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依次遵循条约的文意、缔约目的以及缔约历史对条款进行解读(5)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 Article 31.。
以《ICSID公约》文意视之,管辖权条款仅适用于缔约国与一国国民间因投资直接产生的法律纠纷,其排除了适用于缔约国与缔约国之间以及私人与私人之间投资法律纠纷的可能。根据文意,另一国民,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就法人而言,《ICSID公约》并未明确排除国有企业。
以《ICSID公约》缔约目的观之,鼓励私人投资及去政治化是《ICSID公约》目的的一体两面。《ICSID公约》序言明文提及“本公约旨在促进私人国际投资”,“……考虑到对经济发展进行国际合作的必要性和私人国际投资在这方面的作用……”(6)Convention on the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 between States and Nationals of Other States, Preamble.。说明公约的目的是为促进私人投资而非公共投资[7],其只是不鼓励在公约的管辖范围之纳入国与国之间的投资争端。同时,投资争端的去政治化也是《ICSID公约》缔结目的之一,《ICSID公约》第27条中提及“不得给予投资者以外交保护”就是意在区分传统的国家保护与私人投资之间的界限[8]。由此,兼具公共职能与经济职能的国有企业若以经济职能行事,作为一个普通的市场经济主体,其与《ICSID公约》所鼓励的私人投资无异,《ICSID公约》的目的并不排除对此类投资主体之调整。
最后,回顾《ICSID公约》缔结历史,缔约方已注意到“另一缔约国国民”并不限于私有企业。1965年《世界银行执行报告》早已提及:“《ICSID公约》建立之目的在于建立旨在促进解决国家与外国投资者之间争端的机构从而刺激更多的私人(不仅限于私有企业)国际资本流入希望吸引它们的国家。”[5]《ICSID公约》草案评论也予以印证,当时缔约方已注意到“另一缔约国国民”并不限于私有企业,而是“允许政府所有或政府部分所有的企业以申请方与被申请方身份参与与另一缔约国的投资仲裁”[9]。学者Schreuer甚至言明,“谈判历史资料表明,当时谈判各方一致认为,混合所有制企业或政府所有的公司并不必然被排除在‘另一缔约国国民’范围之外”[9]。
基于公约文意、宗旨与谈判历史对《ICSID公约》第25条的属人管辖规定的分析表明,《ICSID公约》并未排除国有企业作为适格仲裁申请人的可能性。历史发展也证明该结论符合不断变化的市场逻辑。21世纪全球化的第二次松绑加速了全球经济舞台上参加主体的多样性与异质性,当中既有国有企业、私有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ICSID公约》对国有企业开放的态度为迎合全球投资的发展打下基础。
三、ICSID实践对国有企业作为适格仲裁申请人标准的诠释
虽然基于《ICSID公约》文本解读而得出国有企业可成为ICSID仲裁适格申请人的结论,但《ICSID公约》文本并未解决国有企业在何种情况下可以成为仲裁申请人这一核心问题。《ICSID公约》并非“冰封”的法律文本,实践中,由《ICSID公约》之父Broches先生提出的Broches标准及ICSID仲裁庭基于该标准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明晰了上述问题。
(一)Broches标准
1972年,《ICSID公约》之父Broches先生对国有企业越来越多参与国际投资的现状给予了关注。其否定了传统的以出资来源为根本判断标准审视国有企业是否适格仲裁申请人的观点,提出“政府职能”及“政府代理人”说以因应日益变化的国际投资新发展。Broches先生认为:“传统的以出资来源界分公共及私人投资之方法,如果尚未过时,已经不符合当下全球投资发展趋势。大量的国有企业在全球投资中扮演重要角色。”[9]是故“出于《ICSID公约》目的,混合所有制或者政府所有应该被视为另一缔约国的国民,除非该‘充当政府代理人’或者‘行使基本政府职能’”[10]。此谓著名的Broches标准。
Broches标准的提出,进一步阐释了《ICSID公约》适格仲裁申请人的条件,准确把握了国有企业投资者可能存在执行国家职能与执行商业职能。“充当政府代理人”或“行使基本政府职能”要件的提出,也部分反映了自20世纪以来国家豁免及国家责任理论对“商业交易”-主权行为与商业行为界分-判断标准在国际法上的发展趋势。但遗憾在于Broches标准并无对“充当政府代理人”及“行使基本政府职能”两个要件做进一步解释。仲裁庭在日后,出于实践需要,又通过案件对Broches标准做出了阐释与发展。
(二)CSOB诉斯洛伐克案及北京城建集团诉也门政府案对Broches标准要件的阐释
截至2021年底,ICSID正在审理或审结的案件数已多达1150件(7)See ICSID Cases Database, https://icsid.worldbank.org/en/Pages/cases/searchcases.aspx.。其中,CSOB诉斯洛伐克案(8)See CSOB v. Slovak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97/4.以及北京城建集团诉也门政府案(9)See Beijing Urban Construction Group Co. Ltd. v. Republic of Yemen, ICSID Case No. ARB/14/30.是仅有的两个对“充当政府代理人”或“行使基本政府职能”要件展开了有益但并不深入讨论尝试的案件[2]615-616,一定程度上对相关适用门槛做出了规范。两个案件仲裁庭裁决均对Broches标准中的“行使基本政府职能”的判断标准进行明确,但就“充当政府代理人”要件,两个案件仲裁庭均无深入触及。
1.CSOB诉斯洛伐克案。该案中,仲裁申请方CSOB银行为捷克政府所有的公有银行。苏联解体后,为便利捷克和斯洛伐克分立之后CSOB银行的私有化,捷克和斯洛伐克两国财政部签订了《Consolidation协议》。协议规定CSOB银行将部分不良资产组合转让给两个分别由捷克政府和斯洛伐克政府设立的Collection公司。为确保转让顺利进行,CSOB银行分别向两个“Collection公司”提供特别贷款。而后,由于斯洛伐克政府拖欠偿还贷款,1997年,CSOB银行对斯洛伐克提起ICSID仲裁,认为斯洛伐克违反《Consolidation协议》。而被申请人斯洛伐克则对CSOB 银行与斯洛伐克的“Collection公司”签订的贷款协议提出若干管辖权异议。最为核心的异议是,认为CSOB银行不是《ICSID公约》第25条中的“国民”,而是捷克政府代理人,由此仲裁庭对该案缺乏管辖权基础。
经审理,仲裁庭驳回了被申请人的管辖权异议,支持了该案中CSOB银行为适格仲裁申请人的主张。仲裁庭在参考《ICSID公约》立法历史基础上,引入被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广泛认可的Broches标准,分析CSOB银行是否属于第25条中的“国民”。首先,仲裁庭同意不以出资作为判断一企业是否为“国民”的门槛。仲裁庭指出:“一个企业是否为另一缔约方的‘国民’,并不取决于该企业是否全部或者部分由国家所有。”而后,仲裁庭确立双方认同的Broches标准两要件“充当政府代理人”或 “行使基本政府职能”为国有企业被拒绝赋予仲裁申请人资格的条件。在考察“行使基本政府职能”要件时,仲裁庭明确了商业行为性质而非行为目的的“商业交易”判断标准。仲裁庭强调,考察“行使基本政府职能”要件时,应该考察企业行为的性质而非行为背后的目的(涉案行为背后所带有的政府意愿色彩)。因此,仲裁庭认为,CSOB银行行为性质本身具有商业属性,足以认定其为适格的仲裁申请人,尽管CSOB的行为是在国家政策的驱动下实施的,但是这一解释CSOB行为目的性的因素并不足以阻碍仲裁庭认定其为适格的仲裁申请人。而就“充当政府代理人”这一要件,仲裁庭并无对其单独考察,而是将其与Broches标准的“行使基本政府职能”要件结合起来一同考察。
2.北京城建集团诉也门政府案。2017年5月30日就管辖权做出裁决的北京城建集团诉也门政府一案也涉及国有企业的仲裁适格资格问题。该案缘起北京城建集团(全资国企)于2006年初中标的萨那国际机场新航站楼工程的纠纷。2009年7月,也门政府通过军事力量袭击并扣留北京城建集团员工,并强行禁止北京城建集团进入工地履行合同义务。随后,北京城建集团以也门政府违反《中国-也门投资促进及相互保护协定》为由,将也门政府诉诸ICSID投资仲裁。
与CSOB诉斯洛伐克案相类似,北京城建集团诉也门政府案仲裁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双方同样就北京城建集团是否适格仲裁申请人存有分歧。经审理,仲裁庭对北京城建是否适格仲裁申请人做出了裁决。首先,在对北京城建集团性质认定上,仲裁庭承认北京城建集团在其投标文件中对自己的描述为“中国前500强国有企业”的正确性,认定其性质为中国政府设立并公开拨款的全资国有实体。其次,就北京城建集团是否“行使基本政府职能”,仲裁庭同意CSOB诉斯洛伐克案仲裁裁决中做出的“企业行为性质作为判断其是否行使基本政府职能”的判断标准,认为即使“中国政府是北京城建集团的最高决策制定者,但是本案中北京城建集团显然并没有在机场施工地点履行政府职能,其行为仅仅是基于合同”。最后,就北京城建集团是否为中国政府代理人问题,仲裁庭认为本案争议点不在于北京城建集团作为国有企业的公司架构----即使中国政府确实对北京城建集团发号施令,而在于本案证据表明,北京城建集团在该工程项目中均是以商业合同方履行其机场工程项目义务,而并非根据中国政府指示为之。
(三)前述两案Broches标准解读的不足
虽然CSOB诉斯洛伐克案及北京城建诉也门政府案通过仲裁庭实践对Broches标准进一步做出阐释与解读,但笔者以为,相关仲裁庭的解释存在以下两方面不足。
第一,CSOB诉斯洛伐克案及北京城建集团诉也门政府案对国有企业是否属于“国民”-“行使基本政府职能”要件的解读,依赖的是行为性质标准,即国有企业行为性质本质上是商业性还是国家性这一要求进行界分。在CSOB诉斯洛伐克案中,仲裁庭甚至还对不考虑行为的目的做了充分的说理,认为即使CSOB代表国家实施相关行为并存在推动政府政策之目的,但该目的并不能掩盖CSOB行为的商业性本质(10)See CSOB v. Slovak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97/4, Award, 29 December 2004, para.12.。诚然,依赖简单的行为性质标准,把形式抽离出实质,仲裁庭意欲在私人投资者与国家投资者之间做简单的划分,意在达至简单、高效的处理手段与方法,希望构建容易为后案所理解及遵循的“先例”。但是这一简单的标准与界分,无法洞悉行为背后目的之不同而形成的行为性质不同,明显与当下渐趋复杂的国际法实践与国际习惯法的发展不一致。仅仅以行为的性质,而不考虑目的的方法对一行为做国家行为或商业行为之界定,可能与私人主体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事务,而国家机构也越来越多地从事商业交易的现状有所不符[11],而且似乎也与越来越趋向综合的判断标准南辕北辙。
第二,两个案件均未对“充当政府代理人”要件做深入阐释。Broches标准的第二个要件为“充当政府代理人”,该要件自Broches标准被提出后尚未被ICSID任何案件仲裁庭以正确范式深入触及。虽然在CSOB诉斯洛伐克案中,仲裁庭两次注意到斯洛伐克关于“CSOB是捷克的政府代理人”这一主张,但仲裁庭就此并无给予该要件与第一个要件同等的关注度。甚至,该案仲裁庭将“充当政府代理人”与“行使基本政府职能”要件混为一谈,未能为这一标准的正确解释提供任何富有价值性的信息。在北京城建集团诉也门政府案中,与CSOB诉斯洛伐克案相类似,虽然仲裁庭明确了Broches标准两个要件之间的差异,但仲裁庭在分析时却并无对何为“充当政府代理人”做出充分解释,而仅仅简单继续陈述北京城建的行为是商业行为,其基于合同的行为是商业行为这一论断表明其并无“充当政府代理人”,当中仲裁庭对此问题展开的论争、推理、解释之简单着实令人疑惑。事实是,由于“充当政府代理人”说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第8条的“受到国家或政府指示”的相关构成要件具有高度相似性,故对该要件的判断,关键在于判断何时国有企业“受到国家或政府指示”,从而可以合理被视为国家之代表。
四、对Broches标准的正确重构
当前,ICSID仲裁庭实践对Broches标准的阐释是存在若干问题的。“充当政府代理人”及“行使基本政府职能”两个要件在CSOB诉斯洛伐克案与北京城建集团诉也门政府案两案仲裁庭的裁决中均不能反映当前国际法乃至国际投资法对“行使政府职能”与“充当政府代理人”所持有的普遍性态度,应该从应然角度对之进行重构,以保障日后国际投资法治实践与理论在此问题上的延续性。
就第一个要件“行使基本政府职能”要件的解读,当前学界及实务界对行为性质及目的界分的观点存在碎片化认识。就国有企业ICSID适格仲裁申请人的Broches标准“行使基本政府职能”要件的解读,有学者对“行为性质+目的”的标准持有异议,认为考察行为目的的标准需要更为广泛、更有难度的投资母国政策追溯:一是在管辖权阶段对仲裁庭提出了过高要求;二是企业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国家宏观政策的影响,过分强调国有企业投资目的容易背离Broches标准不因所有权属性排除国有企业仲裁适格主体资格的初衷[4]。
笔者认为,此观点是混淆私人行为与国家行为界分、私人行为的商业或国家属性与国家行为的商业或国家属性两对矛盾的表现。行为的性质并非是特定抽象的理念,其是特定相关指向的特定集中性反映[12]。应该考虑到,当前社会,投资目的纷繁复杂,仅仅从行为的性质而不考虑行为的目的去考察一行为之性质根本为商业性抑或国家性,显然是不切合实际的。
其实,对“行使基本政府职能”的判断,长久以来,国际社会已然通过若干国际法律文件之缔结或准备工作形成了界分“国家行为”与“私人行为”的“商业交易”判断标准,并将其归为“行为性质+目的”方法,同时在国际及国内二维层面共同推进。
例如在国际公法层面,在长达近30年的起草与研究以后,于2004年12月2日在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11)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Jurisdictional Immunities of States and Their Property 2004.第一次以多边公约的形式对国家及其财产在国际法上的实践趋势做出相应明确。《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第一次对20世纪以来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所奉行的“绝对豁免主义”与“相对豁免主义”做出了糅合,对实施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国际习惯法中的“商业行为”与“主权行为”之界分给出了标准第2条对商业行为中的核心----“商业交易”的内涵与外延予以明确。同时,在进一步明确商业交易是否存在时,第二款规定“在确定一项合同或交易是否为第1款(c)项所述的“商业交易”时,应主要参考该合同或交易的性质,但如果合同或交易的当事方已达成一致,或者根据法院地国的实践,合同或交易的目的与确定其非商业性质有关,则其目的也应予以考虑。
上述实践亦得到包括美国等经济体国内实践的支持,并体现在美国对待商业行为所持的绝对豁免向相对豁免态度的转变上。1952年前,对于商业行为与国家行为性质的界分,美国一直采取的是绝对豁免主义,即只要由国家及其控制主体所做出的一切行为,勿论行为性质是主权性抑或商业性,均被视为国家行为从而不受一国国内法院管辖。这一举措在美国起源于19世纪,并由著名的Schooner Exch诉McFaddon案(12)See the Schooner Exch. v. McFaddon, 11 U.S. (7 Cranch) 116, 1812, p. 147.所确立[13]。
1952年后,随着国际经济形势发展与国家行为与私人行为界分理论的确立,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认识到对商业行为与国家行为的界分有助于国际贸易与投资的促进,态度从绝对豁免向相对豁免转向,并且明确在界分国家行为与私人行为时,需要考察行为背后的目的。例如在De Sanchez诉Banco Central de Nicaragua and Others案中,美国联邦第五巡回上诉法院就认为:“如果不考察特定行为的目的,就无法确定行为的性质。”(13)See De Sanchez v. Banco Central de Nicaragua and Others, 770 F.2d 1385, (5th Circuit. 1985,) p. 1393.澳大利亚法律改革委员会也指出:“对行为的性质和目的做概念性的区分是不可能的,‘政府性行为’和‘商业性行为’的分类本身就是有目的(purposive)的行为。”[12]加拿大最高法院更进一步明确:“将行为的性质做出与其目的“一劳永逸”般的防腐蒸馏式界分,是在尝试不可能的事情。”(14)Se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 The Public Service Alliance of Canada and others (Re Canada Labor Code), [1992] 2 S.C.R. 50, para. 28
可见,仅仅以行为性质来确定一国有企业是否属于ICSID仲裁中的适格申请人,忽略了当前国际经贸往来中普遍存在的以国有形式行使国家职能或者充当政府代理人的情况,如国有企业可以普遍出于政治目的而非行为目的行事的情况。因此,必须了解、分析、洞察国有企业行为背后的目的,而并非仅仅观察其行为的表面属性。而这一原始的判断标准,在现代公司法的“刺穿公司面纱”标准中已经普遍得到各国国内立法及司法实践的反复确认。
而就第二个要件,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编纂的《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第8条“受到国家指挥或控制的行为”的相关规定以及国际贸易法领域的既有裁决,均对本要件之明确提供了方向。
首先,在《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的语境下,其第8条规定:“如果一人或一群人是实际上是在按照国家的指示或在其指挥或控制之下行事,其行为应视为国家法所指的一国的行为。”(15)See Report of the ILC on the Work of its Fifty-Third Session, UN GAOR, 56th Sess., Supp. No. 10, UN Doc. A/56/10, 2001.与Broches标准的这一要件相似,该条款涉及非国家行为体之行为归因为国家之原则,解决的是非国家实体何时作为国家的代表。就上述规定,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官方评述认为:“作为一般原则,根据国际法的规定,实体的行为不应归因于国家,但若该实体与国家间存在特殊事实关系例外。”而当中又分别存在两种情况,分别是指私人个人或实体根据国家指令行事以及私人个人或实体在国家指挥或控制之下行事(16)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Responsibility of States for Internationally Wrongful Acts: General Commentary, in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on the work of its fifty-third session, UN GAOR, 56th Sess, Supp. No. 10. UN. Doc. No. A/56/10, 2001, p.47.。其中的“指挥或控制”,不仅要求该实体总体上处于国家控制之中,更要求该国实际有效地控制了特定行动。
其次,在国际贸易法层面,GATT/WTO专家组以及上诉机构在相应案件中对非国家行为体作为国家代理人的行为认定标准也有诠释。例如在WTO第一个涉及私人行为案件—美国诉日本消费胶卷和相纸案中,专家组就基于之前GATT报告,做出如下认定:“如果由私人实施的行为中参杂有政府的相应因素,则该行为有可能就被视为是政府行为之代表,从而认定该私人是政府之代理人。”(17)Japan-Measures Affecting Consumer Photographic Film and Paper, Panel Report, WT/DS44/R, 31 March 1998.
可见,对于Broches标准的第二个要件,关键在于考察相关国有企业是否在实际上按照国家的指示或者是在国家的指挥或控制之下行事,如果答案为肯定的,则可视为是国家之代表,如果答案为否定的,则可以视作不以国家身份行事,从而为适格的仲裁申请人。
五、结论及启示
综合前述,《ICSID公约》对国有企业作为适格仲裁申请人持开放态度,只需要国有企业满足并非‘充当政府代理人’或者‘行使基本政府职能’的要件即可。但在如何定性上述要件问题上,ICSID仲裁庭实践所确立的标准存有一定缺陷并与国际趋势不甚相符。有鉴及此,应该结合当前国际及国内两方面实践确立的“行为性质+目的”判断标准对国有企业是否“行使基本政府职能”做出判断,而对于国有企业是否“充当政府代理人”,关键则在于考察相关国有企业是否在实际上按照国家的指示或者是在国家的指挥或控制之下行事。
随着中国成为国际贸易第一大国及国际投资第二大国,中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已经呈现加速增长趋势。据美国私营咨询机构荣鼎集团测算,从2010年到2018年,中国在美年度投资已经从46亿美元一路飙升至456亿美元。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国有企业利用ICSID投资争端解决机制解决投资纠纷的情况将会越来越频繁。随之而来的,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在全球投资纠纷大概率呈现上升趋势。为此,对中国企业有如下启示。
首先,ICSID仲裁实践对“行使基本政府职能”要件判断标准有利于中国国有企业利用ICSID机制保护其合法投资权益。当前ICSID仲裁实践下对Broches标准中的“行使基本政府职能”要件采用的是“行为性质”判断标准,此标准着重关注企业的行为性质而不考虑行为目的,有利于中国国有企业积极利用ICSID机制保护其合法投资权利。因此,在具体实践中,为保证中国国有企业成为适格的仲裁申请人,中国国有企业应在具体商事及投资活动中以市场经济主体身份进行决策判断与审视,力求保证投资行为纯商业性运作。
其次,国际社会“行使基本政府职能”要件判断标准趋势要求中国国有企业以更高标准规范其投资行为。如前述,长久以来,国际社会已然通过若干国际法律文件之缔结或准备工作形成了“商业交易”判断标准,并将判断上述标准的判断标准归为“行为性质+目的”方法,同时在国际及国内二维层面共同推进。这意味着,长远而言,中国国有企业要获得有效的投资保护和身份认可,需要吸收和借鉴竞争中立规则中的合理内容来推进自身的改革,以真正的“现代企业”或“私人投资者”身份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真正做到在行为性质与目的两方面与政府相剥离,成为真正的市场经济参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