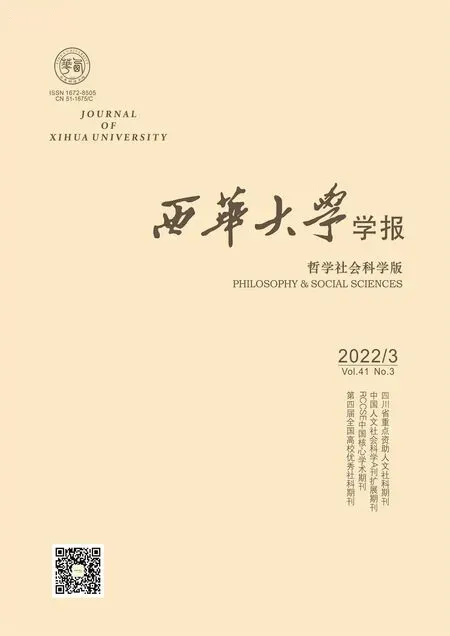数字音乐著作权法定赔偿适用失范与制度匡正
2022-11-22林洋
林 洋
西华大学知识产权学院 四川成都 610039
随着自媒体的发展,数字音乐由最初百度MP3 盗版下载逐步变为各大网络音乐平台争夺正版资源。现今阶段,数字音乐直接被盗版下载的情况比较少见,各大网络音乐平台也很少直接侵害数字音乐著作权,但自媒体平台对数字音乐著作权的侵权却广泛存在[1],表现为短视频平台的各种热门短视频背景音乐未经数字音乐著作权人同意的使用和改编等侵权行为形式。从现有实践看,数字音乐著作权人很少提出维权诉讼,因为诉讼维权一般无法得到相对合理的赔偿[1]。多数学者认为,解决该问题需要完善《著作权法》的立法[2],有学者主张建构数字音乐的大数据著作权信息平台,推行市场化数字音乐著作权许可方式[1]。已有研究很少从数字音乐著作权侵权法定赔偿适用失范角度进行分析,本文从这个角度展开分析以期提出相关建议。
一、问题的提出
通过对数字音乐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现有规则及其司法适用现状进行分析,本文提出在数字音乐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中法定赔偿适用的失范,表现为法官对损害赔偿数额裁量的随意性和数字音乐著作权人较低的维权欲望。
(一)著作权损害赔偿的立法现状
现行法律法规中没有对数字音乐著作权进行专门规定,其著作权损害赔偿规则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①)及其他相关法规和司法解释。其中,《著作权法》自1991年实施之后共经历过三次修正,关于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的规则在第一次修正案中添加②,在2020年第三次修正案中又进行了较大幅度修改③,直接在《著作权法》中添加了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规则意味着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首先适用《著作权法》中侵权损害赔偿规则,之后再行适用普通民事侵权损害赔偿规则。
民事侵权损害赔偿是侵权人全部赔偿被侵权人的实际损失[3],需要被侵权人证明自己的实际损失。此外,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二条④还规定,以侵权人因侵权获益为标准确定人身权侵权损害赔偿范围,该条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法》)第二十条⑤基础上修改得到,有学者将其解释为我国《民法典》确立了获利返还制度[4]。从条文具体内容分析可知,《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二条实质将“侵权人因侵权获利”拟制为“侵权损害”,与“被侵权人实际损失”共同作为侵权损害赔偿确定标准,但该条文仅适用于人身权侵权⑥。《民法典》颁布之前,我国将完全赔偿原则规定为三层次,且三层次具有先后顺序:第一是由被侵权人证明己方实际损失,第二是被侵权人证明侵权人因侵权获益,第三是法院综合侵权实际情况确定赔偿数额。在适用第二层时,侵权人能证明被侵权人实际损失小于己方因侵权获益,法院应按实际损失赔偿。《民法典》实施后,第一层和第二层合并处理,侵权人能够证明被侵权人实际损失小于己方因侵权获益,法院仍按侵权人因侵权获益进行赔偿。
相较于普通民事侵权损害赔偿规则,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规则具有两个方面的特殊性。一是被侵权人无法证明实际损失时,可通过证明侵权人实际获益替代,本质是由被侵权人证明侵权人实际获益推定己方实际损失。在该法律推定适用中,若侵权人证明被侵权人实际损失低于侵权人实际获益,应按被侵权人实际损失赔偿。二是被侵权人对己方实际损失和对方实际获益都无法证明时,由法院根据侵权行为情节综合认定五十万以下的赔偿数额,此种综合认定称为法定赔偿。在民事诉讼理论中,也存在一种类似制度,即法官对民事损害额酌定制度⑦,是法官综合利用审判权超脱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束缚的体现,斟酌赔偿数额也是平衡原被告双方权益的需要。最高人民法院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著作权司法解释》⑧)第二十五条⑨对该法定赔偿规则进行了进一步阐述和发展:一是明确法定赔偿的适用条件和侵害著作权的情节内容,二是提出被侵权人与侵权人协商确定赔偿数额的制度。
《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正案进行了较大变动,包括如下四个方面内容。一是将侵权人违法所得直接作为侵害著作权赔偿的确定标准,即《著作权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一句话实质将“侵权人违法所得”拟制为“被侵权人的实际损失”[5]。立法者对此内容解释是“取消了两者适用顺序,……当事人可以自行选择更有利于其自身权利保护的赔偿数额计算方法”[5]⑩。二是被侵权人用证明权利行使费用存在作为替代其证明实际损失的情况。这种替代性证明实质是法律推定,由被侵权人在无法证明己方损失或侵权人违法所得的情况下证明权利行使费用的存在,推定为其对己方损失达到已证,只不过此处的权利行使费用到底从被侵权人还是侵权人角度并不明确,相关起草者也未提及该问题[5],似乎默认著作权人角度。三是增加恶意侵害著作权的惩罚性赔偿,也被学界称为本次修法的亮点论述[5]。四是提高法定赔偿的数额设置,由最初“五十万以下”改为 “五百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设置被侵权人对侵权人在损害赔偿证明领域的证据协力义务,由法院依职权掌握证据协力义务赋予及其拒绝履行后果[5]。
(二)著作权法定赔偿适用的司法现状
以《著作权》(2001年)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著作权司法解释》第二十五条的内容为关键词在北大法宝案例库进行检索,再以“数字音乐”为关键词在前述检索结果中检索,检索结果共计150 余个案例。对这些案例进行统计分析发现,法官在数字音乐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之中基本都是直接适用法定赔偿,当事人几乎都未完成对被侵权方实际损失或侵权方违法所得的证明。其中,在其他类型作品著作权的侵权损害赔偿之中也存在类似现象,曾有学者专门探讨这一问题并指出我国著作权法中的法定赔偿已经在实践中与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惩罚性赔偿等相近制度混淆并被滥用[6],应该从法定赔偿整体定位角度进行修正。因此,下文主要通过多个实际案例说明司法现状。
实践中,侵害数字音乐著作权的案件包括两种案由。其一是侵害非网络传播权之外的著作复制或发行权等的案由,多体现为数字音乐被复制之后在商场、酒吧、KTV 等娱乐消费场所进行的违法传播。相关案例较多,如“上海声像出版社有限公司诉被告郑州丹尼斯生活广场有限公司航海分公司侵害作品发行权纠纷案”,商场侵害数字音乐著作权中的发行权,在原告未举证的情况下,法官根据录制品数量和歌手知名度酌定500 元以内的赔偿数额⑪。又如“深圳市声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江门市蓬江区金华娱乐城侵害作品复制权、作品表演权系列案”,涉案的KTV、酒吧等娱乐场所侵害数字音乐著作权的复制权、作品表演权,在著作权人未证明实际损失或被告非法所得情况下,法院结合被告注意义务的履行情况酌定赔偿每首歌100~300 元⑫。在这类侵权案件中,侵害数字音乐著作权内容多是复制权、发行权、表演权等,且原告一般无法证明己方实际损失或侵权方违法所得,法院适用著作权法定赔偿时通常从数字音乐本身知名度和侵权行为方式酌定,一首歌酌定赔偿数额通常在500 元以下。另外一种是侵害数字音乐著作权中网络传播权的案由,多是数字音乐平台播放一些未经授权的数字音乐,如阿里音乐、网易音乐、QQ 音乐之间的数字音乐版权纠纷,少数体现为数字音乐被修改后在网络上传播而侵害数字音乐著作权的著作人身权和网络传播权,如“杨新颖与杭州网易云音乐科技有限公司、杭州乐读科技有限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⑬。
在侵害数字音乐著作权中网络传播权的纠纷中,著作权人就损害赔偿数额的证明通常存在以下三种样态。一是不进行任何举证,直接等着法官适用著作权法定赔偿。如“张红与中凯吉韵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中国唱片(广州)有限公司、北京龙天世纪文化有限公司等著作权权属纠纷”中,法官根据侵权行为的性质、持续的时间、情节等因素,酌情确定二十余首歌曲的赔偿为30 000 元⑭。类似的案件还有“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与上海水渡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等案件,法院酌情一首歌赔偿500~10 000 元不等⑮。二是从侵权人违法所得角度进行间接证明,法院通常以其缺乏与侵权行为的因果关系而予以否认。如在“济南驰音广告传媒有限公司、佛山市天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录音录像制作者权权属纠纷”中,著作权人提出被告曾因侵权创收5 个亿,但并未证明该创收与侵权行为的直接因果关系,法院并未按照该创收金额判定赔偿⑯。又如“淘宝(中国)软件有限公司与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中,原告仅是简单指明被告会员收益,并未证明其他损害赔偿相关信息,法院综合考量被告经营规模、侵权行为的性质等因素对每个录音制品的赔偿数额进行酌定⑰。类似的案件还有“淘宝(中国)软件有限公司、上海水渡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广州酷狗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侵害录音录像制作者权纠纷”⑱等。三是从类似案件角度要求法院适用著作权法定赔偿时提高赔偿数额,如“杨新颖与杭州网易云音乐科技有限公司、杭州乐读科技有限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但法院在此案中并未认可原告的举证⑲。
实践中,数字音乐著作权人证明己方损失或侵权方违法所得很难得到法院认可,法院一般直接适用著作权法定赔偿,且不同地区、不同级别的法院适用著作权法定赔偿规则时存在较大差异,相关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法定赔偿数额确定的考量因素并不完全相同,虽然立法仅规定法官需要考量“侵权行为情节”,但不同地区、不同级别法院对“侵权行为情节”理解并不一致,有的案件中将侵权行为情节理解为“行为的性质、持续的时间、情节”⑳,有的将其理解为“数字音乐知名度、社会影响、侵权行为过错程度”㉑,有的将其理解为“被告经营规模、侵权行为的性质、持续时间、后果以及涉案作品的知名度、影响力等因素”㉒。其中,“侵权行为情节”包括的基本内容差异并不大,但对侵权过错程度、数字音乐作品的知名程度、社会影响力等内容,不同地区和级别法院的法官对其认知不一样,在不同个案审理中酌定的影响并不完全一致。其次,法官在不同案件中针对同一首歌曲酌定的赔偿数额差异过大,有的仅是几百元㉓,有的是几千元㉔,有的为上万元㉕;有的同一个案件中的不同歌曲酌定赔偿数额差别也很大㉖。酌定数额差异巨大的原因表现为法官对不同的侵权行为情节把握程度存在差异,具体深层次的原因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分析。最后,同一个案件中的一审和二审针对同样侵权行为酌定赔偿数额偶有较大调整,二审法院一般认为一审酌定数额的把握偏高㉗。有的案件,一审和二审法院对同样侵权行为情节的把握则大体相同㉘。
(三)数字音乐著作权法定赔偿规则适用失范
数字音乐著作权人通常难以证明其实际损失,哪怕其进行简易证明,法院通常也不会从法定证明标准角度予以认可,被侵权人同样难以证明侵权人因侵权获益或权利许可费用。法院习惯性主动适用著作权法定赔偿,且在适用该制度时呈现出以下四方面特点:一是数字音乐著作权人对其损害赔偿是否举证对其损害赔偿没有实质影响,二是确认侵害数字音乐著作权法定赔偿数额的考量情节呈现差异化现象,三是侵害数字音乐著作权法定赔偿具体数额呈现极端化,四是侵害数字音乐著作权的最终赔偿数额普遍偏低。其中,第一和第四个方面的特点导致数字音乐著作权人的维权欲望较低,第二和第三个方面的特点导致数字音乐适用法定赔偿中较为普遍的同案不同判。
1.数字音乐著作权人维权欲望低
从侵害数字音乐著作权的司法判例所涉案由看,多是侵害数字音乐著作权中的网络传播权,且案件类型多是发生在各大数字音乐平台之间或平台与作者之间。自2015年国家版权局广泛推广正版数字音乐以来,事关数字音乐版权的案例逐渐减少,但这并不意味着数字音乐著作权的案件减少。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自2018年逐渐兴起,数字音乐作为短视频制作常备的背景音乐,无论短视频平台,还是用户都在广泛使用数字音乐。虽然抖音等短视频平台努力与各大数字音乐平台达成版权使用协议㉙,但在短视频的背景音乐之中仍然存在很多侵害数字音乐著作权的现象,如擅自改变数字音乐的歌词、谱曲等内容㉚。从数字音乐著作权的相关案例来看,很少有数字音乐版权人针对短视频平台提起侵权之诉,这就不得不去分析这种现象的原因。总体分析著作权损害赔偿的司法实务可以发现,其与其他知识产权损害赔偿证明困难一样,即便进行了证明也很难得到法官的认可,法官在数字音乐著作权法定赔偿适用中对每首歌曲的损害赔偿数额酌定普遍偏低。在该种维权诉讼之中,法官通常直接适用数字音乐著作权法定赔偿很难激起著作权人维权的欲望。在已检索到的侵害数字音乐著作权案件之中,当事人有无举证都对其得到的救济效果没有影响。在数字音乐损害实质难以证明的情况下,法官直接依职权适用著作权法定赔偿且依职权酌定较低的赔偿数额,进而导致数字音乐著作权人在受到侵权时基于利害取舍难以产生维权的欲望。
2.数字音乐著作权法定赔偿适用不统一
从《著作权法》中损害赔偿确定规则实务应用情况看,数字音乐著作权维权案件中法定赔偿适用时,法官对损害赔偿数额大小的确定通常围绕侵权行为情节进行。其中,有些法官普遍将侵害数字音乐著作权的侵权行为情节理解成行为的性质、持续的时间,还有法官在此基础上增加被侵权数字音乐作品的知名度和作者的社会影响力,更有法官将侵权人实施侵权行为的过错程度作为考量因素。不同的案件考量侵害数字音乐著作权的侵权行为细节出现了严重的类案不同判情况,但各种案件考量的因素却独独没将数字音乐的特殊性考量进去。即是说,在大部分侵害数字音乐著作权案件中都表现为侵害数字音乐的网络传播权,数字音乐的高度网络传播性却很少作为法官酌定赔偿数额的因素,在少数案件之中也仅是表现为间接的数字音乐影响力或作者知名度,且不是作为法官酌定的必备考量因素。此外,就同一首歌曲具体损害赔偿数额的酌定,其在一审和二审之中的损害赔偿数额都会出现差异,在类似的案件中法官对数额的酌定也会出现很大差异。具体到一首歌曲,赔偿数额的差异已经达到几十倍,这种差异并不在法官享有的合理裁量权范围之内,这种差异也构成了严重的类案不同判。其中,不同案件之中同一歌曲不同的网络传播量对其损害赔偿数额也没有实质影响,仅是按照每一首数字音乐单独计算,其本身的合理性也成疑。
数字音乐著作权法定赔偿适用的失范,根源于我国著作权法中法定赔偿规则过于抽象,法定赔偿的本质及其与著作权损害赔偿之间关系不明确。现有立法并没有结合各个特定类型作品特征确定不同的法定赔偿适用规则,而以“侵权行为情节”泛化概括,导致法官审判时并不考量不同类型作品的特点,多是以侵权行为严重程度简单裁量一个赔偿数额。本文从法定赔偿现有学理研究出发,分析法定赔偿本质以明晰数字音乐著作权法定赔偿的本质,为解决数字音乐著作权法定赔偿适用失范提出具有理论正当性的规则完善方案。
二、数字音乐著作权中法定赔偿的本质解析
法定赔偿本质存在几种相异的观点,根本区分点在于法定赔偿的目的定位。在明晰知识产权损害赔偿只存在补偿和惩罚两种目的的基础上,法定赔偿应该坚持补偿目的。因此,法定赔偿实质是民事诉讼中损害赔偿数额酌定制度在知识产权侵权领域的具体应用,其实质是弥补差额说无法适用在知识产权侵权领域的缺陷,该缺陷源于被侵权人实际损失难以证明。
(一)法定赔偿本质的解构
法定赔偿存在于知识产权法中,当知识产权侵权损害无法证明时,由法官综合考量侵权行为的情况以确定损害赔偿数额或数额计算方法[7]。法定赔偿弥补了完全赔偿原则在知识产权侵权领域无法适用的缺陷,学理将其理解为一种限制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的实体制度[7]。自从法定赔偿通过立法确立后,其一直都存在被滥用的情况,学者将原因归结为知识产权侵权领域损害的不确定性[8],完善方向也多结合不同类型知识产权细化法定赔偿的计算标准[8]。学界反思前述问题多着眼于法定赔偿与知识产权损害赔偿或惩罚性赔偿之间的关系[9],特别随着民诉法学界对损害赔偿数额酌定制度研究的加深[8],法定赔偿与大陆法系民事诉讼理论中的损害赔偿数额酌定的关系扑朔迷离:有观点直接将两者等同[10];有观点将两者不加区分[11];有观点将两者区分对待,区分对待的原因在于法定赔偿主要考量整体侵权行为情节,而损害赔偿仅是考量权利人实际损失[6]。出现前述问题是因为民事诉讼理论的发展一直滞后于民事实体理论,前者无法解释后者立法中出现的新型制度。民事诉讼中损害赔偿数额酌定制度背后隐藏着差额说,其目的是弥补当事人无法证明实际损失从而无法应用差额说的缺陷[12]。法定赔偿也是弥补差额说在知识产权侵权领域无法应用的缺陷,只不过其规定在民事实体法中。因此,法定赔偿泛化适用背景下,其与民事诉讼中损害赔偿数额酌定制度之间的关系,并不能完全依赖其与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关系来确定,必须去实质分析法定赔偿的本质,以明确其与知识产权损害赔偿之间的真正关系。
学界关于法定赔偿本质的论述可总结为三种观点[13]。第一种是相对流行的观点,认为法定赔偿是弥补差额说中完全赔偿规则在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领域无法适用的缺陷的[7],并不是独立的实体损害赔偿规则,其运用仍应坚持侵权损害赔偿的补偿性[8][9]。这种观点在我国学理上产生较早,在我国民诉理论引入损害赔偿数额酌定制度之后,其便与损害赔偿数额酌定制度相互结合,并彼此作为制度内容的阐释[10]。第二种观点认为,法定赔偿是一种与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相对独立的实体赔偿规则,其核心内容在于让当事人被侵权时可选择法定赔偿或者自行证明实际损失,其相对独立于民事诉讼中损害赔偿数额酌定制度,具有自己独立的计算方式,但目的仍然是维持损害补偿性[14]。第三种观点是少数学者提出法定赔偿与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并无必然联系,其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损害计算实体规则,要同时满足损害赔偿的补偿性和预防性[6]。
前述三种观点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法定赔偿目的、与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的关系、与损害数额酌定制度的关系、确定赔偿数额考量因素等方面。其中,法定赔偿目的作为根本性差异,能够决定其余三个方面的差异,后三者仅是描述知识产权不同赔偿的不同侧面,制度目的却反映制度本质。从法定赔偿目的区分来看,第一种观点中的制度目的定位与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相同,后两种观点则在补偿目的之上增加了一个预防性目的,制度目的之差异自然导致法定赔偿与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关系、与损害数额酌定制度关系等内容的差异。补偿目的定位下,法定赔偿的目的在于弥补损害赔偿适用的不足,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优先于法定赔偿适用,是法定赔偿作为损害赔偿数额酌定制度的具体体现。相反地,预防目的定位下的法定赔偿目的在于预防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产生,其与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并列存在而无先后顺位关系,与损害赔偿数额酌定制度并没有关系,因目的定位于预防而惩罚侵权人过错,其数额确定主要考量侵权行为过错的相关情节。
(二)法定赔偿实为损害赔偿酌定制度的论证
法定赔偿并不是独立于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的实体赔偿规则或制度,其本质仅是辅助实现知识产权侵权损害的损害赔偿数额酌定的实体和程序交叉制度,该制度以赔偿为目的,兼具预防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再次发生的功能,具体论证包括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从制度设置目的观察,法定赔偿应该完全坚持补偿性目的,不宜增加预防性目的设置,更不适宜设置惩罚性目的。从法定赔偿历史沿革看,其起源于英美法系后广泛应用于大陆法系[6],逐步与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侵权损害赔偿制度相互融合,以解决知识产权侵权领域完全赔偿原则适用困境[14]。我国属于成文法系,法定赔偿在我国立法也主要体现于其与侵权损害赔偿确定制度融合过程[14]。出现其与侵权损害赔偿纠缠不清的情况,主要源于法定赔偿在英美法系中的制度设置目的不仅是为了赔偿侵权人损失,更有预防知识产权侵权人侵权的功能[6]。加之大陆法系侵权损害本就具有预防功能[15],有学者指出,我国引入法定赔偿也应该在补偿目的之上,增加一个基本的预防侵权目的[9]。因此,有学者在此观点上提出我国法定赔偿应该回归英美法系的法定赔偿原义,区分于知识产权损害赔偿的赔偿目的设置[6]。前述第二、三种观点就是以预防目的为基础提出法定赔偿相对独立于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进而作为一种独立的实体赔偿的制度。从知识产权侵权损害领域整体观察,赔偿的预防性目的并不适宜作为赔偿确定制度设计的基本支撑,主要是知识产权损害领域并没有预防目的独立存在的必要性。具体来讲,民事实体领域的赔偿主要存在两个基本类型,一种是补偿性民事责任,另一种是惩罚性民事责任,犹如合同违约金分为补偿性违约金和惩罚性违约金。其中,无论何种民事责任在具体适用之中都具有了预防功能,主要制止不合民事法律或民事合同的行为发生。民事责任作为民事违法行为或违约行为的直接后果,当然具有预防功能,但该种预防功能主要通过承担民事责任这种补充性后果实现,即现有民法中的民事责任规范无法直接和单独地体现预防性目的,必须与民事责任中补偿性和惩罚性功能一起实现。因此,单独以预防性功能作为基础论证法定赔偿的独立性并不合适。同理,将预防性和补偿性并列,也无法作为法定赔偿独立设置的目的。因为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普遍存在法定赔偿,法定赔偿自然要区分于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
第二,法定赔偿与民事诉讼损害赔偿数额酌定制度本质趋同,前者属于后者在知识产权侵权领域的具体应用,知识产权侵权的侵害公益性致使法定赔偿在法院依职权调查证据方面有自己的特殊性。从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民事诉讼中损害赔偿数额制度历史沿革来看[16],该制度是为了解决侵权损害赔偿中实际损失难以证明的问题,由法官综合考量侵权行为情节等因素确定一个损害赔偿数额,目的在于解决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实体利益失衡[16]。就损害赔偿数额酌定制度的性质,大陆法系民诉学界历来就存在“证明标准减轻说”“自由裁量权说”“折衷说”等三种观点的争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和理论观点侧重都不相同,规定的相应部门法也不相同[16]。其中,“证明标准减轻说”仍然以“差额说”中完全赔偿原则为适用空间,但“自由裁量说”则相对突破前述民事实体赔偿规则的限制,提出了法官可基于法庭辩论和案件综合情况确定赔偿数额,但“证明标准减轻说”具有优先适用性[16]。自民事诉讼损害赔偿数额酌定制度在本世纪初引入我国之后,民事诉讼学者一直认为其适用范围应该遍及所有民事侵权领域[12][16],法定赔偿仅是前述民事诉讼理论和制度在知识产权侵权领域的具体适用,并且相关观点并没有针对这一逻辑推理阐释理由[10][11][12][17]。前述观点多主张法定赔偿应该按照民事诉讼损害赔偿数额酌定制度进行重构[17],这一观点也被部分知识产权法学者接受[18],也有部分学者从法定赔偿的预防目的角度论述其相异于民事诉讼中损害赔偿数额制度[6]。其中,上文已然指明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中预防目的无法支撑论证其中法定赔偿属于相异于侵权损害赔偿的特殊实体损害赔偿规则。从法定赔偿与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的关系及适用规则观察,知识产权侵权领域适用损害赔偿数额酌定制度的前提条件、性质、损害数额酌定考量因素与法定赔偿基本相同,都是在完全赔偿原则无法适用之时,利用法官自由裁量权考量所有案情确定一个较为恰当的赔偿数额。
三、数字音乐著作权中法定赔偿匡正的总体要求
数字音乐著作权中法定赔偿与知识产权法定赔偿无本质差异,其应用应该以补偿数字音乐著作权人损失为根本目标,数字音乐著作权法定赔偿除了对其制度本体进行必要完善外,法官酌定侵害数字音乐著作权赔偿数额之前还需要设置一个前置程序,即法官依职权调取能够认定数字音乐著作权人赔偿数额的证据。
(一)法定赔偿应坚持以补偿权利人实际损失为目标
数字音乐著作权中法定赔偿本质解析需要以法定赔偿本质为基础,通过分析其相对于一般知识产权两个方面的特殊性,可以明确该特殊性是否影响法定赔偿本质的观点在数字音乐著作权中的直接准用。第一是著作权相对于知识产权的特殊性,第二是数字音乐著作权相对于一般著作权的特殊性。著作权是最原始的知识产权,关于法定赔偿规则的总结和分析很多都是从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修改和分析开始的,法定赔偿也是著作权中作品独创性被侵害的后果难以界定时,法官利用侵害著作权行为的情节酌定赔偿数额。即是说,侵害不同类型知识产权的侵权行为情节直接影响不同类型法定赔偿适用,不同类型知识产权是前述情节不同的基础。从法定赔偿的具体规则内容观察,不同类型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情节已经在制度里进行了规定,不同类型知识产权的内容也会体现在前述侵权行为情节之中。所以,著作权法定赔偿与知识产权法定赔偿的具体制度内容一样,著作权法定赔偿本质与知识产权法定赔偿本质相同,都是民事诉讼中损害赔偿数额酌定制度。同样,分析数字音乐著作权法定赔偿的本质,除了数字音乐著作权本身特殊性体现在侵害数字音乐著作权侵权行为情节之中,其他关于数字音乐著作权法定赔偿与其他类型作品著作权法定赔偿并没有本质区分。
因此,数字音乐著作权法定赔偿本质是民事诉讼中损害赔偿数额酌定制度在数字音乐侵权领域的具体应用,可弥补侵权损害赔偿中完全赔偿原则下差额说无法直接适用于数字音乐著作权侵权领域的缺陷,具体体现为数字音乐著作权人难以证明实际损失的情况。其中,数字音乐著作权法定赔偿制度的应用应该以补偿著作权人损失为根本目标,在法官确定法定赔偿数额时自然就产生预防侵权之目的,其不是一种独立的侵权赔偿实体规则,与侵害著作权损害赔偿具有先后适用关系。
(二)法官酌定损害数额前应依职权调取实际损失证据
宏观角度观察数字音乐著作权法定赔偿制度的实践适用,法官在不鼓励当事人进行举证或简单举证无法满足法官对实际损害相关事实心证需要时,直接适用法定赔偿且简单考量侵权行为情节后,利用自由裁量权酌定一个赔偿数额。权利人得到的实际赔偿与其对侵权损失的预期相差甚远,导致权利人维权欲望低。数字音乐著作权法定赔偿的目的是赔偿权利人实际损失,预防侵权再次发生仅是补偿目的的附带。数字音乐著作权法定赔偿的整体完善需要以实现补偿目的为方向,法定赔偿数额的确定需要以权利人实际损失为标准。
实现这一目标有两种方式:一是法官替代当事人依职权主动调取能够证明数字音乐权利人实际损失的相关证据;二是法官仅是依职权根据案件情况综合裁量数额,并不依职权调取能够证明实际损失的相关证据。第一种方式能够较为容易地认定权利人实际损失,第二种方式则因没有裁量基准,很难认定权利人实际损失。以法官最终认定数字音乐著作权人的实际损失为目标,前述两种方式共有四种排列组合方式,即单纯第一种方式、单纯第二种方式、先第一种后第二种方式、先第二种后第一种方式。单纯第一种很难实现认定权利人实际损失这一目标,知识产权损害赔偿本身的不确定性[8]就导致其适用范围有限;单纯第二种方式因缺乏法官裁量赔偿数额的基准而难以单独适用。同样,先第二种后第一种方式,也因为第二种方式缺乏法官裁量赔偿数额的基准而难以前置适用。所以,以实现认定数字音乐著作权人的实际损失为目标,数字音乐著作权法定赔偿制度的宏观完善应该在当事人证明侵权损害赔偿无果时,由法官依职权调查数字音乐著作权人的实际损失,以明确数字音乐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的优先适用性。侵权损害赔偿在当事人举证和法官依职权调取证据都无果时,由法官结合数字音乐著作权侵权的情况综合酌定一个赔偿数额。
数字音乐著作权法定赔偿的本质与法定赔偿本质一样,属于民事诉讼损害赔偿数额在数字音乐著作权侵权领域的适用。从民事诉讼损害赔偿数额酌定制度的域外规定和理论研究来看,其仅是在当事人证明实际损失无果时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该种自由裁量权被定性为法律适用权,行使时综合考量案件情况、口头辩论趣旨等内容确定一个相对合理的赔偿数额。法官行使该种裁量权时并没有相应的调查取证权,其整体受到民事诉讼中处分原则和辩论原则的拘束,该种拘束建立在当事人首先证明侵权实际损失的基础之上。在知识产权侵权领域适用损害赔偿数额酌定制度单独拟称为法定赔偿,其实质是英美法系的知识产权侵权赔偿与大陆法系侵权损害赔偿相互融合的结果,其应该体现知识产权侵权领域的特殊性。虽然现有知识产权法在理论和立法框架上属于大民法范畴,但相对于狭义民法的强烈私权特征,知识产权不仅带有私权属性,同时也带有社会公益性[19],这种公益性还体现在知识产权故意侵权行为带来行政处罚的后果。基于公益性对知识产权法定赔偿的影响,在法定赔偿数额确定之时不能仅仅由法官依职权考量侵权行为情节,还应该突破辩论主义限制依职权调取确定侵权损害所需的各种证据材料㉛。
在数字音乐整体匡正要求的前提下,必须坚持实际损失认定优先。只有在当事人举证及法官依职权调查取证都无法认定实际损失的前提下,方可由法官依职权酌定损害赔偿数额。因此,探讨具体匡正措施应首先探讨法官依职权调取实际损失相关证据的程度、次序和范围,再探讨现有法官酌定赔偿数额的具体规则如何完善。
四、匡正措施之一:法官依职权调取实际损失相关证据
法官依职权调取能够认定数字音乐著作权人实际损失的相关证据,必须在当事人自行举证无果之后,以达到法官对数字音乐著作权人实际损失形成高度盖然性心证标准。其中,法官需要围绕数字音乐著作权人实际损失、侵权人违法所得或权利人许可适用费用的先后顺序依次确定依职权调取证据范围。
(一)法官调取证据的程度
民事诉讼中辩论主义存在三个命题[20],其中,数字音乐著作权法定赔偿中法官依职权调取证据仅是在第三个命题角度进行的部分突破。法官依职权主动调取知识产权侵权损害所需各种证据材料,目的在于弥补当事人自行举证无法查明实际损失的不足。因为大陆法系民事诉讼理论对法官依职权调查取证需要达到的范围和程度一直没有达成一致观点,理论多认为依职权调查取证需要以法官对相关事实达成必要心证为必要条件[21]。具体到数字音乐著作权法定赔偿适用中,法官针对数字音乐著作权法定赔偿适用之中调查相应证据,需要满足两个方面的要求,详细分析如下。
一是数字音乐著作权法定赔偿适用之中,法官依职权调查侵权损害赔偿的相关证据活动必须在当事人自行举证无果之后。因为数字音乐著作权的侵权损害赔偿毕竟是对私权的赔偿活动,其私益性的本质属性决定当事人必须对自己的利益负责,其只能适用辩论主义第一命题,不能直接采用职权探知主义。如果由法官直接依职权探知所有数字音乐著作权侵权后果的相关事实,当事人便可以不进行任何举证而获得大量赔偿,当事人就会发现针对同一知识产权侵权行为进行集体性维权可以获取大量的收益,这便是知识产权侵权领域的“蟑螂诉讼”等过度维权现象发生的根本原因[22]。其中,判断当事人自行举证结束的标准是法官针对数字音乐著作权人实际损失无法形成高度盖然性的心证,并且当事人没有证据继续举示。同时,权利人不举证的行为必须影响其最后获得的赔偿数额,即法官在调取权利人实际损失的相关证据形成心证以确定赔偿数额时必须依职权主动减去适当数额以防止数字音乐著作权人过度依赖法官依职权调取证据,至于酌定减去的数额可参照法院调取证据的成本或者当事人自行调取证据的成本。
二是数字音乐著作权法定赔偿适用之中,法官依职权调查取证需要达到证明知识产权实际损失的效果,即法官需要按照数字音乐著作权侵权损害后果确定的相关证据依职权进行调取,并且依职权调取证据必须满足法官对实际损害存在的实体事实存在达到高度盖然性法定证明标准的要求。若在数字音乐著作权法定赔偿适用中,法官仅是简单根据侵权行为情节进行损害赔偿数额的酌定,置侵权实际损害后果不顾,非常容易导致单个维权诉讼中赔偿数额过低,从而进一步降低数字音乐著作权人维权欲望。因此,数字音乐著作权法定赔偿适用之中,法官针对数字音乐著作权侵权损害实际存在的必要证据调取必须在当事人自行举证无果之后进行,并且依职权调取证据必须达到能够认定数字音乐著作权人实际损害的程度。同时,法官依职权调取证据不能适用证明妨碍等法律事实推定引发的案件事实推定规则,因为数字音乐著作权侵权领域的公益性特征要求,法官对实际损失大小的证明必须以探求客观真实为基本标准。如果法官在依职权调取证据过程中存在当事人或案外人不配合的情况,只能当作妨碍民事诉讼行为予以司法惩罚。当然,法官依职权调取证据不适用证明妨碍规则以追求客观真实,其并不影响《著作权法》第五十四条第三款中证明妨碍推定虚拟损害规则的适用。
当然,在职权探知之中仍然存在法官依职权调取证据无法形成心证的情况,也存在法官依职权调取证据仍然无法达到法官明晰数字音乐著作权人实际损失的情况,此处只能由法官利用自身享有的裁量权综合考量侵权案件情况确定一个赔偿数额。
(二)法官依职权调取证据的次序和范围
上文已然指明我国《著作权法》对著作权人实际损失的规定已作出实质变动,由原来的“权利人的实际损失”变为“权利人因此受到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且第二顺位的赔偿也由“侵权人的违法所得”变为“可以参照该权利使用费”。其中,人身权的侵权损害赔偿由《侵权法》第二十条变为《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二条,有学理认为这是我国在民法上确立违法所得返还制度。若同样分析我国《著作权法》的历史沿革,也可将此法在2020年的修改作为违法所得返还制度在《著作权法》上的确立。此种逻辑推理的目的在于明确现有《著作权法》已经将著作权侵权领域中著作权人实际损失由单纯的“权利人的实际损失”解释增加了一个扩张解释的内容,即将“侵权人的违法所得”拟制为著作权人实际损失,取消著作权人证明己方实际损失困难时“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与“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的先后顺序[5]。这种修改方式取消了侵权人在违法所得高于著作权人实际损失时的实体抗辩机会,且实质改变了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的目的,由原来单纯适用完全赔偿原则变为预防甚至惩罚侵权人的目的。上文已然分析了《著作权法》作为知识产权法的基本部门法,其侵权领域损害赔偿应坚持补偿性目的,预防目的在实现补偿目的时已经附带实现,惩罚性目的已经通过《著作权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最后一句话确立的著作权法惩罚性赔偿制度实现。《著作权法》的惩罚性赔偿有自己独立适用的要件和法律效果,属于独立于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的实体赔偿规则,两者不可混淆[23]。因此,《著作权法》第五十四条第一句中关于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制度的修改并不恰当,应该按照2010 版《著作权法》中适用顺位进行修改,即著作权人先证明“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法官难以形成相关心证时,著作权人再行证明“侵权人的违法所得”,法官仍然难以形成相关心证时,著作权人最后再针对权利使用费用予以证明以获取侵权损害赔偿。这种修改后的适用顺序同样应该适用在数字音乐著作权法定赔偿的前置程序中,具体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法官依职权调取关于数字音乐著作权人实际损失的证据范围。著作权的权利内容有不同表现形式,且不同类型作品的同一著作权的权利内容表现形式也不同,因此,侵害不同类型作品的著作权的不同内容有着不同的行为表现形式,且导致的侵权后果也不一样。具体到数字音乐著作权,其著作权最重要的权利内容是网络传播权,侵害数字音乐著作权的行为也多是围绕数字音乐的网络传播行为展开的,导致的后果往往是权利人网络传播数量及其收入的减少。所以,法官依职权调取数字音乐著作权人实际损失证据必须围绕侵害数字音乐著作权的侵权行为方式给权利人造成的实际后果进行,特别是侵害数字音乐著作权网络传播权案件之中,法官应该围绕侵权行为导致数字音乐著作权人在网络传播之中的预期损失进行调取证据。第二是法官依职权调取关于数字音乐侵权人违法所得的证据范围。侵害著作权人的违法所得实质是侵害数字音乐著作权的获益,特别是因利用没有合法授权的数字音乐产生的广告营收等非法收入,该事实一般通过侵权人的个人财务流通的证据资料即可证明。我国《著作权法》第五十四条中规定侵权人对其会计账簿等资料承担证据协力义务,其中的会计账簿等证据资料就是证明侵害著作权人违法所得的直接证据。只不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此中法官调取该种侵权人违法所得证据时并不适用证明妨碍推定事实成立之规则,法官必须切实调取到相关能够直接证明侵权人违法所得的证据资料。第三是法官依职权调取权利使用费的证据范围。关于《著作权法》第五十四条中新增的“权利使用费”,立法者给出的解释是“著作权人的许可使用价格或者市场价格”[5],这是从著作权人角度进行的界定。具体到数字音乐著作权人的权利使用费则是指数字音乐具有的一般市场价格,该种事实属于专业领域内容的评价性事实㉜,不适宜由法官直接调查,而是适宜由法官依职权委托数字音乐价格专业领域的专家或者相关专业鉴定机构进行鉴定。
总的来讲,法官依据职权调取能够证明数字音乐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的相关证据必须在当事人自行举证无果之后,并且依职权调取证据应该以力所能及地形成法官对相关事实心证为前提,证据的具体范围要以相关事实范围的直接证据或主要间接证据为限制。
五、匡正措施之二:法官酌定数字音乐著作权赔偿数额规则重塑
为了使法官酌定侵害数字音乐著作权的赔偿数额接近权利人实际损失,在现有《著作权法》法定赔偿的立法规则基础上,必须从适用条件、考量因素、赔偿数额分级等角度就法官酌定侵害数字音乐著作权赔偿数额的具体规则重塑进行探讨。
(一)法官酌定数额的适用条件
虽然《著作权法》将著作权法定赔偿制度与著作权损害赔偿制度相对隔离,但其并未明确地强制要求著作权人针对己方实际损失进行举证,同样未规定著作权人未举证对法定赔偿适用的影响。在著作权人本就难以证明己方实际损失的情况下,著作权人是否举证都不影响其得到的侵权赔偿数额,法官适用著作权法定赔偿并不将其是否举证作为确定赔偿数额的考量因素。因此,司法实践中才会出现当事人已经不再针对己方实际损失举证,法官也不考量当事人是否举证,直接简单根据侵权行为情节酌定一个赔偿数额的情况,忽视了该种规则是否能够实现赔偿著作权人实际损失或激励著作权人维权。因此,现有《著作权法》规定的法定赔偿制度实质赋予了当事人可直接适用的选择权,更有部分法院直接制定地方性司法文件赋予当事人程序选择权[14]。这种选择权现在还扩张到了侵害著作权损害赔偿制度之中,即现有立法取消了权利人实际损失和侵权人违法所得的适用顺序,这种修改有着域外雷同规定作为基础[24]。这种修改已经使得著作权侵权不再直接适用侵权损害赔偿中的完全赔偿原则,当事人可选择较为容易证明的情况进行证明。上文已然指出,在知识产权侵权领域必须准用完全赔偿原则,只有例外情况下适用法定赔偿,并提出了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制度的完善方向。在此基础上,本研究结合《著作权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法定赔偿适用条件,对法官酌定数字音乐著作权人实际损失数额的适用条件进行探讨。
数字音乐著作权法定赔偿在整体定位为补偿著作权人实际损失的目的下,其本身并不是独立的实体赔偿规则,也不同于知识产权侵权领域的惩罚性赔偿。因此,数字音乐著作权法定赔偿的整体适用,必须以著作权人的自行举证或侵权人的协助举证达不到法官对著作权人实际损失形成高度盖然性心证为前提。即便适用数字音乐著作权法定赔偿,法官在依据侵害数字音乐著作权的综合案情酌定一个损害赔偿数额时,也需以法官依职权调取证据无法形成关于著作权人实际损失的高度盖然性心证为前提。在这种适用前提下,法官根据前述当事人自行举证及法官自行调取证据的情况,结合侵权数字音乐著作权的其他案件事实的整体情况,综合酌定一个恰当赔偿数额。需要注意的是,前述法官酌定侵害数字音乐著作权赔偿数额的适用前提条件属于强制性规则,法官必须按照适用条件进行相关证据调取,否则属于法官职权行使不恰当,当事人可以据此提出行使程序异议或申请再审等程序救济权利。其中,法官酌定侵害数字音乐著作权赔偿数额的适用条件必须予以强制坚持,并在未来规定在相关法律或者司法解释之中,以最大程度地使法官酌定赔偿数额接近权利人实际损失。同时,未来司法解释必须明确当事人不自行举证的情况不仅影响法官依职权调取证据确定实际损失数额,也要明确规定当事人不举证会作为法官酌定赔偿数额的一个消极因素。
(二)法官酌定数额的考量因素
从现有《著作权法》第五十四条及其相关条文内容分析可知,数字音乐著作权法定赔偿适用中,法官酌定赔偿数额主要考量侵害数字音乐著作权的侵权行为情节。其中,理论通常认为侵权行为情节是侵权行为性质、侵权的手段、持续时间、损害后果、制止侵权合理支出等内容[13],也有观点认为应该从著作权侵权案件的综合情况进行考量[25],两种观点的差异主要在于是否将法定赔偿理解为民事诉讼中损害赔偿数额酌定制度。我国司法实践针对侵害数字音乐著作权的侵权行为情节包括的基本内容差异并不大,但对侵权过错程度、数字音乐作品的知名程度、社会影响力是否应该作为法官考量因素存在一定差异。因此,为解决《著作权法》第五十四条中“侵权行为的情节”存在的学理分歧和实务适用分析,需要从数字音乐著作权法定赔偿的本质分析入手,分别界定清楚著作权法中法定赔偿数额确定时考量因素的范围和数字音乐著作权法定赔偿适用中法官考量因素的具体侧重点。
上文已然指出,数字音乐著作权法定赔偿是民事诉讼中损害赔偿数额酌定制度在该侵权领域的应用,适用法定赔偿时应该坚持补偿性本质,法官酌定侵害数字音乐著作权的赔偿数额应该尽量接近权利人实际损失。因此,原则上能够帮助法官酌定赔偿数额接近权利人实际损失的任何案件情况都应作为考量因素,而不应该狭义去将“侵权行为情节”仅仅理解为侵害著作权的侵权行为的性质、手段、持续时间、损害后果等,应从整个侵权案件的综合情况进行考量。不过需要注意的问题是,《著作权法》第五十四条中的著作权惩罚性赔偿数额依赖于法定赔偿数额的确定,并且适用条件是侵权人故意侵权且需具体情节严重。即是说,著作权惩罚性赔偿也会考量侵权行为情节,该种情节理所当然包括所有侵权案件情节,并且将能够认定侵权过错的要件直接作为著作权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要件[13]。其中,有学者认为,著作权法定赔偿和惩罚性赔偿并行适用,属于两种不同的实体赔偿规则,具有不同的构成要件和计算方法,并不适宜将两者混淆[5]。但知识产权实务中法定赔偿异化适用时考量侵权行为过错,加之惩罚性赔偿数额确定以法定赔偿数额为基础,导致司法实务中两种相互独立的实体赔偿制度混淆[6]。为了避免在著作权侵权领域产生法定赔偿和惩罚性赔偿的相互混淆,实质应该将能够决定惩罚性赔偿的侵权案件情节剔除在法官酌定法定赔偿数额的考量因素之中。其中,前述情节具体包括能够认定侵权行为过错的一切情节,因为侵权行为过错与否是决定是否给予惩罚性赔偿的前提条件。所以,著作权法定赔偿数额确定考量因素范围应该包括一切客观案件情节,但不包括侵权人主观心态相关的行为情节。
具体到数字音乐著作权法定赔偿适用之中,法官在酌定赔偿数字音乐著作权人实际损失的具体数额时,需要考量的因素是侵害数字音乐著作权的侵权案件情节,当然应该排除侵权人主观过错相关的情节。但该种界定仅是从宏观角度明晰考量因素范围,法官到底应该在侵权案件客观情节之中如何具体考量某些特定情节来确定一个接近数字音乐著作权人实际损失的数额?按照一般侵权责任理论分析可知,侵权案件的综合情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构成要件,即侵权行为、侵权结果和因果关系。其中,侵权行为作为客观因素的核心应该作为法官酌定赔偿数额的核心要素,不同类型作品及其著作权不同权利内容直接影响具体案件中法官确定法定赔偿数额考量因素的侧重点。具体到侵害数字音乐著作权之中,司法实践中的案件多表现为侵害该类作品著作权中的网络传播权,相关侵权行为也多表现为未经著作权人同意擅自修改作品或使用部分内容进行广泛的网络传播,特别是在短视频平台之中广泛传播。其中,侵害网络传播权的侵权行为中关系到侵权损害结果的就是网络传播次数,譬如网络诽谤罪中就将网络传播情节作为定罪情节㉝。但从上文分析我国数字音乐著作权侵权案件的现状可知,我国法官通常将网络传播次数忽略或者仅是通过作品知名度等因素笼统概括,并不将其作为酌定法定赔偿数额的考量因素。所以,上文指出法官裁量侵害数字音乐著作权的具体数额时,不同歌曲出现非常大的酌定数额差距,且法官行使裁量权呈现出随意性特征。因此,在数字音乐著作权侵权领域,法官酌定赔偿数额必须重点考量案情中网络传播次数,并将其作为确定法官酌定赔偿数额的基本标准。其中,在对侵权案件中网络传播次数并不清楚的情况下,法官需要进行必要的证据调查,证据调查的目的在于查清楚侵权行为中实际网络传播次数并以此裁定赔偿数额的基础,其应该首先让当事人自行提供证据,在自行提供证据无果的情况下,由法官依职权调取相关网络传播次数的证据。
(三)法官酌定数额的分档
在当事人自行举证和法官依职权调取证据的过程之中,法官仍然无法形成关于数字音乐著作权人实际损失的高度盖然性心证时,法官必须综合侵权案件整体情况,以网络传播次数为基础酌定恰当赔偿数额,以实现法定赔偿补偿权利人实际损失的目的。只不过法官在酌定赔偿数额时具有非常大的自由裁量权,为实现合理约束前述裁量权,学理多主张对法官酌定赔偿数额进行恰当细化分档。多数学者仅是简单提到要进行分档,并主张法院应该根据司法裁判实际情况制定相关文件限制个案审判中法官的裁量权[16];少部分学者提出了具体分档标准和赔偿数额计算方式,但不同观点之间有着很大差别。如有学者主张借鉴美国版权法中法官确定赔偿数额的规定,整体将法定赔偿数额分为三个区间,作品数量和侵权人主观过错都会影响适用何种赔偿数额区间[24]。还有学者以浙江高院提出的“司法层次分析法”为基础,结合不同影响比重的考量因素建构了一个三层级的法定赔偿数额计算模型[14]。实质分析前述观点可发现,泛化提出应该细化法定赔偿计算方法的观点总体认为并不适宜在《著作权法》等法律层面规定法官酌定赔偿数额计算方式,仅适宜在司法解释或法院系统内部制定地方性司法文件来拘束法官裁量权。相反,提出具体细化法官酌定赔偿数额的观点则是建议从法律上明确法定赔偿计算数额的方式,而不是抽象规定一个数额差异很大的赔偿区间。本文总体赞同第一种观点,因为不同类型作品及其著作权内容的法定赔偿数额存在很大差异,其中能够影响法官酌定赔偿数额的考量因素也有很大差异,著作权法定赔偿数额计算方式应该并不适宜统一规定在《著作权法》之中。在交由司法解释或地方性司法文件确定著作权法定赔偿数额计算方式的背景下,本文主张数字音乐著作权法定赔偿规则采用上述学者主张的浙江高院提出的计算方法,因为我国基于法系差异等原因并不适宜采用美国版权法规定的计算方式。
在一个具体侵害数字音乐著作权的侵权案件之中存在两种可能,一是针对一首歌曲的侵权案件,二是针对多首歌曲的侵权案件。其中,一首歌曲的案件并不存在法官酌定赔偿数额合并或分立问题,但多首歌曲构成的单个侵权案件不适宜合并计算,应该针对不同歌曲分开计算,实务中也采用此种做法㉞,这根源于每一首歌曲都拥有各自的著作权。因此,数字音乐著作权法定赔偿适用必须以一首完整歌曲为适用单位,具体由法官考量侵权案件中全体客观情况,包括侵害数字音乐著作权的行为方式和方法、网络传播次数等内容。具体来讲,法官具体酌定数字音乐著作权的法定赔偿数额时,需要根据网络传播次数的不同区间确定几个不同赔偿数额区间。如果通过司法解释或抽象规定的地方性司法文件进行规定,则相关赔偿数额与侵害数字音乐著作权的侵权行为中网络传播次数之间的关系适宜以万次赔偿百元、十万次赔偿千元、百万次万元、千万次及以上为十万元等关系为参考,因为在流量为王的时代,传播次数越高意味着侵权人可能存在越多违法所得,被侵权人理应得到更多赔偿。法官在确定好一首歌曲侵权案件中赔偿数额区间之后,下一步需要将其他考量因素作为跳跃区间或区间内确定具体赔偿数额的根据,如果其他情节较为轻微则在本区间之内进行恰当数额调整,如果情节比较严重则跳跃区间。基本确定赔偿数额区间后,由法官酌定一个相对恰当的赔偿数额。在确定完成具体赔偿时,需要由法官根据数字音乐著作权人对己方实际损失的举证情况和对方协力举证情况对前述数额进行适当调整,如果是没有进行任何举证活动则减去较大数额,如果进行过一定举证则减去适当数额。
注释:
① 文章中没有特别标明年份的《著作权法》指的2020年修改后的正在实施版本,特此说明。
② 2001年10月27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决定第四十一条规定,增加一条,作为第四十八条:“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
③ 2020年11月1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决定第三十四条,将第四十九条改为第五十四条,修改为:“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因此受到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难以计算的,可以参照该权利使用费给予赔偿。对故意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情节严重的,可以在按照上述方法确定数额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给予赔偿。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侵权人的违法所得、权利使用费难以计算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百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的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人民法院为确定赔偿数额,在权利人已经尽了必要举证责任,而与侵权行为相关的账簿、资料等主要由侵权人掌握的,可以责令侵权人提供与侵权行为相关的账簿、资料等;侵权人不提供,或者提供虚假的账簿、资料等的,人民法院可以参考权利人的主张和提供的证据确定赔偿数额。人民法院审理著作权纠纷案件,应权利人请求,对侵权复制品,除特殊情况外,责令销毁;对主要用于制造侵权复制品的材料、工具、设备等,责令销毁,且不予补偿;或者在特殊情况下,责令禁止前述材料、工具、设备等进入商业渠道,且不予补偿。”
④ 条文原文为“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财产损失的,按照被侵权人因此受到的损失或者侵权人因此获得的利益赔偿;被侵权人因此受到的损失以及侵权人因此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被侵权人和侵权人就赔偿数额协商不一致,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赔偿数额”。
⑤ 条文原文为“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财产损失的,按照被侵权人因此受到的损失赔偿;被侵权人的损失难以确定,侵权人因此获得利益的,按照其获得的利益赔偿;侵权人因此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被侵权人和侵权人就赔偿数额协商不一致,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赔偿数额”。
⑥ 我国民法学界有观点认为该条适用范围应该扩张到一般侵权之中,观点详见王若冰:《获利返还制度之我见》,载《当代法学》2014年第6 期,第80—87 页。
⑦ 损害赔偿数额酌定制度详见毋爱斌:《损害额认定制度研究》,载《清华法学》2012年第2 期等相关文献。
⑧ 法释〔2002〕31 号,该司法解释在2020年经过一次修改,发文字号为法释〔2020〕19 号。
⑨ 条文原文为“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无法确定的,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请求或者依职权适用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确定赔偿数额。人民法院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当考量作品类型、合理使用费、侵权行为性质、后果等情节综合确定。当事人按照本条第一款的规定就赔偿数额达成协议的,应当准许”。
⑩ 该种损害赔偿的规定方式在《民法典》1182 条内容一致,都是以侵权人违法所得拟制为侵权损害赔偿范围,但该种拟制容易导致侵权人因侵权获益的现象。
⑪ 参见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郑知民初字第1035 号民事判决书。
⑫ 参见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2015)江蓬法知民初字第17-26 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4)东一法知民初字第379 号民事判决书等相关判决书。
⑬ 参见杭州互联网法院(2019)浙0192 民初10754 号民事判决书。
⑭ 参见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陕01 民初2047 号民事判决书。
⑮ 参见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5 民初146 号民事判决书等。
⑯ 参见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06 民终9615 号民事判决书。
⑰ 参见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5 民初7479 号民事判决书。
⑱ 参见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原上海市上海县人民法院)(2016)沪0112 民初18585 号民事判决书。
⑲ 参见杭州互联网法院(2019)浙0192 民初10754 号民事判决书。
⑳ 参见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陕01 民初2047 号民事判决书。
㉑ 参见杭州互联网法院(2019)浙0192 民初10 754 号民事判决书。
㉒ 参见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5 民初7 479 号民事判决书。
㉓ 参见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2019)豫0104 知民初148 号民事判决书。
㉔ 参见河北省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冀03 知民初51 号民事判决书。
㉕ 参见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5 民初7479 号民事判决书。
㉖ 参见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原上海市上海县人民法院)(2015)闵民三(知)初字第175 号民事判决书。
㉗ 参见广州知识产权法院(2017)粤73 民终1545-1549 号民事判决书。
㉘ 参见上海知识产权法院(2017)沪73 民终166-168 号民事判决书。
㉙ 详见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08371977653798050&wfr=spider&for=pc,访问于2021.05.12。
㉚ 详见http://www.360doc.com/content/20/0504/20/69582239_910216482.shtml,访问于2021.05.12。
㉛ 关于公益性要件采用法官职权主义的论述可参见家事诉讼程序采用职权探知主义,详见[日]松本博之:《日本人事诉讼法》,郭美松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9—63 页。
㉜ 关于评价性事实的论述详见许可:《民事审判方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26—29 页。
㉝ 条文原文请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3〕21 号)第2 条。
㉞ 参见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原上海市上海县人民法院)(2016)沪0112 民初18585 号民事判决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