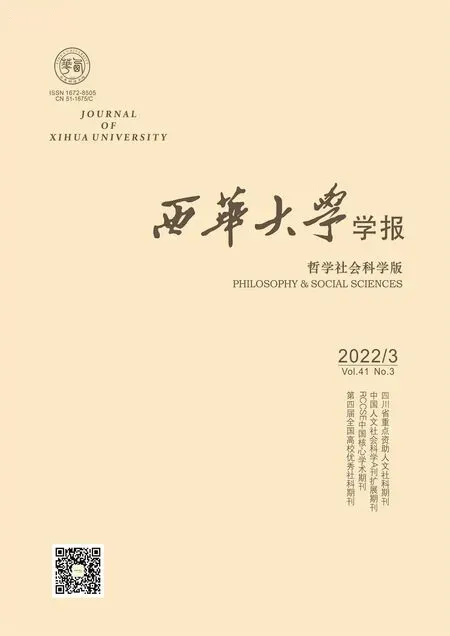李安宅: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一个独特存在
2022-11-22汪洪亮
汪洪亮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四川成都 610068
学术史研究在当下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可谓异军突起,其重要关切之一即是学术与时代的互动。“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诸如先秦诸子学、两汉儒学及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考据学,都分别是其时代的主流思想或学术。学有所兴,必有时趋。讨论近代中国学术,常常离不开传统学术的创新与转型、西学东渐的本土适应与应用、中西学术竞争与融通等几个关键词。近代中国边疆研究自不例外,其凸显了时代需要、学术转型和学科形塑[1]。学术史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关切,就是知人论学。过去学术史研究常关注作品,而忽视作者经历,导致文本解读与文本创制者的切割。有人将这种现象概括为“人的隐去”或“人的消失”,呼吁学术史研究重心要放在人上;指出学术史应该是学术的历史,其主体不仅要有学术,更应有学人;认为学术史研究离不开具体的学术文本,应当回到“学术”的产生过程中[2]。而在学人与学术史的研究中,又存在一种聚光与遮蔽之现象:极少数被反复研究,大多数陷于沉寂。孤星独明,不如繁星满天。历史的真实理应是后者,但历史的研究,却未能呈现这种真实。难怪王铭铭[3]5追求的“人生史”,“最好是选择一位重要,却并非是路人皆知的‘非常人’为对象”。李安宅(1900—1985)就是这样一种“非常人”,其“人生史”近些年来逐步受到关注,但既有研究尚远不能体现其学术与时代的互动,亦远未能反映李安宅人生与学术的丰富性和独特性①。笔者不揣谫陋,试以李安宅为例,对此问题略作讨论,以供学界参考。
一、一个大变动的时代
正如梁启超[4]27-30在1901年所言,相对于中国数千年来的“停顿时代”来说,中国近代是充满变数的“过渡时代”:政治上的“新政体”,学问上的“新学界”和社会理想风俗上的“新道德”,均未能取代旧有,而是新旧交织。“过渡”就是一种“变动”,“过渡时代”就是一种“变动时代”,只是这种变动不是那种决然的“峰回路转”,而是更多具有中西新旧杂糅的特征。
关于中国近代的“变动”特征,很多学者在其著作的标题中即给予明确标识。随意搜检,俯拾皆是。比如汪家熔《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张元济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罗志田《变动时代的文化履迹》(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沈渭滨《士与大变动时代》(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王先明《变动时代的乡绅:乡绅与乡村社会结构变迁(1901—1945)》(人民出版社,2009年)、李良玉《变动时代的记录》(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李志茗《晚清幕府:变动社会中的非正式制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左松涛《变动时代的知识、思想与制度》(武汉出版社,2011年)等等。对这种“变动”的形容,除了“大”,还有其他各种感情色彩更鲜明的词语。比如“巨变”,就有齐世荣、廖学盛《20世纪的历史巨变》(学习出版社,2005年),高瑞泉《巨变时代的社会思潮与知识分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再如“激变”,就有罗志田《激变时代的文化与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王静《激变时代的思考者—郭沫若与其诸子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刘文丽《激变时代的选择—戴季陶政治思想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又如“剧变”,就有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李少军《迎来近代剧变的经世学人—魏源与冯桂芬》(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还有“裂变”,如罗志田《裂变中的传承:20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与学术》(中华书局,2019年)、高钟《文化激荡中的政府导向与社会裂变:1853年—1911年的湖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如此等等,指不胜屈。当然,这些表示变化的形容词,有着不同的指向,其角度和程度也有差异。还有些著述,冠以类似以上各种“变”,并不仅仅用在表述“近代”,有的用来指称历史上的某时期,有的从近代延伸到现代,覆盖了整个20世纪。
毫无疑问,20世纪的中国处于一个大变动时代。一百年间,从晚清到民国,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进程激荡澎湃。20世纪也是这个世界的大变动时代。这个世纪留下的精彩,也许超过既往任何一个世纪,而且就某些指标来看,比如经济指标,或许超过既往所有世纪的总和。这个世纪,整个世界也是空前地相互联系甚至捆绑在了一起[5]7。就中国而言,这个世纪经历了中国数千年来最为剧烈的转型和变动。如20世纪前30年,在当时报人张季鸾[6]的观感中,“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实已经重大之变迁。盖由帝制以至共和,由党政以至党治,由筹备立宪以至国民革命”“就世界言,亦足包括其数世纪进化之阶段”,实不啻为“五千年来未有之新局”。
关于近代中国的“变迁”,李安宅有比较切近的观察。1938年,他在《社会学论集》的自序中说道:“这一段落的中国社会,是在空前未有的非常时期,自无待言。整个社会系统既那样动荡着,活在系统以内的个人也更脉搏紧张地充满了这个节奏。可惜著者不是从事文艺的人,不能写出惊心动魄或如泣如诉的文艺来。更可惜不是从事武备的人,没有在行动上打出一条血路。”[7]1这段话所描述的“非常时期”指的是“九一八”事变后的1930年代。国运与边疆问题密切关联,早在1931年前,中国边疆已经四面楚歌。1931年日本悍然侵占东北,各国“纷起效尤,对于领土之侵略,更明目张胆,不复有顾忌。法占九岛,英窥班洪……一时山雨欲来,风云变色”[8]1。时人认为此前“中国边疆的土地失陷和民族纷扰的事件”虽然“数之不尽”,尚属局部危机,但自“九一八”事变起,“中国全部边疆”都“交了多事之秋”[9]2。刘咸[10]在1935年指出,“年来各国因感于世界危机日益迫切,第二次世界大战万不可免,莫不亟图自卫,未雨绸缪,布置国防,不遗余力”,但是我国“无强大海军,可资保护要塞口岸”“门户洞开,有国无防”。刘咸在1935年即预示二战之将要发生,颇具先见之明。然而当时国力孱弱,前景黯淡,这种山雨欲来的无力感在知识人中传递。
李安宅的上段话内涵非常丰富,虽然仅仅是针对1930年代发言,但表达了那时情势的复杂性和严峻性以及国人在此情势下的进退失据。“直接行动”虽然有必要,但又很难成为知识人的首选。社会动荡与内心纠结,有心作为但壮志难酬,文武难以双全,书生立言也要面对时代,求知与致用的两难,都在这段话中展露无遗。怎一个纠结了得!相比于多数知识人来说,李安宅的人生经历足够丰富,学术领域足够广泛,介入社会的愿望足够强烈,这些也注定他比多数知识人活得更累,浮沉涨跌也就更为起伏多姿。这段话可以视作其夫子自道及其人生注脚,几乎可以解释他在变革时代中人生与学术的全部面相[11]。
无独有偶。对于近代中国困境及个人作为,另一位学者也发表过与李安宅类似的感慨。1945年2月22日,寓居成都的徐益棠[12]在《清代秘史》自序中写道:“士当乱离之世,当必有所建树,或荷戈于疆场,或运筹于帷幄,生何足恋,死亦不惜! 乃余避乱他乡,偷生篱间,消磨于图籍之中,俯仰于饥寒之下,掇拾败纸,辑成斯编,得不为贤者所齿冷乎? ”徐益棠这番话虽是在抗日战争将结束时所言,但描述的却是抗日战争中的际遇与心境,与李安宅所言仍有几分相似。徐益棠所谓“乱离之世”,正是李安宅所谓“社会动荡”,如果联通来看,恰好反映了现今“十四年抗战”之说的合理性:1937年前后抗战情势虽有不同,唯日本侵华进程有异,而国人抗战心绪略同。所谓“有所建树”,也是希望文武两道都有施展,要么荷戈疆场,要么运筹帷幄。千古文人侠客梦,豪气干云,却往往英雄气短。作为学人,二人均对面对国破山河碎而无法有直接建树而感到自责。相比于一直充满革命情怀的李安宅,徐益棠更多一些感时伤世。但我们都可以从中看到他们所处社会的动荡以及他们的无力又奋起的复杂心态。
二、一个特立独行的学者
笔者近些年来一直关注近代边疆学术史,尤其关注顾颉刚、李安宅、徐益棠、张廷休等边疆学人和“边疆学”“边政学”等学科化的努力,此前发表的一些成果,近期也已汇聚成《知人论学:民国时期的边疆学人与学术》一书[13],希望能通过人生史和学科史的解读,认识近代中国所经历的剧变和时代予以个人的激发与挤压。
笔者对李安宅的研究,要追溯到20年前。2001年参与四川师范大学校史人物研究,即以李安宅为研究对象。次年参与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的边疆服务研究,又注意到李安宅是其中的灵魂人物。2009年开始集中精力研究民国时期的边政学,发现李安宅在其中仍然具有不俗的学术成绩与很高的学术地位。2014年开始关注抗战时期华西坝教会五大学的边疆研究,同样发现李安宅堪为华西坝边疆学术的核心人物之一。20年来笔者在各种研究题目的撰著中,未曾忘却对李安宅人生与学术的探寻,撰写的系列论文引起学界特别是民族学界的注意,被认为对民族学界是一种填补性工作。民族学家大多奔走在“田野”上,不怎么关注这方面的题目,即使有关注,也大多只关注自己的师祖爷,从而在种种叠加层累中造成很多学人在今日学术史书写中的遮蔽和隐逸。如果读者对李安宅的人生轨迹与学术历程有所了解,不难看到李安宅是大变动时代中一个特立独行的学者。他的独特性,至少在民族学界与边疆学界无人堪比。他所从事学科研究领域的复合性,学术成长的曲折性,学术政治纠结的复杂性,都使他成为近代学术史上具有典型意义的独特存在。
首先在民族学界与边疆学界,他的治学领域可能是最宽泛的。在既有的学术史表述中,李安宅的头衔有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藏学家、宗教学家、教育家等多种。在其1950年代初填写的相关表格中,在“技术特长”一栏,他一般写“民族学”,但也不忘注明“亦称人类学”②。与同时期的多数民族学家很不一样的是,李安宅的研究兴趣特别宽广,论著兼跨多个学科。如1952年10月,他针对《干部履历登记表》中“过去对那些学科有兴趣?有何特长?”的提问,如是填写:“社会科学、哲学、文学批评、比较宗教学、语言与思想的关系、民族文化与不同文化接触的问题。”③我们检阅其出版的著述,可见其所言不虚。其著作有《〈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意义学》《边疆社会工作》《美学》《语言的魔力》《社会学论集》,编译有《巫术与语言》,译著有《交感巫术的心理学》《知识社会学》《两性社会学》《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等,这些著述大多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中很多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著述。岳永逸[14]认为,“与其说李安宅是狭义的社会学家,还不如说他是广义的社会科学家”,也可以说他是“中国社会人类学家中的哲学家、语言学家”。赵毅衡[15]强调李安宅是中国符号学的前驱人物、中国人类学研究的开创者、藏学的奠基者之一,认为李安宅受到英国学者瑞恰慈影响而写出的《意义学》一书是20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唯一的符号学著作。凌兴珍[16]考察李安宅的边疆教育思想,认为他是“教育社会学家”或“教育人类学家”。当然,李安宅最为学人熟知的研究方向还是藏学,其撰写了关于藏区宗教的系列论文,其著作《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被誉为“有关藏族宗教史的第一部杰作”[17]。
李安宅的这种似乎过于宽泛的研究领域,其实与他的学术成长经历相关。一是其出道晚,求道心切,笨鸟先飞,非常用功。在李安宅的求学过程中,以其祖母为代表的家族势力处处滞碍,幸有其三叔支持才得以脱困,不过当他走出山村,已经21 岁了。李安宅在游历中见识了外面的世界,已非往日之笼中鸟、井中蛙。学习历程中,李安宅可谓逆水行舟,付出了更多辛劳,得以后来居上。二是其生活需要开源节流,学科领域同时也得以拓殖。对李安宅早年生活造成诸多困扰的“封建传统”,始终是个无法抹去的存在。即使李安宅已经在北京站稳脚跟后,大家庭同样如影随形,总有家乡人投奔寄居,很大程度上干扰了李安宅的家庭生活和学术生活。他在与于式玉结婚后,家中常需看护和照顾多个弟妹、子女、侄子侄女,家庭负担极重[18],李安宅只得四处兼职授课,也接单翻译,非常劳苦,这样既增加了收入,也扩展了个人的研究领域。三是其随遇而安,适者生存。李安宅的适应能力不错,学科领域宽广,走到哪里就能研究到哪里,处处都是其田野,也就处处有收获。社会变动不居,李安宅的学术也在移步换景。其学术转型大致可以归纳为四点:从其关注的时代来看,是由古及今;从其学术视野来看,是自西徂东;从其研究区域来看,是从北到南;从其学术旨趣来看,是由虚入实[19]。李安宅的每一转型,既是与时俱进,也是因地制宜,并非硬着陆,而是“华丽转身”。
李安宅虽然出道晚,却拿到了不少“第一”,而且一出手,就引人注目和喝彩。我们不妨看看近代中国留学生在国外的博士论文篇目。如胡适的《中国古代哲学方法进化史》、吴文藻《见于英国舆论和行动中的中国鸦片问题》、李济《中国民族的形成》、徐益棠《云南省的三大民族》、杨堃《中国家族中的祖先崇拜》等等,都是在研究中国问题。在外国人面前讲中国故事,当然是扬长避短,也或许各取所需;而且效率高,能确保较快顺利毕业;而导师也可以借此了解遥远的中国。这种“一石三鸟”的趋向,本无可厚非,但其中或有避难就易的策略考虑。李安宅34 岁始有机会到美国留学,还因为资历问题被人刁难,于是作为“试验品”,不拿博士学位,但可得博士待遇[20]12-13。李安宅迎难而上,知“耻”后勇,没有讲中国故事,而是深入墨西哥州的印第安人部落,写出了近代中国第一个海外民族志《关于祖尼人的一些观察和探讨》,1937年发表在《美国人类学家》杂志,其观点很快“自成一派”④。李安宅回国后,与于式玉在甘南拉卜楞寺从事民族学调查工作达三年,又创下了民国时期在一个地方田野调查时间最长的纪录[21]225。
李安宅在边疆学领域也是独树一帜,是第一个用一本书的篇幅来阐述边疆学理的学者,可以说是在近代中国边疆研究的学科建构上最有成绩的学者。其他学者最多是用一篇文章来阐述其学科构想,比如顾颉刚在《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一文中首次提出学科意义上的“边疆学”,杨成志的《边政研究导论》一文和吴文藻的《边政学发凡》一文指出从民族学和政治学着眼,兼用其他学科来加强边政研究,杨堃的《边疆教育与边疆教育学》一文倡导创建边疆教育学。而李安宅则用一本书的篇幅来论证边疆社会工作学,这就是他应国民政府社会部邀请撰写的《边疆社会工作》一书。在书中李安宅指出,所谓的边疆社会工作,也可以说是应用人类学。他在阐明“边疆工作所需要的条件及其实际方法”时,所贡献的意见就是“不但根据实地经验,亦且依照‘应用人类学’的通则”,接下来,他斩钉截铁地表态:“应用人类学就是边疆社会工作学,只因舆论不够开明,所以热心边疆的人与机关尚多彷徨歧途,而不知有所取法。”[22]36这本书逻辑严密,虚实结合,学用并举,构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边疆学学科体系,具有极强的现实指导意义[23]。
李安宅除了是个学者,还曾经是个军人。在成都即将解放之前,游历美英讲学、访学已经两年的李安宅于式玉赶着回到了成都华西坝。成都刚解放,川西北军政委员会主任、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就找到了李安宅、于式玉,通过他们促成了华西大学边疆研究所一批藏学专家加入了十八军研究室,参与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工作。贺龙为什么如此精准掌握李安宅的才干与行踪?李安宅又为何年届半百还奔向雪域高原?他在昌都、拉萨等地都开展了哪些卓有成效的教育和民族工作?这些问题,都是有待研究的。
就是在私人生活中,李安宅也有其高光时刻。他和于式玉先后生下了两对双胞胎,用今天话说,可谓“人生赢家”,这在民国学者中恐怕也是独一份的。但是他的境遇也有不美好的一面。一是大器无法早成。近30 岁才正式工作,与当时不少留学生一回国就直接被聘为教授无法比拟,其职称晋升也相对迟缓。1929年,比他小一岁的吴文藻一回国即任燕京大学教授,而他这时才毕业留校正式工作。二是与子女聚少离多。李安宅夫妇1938年被迫离开北京去西北,可谓抛家别雏,一别多年,抗战结束后,才与子女在成都短暂相聚,然后又相继去美英等国,再度回国又很快参军进藏,返回内地后,子女均已散离各处。相处时短别亦难,时局使其然。三是晚年相对凄凉,治学已无余力,专长无从发挥,既无门生绕膝,也就无法桃李芬芳。
在民国时期的民族学界与边疆学界,李安宅是个特立独行的存在。无论其人生轨迹,还是其学术历程,都是无法复制的,也是难以雷同的。这里面充满了他冲出牢笼的奋斗,也隐藏了整夜难眠的叹息。通观李安宅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学者成长、成熟的历史,也可以看到一个学者消失和隐逸的历史。他曾经挑灯夜战编译西书,曾经漂洋过海求知问学,曾经跋山涉水调研广袤边疆,曾经投笔从戎走上雪域高原,曾经意气风发讲经说法。研究李安宅,我们要尽力回到其生活的场域中去,触摸他丰富而斑驳的心灵。
三、绕梁的“余音”:李安宅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李安宅和徐益棠在20世纪的学术史书写中,虽偶或在相关学科或某专题研究领域中被提及,但就其人生轨迹与学术历程而言,却无专文论及。尤其是徐益棠,其涉猎学科领域虽不如李安宅宽广,但仍兼采多科,在民族学、历史学等领域均有著述,在历史文献研究和实地民族调查方面皆有丰硕成果,但在学术史书写中却近乎失语,进入新世纪以来,始有学者关注。李安宅研究近十年来可谓异军突起,出现了多学科“围观”的态势。徐益棠研究也已起步,其边政思想得到了初步阐发。但就目前成果呈现来看,还远不足以反映二人跌宕人生的丰富性和知识生产的复合性,甚至还有很多基础性和关键性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比如如何定位吴文藻和李安宅这两位学者的关系?过去学界常将李安宅也列入“吴门弟子”是否科学?近年来学界言说的以李安宅为代表的中国人类学“华西学派”在学理上是否成立?很多问题还似是而非,需要“动手动脚找东西”来加以补足和验证。
与徐益棠研究相比,李安宅研究的学术史相对要久远一些。如邓锐龄在《民族研究》1983年第3 期发表了《介绍李安宅著〈拉卜楞寺〉》。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有关李安宅的文章,多为对其著作《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及其编译、编著或翻译的作品《美学》《意义学》《两性社会学》《巫术与语言》的评介。但总体来讲,除了其藏学研究之外,他的人生轨迹和学术成绩长时间内在国内学界没有得到足够重视,近乎默默无闻。“遗忘”其实只是暂时的,或者只是相对而言的,至少李安宅的作品,还是具有很强生命力的。且不谈民族学、藏学,就是在诸如美学、语言学、意义学等各类学科史的回顾中,李安宅都是榜上有名的,只是较长时间里失之简略罢了。1990年前后,李安宅的部分遗著得到出版,但学界利用率较低,不少论著也还没有被收录。不过,近些年来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李安宅研究渐成气候。无论是其人生还是学术,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掘。其早年的不少作品,在隐逸多年后,也开始被学界重新认识。在当下的学术检阅机制下,李安宅研究的新样貌可谓一目了然,用“全面开花”来形容并不为过⑤。
李安宅研究的兴起,与李安宅人生与学术历程的最后一站四川师范大学的推动密切相关。2014年10月,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与龙泉驿区档案馆合作举办了龙泉驿历史文化名人暨纪念王叔岷先生百年华诞研讨会,主题即研讨王叔岷、李安宅和白敦仁的人生与学术,其中提交的李安宅研究论文即达14 篇。为了传承和弘扬李安宅、于式玉的边疆学术传统和爱国情怀,经笔者倡议,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又先后在成都举办了两次由四川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近现代西南区域政治与社会研究中心牵头承办的学术研讨会。一是在2019年8月6日,即于式玉诞辰115 周年及其去世50 周年之际举办的“于式玉与民国学术”工作坊,与会学者提交了10 余篇论文从不同角度对于式玉的人生与学术作了研讨[24]。二是2020年10月23—25日举办的纪念李安宅诞辰120 周年学术研讨会,来自国内外20 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50 余位学者参加。在这次会上,李安宅妻妹(于陆琳)之女孟运女士、李安宅外孙女任东晓女士及多位学者致辞,或追忆往事,或点评学术,或反思人生,皆情真意切,言近旨远,引起会场师生共鸣。另有30 多篇论文围绕李安宅、于式玉的人生与学术,以及民族国家认同建构、边疆治理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25]。
从期刊发表情况来看,李安宅研究似乎正从冷门走向热点。仅以中国知网搜索为例,以“李安宅”为篇名搜索,1980年代仅3 篇,1990年代仅2 篇,2000—2009年仅7 篇。此后关于李安宅的研究成果激增,2010—2019年达46 篇(其中2015年即有18 篇),2020年至2021年11月17日,即有13 篇,可见学界对李安宅研究的关注“热度”在上升。以“于式玉”为篇名搜索,截至2021年底,有16 篇,其中7 篇题目均含“李安宅”,可见于式玉研究尚未完全取得独立地位。这些成果涉及的学科领域有历史学、人类学、语言学等学科领域。
如果要说当下李安宅研究的特点,笔者觉得有几个方面是比较显明的。一是李安宅的大部分著作(不再局限于藏学)都有人做了新诠释,前文关于李安宅的多学科研究的论述中已有论列,此不赘言。二是李安宅的学者身份多了一个“边疆学者”,其《边疆社会工作》一书近年来得到最多的阐释⑥。三是研究者来自多种学科,除了民族学和历史学外,还有文艺学、美学、民俗学等相关学科。四是其生平研究与学术研究相得益彰,语境分析和文本解读相互促进。李安宅的已刊著作,受到学界关注,其未刊手稿也在陆续发布和解读之中。这些特点都表明了李安宅研究正在走向深入。
对于李安宅和于式玉藏学研究成果的整理,中国藏学出版社厥功至伟,先后于1989年9月出版李安宅的著作《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1990年12月出版《于式玉藏区考察文集》,1992年6月出版《李安宅藏学文论选》,2002年12月出版《李安宅、于式玉藏学文论选》(该书实为二人此前分别出版的藏学论文集之合集)。1991年3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批“李安宅社会学遗著选”丛书,分别为《巫术的分析》《两性社会学》《语言·意义·美学》《〈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这些图书构成了李安宅、于式玉研究的基本资料。陈波2010年在巴蜀书社出版了《李安宅和华西学派人类学》,试图“揭示李安宅为人类学而奋斗的痕迹,和他的人类学对中国人类学的他者意义”⑦。不过,就整体而言,李安宅研究还有很多空间。一是对其论著目前只有专题整理,而缺乏完整而系统的整理;二是其生平研究因受到资料限制,还有一些“未解之谜”;三是其学术和思想研究也尚待深入。
未来李安宅研究该如何走向,笔者不敢妄断,但或许有以下几个趋势值得关注,在此提出来供学界同仁参考。一是李安宅人生与学术的丰富性和独特性,应受到学界更多注意。作为民族学界学科涉猎最广的学者之一,李安宅的学术选择和转型动因,有时代风向标指引,有个人学术旨趣迁变,对此还需要进一步复原历史场景,挖掘其文本之语境与作者之心境,从心灵史角度去体察。二是李安宅的学术成长及其交游,需要受到关注。李安宅求学治学辗转多地,穿插海内外,行走于政学之间,兼涉多种学科,成长历程跌宕,学术交游广阔,需要学界从社会史角度切入,认真梳理史料,复原更多历史细节,以期丰富民国学术界尤其是民族学和边疆学领域学术共同体的图景。三是应从学科史、学术史角度,更为细致地进入李安宅等学人的学术世界,品读其作品的学术价值与时代意义,解析其传播与推广、创造与创新以及应用的概念和话语。李安宅是一个具有原创能力的大学者,他在多个学科领域都具有开创性的贡献,无论是在学科理论还是在社会实务方面都提出了很多独创性的概念和思路,需要我们去提取、提炼,并与同时代学人之思比较、鉴别,从而更加明了其要义及其在学科发展历程中的贡献与位置。同时,我们还要注意,作为一个社会学家,李安宅一直在观察和参与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留下了不少对那个时代的思想文化和社会动态的评论。我们寻索其人生与学术,也就需要从个人与时代、学术与社会的视角去考察。
注释:
① 关于李安宅研究之现状,可以参考拙文《知人论学:纪念李安宅诞辰120 周年学术研讨会述评》,《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21年第3 期。
② 参见其《评级报告表》,李安宅1952年9月1日填写。
③ 参见其《干部履历登记表》,李安宅1952年10月填写。
④ 李安宅:《回忆海外访学》,写于1969年3月19日,由陈波整理,载于《中国人类学评论》第16 辑。
⑤ 具体的研究情况,可参见汪洪亮《李安宅、于式玉先生编年事辑》,《民族学刊》2013年第6 期;《知人论世:李安宅人生与学术史研究的意义与路径》,《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20年第3 期。国外学界对李安宅的研究,可参考龙达瑞《我所知道的李安宅教授:兼谈海外对他的研究》,《中国藏学》2015年第2 期。
⑥ 如彭秀良认为,“从社会工作的角度来考察边疆问题,李安宅是独一无二的”,参见彭秀良《守望与开新:近代中国的社会工作》,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65 页。岳天明指出:“李安宅对社会工作的性质、类别和趋势及边疆社会工作的探讨直面中国边疆社会现实,是一项很了不起的开创性工作,极好地表征着那一代社会学者矢志进行社会学本土化探索的努力,是值得珍视的学术财富。”参见岳天明《论李安宅的边疆社会工作思想—兼及中国社会工作的学术史意识》,《西藏大学学报》2017年第1 期。另有河北大学贾梦瑶、西北师范大学朱志刚两位硕士研究生均以李安宅的边疆社会工作思想为题撰写毕业论文。常宝、席婷婷、郭占峰等青年学者也专文讨论了李安宅的边疆社会工作思想。
⑦ 参见陈波《李安宅和华西学派人类学》,巴蜀书社,2010年。另,该书有两个书评可以参考。参见齐钊《个人心史与学派历史勾连的困境与张力:评〈李安宅与华西学派人类学〉》,《民俗研究》2013年第1 期;苏晓棠《读〈李安宅与华西学派人类学〉》,《华人时刊》2013年第3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