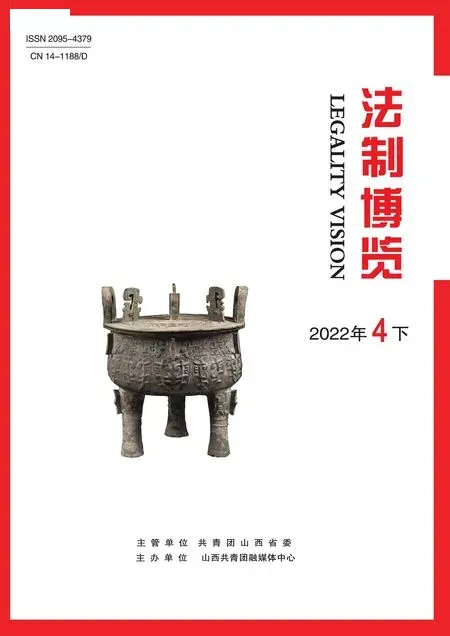《唐律疏议》存在罪刑法定主义论析
2022-11-21李昊桐
李昊桐
吉林师范大学,吉林 长春 130103
一、《唐律疏议》是否存在罪刑法定主义
《唐律疏议》是中华法系的成熟的代表之作。关于《唐律疏议》是否存在罪刑法定主义,学界目前众说纷纭:承认罪刑法定主义存在的肯定说、否定其存在的否定说以及介于二者之间部分肯定的第三说。
以蔡枢衡先生为代表的肯定说提出:虽碍于时代条件和价值追求不同,但只要存在依法定罪定刑的基本特征,就不应否认《唐律疏议》中的罪刑法定。比如,蔡枢衡先生提出:“罪刑法定主义只和比附援引及罪刑擅断势不两立。其他任何解释法律的方法,都不可能全面否定罪刑法定主义,仅能予以某种限制和削弱”[2];杨鸿烈先生以其中的《断狱》《职制》两篇为例[3],主证《唐律疏议》中存在严格的罪刑法定主义;而陈顾远先生也曾提出:《唐律疏议》,其“及现代之法理政理而言,制度之条文固可曰法,制度之见诸明令,为众所守,虽未定于律、入于刑者,又何尝非法?”[4];王立民先生以《唐律疏议》的个别条款为例,这一点与杨鸿烈先生类似,认为其中流露出明确的罪刑法定的思想,他把这些定格为“罪刑法定的萌芽思想”。
持否定说者以西方近现代罪刑法定主义为立论依据,其认为“资产阶级针对中世纪欧洲所盛行的罪刑擅断主义而提出的罪刑法定主义原则,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深刻的阶级内容和积极的社会意义。在中国封建社会,尽管律文中有着一些类于现代刑法关于追溯效力的规定,但是却没有也不可能形成罪刑法定主义原则”。其最主要的论证依据是从《唐律疏议》中的类推明文规定和“不应得为罪”出发,进而否定罪刑法定主义。
首先是类推。《唐律疏议· 名例律》中第五十条规定:“诸断罪而无正条,其应出罪者,则举重以明轻;其应入罪者,则举轻以明重。”即在法律无明文规定时,比照类似的律文作为定罪的依据。其无明文规定而入这一点明显违背罪刑法定主义的基本原则。
其次是“不应得为罪”。《唐律疏议· 杂律》中第四百五十条规定:“诸不应得为而为之者,笞四十;事理重者,杖八十。”由于“杂犯轻罪,触类弘多,金科玉条,包罗难尽”,对“律、令无条,理不可为者”,且“若不轻重相明,无文可以比附”,“临时处断,量情为罪,庶补遗阙”。其实质内涵即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将犯罪人“入罪”,与类推相比,其违反罪刑法定主义之严重更甚。其内涵只有无“出罪”之说。在不当得为罪中,其加以处罚所依据的“理”是儒家思想,以其作评价标准,来决定论罪处刑,这一点与汉代以降的“春秋决狱”内涵一致。对无律令者,即“法无明文规定”本应不为罪、不处罚的行为,依礼制罪。尤其其赋予司法官员较大的司法裁量权,“是法外加罪,是封建刑法擅断主义的体现”。由于“不可为”的覆盖广泛,在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过多的人为因素影响司法审判,现实中必将存在罪刑擅断。正如刘俊文先生所指出的:“推原此律之法意,盖欲补律令、令条文有限,而违法现象无穷之弊”。
至于介于二者之间的第三说,即部分肯定部分否定,其立意综合于两派,即于肯定中持有部分否定,或否定中部分肯定,如杨廷福先生也在其著作中表示:《唐律疏议》存在罪刑擅断,即“给予司法官较灵活引用和解释律文之权”,但杨先生并不否定《唐律疏议》有罪刑法定主义,至少存在其中倾向的存在,鉴于第三说的主要内涵意在综合,故不作赘述。
就肯定说而言,本文是持赞同的。正如蔡枢衡先生所言,《唐律疏议》中虽存在各项与西方以及现代罪刑法定主义所不符的内容(此即否定说的立论之处),但鉴于时代差距,并不能以片面的不符而否定其中蕴含着罪刑法定主义。
二、罪刑法定主义的“源”与“本”
探讨《唐律疏议》中有无罪刑法定问题,必须追源溯本。在通说中,均将罪刑法定作为舶来品,认为其无论是作为一种学说还是作为一种法律制度,均成就于西方近代。
(一)罪刑法定主义诞生历程——“溯源”
罪刑法定,首明于1215年英国《大宪章》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即“对于任何自由人,不依同一身份的适当的裁判或国家的法律,不得逮捕、监禁、剥夺领地、剥夺法的保护或放逐出境,不得采取任何方法使之破产,不得施加暴力,不得使其入狱”;英国1628年的《权利请愿书》、1688年的《人身保护法》,甚至包括美国的《权利宣言》及宪法都对罪刑法定主义思想给予肯定。
现代意义上的罪刑法定主义的法律渊源一般认为是1789年法国的《人权宣言》。其中《人权宣言》第五条规定:“法律仅有权禁止有害于社会的行为。凡未经法律禁止的行为即不得受到妨碍,而且任何人都不得被迫从事法律所未规定的行为。”第八条规定:“法律只应规定确实需要和显然不可少的刑罚,而且除非根据在犯法前已经判定和公布的且系依法施行的法律以外,不得处罚任何人。特别是第八条的规定确定了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方向。
1791年《法国宪法》对这一精神进行了继承和发扬,1810年《法国刑法典》第四条进一步规定:没有在犯罪行为时以明文规定刑罚的法律,对任何人不得处以违警罪、轻罪和重罪。
(二)罪刑法定的基本含义——“追本”
罪刑法定主义,其实质上就是强调两句话,即“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它可分解为以下主要原则:1.事前的罪刑法定,即禁止溯及既往,亦称禁止事后法,顾名思义,某一行为是否犯罪并处以刑罚,必须根据其行为当时的法律,而不能根据行为之后的法律。2.严格的罪刑法定,即禁止类推解释。类推解释将导致刑法的规定使用与相似的情况,而这种相似的情况过于模糊,任何行为都可能与刑罚规定处罚的行为相似,都有被定罪量刑的可能。3.成文的罪刑法定。亦称明确的罪刑法定,因为“只有当人民代表的法意志明确地表现在条文中,从而排除法官作出的主观擅断的判决时,法律保留才能发挥充分的效果”。4.适正的罪刑法定,即要求处罚的适正性。详细来说就是:禁止处罚不当罚的行为和施行不均衡的、残虐的刑罚。
三、《唐律疏议》存在罪刑法定主义的原因解析
现代学者的研究多建立于其自身对《唐律疏议》的了解及研究,所处立场具有一定主观性,但这种主观性我们仍可以从《唐律疏议》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具体条文中加以分析。
(一)历史背景
唐朝初期,政治清明。一方面隋朝以来以律典为主体的法制体系日益完备,另一方面作为法律施行主体的官吏多能恪守职责,而且对律的理解也较为准确划一。因此在唐初法制得以较好的实施、依法行事,“守文定罪”成为可能。其中“守文定罪”与“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制定依据及原则
唐初制定法律多承继隋代以前各法典,如《开皇律》,而其中于某具体罪行之处,或无处罚之法,量刑缺乏统一标准,以致“自是轻重沿爱憎,被罚者不知其然……譬权衡之知轻重,若规矩之得方圆。迈彼三章,同符画一者矣。”
1.量刑同一原则。作为量刑规范,其必须具备实用性和指引性,即“画一”,为了使指引、适用上明确,作为法律解释,《唐律疏议》对所包含的相应律条内容均进行了解释和论证,以增强量刑的可操作性避免轻重失衡现象,即“同一”。
2.《唐律疏议》量刑的全面精准——即严格的罪刑法定。《唐律疏议》的条文虽简明但不失规范,对罪刑考虑充分。它以《名例律》的方式详细具体的规定了刑罚制度,并且详细规定了特殊量刑情节及其处罚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唐律疏议· 名例律》这一部分相当于现代意义上的刑法总则,并且还以“疏议”的形式进行司法解释,并精确了量刑的情节和程度,更在其后的内容中对具体罪行进行了规定,并且详细地考虑了社会危害性及指引性,使司法官员们能够“同符画一”,减少罪刑擅断的危害。《唐律疏议》量刑基准精细且覆盖全面。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尽可能做到“法有明文规定”。这种全面性和精确化实质上就是保证罪刑法定主义在法律实践中的运行。太宗曾说:“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人有所犯,一一於法,上至臣子,下至庶民,概莫能外”。《唐律疏议》以其总则明确“诸断罪皆须因律令格式正文”,及通俗意义上的依法断案量刑,从而使“刑罚不可弛于国,笞捶不得废于家”,进而实现“咸有天秩,典司刑宪”。量刑统一、一断以律,法律一旦确立,便是天下人的共同行为准则。
3.《唐律疏议》明确量刑——即明确的罪刑法定。《唐律疏议》以总则,即《名例律》部分明确了犯罪的处罚原则及对司法官员的司法适用要求,于分则中明确规定了何为犯罪,需受何处罚,即明确的罪刑法定,实际上在这个意义上,也实现了事前的罪刑法定和严格的罪刑法定。《唐律疏议》中对法定刑以“一罪一刑”的形式进行划定。《唐律疏议》所定的刑制,就法定刑而言,是一罪一刑,而并非一罪数刑。这在一定意义上避免了同罪不同罚的不公正现象。《唐律疏议》中同时也充分考虑了犯罪的主客观情况,设立了加刑和减刑的幅度,“称加者,就重次;称减者,就轻次”。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唐律疏议》的制定者们充分考虑到了人治社会所容易产生的主观断案,对加刑、减刑都制定了严格的法律程序和等级,尤其是加重情节中的对应加刑的情况作了严格的限制。比如:其一,依照现行刑法中规定的数额(即较大、巨大、特别巨大)分等,《唐律疏议》中提出“加者,数满乃坐”,其中数满即一定要达到法律划分规定的额度;其二,“二罪以上俱发,以重者论”“等者,从一”“通计前罪,以充后数”,即一个人犯了两个以上的罪,同时或先后被发现,数罪如果轻重不等,从一重而断,不得“罪轻以加重”[2-3],亦不得将几种罪所处的刑罚加在一起,而是以其中之重罪论处,这与现代判罚中的数罪并罚和想象竞合犯中的从一重罪处罚有相通之处。再比如《唐律疏议擅兴》“主将临阵先退”中的规定:“诸主将以下,临阵先退;若寇贼对阵,舍仗投军及弃贼来降,而辄杀者:斩。即违犯军令,军还以后,在律有条者,依律断;无条者,勿论。”此条“疏议”对“无条者,勿论”解释曰:“若违犯军中号令者,军还以后,其所违之罪,在律有条者,仍依律断。直违将军教令,在律无条,军还之后,不合论罪。”
4.对《唐律疏议》中类推及不应得为罪的解释。《唐律疏议》设立类推原则和不当得为罪,表现了立法者希冀以通过“有限”的法律条文的设立(尽管这种设定并不完备,需要以类推和不当得为罪作为补充),来调整“无限”的犯罪可能。唐代的立法者已经认识到法律的滞后性与有限性,进而表现了国家权力的无限性和刑法的干涉性。
正如前文所述,否定论者在否定唐律存在罪刑法定原则时,都以类推、不应得为罪作为例证,但这样的想法过于片面,封建社会的人治客观情况导致需赋予司法官员较大的司法裁量权,从而易造成执法过程中的“无类而推”“无类而举”,这才是对罪刑法定主义最根本的否定,但《唐律疏议》对这一方面进行了极为严格的限定。除前文涉及的“依律断罪”外,又见规定如“诸官户、部曲、官私奴婢有犯,本条无正文者,各准良人”。
此外,唐代在礼法结合中的显著特点就是礼逐渐被法定化,即将礼的某些内容上升为法律规范,同时还明确了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的不同效力,规定了法律规范高于道德规范。同时“义疏”的出现更是中国古代法制追求罪刑法定原则的另一表现。疏议的存在就是为了名章法、释律文,为执法提供具体的“操作指南”,防止罪行擅断。
四、结论
从《唐律疏议》的基本原则及其具体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出,《唐律疏议》中的罪行法定,不是单纯的对人民的“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指引性规定,而且也包含对封建统治者越法断罪量刑行为的限制,即“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这一点虽然与《自由大宪章》的文字表述不同,但都蕴含着“罪刑法定主义”思想。而相较于《自由大宪章》,中国《唐律疏议》中的“罪刑法定主义”思想早了近600年。《唐律疏议》中的“同符画一”,对量刑统一化的追求,对量刑明确性的规定,对刑罚执行的法律限定,都体现出《唐律疏议》的制定者们充分考虑了量刑公正,及罪刑法定。
作为中国法律史上的璀璨明珠,《唐律疏议》可谓精妙绝伦,无论是与现行刑法接轨的总分则结构,还是其中蕴含的慎刑、恤民,其最终的体现,或者说是实现保证,就是其以具体的规定条文,明确了何种行为是犯罪,犯罪适用何种刑罚,从这个意义上说,《唐律疏议》是包含并践行着罪刑法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