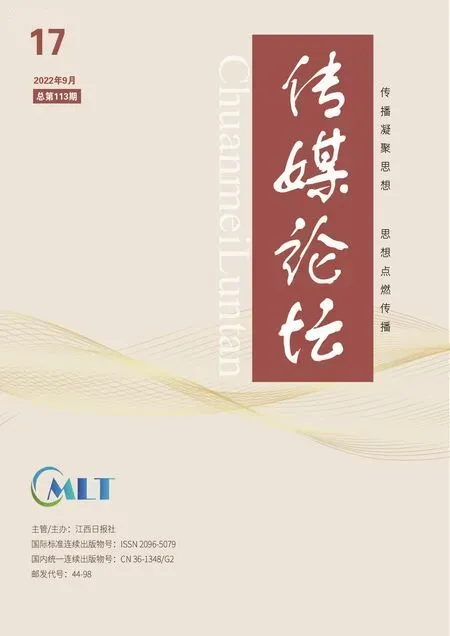反战题材电影中的人文关怀
——以电影《少年H》为例
2022-11-21孙天宇
孙天宇
电影《少年H》由导演降旗康男指导,改编自妹尾河童同名自传小说。影片以一个少年亲历者和见证者的身份为处在战乱时期的日本留存了一份十分珍贵的记忆。电影以昭和初期的神户为背景,深刻反映出战前、战中、战后人们的情感变化。电影中出现的小人物大多善良、谨慎、与世无争,但也有各自的悲哀,悲哀源自理想与命运、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悲伤仅是我们作为观众所感受到的,小人物则是很坦然地接受了这一切。
电影中我们难觅妹尾一家和兵库县的人们的一生轰轰烈烈的奋斗,更没有悲壮的反抗和激烈的斗争,有的只是沉默顺从和泰然处之。在日本陷入战争的时候,政治的残酷让观众感到愤慨,但在这种情况下,平民却能够微笑面对艰难的生活,通过妹尾先生的视角下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描绘出来。
影片情节遵循原著,虽是一部反战电影但镜头并没有直面战争的残酷,而是为生活在战争边缘的普通老百姓按下快门。无论是冷酷无情的森田教官,还是被当作政治犯被逮捕的大哥哥,都只不过是挣扎在战争边缘的小人物。影片借由妹尾肇的视角映衬日本普通大众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迷茫。妹尾一家在电影中虽然是主要角色,但仅是作为时下的一个缩影来体现二战时期日本普通老百姓对战争的困惑和厌倦。
父亲妹尾盛夫经营一家为外国人缝补设计的洋装裁缝铺,是教堂的常客,负责帮助逃难到教堂的难民缝补破损的衣物。妻子敏子是基督徒,经常用教条管教妹尾肇。妹尾肇因穿上母亲编织的带有英文字母H的毛衣,被邻里的小伙伴称为少年“H”。一家四口本可以在偏僻的乡下度过美好的生活,却被突然而来的战争所改变。
“大哥哥”被打成政治犯遭到警察逮捕,男旦艺人下山幸吉因抗拒兵役遭到宪兵围捕,走投无路只能用上吊的方式结束生命。盛夫也因插手教堂事务被便衣带走。日本局势每况愈下,当局要求所有人参与到战后保障工作中,盛夫迫于舆论压力改行做消防员,敏子则加入民间灭火组织,妹尾肇被送往军校打造成为帝国效力的军人。最终日本战败,每个人又重新回到自己的岗位,盛夫依旧投身于自己热爱的洋装事业,敏子则一心照顾家中的小女儿成为全职太太。妹尾肇长大成人,决定15岁这年到外面的世界闯荡一番并依靠绘画的才能成为一名壁画画家。被战争所折磨的孩子,以及在困惑中的成年人。他们每个人都找到了自己的答案,并开始走向重建的道路。
与其他反战题材电影不同, 影片没有过分渲染战争,而是将镜头聚焦在二战中处于大后方的一个城市,远离主战场,但与战争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导演通过兵库县战时动员侧面烘托战争对人民的荼毒来发泄强烈的反战情绪。
一、少年“H”人物形象的塑造
电影中人物形象的塑造对故事情节的展开和推进至关重要。人是电影叙事艺术的中心,在影片《少年H》中也是以人为中心来讲述故事的。观众真正感兴趣的不是电影中的运镜、音响等,而是银幕上的人物。
虽然《一个叫H的男孩》是一部自传体小说,但故事是以第三人称而非第一人称讲述的。在这种情况下讲述故事的意志也就仅限于“H”。其他角色,以及所有情况和事件,都是通过他的眼睛看到的。而且由于“H”是一个小男孩,用来陈述他的观点的风格大部分都十分简易。句子结构简单,词汇符合“H”这个年龄段的男孩。
妹尾肇与其他同龄孩子的不同之处在于,尽管他对同学、电影和性有着共同的关注,但他异常敏锐的眼睛和早熟的怀疑态度使他在一个循规蹈矩的社会中格格不入。虽然有时会面对社会的阴暗,但他总是能够用最轻松的触感和敏锐的幽默感来解决。战争期间的事件是通过男孩H的眼睛描绘的,重要的事情隐藏在冷漠中。在逃离空袭的过程中,他帮助母亲,开始在精神上战胜父母、反抗父母、变得暴力、努力长大成人。
主角妹尾肇身穿显眼的红色H毛衣,气宇昂扬、不畏权势、敢爱敢恨、善恶分明。父亲妹尾盛夫总要把帽子和西服带在身边,把自己装扮成一个绅士,能够宽恕孩子犯下的错误,勇于背负家庭的责任,对政治问题持保守态度。妻子敏子是典型的日本家庭主妇,勤俭持家,受基督教影响为人处世都带着一丝宗教色彩,但不盲目崇拜,从心底里支持丈夫。“大哥哥”深居简出,对妹尾肇关爱有加,将私藏的黑胶唱片与妹尾肇分享,陪伴妹尾肇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森田教官面目狰狞,被军国主义冲昏了头脑,对帮助过洋人的妹尾盛夫有很大的偏见,对妹尾肇也十分苛刻,战争的失败让森田教官与其他狂热的战争分子一样对新生活充满了绝望和恐惧。帮助妹尾肇逃脱森田管制的久门教官让妹尾肇加入了射击部,告诉他们,只是让自己的学生能够在危急时刻不至于手足无措,无心把他们培养成一名被送往战场的狙击手。日本战败,久门喜迎民主时代,重新成为钟表匠的愿望得以实现。
在日本战时社会,每个人都必须小心自己所说的话。没有人敢说出可能被视为非日本人的观点。一切都是秘而不宣的,甚至连天气预报也从报纸上删除,理由是它可能会向敌人泄露信息。当少年“H”大约11岁时,发生了一件引人注目的事件,他乘火车去乡下旅行。当海岸映入眼帘时,乘客自动拉下百叶窗,没有人说什么,因为政府明确禁止任何人向外看海。军舰可能是可见的,但必须保密。H总是质疑这种极端保密的必要性。在战争结束时,他认为不断灌输为天皇而死等思想,使人们无法对如何行事和相信什么做出成熟的判断。
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与父母发生冲突是常有的事,少年“H”也不例外。他对父亲在战后的冷漠感到不耐烦,而他母亲的虔诚和传教士基督教烙印让他越来越恼火。当他把沉重的饭锅盖直接扔给父亲时,他知道是时候搬出去了。然后他试图自杀,但在最后一刻想通了并继续活了下来。这种体验都是青少年走向成熟的一部分,少年“H”必须独立于家人之外,找出自己究竟谁以及自己的使命又是什么。直到影片的结尾,他似乎成功了,因为他已经准备好成为一名壁画艺术家。
二、个性化对白
电影中人物对白是表现人物个性的重要形式。降旗康男在人物台词的设计上别具匠心,语言短小精悍,尽量避免长篇大论和说教式的语言。
战争爆发教会受到牵连,正在参加礼拜的教会窗户玻璃被人用石子打破。妹尾肇向母亲询问参拜敌国的神灵应该是被禁止的,而母亲则认为真神只有耶稣一个人,天皇不是人们宣传的神灵。心有余悸的妹尾盛夫确定四周没有其他人后告诉他们,以后对基督教的镇压还会继续。“不要动怒,不要反抗。”盛夫要求亲人们不要和当局作正面斗争,心中有信仰就已足够。与其说是一种妥协,倒不如说是保护家人的唯一办法,充分表现出盛夫能够看清局势并以大局为重。再比如,盛夫因为美国明信片和协助教会的事情被日本特务严刑拷打,回到家中对妹尾肇说:“战争会演变成什么样子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不好好振作起来,就会被击溃的,现在正在发生些什么,用自己的眼睛去好好见证,虽然有很多不得不忍耐的东西,但只要清楚自己正在忍耐些什么,就可以做到,战争总有一天会结束,那个时候,要是成了可耻的人可不行。”这番话同样表明盛夫有着清晰的头脑,对家人表现出无限的关怀。沉默不是懦弱,忍耐不是麻木。用一个字“忍”体现出妹尾先生的为人处世之道并不过分。父子间的对白在电影中随处可见,模糊了战争片与家庭伦理片的界限。
战火烧到兵库县,妹尾肇和父亲站在满目疮痍的土地上但并没有绝望。妹尾肇告诉父亲,教会在战火中幸存下来,人们被转移到那里。盛夫询问家里人的情况后一脸茫然,对生活丧失了信心。“我本想救出缝纫机的,虽然从二楼搬下来,但还是把它扔到那儿了。”妹尾肇的一番话让心灰意冷的妹尾盛夫找到了生存下去的理由。在战火中保存完好的缝纫机帮妹尾一家走出了战争的阴霾。难民营中因为米饭的分配问题妹尾肇与家里人发生分歧。妹尾肇不愿将大米施舍给邻居,认为施舍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母亲却告诉他,“给予要比接受更能让人幸福”。整部电影中敏子给观众的印象是一种死守教条的日本家庭主妇的形象,但在教育妹尾肇时总是能一语惊人,母亲希望儿子遵守规则的同时也不应被规则所束缚。
三、人文主义关怀
《少年H》作为一部反战题材的电影,有着导演对战争的独特见解和反思,而这份理解则正是通过小人物的命运来体现的。影片无时无刻都体现出人文主义的光辉,盛夫因为自己有做裁缝的好手艺,妻子又是基督教信徒,理所当然地成为教会慈善中心的常客。兵库县很多人都不理解盛夫为什么帮助从纳粹德国迫害国家流浪来的犹太难民,而对盛夫来说,自己没有将这件事当成一种累赘,而是当成一件神圣的义务。盛夫这种博爱和人道主义精神也正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
妹尾肇的父亲的妹尾盛夫存在意义重大,他客观辩证地看待战争和自己家庭之间的联系,并试图礼貌地向少年“H”传达这一观点。古罗马诗人奥维德曾经说过:“忍耐和坚持是痛苦的,但它会逐渐给你带来好处。”基督教被镇压,盛夫选择忍耐,他清楚地认识到生活并不是战场,没必要分出高下。多一分理解就会少一点误会,多一分包容就会少一些纷争。因美国明信片受牵连的盛夫告诉妹尾肇,“小一”不是故意泄漏消息,过错方实际在于美日战争。父亲教儿子不要以己度人,不要强加自己的观点,更不要期望别人能完全理解自己的所作所为。在被质疑除基督教皆为邪教时,盛夫告诉妹尾肇每个人的信仰不同,换作其他教派的人看基督教也会被当作邪教。因此人要学会换位思考,不以自我为中心而蔑视他人。盛夫以一颗谦卑和恭敬之心来对待身边的人和事,正是这样才能保护家里人不受迫害,才能在战后挺起胸膛大步向前。
与妹尾盛夫的保守忍耐不同,妹尾肇选择与外界抗争到底,他不畏森田教官的淫威,继续追逐自己的艺术理想而遭到暴打。听到班长的“激情演讲”并没有像其他不明真相的同学随声附和,反而将日本快要战败的事实摆在大家面前,进而遭到班长的拳打脚踢。
四、迷茫和困惑
迷茫和困惑是整部影片的基调。我们透过妹尾肇的眼睛找寻战争中那些迷茫而又无助的人。“大哥哥”被扣上思想犯的帽子被带走,只留下妹尾肇一人不知所措地看着这一切,却又没办法去改变,无助和愤怒涌上心头。久门教官没有将妹尾肇培养成狙击手送往前线,认为将新兵送往战场无异于谋杀,迷茫和困惑反而让久门变得更加理智。森田被军国主义所同化,军校期间对少年H十分苛刻。日本被美国击败后,森田不愿接受日本战败的事实而跪在地上狂呼。实际上这类人仅是在迷茫中找寻一丝快感和存在感而已。班长先后在二战期间和二战后发表“振奋人心”的演讲。第一次日军吃紧缺乏兵源,班长鼓励大家投身于战斗中,就算是战死也要为天皇作出贡献。第二次日本已经战败,班长向全班人喊话不承认失败,誓要将上岸的美国人全数歼灭。由此可见军国主义对人的毒害之深。时至今日,依旧有一小撮日本人美化侵略战争,美化军国主义,而这才是最为迷茫,最为困惑的一群人。
五、日式战争题材电影的缺陷
影片继承“家族电影”的优良传统,用朴实无华的语言讲述妹尾一家在战争中所经历的磨难,以及国与国,国家与人民之间的矛盾,最终凭借顽强的精神和永不消逝的信仰如凤凰般重获新生的家族物语。电影《少年H》诠释了战争对人的戕害,却用跌宕起伏的剧情巧妙地规避对战争本质的刨根问底,这也是为什么日本所摄制的反战题材电影大多被打上不认真反思侵略历史的烙印。二战中,日本给其他国家所带来的灾难要远比自己所承受的灾难要严重得多,而在电影中导演暗示战争双方都是有罪的,日本同样是战争的受害国,却忽视了日本才是战争的发动者,是应负主要甚至全部责任的一方。
从海明威《永别了,武器》小说中我们可以深切感受到“迷惘的一代”所面对的失望、迷茫、颓废、折磨和伤痛。“战争是罪恶的、残酷的,除了带来死亡和毁灭,对人类毫无意义”。这与《少年H》中所要描绘的战争完全一致,战争一无是处,世界上再没有比战争更糟糕的事情。同时,他还谴责战争的发动者,也正是在他们的煽动下,越来越多的不明真相的追随者成为战场上的炮灰。
日本导演大多停留在个人立场孤立且片面地看待战争,未能在客观分析的基础上深究战争责任。电影中出现的受害者千篇一律是日本老百姓或日本士兵,而对其他国家的侵略战争鲜为提及,有故意美化战争之嫌,反战态度也相对消极,片中人物则是建立在错误的是非观基础上,对战争的厌恶更多的是出于一种本能,而非发自内心的反省和忏悔。《少年H》中的主人公妹尾肇并没有强烈谴责日本军国主义的对白。日本战败,妹尾肇去森林埋枪,也仅是高呼这场战争毫无意义而丝毫没有把侵略事实和承担的责任表现出来,此外,影片把日本打造成为遭二战纳粹德国迫害的犹太人避难的天堂,战败后美国大兵和日本当地居民就像是战争从未发生过一样竟然成了好邻居。
在军国主义盛行的日本,身穿母亲亲手缝纫并带有字母“H”的毛衣,充满好奇心又有着自己想法的男孩。妹尾肇有孩子气的一面,也有成人的一面。他对这个被战火侵扰的国家产生好奇并质疑世界的荒谬。日本平民在战前和战时对军国主义和天皇的盲目崇拜是媒体舆论煽动的结果,但妹尾肇的父亲与居住在神户的外国人互动,冷静地判断和分析用自己的头脑思考日本局势,并真诚回答解答妹尾肇的提问。
六、结语
虽然影片缺乏对战争的正面剖析,但《少年H》不失为一部发人深思的电影。一部影片能否够抓住观众的内心,引发观众的共鸣,不是单靠凭空捏造的“情境”来煽情,重要的是在假定性的情境中表现真实的感觉,通过细节的真实带动整体氛围的真实,从这个角度看,降旗康男的《少年H》可以说是一部从原著作者年轻时的角度描绘战争时期生活的优秀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