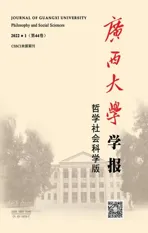爼豆与军旅非二事:阳明学人的用兵实践与工夫修炼
2022-11-21刘荣茂
刘荣茂
明代士人谈兵甚至亲自带兵是一个颇为流行的现象。①赵园:《谈兵——关于明清之际一种文化现象的分析》(上、下),《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02 年第1 期、2002 年第2 期。这既源于长期困扰明代的北部边防、东南倭寇、内部盗寇等诸多国防问题,又与明代政府常以文人督抚军务、限制武将兵权的制度安排有关。特殊的时代因素激发了明代士人的兵学思考。作为明代学术传布最广的阳明学,在此方面表现突出。除了军功显赫的王阳明(名守仁,1472—1529),阳明后学中不乏重视军事的学者。王阳明及其后学作为儒家学者不再如先儒一样,对兵学否定而摒弃,而是有限甚至积极地肯定与吸纳。值得注意的是,在明代的兵学思潮中,阳明学人之兵学不是技术性或功利性之趋向,他们以儒家思想为底色,赋予用兵的目的、方式及具体施行以人文价值,在儒学精神与伦理的层面上勘定兵学之意义。时贤对王阳明本人的用兵之术已多有考述,②张祥浩:《王守仁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第206-254 页;钱明:《王阳明的兵学术及武备策》,《浙江学刊》2019 年第1 期。然阳明后学的兵学论述罕有提及,而且阳明学人的兵学实践与心学(儒学)的密切关系并未得到充分探讨。从阳明学的整体看,他们卓越的军事功勋以及丰富的兵学思考蕴涵着一种论域广泛、观点鲜明的儒家式兵学的向度。本文尝试从用兵之必要、儒门兵将、用兵工夫等三个方面概括阳明学人独特的兵学思想,揭示其兵学实践中丰富的思想意蕴。
一、从“善战者服上刑”到“文武合一”
儒家自来反对兵战。子贡问政,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这似乎是对兵事的肯定。不过,孔子随后在三者之间先“去兵”的做法显示,养兵似乎是出于防卫的不得已之计,并非立国之本。卫灵公曾问兵事于孔子,他答之以“军旅之事,未之学也”(《论语·卫灵公》)。对于季康子“如杀无道,以就有道”的提问,孔子曰:“子为政,焉用杀?”(《论语·颜渊》)在为政上,孔子明确反对刑罚,而提倡“德政”,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以上均表明孔子在治道上力主“文治”而非“武功”,这开启了儒学反对暴力和刑罚的思想基调。
孟子之世,列国之间“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指斥“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孟子·离娄上》)。他游说诸侯,和孔子一样“无道桓、文之事”,提出“保民而王”的“仁政”之道,反对通过发展武力来实现国家强大。比孟子更具现实主义精神的荀子接受了当时列国养兵的现状,他专辟一篇《议兵》论养兵之道。不过,他认为用兵的根本不在于兵家所言的对“天时”“地利”“敌情”的重视,而是“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君、将、臣、民一体同心才是“仁人之兵”“王者之兵”(《荀子·议兵》)。
及至宋代,张横渠(名载,1020—1077)年少谈兵,被范文正(名仲淹,989—1052)责之以“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并劝其读《中庸》,遂成一代理学大儒。①张载:《张载集》,章锡琛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78 年版,第381 页。二程言:“兵也者,古人必不得已而后用。”②程颢、程颐撰:《二程集》,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版,第51 页。他们批评当时的兵事曰:“方今有古之所无者二,兵与释老也。”③程颢、程颐撰:《二程集》,第90 页。
王阳明受命平定地方动乱,难免毁伤生灵,波及无辜。阳明坦言:“兵凶战危,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者也。”④王守仁撰:《王阳明全集》(新编本),吴光等编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563页。他亲自督战,更能切身感受战争之危害:“古者不得已而后用兵,先王不忍一夫不获其所,况忍群驱无辜之赤子而填之于沟壑?且兵之为患,非独锋镝死伤之酷而已也。所过之地,皆为荆棘;所住之处,遂成涂炭。民之毒苦,伤心惨目,可尽言乎?”⑤王守仁撰:《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1011 页。此非阳明之煽情,他在平定南赣汀漳之贼寇时多以告谕劝降,后期征讨广西思恩、田州叛乱时通过解甲休养而安抚思、田土官。此外,阳明认为争斗频发乃由于教化不明,民风未善,所以他在地方安定之后广兴社学,转化一方风俗。⑥《阳明先生年谱》对此有多处记载,见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1251、1258、1326 页等。诸此均表明阳明之事功不是唯仰赖其武力,而是贯穿着儒家仁政之关怀。
南中王门唐荆川(名顺之,1507—1560)以带兵讨伐东南倭寇而知名。他亦言用兵杀敌之不得已是为保全更多人的生命:“生者,阳道;杀者,阴道。天生、天杀,虽云并用,而上帝好生,不得已而杀之……上古有罪者,一人不杀,则千万人不能生,故杀人所以生人也。”⑦唐顺之:《重刊荆川先生文集》卷十四《祭六纛司旗牌司刀之神文》,四部丛刊初编收明万历元年(1573)纯白斋刻本。在兵战中,仁民爱物仍是第一义的。对于兵事征伐,阳明学人以“全生”为尚。王阳明非常推崇《孙子兵法》中“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仁道精神,他对此评论道:“孙子作《兵法》,首曰‘未战’,次曰‘拙速’,此曰‘不战,屈人兵’。直欲以‘全国’、‘全军’、‘全旅’、‘全卒’、‘全伍’。‘全’之一字,争胜于天下”。⑧王守仁撰:《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1563 页。阳明弟子季彭山(名本,1485—1563)发挥阳明之意说:“兵,凶器;战,危事。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虽用之,必计万全焉。岂可因贪忿兴兵,而以所不爱及其所爱哉!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虽百战百胜,犹服上刑,而况未必尽胜乎!圣人所以慎战,为计万全耳。然临敌而始慎之,则晩矣,亦其所不得已也。是以君子之息争也,不在于微辞请罪之日,而在于修好睦邻之初。”⑨季本:《说理会编》卷八,《续修四库全书》第938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版,第650 页。“必计万全”不仅仅是尽可能保全我方兵卒之生命,而且使战争损伤最小,尽可能减少敌我双方之伤亡。
阳明和孟子一样认为,要使战争立于不败之地,根本是施行仁政。梁惠王曾向孟子请教在战国诸侯争霸时如何取胜,孟子的回答是:“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孟子·梁惠王上》)当弟子邹东廓(名守益,1491—1562)问老师兵法时,阳明的回答如出一辙:“何必孙吴,圣门自有节度矣。省刑薄敛,深耕易耨,孝弟忠信,爱亲死长,则坚甲利兵,可持梃而挞,彼民之爱我也如父母,而视寇夷也若仇雠,则狙诈咸作使,而奚宁谧之弗济!”①邹守益撰:《邹守益集》,董平编校整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 年版,第160 页。
用兵的根本在于“文治”而非“武功”。尚武只能助长暴力,以暴易暴,没有穷尽。而仁政养民才是平息争斗的长久之道,这既可以止息战争侵伐之戾气,又能够获得民心,巩固国本,为不得已之战争提供坚实的民力基础。究极而言,阳明和传统儒家一样,对用兵或兵事总体上持消极之态度。对他们来说,用兵是应对动乱及侵犯的一种被动的防御方式,不值得提倡与重视。所以,当弟子频频请教兵法时,阳明常转向其他更根本的层面。但是,随着明代南倭北虏边防形势的愈加严峻,阳明后学愈发重视兵事。
唐荆川除亲自指挥并参与抗击倭寇的战争外,还编纂过一部《武编》。此书汇集历代用兵之旨要,分将士、行阵、火药等151 门,内容十分详备。在编纂的另一部《历代史纂左编》中,他在“名臣”之外单列“将”之一目,将其视为国家治理之不可或缺者。好友王龙溪(名畿,1498—1583)在此书序言中对荆川重视兵学有进一步的阐述:
自问阵之对出于孔子,学者遂分爼豆、军旅为二事。不知此特有为而言耳。观夫文事武备之请,岂真未尝学者耶?圣人之学不传,儒者徒以雍容肆习、盘辟委蛇为文。而抱桴鼓、挥长戈专为武夫之所守,儒者益摈而不讲。不知雍容、盘辟非所以议爼豆,而抱鼓挥戈亦非所以尽军旅之事也,两失之矣。②刘荣茂:《王龙溪〈历代史纂左编凡例并引〉佚文》,《鹅湖月刊》2016 年第5 期。
以龙溪之意,儒学最初完备的礼、乐、射、御、书、数之“六艺”被后世割裂为文武二途,以礼乐为儒者之文,射御鼓戈为武夫所守,两者不相往来,遂失儒学文武皆备之原旨。唐荆川和王龙溪以儒学融摄兵学的努力不是孤鸣之音。黄梨洲(名宗羲,1610—1695)在《明夷待访录》中分三篇详细剖析了明代乃至历代兵制之得失。梨洲指出,明代军力疲弱的一个原因是文武分途,文臣专任计饷节制,武将只能操兵。表面上看此可犬牙相制,实则导致明代武人拥兵自重、朝中缺乏忠义勇略之将的败局。梨洲认为文武分途的制度也致使儒学存在重文轻武之弊病:
自儒生久不为将,其视用兵也,一以为尚力之事,当属之豪健之流;一以为阴谋之事,当属之倾危之士。夫称戈比干立矛者,士卒之事而非将帅之事也,即一人以力闻,十人而胜之矣。兵兴以来,田野市井之间膂力稍过人者,当事即以奇士待之,究竟不当一卒之用。万历以来之将,掩败饰功,所以欺其君父者何所不至,亦可谓之倾危矣……使文武合为一途,为儒生者知兵书战策非我分外,习之而知其无过高之论,为武夫者知亲上爱民为用武之本,不以粗暴为能,是则皆不可叛之人也。③黄宗羲著、吴光主编:《黄宗羲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 年版,第35 页。
梨洲的文武合一,一方面是要儒者谙习兵书战策,另一方面则培养武人的人文情怀,融化杀伐之气,使两者相互补充,增强国力。晚明阳明学人的重武风尚随着清朝的建立而趋于衰竭,但在清末民初国家遭受内忧外患时又引起强烈回响。不论是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派,还是章太炎等人的革命党,皆把王阳明推崇为尚武之典范。阳明之武功、阳明学之勇猛无畏精神在近代军国民主义思潮的背景下再次得到肯定、推崇。④陈立胜:《阳明学登场的几个历史时刻——当“王阳明”遭遇“现代性”》,《社会科学战线》2018 年第7 期。从晚明重武的历史看,阳明学在近代的“登场”,除了由于日本明治维新的外在刺激,也离不开历史的内在因缘。
二、儒门兵将
相较于近代推崇王阳明时仅仅崇尚武功、事功,阳明学人以儒学的视角看待兵学,自觉地以儒学融摄兵学。王阳明及其诸多后学都认为儒学与用兵存在相通之处。王龙溪对兵家之学有一个大胆的判断:“《孙子》十三篇,兵家之《六经》也。其言必原诸天,而曰:‘将之道,智、信、仁、勇、严’。斯五者,是即吾儒之德行也。‘治心’、‘治气’,即吾儒‘养心’、‘养气’之旨也。‘无智名、无勇功’,即吾儒‘忘己’之实也。‘其君信吾说则从、不信吾说则去’,即吾儒进退之节也。审若是,将之为将,是即吾儒之爼豆也,顾可专以军旅之事少之乎?”①刘荣茂:《王龙溪〈历代史纂左编凡例并引〉佚文》,第53 页。龙溪认为,《孙子兵法》所言将之德行、修为以及立身等为将之道与儒学观念十分接近,所以儒家不能因为兵学涉及杀伐而排斥之,同时儒家之道也有助于研习兵学。事实上,阳明及有兵事经历的后学多以儒学修身作为将领之素养。
钱绪山(名德洪,1496—1574)曾问乃师用兵之术,阳明答曰:“用兵何术,但学问纯笃,养得此心不动,乃术尔。凡人智能相去不甚远,胜负之决不待卜诸临阵,只在此心动与不动之间。昔与宁王逆战于湖上时,南风转急,面命某某为火攻之具。是时前军正挫却,某某对立矍视,三四申告,耳如弗闻。此辈皆有大名于时者,平时智术岂有不足,临事忙失若此,智术将安所施?”②王守仁撰:《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1498 页。“不动心”不仅是儒家修身之目标,在此也成为兵将临阵不惧的必备素质。
阳明再传弟子王敬所(名宗沐,1523—1592)曾担任江西右布政使、右佥都御史,平定江西动乱,巡视宣府、大同,身履兵事的他亦自觉以儒统摄兵学。王敬所特别撰写《儒将》一文,从儒学立场阐释用兵之道。他提出七种成为将帅的品质:“将者,兵之柁也,柁运则舟从;心者,将之机也,机从则柁应。坐作击刺与夫旗鼓进退有法可循者,姑置弗道也。而由主将者之心,其必不可已者,盖有七焉。凡当机欲圆,赴机欲迅,应卒欲闲,持议欲定,秉气欲壮,怀忠欲烈,虑势欲远……凡此七者,得二焉可以将,得半焉无不胜,全则无敌于天下。自非久于学以明其心,完其养,以定其气,其奚以及此!”③王宗沐:《敬所王先生文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11 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 年版,第349-350 页。此七种为将之品质,适用于兵刃相交的战场上,而它们需要通过一般的明心、完养、定气之修养工夫而获得。
季彭山弟子徐文长(名渭,1521—1593)与王敬所的观点十分契合。徐文长曾作为胡梅林(名宗宪,1512—1565)的幕僚参与后者指挥的东南抗倭战争,这段经历促进了他对兵学的思考。徐氏专辟一长文辩说将帅修养的重要性。他认为勇敢、气势鼓荡、决断等一般人看重的将帅品质仅是“将之粗”,将帅的关键在“治气”与“治心”。治气、治心以孟子的“浩然之气”与“不动心”为目标:“古之将多矣,无不治其气与心,而其治气与心,无不养之于闲,而始责期于猝,炼之于缓,而始求其效于临时……孟子儒于将,能将而未尝将者也,其欲跻齐宣而王之也,犹反手,此非将之效,而何效乎?至于尽授其诀于公孙丑,则特有‘善养气’与‘不动心’二三言耳。孰谓养气者非将之治气,而所以致其心之不动焉者,非将之治心耶……彼孟子者方且孺其服,士其冠,缓其带,安其履,委委蛇蛇,进而与齐梁之君谈道而论德,退而与其徒学孔而希周。明而以对于人,幽而以谨于独,办事之非义,而决不敢妄于一行,辨人之非辜,而决不敢妄于一杀。其致密于一尘一芥之微者既如此,而其昼夜之所从事,乃在于‘助’与‘忘’,‘帅’与‘充’,‘至’与‘次’,‘蹶’与‘趋’、‘得于言’与‘不得于言’,‘揠苗’与‘不耘苗’者也,而非有他也。研其几于有无之间,而致其谨于鬼神所不得窥之际,视其气息之柔,若属纩而欲绝,而心之澄且烛也,若渊之未澜而旭之始登,以至于枉直辨,义利明,则大者塞于天地,然后机之敏而断也若舍括。而胆之所向而所决也,虽百贲育于吾前而无所用其勇也,然后敢开口而决之曰,齐可王,而王可反手也。盖为将者之气与心,必至此而后可以言治,而治气与心,必如此而后可以尽将之道而无遗。噫,此诚未易以言也。古之言将者,儒与将一也,儒与将一,故治气与治心一也。”①徐渭:《徐渭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版,第892-893 页。徐氏此文甚长,笔者择要引述。徐氏以为,孟子“儒于将”“能将”,只是没有成为将帅的机会。这个论断可能有争议,但是他认为孟子在进退出处之中涵养的“浩然之气”“不动心”与“将者之气与心”并无二致,这一观点意蕴深厚。
徐文长和王龙溪、王敬所等阳明后学的看法总体一致:文武应当合一,将帅当以儒家理念为底色。值得注意的是,三人对儒学与兵学的会通中特别突出以儒学修身工夫作为将帅修养的重要性,他们共同指出,孟子的“养气”“养心”(“明心”“治心”)之说不仅是一种儒家工夫论,而且是将帅制敌取胜的要诀。《孙子兵法》本有“治气”“治心”之说:“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孙子兵法·军争第七》)此“治气”指克治敌军之气势,“治心”指克治敌军心理和情绪,两者均以制敌言。龙溪认为《孙子兵法》之“治气”“治心”即儒家之“养气”“养心”,这显然有误。不过,他将孟子的“养气”“养心”之说转变为一种为将之道,可谓“创造性的误读”。阳明后学宣称军旅不在“爼豆”之外,并非是空泛无实之口号。王敬所和徐文长对“儒将”的分析均指出,将帅在战场上必备的处乱不惊、相机而动、深虑果决等品质,要靠平日修养之积累,而孟子提出的“勿忘勿助”“扩而充之”“志帅气充”等修身方法恰恰是将帅修炼的最好指南。孟子原本极力反对战争,高呼“善战者服上刑”“杀一无罪,非仁也”等,不承想其人格修养的诸种方法在阳明后学处,竟能转变为兵事活动中的实践能力。
阳明学人主张儒学与兵学之相通,除了儒将合一之论,还认为儒学有助于兵法谋略。季彭山指出,兵法要以仁义为指导,“兵法以仁为主而以严行之。非仁则人心离,非严则人心玩,皆取败之道也。严与仁,礼乐之别名也。而谓行兵者,不本于中和之德可乎”②季本:《说理会编》卷八,第649 页。。仁义礼乐亦是带兵备战的行事原则。徐文长的说法与之相似:“盖天下之事无一不成于道,败于不道,而道莫要于孝弟。议者不察乎此,而谓兵之家尚诡与毅,于是率卤莽于家庭,而侥幸于阃毂,一涉孝弟事,则见以为迂阔钝迟,徒老生耳,一切置不讲。而不知赵括长平之败,乃由不善用其父书,而伯禽卒成淮徐之功,则以其敦信义习礼让,推本所致,乃自木叶俯仰中积累而然……夫兵犹博也,孝弟者其资也,胜而成功其采也,资高则气安而必胜,资寡则气不安而必不胜。”③徐渭:《徐渭集》,第562-563 页。徐氏步乃师后尘,也认为孝悌仁义是用兵取胜的关键,兵法兵计离不开儒学伦理。
并不是所有用兵之道都与儒家伦理相符。兵法中的诡道计谋常遭到儒家批评。荀子对兵事的重视程度超过孔孟,但他批评战国兵家以变诈袭击对方的谋略:“仁人之兵,不可诈也;彼可诈者,怠慢者也,路亶者也。”(《荀子·议兵》)荀子认为用兵攻占之本在于士民归附,而用变诈则会使君臣离德、敌方丧失归附信心。随着战争愈加复杂,后儒对计谋诡道也有所接受。宋儒二程认为,两军对阵,用计谋是必要的,但是当学生问及“间谍之事”,二程说“这个不可也”④程颢、程颐撰:《二程集》,王孝鱼点校,第217 页。。然而,阳明之用兵不但善于用智谋,而且还善于“用间”⑤黄懿:《浅谈王阳明“用间”艺术》,载张海晏、熊培军主编《国际阳明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79-86页。。不过,阳明对此三缄其口,密守不传。相反,他强烈批评阴谋诡计之行。⑥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27 页。或许阳明担心说出用兵计谋会“长乱导奸”,所以才“不形于奏,不宣于语”。⑦钱绪山曾提到,阳明在平宁藩之乱中用过反间计,后来却不再提及:“及事(平濠之事——引者注)平,报捷疏内,一切反间之计俱不言及。亦以设谋用诡,非君子得已之事,不欲明言示人。当时若使不行反间,宁王必实时拥兵前进,两京各路何恃为备?所以使之坐失事机,全是迟留宁王一着;所以迟留宁王,全是谋行反间一事。今日读奏册所报,皆可书之功,而不知书不能尽者十倍于奏册……先生有言:‘孔子修《春秋》,于凡阴谋诡计之事皆削之,以杜奸。’故平藩用间不形于奏,不宣于语,门弟子皆不闻,亦斯意焉。”参钱德洪:《平濠记》,《徐爱、钱德洪、董沄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234页。
阳明弟子对于计谋诡道则相对激进,对其必要性加以辩护。季彭山说:“以力角力,取胜为难。虽或胜之,而弟子之舆尸必众,此仁者之所不忍也。故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多方以误之,力争者之要法也。夫诡道,非圣人之所尚。然不能弭乱于未萌,酿成其势,至于不得已,则急于救人者必有仁术,故诡道不可尽废焉。”①季本:《说理会编》卷八,第649 页。用谋不仅可以增加取胜筹码,更重要的还在其能减少敌我伤亡人数。唐荆川在《历代史纂左编》将“谋臣”单列,王龙溪将其与盗贼之谋相区别:“神圣有神圣之机,盗贼有盗贼之机。神圣之机亦神圣之谋也,盗贼之机亦盗贼之谋也。故机慎则谋审,机藏则谋深,机密则谋不疏,机圆则谋不滞。或握其机,或窃其机。神圣握之以妙应,盗贼窃之以神奸。举不能外也。是造化之阴符,未尝轻以示人……或者以为神圣、盗贼之机混而为一,孰从而辨之?是不然。必为善,必不为恶,人之本心而天之机也,由君子以入于神圣。其握而用之,乃其天机之自然而不容已。彼小人之为盗贼,则所谓失其本心,窃之而已矣。”②刘荣茂:《王龙溪〈历代史纂左编凡例并引〉佚文》,第53 页。龙溪认为君子之心本具有不可测之机,小人作恶、失其本心才产生欺诈之术。由先儒反对诡道到彭山、龙溪等阳明后学的大胆肯定,亦是后者重视兵学、以儒摄兵的一个方面。
三、用兵工夫
阳明学是修身成德的圣贤之学,阳明学人追求“无一时不在于学,无一事不以学为证”,③王畿撰:《王畿集》,吴震编校,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 年版,第466 页。兵事活动为他们的修身之学提供了特殊的境遇。王阳明兵事之暇不忘与门人讲习讨论,唐荆川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在维扬(今扬州)任佥都御史巡抚并筹划兵务时,亦与王龙溪共讲良知之学。对于阳明及其后学来说,在兵事中为学不仅包括讲学论辩,更在于兵事中做修身的工夫。这一点可从荆川与龙溪在维扬的对话中得到清晰的展现。
荆川唐子开府维扬,邀先生往会。时已有病,遇春汛,日坐治堂,命将谴师,为防海之计。一日退食,笑谓先生曰:“公看我与老师之学有相契否?”先生曰:“子之力量,固自不同,若说良知,还未致得在。”荆川曰:“我平生佩服阳明之教,满口所说,满纸所写,那些不是良知?公岂欺我耶!”先生笑曰:“难道不是良知,只未致得真良知,未免搀和。”荆川愤然不服,云:“试举看?”先生曰:“适在堂遣将时,诸将校有所禀呈,辞意未尽,即与拦截,发挥自己方略,令其依从,此是搀入意见,心便不虚,非真良知也……荆川怃然曰:“吾过矣!友道以直谅为益,非虚言也。”④王畿撰:《王畿集》,第7—8 页。标点略有改动。
王龙溪对唐荆川致良知工夫的剖析全文较长,此处省文为便。龙溪指出,从战前筹划(“制木城、造铜面、畜猎犬”)、请兵誓师(“闻兄请兵,意气横发”)到战争期间的商讨(“议论未合,定着眼睛,沉思一回”)、应对(“奋棹鼓激、厉声抗言”)及决策(“官将地方事体,请问某处该如何设备”),再到事后赏罚(“有时行不测之赏、加非法之罚”)等整个兵事活动的过程中,荆川之修身工夫“搀入”诸多主观因素(“搀入意见”“搀入典要”“搀入拟议安排”“搀入气魄”“搀入格套”“灵根摇动”等),而不能达到“心虚”“神机”“无凝滞”“心正”等“真良知”的境地。龙溪对荆川的言行(“辞令”“举动”)、身体仪态(“定着眼睛”)乃至心理活动(“懊恼不快活”)进行了全方位审视,既揭橥其兵事行动中的多种工夫弊病,又展现出荆川在兵事活动中丰富而又致密的修身事项。对于唐荆川的兵事行动,龙溪之剖析如抽丝剥茧,细密深入,他不仅以他者的角度辅助荆川提高其致良知之学,而且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事上磨练”、在实践中用功的事例。
兵事活动作为性命攸关、充满危险的处境,在其中的修身工夫与日常之修养多有不同。王龙溪在与唐荆川的探讨中特别强调:“若是真致良知,只宜虚心应物,使人人各得尽其情,能刚能柔,触机而应,迎刃而解,更无些子搀入。”⑤王畿撰:《王畿集》,第8 页。标点略有改动。他认为,在敌我军情瞬息万变的情况下,将帅最重要的素养是顺应事态、快速而准确地应对,而要做到“触机而应”,需要将领之良知虚明无凝滞。王龙溪的观点与前文王敬所“当机赴机”说、徐文长的“治气治心”说异曲同工,他们认为用兵者“知机”与沉着镇静是取胜的关键所在。在阳明后学中,“机”本指个人意念端倪初露、意向未定之征兆,属自我意识,①牟宗三认为阳明后学所言“机”为个人意念“定吉定凶定善定恶之先兆”(其著《从陆象山到刘蕺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版,第258 页)。彭国翔对此有辨正,他认为龙溪之“机”是“良知心体呈露端倪而尚未形成固定意识状态的最初发动状态”而不属于经验层面,参其著《王龙溪与中晚明的阳明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年版,第136—141 页。而在用兵行动中,“机”则转指兵事事态发展之趋向或征兆。尽管他们并未列出这一区别,但用兵之事关生死的利害关系导致其对事态本身的关注是十分明显的。不过,在阳明学人看来,洞察兵事几微的前提是用兵者能够临危不惧、镇定从容,他们不约而同地认为这恰恰是孟子“养气”“养心”“不动心”等修身说所指之处。不论是王敬所、徐文长等兵事的亲历者,还是如王龙溪、钱绪山一样的旁观者,均指出“此心不动”在危险的兵事处境中的关键意义。对此,我们还可从王龙溪对乃师的回忆中得到印证:
夫人心本神,本自变动周流,本能开物成务,所以蔽累之者,只是利害毁誉两端。世人利害不过一家得丧尔已,毁誉不过一身荣辱尔已。今之利害毁誉两端,乃是灭三族、助逆谋反,系天下安危。只如人疑我与宁王同谋,机少不密,若有一毫激作之心,此身已成虀粉,何待今日?动少不慎,若有一毫假借之心,万事已成瓦裂,何有今日?此等苦心,只好自知。譬之真金之遇烈焰,愈锻炼愈发光辉。此处致得,方是真知;此处格得,方是真物。非见解意识所能及也。自经此大利害、大毁誉过来,一切得丧荣辱,真如飘风之过耳,奚足以动吾一念?②王畿撰:《王畿集》,第343 页。
依龙溪之理解,阳明用兵常胜的关键不是兵法秘技,而是临危不惧的心理素质,这和上文绪山所言高度一致。不论是绪山所说的“此心不动”,还是龙溪此处说的“不动一念”,抑或徐文长申辩的“治气”与“治心”,等等,都清楚地说明在孟子那里原本并非核心观念的“不动心”,在兵事行动中变得尤为首要。阳明学人的“不动心”其实也有理学工夫论的渊源,它与程明道(名颢,1032—1085)的《定性书》颇为近似,两者都指向一种内心的安定状态。区别在于,《定性书》要破除一种抗拒外物、封闭内心的错误做法,而用兵中的“不动心”则须克服患得患失、畏惧死亡的心理恐惧。显而易见,后者的处境更艰险,对修身者的历练也更彻底。如龙溪所言,两军对峙的危险境况也给修身者提供了一个检验自我、突破自我的极端机会。王阳明生命之跃升离不开他经历的种种战事,他自言:“某于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非是容易见得到此。”③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第236 页。“我自用兵以来,致知格物之功愈觉精透。”④王畿撰:《王畿集》,第343 页。当然,长期的征战生涯促进阳明思想之转进的同时,阳明修身工夫与其平定宸濠之乱等卓越的军事功绩亦关系匪浅。⑤王守仁撰:《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1497-1498 页。就后学唐荆川、王宗沐等用兵者而言,兵事行动与为学工夫也成为一个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回环。
四、总结
王阳明及其后学中的用兵者自觉以工夫论的角度融摄兵学,这是阳明学人军事实践的一大特点。王阳明从不夸耀自己的军事武功,他认为用兵是不得已的防卫性行为。但王龙溪、唐荆川、黄梨洲等人愈发强调兵事的重要地位,他们希冀儒家文治与兵家武备能够统一。阳明后学既遵循先秦儒家对兵事的基调,认为用兵是不得已,要以“全生”为上,又逾越先秦儒家和宋儒对兵学的批判和抵制态度,大胆承认现实中兵事的必要性。不仅如此,王阳明及其后学自觉地发掘儒学与兵家相通的元素,将修身工夫视为将领的关键素养,并将其提高到比兵法兵技更重要的地位,这与重视兵法、重视分析军情的传统兵学理念有着显著的区别。兵事行动作为生死攸关、充满危险的处境,给王阳明、唐荆川等人提供了一个特殊的工夫修炼的境域。儒家“养气”“养心”之修身工夫能让兵将在险境中成就“不动心”,沉着镇静,从容应对。同时,应对纷繁复杂的兵事活动又是检验其工夫修炼最佳的磨刀石和试金石。王阳明及其后学的用兵实践是阳明学“事上磨练”之工夫论旨趣的一个生动呈现,它既彰显出儒学工夫论的实地用功特质和实践效力,又是对传统兵学的拓展。总之,阳明学人的兵学实践十分丰富,不仅体现了阳明学的实践性格,而且是儒家工夫论的实地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