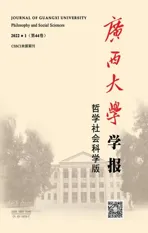意识作为“我对我环境的关系”意味着什么
——《德意志意识形态》与马克思的认识论革命
2022-11-21张义修
张义修
近年来,马克思的认识论思想重新获得学界的关注。在这一问题上,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早已超越苏联教科书体系的物质决定论诠释,强调“实践”之于认识的本质性作用,取得了重要突破。同时,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关于马克思认识论的研究也陆续译介进来,促进了学界对相关问题的理解。不过,大部分研究者主要依据的马克思文本是《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及马克思后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著作。如果回到马克思初次系统阐发历史唯物主义的文本——《德意志意识形态》,则会发现马克思留下的“我对我的环境的关系是我的意识”①[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28 页。虽然《德意志意识形态》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作,现存的相关手稿也交错着二人的笔迹,但其核心思想仍然是马克思的,同时为了论述清晰起见,本文在引述相关内容时均将之视为马克思的思想。等论述具有认识论革命意义,其内涵仍然有待挖掘。本文结合广松涉版《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相关手稿和笔记,希望深化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一、意识受到的三重“纠缠”:马克思对认识论前提的重置
笛卡儿以“我思”作为无可置疑的起点,开启了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也代表了认识论的通常倾向:将意识的起点或认识机制设定为某种原初、纯粹甚至先验的存在。按照笛卡儿的思路,可以反思一切事物之前提,却无法反思“我思”之前提。因此,将“我思”作为无可置疑的前提是逻辑之必然,反思“我思”之前提则是不合逻辑。康德通过追问“先天综合判断是如何可能的”,①[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第15 页。解析了“我思”所遵循的理性形式,但是他没有提出“理性形式的存在是如何可能的”这一前提问题。在马克思看来,认识论是否只能从认识本身出发,“我思”是否没有前提,这不是一个单纯的逻辑问题。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正是要打破意识的无前提性的假设,为认识论确立新的前提。
在马克思看来,研究“意识”的起点不在意识自身,因为“意识”从来不是自由洒脱而不受限制的,事实恰恰相反:“这种意识并非一开始就是‘纯粹的’意识。‘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②[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译,第26、28 页。马克思以反讽的语气谈到的这种物质的“纠缠”,就是指“意识”自其初始状态起,就受到外部因素的制约。对于意识所受到的“物质的‘纠缠’”,马克思作了三个层面的说明:
其一,从最切近的意义上,意识总是受到语言的制约。马克思指出:“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③[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译,第28 页。这一点已经得到人类学和脑科学研究的证实:从人类学层面看,大脑的进化与语言的诞生密切相关;从脑科学层面看,语言对于大脑神经网络的发育及其意识发展具有显著作用。马克思以历史性视角突破对意识和语言的静态理解,并进一步指出,无论语言还是意识,都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④[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译,第28 页。马克思显然没有把“需要”和“意识”画等号,也无意进行“先有意识还是先有交往”这种“鸡生蛋,蛋生鸡”的讨论,而是强调意识不可能脱离人们的现实交往需要这一前提。既然交往的需要推动了语言和意识的发展,这种需要的范围和程度也就制约着语言和意识的发展。在马克思看来,语言不仅是意识的载体,其本身就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才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⑤[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译,第28 页。在这里,马克思已经通过对语言的分析触及了意识的实践指向与主体间关系特征。如果考虑到20世纪哲学的“语言学转向”,马克思此处以语言来突破认识论的自足性假设的思路,可谓具有一定前瞻性。
其二,从结构性的意义上,意识无法脱离物质生产及其形成的历史性关系。如果说意识是人类交往的产物,这种交往的背后则是人类物质生产的历史性变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以人要活着(zu leben)作为人类历史的前提,将人类“第一个历史活动”明确为“生产物质生活(materiellen Lebens)本身”,⑥[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译,第22 页。Vgl.Marx-Engels-Gesamtausgabe,Bd.I/5,Ber⁃lin:de Gruyter,2017,S.26.阐发了人类历史性存在中的四重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谈及“意识”。换言之,对历史的结构性分析为“意识”问题奠定了全新前提。马克思指出:“生活(Leben)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达到的自己生活的生产,或是通过生育而达到的他人生活的生产,每次都表现为一种双重关系(ein doppeltes Verhältniß):一方面作为自然关系,另一方面作为社会关系;社会的含义在这里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⑦[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译,第24、26 页。Vgl.Marx-Engels-Gesamtausgabe,S.28.译文参考原文有改动。一方面,这里的生产是广义的,既包括为自己的生活而生产,也包括为他人的生活而生产(就此而言,生育只是其中的原初形式);另一方面,生产活动表现为“一种”“双重关系”,既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人与人的关系(家庭关系被认为是最初的社会关系)。⑧[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译,第24 页。以上四个方面并不相互独立,而是对同一个活动过程的结构性解析。这一解析也构成理解马克思认识论的前提:在苏联教科书体系中,“意识”往往被归结于某种实体性的物质基础,而马克思是以活动生成关系,以关系解析活动,然后才在这种关系结构的基础上谈到“意识”。
其三,从基底性的意义上,人的意识总是同人的特定的生产方式一道受到人自身及其外部自然条件的历史性制约。请注意,马克思这里讲的不是意识受到物质生产的制约,而是更深一步:物质生产本身也受到制约。马克思在手稿此处的边栏,以及后来写下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开头部分的新手稿中反复强调,生产方式不是人类可以自由选择的,毋宁说是某种自然选择的结果,是“人们自身的生理特性”同“人们所处的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山岳水文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①[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译,第23 页。历史性互动的结果。为了说明意识乃至生产过程都不具备自足性,马克思还特地在手稿的边栏补充道:“人们之所以有历史,是因为他们必须生产自己的生活(Leben),而且必须用特定的(bestimmte)方式来进行:这是受他们的肉体组织制约的,人们的意识也是这样受制约的。”②[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译,第26 页。Vgl.Marx-Engels-Gesamtausgabe,S.30.译文参考原文有改动。人自身及其所处自然条件的种种限制,不仅存在于人类历史的开端,而且在历史的全过程中始终存在。③[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译,第23 页。马克思的这些论述提示我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必须彻底:马克思不是把“实践”或者“物质生产”作为某种自足性的前提,以此替换“我思”或其他范畴的位置。他并不从任何自足的原点出发——无论是“意识”,还是“生产”“实践”,都有其现实前提,受到自然和历史的制约。这是马克思区别于一切旧哲学(包括旧唯物主义)的关键。
总之,并不存在纯粹而自足的意识,“我思”不仅有前提,而且前提不止一个。如果说将认识论问题独立出来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突破,那么马克思对意识前提的重置,则以否定认识论问题独立性的方式,实现了认识论的再度突破:在康德看来,彻底的认识论只有聚焦理性自身才是可能的;而在马克思看来,彻底的认识论只有结合社会历史基础才是可能的。
二、给定的“环境”与为我的“关系”:马克思认识论的内在张力
在分析了“意识”的多重现实前提之后,马克思开始探讨“意识”本身的特征与发展,进入传统认识论问题的核心语境。在这里,马克思留下了一个意味深长的论断:“我对我的环境的关系是我的意识(Mein Verhältniß zu meiner Umgebung ist mein Bewußtsein)。”④[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译,第28 页。Marx-Engels-Gesamtausgabe,S.865.为了准确理解这一表述,本文先对其中的“环境(Umgebung)”和“关系(Verhältniß)”概念加以解析:
“Umgebung”源于动词“umgeben”,后者由前缀“um-(围绕)”和动词“geben(给)”构成,故为“环绕、包围”之意。由此衍生出的名词“Umgebung”,指的便是环绕在某人、某物周遭而给出的东西,因此常常译为“环境”“周围”。不过,如要准确理解的话,我们便不能直接以中文的“环境”来理解这一概念:一方面,中文语境下的“环境”一词一般对应于另一个德文词“Umwelt”,并且倾向于指代某种物性的、可供活动的场域,甚至指非主体性、偏自然性的外部空间。而“Umgebung”并不指某种空洞的场域,而是有具体事物填充其间,只不过并非处于中心,故而也有“郊区”之意。另一方面,这种围绕在某人、某物周遭的“Umge⁃bung”并不单单是物性的、自然性的,也包含“周围的人”的意思。因此,马克思此处所使用的“Umgebung”不能简单替换为“Umwelt”意义上的环境,因为意识所面对的不是一个在主体以外的纯然物性空间,而是环绕着意识主体的人、事、物所共同组成的世界。在此意义上,“Umgebung”一方面突出了被环绕的“意识”这一中心,另一方面包含了意识所遭遇的、被给定的一切人、事、物。
“Verhältnis”(由于历史原因,在原文中有时拼写为“Verhältniß”)源于动词“verhalten”,后者由前缀“ver-(接动词时使之及物)”和动词“halten(持有、认为)”构成,故而一般有两个意思:一是在观念层面,表示“持……的态度”“当作……来对待”;二是在客观层面,表示“处于……的情况”。也就是说,它涉及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就人面向其他人或者物的关系而言,它可以指前者看待、对待后者的方式;就人与人、物与物的关系而言,它又可以指彼此所处的相对位置、境况。因此,由此引申出来的名词“Verhältnis”也就包含以下意思:(1)人或物之间可衡量、可比照的关系;(2)比例;(3)复数“Verhält⁃nisse”表示情况、境况、局势。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除了使用动词“verhalten”及名词“Verhält⁃nis”,还使用了“Zusammenhang”“Beziehung”“Band”等表示“联系”的概念,但后面几个概念均侧重于事物之间“有没有”联系、联系“有多紧密”,而“Verhältnis”则将“有”联系作为前提,进而侧重于事物之间构成一种“怎样的”联系,这也符合中文“关系”的内涵。总之,“Verhältnis”即“关系”,它强调相互联系的各方所处的特定相对境况。而结合动词“verhalten”来理解,这种关系还包含主客体之间的特定方向性。马克思对社会关系、生产关系的探讨,使用的也都是这一概念。
经过以上概念辨析,回看马克思“我对我环境的关系是我的意识”及相关论述,马克思的认识论思想便更加清晰了。具体而言,马克思强调了如下几点:
其一,意识的对象不是纯然外在于意识主体的“自在之物”,而总是其周遭(um-)所给予(geben)它的人事物,即“Umgebung”。一方面,这种“环境”不是由意识主体个人的活动所决定的,而是受到特定社会、特定时代的人类活动与自然条件的制约。另一方面,每个意识主体的“环境”又不尽相同,因此马克思强调它只能是“我的环境(meiner Umgebung)”。在此基础上,才会有某些“看似”脱离周遭世界的意识活动。说是“看似”,是因为马克思反复强调意识的非纯粹性、非自足性:既不存在直达外物而不受主观干扰的意识,也不存在完全主观完成而超越客观局限的意识。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时曾用“樱桃树”的例子说明,即便是看似最基本的“感性确定性”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交往才被给予(gegeben)他的……樱桃树和几乎所有的果树一样,只是在数世纪以前由于商业才移植到我们这个地区。由此可见,通过(durch)一个特定的社会(einer bestimmten Gesellschaft)在一个特定的时代(einer bestimmten Zeit)的这种活动(Aktion),樱桃树才被给予(gegeben)费尔巴哈的‘感性确定性’”。①[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译,第16、18 页。Vgl.Marx-Engels-Gesamtausgabe,S.20.译文参考原文有改动。可见,意识只能遇到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所给予它的对象,总是处于某种无法完全自主、无法完全脱离,而且个体之间并不相同的周遭环境之中。这与海德格尔关于此在的“被抛”状态的分析具有相通之处。“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②[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译,第28 页。认识对象的这种社会历史性,被马克思视为摘掉“哲学家的‘眼镜’”③[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译,第17 页。方能认清的事实,因为他自己不是通过哲学推演,而是通过经济学等研究认识到这一点的——实际上,樱桃树移植的历史事实,就来自马克思此前在曼彻斯特摘录的《商业年鉴》。④Vgl.Marx-Engels-Gesamtausgabe,Bd.IV/5,Berlin:de Gruyter,2015,S.266.
其二,意识的形成过程不是单纯的被动接受,而是以意识主体为中心主动与对象建立“关系(Verhält⁃nis)”的过程。当马克思将意识界定为“我对我环境的关系”时,这个“关系”是由意识主体“我”所主动发出的,而且与“我”的主观“看待(verhalten)”联系在一起。因此,在德文原文中,马克思用介词“zu(对)”来表示我“对”环境发生关系的主动性、方向性,而不是用客观的、无方向性的连词“und(和)”。马克思在手稿的边栏补充强调,这种“关系”是为意识主体“我”而存在的:“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für mich)而存在的。”⑤[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译,第28 页。Vgl.Marx-Engels-Gesamtausgabe,S.30.马克思在此强调的是,人的意识活动具有主动性,这种活动所形成的“关系”总是呈现出“为我”的个体性。在某种意义上,这种个体性的关系超越了康德对于认知形式之普遍一致性的分析,继承了黑格尔对于意识“自为”发展的分析思路。正是这种主动性、个体性,使人的意识活动区别于动物对于外界环境刺激的被动反应,表现出更高级的状态。“动物不‘看待(verhält)’任何东西(zu Nichts),而且根本不‘看待’;对于动物来说,它对他者(andern)的关系(Verhältniß)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①[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译,第28 页。Vgl.Marx-Engels-Gesamtausgabe,S.30.译文参考原文有改动。汉译本将此处“verhält”译为“发生关系”,但是,马克思在何种意义上说动物不与他者“发生关系”呢?笔者的理解是,马克思想要强调的是人具有主动“看待(verhält)”环境的意识能力,即主动对事物“持有”某种观点与态度,而动物对环境的意识还停留于被动接受刺激和反应的水平。因此,动物对他者的关系也就不会像人一样,作为一种主动性、个体性的“为我”的“关系(Verhältniß)”而存在。
其三,意识这种主动与对象建立关系的能力不是与生俱来、亘古不变的,而是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马克思阐述了人的意识随着生产进步和分工发展,从原本“纯粹动物式的意识”②[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译,第28 页。转变和提升的进程。这提示我们:马克思无意将“关系”或“意识”先验地预设为独属于人类的范畴,然后再凭借是否存在“关系”或“意识”来区分人与动物。③马克思在后来的写作中明确否定过这种区分的意义,而继续强调生产实践的基础性:“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参见:[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译,第23、25 页。马克思要分析的是人的意识如何伴随实践的发展而超越直接性的动物本能,不再“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界”,④[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译,第28 页。而是具备“现实地想象(wirklich einbilden)”和“现实地设想某种东西(wirklich etwas vor⁃zustellen)”⑤[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译,第30 页。Marx-Engels-Gesamtausgabe,S.31.译文参考原文有改动。的高级能力。就此而言,马克思尽管在曼彻斯特笔记中摘录了欧文关于“外部环境(äussern Umstände)”对人的思维、行动、性格的“预先确定(prädeterminirt)”作用的论述,⑥Vgl.Marx-Engels-Gesamtausgabe,Bd.IV/5,S.180.但他未必认同欧文的环境决定论。因为人的意识在面对环境时已不只是动物式的被动接受,而是能够在历史性实践的推动下,发挥越来越大的主动性、个体性,甚至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⑦[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译,第30 页。当然,“纯粹的”只能打引号。
如果说近代哲学已经将认识问题转向了主体,那么马克思并不否认认识的主体性,而是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强调:这种主体性的认识始终无法突破周遭环境对认识对象的制约,又始终依托于实践发展对认识机制的深化。这就是马克思认识论在给定的“环境”与“为我”的“关系”之间所具有的历史性张力。在此,我们不难看出黑格尔关于意识发展的辩证分析对马克思的影响:前者以“实体即主体”的原则⑧[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先刚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年版,第11 页。打通意识对象与意识自身,而马克思认为,二者的内在统一不是由绝对精神的实现所驱动的,而是由人类的历史性实践所推动的。
三、颠倒的意识与狭隘的关系: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初步破解
马克思在阐述了人类历史性存在的原初“关系”之后,又将“意识”同样界定为“关系”,这意味着什么?笔者认为,这不仅说明关系性的分析视角构成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重要维度,而且说明意识的形成同社会生产生活方式本身存在同构性。理解这一点与直观主义反映论的区别,是我们准确把握马克思的认识论及其意识形态批判的关键。
首先,意识与实践并不是相互独立地构成两种关系,而是构成同一种关系的不同侧面。如前所述,人类在生产生活中与周围世界形成的是“一种”“双重”关系,即融合自然关系与社会关系两个维度。而在这样一个关系网络中,每一个维度又都无法脱离人的意识而存在:在自然关系中包含了人对自然的意识,在社会关系中包含了人对人的意识。这种关系不仅包含意识,而且塑造意识——不仅赋予意识以“质料”,而且塑造了意识的“形式”。也就是说,社会生活的关系结构不是直接“映射”在白纸般的意识之中,而是逐渐让意识的运作也具备了关系性、结构性特征。就此而言,动物之所以无法与他者形成像人类一样的“关系”,不仅因为其生活中并不存在如此复杂的关系,也是因为其意识并不具备这种关系性、结构性的认知能力。动物之间只有简单的族群关系和简单的族群观念,它们无法理解更复杂的社会关系。人类也经历过这样一个“纯粹的畜群意识”①[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译,第28 页。的原始阶段。马克思说:“意识起初只是对周围的感性环境(nächste,sinnliche Umgebung)的意识,是对处于个人以外的其他人与物的狭隘联系(bornirten Zusammenhanges)的意识,个人开始意识到自身。”②[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译,第28 页。Vgl.Marx-Engels-Gesamtausgabe,S.30.译文参考原文有改动。而当分工发展到单个人、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相互交往的个人的共同利益产生矛盾的阶段,便产生了阶级关系以及国家观念。③[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译,第35 页。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④[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译,第35 页。但它又是“不同阶级间的真正的斗争”⑤[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译,第35 页。的场合。这种现实关系与观念架构的同向发展表明,人的意识形式之所以具有普遍一致性,不是纯粹出于大脑的构造,而是基于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特定历史阶段的普遍一致性——不难想象,假如古人“穿越时空”来到现代国家,也同样不具备对现代社会关系的感知和理解能力。因此,作为“关系”的“意识”并不是独立于四重原初关系之外的第五重关系。确切地说,人类社会生活的每一种关系都包含实践与意识的相互交织、彼此深化。正如马克思后来所总结的:“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⑥[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译,第29 页。因此,“我对我的环境的关系”不仅是“我的意识”,而且是“我的实践”与“我的意识”的同构性融合。
其次,作为同一关系的不同侧面,理解实践关系对于理解观念、意识的作用不可忽视。而如果以直观的、反映论的方式,简单将观念、意识对应于客观实在,恰恰会错失观念、意识背后的实践关系的内涵。这一点集中体现于马克思对“错误的、虚幻的意识”的剖析。
在直观主义反映论看来,既然是“错误的、虚幻的意识”,就是未能如实反映现实,而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这种意识的存在恰恰表明现实中存在着某种狭隘的物质联系、颠倒的社会关系。马克思说:“这些观念都是他们的现实关系(wirklichen Verhältnisse)和活动、他们的生产、他们的交往、他们的社会和政治关系有意识的表现(bewußte Ausdruck),而不管这种表现是现实的还是虚幻的……如果这些个人的现实关系的有意识的表现是虚幻的,如果他们在自己的观念中把自己的现实颠倒过来,那么这又是由他们狭隘的物质活动方式(bornirten materiellen Bethätigungsweise)以及由此而来的他们狭隘的社会关系(bornirten gesellschaftlichen Verhältnisse)所造成的。”⑦[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译,第27、29 页。Vgl.Marx-Engels-Gesamtausgabe,S.989.马克思此处的解析非常深刻。正如意识不会凭空出现一样,虚幻的意识也不会兀自虚幻起来。而如果只是强调意识没有脱离现实,还不足以说明虚幻的意识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现实的影响。马克思则更进一步说明:意识的虚幻性,恰恰来自意识主体在现实关系中的狭隘性;对现实的颠倒意识,恰恰体现了意识主体在现实中所处的颠倒地位。因此,这种意识也不是像费尔巴哈所设想的那样,可以通过宣告其错误和虚幻性而加以消除——如果不改变背后的社会关系,所谓的虚幻意识也就不可能被消除。
不过,这里对虚幻意识的解读不应泛化,它针对的是在一个特定社会中具有一定影响的“意识形态(Ideologie)”:“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成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①[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译,第29 页。可见,马克思不是要将全部意识活动还原论地归结为人们的现实活动,而是致力于对一个社会中颠倒性的实践关系与结构加以深入洞察,通过破解意识形态之谜,为推动现实历史变革奠定基础。而一旦走上这样一条新的道路,马克思便不再想与德国的思辨哲学家们继续纠缠“关于意识的空话”了:“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②[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译,第33 页。
马克思的这番宣言,不仅对于唯心主义思辨哲学具有批判意义,也对我们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深具意义。关于“意识”问题,我们需要避免重蹈费尔巴哈的覆辙:过度强调感性与直观,却无法深入历史和关系。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时说:“正是在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者看到改造工业和社会结构的必要性和条件的地方,他却重新陷入唯心主义。”③[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译,第20 页。或许也可以这样说:如果我们对“意识”的解读完全脱离“工业和社会结构”的历史关系性内涵,而只有关于主客体的抽象思辨,我们也要小心自己重新陷入唯心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