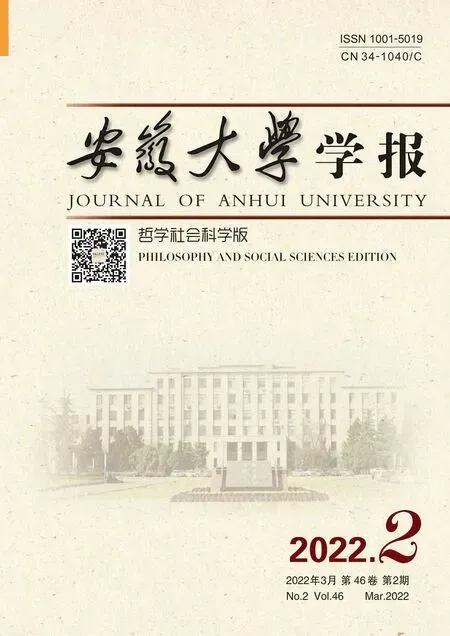正义与自我利益相悖吗?
——以《理想国》中哲人回归洞穴为典例
2022-11-21张波波
张波波
一、引 论
《理想国》中的哲人在回到政治生活的“洞穴”(1)“洞穴”在此象征着与“可理知领域”相对的“可感知领域”,而后者与政治事务紧密相关。关于柏拉图洞穴喻的探讨,参见D. Hall, Interpreting Plato’s Cave as an Allegory of the Human Condition, Apeiron, vol. 14, no.2 (1980), pp.74-86。中承担起王权的职责时是否为了“正义”牺牲了自身利益,这是《理想国》中最具争议的论题之一。有些人从“哲学活动对于政治活动的优越性”“强迫”等角度入手来给予肯定回答(2)Cf. J. Annas, An Introduction to Plato’s Republi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269; J. Annas, Platonic Ethics, Old and New,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05-106.,有些人则基于“政治正义”对于幸福的重要贡献来说明答案是否定的(3)Cf. Plato, The Republic of Plato, trans. with interpretive essay by A. Bloo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1, pp. 407-408.。针对此难题,本文采取后一种立场,并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供一个新的解决方案,以说明对柏拉图而言,“政治正义”和“灵魂正义”一样,都是一个人幸福和自我利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而“哲人—统治者”在根据“政治正义”的要求治理理想城邦时并未牺牲自己的利益(4)这里的“政治正义”(political justice)也叫 “公民正义”(civic justice)或“社会正义”(social justice);同样,“灵魂正义”(psychic justice)也叫“个体正义”(individual justice)或“内在正义”(inner justice),参见T. Mahoney, Do Plato’s Philosopher-rulers Sacrifice Self-interest to Justice?, Phronesis, vol. 37, no. 3 (1992), pp. 265-282。。
有关哲人重返洞穴的问题其实源于苏格拉底对哲人王候选者施加的一个强制性要求:理想城邦的统治者在完成了一系列哲学教育之后,需暂时从其珍爱的哲学沉思中抽身出来,将纯理论的研究搁置一边,以便全职担任政治职务(519c-d)(5)文中所参照的柏拉图文本为Cooper等人编的英译本,以斯特凡努斯标准边码随文夹注,见Plato: Complete Works, eds. by J. Cooper & D. Hutchinson, Indianapolis: Hackett, 1997;同时也参考了J. Burnet校订的希腊文本, 见Plato, Platonis Opera (5 vols.), ed. by J. Burne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00-1907。。在苏格拉底提出这一要求后,格罗康立即发问,这样做是否对哲人不公,是否与他们的切身利益背道而驰?(519e)苏格拉底连忙辩解说,理想城邦的法律并不是为了给某一特殊群体带来最大的幸福而设计的,而是以促进整个共同体的繁荣为宗旨。也就是说,立法的目的之一在于保全城邦的整体利益,而不是为追求局部利益的最大化而牺牲利益分配的均衡性(519e-520a)。他接着指出,对哲人的要求看似过分,实则恰如其分:既然哲人从城邦提供的优质教育资源中获益良多,加之这种资源使得他们比其他群体更有资格统治城邦,那要求他们腾出一些私人时间用于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自是再公正合理不过的了(520a-d)。他们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定会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安排的公正性,最终会接受它,无论他们心里有多么不情愿,心中有多少无奈情绪(520e-521a)。
这番对话产生了一个不良后果,即它似乎破坏了柏拉图在证明正义总是符合“行动主体”最佳利益这件事情上所付出的努力(6)Cf. A. Adkins, Merit and Responsibility: A Study in Greek Valu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 290-293.。因为519a—521e这段文字意在说明,尽管哲人会因为认识到这一要求的公正性而去遵守它,但他们的遵守是不情愿的,因为他们已见(7)这里的“看见”是比喻性的,指的是“用心灵的眼睛看”。这是柏拉图经常使用的一个比喻。Cf. T. Mahoney, Do Plato’s Philosopher-Rulers Sacrifice Self-Interest to Justice?, Phronesis, vol. 37, no. 3 (1992), pp. 265-282.过“好之相”并能充分认识到,与统治城邦的政治活动相比,纯粹的哲学活动对他们有更大吸引力和更大好处(521a-b)。他们内心的不情愿是人之常情,似乎也为柏拉图所赞赏,因为柏拉图认为,如果一个城邦的全体公民都把统治视为一件美差,都为了争夺公职而相互争斗,那这个城邦就不可能得到善治(347d;比照521a、540b)。所以他貌似在暗示,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正义行动与个人利益背道而驰。这一暗示似乎与他在第二卷中承诺要论证的核心原则“正义与自我利益必然相统一”相冲突(8)很多人注意到这里存在某种不一致性。艾尔文等人认为,在《斐多》和《理想国》中,柏拉图有时被一种沉思的理想所吸引。虽然这不是柏拉图晚期对话录中的主要理想,但它误导读者认为柏拉图觉得哲人并不乐意承担公共服务职责。Cf. T. Irwin, Plato’s Moral 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 p. 163; T. Irwin, Plato’s Eth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pp. 299-301; T. Irwin, The Development of Ethics: A Historical and Critical Stud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107.。
我们并不否认这里的矛盾。因为正如很多研究者(9)Cf. R. Kraut, Return to the Cave: Republic 519-521, Plato 2: Ethics, Politics, Religion, and the Soul, ed. by G. Fin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235-254; T. Brickhouse, The Paradox of the Philosophers’ Rule, Apeiron, vol. 15, no. 1 (1981), pp. 1-9.所见,《理想国》的整个计划是要论证正义和自我利益之间不存在冲突。然而在519a—521e这段文字中,柏拉图似乎在默示,他笔下理想之城的一大特色是,某些有资格进行统治的成员自身的“好”与正义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分歧。让哲人去统治,尽管是正当的要求,但这不符合哲人的最佳利益——这一事实正好被柏拉图用来向其他公民说明:政治职位不是给那些只知道谋求私利而不关心共同体安危的人准备的,而是给那些为了城邦利益而牺牲自我利益的人设置的。因此,519a—521e这段文字的主要内容之所以令人费解,不仅是因为它为该对话录的主要论点提供了一个反例,还因为柏拉图本人貌似也认识到了使其成为反例的原因,即哲人视统治为一种内在的恶(10)不少学者认为哲人王视统治为一种内在的恶。Cf. R. Heinaman, Why Justice Does Not Pay in Plato’s Republic, The Classical Quarterly, vol. 54, no. 2 (2004), pp.379-393.。
以往学者采取的解决策略主要分为两种:一是用519a—521e这段话来表明,与字面意思相反,柏拉图从未承诺要从自我利益的角度出发,为正义进行全面辩护。因此,按此策略,柏拉图认识到,在这一特殊事例中必须“破例”,必须违反正义与自我利益相统一的原则(11)这种解决策略以哲人回归洞穴为反例,主要致力于揭示“正义”与“自我利益”之间的张力不可调和,而柏拉图也清楚意识到这与他在《理想国》中提出的主要论点相矛盾。Cf. S. Aronson, The Happy Philosopher—A Counterexample to Plato’s Proof,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vol. 10, no. 4 (1972), pp. 383-398; N. White, A Companion to Plato’s Republic, Indianapolis: Hackett, 1979, pp. 189-196; N. White, The Rulers’ Choice, Archiv fü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vol. 68, no. 1(1986), pp. 22-46; R. Heinaman, Why Justice Does Not Pay in Plato’s Republic, The Classical Quarterly, vol. 54, no. 2 (2004), pp.379-393.;二是从利己的角度来努力说明从长远来看,统治起着积极作用,终究能促进哲人的最大好,而《理想国》整个文本在此问题上的看法是一以贯之的(12)这种解决策略则致力于从“自利”的角度为柏拉图关于“正义有偿”的说法进行辩护,以期对《理想国》的整个论证做出一种融贯的解释。Cf. C. Reeve, Philosopher-Kings: The Argument of Plato’s Republic, Indianapolis: Hackett, 2006, pp. 201-203; R. Kraut, Return to the Cave: Republic 519-521, Plato 2: Ethics, Politics, Religion, and the Soul, ed. by G. Fine, pp. 235-254; J. Beatty, Plato’s Happy Philosopher and Politics, The Review of Politics, vol. 38, no. 4 (1976), pp. 545-575.。本文将提出的解决方案遵循第二种策略,并重点说明统治的内在价值及“政治正义”是如何使哲人受益的(13)还有些学者从“政治正义”“灵魂正义”与“相”之间的内在关联性角度试图说明柏拉图并未觉得“统治”与哲人的幸福背道而驰。本文的立场更接近于这种解释。Cf. R. Kraut, Egoism, Love, and Political Office in Plato,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vol. 82, no. 3 (1973), pp. 330-344; R. Kraut, Return to the Cave: Republic 519-521, Plato 2: Ethics, Politics, Religion, and the Soul, ed. by G. Fine, pp. 235-254; T. Mahoney, Do Plato’s Philosopher-rulers Sacrifice Self-interest to Justice?, Phronesis, vol. 37, no. 3 (1992), pp. 265-282.。
二、统治是否与哲人的最佳利益相悖?
统治是否与哲人的最佳利益相悖?由上文可知,部分学者根据519a—521e处的说法而推断出,在柏拉图看来,当哲人统治理想城邦时,他们的举动违背了其最佳利益。我们认为,这种推断缺乏说服力,实不可信。
从这一问题产生的语境看,这些解读者未能注意到这段文字中的一个关键细节,即苏格拉底在交流中面对格罗康提出的一些问题有意选择了沉默或回避。由此或许可以推断出,苏格拉底认为当前时机还不成熟,无法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例如,当格罗康问统治者是否因被强制要求统治城邦而过上更糟的生活时,苏格拉底却答非所问地说:“设计理想城邦的用意不在于让哲人获得最大幸福”(519d-e)。无论在519a—521e处,还是在《理想国》其他地方,苏格拉底都没有再回到格罗康的这一问题上来,即未阐明哲人如何从统治或担任政治职务中得到好处。苏格拉底虽然强调这一要求是正当的(520a-e),但显然不认为这一说法从“自我利益”的角度来看是站得住脚的。当然,也应承认,文本中也没有任何信息表明,必须将这里的“沉默”视为一种无声的让步,即不能从纯“利己”的角度来为这一要求展开辩护(14)参见包利民《古典政治哲学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52页。。
沉默在对话录中有时的确可被理解为默认或回避,但这本身并不是一个强有力的证据。针对柏拉图为何不在这段话中尝试说明统治符合哲人的最佳利益这一问题,其实还可以找到一个更好的解释,即他此时仍处在建设理想城邦的过程中,还远未完成“正义比不义于人更有益”的论证。在他看来,要了解为何统治对哲人有利,就必须更深刻、更全面地了解哲学生活所涉及的内容以及为何这种生活比其他任何一种生活都好。尽管在完成对哲学生活的描绘之后,柏拉图并未说明这种生活的政治成分以及为何哲人去统治于己有利,但他认为读者的工作就是要认识到从“自我利益”角度对正义展开的辩护如何能适用于这个特定的案例。
于是,正如很多阐释者正确指出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解释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用“自利”这一术语来捍卫正义的努力,因为要是误解了他的论证,也就无法理解为何正义在这个特殊案例中也是于己有利的。
然而,人们注意到,在519a—521e这段文字中,柏拉图似乎不只对统治是否以及如何使哲人受益的问题保持了沉默(15)Cf. T. Irwin, Plato’s Moral Theory, p. 163; T. Irwin, Plato’s Ethics, pp. 299-301.。有些学者(16)Cf. R. Weiss, Wise Guys and Smart Alecks in Republic 1 and 2,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Plato’s Republic, ed. by G. Ferrar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90-116.甚至更进一步得出,519a—521e这段文字所提及的“强制”一词清楚地表明,根据柏拉图,统治与哲人的“好”相悖。然而,我们认为这种理解值得商榷。
柏拉图确实多次说过,哲人是被迫统治的,他们视统治为一种必要,而非美差(347d, 520a, 520e, 52lb, 54lb)。很多人觉得,这似乎强调政治活动对他们不利,因为如果哲人能看到统治符合他们的利益,那为何还要强制他们呢?(17)Cf. N. White, A Companion to Plato’s Republic, pp. 24-25.
这个问题其实取决于对“强制”这一表述的理解。一般认为,这里所谓的“强制”意味着哲人是被迫接受政治职位的(18)一些人认为之所以要逼迫哲人统治,是因为“哲人只想过快乐的哲学生活,而不愿过痛苦的政治生活”,参见马华灵《古今之争中的洞穴隐喻:1930年代施特劳斯的思想转型》,《学术月刊》2016年第2期。。但实际上柏拉图并没有以惩罚相威胁来诱使哲人去统治(347c)。相反,他提出哲人应去统治,这出于哲人对自己所受训练的最终目的的清醒认识,即训练最终旨在让他们为治理城邦做好准备(19)Cf. N. Smith, Return to the Cave, Plato’s Republic: A Critical Guide, ed. by M. McPherr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83-102.;统治是正义之举,而正是哲人们接受了这一点,才愿担任政治职务。此外,如果哲人有能力理解《理想国》的核心论点,即正义与自我利益相一致,那他们定会认识到自己不会因担任政治职务而牺牲自己的利益。
可是,当柏拉图说哲人被迫去统治,且他们将统治视为一种必要时,他想表达什么呢?很显然,这些说辞并不意味着统治与哲人的“好”相违背,因为(P)主张某个行为是必要的说法完全可以与(Q)认为它符合一个人的最佳利益的说法相兼容。可见,519a—521e这段文字的核心要义是,在这种情况下,哲人无法随心所欲,不被允许做其认为的最好之事(20)Cf. N. White, A Companion to Plato’s Republic, p. 192.。哲人无论如何都不能脱离共同体自由行动。他们既然从城邦获得了巨大利益,城邦就理应得到同等回报。共同体中的任何人都不能以其认为的最好方式行事,这正是苏格拉底在520a这里所强调的。成员要融入集体,可能就需要“委曲求全”,尤其需要以促进整个共同体利益的方式活动。
由上可见,既不能从苏格拉底对“统治如何给哲人带来好处”这一问题的沉默中推断出正义与自我利益之间存在冲突,也不能从苏格拉底的说法中推断出,无论哲人愿意与否,他们都将被迫担任政治职务。然而,有人可能会认为519a—521e这段文字明确表明,根据柏拉图,哲人在返回洞穴时确实牺牲掉了自己的“好”(21)参见程志敏《从“高贵的谎言”看哲人与城邦的关系——以柏拉图〈理想国〉为例》,《浙江学刊》2005年第1期。。因为柏拉图多次说过,哲学高于政治,哲学生活好于政治生活,因而哲人不愿放弃一定量的哲学活动来担任政治职务,是正当的(520e-52lb,540b)。有相当一部分学者(22)参见包利民《“内化正义”是何种正义?——试析柏拉图的政治方案》,《河北学刊》2009年第5期;张立立:《“哲人王悖论”新解》,《思想与文化》2017年第1期。甚至认为,这些陈述明确无误地表明,即使哲人接受政治职务这一行为本身被认定为正义之举,但他若能违背这一要求,继续追求心中所爱,从事心爱的纯哲学活动,过纯粹沉思的生活,定会过得更好,更幸福。
若这样理解这段话,那显然是将两个有必要加以区别对待的问题混同了:
A1. 哲学活动好于政治活动吗?
B1.被理想城邦培养出来的哲人是选择(1)继续不受干扰地进行哲学研究,不惜违反统治城邦的正义要求,还是选择(2)腾出一些时间治理城邦,从而满足从政的职责要求?
A1这个问题已经在《理想国》文本中得到了明确的肯定回答。但如果像部分学者(23)Cf. N. White, A Companion to Plato’s Republic, p. 23; N. White,Plato’s Concept of Goodness, A Companion to Plato, ed. by H. Benson,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6, pp. 367-368.所认为的那样,对A1的回答等于对B1的回答,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当哲学研究是在使自身不义的情况下进行时,它的不义性就会降低其所具有的价值,更何况从各方面来看,相比于遵从政治正义的要求统治城邦一段时间,哲人作为正义之人若以不义的方式进行哲学研究,其性质会更恶劣(24)Cf. T. Irwin, Plato’s Ethics, p. 299.。换言之,不能贸然假定问题A1背后必然暗藏一个激进的说法,即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从事哲学活动都好于从政。问题A1背后的潜台词或许是,同等条件下,哲学好于政治,哲学生活优于政治生活(25)Cf. R. Kraut, The Defense of Justice in Plato’s Republic,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Plato, ed. by R. Krau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311-337; T. Mahoney, Do Plato’s Philosopher-rulers Sacrifice Self-interest to Justice?, Phronesis, vol. 37, no. 3 (1992), pp. 265-282.。如此便可明白,为何柏拉图会认为在哲学活动夹杂不义行为,而政治活动是正义之需时,从政乃是促进自身之好的更优之选(26)部分学者强调,哲人回到洞穴表明柏拉图认识到,城邦的好有时需要暂时消减个体公民的整体幸福。回到洞穴的哲人所经历的幸福的削减并未大到剥夺其幸福的地步,因为他们保留着美德,而美德足以带来幸福。这种暂时的幸福削减符合哲人的最佳长远利益,因为如今有更强大的城邦可以在未来更好地照顾他们。Cf. D. Morrison, The Happiness of the City and the Happiness of the Individual in Plato’s Republic, Ancient Philosophy, vol.21, no. 1(2001), pp. 1-24.。
若柏拉图的确如此认为,那他就应解释,为何正义地行事和不义地行事在哲人那里会有如此大的差别。他必须说明为何正义地行事符合哲人的利益,即使这样做需要哲人放弃一定量的哲学活动。如前所言,他在519a—521e这段文字中在“为何在这个特殊的案例中正义如此有利”这一问题上的沉默并不意味着他不能对此给出任何论证。
行文至此,初步的结论是,对于“哲人违背政治要求会过得更好”这一论点,《理想国》中找不到支持它的确凿证据。哲学活动比政治活动更有价值是事实,但该事实本身并不表明,不正义的哲学活动比接受任职要求的正义行为于己更有利。柏拉图在第二卷中承诺要证明,正义总比不义更有利,而当前所关注的519a—521e这段文字的内容并未显示他想要或需要在哲人返回洞穴的这个例子中违背正义与自我利益必然相统一的原则。
三、统治何以是正义的要求
上文表明从519a—521e这段文字中不能得出柏拉图认为哲人从政违背了其最佳利益,但还需要从统治的价值角度来继续追问:柏拉图何以证明哲人遵从政治要求比不遵从好?
对此,常见的一种解释是,哲人最好服从政治要求,因为他们若不这样做,就会导致觊觎权力者因争权而内讧,而这会严重损害其幸福。哲人的幸福在于获得尽可能多的伴随认识和学习真理而来的快乐,而统治则纯粹是实现这一人生目标与追求的工具性手段(27)Cf. T. Irwin, Plato’s Ethics, p. 300.。如果哲人拒不统治,理想城邦必然会被拙劣的统治者葬送,而哲人只能降心相从,生活于那些社会环境不太理想的城邦之中,从此几无机会获得认识真理的快乐。
这种解释看似很有道理,实则存在两大误区:一是“唯经验计算”。该解释认为,柏拉图基于推测性的经验计算得出哲人投身政治比逃离政治会获得更多的沉思之乐。换言之,那些完成学业的哲人留在理想城邦,会比为避免统治城邦而逃到其他非理想的城邦继续进行理论研究享受到更多的沉思快乐。然而,只有在除理想城邦外没有其他任何城邦允许哲人继续进行哲学思考的情况下,这种经验计算才正确。问题是,经验计算是柏拉图在《理想国》或其他对话录中都未曾诉诸的。《理想国》也不可能将对沉思快乐的经验计算作为其整个论证的基石。
二是“唯哲学快乐至上”。该解释将获得哲学快乐的多少作为评判哲人该不该回归政治的唯一指标,而未用到苏格拉底在解释为何哲人应该统治时所依赖的那个不可或缺的前提:哲人从城邦得到了最好的教育,所以他们应学会感恩,用这种教育回馈社会,造福城邦,服务他人,以偿还这笔教育债务,而这可视为再正义不过的事。然而,根据该解读,利用知恩图报、互惠原理来劝服哲人管理城邦事务这一策略本身对哲人没有说服力;哲人统治的真正原因在于未来收益将大于成本,也就是说,哲人用“功利主义思维”行事,其计算出,留在理想城邦内所增加的哲学快乐在抵消了统治的负担带来的痛苦后仍有结余。但该解释所强调的这个原因柏拉图并未提及,而且它会使柏拉图在文中明确给出的理由变得无关紧要,而后者恰恰在柏拉图看来是哲人同意统治的首要理由(28)对柏拉图而言,只有“正义”才能迫使哲人统治。正如在第一卷和第七卷中所描述的那样,统治本身就是一项繁重的任务,是最优秀的人(即哲人)所认为的不好的苦差事(347c,540b)。由于统治的本质是关心他人,因此对他人有利,所以苏格拉底坚持认为,即使是那些想要统治的人,也不渴望统治本身,而是渴望统治给他们带来的回报:权力、财富、荣誉和无限的自由,以及它们所保障的东西。关于统治之价值的探讨,参见D. Sedley, Philosophy, the Forms, and the Art of Ruling,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Plato’s Republic, ed. by G. Ferrar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108。。
进一步说,该解读坚信,统治的益处与其正义性无关。因为使该政治要求合乎正义的是人应该以善报善的假设。如果正义和最大利益在此情况下恰好重合,那在该解读看来,这将是一个幸运而奇妙的巧合(29)Cf. C. Reeve, Philosopher-Kings: The Argument of Plato’s Republic, p. 246.。然而,很明显,作为一心寻求确定性的思想家,柏拉图不可能承认正义和自我利益的关系是如此松散。他希望表明,正义因其本身必使人受益,不义则因其本身对人有害。因此,若要说明受过理想城邦课程训练的哲人最好统治一段时间,那就需要论证,让哲人去统治是一个公正合理的要求。这意味着,若想对519a—521e这段文字作出合理的解读,除需说明哲人为何受益于统治外,还需从柏拉图通过这段文字表达的观点中推导出统治和利益之间的内在联系。
沿着这样的思路,本文将在第四部分着重说明自己的解决方案。但在此之前,有必要先厘清《理想国》的总论证策略,因为为何哲人去统治于己有益这一问题与该策略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为何拥有正义的灵魂本质上是可取的——密切相关。
首先,必须澄清,柏拉图对正义灵魂内在价值的证明结束于第九卷,而不是第十卷。苏格拉底在完成了对僭主的描述后,便让格罗康比较前面几卷描述的五类人(即哲人王、荣誉政体者、寡头政治家、民主党人和僭主)哪个最幸福。格罗康得出结论说,每个人的幸福或悲惨与其美德成正比:哲人王最幸福,因为他最有德性,僭主最悲惨,因为他最坏,而其他人则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580b-c)。接着,苏格拉底满意地宣布,自己已完成关于正义灵魂内在价值的证明(580c)。
其次,柏拉图关于哲人王最幸福而僭主最不幸的说明真正起始于第五卷的结尾,因为在那他开始描述哲人与其他类型的人在哪些方面不同,而当他在第五卷中说到最幸福的人是像国王一样“统治”自己和他人的人时,他指出此人就是哲人王(580b-c)。所以他对哲人王的生活是最好生活的证明依托于第五卷中关于哲人王统治自我与他人的论述,而根本没有诉诸哲学生活的快乐。只有第九卷中在说明哲人生活相比僭主生活的优越性时,他才诉诸快乐。因此,不管哲学生活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根据第五卷中的这个论点,柏拉图认为使哲学生活成为最好生活的原因,不是哲学生活的快乐,也不是哲人对这种生活所包含的快乐的正确判断,而是这种生活所包含的“统治”(30)不少学者认为哲人之所以视哲学生活为最好,主要是因其快乐。本文不认可这种看法。Cf. N. Pappas, Routledge Philosophy Guidebook to Plato and the Republic,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pp. 118-127.。
最后,柏拉图关于哲人的说明与他在第四卷中对于灵魂各个部分及其适当安排的论述密不可分(31)Cf. J. Annas, An Introduction to Plato’s Republic, pp. 321-330.。他在第四卷中将具有正义灵魂的人描述为以理性“统治自己”的人(443d),而在第五卷中则把最幸福的人称为“自己统治自己、自己当自己的王”的人(580c)(32)有关柏拉图的“统治自己”、自主性以及“正义之人”的内涵之间的关联性的详细探讨,参见Plato, Laws 1 and 2, trans. by S. Mey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170。。换言之,幸福需要灵魂各部分之间保持适当的关系,而把这些部分安排得井井有条的是哲人王。这意味着,哲人王是正义之人的典范。
一旦将第四卷中关于灵魂各个部分及其适当安排的论述与第五卷到第九卷中阐释的哲人概念连接起来,便可明白《理想国》的核心论点:正义是一种美德,而美德是灵魂和谐,而灵魂和谐则是幸福。这意味着,正义在于灵魂的和谐,在这种和谐状态中,每个部分都在做其自然适合执行的工作。而要达到和谐状态,就需要“理性”的统治,因为灵魂不能跟着感觉走,不能意气用事,同时还需要了解什么才真正对灵魂有益。而什么真正对灵魂有益,以及灵魂如何获得这种知识,是柏拉图《理想国》中形而上学和认识论部分所回答的问题。普通人习惯用“肉眼”看世界,看重的只是永恒不变的“实在”的影子之类的东西,而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只能借助“心灵之眼”来发现。最有价值的认识对象是“相”,尤其是“好之相”。这意味着,对灵魂最有益的就是去理解和模仿“好之相”,而哲人在这件事上做得最好,所以他们的生活最幸福。
然而,柏拉图的正义理论除了涉及对灵魂正义的内在善的说明之外,还延伸至对政治正义的关注,而对政治正义的关注使得他不得不关注人类事务,尤其是涉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处理(517c)。在政治领域,柏拉图总是将正义与人际关系中的某种结构或模式联系起来。在此,很多人(33)Cf. J. Mabbott, Is Plato’s Republic Utilitarian?, Mind, vol. 46, no. 184 (1937), pp. 468-474.将柏拉图视为功利主义者,这是失之偏颇的。功利主义者不是为了人类自身的利益而在人类之间寻求建立起一种结构性关系,而是以个体幸福为基本单位,并试图将其最大化。功利主义以人类或所有有知觉的生物(而不是某个有限的有机整体)为其考虑对象,所以其目标不是将某种秩序或结构强加给“人性”,而是尽可能多地增加善并尽可能多地减少恶,从而产生尽可能高的幸福总和。在功利主义看来,人性或感知能力是一堆不成形的东西,而政治任务就是使这堆东西的福祉总和尽可能地增大(34)Cf. R. Kraut, Return to the Cave: Republic 519-521, Plato 2: Ethics, Politics, Religion, and the Soul, ed. by G. Fine, pp. 244-245.。
不同于功利主义者,柏拉图认为,城邦不仅仅是其成员的总和,城邦的整体幸福具有一种结构性属性,而这种结构性属性不能被简化为各部分的幸福之和。因此,他并不认为政治任务是一种简单的加减计算,即把个体幸福的总量加起来,同时减去个体的不幸福总量,这样就可以看出整个城邦的幸福水平(35)Cf. R. Barrow, Plato, Utilitarianism and Educ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pp. 1-13.。相反,他将城邦的塑造比作雕像的设计,并断言,只有当其各个部分都幸福(而不是尽可能幸福)时,它才是好的设计(420c-42lc)(36)柏拉图这里虽然说,他的目标是实现城邦最大的幸福(421c),但他的意思仅仅是指,如果让他在一个不那么幸福的城邦和一个更幸福的城邦之间进行选择,他会毫不犹豫选择后者。当然,他的意思并不是指,要确定一个城邦有多幸福,首先要确定每个人有多幸福或不幸福,然后用加减法运算。相反,正如一些人指出的,他对统治阶层有多幸福这个问题漠不关心,因为统治阶层幸福的增加,不管多么伟大,都不能证明其他阶层的不幸福是正当的。这表明,他对城邦的幸福施加了一种形式上的约束,即城邦的幸福必须来自其所有组成部分的幸福,而不能仅仅是一个总和。Cf. R. Kraut, Return to the Cave: Republic 519-521, Plato 2: Ethics, Politics, Religion, and the Soul, ed. by G. Fine, p. 245, n. 16.。他的城邦模型强调了公民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城邦要让每个人都必须得到幸福,同时要求每个人都必须为他人的幸福做出贡献。这意味着,理想城邦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不允许任何人将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不幸福之上。因此,《理想国》关注的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中各部分之间的某种互动模式,而这是一个比功利主义者提出的目标更有条理的目标(37)Cf. J. Creed, Is It Wrong to Call Plato a Utilitarian?, The Classical Quarterly, vol. 28, no. 2 (1978), pp. 349-365.。
由此可见,柏拉图对“正义”(dikaiosune)的关注其实包含了对“普通正义”概念的关注。正义是由人际关系中的适当模式构成的,不能简化为每个人的福利的总和。“正义”的共同准则(如以德报德、给每个人应得的东西及公平分配负担和利益)揭示了这种美德的重点不是总和,而是模式。正义不只是行善积德,其所需求的不仅仅是利益,还有对利益的合理分配。
对柏拉图政治正义概念的阐释不仅有助于说明柏拉图对“正义”的辩护确实包含对“普通正义”的辩护,而且还显示出他的“相论”在其论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38)Cf. J. Annas, Plato and Common Morality, The Classical Quarterly, vol. 28, no. 2 (1978), pp. 437-451.。因为“相”是构成模式的对象;每个“相”都与其他“相”有关系,因此“相”不能被孤立地理解,而必须放在关系中来把握(39)在晚期对话录(如《智者》《政治家》《蒂迈欧》和《菲丽布》)中,柏拉图探索了“相”与“相”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理解它们所需要的概念工具。在《理想国》这里,柏拉图则暗示了哲人在沉思抽象对象时其实是在模仿它们,因为苏格拉底说:“当哲人观察和沉思那些有序且始终不变的事物时……他会模仿它们,并尽可能地变得像它们一样”(500c)。。柏拉图在此提出了一种抽象的正义概念:正义是“元素”的合理结构,是一种组织,其中每个部分都与其他部分有适当的关系。
在柏拉图看来,正义符合适当的模式,所以为了正义本身而在人类当中寻求正义,就是欲求人类制度中的适当结构。这种“外在和谐”,即每个人都做自己的工作并得到其应得的,在结构上类似于灵魂的每个部分都做自己的工作的“内在正义”。而这两种结构,(J1)“政治正义”和(J2)“灵魂正义”,都反映了永恒存在于各“相”之间的和谐关系(40)关于“相”与“相”之间的关系,柏拉图指出,它们既不给对方做不公正的事,也不接受对方的不公正,因为它们的一切都是和谐的、合乎理性的(500c)。。理解正义之本性的人会认识到,在多变的世界中促进正义——不管是灵魂正义还是政治正义——就是在事物之间建立一种近似于“相之秩序”的秩序(490b, 500c-d)(41)柏拉图在一些对话录(如《理想国》490b;《斐多》79d;《蒂迈欧》90a-c)中频频断言,灵魂(或灵魂的理性部分)类似于“相”。有些学者(如克劳特)据此认为,一个和谐的灵魂比一个不义的灵魂更类似于“相”,人类关系中的正义模式比不义的政治制度更好地模仿了各“相”之间的关系。本文认为这种看法有一定文本依据,因为柏拉图在《理想国》500c—500d处指出:哲人通过研究各“相”之间的秩序除了使自身灵魂变得有秩序外,还能据此模型塑造人类制度,使之反映神圣秩序。因此,当一个人的灵魂要素之间的关系趋于和谐时,他在内心就获得了一个暂时的、不完美的合乎理性的秩序或结构,这是他能达到的最接近“相”的状态。同样,当一个人在自己的城邦中促进正义时,他与他人的外部关系就会变得接近于人类关系所能达到的神圣领域。如此观之,统治城邦的哲人正在参与一项神圣的工作,即整顿宇宙。Cf. R. Kraut, Return to the Cave: Republic 519-521, Plato 2: Ethics, Politics, Religion, and the Soul, ed. by G. Fine, p. 246, n. 17; J. Gosling, Plato,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3, p. 71.。
柏拉图的正义之人不同于色拉叙马霍斯等普通人。在色拉叙马霍斯看来,当一个人力量强到可以为所欲为而不受惩罚时,他还以不作恶来限制自己,只会显得很愚蠢。因为,按照常人的逻辑,既然可以逍遥法外,那一定要无限制地去追求世俗物质。柏拉图认为人对“外在善”的获取需要有一个“度”,这个“度”取决于灵魂的和谐结构;这个和谐的结构,甚至比灵魂更值得一个人去爱(42)有关内在正义与“相”之间关联性的论述,参见J. Lear, Inside and outside the “Republic”, Phronesis, vol. 37, no. 2 (1992), pp. 189-201。。对人的外在行为加以限制,不仅是内在和谐的一种表征,更是对各“相”之间关系之美的模仿。在外部关系中促进正义的人必然是适当结构的爱者,而人一旦认识到人类制度只是更大的结构秩序(即宇宙秩序)的一小部分,就会认为对人与人之间正义关系施以真诚热爱是非常值得且合乎理性的(43)Cf. T. Irwin, Plato’s Ethics, p. 252.。
总之,柏拉图力图说明,对正义制度的支持,对灵魂及其和谐结构的爱,以及对“相”的理解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由此可见,让哲人去统治并非是非分的要求,而恰恰是正义的要求,因为遵从政治要求本身无论从灵魂正义还是从政治正义来看都是对“相之秩序”的维护。
四、统治如何使哲人受益
回到此前本文所提出的关切,统治之善,即统治的内在价值究竟是什么?在柏拉图看来,一旦弄清楚了这点,便可明白为何哲人最好去接受其担任政治职务的正义要求。
首先,柏拉图对于统治之内在价值的说明直接关联于其“善论”和“相论”。他坚信,“善”是和谐或统一,这无论在社会层面还是个人层面都成立;“好之相”是人类最大的研究对象(505a-b),而对这种对象的研究必然包含对人际关系重要价值的关注。基于这样的价值导向,他相信人与人之间的某些关系是恰当而和谐的,而一个人如果在适当的时间,出于适当的动机,以适当的方式,“分有”了这些有序的关系,那这种分有本身就构成了对“相”的模仿。因此,他认为一个人如果理解了正义的本性,但仍违反人类关系中的公平要求,就是拒绝将“相”作为人类行为的“典范”。“相”作为“存在于不同于可感世界的一个独立领域中的实体”(44)张波波:《“辩证法”是何种方法?——试析柏拉图的认识论工具》,《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构成了最高的和谐秩序,而当人类以理想城邦规定的模式相互关联在一起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生成了一种特殊的结构,而这种结构是对“相”的最佳政治模仿(45)关于“相”在灵魂正义与城邦正义之间的桥梁作用的探讨,参见S. Broadie, Plato’s Sun-Like Good: Dialectic in the Republi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 p. 34。。相反,如果一个人知道某种政治安排是公正的,并因此觉得自己应该为城邦的福祉作出某种贡献,那如果他拒绝做出这种贡献,就是有意识地拒绝将“相”作为一种要模仿的模式,这就会损坏其自身利益。也就是说,人类最好的生活离不开对“相”的精致模仿。
其次,柏拉图关于“相”作为人际关系之范本的说明妥善地解开了我们在519c—520e这段文字中遇到的迷雾疑团。从正义与互惠之关系的角度来看,当一个人接受了哲学教育,并能用这种教育来帮助那些曾以某种方式对这种教育做出突出贡献的人时,如果他拒绝提供此帮助,就会破坏人际关系的正确秩序。接受他人的帮助,日后予以回馈,是正义之要求:凡有所得,必有所付出。一个人若没有对他人的恩德作出报答,就会成为混乱的制造者,因为人际关系的和谐涉及互惠,即对“利益”的各有所让和各有所得,而这些利益与个人的才能和需求息息相关(46)柏拉图这里显然使用了卷一中西蒙尼德的正义观:正义涉及归还一个人所接受的。关于正义与互惠之关系的探讨,参见T. Irwin, Plato’s Ethics, p. 174。。所以柏拉图关于“哲人应该统治”的论点并不取决于不正义地拒绝统治可能会产生的有害后果。他在此假定,这种不服从的不公正性本身就是阻止哲人放弃统治的决定性因素,因为拒绝人际关系中适当秩序的行为,使人远离“相”,这将导致其走向混乱无序,最终可能会灭亡。
总之,对柏拉图而言,正义符合一个人的利益,即使对正义的坚持需要放弃一些纯粹的哲学活动。一个人的“最高之好”并不总是通过纯粹思考“相”而得到。一个人的“最高之好”与“相”建立起并维持着一种特定的模仿关系,而当他未能在一个正义的共同体中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时,这种关系就会破裂。通过将社会和谐与抽象事物的和谐联系起来,柏拉图阐明了人类关系中的正义应具备的吸引力(47)Cf. R. Kraut,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Plato,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Plato, ed. by R. Krau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328-329.。
因此,在哲人返回洞穴的动机问题上,我们不同意一些人的看法:该动机与他们这样做能使别人受益这一事实无关(48)Cf. J. Cooper, The Psychology of Justice in Plato, American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vol. 14, no. 4 (1977), pp. 151-157.;也不赞成另一些人的观点:哲人不是在寻求自己的幸福,也不是在寻求别人的幸福,只是在做客观上最好的事(49)Cf. J. Annas, An Introduction to Plato’s Republic, p. 267.。这些观点显然很难与519c—520a这一段文字中强调的事实相协调,即哲人必须统治,因为福祉和益处必须分配给城邦的所有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给某个群体或个人。哲人的目标是以某种模式造福他人,这在于柏拉图认为真正的统治者不是为自己的利益而统治,而是为被统治者的利益而统治(342e, 346e, 347d)(50)与第一卷中声称统治只是统治者以牺牲被统治者为代价来丰富自己的手段的色拉叙马霍斯相反,苏格拉底认为真正的统治者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统治,而是为了被统治者的利益而统治。如果哲人被视为真正的统治者,那么柏拉图显然认为哲人具有很强的利他心。Cf. T. Mahoney, Do Plato’s Philosopher-rulers Sacrifice Self-interest to Justice?, Phronesis, vol. 37, no. 3 (1992), pp. 265-282.。所以,不少人(51)Cf. J. Cooper, The Psychology of Justice in Plato, pp. 155-156.支持的这一结论“哲人的终极目标是将整个世界的理性秩序总量最大化”是我们所不认可的。如果这是哲人的目标,那么即使在一个没有给他提供哲学教育的共同体里,他也会被要求从事政治活动。然而,在520b处,柏拉图明确授意,允许哲人在这种情况下放弃政治活动。
在我们看来,哲人返回洞穴的动机在于对正义的坚守与热爱。柏拉图认为哲人必然会在人际交往中公正行事,因为他们认识到某种分配模式是合适的。回到洞穴中的哲人之所以选择回归,并非全是为了避免被不如自己优秀的人统治(52)塞德利认为哲人同意统治,是为了避免被不如他们的人统治。Cf. D. Sedley, Philosophy, the Forms, and the Art of Ruling,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Plato’s Republic, ed. by G. Ferrari, pp. 256-283.,也不仅仅是因为他想做一个救世主,一心想让被困在那里的人受益(53)Cf. C. Reeve, Platonic Politics and the Good, Political Theory, vol. 23, no. 3 (1995), pp. 411-424.,而是因为他作为懂得感恩的人,记得别人为自己做过的好事。他认识到,这种偿还债务的方式,正是当前形势所要求的。他作为爱正义者必然是人类事务中某种模式的爱者,而不仅仅是其他人的爱者。这意味着,他不是随机将利益分配给别人,而是为了在人际关系中达到一定的平衡而将利益合理分配给他人。因此于柏拉图而言,爱社会安排中的正义与爱“相”之间的秩序之间存在着某种亲缘关系。
若这样理解,便不难看出,要求哲人统治的正义性与在这种情况下统治的好处紧密相连。一个人不可能从那种使自己脱离于“相”的行为中获益。他如果想过上最好的生活,就会明白模仿“相”就是他必须一直努力奋斗的目标(519c-519e)。“相”是一种正义秩序(54)在柏拉图看来,“相”是一种理性秩序。因为“相”从不偏离这一秩序,所以它们永远不受不正义的影响。。若拒绝在人际关系中按正义的要求行事,就无法模仿“相”。哲人统治时,并未停止凝思或模仿“相”。在政治领域,他们的模仿活动不再仅仅是沉思型的,而是以“相”层面上的和谐为模本,开始以一种在城邦中产生和谐秩序的方式行动(55)Cf. R. Kraut,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Plato,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Plato, ed. by R. Kraut, p. 328.。统治的益处在于与“相”拉近距离,而不是与之疏远。哲人一旦理解为何去统治是正义之事,就会立即明白,置统治于不顾而继续从事纯粹的哲学活动,将与自己的切身利益相悖,即使哲学这种活动在其他情况下会比政治活动于己更有利。哲人的偶像是神,就如《泰阿泰德》(176c-177a)所指出的,哲人追求美德,是为了“尽可能地变得像神一样”。而神绝对正义,所以哲人绝不会背离神,做不义之事(56)关于柏拉图的“我们应该追求美德,以便尽可能变得像神一样”这种说法所暗示的“似神般哲人”概念的探讨,参见M. Jenkins, Plato’s Godlike Philosopher, Classical Philology, vol. 111, no. 4 (2016), pp. 330 - 352。。
在此,人们可能对这种解释提出一系列疑问。
首先,从尊重个人意愿的角度来看,有人(57)Cf. R. Brandt, Ethical Theory: The Problems of Normative and Critical Ethics, Upper Saddle River, N. J. : Prentice-Hall, 1959, p. 369.可能会指责本文的解读忽略了哲人不愿统治的观点。在我们看来,哲人应急切地重返政治岗位,因为这样做他会模仿“相”,从而使己受益。但必须承认,柏拉图强调了这点,即哲人不认为统治是一项特别有吸引力的活动,实际上,统治不是一件美好之事,而是必要之事(540b)。
很明显,该指责忽略了如下情形:一个人可能因为某项活动所具有的某一属性而急于执行这项活动,而又因为其所具有的另一属性而不愿这样做。显然,哲人对为了治理好城邦而必须进行的琐碎而平凡的实践活动没有兴趣。也就是说,他不想对他人行使权力或下达命令。但这与他热爱那种回到洞穴时要执行的活动所具有的另一属性并不矛盾,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对他人行使权力正是“正义”所要求的。哲人必须热爱正义。因此,仅仅盯住哲人不愿统治这一点而忽视他对政治正义的热爱是不对的。他不喜欢政治职务,但爱正义。他对政治活动的这种复杂态度将使得那些被他所统治的人确信,他的统治动机源于对正义的热爱,而不是对权力、钱财和政治荣誉的热爱。
其次,从灵魂和谐与外在行动的关联性角度,还有人(58)Cf. D. Gauthier (ed.), Morality and Rational Self-interest,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1970, pp. 1-2.可能指责我们似乎忘记了这一点:对柏拉图来说,个人的正义不在于其所采取的外在行动,而在于其灵魂各部分之间的和谐关系。虽然正义的人必须以适当的方式对待他人,但人们可能会认为,促使哲人公正待人的原因仅仅在于这种待人模式对他的理性、激情和欲望之间的和谐关系有影响。然而,本文对为何哲人去统治城邦于己有益的讨论显然忽略了柏拉图正义理论的这一核心特征。因为,按照本文的解读,哲人从统治中获益,仅仅是因为他以善报善,并以这种方式模仿“相”。
对此我们需要做一些澄清。本文并不是说,根据柏拉图的理论,一个人按照“正义”的要求行事时,就会从模仿“相”这种行为中获益。相反,只有当他的某一行为表达了某种灵魂状态时,他才会从该行为中受益。换言之,他必须是一个热爱正义本身的人,必须对这种美德所包含的内容有深刻的理解。反之亦然,唯有对正义有深刻的理解,才能对其有深刻的热爱。哲人会从统治中受益,是因其认识并热爱“相”的秩序,并试图安排其灵魂和活动,以便让它们模仿“相”。他之所以受益,是因为他所做的正义行为表达了他对“相”的热爱,而他对“相”的热爱是其灵魂理性部分的一种状态。
再次,从灵魂受益的方式来看,还有人(59)参见朱清华《本体论的差异——柏拉图的哲人王与先秦儒家圣王的比较》,《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可能会说,根据柏拉图,判断一种行为是否正义的唯一方法就是抛开应如何对待他人的问题,而完全专注于考虑该行为能否通过产生灵魂要素的正确秩序而有益于灵魂。相比之下,根据我们的解读,对哲人统治的正义性的论证主要基于如何对待他人的问题。从519a—521e处的说法可知,柏拉图在捍卫政治要求的正义性时,确实用了某种适当的社会关系概念。这表明,他并不打算将人类个体的正义(灵魂的适当秩序)当作行动的唯一的充分标准。诚然,第四卷的结尾指明,正义涉及理性的统治、激情的协助及欲望的服从。但这个通用公式本身并没有足够的内容来在每一种情况下都筛选出正确的行动。虽然理性必须起支配作用,但当涉及如何行动的问题时,理性往往别无选择,只能考虑人类之间的适当关系。柏拉图对于“哲人必须统治”的论证表明他接受了这一点,因为他并没有通过将政治要求与灵魂的和谐联系起来来证明其合理性。尽管理性在做对个人最有利的事情时起支配作用(441e),但要确定什么对人最有利,务必要考虑到人所生活的世界的特征(如交往特性)。一个人必须认识到“相”的存在和和谐安排,并选择那些模仿它们的行为。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考虑到我们在成长过程中亏欠那些使我们受益的人什么(60)Cf. D. Davidson, Plato’s Philosopher, Apeiron, vol. 26, no. 3-4 (1993), pp. 180-194.。
最后,从沉思“相”与模仿“相”的关联性角度,有人(61)Cf. J. Harman, The Unhappy Philosopher: Plato’s Republic as Tragedy, Polity, vol. 18, no. 4 (1986), pp. 579-580.可能会提出,根据柏拉图,通过纯粹的哲学活动来沉思“相”本身就是对那些抽象对象的模仿。所以即使承认,在灵魂中表达“正义”的行为,是模仿“相”的,柏拉图也面临一个难题:为何哲人应以这种方式而不是那种方式模仿它们。如果哲人无视政治要求而继续沉思,他就会凭借沉思而继续模仿“相”。如果他统治,他就通过正义的活动,以不同的方式模仿它们。柏拉图如何证明这种模仿“相”的方式比另一种更好,就成了一个亟待回答的重要问题(62)Cf. A. Payne, The Teleology of Action in Plato’s Republi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 125-126.。
对此,我们的看法是,对柏拉图而言,当一个人为了做别的事而中断其纯粹的哲学活动时,他并没有因此而拒绝将“相”作为模仿的模型,因为无人能不受干扰地一直从事这种活动。如果模仿“相”是一种不间断的活动,那这对人来说就不是一个切实可行的理想。因此,从沉思中抽出时间这一行为本身不能被视为对模仿“相”的理想的拒绝,否则每当一个人不再沉思(如睡觉、醉酒或昏迷)时,就是在拒绝这一理想。相比之下,一个人拒绝统治就不只是中断了一项模仿“相”的活动,更是拒绝把“相”作为模型。换言之,柏拉图认为,坚持纯粹性原则,即永远不要拒绝作为模式的“相”,比做出妥协以便进行尽可能多的最佳单一活动更符合哲人的利益。有人(63)Cf. S. Broadie, Plato’s Sun-like Good: Dialectic in the Republic, p. 122.可能会问,是否有论据支持这一纯粹原则?实际上《理想国》中很难找到这样的论据。但我们的解释也并不否认柏拉图在其他对话录中对该原则给出了支持。
如果本文所支持的这种解释能站得住脚,那至少会有两方面的优势:其一可使柏拉图免于如下指责:他的目的与其策略自相矛盾,即他用“哲人返回洞穴违背自我利益”的例证为《理想国》的中心论点提供了一个反例,从而让论证的方向背离了原初的目的;其二,对理解《理想国》中一些颇具争议的重要主题产生了重要的指引性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从理智论角度看,该解释可以清楚地表明,柏拉图的人类善的概念不属于强理智论范畴,因为他不认为,在任何情况下,一个人只要通过最大化纯粹的智性活动,即对“相”的沉思,就能以最佳方式促进自己的善。如果有一个我们应该始终为之奋斗的单一目标,那就是对“相”的模仿,而不是对“相”的沉思。模仿“相”的计划,不只是存在于一种活动中,而是具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如统治、做纯理论研究)。因此,与一些人(64)艾尔文声称,哲人们不会因为统治而牺牲自己的幸福。而为了支持这一论点,他把他在《会饮》中发现的实践理想搬到了《理想国》中,而他在《理想国》那里发现了沉思的理想。由此,他认为,柏拉图在这两种理想之间随意切换。Cf. T. Irwin, Plato’s Moral Theory, pp. 236-243; T. Irwin, Plato’s Ethics, p. 300.的看法相左,我们认为,柏拉图关于哲人返回洞穴没有牺牲其利益的说法并不是自相矛盾或令人困惑的,他并没有在沉思的理想和实践的理想之间来回切换。他深信沉思是唯一的最好的活动,这种信念使他可以说哲人不情愿去统治,这与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统治终究符合他们的最佳利益的信念是相容的。他在《理想国》中设定的理想虽与沉思有关,但不是指对沉思活动的最大化,而是指对“相”的模仿(65)关于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的“沉思理想”究竟是指最大化一个人的沉思活动,还是指模仿“相”这一问题,本文的看法与克劳特的看法保持一致。Cf. R. Kraut, Return to the Cave: Republic 519-521, Plato 2: Ethics, Politics, Religion, and the Soul, ed. by G. Fine, p. 252.。
第二,从个体利益与共同体利益的统一性角度看,该解释可以更清楚地表明为何柏拉图相信,公民个人的好和正义的政治共同体的好必须始终一致(66)社会正义和个人自我利益之间不可能存在冲突,这是扎根于柏拉图哲学中的一个假设。Cf. T. Mahoney, Do Plato’s Philosopher-rulers Sacrifice Self-interest to Justice?, Phronesis, vol. 37, no. 3 (1992), pp. 265-282.。柏拉图认为每个人都有理由追求自己最大的好,但同时他也期望理想城邦里的公民总是做于共同体最有利的事。他之所以坚信做于己最有利的事与做对共同体最有利的事总是一致的,原因在于他预设:(1)个人最好专注于去模仿这些“相”;(2)这些“相”之间的和谐关系本身构成了理想的道德共同体的运行机制,而这种机制是个体关系中最高层次的关系形式,对其他关系形式具有约束和规范作用。由此,柏拉图得出:颠覆对共同体最有利的分配正义体系,绝不符合“行为主体”的利益。因为这样做一个人就会破坏其与“相”的关系,并被剥夺他自己所能拥有的最大好(67)Cf. G. Santas, Understanding Plato’s Republic, New Jersey: Wiley-Blackwell, 2010, p. 145.。
第三,从利己角度看,这种解释可以更加确证,柏拉图并非强利己主义者或极端自我主义者(68)Cf. R. Kraut, Egoism, Love, and Political Office in Plato,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vol. 82, no. 3 (1973), pp. 330-344.。当然,这个问题牵涉到利己主义的定义。柏拉图确实相信,如果一个人正确理解了自身的利益,那只要他把这种利益时刻放在心上,并做对自己最有好处的事,就永远不会迷失自我,永远不会出错。假定这就是利己主义的定义,那他就是利己主义者。但很多人提醒我们要考虑到还有一种强利己主义:它不仅认为“利己”永远是行动的正确指南,而且认为其必然是正确的指南,因为不存在其他指南。根据这种强利己主义,共同体(即便是理想的共同体)的好作为行动的理由便没有丝毫的分量和说服力。因此,根据这种“主义”,如果共同体的好与个体的好发生冲突,当然必须优先考虑后者。
五、结语:正义与自我利益的统一
综上,柏拉图不属于强利己主义者,他不会无视应如何对待他人的问题。他在《理想国》中两次明确表示要与强利己主义划清界限:一次是在519c—520e中;另一次是在此之前的419a—421c中,在那里他主张要完全剥夺护卫者的私有财产,因为这样做对共同体的幸福大有裨益。在这两段文字中,他都坚称,判定一种社会安排是否合理的标准在于其是否为构成社会的各个群体创造了幸福份额的适当分配模式。于他而言,对各种政治制度合理性的检验,不是看它们能否使社会中的某个群体尽可能地幸福,而是看它们能否让社会中的各个群体尽可能地幸福。这意味着群体的好优先于构成该群体的部分的好,也就是整体最优优先于个体最优。而这反过来又说明,如果个体最大的好与共同体最大的好发生冲突,前者应让位于后者。当然,正如不少学者指出的,柏拉图认为这样的冲突在其设定的幸福理论框架下不会出现,因为他坚持一种尽可能与正义的共同体之好相一致的个人之好的概念。即便如此,他还是明确指出:万一发生这样的冲突,那完全可以为了整个共同体的好而牺牲个人的好,也就是说,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69)人们通常在“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是否试图证明正义和自我利益总是一致”这一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有些人认为柏拉图并无这方面的意图,也有些人则认为柏拉图确实有这方面的意图。本文在此持后一种观点。关于这种分歧的探讨,参见R. Kraut, Egoism, Love, and Political Office in Plato,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vol. 82, no. 3 (1973), pp. 330-344; R. Kraut, Return to the Cave: Republic 519-521, Plato 2: Ethics, Politics, Religion, and the Soul, ed. by G. Fine, p. 253。。
有人(70)Cf. P. Nicholson, Unravelling Thrasymachus’ Arguments in “The Republic”, Phronesis, vol. 19, no. 3 (1974), pp. 210-232.可能会反驳说,既然柏拉图不是强利己主义者,那他为何要如此不遗余力地证明正义与自我利益相一致呢?他何不直接同意道德怀疑论者色拉叙马霍斯的看法:正义是他人的好?柏拉图这么做的原因在于其立场介于强利己主义与强利他主义之间,这使他觉得,当向某人鼎力推荐某样东西时,所能采取的最佳策略只能是竭力向对方说明这种东西如何能促进其最大好。他承认对自身利益的欲求,虽不是一个人做事的唯一的激励因子,但无疑是一个很强大的激励因素,并认为如果共同体成员认为正义和自我利益经常发生冲突,而只有通过好运二者才能相统一时,那该共同体的稳定性就很容易遭到破坏。一个人若不去调查自身的“好”究竟在哪里,一味地人云亦云,不加反思地接受社会上关于人类幸福的流行定义,则很可能会受到误导,进而迷失自我,最终只会害人害己。进而言之,柏拉图认为哲人最终选择统治城邦,而不是否定统治的内在价值,是因为哲人已经认识了“好之相”,并因此理解了什么是真正的好(幸福),从而“能够在公共或私人场合明智地行事” (517c)。这种认识使他们确信,去统治是对“相”的模仿,同时也是“政治正义”的要求,而“政治正义”同“灵魂正义”一样,都是一个人幸福和自我利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71)关于“好之相”对哲人价值观的影响,参见T. Irwin, Plato’s Ethics, p. 301; T. Mahoney, Do Plato’s Philosopher-rulers Sacrifice Self-interest to Justice?, Phronesis, vol. 37, no. 3 (1992), pp. 265-282。。如此看来,作为《理想国》中“哲人—统治者”形象的设计者,柏拉图不可能是只考虑自己利益的极端自私自利者,也不可能是一心仅为他人利益着想的无私者,而极有可能是弱利己主义者或弱利他主义者,即一位试图平衡和兼顾两方面利益的思想家。正是对“自我利益”和“他人利益”的双向关注,促使他努力证明正义和个人的幸福必然一致(72)正如很多学者指出的那样,柏拉图认为正义之人之所以公正行事,是出于对他人的福利和权利的关心和尊重,而且这种关心和尊重的程度丝毫不亚于其对自己的福利和权利的关心程度。所以绝不能把柏拉图式正义之人与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相提并论。关于《理想国》中正义与他人之好的关系的深入探讨,参见F. White, Justice and the Good of Others in Plato’s Republic, History of Philosophy Quarterly, vol. 5, no. 4 (1988), pp. 395-410; C. Morris, The Trouble with Justice, Morality and Self-interest, ed. by P. Bloomfiel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16-17。。
总之,柏拉图哲学,即使在厌弃政治权力和政治职位而追求灵魂正义和纯粹的哲学活动的情况下,也依然透露出了对人际和谐、自然秩序与政治正义的珍视和肯定,并表现出思辨性思维高于直观领悟的特征。也许,这就是柏拉图哲学在“洞喻”中对于亚里士多德哲学(无论是人的政治化还是哲学生活的理论化及其最优性)的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