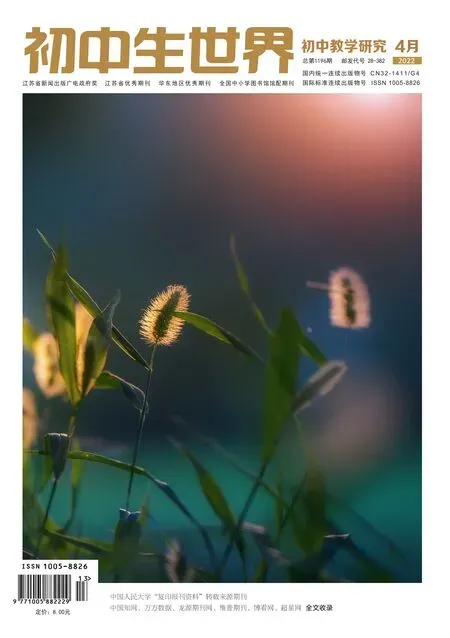如何顺势开展“背景导读”
2022-11-20徐连松
■徐连松
初中文学作品教学中常常需要补充一些写作背景,以帮助学生准确、深入地理解作品创作意图。而日常教学中经常出现背景材料的呈现不合时机,效果适得其反。
一、文学作品阅读中“背景导读”的呈现现状
1.两大基本导读类别。
一是教材单篇课文的导读。如统编教材《语文》(以下简称《语文》)九年级下册《海燕》的背景导读:“本文写于俄国1905年革命前沙皇统治最黑暗的时期。当时俄国工人运动不断高涨,动摇着沙皇统治的根基。作者敏锐地预感到时代的风云变幻,创造出广为传颂的‘海燕’形象,鼓舞了一代又一代革命者。‘海燕’在俄文里含有‘暴风雨的预言者’之意,阅读时要注意体会这一形象的象征意义。”
二是整本名著的导读。此类导读比比皆是,甚至成为众多读本针对中小学生群体的特有卖点。
2.导读的主要形式。
导读的主要形式包括背景介绍,内容概括,艺术特色。不少名著导读还精心设计了“圈点批注”的样式,从内容概括到艺术特色等诸多精彩、有价值之处,或和盘托出,或加以“引导完善”。
二、成因分析
1.“背景导读”之“利”。
对那些时代较为久远,形象相对比较“含蓄”的文学作品,若要准确、深入地理解创作意图,了解作者的写作动机和时代背景等资料就显得尤为重要。写作背景对理解文章的重要性,早已得到广泛认可。“知人论世”“披文入情”等观点,都在强调着写作背景对文意理解的重要性。
确实,恰当的背景介绍不但能够还原文学作品写作的现场,再现文本呈现的时代背景,让学生走进文本内核,也常常能够引起学生的阅读兴趣,丰富学生的知识,开阔学生的视野。
2.“背景导读”之“弊”。
写作背景导读的前置,容易束缚学生的解读思维。教师过早地把写作背景资料和盘托出,会给学生阅读文本造成先入为主的影响,不利于学生获得阅读的真实体验和独立感悟。如有些学生读完《海燕》的导读,再看看作者的名头,自我体验已经几乎荡然无存。毕飞宇说:“好作品的价值在激励想象,在激励认知。仅仅从这个意义上说,杰出的文本是大于作家的。”
导读,貌似“多快好省”,实则是植入式“快餐”,可以迅速“饱腹”,但长久“服用”必然导致“亚健康”,僵化思维路径,窄化思维宽度,弱化思维深度。
例如,《语文》八年级下册《小石潭记》的背景导读是:“柳宗元被贬谪到湖南永州后,常常探山访水,流连于自然胜境,以排解心中郁积的苦闷,写下了备受后人推崇的‘永州八记’,本文为其中之一。”
此段导读,让学生在阅读文本之前,既知晓了文章的内容,又明白了文章的写作意图,剩下来要做的就是“对号入座”,进行标签化解读。
再如《语文》八年级上册《白杨礼赞》的导读——“本文写于1941年抗日战争相持阶段,作者曾说:‘《白杨礼赞》非取材于一地或一时,乃在西北高原走了一趟(即赴新疆,离新疆赴延安,又离延安至重庆)以后在重庆写的。’”
尽管在这段导读中,写作意图尚给读者留下了揣度的空间,但背景介绍仍然偏早,容易影响学生初步接触文本后的个性化解读。可见,“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适配问题应引发教师的深入思考和审慎选择”。
三、顺势介入“背景导读”的几个“节点”
1.在事件或景象展开的关键点介入。
在文本事件或景象逐步展开的紧要处呈现背景,可以“引爆”学生的阅读思维能力点。如充分体会《记承天寺夜游》的文本画面后,教师此时引导学生结合背景导读,读到的还仅仅是一个简单的“闲”字吗?结合背景,学生明白,这里的如水之“清”自然指向了世道之“浊”,这里的竹与柏也自然显现出作者的气节。
反之,也经常可以见到一类公开课:教师上课伊始便对此文写作背景作详细呈现,接下来的教学过程只是从文本来“验证”背景材料,使得学生失去了应有的初步解读的自由与个性,与阅读教学应注重的“对话”原则背道而驰。文学作品阅读中的“对话”,主要就是“读者与文本的对话以及读者之间(包括教师)就文本解读展开的对话”。
2.在对全文内容整体了解的基础上介入。
在学生对全文内容了然于胸后,呈现背景可以整体促进阅读理解由表及里。张抗抗的《地下森林断想》,描绘的景象蔚为壮观。读完全文,可以深入思考:文章仅仅是在描绘赞美一个奇异的地下森林吗?其创作背景是张抗抗于19岁那年到农场当农工,在那里生活了8年。正值青春好年华的8年啊!出于对文学的执着,她于1972年10月发表了第一篇小说《灯》。
和所有的同龄人一样,张抗抗沐浴过灿烂的阳光,遭遇过“文革”的苦痛。然而张抗抗能成为一个作家,与她的不向命运妥协的精神密切相关。了解了这些背景,再读《地下森林断想》,就会更加理解作者的字字心声。同样,如果将这个背景前置到预习阶段,学生由表及里的思维能力将无法得到提升。
再看《紫藤萝瀑布》的背景。宗璞一家在“文革”中深受迫害,“焦虑和悲痛”一直压在作者的心头。写此文时,作者的小弟身患绝症,作者非常悲痛,徘徊于庭院中,见到一树盛开的紫藤萝花,由花儿自衰到盛,感悟到生的美好和生命的永恒,于是写成此文。
结合背景,是不是也就很容易读懂这些“景语”背后的“情语”呢?学生对文意的深入理解也就水到渠成了。而如果将背景前置,不但难以水到渠成,反而如“水过地皮湿”一般,只能停留在表象的“知道”层面。
3.在由浅入深的背景螺旋呈现中介入。
在适时适度的背景呈现中,可以获得由浅入深的阅读乐趣。看看小说《呼兰河传》的这个片段,读者读到的仅仅是一种自由的快乐吗?
“蝴蝶随意地飞,一会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又从墙头上飞走一个白蝴蝶。它们是从谁家来的,又飞到谁家去?太阳也不知道。”
在深受文本触动的基础上再了解创作背景,是否会读出自由背后的更强烈的心声呢?是否会读出在看似闲适、自由的语言背后,不幸的作者那份对自由的渴望,对不公命运的感慨?
我们还可以看一些故事性的背景。《丑小鸭》是一个几乎伴随了几代人的美丽故事。作者安徒生出生于贫穷人家。父亲是鞋匠,母亲是佣人。他早年在慈善学校读过书,当过学徒工。11岁时父亲病逝,母亲改嫁。为追求艺术,他14岁时只身来到首都哥本哈根。经过奋斗,他终于凭诗剧《阿尔芙索尔》崭露才华。
至此,丑小鸭的处境,丑小鸭的心愿,我们还能读不深,读不透吗?我们在读的时候还能只觉得“蛮搞笑”的吗?很多时候,我们又何尝不是丑小鸭呢?
最好的阅读是首先自由地阅读,自由地感悟,然后再结合背景与自己的理解做比较,这样,阅读就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奇妙过程。如《湖心亭看雪》,背景一前置,这篇精致美文的韵味已被损坏殆尽。其实,若只是自由初读,作者痴情于山水的情感自不难理解。此时再结合背景细读,自然就可以关注到文章以明朝崇祯皇帝纪年来开篇的用意了。包括“舟中人两三粒而已”中所透露的渺小无助感,学生也都能够比较自然地感悟得到。
四、没有背景导读的解读结果
没有写作背景的呈现,从某种程度上说,反而会给读者留下更为丰富的理解空间,也更合乎文学批评中“一千个读者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基本准则。
《语文》八年级上册《答谢中书书》便是典型。“晓雾将歇,猿鸟乱鸣;夕日欲颓,沉鳞竞跃。”这样的美文,和《与朱元思书》一样,也有景象与情感的空间,可供放飞解读的羽翼;正因为没有提供确凿的背景,反而能留足理解空间。学生依托文本,既可以将其理解为对友人仕途失意的宽慰,也可以将其理解为面对友人汲汲于功名,婉拒对方的“出世”的表白……
尤其是更为简约的古诗词文本,写作背景提供得越少,越能激发学生的想象力,越能呈现诗词本身特有的语言张力。如《观沧海》《行路难》《野望》……在学生信马由缰地驰骋于精约文句的基础上,教师再示以背景,既保证了文本理解的“入轨”,更保留了文本阅读的初体验、多体验的快感。
五、结论
教学中,教师对那些一眼就能看到的“发现”的过程,无须发力;教学的着力点应该放在一眼看不到的部分,引导学生紧扣字句及文本中的人物、境况来揣摩,比如为什么要如此交代事件这样的发展过程。换言之,“写了什么”,只是一个阅读铺垫,远没有“为什么写”重要;而“怎么写”也只能在透彻理解“为什么写”的基础上进行解读。
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言:“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大意是:作家创作,总是由内而外,即先有客观现实的感发而产生的内在情态,这种情态通过辞章表达出来;阅读文章的人通过文辞来了解作者所要表达的感情,找到文章的源头,即使是幽深的意思也将显现,被人所理解。“沿波讨源”,此处的“沿波”,其实不仅指“文辞”之“波”,也指“写作背景”之“波”,顺着这些,文章的“源头”才能被准确发现,对文意的理解也才水到渠成。
所以,教师在紧贴文本解读文学作品的过程中,应适时适度、顺势而为地交代背景,只有这样,自然而深入的理解才能也必能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