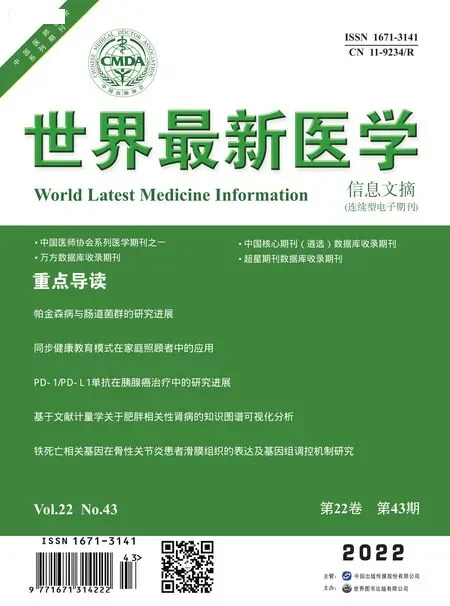帕金森病与肠道菌群的研究进展
2022-11-19翁世丽周哲屹顿玲露徐宏
翁世丽,周哲屹,顿玲露,徐宏*
(1.广西中医药大学,广西 南宁 530000;2.柳州市中医医院(柳州市壮医医院),广西 柳州 545001)
0 引言
帕 金 森 病(Parkinson’s disease, PD)以 震颤、肌强直等运动症状为主,其发病趋势呈渐进性,是全球第二大神经退行性疾病,仅次于阿尔兹海默症。目前全球发病率逐年升高,有大约7000~10000的患者每天生活在该疾病的阴影下,严重影响生活质量[1,2]。目前临床治疗帕金森的药物种类多种多样,例如左旋多巴、多巴胺受体激动剂、儿茶酚-O-甲基转移酶(COMT)抑制剂等,但对于帕金森晚期治疗效果并不理想[3]。近期研究发现,PD主要病理产物α-突触核蛋白可以在黑质和肠神经系统中发现,说明PD有可能最早起源于肠道[1]。近期研究发现,肠道菌群可能通过脑-肠轴中中枢神经系统、肠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等不同通路影响帕金森疾病进程,本文就帕金森与肠道菌群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为治疗帕金森病提供新的研究靶点。
1 肠道微生物组成及作用
肠道菌群又有“第八大器官”之称,肠道微生物群落由六个科组成,其主要的优势菌群包括厚壁菌门及拟杆菌门,肠道菌群有多种不同的生物功能,调节肠道代谢、塑造免疫系统、作为黏膜屏障的组成成分和抵抗病原体定植等。有研究表明肠道菌群与疾病的发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肠道菌群失调可引起人体许多内科、外科疾病[5-6]。肠道菌群与人体形成共生关系,脑肠轴作为二者中介,主要表现在人体免疫和代谢方面,肠道上皮细胞受到肠道菌群的刺激分泌粘液,可以增强肠道屏障保护功能,从而对病原微生物侵入人体有抵抗级免疫作用。
2 脑肠轴
中枢神经系统(CNS)可以调节肠道的功能和稳态,并与胃肠道关系密切。因此近年来提出了微生物-肠-脑轴概念,该轴是一个双向信息交流系统,与迷走神经通路、免疫方面和内分泌方面相关,可将大脑和肠道功能进行整合[7]。该轴还包括多个神经系统,例如中枢神经系统 (CNS) 、自主神经系统 (ANS) 的分支和肠神经系统 (ENS) 。当微生物-肠-脑轴进行双向信息交流时,主要有两条途径:
从肠道到CNS的传入纤维、肠道平滑肌的效应纤维[8]。现在普遍观点认为在肠脑轴进行双向信息交流时, 微生物菌群具有很强的活跃性,在信息交流时具有一定影响。
3 肠道菌群与PD的关系
PD是一个中枢系统退行性变,其主要病理变化是异常α突触核蛋白聚集[9]。肠道中的上皮细胞和免疫系统与肠道屏障功能及通透性相关,当肠道屏障功能和通透性被破坏时,意味着肠道微生物的组成发生了改变,这种改变同时伴随炎性反应,这被认为是间接或者直接导致α-突触蛋白错误反复折叠的原因[10]。α突触蛋白的炎性反应存在于多种蛋白反应中,肠道微生物可激活原始免疫反应引起炎性反应发生,在动物的PD模型中可以观察到周围炎性反应导致多巴胺神经元的损害,加速PD的发展进程[11-12]。肠道菌群还可以通过调节内分泌的方式调节全身的激素分泌等影响PD的发病和进程。以下将从神经、内分泌、免疫方面进行分述:
3.1 神经方面
在神经途径中,迷走神经传入神经将感觉信息从内脏传递到中枢神经系统。迷走神经通过中枢神经系统和延髓神经系统之间传递,是副交感神经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迷走神经中包括传入纤维和传出纤维,其中大部分是传入纤维,少部分为传出纤维。迷走神经传入纤维分布范围较广,存在于消化壁各层,因其不与上皮层相通,使得肠道内腔微生物群不可与传入纤维直接接触。因此,这些纤维只能通过上皮中传递腔内信号的其他细胞可间接感知微生物群信号,或者通过细菌化合物或代谢物的扩散[13]。迷走神经在脑-肠轴理论中有重要作用,肠肌神经丛和节后神经元形成突触联系,这种联系主要存在于传出纤维的末梢,大脑可接受其传递过来的肠道内的信息。α-突触核蛋白从肠道中传播至脑内的过程已经在动物模型上重现。接受迷走神经切断术的患者与普通人群比较,接受迷走神经切断术的患者患帕金森病的风险显著降低[14]。迷走神经传入末梢有三个亚型,这些末梢对化学和机械都很敏感。迷走神经化学感受器最有可能通过感知短链脂肪酸和胃肠激素参与微生物群和大脑之间的交流,当肠道中的短链脂肪酸降低时,患者脑内α-突触核蛋白的聚集约多,从而加重患者病情[15]。
肠道中的CD103+树突状细胞可以迁移入淋巴结,对T细胞的适应性免疫进行调节。T细胞可分化为辅助性T细胞(T-helper, Th)1、Th2、Th17和调节性T细胞(regulatory T cell, Treg)。迷走神经受到刺激后,肠淋巴液内CD103+树突状细胞数量得到一定程度的上涨,达到细胞之间的平衡。这些结果提示肠道CD103+树突状细胞可作为调节T细胞之间平衡的媒介,刺激迷走神经从而抑制过度失衡的炎症风暴[16-17]。
3.2 内分泌、免疫方面
在内分泌途径中,肠道微生物组在对应激反应至关重要的下丘脑-垂体-肾上腺(HPA)轴的发育和调节中起主要作用,肠道菌群主要通过HPA作用于肠内细胞。使得肠内细胞分泌的肾上腺素皮质激素、去甲肾上腺激素等激素增多,加速人体内肠道致病菌群的增值和附着;使人体内皮质醇分泌增多,肠道屏障功能减弱,促进更多肠道菌群转为内毒素,引起机体自身免疫功能的改变作用于中枢[17]。对患有认知障碍的小鼠的研究表明[18],出生后暴露于肠道微生物组会影响HPA轴的设定点。肠嗜铬细胞是散布在肠上皮中的肠内分泌细胞,可以响应于腔内刺激而分泌神经递质和其他信号肽,并因此充当肠-内分泌-中枢神经系统途径的换能器。此外,血管活性肠肽(VIP)是一种在肠道和大脑中合成的肽类激素,肽类激素中的神经降压素可促进多巴胺的释放,机制是肽类激素神经降压素可抑制多巴胺D2受体,可介导中枢神经系统炎症期间的免疫调节[19]。虽然微生物组对VIP表达的直接影响尚未确定,但饮食干预能够增加肠道VIP,这可能暗示了微生物组的作用。
免疫途径似乎是微生物-肠道-中枢神经系统信号传导的独立机制。中枢神经系统虽然被视为免疫特权场所,但并非没有免疫细胞,免疫细胞中多种细胞,例如巨噬细胞、树突状细胞、小胶质细胞、白细胞等分别存在于脉络丛、脑膜、脑实质、脑脊液中。中枢神经系统异常引起的自身免疫,可使神经组织直接免疫破坏[20]。共生微生物群,可重塑宿主免疫系统,影响外周免疫细胞对中枢神经系统的自身免疫反应。其次,免疫对中枢神经系统的交流也是由免疫因子的体循环介导的,这与抑郁症等神经精神疾病有关。事实上,增加外周炎症标志物如C反应蛋白(CRP)、IL-1、IL-6和肿瘤坏死因子(TNF-α)的因素也是抑郁症的危险因素[21]。在这两种途径中,都有抗炎机制,可以对抗免疫介导的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症状。肠道菌群的代谢产物SCFAs,游离脂肪酸受体影响SCFAs与肠道免疫细胞的相互作用,调节炎症因子白介素的水平。以上的功能均可以直接影响神经炎症,神经炎症日久间接影响情绪、记忆等高级功能[21]。
4 肠道菌群与帕金森的双向调节
中枢神经系统和脑肠轴之间的双向交流在健康或者疾病状态下均可发生。胃肠功能被神经网络控制,其为四级综合组织,包括内在和外在神经系统:肌间、粘膜下丛以及肠神经胶质细胞的神经元为代表的神经系统是第一个层次[22]。第二个层次是椎前神经节[23],脊髓和脑干中的ANS为第三个层次,为接收和产生信号的中转站,迷走神经的传入及传出纤维(VN)在此通过。第四级是大脑中枢[24]。微生物群-肠道-大脑轴之间存在双向交流,分为“自下而上”(从肠道微生物群到大脑)和“自上而下”(从大脑到肠道微生物群)。自下而上的交流主要通过神经内分泌和神经免疫系统进行,涉及神经内分泌细胞、上皮细胞、肠粘膜屏障和血脑屏障。自下而上沟通的关键因素是肠道菌群的代谢物,如短链脂肪酸等。神经内分泌调节系统包括其细胞分泌的各种激素或者是神经肽[25]。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是神经内分泌系统的一部分,可以对紧张性刺做出反应,可以激活这个系统;皮质醇的释放通过下丘脑分泌肾上腺皮质激素刺激垂体获得,也属于神经内分泌系统的一部分[26]。自上而下的交流主要通过神经解剖学途径、肠道屏障的调节和神经递质(如 5-羟色胺和儿茶酚胺)的释放进行[27]。自主神经系统(ANS)由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和 ENS分支组成,可调节身体功能,如心跳、呼吸、排尿和消化等。ANS活性可影响肠道神经元系统与微生物群相互作用[28]。
肠道微生物群的新兴作用增加了胃肠系统在帕金森病中的作用。PD患者的肠道微生物群发生了改变,徐美玲等[29]发现,A53T转基因小鼠肠道对比于野生型小鼠,拟杆菌门及红细菌目降低,拟杆菌减少,使肠道粘膜屏障破坏及通透性增加。在帕金森病患者中,小肠细菌过度生长(SIBO) 是非常普遍的,主要表现是吸收不良。帕金森病患者常发生胃肠动力障碍,这使得 SIBO发生率提高。与此同时,SIBO病一旦发展,它可能会增加肠道通透性,导致细菌转移,从而延长炎症反应[30-31]。已有研究表明帕金森病的进展与肠道炎症有关。帕金森病的病理可以从肠道扩散到大脑。最近有研究显示在大鼠模型中将外源性α-syn 注射入肠壁后,帕金森病理从胃肠道扩散到大脑且认为迷走神经是肠道和大脑之间的神经元连接,是帕金森病病理扩散的途径。最近有几项关于对不同批帕金森病患者的肠道微生物群含量的研究。第一项研究表明粪便细菌归属不同种群,且发现了促进健康的神经活性短链脂肪酸(SCFA)的主要生产者——更低丰度的普雷沃特拉,这与帕金森病患者体内这些维生素水平的降低是一致。普雷沃特拉或许能减少粘蛋白合成,粘蛋白合成减少与肠通透性增加有关,还可加强细菌抗原的转移[32-33]。该研究表明,SCFA值的降低可能会导致肠道渗漏。SCFA浓度在帕金森病患者中也有所降低,在 PD 粪便样本发现乙酸盐、丙酸盐和丁酸盐显著减少。SCFA 减少可能有助于调节肠上皮细胞的蠕动,缓解胃肠动力障碍。此外,SCFA丁酸盐还有抗炎作用,能减少肠屏障功能障碍发生[34-35]。已有研究表明[36-37]PD患者肠道中的菌群分别在门、纲、科三个水平上与正常人存在差异;在门水平上,PD患者放线菌群丰度增加,拟杆菌门显著降低;在纲水平上,芽孢杆菌和革兰阴性杆菌增加;在科水平上,伟荣球菌、链球菌以及双歧杆菌的丰度均上升,巴斯德杆菌则低于正常健康人群。这些均能引起α-突触蛋白的异常沉积,可能作为一种潜在的致病因素存在,最终引起PD的发病。
肠神经系统可引起帕金森患者便秘,可作为其主要靶点。已有研究证实,帕金森病患者死亡后,在肠系膜和黏膜下神经元内仍找到路易小体[38]。在特发性便秘结肠切除术患者中,有一部分出现耐药、严重慢传输的便秘患者,其肠下、黏膜下神经元均有改变。帕金森病患者便秘的症状与外周血细胞CD4+T细胞亚群有关,帕金森病的发病与系统性炎症有直接或间接的相关性,结肠黏膜免疫激活反应可引起结肠黏膜炎症,而帕金森病伴便秘可能引起激活反应从而引起结肠黏膜炎症[39]。肠道屏障破坏与α-突触核蛋白错误折叠和沉积具有一定相关性。糖探针分子检测技术广泛运用在医学研究领域,有研究证实PD患者的小肠及结肠的肠道通透性的确发生了改变,呈现高渗透性[40]。炎症反应的发生存在于多种神经系统疾病。研究发现,PD患者结肠中的促炎性因子上升[41],胃肠道长期慢性低水平的炎症反应与诺如病毒感染的患儿胃肠道内α-突触核蛋白表达量相关。
5 结语和展望
肠道菌群是胃肠道和大脑的双向沟通的枢纽,其在沟通过程中通过直接途径或间接途径与神经系统相互作用,其沟通方式较为复杂。现代医学通过增加或调节肠道菌群数量、改变肠道菌群菌属成分变化、重建肠道微环境,对治疗PD的非运动症状及运动症状均有一定作用。随着脑肠轴理论的提出,且肠道中短链脂肪酸作为肠道中优势菌群,可通过调节肠道菌群稳态减少α-突触核蛋白沉积,降低抗炎症因子的过度释放,从而改善帕金森患者非运动症状。目前对于肠道和帕金森的干预研究还在起步阶段,未来可能通过肠道菌群中菌属变化干预PD的发生及发展,为临床治疗帕金森提供新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