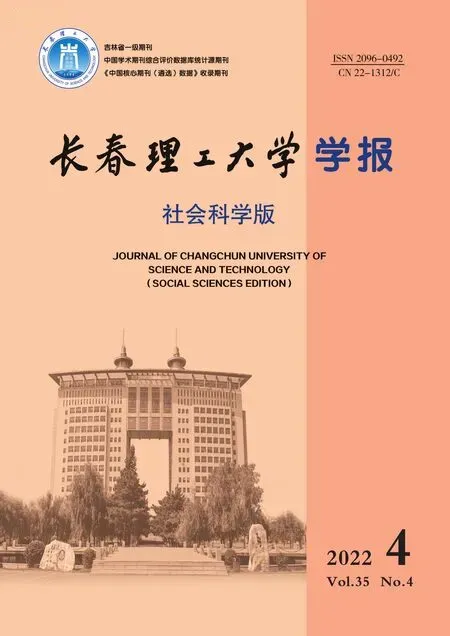女性主义视角下《漫长的沉默》中的战争书写
2022-11-19夏西遥
夏西遥
(重庆外语外事学院西方语学院,重庆,401120)
一、引言
西班牙当代女作家安赫莱斯·卡索的内战主题小说《漫长的沉默》曾获得2000年的费尔南多·拉纳小说奖。在这部以西班牙内战为背景的小说中,作者回避了历史的宏大叙事,讲述了一群支持共和派的普通女性在那场手足相残的浩劫中虽然屡遭不幸,但最终凭借坚韧乐观的精神相互扶持、共渡难关的故事。这部小说虽然面世已有二十余年,但因种种原因在学术界获得的关注不多,目前仅能找到哈维尔·桑切斯(Javier Sánchez)发表于2018年的《作为“记忆之地”的〈漫长的沉默〉》一文。该作者运用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提出的“记忆之地”的概念——即通过在国家历史中被静默的声音重构过去的个人记忆空间,分析了安赫莱斯·卡索如何在这部作品中通过维加母女等人在西班牙内战及弗朗哥独裁期间的遭遇,重现了一直以来被噤声和边缘化的共和派女性的那段艰苦岁月。
在第二共和国后期,西班牙国内时局混乱、左右翼冲突加剧,终于在1936年爆发了共和政府与弗朗哥右翼集团之间的内战。在最初阶段战况胶着,随着弗朗哥获得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政府的大量兵力和武器支援,而共和政府则由于英法等国的不干涉政策和后期苏联援助的撤回,难掩颓势,最终在1939年4月1日弗朗哥一方宣告获胜。这场持续三年的内战伤亡惨重,据统计,“死难者将近60万:30万军人阵亡,10万平民被处死,20万死于战争带来的疾病或轰炸”[1]。自此,西班牙也进入了一个前途未卜的历史阶段——弗朗哥开始了长达30多年的独裁统治。他反对自由民主体制,依靠长枪党、军队和教会来巩固政权;天主教再一次被奉为国教,也成为了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主宰。战后一大批支持共和制的知识分子被迫流亡国外,书写了大量内战题材的见证文学;而在西班牙国内,因弗朗哥统治下全国保守氛围浓厚,对文化和思想领域的审查制度森严,整个文坛噤若寒蝉,支持共和派的作家不得不集体沉默。
直到弗朗哥统治后期,随着西班牙逐渐开放边境和贸易,经济开始复苏,审查制度才随之松动,涌现出了一批反思内战的文学作品。但在此期间,受到关注的仍主要以男性作家的作品为主,如安赫尔·玛丽亚·德莱拉(Ángel María de Lera)的《最后的旗帜》(Las últimas banderas)、哈维尔·塞卡斯·梅纳(Javier Cercas Mena)的《萨拉米斯士兵》(Soldados de Salamina)等。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女性一直被认为不适合参与政治、战争等男性“专属”的领域,因此女作家书写的战争文学也难以获得关注和重视。然而事实上,从20世纪50年代的战后第一代女性作家开始,就一直不乏对内战历史进行反思和揭露的以女性视角书写的文学作品,如战后第一代女作家安娜·玛丽亚·马图特(Ana María Matute)在诸如《在这边土地上》《死去的孩子》等小说中,就以“内战和战后西班牙社会为解剖对象,从人道主义角度对那场无谓的手足相残以及由此造成的仇视提出含蓄的谴责,对现存的价值观念提出诘问”[2]。进入21世纪之后,更是有越来越多的女作家打破沉默,重写被遗忘的内战历史,尤其是其中被忽视的女性的历史。诗人、小说家杜尔塞·查孔(Dulce Chacón)的作品就主要反映了弗朗哥独裁的压迫和女性处境,如代表作《沉睡的声音》;阿尔穆德娜·葛兰黛丝(Almudena Grandes)近年来也把创作重心转向了有关西班牙内战和弗朗哥统治时期历史的发掘,代表作品有《冰冷的心》和系列小说《无尽的战争轶事》等。
在此背景下,一直关注女性故事、致力于发掘被遗忘的女性声音的安赫莱斯·卡索创作了这部以“漫长的沉默”为题的小说——意指无数像女主人公一样的共和派女性不仅遭受了战争的摧残,更是在战后弗朗哥政府的高压统治下,甚至直到西班牙实现民主化之后仍然不得不保持沉默,无法言说自己的伤痛。1975年,随着弗朗哥的去世,继任者胡安·卡洛斯开始在西班牙推行民主化改革,然而,改革政府为了实现不流血的民主化进程以争取各方支持,采取了倡导“和解”和“遗忘”的妥协政策,对弗朗哥统治期间的罪行态度暧昧。1977年,西班牙政府更是颁布了《赦免法》(Ley de Amnistía),赦免弗朗哥政府在内战和独裁期间犯下的一系列反人类罪行,以争取实现与弗朗哥支持者和解,从而为国内经济腾飞让路的目的。从西班牙民主化进程取得的成果来看,此举无疑是成功的,但与经济飞速发展一同而来的结果还有对内战历史感到无知和麻木的西班牙新一代。女性与战争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战败方的女性们在过往的岁月中又经历了哪些不为人知的苦难,这是笔者通过本文想反思和讨论的主题。
二、后现代女性主义的战争观
安赫莱斯·卡索颠覆了战争文学中通常聚焦于激烈战场、渲染战士们英勇战斗的传统,将视线投向了战争年代的普通女性。在《漫长的沉默》中,以维加母女为首,贯穿主要情节的人物几乎都是女性。她们在和平年代是平凡的妻子、母亲和女儿,这场无情的战争迫使她们一边要扛起家中因战缺席的丈夫和父亲的重担,承担比往日更多的责任和风险;另一方面,出于同样坚定的信仰,她们中的很多人也积极投身政治运动,直接或者间接地参与了反抗弗朗哥法西斯的斗争,因此也面临着残酷的政治迫害。这些女性虽然没有直接在战场上流血牺牲,但她们在后方为家庭和革命作出的巨大牺牲和贡献是不应被“隐形”和遗忘的。
在内战爆发初期,阿莱格里亚就参与了各种女性团体的地下革命活动,比如“在街上分发反法西斯的宣传单,照顾工人区的孩子们”[3]119等,以至于当弗朗哥的军队即将攻打到他们所在城市的时候,她知道因为自己曾经参与的那些行动,等待她的一定是牢狱之灾,因此除了逃跑别无选择;米盖尔的妻子玛格丽特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对政治有着自己的见解。她与米盖尔一见如故,他对于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的清晰理解让她十分欣喜:“虽然她从未想过如何表达这些想法,但米盖尔完全说出了她的心声,她甚至都不曾想过世界上竟会有人跟她的世界观如此一致”[3]145。在战争爆发后,米盖尔怀着满腔热血报名参军准备奔赴前线,面对即将独自抚养两个孩子的重任,玛格利特没有抱怨,也没有阻拦丈夫,反而鼓励他要英勇杀敌。离别的伤感之后她更是迅速打起精神,继续投身于各种共产党妇女组织的运动,抱着两个襁褓中的孩子参加各种游行集会。如果不是碍于做母亲的责任,她甚至想过自己参军上前线。玛丽亚·路易莎的朋友特蕾莎更是在战时和丈夫一起参军,共和派战败后他们双双被俘,结果丈夫被处决,而她自己虽然侥幸逃生,但因两年的牢狱生活也落下了病根,在生命的最后时光一直被病痛折磨。
这些女性无不在以她们自己的方式为信仰而战,早已颠覆了女性在战争中无所作为、只是从属于男性的“第二性”的传统观念。从战争史上来看,女性从古到今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据美国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家爱尔希坦(Elshtain)的研究,在战事频繁的古希腊,全民不分性别皆为战士,亚马逊族英勇女战士的传说更是家喻户晓;到了现代,二战中苏联军队中的女飞行员、反殖民战争中的女游击队员,以及如今美国军队中人数接近总兵力12%的女兵,都为己方军队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4]。女性不应该在战争中被“隐形”,也不应该把女性本质化地视为与战争绝缘的和平主义者,这是提升人们对性别和战争关系问题认识的关键。
一直以来,人们通常认为女性是爱好和平的,而男性则是暴力、有攻击性的,“战争是男子的事情,男子发动战争,战争也主要由男子参加,由男子争夺战利品”[5]。关于男女两性与战争的关系,女性主义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基于生物决定论,认为男性天生推崇暴力,而女性则爱好和平,因此倾向于赞赏女性的这种“优于”男性的“和平基因”;第二种观点同样也着眼于男性的暴力天性,但对于女性的和平天性则没有持赞赏的观点,认为一味强调这种在暴力问题上男女之间的性别差异会强化和掩饰男性利用暴力压迫女性、削弱女性力量的企图;同时她们也认为,为了避免沦为男性暴力的受害者,女性应该跟男性一样借助暴力手段维权,以暴制暴;而第三种观点,即笔者采用的后现代女性主义的观点,则认为战争的根源在于人类社会的等级制度,其发生是基于男女两性共同作用形成的父权制的军事体系,因此只有消除传统的性别刻板印象,消除本质主义的影响,建立起基于新的两性关系的世界秩序,和平才有可能实现[6]。实际上,战争还可以被视为劳动性别分工的一种特殊形式,基于生物决定论的劳动性别分工认为男性适于从事对外的公共活动,而女性则应该属于家庭的私人空间[7],因此战争应是专属于男性的“事业”。然而我们可以发现,书中并不是所有男性人物都是狂热的战争和暴力分子。玛格利特的第二任丈夫埃米利亚诺对政治和战争就完全不感兴趣,“战争对他来说不光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更是与他的生活毫无关系的。当政府要动员男性公民参战的时候,他就明白,不管是为了国王还是上帝,或者金钱,他都既不愿意夺去别人的生命,也不愿意自己丧命”[3]169。因此,为了不被卷入战争,他带着玛格丽特逃离了即将被弗朗哥军队占领的家乡,藏身马德里,并在那里度过了余生。同样不问时政的还有卡米娜的丈夫马诺洛,作为当时盛行的无政府主义的信奉者,他反对为国家和阶级服务的战争,只想环游世界浪迹天涯,实现年轻时的梦想。所以当西班牙笼罩在内战硝烟中的时候,他已经远在大西洋彼岸的古巴享受着阳光沙滩了。
学者恩洛埃(Enloe)就指出,男性并非天生的战士,是针对男女两性不同的社会化过程使男性从小就相信战争是勇敢和高尚的行为,并且认为用军事行动来解决不可调和的政治分歧是正确的;嘉奖在战场上牺牲的士兵、将幸存的战士视为荣誉公民也应是天经地义的。该作者把这种现象称为“军事化的男性气质”[8],以此与传统意义上的“男性气质”对应。在《圣杯与剑》中,理安·艾斯勒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他认为,虽然在数千年来的历史中,各个文明的男性都经历了无数的战争,剑已成为了男性的象征,但这并不意味着男性必然是残暴和好战的。在历史记载中就能找到很多男性爱好和平、反对暴力的证明,问题的根本在于我们的社会制度把暴力统治等同于真正的男子气概,而且把不符合这种社会理想的男性看成是“女人气”的,并通过教育使下一代也秉持了这种价值观[9]。这种本质主义的性别观不仅使女性沦为父权制的受害者,也使男性成为了军国主义的牺牲品,他们为了追求“男子气”,付出的往往是血肉的代价。
三、内战中共和派女性的多重苦难
有史以来有文字记载的战争中,男性士兵占绝对主力的前线总是获得了更多的关注和歌颂,而后方则常常被忽视。这也造成一种印象:相比于直接参与战争的男性士兵的伤亡来说,战争对后方女性的影响似乎不值一提。然而事实上,在近代之后,军队中女性军人的数量已经大幅增加,另外,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生化武器和其他现代战争武器开始被使用,平民的死伤人数大规模上升,在二战后已经逐步超过了战场上军人的伤亡人数,现代战争中的前线和后方已经很难截然区分[10]94。在《漫长的沉默》中,在内战和弗朗哥独裁统治期间,以维加母女为首的支持共和派的女性们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创伤。她们一方面遭受着当权的弗朗哥政府残酷的政治清洗和迫害,不仅自己身心饱受摧残,很多人也因此失去了丈夫和其他亲人;更雪上加霜的是,身处父权社会的她们同时还面临着来自拥有绝对权力的男性的剥削,处境苦不堪言。这些战败方的女性们所受的压迫不是单一的,而是相互交织、相互强化的,凭借她们自己微薄的力量几乎难以挣脱更难以抗衡。但即使身处这样的困境中,她们也没有放弃生活的尊严与希望,这种绝境中的坚韧更令人动容。
目睹家园被敌人的炮弹摧毁、亲人同胞在战火中丧命的经历给她们留下了无法治愈的创伤。如战争创伤理论家亨特所言,战争带来的创伤强度如此之大,以至于发生时人们往往会精神崩溃,而且会产生逃避、情感麻木等症状,使人的生理和精神状态发生极大的甚至永久性的变化[11]。向来坚强的玛利亚·路易莎在看到战后面目全非的家乡后也几近崩溃,她绝望地想到:“那个被叫做‘生活’的其实是个任性的造物主,他把众生的命运玩弄于股掌之间,就像她小时候玩洋娃娃一样”[3]22。战争开始之后,米盖尔在前线目睹了战争的残酷、无数战友的惨死后,一直以来的信仰开始动摇,也预感到了自己的死亡和己方的失败,并在不久之后都成为了现实;父亲普布里奥也因信仰崩塌从此一蹶不振,直到在精神错乱中病逝。因为他们的相继离开,整个维加家都笼罩在了阴云中,亲人的去世让她们真正明白“战争不是游戏,不是报纸上的新闻,不是咖啡馆里的热烈讨论。战争不是闹着玩儿的,那是死亡,是恐惧,是悲伤,是愤怒,是毁灭”[3]46。然而,米盖尔和普布里奥不过是这场浩劫的无数牺牲者之一,每家每户几乎都经历着生离死别。在街上,“人们谈论着集体处决,谈论着大规模的逮捕,谈论着出人意料的告发”[3]117,整个国家都笼罩在阴郁恐怖的气氛中。
由于父亲普布里奥和哥哥米盖尔在战前就是四邻皆知的坚定的共和派支持者,因此对于维加家的女性来说,她们在战后要面对的弗朗哥当局对异见方报复的腥风血雨并不比战争的炮火更温和——虽然内战本身结束于1939年,但是对于那些共和派的支持者来说,战争与厄运都远没有结束。在战后的弗朗哥独裁统治期间,天主教教会扮演了极为重要角色,甚至有为数不少的神职人员在政府中担任要职。弗朗哥之所以极力推崇天主教,一方面是想借此拉拢梵蒂冈的罗马教廷,争取国际社会对独裁政府合法性的承认;另一方面是想利用天主教的保守思想,建立一个基于传统家庭结构的政教合一的体制,从而更有利于维护政权和社会的稳定。这种浓厚的宗教保守氛围在书中随处可见,故事开头描写的卡斯特罗亚罗万人空巷、虔诚的民众迎接因战火被转移至外地的雨神像回归神龛的场景就极富戏剧性。战后弗朗哥政府对共和派的残余势力还进行了包括教育在内的各个领域的政治清洗。玛丽亚·路易莎和特蕾莎都因为她们的“红色”背景丢掉了原本学校的教师工作,让没有任何收入来源的家庭陷入了经济困境。数据显示,当时对教育系统的清洗是全国性的,凡是反对天主教教义和弗朗哥政权的,从教职员工到图书管理员无一幸免,甚至连相关书籍都全部被销毁。在战后的40年代,肃清政敌的行动甚至发展到凡是没有参加过弗朗哥长枪党在1936年7月18日发动的政变的民众,都会被视为可疑的反动分子而遭到叛国罪的控告和监禁。
统治者的高压政策固然可怕,来自同胞的告发和疏远对这些战败者精神上的伤害则更大。战后“疑者即有罪”的告发制度使民众人心惶惶,为了自保,邻居、朋友甚至亲人间的告发都十分常见。在战争刚爆发时,精明的房东佩特拉太太就一改往日对维加一家的热情态度,对他们冷眼相待,迅速与可能给自己带来麻烦的共和派人划清了界限,这也直接导致了普布里奥的精神崩溃。当她们在战争结束后重回卡斯特罗亚罗的家时,房东佩特拉更是直言她家不欢迎共和派人,她已经把房子租给了其他人,也没有保留她们的任何物品;菲达的男友西蒙一直是弗朗哥的追随者,在战争开始后就加入了他的军队效力,并因为表现出色,战后在弗朗哥政府的司法部开始了仕途,前途光明。虽然天真的菲达对他死心塌地,甚至在家人准备逃难时要为了他自己一个人留下,西蒙却因为担心影响自己的前程,无情地单方面结束了与菲达的关系;阿莱格里亚战前在一家药店工作,是一位尽职尽责的好员工,当战争结束后她想请前老板阿黛拉太太允许她继续在那里工作好维持生计时,怕受到牵连的老板借口阿莱格里亚没有弗朗哥政府颁发的“参与国民运动证明”而拒绝了她的请求。因为阿莱格里亚的共和派背景,老板是心知肚明她无论如何不可能得到这个证明的。胜利的一方不光赢得了战争,更是在战后对共和派赶尽杀绝,挤压了他们几乎所有的生存空间。走投无路的阿莱格里亚甚至觉得“从前获胜者把战败者全部变成俘虏的做法还更人道一点,至少不会让他们像现在这样被饿死。”[3]203
西班牙学者阿隆索(Alonso)曾指出:“内战中战败方的女性因为同时身为女性和共和派而遭受了双重压迫”[12]60。战争时期的女性比男性承受着更为复杂和特殊的创伤。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专家李英桃也提出:“无论是在国际冲突还是国内冲突中,妇女受到的伤害绝不亚于男人,平民承受的苦难也绝对不少于前方的战士。妇女与男子同是武装冲突的受害者,但是与男子相比,妇女的经历有很大的特殊性”[5]。如果说对于支持共和派的男性而言,弗朗哥政权的高压统治已是惨无人道,那对于共和派的女性来说,身在父权制社会,当权者普遍带有厌女思想的现状则让战胜者对战败者的压迫显得更无人性,“战争从心理上为男人发泄对女人的蔑视提供了绝佳理由”,“女人是边缘的,与世无关的,只能被动观看舞台中央男人们的表演”[13]27-28。
在第二共和国时期,顺应潮流的改革政府曾颁布了一系列对女性友好宽松的政策,如女性拥有了投票权,可以从事带薪工作和参与公共事务等,甚至女性也可以担任党内要职。但从内战之初起,这些女性来之不易的权力就开始丧失,直到战后的40年代对女性生存空间的挤压达到最顶峰。在天主教保守思想的指导下,女性的贞洁和生育义务又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堕胎被视为将受到严厉惩罚的罪行,更是连文学作品中对女性身体的描写都不被允许。各种保守派建立的女性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然而他们的目的不是争取女性的权益,而是维护传统的社会秩序、宣扬女性的生育职能,教育女性成为服从丈夫的妻子和传播天主教教义和弗朗哥思想的教育者母亲。在书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圣母玛利亚的雕像在弗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随处可见,弗朗哥政府想以此规训妇女成为如同玛丽亚一样的为家庭奉献一切的圣女,女性再一次被完全禁锢在家庭中。
在内战时期,女性一方面丧失了经过不懈斗争才争取到的权力和地位,另一方面,她们照料老人和孩子的“天然”义务即使在战争时期也不能免除,再加上家中的丈夫和儿子大多因为参战处于缺席状态,作为妻子和母亲的女性们家庭责任更加繁重。由于需要照料家庭成员,同时整个国家民生凋敝、经济萧条,女性想从事带薪工作几乎不可能,这造成在战时由女性充当“临时家长”的家庭很可能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在战争结束之后,因为父亲和儿子的过世,积蓄渐尽的维加母女举步维艰,甚至连返乡的路费都要靠好心的神父接济。作为被清洗和排挤的对象,几个姐妹经过无数努力仍然无法找到工作,走投无路之下,玛丽亚·路易莎甚至只能和好友特蕾莎冒着极大的风险乘火车翻山越岭倒卖食物,以勉强维持一家老小的生计。更有甚者,原本战时由于交通中断、生产停滞等原因造成的物资短缺几乎就是普遍的情况,再加上内战中西班牙主要的粮食产区几乎都落入了弗朗哥一派手中,共和政府残留的区域都遭遇了严重的粮食短缺。而此时女性还承担着采买家中食物、药品等责任,为了购买生活必需品,她们常常需要步行很远的路程才能找到仍有商品出售的商店,并且要经过长时间的排队等待,这让她们更多地暴露在了轰炸和遭遇骚乱的风险中[14]。
另一个战争时期难以绕过的沉重话题就是战败方女性遭受的性剥削。玛利亚·路易莎的丈夫费尔南多被俘后被关押在一个偏远地区的监狱,按规定不允许家属探视。出于对丈夫的思念,玛利亚·路易莎长途跋涉前往监狱探视,不出意外遭到了拒绝。为了能够见丈夫一面并把他转移到家乡的监狱,面对好色的监狱长,无奈之下的玛丽亚·路易莎不得不屈辱接受他提出的交易条件。在这种战败方和战胜方之间权力完全不对等的关系中,处于绝对弱势的女性除了屈从别无选择。有史以来,在战争中针对妇女的暴力就一直以不同的形式和程度发生着,从谋杀、强奸、严刑拷打、强制怀孕、监禁、强制卖淫,到口头侮辱、谩骂等等[15]。根据相关统计,在内战期间有数千共和派妇女被处决,而在行刑之前强奸女囚的做法则非常普遍[12]58。战争的胜利赋予了这些原本平凡的战胜方男性以巨大的力量,对于他们来说,蹂躏战败方妇女的身体作为一种征服行为,具有与占领敌方土地类似的象征意义。从古希腊时起,战时的强奸就是常见且被社会认可的行为,女人是战胜者可以随意享用的合法战利品,在战争中,“妇女只能是可怜的受害者,只能是附带的、无法避免的牺牲品”[13]27。
四、结语
无数的西班牙共和派女性经历了各种苦难却无法言说,她们因为内战的失败而被独裁者判处了长达几十年的漫长沉默。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2000年西班牙民间成立非政府组织“历史记忆恢复协会”,以及2007年西班牙国会通过《历史记忆法》(Ley de la Memoria Histórica),西班牙也迈入了重新反省和定义历史记忆的新阶段。恢复这一段历史和记忆不是为了复仇,而是一种现实的需要和责任,今天的西班牙人只有在这段用被遗忘的声音和血肉之躯铸就的记忆中,才能最终寻回他们的身份。
在当今的国际关系研究中,在探讨如何才能实现和平、避免冲突和战争时,应有更多女性主义视角的注入:一方面是要让战争中的女性不再“隐形”,找回那些一直以来被遗忘的、在战争中经受着多重苦难和创伤的女性的声音;另一方面要认识到战争爆发的根源与父权制传统是密不可分的,“军国主义是父权制的产物,军国主义反过来又强化了父权制社会中妇女的不利地位。只有改变父权制的社会结构,铲除军国主义,才有可能消弭战争、制止暴力,实现真正的和平”[1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