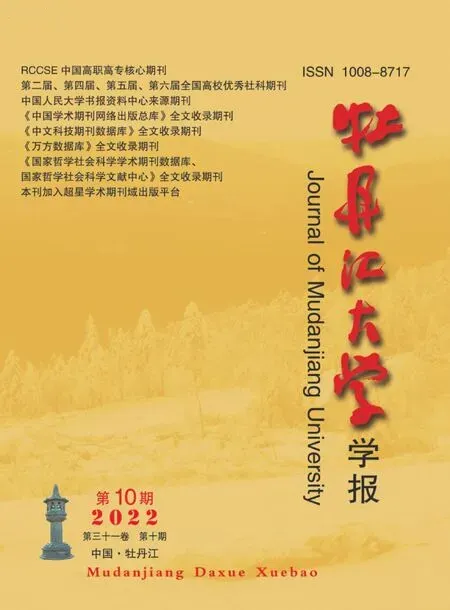矛盾的田园共同体
——论狄兰·托马斯《梦中的乡村》中的和谐与冲突
2022-11-18文箐一帆刘明录
文箐一帆 刘明录
(广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1)
引言
提到二十世纪的英国诗人,狄兰·托马斯必然是其中不可忽略的一颗明星。20岁的他,以一首《死亡与出场》(Death and Entrance, 1946)树立了自己的名声,而后在诗作中延续他对生、死、欲三大主题的终身思考。他没有投身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的时代创作激流中,反而回归浪漫主义传统,但又在字里行间点缀些许前卫的超现实主义写作技巧。出身在威尔士的托马斯,故土的田园风光和狂野的风格精神始终是他灵感的腹地。正如海岸在《狄兰·托马斯诗选》的译序中评述,“托马斯的诗歌感性而坚实,绝少流于概念或抽象;他的诗歌很少涉及精神分裂、自我怀疑等现代诗常见的主题,他的诗纯粹朴实,自成一体,赋有强烈的节奏和密集的意象”。[1]1
然而,国内外对于《梦中的乡村》一诗的研究仅仅是一笔带过,仅有一篇《狄兰·托马斯之<梦中的乡村>:他矛盾的感知》(DylanThomas’s“InCountrySleep”:HisParadoxicalSensibility)专门研究诗中的情感。[2]12《梦中的乡村》作为托马斯后期的作品,剥离了早期晦涩难懂,既轻快明朗又富于凝练深刻的内涵,可谓是他为数不多的田园牧歌中的集大成之作。放眼英美诗坛各式各样的田园诗歌,《梦中的乡村》也是独特的。它的独特不仅在于托马斯构建的田园共同体中带有危险、暴力、不安的因子,不似一般的田园共同体一派和谐静谧;而且在于它杂糅了童话、宗教和其他文学文本的内容,形成了一种特别的叙事模式,丰富又颠覆了传统乡村田园诗的主题和内涵。
基于此,本文力图在揭示《梦中的乡村》中和谐与不安特征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作者构建此田园共同体时使用的独特语言和创作技巧,并最终通过挖掘托马斯的人生经验以阐明矛盾的田园共同体存在的原因和价值。
一、田园共同体中的和谐之音和冲突因子
“田园共同体”这一概念从属于费尔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提出的“共同体”这一核心概念。 “共同体”(Community)一词源于拉丁文communis,原义为“共同的”(common),即“共同体是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社会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的和表面的共同生活。因此,共同体本身应该被理解为一种生机勃勃的有机体,而社会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机械的聚合和人工制品。”[3]45田园共同体,顾名思义,指的是包括田野、田地、乡村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在内的所有在田园范围内具有高度内在一致的共同存在。据滕尼斯所言,“生机勃勃的有机体”是共同体最本质的特征,[4]71这也就意味着共同体是一个流动的、辩证的、开放的、包罗万象的持久共存的集合体。无独有偶,田园共同体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增添新的内容,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呈现不同的形态。
《梦中的乡村》(InCountrySleep)从第一人称“我”的视角出发,以我的目光记录了乡村中的一切景观和事物,并穿插着“我”对心爱姑娘的呢喃劝告。纵观全诗,整个乡村中的事物均紧密粘合在一起,同时互相促进,生生不息,符合田园共同体基本的定义和特征。由于托马斯的重心落在乡村中的一草一木和奇崛的想象上,使这个田园共同体和传统的、脆弱的、人为的乡村共同体割裂开来。同时,不同于以往田园诗的宁静和谐书写,托马斯笔下的田园静谧而危险、恬淡又野蛮。诗中的意象也被分为愉悦积极和紧张消极两类,并进一步影响了田园共同体的特征和内涵。
诗中用于营造和谐氛围的积极意象主要有鲜花、翠绿的森林、清悦回响的月光等典型的象征着自然安逸静谧特点的事物,由此创造了一个宁静祥和的欣赏空间。托马斯在诗中直言:“乡村多么神圣;哦,住在自然亲切的乡村里。感奋绿野的美好……”[1]215,传达的是对乡村正面的评价和带给人们的美好印象。所谓和谐,即和睦协调,和谐是文学的基本审美形态之一。[5]67之所以称《梦中的乡村》是和谐的,不仅是因为乡村中的一草一木相互依存、欣欣向荣共生,更重要的是因为乡村给予人“美好、神圣、亲切”等主观的感受和联想。同时这样和谐的氛围也与共同体的特征遥相呼应,即真正的共同体内部一定是和谐的、流动的、粘合的,托马斯笔下的乡村是为经典。
相应的是,诗中暴力的、野蛮的、甚至稍显血腥的意象同样引人注目。有吞食心肝的狼、寒鸦栖息的山崖、跪在血泊里的狐狸等暗黑骇人的意象,又给诗歌笼罩上一层可怖的阴影,显示出和宁静田园完全相反的阴森气质。托马斯运用这些“哥特式的崇高”意象,除了带给读者与传统田园诗不一样的审美体验之外,也流露出涌动在共同体潜在涌动的不安、疯狂与矛盾。
这样的矛盾显然是诗人的精心安排,托马斯曾自述:“我的诗需要一系列意象,因为诗的中心就是系列意象的组合。我创造一个意象,尽管创造这个词不确切;也许使一个意象在我的激情中生成,而后赋予其我所具有的才智和批判力量让它生发出另一个意象,让它与第一个意象相冲突, 让第三个意象生成于前两个意象中,再产生第四个相冲突的意象。让这所有的意象在我定下的范围内冲突抗衡,每一个意象都带有自我毁灭的种子。我理解的辩证法就是把出自中心位置的意象不断摧毁而重建”[6]281。这样的理念直接影响了托马斯对意象的选择及意象之后的毁灭的颠覆。托马斯擅长堆叠陌生化的意象来扩大诗歌的美学张力,因为在阅读时,这样的意象不会跳转到通常的、传统的本体、喻体,而是挣脱常规的藩篱,引发读者新奇的、陌生的联想。
这样一来,看似悖论的各种意象进一步构成了矛盾而新颖的田园共同体,且托马斯在诗歌的形式结构上也煞费苦心。《梦中的乡村》行文十分规律,通常是在几个和谐意象的描写后紧接着几个不和谐意象的描写,显得张弛有度,互相衬托,使和谐面和不安面都得到了凸显和加强。例如:
……最阴森的幽灵猫头鹰
发出不详的哀鸣。狐狸和林地跪在血泊里。
此刻童话赞美
星星在草场上空生起,寓言整夜地放牧
在绿草摇曳的圣桌。永远不必害怕[1]215
上述节选先言乡村的不安因素,以阴森、幽灵、不详等词汇修饰;后立刻一转笔锋,将神圣的餐桌、星空和令人安心的绿色呈现眼前,通过这种对比使共同体中的和谐之音和不安因子都得到了最大化的彰显。正如肖建云所说:“运用这种(对比)手法,有利于充分显示事物的矛盾,突出被表现事物的本质特征,加强文章的艺术效果和感染力。”[7]55托马斯如此布局,符合他一贯的以“后一个意象打破、颠覆前一个意象”的创作风格,也为揭露全诗的主题和传达自身对矛盾的田园共同体的理解和情感作了铺垫。
二、矛盾共同体的建构:《梦中的乡村》的叙事线
托马斯曾自述:“每一首诗都必须有一根结构的走向线,主题。一首诗越主观,其叙事线就越清晰。”[8]157这一宗旨促使《梦中的乡村》也有明确的叙事线而不流于抽象的概念。因此,托马斯笔下的田园共同体的呈现并不只是两面性意象的堆砌,更多的是有相应的叙事内容赋予它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意蕴。在这一点上,托马斯的叙事线由神秘的宗教故事、浪漫童话以及警世寓言构成,并辅以奇喻的修辞手法来使田园共同体具象而跃然纸上。
(一)神秘的宗教故事
本诗中的宗教意象主要有牧师、女修道院、圣母玛利亚、天使、圣桌等。据《圣经》可知,象征着高贵纯洁的圣母玛利亚在马厩里奉上帝之意诞下人类的救赎者——耶稣。但在传播福音和和平,拯救世人于水火后,耶稣却还是迎来了最后的晚餐。《新约圣经》“福音书”记载,耶稣在最后晚餐时,拿起饼和葡萄酒祝祷后分给门徒说:“这是我的身体和血,是为众人免罪而舍弃和流出的。”[8]602圣桌上见证的是耶稣为世人蒙受苦难和罪恶痛割骨血的仪式,其神圣和伟大不言而喻。当耶稣已然不在,人们的信仰和祈祷却还能在牧师的努力下在修道院中得到庇护。托马斯按照耶稣降临——举行圣餐仪式——修道院祷告的时间顺序,层层递进,将这些宗教原型映射到当时社会和人民的信仰危机四伏的情况,而托马斯独求能在修道院和牧师的指引下寻得一方心灵净土,以此来虔诚地祷告并宣发与上帝灵肉合一的希望。
(二)浪漫的童话元素
所谓童话,是指介于古老的“口头民间传说”和文学之间的故事形态,篇幅不长,童话元素通常指涉文本中超自然的、带有魔法、奇幻和浪漫的元素。[9]9《梦中的乡村》中童话元素屡见不鲜,较典型的如下:
裹着羊毛头巾咩叫的大灰狼,也不必害怕
长着獠牙的王子,在春情荡漾的农庄陷入
爱情的泥潭,但是要警惕那露水般温顺的贼。[1]215
美好青涩的爱情、突然闯入的盗贼、甜美绚烂的梦境都是童话故事里常有的情节;披着羊皮的狼、亦正亦邪的王子、佯装虚伪的贼、法力高强的女巫也是童话中经典的形象。与其他文体不同,童话元素很好地调和了严肃的气氛,使诗歌更易读。值得注意的是,托马斯诗中的童话情节和童话人物并不是善恶两边、泾渭分明的:王子也可以长出獠牙;大灰狼的咩叫也不必害怕;爱情固然甜蜜,却仍有盗贼会偷走女孩纯洁的心灵和童贞。托马斯故意打破这种二元对立,将田园中的不确定性和矛盾双方的互相转化性展示出来给读者看,旨在颠覆传统的田园共同体形象,进一步丰富了田园共同体的内涵。
(三)哲理性警示寓言
最后我们不难发现,《梦中的乡村》在行文下隐藏着一则警世寓言,即警告天真烂漫的女孩要小心表面温顺的贼,那个贼可能“偷走她的信仰,又在阳光苏醒之际将她抛弃”。[1]218寓言作为一种由来已久的文学形式,可追溯到公元前6世纪的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学派对《荷马史诗》进行了阐述,他们认为诗歌内容显现了真理,言外之意正是寓言的核心。这一言说却被柏拉图所否定,注重模仿性的柏拉图认为,“寓言跟反映现实本质的思维方式相反,也就是说,它反映的不是,或者说基本上对立于感觉和理性所确认的论据。”[10]6综合两人的看法,寓言用一些事例来表达抽象观点,以此满足哲学论证的要求,但它的表现形式却充满了诗意。显然,《梦中的乡村》用充满诗性的语言讲述了一个作者说教性的观点。托马斯表面上只言女孩美梦之欢愉,最多也只隐晦说到让女孩小心黑心的豺狼、长着獠牙的王子,并未光明正大地说出贼人的身份。但从“让她独自赤裸着身,悲哀他的离去”[1]218这一简短的线索不难发现,托马斯阐述的是外在因素对童真、纯洁、信仰的灾难性的影响,借此警告世人要独善其身,坚守信念。
(四)匠心独具的奇喻
据现有研究表明,托马斯的诗风和内容深受玄学派诗人的影响,如章燕在文中指出“托马斯诗歌中的生死观有可能受到前人, 特别是玄学派诗人约翰·多恩的影响。”[11]64《梦中的乡村》作为托马斯有代表性的诗歌,其中运用奇喻的技巧可谓是炉火纯青,如咆哮的锁孔、干草般金黄的马厩、飞旋的尘土犹如星星自天空陨落、兔子般跳跃的狂风、红色的狐狸在火一般的公鸡间燃烧等。所谓奇喻,其落脚点在“奇”字上,力求带给读者以惊诧、新奇之体验。托马斯此处多次的奇喻可谓是反向的彼特拉克式奇喻。我们都知道,彼特拉克式奇喻重在夸张,比如将眼泪比作洪水,将叹息喻为风暴,这些都是彼特拉克式奇喻。[12]75可托马斯跳出藩篱,另辟蹊径地将本身较大的事物以比它小得多的事物作比;或是将能起到统领总结的概念性事物具体到常见的动植物上去。托马斯故意采用抑制的手法,将大自然中强劲的狂风、星星、火焰等比作乡间随处可见的公鸡、干草、锁眼、尘土等,合乎情境又富有哲理。
综上所述,为了构建这个充满矛盾的田园共同体,托马斯借助多种文学样式,杂糅古今著名的文本内容,并加入独特的警世寓言,让这个共同体独树一帜。
三、托马斯的人生体验及矛盾的田园共同体之价值
可以说,这也是诗中共同体存在的必要性的体现。至于主题的呈现与矛盾的田园共同体内涵是密不可分的,知晓了田园共同体创作背后的来龙去脉,其对现实生活的意义和价值也就不言而喻了。
狄兰·托马斯出生于1914年,去世于1953年,一度年轻的托马斯不屑与奥登等人的写实主义诗歌为伍,坚持创作充斥丰盈想象、梦幻狂想、故土眷恋的“象牙塔”式诗歌。但两次世界大战的严酷现实——战争对生命的漠视、对人性的摧残强烈地撞击着他的心灵,使他再也无法逃避或掩饰。于是,托马斯不自觉地将对于战争、人性、生命、死亡、危机的思索隐匿在他一向拿手的看似无理性或逻辑的诗行当中。托马斯并未背离他一贯追求的艺术风格,那种隐喻式的语言表达和拼贴、跳跃的密集意象以及赋有音乐旋律的节奏很好地承托了现实对象和政治社会理念,并内化成更深层次的诗人感悟。
正如很多评论家指出的那样,托马斯的诗歌使人强烈地感受到生与死之间的矛盾和共存,[13]18《梦中的乡村》也与这个特点一脉相承——在任何表面平静的环境下,和谐和冲突也在激烈地碰撞和并存着。但值得注意的是,《梦中的乡村》中虽有无数不安的、消极的因子,但托马斯却从未对其进行负面的、否定的评价,他仅仅是呈现这些因子给读者们知晓与感受。不仅如此,托马斯还在诗歌结尾处发出重要论断:
我的宝贝,今夜他正走来,自从你降临人世,
夜晚永不止息:
你会从梦中的乡村醒来,在黎明以及最初的每个
黎明,
你的信仰永生不灭,犹如受控的太阳爆发的呐喊。[1]219
这里的夜晚代指的是世间一切不利的、黑暗的、危险的元素,他们的到来具有不可抗力,这亦是自然规律的体现。但很快托马斯笔锋一转,写到黑夜后迎来每一个宝贵的黎明。托马斯此言是在告诫人们,黎明终将冲破黑夜,要始终坚信黎明带来的希望。并且针对战争下信仰缺失的主流话题,托马斯也振聋发聩:信仰不会流失毁灭,并且它的力量和光芒堪比初生的太阳,只要坚定信仰,连客观的太阳亦能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所控制,成为人类内心希望的发言人。
在散文《论诗》中托马斯强调:“一首好诗是对现实的贡献。一首好诗问世,世界就再也不一样了。一首好诗有助于改变宇宙的形状和意义,有助于扩展对自己和周围世界的认识……”[14]157托马斯后期的诗,均以现实为主要驱动力,他诗歌的题材来自于现实生活,如《拒绝哀悼死于伦敦大火中的孩子》和《黎明空袭中有位百岁老人丧生》;诗歌的落脚点也回归现实,旨在改造一个更美好的现实,以诗歌为现实增添力量和色彩。托马斯本人的人生态度也一直影响着他诗歌的面貌:托马斯一向笑对生活,他曾受邀在BBC(英国广播电视台)作演讲和广播,传递自己对人生乐观的态度和积极向上的看法。在托马斯众多关于生与死、短暂与永恒、欲望与希望的诗歌中,《梦中的乡村》则提供了另一幅图景。生活中,有犹如清澈湖面、和煦微风、摇曳花朵、蜜糖心灵一样的世外桃源存在,就有残忍的偷盗者、黑心肠的贼人、危险的狼群如影随形。这个矛盾的田园共同体之价值所在在于号召人们只能依靠十年如一日的坚定信念和信仰,将希望的光耀洒向世间大地,在这样的悖论和迷离中坚守自我、升华自我。
结语
托马斯的诗歌《梦中的乡村》以细腻精致的想象力,描绘了一个和谐与冲突并存的田园共同体。在诗中,托马斯一方面借神秘的宗教故事和浪漫的童话刻画出乡村中宁静、甜美、和谐的氛围;另一方面以奇喻、警世寓言的手法告诫世人警惕不安、野蛮、暴力的因子。表面上看来,这个矛盾的田园共同体不过是寄托托马斯个人幻想的一纸妄言,实则是托马斯对于战争年代人们信仰缺失、无所适从问题的回应。托马斯以小见大,以贴切的意象和凝练的诗句将世间美好犹存,危机四伏的矛盾状态写了出来。最后又现身说法,提出坚持信仰的重要性,力图将人们从颓废、悲伤的浪潮中解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