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规范到快感:政治哲学与精神分析的双重考察
2022-11-17吴冠军
吴冠军
(华东师范大学 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上海 200241)
一、 规范性的向度:“因为我这样说!”
从发端时刻迄今的政治哲学,可分为两个完全对立的派系:“规范政治哲学”(normative political philosophy)和“激进政治哲学”(radical political philosophy)。前者致力于阐述与论证各种规介(regulate)人之群处的普遍规范,典范如约翰·罗尔斯对于“正义”原则以及“万民法”的发掘与论证。后者则恰恰挑战规范——不管是既有的、实然的抑或超越的、应然的——的普遍性与正当性。规范政治哲学预设共同体秩序的稳定性建立在规范的普遍性与正当性上,而激进政治哲学则恰恰旨在推翻这个预设。两个派系针锋相对,结构性地构成了政治哲学的撕裂。为了深层次地探究政治哲学的这个内在撕裂状况,我们有必要聚焦于“规范”(norm)这个看似中性的概念,探究其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首先,任何规范(律令、法条、守则,甚至不成文的习俗成规等),实质上结构性地是一种禁令(prohibition)、一种压制(repression)。规范与压制,实是同一个机制的两种表述。譬如:“文明用语”这一规范,意味着不能说脏话;“生命权”,意味着不能杀人;婚姻,意味着不能“出轨”……各种规范/禁令,皆以不容挑战与违反的强势方式规定了什么可做与什么不可做。那么,决定可做与不可做的规范/禁令,其自身的根据是什么呢?一件事变成了“规矩”,它总得有点依据吧。
对于规范本身之“正当性”问题,古典政治哲学(形而上学)给出的答案是“自然”(“自然法”“自然秩序”)抑或“天道”,政治神学给出的答案是“上帝”(“神法”)抑或“天志”。精神分析给出的答案则是“大他者”(the Other)。而“自然”“上帝”“天”,实则都是大他者的不同具身(embodiments)。由西格蒙·弗洛伊德所开创、雅克·拉康所重构的精神分析,是后形而上学-后神学的,因为扎根在语言系统的“大他者”并没有本体论根据,故此,它没有绝对意义上的权威——大他者构成了规范的根据,然而却“不存在大他者本身的大他者”(There is no Other of the Other)。在不同版本的形而上学中,“自然”“天道”都是真实存在于那里的;在不同版本的神学中,“上帝”抑或其他“神”亦是真实存在着的。而对于精神分析而言,这些都是大他者的具身,都是符号性的构造物。故此,它们并没有绝对的权威,而只具有符号性的权威。(1)参见吴冠军:《有人说过“大他者”吗?——论精神分析化的政治哲学》,《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第75-84页;吴冠军:《大他者到身份政治:本质主义的本体起源与政治逻辑》,《文化艺术研究》,2022年第3期,第1-1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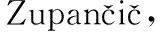
实际上,当把这些古典概念视作为内嵌矛盾的概念时,我们并不用急着把它们移除,然后再在它们留下的空位上重新填上新的“一”,譬如“理性”。政治哲学上那著名的“古今之争”,究其根本,实则就是现代哲学家用“理性”来取代古代的“自然”“天”抑或“上帝”。也正因此,规范政治哲学与激进政治哲学的对立要比古典政治哲学与现代政治哲学的对立更为根本:古今两种政治哲学,都在规范政治哲学的范畴中,仅仅是“规范”的根据有所不同;而以精神分析为核心思想资源的激进政治哲学,则恰恰激进地拒斥各种整体性的“一”(不管是“上帝”抑或“理性”),将它们皆视作那位冒称“绝对”(the Absolute)的大他者的不同具身。(3)参见吴冠军:《“大他者”的喉中之刺——精神分析视野下的欧洲激进政治哲学》,《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6年第6期,第20-3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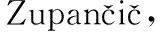
拉康提出,大他者的权威(符号性权威),原初就来自“父亲”这个位置。作为大他者在家庭结构中的具身,“父亲”很值得分析,因为他不像后来的那些具身(如“天道”“上帝”“理性”),个个都用一套庞大的话语包来强势包装,使之凛然不可侵犯。“原父”(primal father)出身简陋,没甚话语包装,于是他的权威之根据就老老实实地暴露在外: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只能这样做而不能那样做?没有根据,“就因为我这样说(Because I said so)!”对于哇哇啼哭和牙牙学语的婴孩来说,即便儒家的父亲也没法跟他/她讲“王道三纲”,基督教的父亲也没法跟他/她讲“十诫”。给婴孩施以规范/禁令的,就是“父亲”的在场。原父的功能,就是施加原始压制(primal repression)。
于是,颁布律令的“父亲”,便是支撑共同体——一个符号性秩序——的原初根据。用政治哲学的用语来说,“父亲”所提供的正是规范性的向度——使孩子“正常化”(normalized),亦即,使他们社会化。“父亲”使孩子成为“人”,成为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政治的动物”。于是,“父亲”就构成了家庭(共同体)中一个独特的结构性位置——看不见的大他者,通过“父亲”这个具身而维系住家庭这个共同体的秩序。
孩子因“父亲”而产生“阉割”焦虑,怕爸爸会对其下狠手,所以他们对父亲充满憎恨,恨不得“弑父”而独占妈妈,这就是“俄狄浦斯情结”。弗洛伊德笔下“阉割”这个词为很多评论者所不喜,但孩子怕父亲的惩罚,这份害怕是确确实实的。出于这份害怕,孩子只能恨恨地看着妈妈和爸爸亲密,而不能整个地使自己占有妈妈。弗洛伊德用“阉割”焦虑、“俄狄浦斯情结”等概念想要表述出的,就是这份恨意与恐惧。(5)故而,我们实际上可以把“阉割”视为一个隐喻。而弗洛伊德之所以饱受诟病,就在于当他说男孩怕被父亲“阉割”时,他是从字面意义上而非隐喻意义上使用“阉割”一词。参见Anthony Storr, Freud: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35。对于父亲那霸道的“就因为我这样说”的权威,孩子因害怕惩罚而只能表面遵从,背地里则总是想办法逾越父亲的禁令。在原父之后的“上帝”“天”这些大他者具身,除了各有一整套话语包让你听话地服从其规范外,都保留乃至升级了让你害怕的能力,而不只是“父亲”手里的藤鞭与“老师”手里的教鞭。再后来推翻“上帝”“天”而兴起的“理性”,似乎只是跟你讲道理(听从你自己“理性”的声音),但大他者的这个现代具身有个“分身”专门承担让你害怕的工作,把这个鞭策就是教化的文明传统延续了下去。
在转而讨论理性的这个隐秘“分身”之前,此处值得提到的是,“父亲”在政治哲学上的这种关键性,实际上是由拉康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做出的一个关键改造所奠定的。在弗洛伊德这里,“俄狄浦斯情结”是指孩子总是无意识地欲求其对立性别的家长,并视相同性别的家长为对手。故此,同男孩“弑父”倾向相反,女孩欲求其父亲而憎恶其母亲。这也导致了,只有男孩会感受到“阉割”威胁。(6)在弗洛伊德的论述里,女孩首先会和母亲产生感情,但当她发现自己没有男根并因此低人一等时便会将这个缺陷归咎于母亲,从而将爱转而投向父亲,开始幻想他能使她受孕,受孕后所生的孩子会填补女孩对男根的“缺”。这个繁复的解释,有效地弱化了弗洛伊德笔下“俄狄浦斯情结”的解释力。但在拉康这里,孩子(不论男女)总是欲求母亲,而父亲则总是其对手。这样一来,“俄狄浦斯情结”才实质性地成了“弑父情结”,而“父亲”也成了一个独特的结构性位置。在对孩子“做规矩”时,生活中的母亲可以暂时性地站在“父亲”这个位置上。但“父亲”不会再像弗洛伊德笔下那样,因孩子性别不同而随时同“母亲”发生对调。“父亲”(可以是现实中的爷爷、外婆或妈妈),成为一个家庭结构中的一个特定位置——大他者的位置。
二、 自律的暗黑面:康德主义理性与萨德主义皮鞭
在人类学中,“乱伦禁忌”被视作人类“文明”开启的标识——动物世界里“乱伦”随处可见。在精神分析中,“父亲”所颁布的规范便正是以乱伦禁忌为典范性禁令(“不得乱伦”)。“父亲”的压制性在场,使得孩子日后能够成长为人类共同体中的一个“正常”成员。这就导致了人类文明的一个普遍现象:作为共同体成员的人类个体,总是倾向于服从大他者(从“天道”“上帝”到“国王”“总统”“领导”“老师”,再到“理性”……)的权威,但这个服从也不会像康德在论述“绝对律令”时所设想的那样能达到百分百,而是总会偷偷搞些越界性的小动作,譬如说,说谎,又譬如说,出轨。也就是说,文明人对于文明社会施加在他们头上的规范、律令,总是总体服从而有时偷偷越界。
作为现代哲学的扛鼎者、开启哲学之“哥白尼式革命”的康德,坚信人类个体能够依据其理性天赋(faculty of reason)而严格践行绝对律令(譬如“不能说谎”)。这,无疑是对人类个体“理性天赋”的误判。但康德的独特贡献就在于,他将大他者律令中的一部分经由“实践理性”的普遍性测试程序而转化为“自律”(autonomy),即“依照一个能够像一项普遍法律那样有效的法律去行动”(7)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沈叔平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29页。。在康德看来,如果你服从的规范都是外部施加过来的,那么你其实就是生活在“自我施加的不成熟性”(self-incurred immaturity)(8)③ Immanuel Kant, “An Answer to the Question: ‘What is Enlightenment?’” Hans S. Reiss ed., Kant: Political Writing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54; p.55.中:你其实已经成年了,可以用理性来进行思考了,为什么还要让牧师来告诉你该怎么做事呢?这意味着,你虽然成年了,但没有启蒙。启蒙意味着,你不再倚靠“父亲”“导师”“牧师”“精神分析师”“领导”“总统”告诉你该怎么行动,这都是“他律”(heteronomy),你得靠自己的“理性”来行动,服从自己给自己设定的法律。比如你想出轨,但你用实践理性一思考就知道这件事做不得:倘若你的伴侣也出轨,你受得了吗?康德说,道德不是来自外部的律令,而是理性施加给自身的律令。学会听从理性的声音,这个时候,你就成熟了。
我们看到,在康德这里,现代政治哲学完成了对古典政治哲学的取代:“理性”成为一切律令最后的根据——人类用“自由抉择的最初尝试”取代了“上帝的声音”。(9)康德:《人类历史起源臆测》,何兆武译,《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63页,第61页。换言之,各种大他者具身的律令都是他律,只有实践理性的律令才是自律。这实际上就意味着,现在,“理性”把“自然”“上帝”“天道”以及“父亲”等全部掀翻了,自己坐到了它们的位置——大他者的位置上。这就是康德所说的“启蒙”。尽管“理性”可以说是一个最不像大他者的大他者具身(从“外部”转移到了你的“内部”),但同样是以绝对(“绝对律令”)面貌出现,甚至更为严苛。
康德本人既强调自由,又强调服从权威(譬如,对普鲁士腓德烈二世“你喜欢怎么争辩和争辩什么都可以,但是要服从”的说法盛加推崇(10)① Immanuel Kant, “An Answer to the Question: ‘What is Enlightenment?’” Hans S. Reiss ed., Kant: Political Writing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54; p.55.),因为自由和服从律令在他这里变成了一回事——“理性”的自我立法。(11)参见吴冠军:《康德论服从与权利——与何怀宏商榷》,《二十一世纪》,2002年8月号,第118-123页。成为康德主义主体后,你会发现,此前“父亲”以及“牧师”“导师”给你设定的绝大多数规范你都还是要遵守的,一个也不能少,并且还要更一丝不苟地严格实践,因为现在违反它们就不再是跟你那专制的“父亲”对着干,而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了。
在现代状况下,人的“理性”取代了“自然”“上帝”“天道”等前现代的外部“伪绝对权威”,成了规范背后的绝对根据。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人类主义(humanism,旧译“人文主义”抑或“人本主义”)得以盛行。然而,有意思的是,几乎所有的现代社会,都没有把“法律与秩序”这件事交到人的“理性”手上,并未任由理性主体自行判断其行动是否符合绝对律令,而是交由专门的执法机构来监督。在现代社会中,大他者仍然在外部有一个具身——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将其称为“压制性国家装置”(repressive state apparatus),包括军队、警察、监狱等等。拉康曾经提出“康德伴随着萨德”(Kant avec Sade)这个命题,意指康德主义理性主体背后结构性地跟着一个手拿鞭子的萨德主义督行者/施虐者。“理性”的内部声音很温和,只是让你有勇气去自己做出思考(行动是否能普遍化),但大他者在外部的“分身”则专门行使让你害怕与遵从律令的工作。在人类主义地平线上,站在前台的是大他者的康德式具身,而身侧还站着一个萨德式具身。启蒙(理性),有一个暗黑分身(皮鞭/警棍)。
对于启蒙的暗黑分身,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案例分析来揭示它的隐秘操作。在美国广播公司(ABC)出品的经典美剧《成长的烦恼》(GrowingPains)第二季第10集中,进入青春期的长子迈克偷着出去和死党狂欢,午夜爬窗回家时被父母杰森和麦琪发现。他谎称,路上遇到火灾,因救火而导致晚回家。不幸,谎言被识破,迈克被关了禁闭——整个周末不许有任何娱乐活动(包括看电视),八点必须上床睡觉。在这个自由主义家庭中,父亲杰森(一位精神分析师、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权威不是来自“因为我这样说”,其权威实际上是督行者的权威:作为十几岁的人应该懂事了,懂得自律(把外部的律令转化为理性设定给自己的律令),然而迈克不但偷跑出去还当面说谎,于是遭到惩罚。启蒙要达到效果,总是结构性地需要其暗黑分身出面进行管教。
随后,受到惩罚的迈克,正好撞见母亲麦琪为了要和杰森周末同去大西洋城而向报社领导推说家里有急事。“不能说谎”这条律令被逾越,逾越者恰恰是督行者。作为“一家之主”(督行者的督行者)的杰森,显然是一个康德主义者。为了教导迈克接受“对任何人来说,说谎都是错的”(亦即,康德主义绝对律令)而非他所认为的“只有那些造成灾难性后果的说谎才是错的”(亦即,效益主义-后果主义律令,康德笔下的假言律令),杰森要求妻子麦琪也接受同样惩罚——周末在家关禁闭,由女儿卡萝尔代替麦琪去大西洋城。
麦琪的母亲得知连环禁闭一事之后的第一反应是惊问麦琪:“你在孩子们的面前说谎?”这句话恰好暴露出了康德主义绝对律令在日常生活世界中的实际情况:“不能说谎”这条律令实际上总是被偷偷地逾越,只要不被大他者(督行者)抓住就行。在周末的禁闭过程中,麦琪——仍扮演着督行者的角色——要求迈克不能有任何娱乐活动,并且必须在八点上床睡觉,与此同时自己却准备好零食打算通宵看电视。麦琪母亲(作为已不具实际权力的前督行者)提醒麦琪:她自己也正在接受处罚中,同样不应有任何娱乐活动。结果那晚半夜偷溜出去的迈克,被半夜看电视的麦琪抓现行。迈克被抓到后再次说谎,称自己在梦游。而正当麦琪训斥迈克竟用说谎来逃避本来就因说谎而受到的惩罚时,迈克发现作为督行者/违法者的麦琪也在逃避处罚。迈克反问母亲:难道惩罚不对作为督行者的她自己生效?并且,他认为,母亲每次在抓到他做“错事”时,本身正体验着某种隐秘的快乐(亦即,萨德主义的施虐快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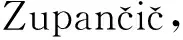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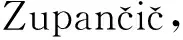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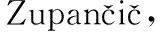
三、 启蒙/致暗:实践理性、计算理性与快感
康德的哲学体系里完全没有快感的位置——康德把没有按纯粹实践理性行动的人与现象直接打包在了一起,交由“病理性”(pathological)一词来统摄。在理性的国度里,快感很难找到位置。那位躲在康德阴影里的萨德则很懂得快感。现代性的社会运行表面上交给了康德主义者,然而实际上很大程度上交给了萨德主义者。在现代文明中,“理性道德人”很体面,但“理性经济人”的势力却大得多,(18)此处“理性道德人”与“理性经济人”对应于罗尔斯所说的两种“理性”(reason/rationality)。罗尔斯对两种理性的区分,请参见John 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 expanded edi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48-54。更不要说文明还有各种暗层,里面有大量比“理性经济人”更懂得快感门道的高手。更让情况变得复杂的是,上述三种“理想型”(19)“理想型”这个概念借自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根据韦伯本人的界定,“一个理想型通过对一个或多个视点的单面聚焦,以及对大量弥散的、离散的、或多或少在场但有时缺席的具体的个体现象的统合而形成,这些现象按照那些单面强调的视点被安排成为一个统一化的分析性建构”。参见Max Weber, The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1903—1917), Edward A. Shils and Henry A. Finch ed. & trans., Free Press, 1997, p. 90。人物,在日常生活世界可以完全是同一个人:在微信朋友圈里很体面,在职场经营中很算计,下班后与回家前则有一些暗地里的喜好……
像“不能说谎”这样的由“纯粹实践理性”所得出的律令,在日常生活中总是会被逾越——对此,对“理性”信心满满的康德并不认可,他认为这只是一些人没有勇气运用自己理性的结果。然而,对律令的逾越,则以似有若无的方式产生出康德毫不关注的某种隐秘快感。同样地,抓住逾越者并施以羞辱与惩罚,也会似有若无地产生出某种隐秘快感——一种萨德主义施虐者很熟悉的快感。快感,既不同于“理性”(道德实践理性),也不同于康德笔下的“病理性”(经济计算理性)。(20)关于经济计算理性的讨论,请进一步参见吴冠军:《爱的算法化与计算理性的限度——从婚姻经济学到平台资本主义》,《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2年第10期,第54-67页;吴冠军:《爱的革命与算法革命——从平台资本主义到后人类主义》,《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第11-23页。功利心强的“凤凰男”和会过日子的“经济适用男”,他们与偷偷在外面养小三的“渣男”(更不要说暗地里玩BDSM(21)BDSM即绑缚与调教(bondage & discipline)、支配与臣服(dominance & submission)、施虐与受虐(sadism & masochism)的合称。的“变态男”)有着很大不同(22)尽管日常生活中这些“理想型”可以在同一个人身上发生重合。,后者所做之事,是包括霍布斯、洛克、斯密、康德在内的规范政治哲学家们皆彻底忽视的——这样的行动既无法通过普遍性检测程序,也并不符合过日子的经济计算。会付出包括死亡与社会性死亡在内的惨烈代价的出轨(亦即,越出规范性的“轨道”),古往今来都有那么多人前赴后继地乐此不疲,这绝不是“病理性”一词能够打包解释的现象。
在解释这类弥漫于社会暗层、总是以偷偷摸摸的形态发生的现象时,“快感”是比“病理性”或“计算理性”恰当得多的概念。“启蒙”(enlightenment)本意就是引光,康德呼唤现代人要有勇气让理性之光照进来(代替上帝之光)。然而,理性之光恰恰有许多照不到的暗层,在那里,快感而非理性(不管是道德实践理性还是经济计算理性)才是行动的核心驱力。现代性并非只有“启蒙”,还有“致暗”(endarkenment)——“要有勇气公开运用你的理性”这句启蒙号召,实际上总是有一个结构性的致暗补充,即“要暗地里私下追逐你的快感”。(23)笔者从大卫·基希克这借来“endarkenment”一词,但本文中的用法是笔者自己的。参见David Kishik, The Power of Life: Agamben and the Coming Politic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17-44。
“快感”乍看上去很日常,大家都很熟悉,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很诡异的事物——许多快感若要深究起来,你会发现它们并不直接产生于诸种生物性-生理性需求的满足,而是往往和各种幻想场景相关。换言之,就其肇因而言,这些快感是纯精神性的。这也导致了,其很难用测量与量化的方法论进路来进行研究。如果你用解剖学的方式研究一位隐秘的萨德主义施虐者,成果恐怕会很有限。而我们可以在精神分析与人类学研究的基础之上,为非生物性的快感提供一个解释性与分析性的视角。
首先,我们要处理一个至为根本性的问题:是否真的存在非生物性-器质性的快感?即便生活中有许多人会用“极乐”(ecstasy)以及“巨爽”(jouissance)这些词来形容说不清楚、无法量化的巨大快感,但如果解剖学或其他生理学、心理学手段检查不出相关的生物性机制或者生物化学进程,我们就总是心里没底——快感似有,又若无。在探究这个问题时,施虐者是比受虐者更好的案例。对于各类BDSM实践里的受虐者,笔者很支持采用生理学和解剖学进路去研究的建议:我们可以先猜想是某个(些)隐秘的生物性元素或因子导致了某些具体的人类个体把痛感体验成了快感,然后通过实证性研究来验证或证伪该猜想。当然,这项研究实际进行起来难度会非常高,因为痛感与快感都无法进行有效量化。(24)不仅是快感无法量化,痛感其实亦无法有效量化,但不少心理学家会强行弄出一个数值来(比如1~10),更有心理学家把爱也弄出一个量化数值来。受虐者往往还会把耻辱(25)此处关于“耻辱”一词的严谨表述是:同一社会与文化背景中的大多数人,在相同情境下会产生出被羞辱的感受。体验为愉悦,这更进一步增加了研究难度——耻辱比肉身痛感更无法量化。(26)当然,某些心理学家会用粗暴的量化方式弄出一个数值来,也正是此类操作使心理学在科学共同体里面地位不高,距离“硬科学”很远,几乎快接近社会科学里那些偏人文的学科了。
然而,对于施虐者,解剖学、生理学、心理学这组研究进路便彻底陷入困境。归根结底,施虐者至多只是在生物性层面上消耗了一些体力(整体能量消耗亦十分有限,可以通过穿戴设备来得到量化的值),以及口头做出了一些羞辱性的表述(羞辱性的具体程度无法有效量化,口头说话有一些微小的能量消耗)。那么,是什么生物性机制导致施虐者体验到满满的快感呢?这些生物性层面变化的数值与快感程度存在相关性(且不说因果性)的关系吗?如果施虐者在BDSM的密室里不断跑动并挥舞鞭子,同时口中喃喃不停,是否会带来反复验证皆成立的快感的飙升?施虐者的快感,无法在生物性-器质性的层面上定位到。但这种快感显然是存在着的,驱使着施虐者乐此不疲地投入其中,并且冒着被曝光后社会性死亡的风险。人类主义价值系统禁止施虐-受虐这种活动(哪怕双方都是自愿的),各种BDSM实践皆只能隐秘地存在于社会的阴暗面(地下室、密室、私人会所……),暗地里进行,像极了偷情——很多人实际上把它们归为一类,丈夫偷偷跑出去找相好的制服女来鞭挞自己,就是出轨了。
在娱乐时间电视网(Showtime)出品的美剧《亿万》(Billions)中,男主角是一位受人尊重的检察官,然而却好受虐这一口,总是让心理诊疗师的太太在家做施虐者,妻子也答应了。然而,检察官还经常偷着跑去私人会所找更专业的人士来对他施虐,这就成了他和妻子婚姻中的许多致命性矛盾之一,最后导致两个人分居。而检察官这个私人喜好被对手挖出来曝光后,更是差一点直接“社死”……在当代社会,搞BDSM这一套,被曝光后其代价即便赶不上出轨,但也很接近了,并且在很多人眼里,这两者本来就是同一性质的事情。所以,我们就面对这个问题:是什么样的快感使那些人就像出轨者一样乐此不疲地往里冲?当然,我们也可以用“变态”“心灵扭曲”“不正常”等词来直接结束研究,并宣布非生物性的快感并不存在:这些人之所以虚幻地感到某种“快感”,是因为他们太变态了,不是正常人。
如果你觉得施虐者的例子口味太重,那么就让我们再举另一个更为日常的例子来论述非生物性的快感。在上一节讨论过的《成长的烦恼》场景中,半夜里麦琪带着麦克违反杰森(父亲/丈夫)规定的禁闭惩罚而偷跑出去吃比萨,口感上得到的满足并不会比平时多(吃的是同一种比萨),但吃起来就是感觉比平时爽。这份奇怪的多出来的“爽”,就是纯精神性的快感,它在生物性层面上难以被定位到。该快感,纯然是通过对规范的“出轨”而诡异地产生出的。拉康形象地生造了一个术语“多余快感”(surplus enjoyment,亦译为“剩余快感”)来形容这种多出来的“爽”——“surplus”就是“超”(sur)+“多出来”(plus)。拉康提出该概念的灵感便来自马克思的著名术语“多余价值”(surplus value,汉译普遍译作“剩余价值”)。当代激进政治哲学(代表人物包括斯拉沃热·齐泽克、阿兰·巴迪欧、恩内斯托·拉克劳等)的核心思想资源,就正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拉康主义精神分析。在齐泽克看来,“作为一个政治元素”的多余快感,实是所有规范政治哲学皆无法直面的暗黑创口。(27)Slavoj Žižek, For They Know Not What They Do: Enjoyment as a Political Factor, Verso, 1991.
拉康本人是在造词意义上做了一个形式上的借鉴,齐泽克等学者亦是在概念之形式意义上将拉康与马克思关联在一起。然而,于此处我们可以在学理层面做出进一步推进,使“多余价值”与“多余快感”发生实质性关联。马克思告诉我们:工人的劳动所创造出的多出来的价值,被资本家尽数掠夺走了。我们可以接着提出,这里面其实就涉及了多出来的快感。尽管价值(在马克思所使用的意义上)可以进行量化计算,而快感则无法以量化方式体现出来,但恰恰是后者,使得企业家真正意识到自己是资本家。对于当代世界中的绝大多数企业家而言,一大群雇员为自己打工这件事本身并不会直接给他们带来快感。在企业家眼里,自己在变化无常的市场里打拼,就和打工人一样——区别在于企业家带着企业打拼,而打工人带着自己肉身在打拼;但他们都接受着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调配,有成功者就有失败者,企业家做得不好也会成为打工人,而后者也可以凭自己本事变成企业家……这样的企业家,往往会为自己每月要支付一大笔钱养活这么多打工人而焦虑,而不是感到爽。
之所以快感没有滋生,那是因为企业家们没有从“多余价值”视角来看问题,而是认定自己付工资给打工人,是自己养活了对方。如果他们知道自己偷偷地霸占了工人应得的那一份,那么这就会像偷偷跑出去吃到了比萨那样,快感油然而生。换言之,当企业家认为这就该是我的,他就是在按经济理性来思维。当企业家发现这不该是我的却被我暗中霸占了时,他便遭遇快感——拿到“多余价值”,就会给他带来“多余快感”。正是在这个时候,企业家就会感受到属于资本家的淫秽的爽(obscene enjoyment)。(28)本文采用“多余价值”“多余快感”而非“剩余价值”“剩余快感”这组译法,正是因为后者未能凸显出“多出来”这一层意思。关于资本主义秩序与多余价值的进一步分析,参见吴冠军:《从人类世到元宇宙——当代资本主义演化逻辑及其行星效应》,《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2年第5期,第14-25页。张乐平在《三毛流浪记》里如果只画大肚皮的资本家吃大餐,这不会产生淫秽的感觉(资本家其实顿顿都是大餐),但画资本家对着门口目光与大餐连成线的饥饿三毛大快朵颐,就能让我们透过纸面感受到那个资本家的淫秽的爽。就他可以吃,别人只能看,他吃到肚里的都是别人的痛苦。很相似地,萨德主义施虐者的爽,就是当他看着别人痛苦时快感在纯精神层面的暗暗飙升。
对于阿尔都塞所说的警察、监狱等“压制性国家机器”,可以用社会科学的方法论进路进行研究,理性能够解析出各自运作的方式与逻辑。但这个系统里冒出来的那些致暗性的现象,如激发“黑命攸关”(Black Lives Matter)运动的那些警察,却总是无法被社会科学的解释框架(如种族主义等)所穷尽,那是因为,作为启蒙之暗黑分身的皮鞭/警棍/枪,恰恰同一种似有若无、理性无从辨识的快感相关联。直面现象的政治学研究,因此有必要将快感纳入分析视野,并追踪快感的生成学。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代激进政治哲学会以精神分析作为核心思想资源的根本性缘由。那么,我们如何来追踪那理性不予处理抑或无力处理的快感?
四、 可以没有爱,但不能没有快感
上一节对施虐者的讨论,业已让我们看到:成人的快感(enjoyment)和小孩子所感受到的快乐(pleasure),实则完全是两种东西。小孩子能很快乐地玩到一起去的游戏(譬如扮家家)里,是不会产生出BDSM这种形式的,只有文明社会里的成人才会想出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寻求“极乐”般的巨大快感。于是,很诡异的是,快感的产生同快乐的丧失有着关联。
精神分析开创者弗洛伊德对快感的研究做出了基础贡献。在《论爱的场域中普遍的贬值倾向》一文中,弗洛伊德提出,孩子社会化的代价就是“快乐的丧失”(loss of pleasure)。(29)弗洛伊德认为婴孩在某个阶段能够体验到“完整的快乐”。Sigmund Freud, “On the Universal Tendency to Debasement in the Sphere of Love”, James Strachey ed. & trans.,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Vol. 11, Hogarth, 1957, pp. 189-90.面对“父亲”的压制性在场,孩子不得不放弃“快乐原则”(pleasure principle),转而遵循“现实原则”(reality principle)——认清“现实”,接受“快乐”的丧失,才能成长为一个“正常”的人。一个人倘若没有“父亲”压制而纯然遵循快乐原则,是不可能实现群体的合作与发展的。个人社会化与人类文明化,就是追逐本能快乐的“本我”(id)被压制并转变为遵守现实原则的“自我”(ego)的过程。在《文明及其不满》中,弗洛伊德写道:
文明,通过削弱与消解个体危险的侵犯欲望,并通过在他内部建立一个机构来进行监察,从而取得对该欲望的控制。(30)Sigmund Freud, “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James Strachey ed. & trans.,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Vol. 21, Hogarth, 1961, pp. 123-124.
通过有效消解并长期控制住自身的“本能”(侵犯性的性冲动、破坏性本能),人变得“文明”。正是受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启发,法国思想家乔治·巴塔耶将如下论断贯彻到他的所有文学与哲学作品中:“人并不等同于那关于快乐的器官。”(31)Georges Bataille, Death and Sensuality: A Study of Eroticism and the Taboo, Mary Dalwood trans., Walker and Company, 1962, p. 269.也就是说,“人”追求的快感,从来不是简单地来自快乐的器官,而是必须经过原始压制这道“文明化”程序后转化出来。
德裔美籍哲学家赫伯特·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一书中,将弗洛伊德的这一洞见称为“文明的辩证法”:“文明以对人诸种本能的永久镇压为基础。”“文明”的进步,就是对人本能——尤其是爱欲(eros)——之压制的不断提升。反抗压制,就是反抗“文明”。于是,马尔库塞提出其著名论断:文明的进步,并不是自由的进步——在工业文明中,“密集化了的进步同密集化了的非自由紧密相连”。(32)Herbert Marcuse, Eros and Civilization: A Philosophical Inquiry into Freud, Beacon, 1966, pp. 3-4.
当代精神分析学家布鲁斯·芬克进一步提出,以往弗洛伊德研究者多把丧失的“快乐”界定在性(“爱欲”抑或弗氏自创的“力比多”)的层面上,实则,爱(love)往往成为这个“正常化”(社会化/文明化)进程的牺牲品:
弗洛伊德式父亲的阉割威胁,可能被一些男孩理解为爱与性是非此即彼的,而不是仅仅要求他们将其对母亲的爱转移到其他像她那样的女性之上。这也就多少意味着,往往不是父亲(或父亲替代者)所直接使用的那些字与词在发生作用,而是这些字词如何被儿子阐释。父亲的意图可能是传达给他儿子:他必须去寻找一个他自己的女人。而儿子可能把它理解为禁止所有对女人的爱,甚至是禁止所有的爱,就此打住。(33)Bruce Fink, Lacan on Love: An Exploration of Lacan’s Seminar Ⅷ, Transference, Polity, 2015, pp. 21-22.
芬克提出这样一个见解:孩子会对父亲的禁令做出自己的阐释,尤其是,害怕遭到父亲惩罚的孩子会对其禁令层层加码。当对母亲的爱被禁止后,孩子会对这份禁令自行加码,最后演变成这样的情况:爱整个地被禁止。这样一来,“父亲”的阉割威胁实际上并没有彻底“阉”掉性——性仍可以背着“父亲”而获得,而爱则整个地被牺牲掉了。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人类文明中,爱在话语层面与实践层面具有着“结构性不诚”现象:“爱的革命”在话语表层高歌猛进,甚至被视作共同体秩序的最后基石(34)巴黎七大哲学教授、法国前教育部长吕克·费希认为爱是“意义的一个新的原则”,并宣称“好生活问题的答案,就在于爱的激情当中”,而不在于抽象的“国家、革命,甚至进步(那些外在于和超越于人性的理念)”中。参见Luc Ferry, On Love: A Philosophy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ndrew Brown trans., Polity, 2013, p. 35ff, p.47;吕克·费希、克劳德·卡佩里耶:《最美的哲学史》,胡扬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第62页,第386-387页,以及第398页以后。;而现实生活中则恰恰是一地鸡毛,各种对爱的背叛、出轨不绝如缕。爱,恰恰有如神迹/奇迹,只听闻,但无处觅。人类“文明”对爱的普遍贬值乃至彻底缺失,提供出了实际的替代品。它就是:快感。如果对数千年的文明史做一个细致的考察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人类的存在性状况是,他们可以没有爱,但不能没有快感。
快感和快乐,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后者存在于“父亲”的原始压制之前,而前者则产生于压制之后,由大他者所隐秘提供。换言之,快感,并不是通过生物性满足而获得的直接快乐:它绝非简单地来自“快乐的器官”。反过来,恰恰是诸种本能性的快乐丧失后,快感才得以产生。快感并不源于生物性满足,而是凭空“多”出来的,但它能够介入性地影响器官性-生物性的进程,比如让你心跳加速、肾上腺素(epinephrine)与去甲肾上腺素(norepinephrine)急剧飙升。施虐者与受虐者能够帮助我们定位到快感的生成。施虐与受虐尽管行动的方向相反,但在人类主义价值系统里都被禁止——哪怕双方都是自愿的。于是在现代社会中,这种活动只能以淫秽越界的方式隐秘地存在于“文明”的暗面。这套“禁令(规范)+越界(出轨)”的文明机制,让受虐者把身体的痛感与精神层面的耻辱转化为“爽”,让施虐者凭“空”多出来“爽”,并产生出生理上的诸种反应,感受到“极乐”般的快感。
如果说施虐/受虐只是为社会上少数的边缘人所实践的活动,那么让我们再从现代文明的阴暗面(萨德)转到其奠基石(洛克)。对于洛克列出的三大权利之一的“产权”(property right),笔者要提出如下这个颠覆性论题:“产权”被设定为普遍的权利(否则就成特权),然而在日常实践中其普遍性恰恰是缺失的。产权在形式上诚然适用于所有人,平等地保护所有人的财产。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
在现代社会中,产权的问题并不在于法律层面的非普遍性(传统社会经常有这个问题),而在于快感层面的非普遍性。产权能够有效地给有钱人(而非所有人)制造快感——我有名牌包而你没有,我在大快朵颐而你只能看着我吃,快感就出来了。产权内嵌着禁令:这是我的,你不能碰。东西还是同样的东西,倘若我有你有人人都有,拥有时就不会感受到这份快感。“经济适用男”不会给女友买名牌包,因为性价比太差了,对他来说,家门口大卖场卖的包设计前卫、容量更大——这是计算理性的思维。但计算理性抵达不了快感——要了解女友看到“大卖场时尚包”为什么心情不爽,你需要的不是“启蒙”,而是“致暗”。同样地,一样的食物,一样的烹饪工序,如果人人都能吃到,好吃程度就会直线下降。于是乎,对于很多人来说,鱼子酱根本不腥,鹅肝也绝不肥腻,而是极其好吃,甚至为世间最美味。于是乎,很多奶茶店会让你排队三小时才能买到一杯奶茶,虽然价格上工薪族还算都买得起,但我喝到了而你只能在旁边看,这好喝程度便噌噌地往上涨。很多人还要拍照片发朋友圈,让更多人围观,每个点赞都加深了好喝值。人的快感与口感的关系真不大。于是,纯精神性的快感并不只是“施虐/受虐快感”,还包括其他看上去很日常的快感,你会错以为它们是由舌尖或性器官所提供的,抑或是来自内心中的真爱(不管是真爱的人还是真爱的包)。
在人类“文明”中,快乐须遭到实质性的打压,否则人类无法进入文明状态——人不能活得像动物,为即时性的器官快乐而活。对于放弃“快乐原则”而接受“现实原则”的人类个体,快感就是他们所孜孜以求的“文明性”的体验。一个只有压制而没有快感的共同体,很快就会崩塌——一个典范性的例子就是二世而亡的秦朝。出轨所获得的致暗性的快感,恰恰不是生物性的,而是文明性的——它来自对婚姻规范的暗地里的淫秽逾越。同样地,在根本意义上,一个政治秩序的稳定性,恰恰不是建立在规范的普遍性上,而是建立在对它进行隐秘越轨而获得的快感上。这,便根本性地构成了规范政治哲学与激进政治哲学的路向性对立。规范政治哲学致力于为普遍规范寻找到某种绝对基石(实则是大他者的某个具身),从而达成共同体的长久稳定性。激进政治哲学则恰恰提出:规范没有绝对的权威(只有符号性的权威),在实践中其“普遍性”总是被越界;而经由越界所产生的快感,才是共同体不至于很快崩塌的那块隐秘“基石”。
经由前文的分析,我们现在能够看到:激进政治哲学的激进性瞄准的正是规范政治哲学的规范性。对规范的服从结构性地倚赖压制——从“原父”到“压制性国家机器”。快感的填入则实质性地使得“规范+对它的隐秘逾越”这个结构得以长久维系。从康德到罗尔斯的规范政治哲学家将快感这个致暗性的“政治元素”排除在研究视域之外。同政治哲学的这个主流派系相对,从马克思到齐泽克的激进政治哲学家,实际上皆致力于揭示出这份隐秘的快感,从而使得规范(譬如“产权”)露出赤裸裸的压制性内核。由于激进政治哲学直接瓦解规范政治哲学的理论大厦之地基,故此两者之间并无法形成某种调和,甚至有效的对话都难以形成。
于是,我们不得不长期面对着政治哲学内部那无从化解的撕裂性图景。作为政治哲学的主流派系,康德以降的历代规范政治哲学家始终牢牢高擎“启蒙”大旗,将“理性”(从实践理性到公共理性、沟通理性……)视作规范之“后形而上学”地基。而在另一边,当代激进政治哲学家们则紧紧瞄准“理性”所彻底看不见的启蒙之暗黑分身(“致暗”),借助拉康主义精神分析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开启的双重分析视角,细致地追踪“多余快感”的生成及其政治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