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掘古墓葬罪既遂未遂问题论析
2022-11-17靳平川
□靳平川
(山西警察学院,山西 太原 030401)
我国刑法“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涉及两类对象,一是作为古代社会生产、生活遗存的古文化遗址,一是古墓葬。由于该罪是选择性罪名,因此盗掘这两类对象,分别构成盗掘古文化遗址罪和盗掘古墓葬罪,这两个罪名可以合并使用,也可以分别使用。本文主要研究盗掘古墓葬罪,并且集中讨论盗掘古墓葬罪的既遂和未遂问题。盗掘古墓葬罪作为“盗掘——盗窃——倒卖——走私”文物犯罪链条上的源头性犯罪,数量最多,危害最大,是打击重点,也是研究的重点,而该罪既遂未遂问题更是重中之重。
一、问题由来
(一)解放后我国大陆盗掘古墓葬罪立法综述
我国大陆解放以后相当一段时间,有关盗掘古墓葬问题只有一部分政府政策规定,延续到改革开放初期颁行的首部刑法典,也无相关罪名规定,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内地启动相关刑事立法探索,渐次经历了以盗窃罪名加以论处、在刑事单行法规中增设专门罪名、在刑法典修订中引入相关罪名三个阶段,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在相关立法总体保持相对稳定的同时,努力推进着立法细节的周延和完美。
从新中国建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大陆地区没有刑法典,仅有的单行刑法中也没有盗掘古墓葬问题的线索,但有关问题在中央政府的政策文件中有所体现。如1953年政务院发布《关于在基本建设工程中保护历史及革命文物的指示》,要求对那些对“古墓葬及古文化遗址等采取粗暴态度,任意加以拆毁、破坏,致使遭受不可挽回的损失者,应由各级文化主管部门提请监察部门予以适当的处分。其情节重大者,依法移送人民法院判处”。1956年,国务院在《关于在农业生产建设中保护文物的通知》中,也有类似规定和要求。
改革开放初期,百端待举,1979年颁行的刑法典中,仍然没能寻觅到盗掘古墓葬罪的踪迹。进入八十年代,盗掘古墓歪风沉寂三十年后,在内地部分地区死灰复燃,并在短时间内席卷全国,江西余干、丰城、河南淮阳、青海民和、浙江龙泉、福建浦城、山西襄汾、湖南邵阳、四川屏山、内蒙赤峰等地,都先后发生了比较严重的群体性盗墓事件。事异备变,理论研究和立法活动随之紧锣密鼓展开。1982年颁行的第一部文物保护法即以附属刑法形式规定了应当接受刑事处罚的八种文物犯罪行为,其中就包括了“私自挖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犯罪活动。适应严峻文物安全形势需要,1987年“两高”作出《关于办理盗窃、盗掘、非法经营和走私文物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司法解释形式规定:私自挖掘古墓葬、古文化遗址的,以盗窃罪论处;相关罪刑确定,不以古墓葬、古文化遗址是否已经确定为文保单位为限,不以是否窃取到文物为限。1991年全国人大常委作出《关于惩治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犯罪的补充规定》,正式单独增设“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不再以盗窃罪罪名处理,并且规定了情节特别严重的4种情形,其最高刑可至死刑。1997年系统修订刑法典,保留了上述单行法中盗掘古墓葬罪罪名,基本维持该罪规定,仅部分调整了法定刑。至此,我国刑事法律中关于盗掘古墓葬罪的立法体系基本成型。
进入新世纪后,主要以修正案和司法解释形式对盗掘古墓葬罪的有关刑法规定进行了细化、美化。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取消了该罪死刑配置。2015年12月“两高”颁布《关于办理妨害文物管理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确认构成盗掘古墓葬罪既遂,需要满足“实施盗掘行为”和“已损害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两个条件。
(二)盗掘古墓葬罪既遂未遂的理论和实务界观点回顾
在基层一线此前长期的办案实践中,盗掘古墓葬罪基本上不存在既遂和未遂的争论,即认为是行为犯,只要实施盗掘行为,通常就构成犯罪既遂。在文物法学理论界,关于盗掘古墓葬罪既遂未遂问题的争议持续时间较长,大致可分为“盗得文物说”、“损坏结果说”和“盗掘行为说”三种观点。其一,“盗得文物说”,认为盗墓者的目的是获取古墓中的文物,只有从古墓葬中盗取到文物才构成犯罪既遂,只有挖掘行为而没有盗得文物是犯罪未遂。这一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我国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按盗窃罪处理盗掘古墓葬行为做法的影响,因为盗窃罪构成既遂的重要标准就是窃得财物。其二,“损坏结果说”,认为构成盗掘古墓葬罪既遂,须有对古墓葬造成损坏的结果,如果只有挖掘行为,没有造成实质损坏,属于未遂。其三,“盗掘行为说”,认为盗掘古墓葬是行为犯,只要盗墓者实施了非法挖掘行为,即构成既遂,而不需要对古墓葬造成损坏,更不需要窃得墓葬文物。[1-2]有学者还提出“分别说”作为第四种观点。所谓“分别说”,即对盗掘古文化遗址罪和盗掘古墓葬罪的既遂问题分开来讨论:盗掘古文化遗址罪实行行为完成的标志是行为人挖掘到了古文化遗址的文化层;而盗掘古墓葬罪实行行为完成的标志则是挖掘到了古墓葬的内部设施。[3]笔者认为,一方面本文只讨论古墓葬一种对象,不存在区别两种不同对象分别加以论述的问题;另一方面,即便古文化遗址和古墓葬两类对象同时讲,“分别说”似也没有作为一种既遂类型提出的必要,因为无论“挖掘到了古文化遗址的文化层”,还是“挖掘到古墓葬的内部设施”,都说明挖掘行为已经对对象造成损害,均可归入上述的“损坏结果说”,并非一种单独形态。
经过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十年间的反复研究辩驳,“盗得文物说”被最初的提出者放弃,其过渡形态是1987年11月“两高”《关于办理盗窃、盗掘、非法经营和走私文物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盗掘古墓葬、古遗址,虽未窃取到文物,但情节严重的,也应以盗窃罪处罚”的规定,其终极标志则是以盗窃罪罪名处理盗墓行为的规定的废止,盗掘古墓葬罪独立成罪,并在后来进入刑法典。在法学理论界,盗掘古墓葬罪既遂和未遂的争论随之集中到“损坏结果说”和“盗掘行为说”两种观点上。随着研究深化,认识逐步趋于一致,“盗掘行为说”成为主流。究其原因,主要是认识到不止墓葬内的随葬文物,而且包括封土、填土和墓室等墓葬本体,均是不可再生的重要文物,墓葬形制、封土填土的内容物、墓室材料结构等传递着古代社会重要的文化信息。长时间、大范围的盗掘犯罪造成古墓葬毁灭性破坏,需要强化刑事手段,对盗掘行为发出严厉警告,对古墓葬在被毁损之前即予以特别的有效保护。追寻相应认识深化、固化的标志,是相关刑事法律条文的确认,比如现行刑法第328条把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表述为“盗掘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就是说,对于具有价值的古墓葬,实施非法挖掘行为就构成犯罪,造成损坏结果和达到窃取随葬品目的没有进入该罪的基本构成。
至于法律实务领域,正如一开始所言,一线办案人员一直认为盗掘古墓葬犯罪是行为犯,他们在认识中认同、在办理案件的实践中实施着“盗掘行为说”。多年以来,没有出现实质性失误和根本性问题。
(三)新司法解释带来新问题
问题再次进入视野,是几年前的事,而切实地引起公安理论和实务界关注,是在2018年年初,从那时开始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斗争全面发动,大量文物涉黑涉恶案件短时间内集中“踢爆”,盗掘古墓葬案件实际办理中既遂未遂的疑问和争议迅速累积凸现。
追溯源头,此一轮争议肇端于立法层面。2015年12月30日,“两高”颁布《关于办理妨害文物管理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15年司法解释”)。该司法解释第8条第2款规定:“实施盗掘行为,已损害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应当认定为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既遂。”意思很清楚,即便嫌疑人实施了盗掘行为,但如果还没有损害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就是盗掘未遂,而非既遂。这在法律上以间接方式明示了盗掘古墓葬犯罪存在未遂形态,而且规定构成盗掘古墓葬罪既遂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行为人实施了盗掘古墓葬行为;二是损害了古墓葬的价值。相较于刑法典,这个司法解释所规定的盗掘古墓葬既遂的判断标准,在盗掘行为之外,新增加了一条,即“损害价值”。可以说,新司法解释采行的是“损害价值说”,其本质上属于三、四十年前盗墓既遂理论中的“损坏结果说”。
2015年司法解释在起草征询意见阶段,有学者提出把损害古墓葬价值这一结果作为构成盗掘古墓葬罪既遂的必要条件之一,存在操作障碍。原因在于:其一,是否损害古墓葬的价值,其标准并不像表面上、字面上那样好掌握;其二,是法条表述不严谨,为盗墓嫌疑人一方以“虽实施行为、但未损害价值”的借口为自己开罪,留下了不小的操作空间,这与应对严峻的文物犯罪形势的迫切需要不相适应,不利于打击严重的盗掘古墓葬犯罪活动。然而,司法解释还是坚持了“损害价值”这一表述。
2015年司法解释的起草者认为,对于盗掘行为是否损害古墓葬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判断,可以采用是否破坏文化层的判断标准。文物学、考古学上所谓的“文化层”,是由于古人活动而在古文化遗址、古墓葬中留下来的痕迹、遗物等所形成的堆积层。该司法解释起草者认为:“如果盗掘行为未触及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的文化层的,并不会对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造成实质危害,不宜认定为犯罪既遂”,相反,“司法适用中,只要盗掘行为涉及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的文化层,原则上应当认定为既遂”,即“在司法实践中,对盗掘行为是否损害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判断,可以采取是否破坏文化层的判断标准,并不存在操作的困难”。[4]
二、工作疑惑
从办案实践来看,操作困难还是存在的。我们不能滞留在“古墓上挖个洞”这种简单的语境下思考盗掘古墓葬的有关法律问题。盗墓犯罪已经发生全盘的根本性变化:在探墓定位上,传统铁头木柄洛阳铲被新型全金属可拆解铲代替,演变出探针扎杆,引进了高精度、大深度探测仪;在挖掘方式上,由传统手工挖掘转化为挤压式爆破,大甩铲、移动辘轳等新工具不断引进;在盗洞形制上,除去竖洞之外,平洞、竖平混合洞出现并迅速增加。魔道竞力,这些盗墓方面全方位的、深程度的变化,不可能不在公安侦查等刑事司法工作中集中反映。认为古墓葬的墓室属于文化层,挖掘行为触及墓室即构成既遂,对此未见异议。实际操作中的困难和疑问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古墓葬的地上封土、墓道的填土和墓坑的填土是否属于文化层?二是未涉及所谓文化层的盗掘行为是否都能认定为未遂?
(一)古墓葬的地表封土、墓道填土、墓坑填土是否文化层
如果认为古墓葬地表以上的封土和地表以下的墓道、墓坑的填土是文化层,那只要在古墓葬上实施挖掘,就破坏了文化层、损害了文物价值,构成盗墓既遂,这跟以前的操作没有两样,另作司法解释似没有什么必要;如果封土和填土不是文化层,如有学者认为古墓葬的“文化层非常稀薄,研究价值有限”,[3]墓室及其内部的随葬品才有较大价值,那么,是否可以说接触到墓室之前的所有挖掘行为,即便采取破坏性极大的挤压式爆破手段,即便以大型挖掘机械肆意挖掘,也不构成既遂?一线办案人员对此是有疑惑的。
(二)未涉及古墓熟土层的盗掘行为是否都可认定为未遂
理论和法条是灰色的,现实多姿多彩且变动不居。在墓室之外,古墓葬的地表封土、墓道墓坑填土属于文化层是当然的,连盗墓者都知道根据洛阳铲带出的所谓“五花土”推断墓葬的年代、结构等文化信息。现在的问题在于,即便把涉及地表封土和墓道墓坑填土等熟土层、文化层的盗掘行为均认定为既遂,仍然存在问题。举两类实例加以说明。
一类情况是在涉及商周时期竖穴土坑墓的盗掘案件中,已发现有盗墓人在“方墓吊底”,即在用洛阳铲确定了墓穴长宽边界和深度后,为了避免损坏墓葬随葬品,以便获得更大非法经济利益,他们不是在墓穴边界内,而是在墓穴边界外、紧靠外边界处选取适当位置,用洛阳铲打出孔径约10公分、深度不等的细长形孔洞,置入炸药雷管,实施挤压式爆破,所形成的炸洞底部接近墓室中置放随葬文物的位置,随后使用铣、镢等常用工具挖掘,在很短的时间内即可进入墓室,盗走随葬文物。在某省文物专案组侦破的某商代古墓葬盗掘案件中,后期文物系统抢救发掘所做的墓穴立壁剖面,清晰地呈现了盗墓者挤压式爆破在竖穴土坑墓外缘所形成的盗洞痕迹(图1)。我们假设一下,在实施挤爆形成炸洞后,盗墓人员被抓,迫使挖掘行为停止下来。经勘测,纵的方向的炸洞沿竖行墓坑的外缘向下延伸,就在方寸之间,但刚刚好没有接触、涉及到墓坑和墓室。怎么办?能否因为该种盗掘行为在生土层进行、没有涉及墓葬的竖穴填土,即所谓文化层,就认定为盗墓未遂?应当明白,在事实上,这种行为使得古墓葬的墓坑墓穴等文化层及墓室随葬品处于直接现实的受侵害的危险状态,加之电瓶驱动的小型鼓风机及其配套的塑料软管等排风器具的引入,随葬文物在极短时间内随时可以被窃走,其危害程度不亚于甚或大于直接在墓坑和墓穴封土上实施的挖掘行为。

图1 某商代古墓葬盗掘案的盗洞纵剖面
另一类是在采用平洞或竖平混合洞实施盗掘的案件中出现的情形。近些年,我国大陆地区盗墓犯罪活动有许多“创举”,其中在盗洞形制方面的重要变化,是在传统竖洞之外,出现了平洞和竖平混合洞。这主要是因为古墓附近遮蔽物少、隐蔽性差,形格势禁,盗墓者选择从距离较远的位置着手,向古墓方向掘进。行内人所说的“平洞”,是以横的水平方向为主的盗洞。1993年5月,山西省闻喜县郑某某团伙盗掘×××古墓区,因为古墓在土山顶部相对平坦的农田里,人来人往,为避人耳目,该团伙行贿管理者撤走岗楼哨兵、破拆铁丝网,进入紧邻的省储备物资管理局×××库所在山沟,挖掘140余米的平洞,侵入3座东周时期古墓葬的墓室。(图2)在另一案件中,1993年3月,闻喜县×××乡××村崔某某纠集多人,在本村烈士陵园内的窑洞内挖掘290余米的平洞盗掘古墓。在同期的闻喜县××庄和近年的平陆县××镇,都出现过类似的在旧窑洞内挖平洞盗墓的案件。至于说到“竖平混合洞”,是指竖洞和平洞结合所形成的盗洞,盗墓人在墓穴邻近的比较僻静的地方先根据墓穴深度向下挖一竖洞,再在竖洞底部向墓穴方向挖掘平洞。(图3)2000年下半年,运城市黄小军纠集多人盗掘河南省三门峡市虢国墓博物馆院内古墓,他们在博物馆院墙外以制作化肥为名租赁院落,在空房内先向下挖掘12米深的竖洞,又横向掘出一条长达300余米的平洞,盗掘已经圈入博物馆院墙以内的周代古墓3座,窃走文物数百件。[5]在上述案件中,盗掘人员均侵入墓室,盗走了珍贵文物,当然构成盗墓既遂。理论研究应当超前考虑,可以做必要的假设和推测。我们设想嫌疑人以挖掘平洞或竖平混合洞方式盗掘古墓,盗掘行为在即将要接触到墓室时,盗墓者被抓,或因为其他外部原因盗墓活动被迫停止,即盗洞即将达及熟土,但仍处于生土层中,那此种行为应当如何认定?如果按“文化层”标准,因为该行为尚未触及墓坑、墓道或墓室的扰土层,因而认定为盗墓未遂,那对此类价值极高的大型墓葬的保护是有利还是不利?这留给盗墓人员的操作空间是否过大,存在不存在轻纵重大盗墓犯罪嫌疑人的问题?存在不存在文物系统同志担心的不利于打击猖獗的盗墓犯罪活动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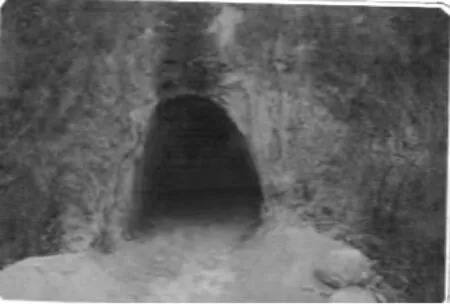
图2 闻喜×××库平洞入口

图3 榆次某墓地竖平混合型盗洞入口
事实上,在这些采用平洞或竖平混合洞盗掘古墓葬的案件中,在没有触及熟土层,在就要挖到墓室、马上就要拿到随葬品时,盗墓活动被发现的情形已经在现实中出现。2005年9月初,在陕西省韩城市××村,一盗墓团伙利用山沟地形挖掘30米长的平洞,在距离正在实施考古发掘的该墓区规模最大的周代中字形大墓墓室极近的时候,被发现制止。如果这一案件发生在2015司法解释之后,既遂未遂怎么定?本人把这类以盗掘古墓为目的、在该古墓紧邻的生土层中挖掘,但迫近古墓墓室的对于古墓葬的危险侵害行为,称作“直接的、现实的危险”。这里的问题是,在面临此类直接现实危险时,能否采用所说的文化层标准,认定为盗墓未遂?
三、对策建议
工作操作层面的困难,是与理论上的疑惑及立法上的反覆相联系的。作为参与办案的教学科研人员,本人尝试的解决路径是在学理分析基础上提出立法建议,同时为办案单位提供目前阶段在现有法律规定框架下的可行的具体操作意见。
(一)理论分析及立法建议
质言之,现在需要直面盗掘古墓葬罪既遂的“损害价值说”与主流的刑法学理论和有关司法解释及其上位的刑法条文的不一致,设法消除矛盾冲撞,找到破解出路。
1.解决与刑法学理论的不一致
刑法学理论关于犯罪既遂问题的研究大致分为“目的说”“结果说”和“构成要件说”三种主张。“构成要件说”认为,既遂与未遂区别的标志是犯罪实行行为是否具备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具备的是既遂,未完全具备的是未遂。[6]至于谈到“目的说”和“结果说”,实际情况是,目的的达到或者结果的发生,的确分别是一部分犯罪的既遂构成条件,但这两种观点的症结在于不具有普遍性,各自均不能适用于所有类型犯罪,不能成为所有犯罪构成既遂的标准,即“目的说”或“结果说”无法把每一种犯罪的既遂和未遂均明白无误地区别开来,其不完整性和不准确性明显。与之相对照,犯罪既遂的“构成要件说”更能弥补不足,普遍适用于各类犯罪,被越来越多地接受。
具体联系到盗掘古墓葬罪,援引一般刑法理论的“构成要件说”,以盗墓者行为是否具备刑法分则中该罪的全部构成要件作为既遂的标准,当然也是可行的。盗掘古墓葬罪的主体是年满十六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在客体上盗墓行为破坏国家文物管理秩序、侵犯国家对古墓葬的所有权,该罪的客观方面是非法挖掘行为。可见,盗掘古墓葬罪的主体和主观方面分别是一般主体、一般故意,具有一般性、通常性,无甚特别。该罪构成的不一般性、复杂性,集中在客观方面和客体上,在确定该罪的犯罪构成时,需要重点考察是否发生实质的挖掘行为,该挖掘行为是否属于没有经过赋权机构批准的非法挖掘行为,该挖掘行为是否破坏或侵犯国家文物管理秩序和国家对古墓葬的所有权这一客体?很清楚,该罪犯罪构成的确定,集中在了对其行为的考察上。在此意义上,一般刑事法学既遂的“构成要件说”,在具体到文物刑事法学的盗掘古墓葬罪的既遂形态考察上,可以说实质上就是本文一开始所讲的“盗掘行为说”。
通过上述论述可见,在盗掘古墓葬罪构成要件中并没有“损害古墓葬价值”这一结果存在的线索或因由。初步的结论是,一般刑法学既遂理论的“结果说”,文物刑事法学中盗掘古墓葬罪既遂的“损坏结果说”及作为其新变种的2015年司法解释的“损害价值说”,应该说已经在学术研究领域被放弃。来之不易的研究成果应当很好继承延续,并以法条形式固定下来,似不应当在理由不充分的条件下轻易否定。
2.解决法律规定内部的不一致
在此,其实就是立法层面下一步如何动作的问题。现在的不一致,主要不在理论界,更不在一线司法实务界,而在介乎二者之间的立法环节,在法律规定的内部,具体就在刑法第328条和2015年司法解释第8条之间,前者是“盗掘行为说”的落实,后者是“损坏结果说”的体现。系铃解铃,最终解决不一致只能从立法上着手。法律高于司法解释,司法解释服从服务于法律。可行的途径也许只有一条:拨乱反正,在仔细反复研究确定没有其他负面影响的情况下,在未来某个适当的时间节点,删改2015年司法解释第8条第2款。法典与司法解释的不一致,完全可以在进一步的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中解决。
(二)当前办案操作层面的建议
在实际办理案件中,受时限限制,容不得议而不决。法无规定不为罪,法有规定得执行。在刑法典、附属刑法及司法解释等构成的现行刑事法律框架下,盗掘到墓室即构成既遂,而在价值不大的古墓上挖个小洞、在有价值的古墓上挖一锹土一类“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行为,可以依照刑法第13条不以犯罪论处,这样处于两个极端、但界线分明的行为,不多纠缠,在此主要围绕前述困惑,对盗掘古墓葬罪办案操作层面提出三个具体建议:
1.把古墓的地表封土和地下部分的墓道、墓坑填土均视为文化层,只要具有盗墓主观故意,且对有价值的古墓葬的封土和填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实际挖掘,即认定为破坏了古墓葬的文化层、损害了古墓葬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应当认为其构成了盗掘古墓葬罪的既遂形态。
2.在有价值的古墓的墓道、墓坑、墓穴紧邻的外边缘位置,以爆破形式或机动挖掘设备实施挖掘,虽然盗洞未直接触及封土和填土,但是所产生的强烈震动势必破坏古墓葬原有的稳定状态,可以认为其行为已经损害古墓葬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应当认定为既遂。这样认定,与挤压爆破、机械挖掘的特殊危害性是相当的。另外,鉴于我国对于爆炸物品特别严管的刑事政策环境,对于涉案的雷管、炸药及相关物品必须溯源,对相关直接行为人或责任人必须予以追究。
3.以平洞、竖平混合洞方式挖掘,以古墓的墓室为目标,且已挖掘形成一定距离的盗洞,但尚未触及古墓葬封土、填土的,操作意见有两点:其一,按未遂定性,即在盗掘古墓葬罪罪名后以括号标出“未遂”字样;其二,不宜从轻或减轻。刑法第23条第2款规定:“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就是说,法律对未遂犯通常是要从轻或减轻处罚的,但是,这里的表述是“可以”,而非“应当”,采行的是得减主义,而非必减主义。对于以平洞、竖平混合洞方式挖掘,虽然尚未触及古墓葬的封土、填土,但目标为古墓墓室,且已挖掘形成一定距离,特别是那种已掘出的盗洞的末端部分已经抵达古墓葬的墓室的外缘,墓室及随葬文物面临“直接的现实的危险”的情形,不应当等同于一般的大多数未遂犯,不适宜从轻或减轻处罚,这也许更加地符合罪责刑相一致的刑法基本原则。
总而言之,引起疑惑的“具体”,不如适当的“模糊”。对于2015年司法解释中“已损害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这一盗掘古墓葬罪既遂的表述,可否在未来予以修改甚或删除,以给基层办案人员极少量但极必要的自由裁量空间,便于其视具体情况更加合理地予以处置,以更加及时、强力和高效地应对猖獗的盗掘古墓葬犯罪的问题,当然可以从其他方向和层次上继续讨论,拓展深化,以期最终妥善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