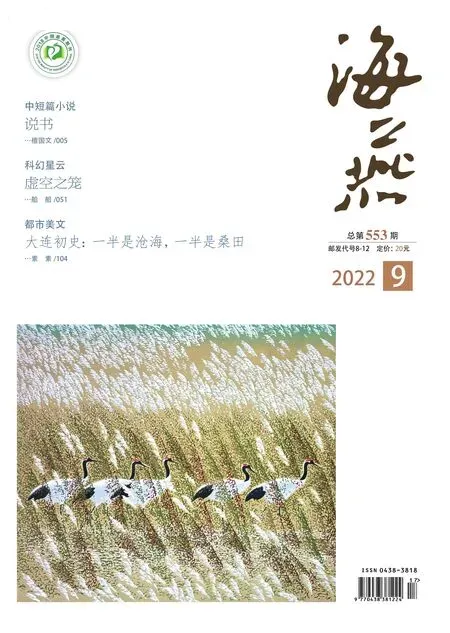无处停泊的光阴
2022-11-17于厚霖
文 于厚霖
我们生产队有一条昵称“小撅子”的独桅小船,桅杆插在船中间略靠前,桅根吊着捆成一束的紫色帆篷,桅、帆和吊绳构成近似4的形状;桅尖飘扬的小红旗,不仅为小船涂了一抹亮色,更为寂寥的海岸平添几分动感和生机;一双“燕翅”翘起在船尾,“燕翅”中间镶着b形舵板;光秃秃的舱盖上躺着一支大橹、一支挽篙。
“小撅子”是发音,书面表达时,也有人写成“小橛子”“小榷子”“小脚子”(脚发音juě)。后者形容小船像一只踩着波浪的脚,精致,玲珑,颇有意趣。“小撅子”载重量一吨左右,比单纯摇橹的舢板大,却是帆船中的袖珍级。这样的小船单人即可驾驶,但要出海作钓,总得两个人吧。就有了两名不能称之为渔民的船员。
我们于家屯坐落在海岸,却不是渔村,也就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渔民。石城岛是农业岛,主业是种地。我们屯有三百多亩地,人均近三亩。坡地多,土层薄,“石头骨子”“偏脸”“转圈楼”……从耕地名称可见其险峻和贫瘠。在没有修成梯田的年代,坡地存不住水,粮食亩产低,但总产量高。地多,坡陡,决定了社员们要付出更多的辛苦和劳累。只有深秋时节,两辆胶轮马车拉着垛成小山一样鼓鼓胀胀的麻袋包,一趟一趟到公社粮站交公粮、卖余粮时,大家才松出一口气。一年的劳累告一段落,但口粮不足仍然是各家各户面临的大问题。怎么办?向海里要啊!
“小撅子”成为连接农田和海洋的纽带。
于家屯位于石城岛北部U形海湾的底端。潮水像一只巨大的舌头,伸进来时将海湾填得满满当当,缩回去时海湾变得空空如也。涨潮了,潮头爬过泥滩抵达岸边的沙滩,又沿着沙滩斜坡上涨,大汛潮满潮时一湾滚荡的碧水不仅将整个沙滩淹没,还会淹没岸崖的根基直至半腰,陆地凭空矮了几米,海岛像要漂起来;潮水哗哗退去后,贝壳和海草遗留在沙滩的斜坡上,被岸崖环绕和海水镶边的裸滩扩大再扩大,展出一幅“枯潮”的景象。潮水周而复始地涨落,海湾爆满和干枯交替呈现,生生不息的贝类、虾蟹、杂鱼等小宗水产品轮番登场,在粮食之外给了我们更有滋味的喂养。口粮不足的年月,不仅鱼虾蟹贝,海麻线、海葛子、谷穗菜、龙须菜和海青菜等藻类,都是我们食物的重要补充。向海索要,每个人都发挥出巨大潜能,那只“小撅子”也功不可没。

石城岛周边的生产队,都有一只“小撅子”。石城岛矗立在大陆架上,周围水浅,经济鱼类少,公社捕捞场的机帆船都在山东沿海一带作业。“小撅子”却像眷恋母亲的孩子,偶尔离岸溜达一圈,旋即回转。我们屯那条“小撅子”经常锚泊在岸边,退潮后平稳地落在嵌入泥滩的硬质沙滩上,成为岸带风光的点缀。那片沙滩由雨季的洪水冲刷而成,河流携带沙石入海,与上涨的潮水交汇冲撞、沉淀,沙石覆盖了部分泥滩,铺出一片场院大的扇形硬滩。硬滩表层板结,滩基深硬,滩里隐藏着无数我们称为鲈虾的蝼蛄虾,为钓鲈鱼提供匹配度最佳的诱饵。不同渔季,“小撅子”钓石鳉鱼、鲈鱼和波螺蛸。断断续续的小打小闹塑造不出职业渔民,所以船员的主要角色仍是种田人,挑、抬、锄、割等农活一样不少干,只有在出海作钓时变身为临时渔民。
出海不分早晚,根据潮汛,夜间出海是常事。不是垂钓,是延绳钓,放很长很长的线到海里,线上拴了很多把钩。出海之前,船员要往渔钩上挂饵。如果是夜间出海,头一天就要把所有渔钩挂上鱼饵。染了猪血的暗紫色主线硬撅撅地盘在圆形筐里,一筐线百把钩,五六筐线摞起来,像一座多级木塔;扎在筐沿草绳上的一圈钩饵,为每层“木塔”镶了花边。钓石鳉鱼用烀熟的蚬子肉当饵,钩尖从蚬肚穿过,轻易不会脱落。钓鲈鱼用活鲈虾当饵,钩尖穿过虾身,虾仍保持问号一样弯曲的身形,对鲈鱼构成诱惑。钓波螺蛸用比拳头还大的红里子波螺壳,一根草绳拴几百个钻了眼的螺壳下到海里,就为波螺蛸投放了几百间栖身的豪宅。波螺蛸之所以叫波螺蛸,是因其遇到合适的波螺壳就钻进去,以保护柔软的躯体,岂料是自投罗网。后来知道,这种八爪鱼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桃花蛸,因其在三四月桃花盛开时最肥,硕大的脑核是硬硬的一包籽儿。
“小撅子”上岸时,屯子热闹起来。社员要买鱼或波螺蛸,先称了记账,年底结算。波螺蛸一毛三分钱一斤,石鳉鱼和鲈鱼的价格不记得了。生产队分值低,社员收入少,舍得买鱼的人家不多。“小撅子”钓上来的鱼,大都卖给了公社水产供销站。我们有海鲜吃,得感谢那片慷慨的海域。趁中午休工,拿着蛎钩和罐头瓶到海边礁石上打半小时蛎肉,就够下一顿面条。海里有花盖蟹、赤夹红蟹、红里子刺螺、蚬子、毛蚶、蚆蛸、胖头鱼等,学名“吐铁”的泥溜更是泥滩上的主角,晴天时泥滩上密密麻麻一片连着一片,都是泥溜凸起的坑点。退潮后,近岸的泥滩上是一群弯腰捡泥溜的人,远处硬滩上蹲着扒蚬子、捡毛蚶、挖蚆蛸的人,从岸边通向海里的凉道像一条轴线串起泥滩和硬滩,滩上一派繁忙景象。我和小伙伴们常到滩上捡泥溜,每每把自己涂抹得像泥猴儿。毫不夸张地说,这片海产出的低端海物,我们都吃够了。烀海鲜是家常便饭。伴随袅袅炊烟,弥漫的海鲜蒸汽飘满大街。如果几家同时烧火烀不同品种,有烀蛎头、烀蚬子、烀波螺、烀蟹子的,那小屯上空飘荡的鲜味就别提多复杂多浓郁了,能呛人一跟头。海鲜熟晒是家家户户小院的风景。焦黄的蚬子干,浅黑的蛎子干,半黑半黄的波螺干,赤红的毛蚶干,还有生晒的胖头鱼干,各种各样的海鲜,都能晒出独特的鲜味。生鱼干熥了就饭,熟海鲜干可当零嘴儿(零食)。就说乌黑的泥溜干吧,上手一搓,吹一口气,酥脆的薄壳就轻飘飘地飞走,手心剩下干硬的泥溜肉,一粒一粒填到嘴里,嚼起来艮纠纠的,有一股弹牙的劲儿,别提多有滋味和感觉了。
我们不缺海鲜,缺的是档次。缺者为贵。轻易得到的普通海物似乎难登海鲜美食家族的雅堂,而对“小撅子”捕获的海鲜情有独钟。自家能赶到的蚬子、蛎子、毛蚶等,就像苞米、高粱、地瓜等五谷杂粮,“小撅子”钓上来的波螺蛸、鲈鱼等好比大米白面。那个年月,大米白面可是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到。所以偶尔高消费一下,买几斤波螺蛸和石鳉鱼,换换口味。波螺蛸炒韭菜是让人一听就流口水的美食!石鳉鱼清炖,鲜嫩,又略带土腥味,不是很受欢迎,但因为是“小撅子”钓上来的,身价就有些高。石鳉鱼学名石鲽,在比目鱼中排名靠后,因背部边缘有一排像膙子一样凸起的硬结,又称石膙鱼。钓上来的石鳉鱼,都从紧闭的小嘴里伸出一段透明的尼龙线。那是在拔线收鱼时,船员为了抢时间,来不及把深扎在鱼喉中的尖钩摘下,只好剪断子线,渔钩便留在了鱼嘴里。最好吃的是鲈鱼,鱼轱辘切薄,像一张一张椭圆形的饼,开锅后咕嘟咕嘟多炖一会儿,炖好后撒些葱花香菜,汤里漂着晶亮的鱼油珠儿,香绝了。鲈鱼价格稍贵,但不用买,用鲈虾换。鲈虾是从岸边的硬质沙滩“钓”上来的。屯里的婶子大娘们“钓”一筐鲈虾,就能从“小撅子”上换一条十几斤重的鲈鱼。新鲜的大鲈鱼,鱼嘴张开,鱼身弯曲着躺在元宝形长筐里,鱼头和鱼尾都露在筐外,看着就大饱眼福,更别说炖出一锅浓郁的鲜香了。
船员换过几轮,都是我熟悉的,我称他们“大爷”“二叔”或“三哥”。当船员比种地要少出力,但要经常起早贪黑,虽说只在海峡转悠,遇到风浪也挺可怕。船太小了。所以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当船员。我父亲年轻时曾在大连水产公司的渔船上工作过,后来回到生产队,只干赶大车、招犁杖等“技术”活儿,从未在“小撅子”上当过船员。
我经常和小伙伴们到沙滩上,在“小撅子”近旁看船员弄这弄那,充满好奇。因为爷爷驾驶的那艘大型帆船的缘故,我对船的“研究”近于痴迷。“小撅子”也有独到之处。除舱盖是平面,其余部位都由曲面组成,直、曲、凹、翘构成美妙的外形。拴着缆绳的“小撅子”在波浪中摇摆时,像牛犊被牵住了鼻子,想挣脱,又挣脱不得。船头永远逆风,没有风的时候船头朝着潮水涌来的方向。满潮时海水停止涌动,“小撅子”就像没了主心骨,扯着锚缆在海面打转转。摇橹是一门技术。我在小小年纪就能笨笨磕磕地摇动一只“小撅子”,很有些自豪。在我看来,招舵更有含金量,张篷航行时舵把一转,就能改变航向,非常神奇,我却一直没有机会尝试。
“小撅子”不在岸边停泊,就是去里长山海峡钓鱼。石城岛与庄河大陆之间的海峡上,偶有大型拖轮像火车头拖车厢一样拖着三两艘满载煤炭的“大驳子”船,缓慢地从海峡横穿而过。行驶在海峡之上的大型木帆船队,是石城岛北部海域特有的景观。那些木质运输船,是“跑贸易”的,又称贸易船,巨大的黑色或紫色帆篷是海峡移动的风景,岸是风帆的归宿。当它们现身海峡时,距石城岛端头港就不远了。端头港大出风头的机会随之而来。退潮时,那些平底帆船巍然挺立,桅杆上的绳索抖出尖音;尖底船偏着船身,欲倒未倒,待潮水涨上来才能扶正。那些庞大的船体、高耸的桅杆,显得威武霸气,我们屯的“小撅子”如果混迹其间,小到几乎可以忽略。那些有两支桅、三支桅的大型运输帆船,常年行驶在大连至山东烟台、浙江舟山等航线,能在岛上看到它们相聚的身影,会瞬间热血沸腾。美中不足的是,大型帆船停泊在端头港,而不是我们屯的海边。端头屯在石城岛U形海湾东侧,可以较早迎来潮涨,而我们于家屯近岸滩高,潮水姗姗来迟又较早退去,通往海岛腹地的道路也比较崎岖,故没有能够成为良港的幸运。
更多的时候,我们站在崖上,遥望的不是那些大型帆船,因为知道望不到它们;我们在辽阔海峡上搜寻的目光,最终落在由小到大、逐渐清晰的一个点上。从高处北望,海面立体了,是远高近低的一幅画,那紫色小帆点从北嘴的山崖后移出,刀形帆篷一撅一跌,躲开暗礁和明礁组合的礁群,从覆盖滩涂的碧波上驶过,缓缓抵岸。“小撅子”回家了!降篷,拔舵,抛锚,一气呵成。我们会跑上沙滩,看船员卸鱼。目送小船远去,会有另一种心境,是隐隐的担忧。“小撅子”的航线在海湾偏西,路过“小北嘴”,从高出海面的一座蛤蟆状礁石旁边经过。那里有一大片暗礁,潮退半架子时渐次现形,最终全裸,像一些巨大棋子摆在滩上。小渔船要途经暗礁上方。我们熟知那些礁石的形状和杀伤力,在水深不够的时候,“小撅子”必须躲开暗礁的礁尖。
我们会在游泳时攀爬到“小撅子”上。十岁左右,正是调皮的年纪。我们游到船边,抓住缆绳。几个人同时爬上船帮的一侧,小船就偏了,激起海面一片片浪花水沫。
我们从水中拔起身体,翻过船舷,落在滚烫的甲板上,“咚——”空心船像乐器的音箱,被撞击后发出沉闷、响亮且久久回荡的声音。海的弹力传递到甲板,小船摇晃的频率加快,船头在波浪里一撅一跌,又一撅一跌,像快速起伏的跷跷板。“小撅子”的名儿是不是这么来的?
舱盖晒得像烙铁,我们身上流下的海水和脚踩出的湿痕很快就蒸发得无影无踪。我们躺下,不断地翻身,用身体湿的一面去为船板降温,也让自己舒服一些。在船上晒一会儿,皮肤晒得发紧,身上泛出盐碱,一挠就出白道道,再纵身一跃,扎入水中,游上岸来。回头再看,我们刚才待过的小船,正轻轻点头,向我们致意呢。
船上的海腥味因干燥而浓烈。舱门没锁时,我们会翻看,看到锅里有船员吃剩的熟波螺蛸,煳锅了,缩成一个个乌黑的小球,我们就喜出望外,用手当筷,抓了吃。波螺蛸囫囵个儿煮,省了用刀;挑小的煮,可能是考虑熟得快吧;用海水煮,不放盐也咸得齁嗓子,吃得舌头发苦发涩,鲜味被苦和涩抵消了大半。有时能吃到剩在锅底的炖鱼,也是煳的,也同样苦涩。船员们吃剩下的不往家里拿。在船上随便吃,拿到家里就是事。或许他们是留待再出海时食用,结果被我们给分享了。
我们攀爬上船,开始有些害怕,怕被船员发现了喝斥。但是没被发现,或者发现了也没人当回事,我们胆子就大了起来。那天不知是谁起的头,我们几个把船锚拔了,然后轮换着摇橹。我还想把吊起在半空的船舵降到水里,过一把招舵的瘾。没想到,在船员手里非常驯服的小小渔船,到了我们手里竟然难以驾驭。我们费力地把桅碗扣上橹锥,没摇几下,橹就掉了,“嘭”的一声砸到甲板上。我们想把船弄到岸边,船头却刚正过来又偏过去,欺负我们年纪小力气弱吗?越着急越慌乱,还怕被岸上的人发现。橹不管用,拿挽篙蹬也不行。很快开始退潮,桀骜不驯的“小撅子”离岸越来越远。这可是生产队的财产啊!
我们都吓哭了,也吓傻了,居然忘了应该把船锚抛到海里。
小船要是一直漂下去,漂到庄河也不一定。我们把祸惹大了。正一筹莫展,一只小船从岸边飞奔而来,从侧面靠拢,一个人跳上来,夺过我们手里的橹,驾轻就熟地拨正了船头。我们几个都蒙了,好像在做梦。那条小船是哪里来的?是大人们发现我们把船弄跑了,到邻近的生产队借的?
登船来救我们的,是本屯船员老王。他是走“五七”道路的职工,家住我们生产队,曾在“小撅子”上当了一个时期的船员。
我们没有受到批评和斥责,却从此明白了,在我们这个年纪,很难驾驭一条船,哪怕是条“小撅子”;我们可以摇动大橹,但抵御不了无情的海溜子。
“小撅子”后来出事了。
那天,我们目送“小撅子”扬起紫色帆篷,贴着海湾西侧向北驶去,要到海峡里钓鱼。“小撅子”本来一帆风顺,却在奔跑到小北嘴时突然降下帆篷,驴拉磨一样转了几圈,然后急切地向岸边奔来,是一张大橹摇回来的。我们异常震惊地看到,坐在船头的老王一只手握住另一只手,惨白的脸上扭曲着痛苦的表情。
原来是潮水还没涨够,“小撅子”略微偏离航线,不偏不倚骑上了暗礁的礁尖,船身过去了,舵过不去,飞速行驶的“小撅子”被突然拦截却停不下来,舵朝后拉,舵把压向船板,正在招舵的老王来不及反应,一只手被严重挤压,伤势严重。
老王受伤的手由赤脚医生负责处置。“小撅子”也残疾了,舵板横在船上,船尾镶嵌舵柱的两道卡槽都被扯裂,露出惨白的木茬。
从那以后,“小撅子”留给我的印象就有些模糊了。它无疑是被修好了,并且重新出入海峡,从事延绳钓。生产队解体之后,那条“小撅子”就不知去向。随后,石城岛北海湾修起养虾场,连可供小渔船停泊的那片硬质滩涂也被虾场的土坝占领,即使有船,也无处停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