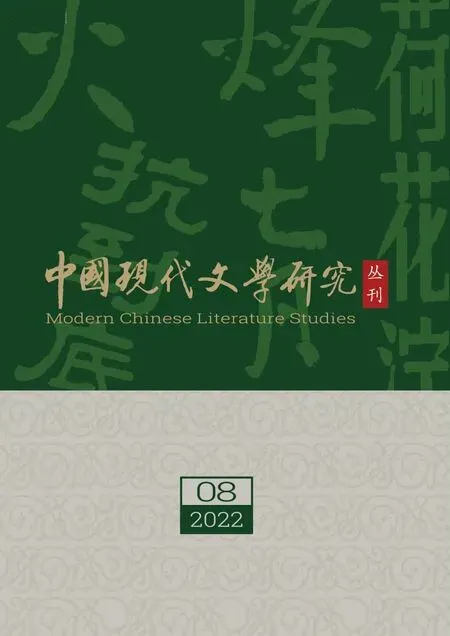恶性通胀的文学显形与民族国家的必要性※
——重读沙汀长篇小说《淘金记》
2022-11-17廖海杰
廖海杰
内容提要:关注抗战时期蔓延大后方的恶性通货膨胀,显形这一现代经济灾难,是沙汀长篇小说《淘金记》未被注意到的独特之处。小说凝聚着战时经济生活中的生存体验,揭示了人退化为“经济人”、丧失主体性的境遇,呈现出整体层面的反讽并带上一些现代主义色彩。在政治关切上,《淘金记》表现出对恶性通胀加剧独立王国状态、地方无法被整合进现代中国的嘲弄,而对经济困境中人人相互为敌的自然状态的展示,又从反面证明了通过革命建立真正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必要性。
《淘金记》,一部不太起眼的中国现代文学经典,自问世以来,虽也挑起过短暂的论争,但在今天,常被作为一部平平无奇的“乡土-地域文化”小说来读。关于它的新研究越来越少,偶有一些书中的段落,涉及茶馆、袍哥的,被用作历史学界的材料。不过,我却认为,《淘金记》是独特的,这种独特不仅是地域文化维度的独特,也不仅是“暴露与讽刺”维度的独特。《淘金记》涉及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恶性通货膨胀问题,又与民族国家意识息息相关。
不妨从《淘金记》接受史中的一个问题说起。自1943年问世之后,《淘金记》的写实技巧得到各方论者一致认同,但也有一个常被谈及的“瑕疵”。部分左翼批评家认为小说缺乏对出路的展示,过于“客观主义”①冰菱:《〈淘金记〉》,《希望》第1卷第4期,1946年4月。、甚至“作者对他所描写的人没有充足的感情,因之也就不可能把他所认识的来感染读者”②鹒溪:《〈淘金记〉读后》,《抗战文艺》第9卷第1、2期合刊,1944年2月。。一些态度平和的论者也常常在称许了小说的成就后,指出小说有“自然主义的阴暗的气息”③石怀池:《评沙汀底〈淘金记〉》,《群众》第10卷第10期,1945年6月。芦蕻在1947年谈《困兽记》的文章中,也顺带谈到《淘金记》的“自然主义的阴暗的气息”,参见芦蕻《沙汀的〈困兽记〉》,《文艺复兴》第3卷第5期,1947年7月。之感。在1950年代的三本现代文学史著中,王瑶、丁易、刘绶松都以此作为《淘金记》的不足之处来论述。④参见陈思广《纠偏与审美——1944—2011年沙汀长篇小说接受研究》,《江南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改革开放以来,这一问题也被许多学者注意到,并尝试为沙汀那冷静的叙述方式正名,王晓明、万书元的文章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两篇。⑤参见王晓明《论〈淘金记〉》,《新文学论丛》1982年第3期;万书元《〈淘金记〉的叙述体态和语言风格》,《文学评论》1987年第4期。关于《淘金记》的“阴暗气息”,王晓明认为问题在于读者,“有些理解较弱的读者很可能因为害怕陷入阴郁情绪,而不敢细察沙汀描写的世界,自然也就无法深入领会作者的暗示”;万书元则指出,小说中有两种叙述语言,其中有一种是“灼热的、直露的、嘲弄的”,作者并非那么不合时宜的“客观冷静”。不过,一部带有批判性的小说,其叙述的冷静与否只是风格问题,本文并无意在技巧上为《淘金记》再一次正名,真正值得注意的问题出现在这部小说与历史现场的对话关系中。为什么在小说问世之初,其冷静的叙述方式和“阴暗的气息”会给各方论者或多或少的不适之感?这基于背后怎样的历史情境?如果左翼文坛内部的人事纠葛⑥《淘金记》被扣上“客观主义”的帽子,有被七月派借为靶子用以操演“主观论”的因素。在“主观战斗精神”的烛照下,即便是寻常的作品也会显得“客观主义”。这背后还可能隐含着对沙汀生活选择的指责。“客观主义”“自然主义”有缺乏立场态度的意思,似乎暗示着沙汀在抗战时期离开延安和重庆后长期避居家乡安县,是对革命的逃避和旁观。沙汀在1980年代回顾《淘金记》时,还对路翎当年的批评耿耿于怀。不过,单从这一层面考虑,并不能解释为何许多非左翼的评论者也对小说有“阴暗”之感。不能完全解释这一问题,我们就不妨在文史对话中重读文本,并首先弄清楚,《淘金记》到底写了一个什么故事,“阴暗的气息”又来自何处?
一 通货膨胀的文学显形
《淘金记》问世之初在接受场域中激起的那小小“不适”,归根结底出自论者对文本批判性的怀疑——冷静的叙述被怀疑不是风格的体现,而是作者冷漠态度的流露。否则,小说带有“阴暗的气息”就不可能是一种瑕疵,而是一种成功的艺术效果。显然,在历史语境中,《淘金记》承受着某种较高的道德压力,今天看来并无不妥的作品,让当时的评论者感觉到了或多或少的不适。“阴暗的气息”不是一个艺术技巧问题,而是一个历史问题——可以推论,《淘金记》所触及的那个作为情节核心的现实,是一个让许多同时代评论者难以忍受、难免作出过度反应的现实。
回到引言处的问题,《淘金记》究竟写了什么现实?“阴暗的气息”又来自何处?引入抗战时期大后方发生恶性通货膨胀这一历史事实,有助于理解这一问题。
《淘金记》讲了一个争夺金矿开采权的故事,但参与争夺的两方又都并非金矿所在地烧箕背的主人,这构成了情节的张力。真正的主人试图维护祖坟的风水,最终被强力所击败,又被外力所挽救。小说以三股力量的冲突编织成故事,一是白酱丹、彭胖、联保主任龙哥组成的利益联盟,是镇上的“在朝派”,最终成为争夺烧箕背金矿开采权的胜利方。二是林么长子及其手下,即北斗镇的“在野派”,是争夺中的失败方。第三方是烧箕背的土地所有人,何寡母及其儿子何人种,最后被迫让出了金矿开采权。以抽离出的故事概要来看,《淘金记》确实可谓“围绕着开采北斗镇筲箕背金矿的线索,展开了四川农村恶霸、粮绅、地主间为发国难财而掀起的内讧”①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97页。《淘金记》在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修改,地名“烧箕背”改为“筲箕背”,本文基于《淘金记》较早的版本进行研究,故仍称为“烧箕背”。。若是对《淘金记》的理解止步于此,它也就真是一部平平无奇的“乡土-地域文化”小说,但以上的故事概要在简化中遗落了小说的情节发展动力——恶性通货膨胀。事实上,围绕烧箕背金矿开采权争夺的,不是静态的乡土社会中的利益冲突,而是现代性侵入后所引发的剧烈变动。
通货膨胀是推动《淘金记》情节发展的动力。在小说一开始,北斗镇就处于一种并不平静的氛围中,看似无关紧要的地方风物描写,道出了原因:“除开棉花、玉米和沙金,乌药和碱巴也是北斗镇一带山域地区的特产。但是从前一般人并不怎样重视,谁也想不到它们会在抗战中大出风头,因此繁荣了市面。而且胀饱了一批批腰包,许多人都因为它们发了财了。”②沙汀:《淘金记》,文化生活出版社1947年版,第6页。版本后同不赘。乌药和碱巴能“大出风头”,胀饱了“许多人”的腰包,其中固然有战时物资短缺的因素,却更是通货膨胀的直接后果。关于战时大后方的通货膨胀(即法币严重贬值现象),简单地说,起源于国民政府维持战争开销的需要。沿海工业地带相继沦陷、税源大量丧失,国民政府又栖身于并无牢靠政治基础的大后方省份,除了借外债,也只能通过超量发行货币来汲取社会资源。①关于抗战时期恶性通货膨胀的具体机制,民国时期曾任中央银行行长的张嘉璈(张公权)所著《通胀螺旋》(又译《中国通货膨胀史1937—1949》)一书是经济史学界绕不过去的一本著作,该书第一至五章中对此有清晰简明的阐释。参见张嘉璈《通胀螺旋:中国货币经济全面崩溃的十年》,于杰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起初,超量发行货币可谓是一种隐蔽的税收,具有支持抗战的正当性,但在1940年前后(这也正是《淘金记》中故事发生的时间),物价开始失控,通货膨胀进入恶性循环的状态,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得到控制。除了国民政府方面的原因,日方破坏法币信用的“经济战”手段,也为物价上涨推波助澜。②关于抗战时期日方破坏中国金融系统的种种手段,参见齐春风《没有硝烟的战争——抗战时期的中日经济战》,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可以说,通货膨胀所造成的经济灾难,亦是日本的战争罪行之一。
在通货膨胀循环加剧的背景下,北斗镇那些看上去胀饱了的腰包,并不能高枕无忧,因为法币也在持续不断地贬值。仅仅几页之后,《淘金记》中便出现了这样的句子:“因为生活过高,现在通不兴玩漂亮了。”③沙汀:《淘金记》,第12、113、319页。通货膨胀造成的物价畸形上涨,异化出许多如乌药和碱巴一样的获利空间,这对于有产者而言,既是获得暴利的诱惑,又是财产贬值的压迫。不管是淘金业在北斗镇的兴盛,还是白酱丹和林么长子的“起心”,都基于通货膨胀所造成的情节动力,“生活还在上涨,金价已经爬到百换以上,他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对烧箕背断念头的”④沙汀:《淘金记》,第12、113、319页。。随着故事时间的推移,隐藏在背后的物价也随着小说页码的增长而增长。尽管,经济逻辑很快遭遇了乡土伦理的阻碍,但白酱丹最终仍借助政治强力压服了竭力守住祖坟的何寡母。荒诞的是,在小说的最后,白酱丹的努力最终被证明是白费,烧箕背还是被保了下来——由于粮食价格的持续高涨,淘金的成本已大幅增加,在“没有百分之百的钱赚,任何买卖便都不能说是买卖”⑤沙汀:《淘金记》,第12、113、319页。的新形势下已失去了吸引力。《淘金记》中,最“足智多谋”的白酱丹亦不是能主宰自己命运的人,他被恶性通货膨胀所摆布。
《淘金记》被同时代评论者所读出的“阴暗的气息”,正是通货膨胀中的生存体验。众所周知,抗战时期文人的生活境况普遍窘迫,“文协”为此还曾发起过一个“保障作家生活运动”,教师、小公务员也沦为低收入阶层。过去认为这是战时物资短缺造成的普遍困境,其实不然。善于社会剖析的茅盾就在散文中记载过,在战时饭馆里,“常见有短衫朋友高踞座头,居然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中山装之公务员或烂洋服之文化人,则战战兢兢,猪油菜饭一客而已”①茅盾:《“雾重庆”拾零》,《茅盾全集》第十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7页。。从通货膨胀的角度看,由于文人阶层一般不接触生产经营活动,长期依赖货币形式的薪水生活,当物价上涨时,其收入无法自然“水涨船高”,因此成为受冲击最大的阶层。历史上作为四民之首的“士”,在抗战时期沦落到与底层人民相同甚至更悲惨的生活境况中,精神上所受的冲击是极大的。②参见严海建《抗战后期的通货膨胀与大后方知识分子的转变——以大后方的教授学者群体为论述中心》,《重庆社会科学》2006年第8期。因抗战受穷的文人,面对因抗战而求富的群体,心中有着强烈的不满,是再正常不过的了。《淘金记》以通货膨胀为情节动力,所讲的又正是人们在抗战中求富的故事,戳中了同时代评论者的敏感点,因而承受着强大的道德压力。其实细究起来,《淘金记》的故事谈不上“阴暗”或“黑暗”,虽说白酱丹行事阴险狡诈、龙哥和林么长子大耍流氓做派,最后不也通通没有得逞?既然“阴暗”的人最终失败,整个故事又有何“阴暗”可言?可行的解释是,评论者对故事的氛围——也就是那通货膨胀的大环境感到“阴暗”。这与其说是小说的“阴暗”,倒不如说是小说激发了他们日常生活中的阴暗体验。
《淘金记》所写,并不止于“乡土-地域文化”层面的民间争斗,它真正的主角,是通货膨胀。这么说,难免给人故作惊人之语的感觉。通货膨胀是社会现象之下的深层次经济问题,是个抽象概念,映射在战时生活中只是阳光、空气一般的存在,作者何以能把握这样的存在,它又如何能成为小说的“主角”?或许,我们不必如《淘金记》的同时代人那样,过于关注小说中的人物和事件、“黏住和局限在现实里”③卞之琳:《读沙汀〈淘金记〉》,《文哨》第1卷第2期,1945年7月。,不妨搬出几年后在地球另一端问世的《鼠疫》作对照。我们看加缪的《鼠疫》,难道仅仅满足于奥兰城中人们抗击鼠疫的英勇行动吗?《鼠疫》的主角不是里厄、格鲁、科塔尔,而就是“鼠疫”本身,《鼠疫》写的是“鼠疫”的氛围,以及人们与“鼠疫”的互动关系。当然,这并不是说《淘金记》就是一部现代主义小说,而是说,它不是仅仅满足于塑造典型人物形象的现实主义小说,它也如《鼠疫》一般,试图表现某种超越故事表象的存在、某种环境和氛围。这里,我们还可以联系沙汀在《淘金记》创作过程中所写的短篇《三斗小麦》(1942)来看。《三斗小麦》基于与《淘金记》相近的生活材料写成,可称为某种意义上的“伴随文本”。小说讲了刘述之为还赌债,在是否卖掉囤积的三斗小麦问题上与姐姐发生冲突又和好的故事。刘述之受不了又离不开那“长姐如母”的羁绊,可以说就是《淘金记》中何人种与何寡母关系的翻版。但《三斗小麦》并非观照家庭关系的小说,最后姐弟俩的和好完全是因为粮食价格的数倍上涨,让姐姐家长式的霸道作风获得了被经济利益验证的正当性。如果只看《三斗小麦》人物层面的故事,会觉得平淡乏味,但如果理解这部小说真正的主宰者是通货膨胀,看出作者是在以小见大地对时代进行“写意”,其艺术感染力便增加了。以《三斗小麦》观《淘金记》,《淘金记》的价值也不仅在那些表面的人事,而在发现了作为氛围和环境的经济主体——通货膨胀。
1980年代,沙汀在回忆录中写道:
茅公对我讲述的当时四川一些社会现象,倒相当感兴趣。我记得,我曾向他摆谈过这样一个故事:由于物价不断上涨,一位略有存款的财主,眼疾手快,赶紧把它拿去买了一箱洋钉囤积起来。很快,洋钉一再涨价,他就把这箱洋钉拿到一家银行作压,借了一笔较大的款项,买了两箱洋钉。一转眼,洋钉价钱又上涨了,于是他又拿自己囤积的洋钉去抵押借款,抢购到更多洋钉。而如此循环往复下去,两三年来,他大发“国难财”,变成暴发户了。茅公听罢哈哈大笑,随即摸来个小本子,把它记上。我不知道这个小故事他后来利用没有,但它却是我尔后写作《淘金记》的因由之一。①沙汀:《皖南事变前后——四十年代在国统区的生活概述之一(节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6年第1期。
茅盾的“相当感兴趣”,显示了社会剖析派作家的敏锐,在1941年初,他将沙汀所讲的这个故事写进散文《“雾重庆”拾零》。同是社会剖析派出身的沙汀,在战时虽长期身居边缘地带,也敏锐地感觉到了从潘多拉魔盒中被放出的那看不见摸不着的现代怪物。正如风的被看见只能通过树的被弯曲,沙汀看似在写北斗镇战时生活中的趣事,实则将那抽象的现代怪物用文学显形出来。
二 “经济人”与反讽
“作者却仅仅走到现象为止,在现象底结构上拨弄着他底人物”①冰菱:《〈淘金记〉》,《希望》第1卷第4期,1946年4月。,这是路翎在《淘金记》问世之初写下的印象。这篇有名的批评文章为《淘金记》戴上“客观主义”的帽子,但路翎对小说人物的感觉却是敏锐的,《淘金记》中的人物,似乎受着作者的“拨弄”。卞之琳对此也有同感:“他们的心机复杂得简直不下于道格拉斯飞机厂里的新机器,而得心应手的作者,却跟高悬在这些可恶的可怜虫上边的一个命运似的,稳稳的作了他们的主人。”②卞之琳:《读沙汀〈淘金记〉》,《文哨》第1卷第2期,1945年7月。这么说当然没错,但更准确的说法应是:作者所发现并显形的通货膨胀,像拨弄棋子一样拨弄着小说中的人。
由于小说聚焦于显形通货膨胀这一经济主体,可以说,《淘金记》中并没有作为主体的“人”,只有被经济主体摆布的“人们”。比起白酱丹、林么长子、龙哥、何寡母这些显而易见的人物,《淘金记》的叙述者还常常使用一个不是人物的人物——“人们”。
小说这样开篇:“一九三九年冬天。早晨一到,整个市镇的生活又开始了。人们已经从被窝里钻了出来。”③沙汀:《淘金记》,第1页。如果说从被窝里钻出来的“人们”是小说的第一个人物,当然有些荒唐,这也许只是一段平平无奇的背景描写而已。但“人们”在整个文本中出现了39次④根据本文所用的《淘金记》1947年沪版统计而来。本统计已排除了无效的“客人们”“女人们”等词。因是人工统计,或有不准确之处,但大致可以看出,《淘金记》作为全文仅十万字出头的小说,确实多次出现了代表北斗镇共同体的“人们”一词。之多,发表着许多有趣的看法,又与恶性通货膨胀息息相关,这就值得细细观察一番了。这里试举三例:
淘金的,是“人们”——
最近的一个时期始于七七前后。起初的措词也一样,因为刚才遭了荒年,但随着抗战的开展,矿洞增多,最显著的是黄金价格的高涨,旧的借口讲起来要红脸了。同时,人们也似乎变质朴了,他们坦然地流露出对于黄金本身的迷恋。但却又立刻来了新的口实:他们是开发资源,是在抗战建国了。他们于是大挖特挖。①沙汀:《淘金记》,第14、234、316页。
做生意的,也是“人们”——
但是时间是一件治疗任何心病的妙药,到了腊月间,不管是局内人,局外人,大家都似乎把烧箕背的事件丢冷淡了。而且,一切生意又都那么好做,仿佛变戏法一样,任何东西过一道手就涨价了,所以人们全都沉没在各种各样买卖里面,财富和法币的追求里面,一切闲事都被遗忘所淹没了。②沙汀:《淘金记》,第14、234、316页。
评议北斗镇时事的,也是“人们”——
他们都暂时搁下宝经牌经,买卖上的商讨以及对于生的怨嗟,专为这个新鲜的话题而努力了,他们打开记忆之门,而且非常勇敢的钻进所有当事人的灵魂里去,以便翻检对于自己的论断有利的材料。就连举人老爷也被提谈到了。一直到第三天上,所有的舌头上才又转动着别的新的话题。因为现在并非平时,生活太紧张了,变动也太快了,太大意了就会逃走一笔大的利益,或者给生活添上窟窿。所以有钱的都要忙钱,没有钱的那就更不必说了。那些还在口上心上念念难忘的,只有少数懒虫,以及有着特别利害关系的人们。③沙汀:《淘金记》,第14、234、316页。
“人们”自然是茶馆里的人们,由于市镇上的人几乎都去茶馆,也就代表了北斗镇共同体。“人们”的看法、“人们”的感受,又展示了北斗镇共同体在通货膨胀环境中的种种体验。不管是白酱丹、林么长子还是何寡母、何人种,都是“人们”中的一员。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淘金记》中,“人们”常常出现在章节靠前的位置,“人们”出场后,才有林么长子、白酱丹的空间,他们似乎是从“人们”中显影出来,既是“人们”的谈论对象,也是“人们”的具象化。总之,“人们”就是沙汀在1942年的信中谈到的“一批士绅”①沙汀:《关于〈淘金记〉的通信》,《沙汀文集》第七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59、60、59页。和“一批恶棍”②沙汀:《关于〈淘金记〉的通信》,《沙汀文集》第七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59、60、59页。。但对故事中的市镇而言,却不是“一批”,而是大多数,如沙汀所说,“抗战在后方把人们的私欲,更扇旺了”③沙汀:《关于〈淘金记〉的通信》,《沙汀文集》第七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59、60、59页。。“人们”是被通货膨胀摆布的人们,“人们”的行动和感受显示了通货膨胀的无处不在。
当然,大篇幅地呈现“人们”在《淘金记》中的重要性,并不是说小说的人物形象塑造不鲜活、不成功,而是说,被塑造的白酱丹、林么长子等人不是充满主体性的人,而只是典型的“经济人”。“经济人”是一种被简化的人,古典经济学得以成立,就是基于“经济人假设”。“经济人”被假设为理性的、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每当环境的“激励”有所改变,“经济人”就会运用理性调整自己的行为。白酱丹、林么长子还有市镇上那些做着各种生意、追逐通胀浪潮的人们,就是典型的“经济人”。龙哥、彭胖等人因为粮价上涨而放弃到手的烧箕背开采权、造成白酱丹功亏一篑,在袍哥的江湖伦理中,可谓是背信弃义的行为,但从经济学角度看,却是典型的“经济人”决策。而看上去为了“祖坟”这一乡土文化符号坚决对抗经济利益的何寡母,实则也是因为迷信“发坟”,认为破坏了风水,家道便会中落。因此烧箕背之争是典型的实利之争,没有太多非理性、信仰层面的东西。“经济人”的行为具有可预见性,只要外部环境的“激励”发生变化,人自然就随之而动。《淘金记》中的人们,只是附着在通货膨胀上的一种存在,物价怎么变,他们的行为就随之改变。正因为这种极高的可预见性,“经济人”谈不上自由意志和主体性,如果人活成了彻底的“经济人”,那就是不完整的人。套用苏格拉底解析人性的“激情、理性、欲望”古典三分法④关于“激情、理性、欲望”的人性古典三分法,参见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56~176页。,“经济人”就是缺失了“激情”、只剩下理性和欲望的人。在《淘金记》中,主要人物的命名方式也颇有考究。从角力的三方看,白酱丹是一味烂药之名,隐喻性地替代了白三老爷的本名,林么长子和何寡母的称呼则是身材(“长子”即四川方言中的高个子)和身份的提喻。三方最重要的人物连本名都隐而不现,喻示了其主体性的残缺。唯一以本名出场的重要人物是何人种,但这名字可谓是反讽——何人种懦弱无能,长期被母亲关在家里抽大烟,没有任何做决定的自由,既难称人,也没有种。
由于通货膨胀的强势在场和人物主体性的残缺,这部看上去十分写实的小说,具有了一定的现代主义色彩,它不仅是在讲述北斗镇的故事,也在看似冷静的叙述态度中后退一步以观全貌,试图摹写现代经济紊乱中独特的生存状态和困境。如果说,“用另一种囚禁状况表现某种囚禁状况”的《鼠疫》以隐喻为核心表意方式,反讽(irony)则是《淘金记》中值得注意的表意方式。
自然,《淘金记》中的人们是主体性残缺又缺乏道德的,套用诺思罗普·弗莱在《批评的解剖》中的划分方式,无疑是一部反讽型的作品。但本文所关注的反讽并不止于语句修辞层面,而是关于整部作品表意机制层面的反讽,即赵毅衡所称的“大局面反讽”①赵毅衡:《反讽:表意形式的演化与新生》,《文艺研究》2011年第1期。。吴晓东曾精彩地论述过骆宾基《北望园的春天》中的反讽——“它不仅仅是叙事的姿态和调子,还与作者的战时认知和体察世界的方式相关联,也是一种认知方式和美学态度,最终有望生成一种与战时文化语境相适应的小说美学”②吴晓东:《战时文化语境与20世纪40年代小说的反讽模式——以骆宾基的〈北望园的春天〉为中心》,《文艺研究》2017年第7期。,这也是从整部作品的表意机制层面讲的。作为同时期作品,《淘金记》并没有《北望园的春天》那样独特的不可靠叙述者和弥漫全篇的意义空无感,它的反讽是因显形通货膨胀而生。
抗战时期大后方的通货膨胀并非古已有之的社会现象,而是基于现代信用货币体系的现代怪物。在传统社会中,虽也有王朝“行钞”(即发行纸币)以汲取社会资源,但毕竟受到贵金属货币的牵制,古代纸币也多能与金银兑现。但1935年改革之后的法币,是一种由国家信用担保的、不可与金银兑现的纸币,一旦管理不善,造成的就是剧烈、迅速、难以想象的现代灾难。如果说剧烈变动的速度是现代性的一个特征,恶性通货膨胀及其连带反应就体现了这种现代速度推演到极端后的情况,用小说最后一章开头的话来说,“那速度,用句乡下人的话说,是套起草鞋也赶不上的”,“其间的变动,却颇相当于我们祖父辈一生的经历”。①沙汀:《淘金记》,第366页。说的正是一种典型的现代体验。复杂的现代体验适合以反讽来表达,因为反讽最基本的特征是表面意义和深层意义的背离,“是思想复杂性的标志,是对任何简单化的嘲弄”②赵毅衡:《反讽:表意形式的演化与新生》,《文艺研究》2011年第1期。。恶性通货膨胀的现代速度,冲击着处于边缘地带的北斗镇,产生了复杂的现代现象,写实的《淘金记》因之而生出反讽,主要体现在以下情节中:
其一体现在喜剧性的结局上。在烧箕背金矿的开发问题上,白酱丹与何寡母斗智斗勇,“谋略”堪谓高明。但这一切努力都被证明是白费,白酱丹的“谋略”完全败给了不讲理的通货膨胀环境。此后,他也做上了不必动脑筋的囤积生意,倒是小有收获。白酱丹可谓是书中最“机智”的人,却因“机智”而失败,因放弃“机智”、随大流而成功。白酱丹被戏耍是一场喜剧,而书中的人物几乎都在小说中得偿所愿,更是皆大欢喜。不但市镇上的“人们”在囤积中获得了极大收益,即使是佃农们,在何寡母看来也是“每个人拏出来就是五元十元的票子,比我们这些人还漂亮”③沙汀:《淘金记》,第100页。。这虽然有出自地主眼光的夸张成分,但也确实显示了粮价上涨暂时改善了贫苦农民生活的经济史事实。表面上看来,小说中充满着喜庆气氛,但背后映射出的却是通货膨胀更趋严重的社会形势,这就是“阴暗的气息”。
其二是挖祖坟事件在文化意义上体现出的反讽。杨义曾经敏锐地指出,“《淘金记》写的是现世的黄金追逐对祖宗鬼魂崇拜的欺凌和侵蚀”④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69页。。确实,争夺烧箕背事件的实质是现代性对封建传统的冲击。在第一回合中,何寡母请求叶二大爷以袍哥议事的方式暂时守卫了祖坟,可谓是以传统对抗现代性。第二回合,白酱丹使出去县上打官司的手段、邀请国家政权以“抗战建国”的名义介入,终于压倒了民间的“迷信”。表面上看,通货膨胀这一现代怪物冲击着乡土社会,传统观念仓促应战,最终不敌。但故事发展到最后,从深层意义上说,又是通货膨胀守卫了何家祖坟,现代怪物守卫了传统。
其三是对“抗战建国”的反讽。小说一开头就写到,以“抗战建国”为名,北斗镇的人们在金价高涨的形势下大肆淘金。后来,白酱丹在县上的官司之所以能打赢,也是借了“抗战建国”之名。乍看起来,这种借用是不光彩的,但从深层意义上说,对抗战时期缺少黄金储备的中国而言,开发金矿又确实是典型的“抗战建国”之举,这并不因动机而转移。白酱丹、林么长子试图开发烧箕背金矿的行为虽动机不纯,但用古典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的话说,是受到“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从而实现了私利与公益的高度统一。表面上看,白酱丹、林么长子是不顾抗战大局、只顾个人私利的小人,但从深层意义上说,其试图打破“迷信”、开采金矿,恰恰又是在为“抗战建国”作贡献。这样的“实业救国”最后失败了,从某种意义上说,白酱丹竟成了吴荪甫式的悲剧英雄,这也难怪当时有论者读出了这样的意味:“故事中清楚地提示了抗战过程中整个工业生产减缩的严重现象。”①鹒溪:《〈淘金记〉读后》,《抗战文艺》第9卷第1、2期合刊,1944年2月。
整部作品表意机制层面的反讽造成的意义复杂化,并不意味着叙述者面对通货膨胀的暧昧态度,它只是通货膨胀成为小说“主角”的结果。沙汀以丰富的经验、敏锐的感觉,将通货膨胀所引起的现代乱象和现代体验凝聚在文本中,自然形成了意义的复杂化。《淘金记》并非典型的现代主义小说,但反讽的存在使其或多或少带上了现代主义色彩,这也是其问世之初在接受场域中遭遇那小小“不适”的原因之一。不过,《淘金记》反讽的表意方式在深层意义上又蕴含着强烈的批判性,它呈现了主体性残缺的“经济人”被作为主体的通货膨胀所摆布的状态,虽然故事发生在“前现代”的北斗镇,却又像极了现代经济紊乱中人的普遍境遇。从更现实的层面看,它还体现出对地方“独立王国”与抗战时代格格不入的深刻忧虑。
三 在地方呼唤“中国”
《淘金记》中的一个看上去与情节主线无关的小情节,隐含着小说的政治关切。故事中,1940年新年,北斗镇照例应该举办一些玩龙舞狮的传统民俗活动,但这毕竟又属于娱乐消遣,似乎与抗战时期一切从简的时代氛围不符。这时,白酱丹想出了变通之计:
他提议龙灯可以不玩,至于狮子,倘若改成麒麟,那就丝毫没问题了。这是一个旧瓶子装新酒的办法。太阳不就是日本么?那么狮子若果变成麒麟,这就不是娱乐,而是宣传抗战的好东西了。这不仅获得了委员们的承认,便是龙哥以及别的大绅也用少有的欢欣接受了它,放了比往年更多的花和鞭炮。①沙汀:《淘金记》,文化生活出版社1947年版,第236、83、130页。
自然,这一插曲可以帮助塑造白酱丹诡计多端的性格,但这个“狮子变麒麟”的故事又正是抗战时期北斗镇存在状态的寓言。北斗镇,一个川西小镇,处于中国人文地理中十分边缘的地带,仿佛一个雷打不动、油盐不进的“独立王国”,即便是相距并不遥远的省会,也无法管辖它,如一位茶客所言,“成都是成都,它还管不到北斗镇来!”②沙汀:《淘金记》,文化生活出版社1947年版,第236、83、130页。全面抗战爆发,国民政府内迁,带来的影响无非是物价飞涨刺激了北斗镇“人们”的神经。抗战的时代浪潮传递到这边地,不过是“狮子变麒麟”“旧瓶装新酒”,什么也没有改变——那象征着传统秩序的何家祖坟虽然受到威胁,最终仍安然无恙。当然,正如何家祖坟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被威胁,通货膨胀作为独特的现代现象、法币作为国家经济现代性的象征,也似乎要冲击改变那独立王国的种种秩序,将其与国民政府联系起来。但最终,新的经济秩序融合进了旧有的地方秩序,“夜壶还是夜壶”③沙汀:《淘金记》,文化生活出版社1947年版,第236、83、130页。。《淘金记》反讽、嘲弄着地方无法被有效整合进“现代中国”的现状,这种民族国家意识的彰显,使它成为典型的“抗战文学”。
对抗战时期的大后方而言,“抗战建国”是时代主潮。当然,如张中良先生所言,将“建国”理解为建构现代民族国家是“想当然”④张中良:《中国现代文学的民族国家问题》,《文学评论》2014年第4期。的,在当时的语境中,应是“建设国家”的意思。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建构现代民族国家不是抗战时期的一个重要问题。国民党政权,如易劳逸所论,“以当代西方的国家观念来衡量,国民党中国同同时代的欧洲国家相比,并不能算是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⑤易劳逸:《毁灭的种子:战争与革命中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9)》,王建朗、王贤知、贾维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这是因为国民政府对大后方省份的实际控制十分薄弱,一个与现代文学相关的例子是,龙云所控制的云南省屡次与重庆政府分庭抗礼,这才在对抗结构中造就了昆明知识分子和作家群体相对宽松的言论环境。在基层社会,国民党政权的控制力也十分不足。传统社会素来“皇权不下县”,1939年,国民党政权虽开始推行“新县制”,试图把政权延伸到县下的区,但实际效果却并不明显,“区政权本为国家权力的延伸和加强,其结果却成为土劣借以自豪自雄的工具”①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415页。。《淘金记》中的联保主任龙哥,自然就是这样一位土豪劣绅,他原是匪徒出身,权力的基础完全来自暴力。龙哥不是国民党官员的代表,而是一个“山大王”式的角色。在这个意义上,北斗镇与其说是国民党统治区域的代表,倒不如说是“国民党不能统治的区域”的代表。
《淘金记》之所以能被作为一部“乡土-地域文化”小说来读,也正是因为塑造了北斗镇这样与外部相区隔的文学空间。在这个独立王国里,袍哥主持着社会秩序,举人的后代已不再吃香、成为被争抢的肥肉,甚至袍哥内部还有鄙视链②在《淘金记》中,白酱丹作为破落绅士,是“绅粮班子”,对林么长子这样“赌棍或出身不明的人总多少感到一点厌恶”,但他又偏偏依靠着匪徒出身的龙哥而维持在镇上的地位。,真是自成体系。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版本中,作者曾作出几处修改,试图联结起北斗镇和国民党政权的关系,如1947年版第10页的“那个代表一个银行收买金子的委员”被改为“那个代表国家银行收买金子的委员”,第238页龙哥曾受过“社训”③“社训”是军阀刘湘主政四川时期所开办的面向基层政权参与者的训练班,与国民党关系不大。参见於笙陔《刘湘主川开办的“七训”》,《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36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被改为“到成都受过国民党一个月的训练”。这种事后联结北斗镇与国家政权的努力,恰恰证明了在初始的文本中,北斗镇是一个若即若离的存在。
《淘金记》的批判性不止指向白酱丹等人的利己之私,更指向地方不能被整合进民族国家有机体的地方之私。这种针对“私”的双重批判,触及了通货膨胀时代的新问题。1935年国民党政权所建立的法币体系,是具有进步性的现代民族国家经济整合机制,全面抗战时期的北斗镇能受到法币币值波动的影响,是其从经济上与现代国家和统一市场有了连接的标志。但正如前文所述,法币是由国家信用背书的信用货币,全面抗战中期通货膨胀转向恶性,法币剧烈贬值,事实上就是国家合法性的贬值。通货膨胀的无法控制,意味着政治衰败。因此,《淘金记》揭示出历史情境中严峻的问题:北斗镇被那纤细的法币纽带象征性地系在“现代中国”上,但又因币值的不断跌落,越来越回到国家不在场的自然状态。
通货膨胀状态给北斗镇“人们”带来的颇具现代意味的流动感、刺激、焦虑,已在《淘金记》中多处传达。严重的通货膨胀,表面上看起来繁荣了市场,实则破坏着市场规则,造成霍布斯所说的“人人相互为敌”①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94页。的状态。如前文所论,白酱丹试图组织开采金矿,若在正常的市场秩序中,本是将私利和公益结合的双赢之举。这种被市场造就的双赢,以及由此驱动的技术创新,正是近代以来世界经济能够持续增长的秘密。但恶性通货膨胀的持续压迫,最终取消了双赢的可能性。当物价持续上涨、货币持续贬值、市场秩序不复存在的时候,人们只得选择持有实物而非货币,于是货币信用进一步下降,通货膨胀更趋严重。在小说的结尾,龙哥、彭胖不愿拿出现金入股白酱丹组织的金矿开发,是因为他们要将现金换成能抵御通胀的粮食,通胀让曾经的合作伙伴分道扬镳。这揭示出大环境的残酷性:人们在囤积中看似是自保,实则是互害,但如果不囤积,就只能被害。在《淘金记》的结尾,每个人看似都获得了收益,但局外人一眼可知,这收益是虚幻的,随时会被物价的上涨再次淹没,而大环境已经到了崩盘的边缘。这正是敏锐的诗人卞之琳所读出的意味:
事实上,《淘金记》到临了也未尝不令人有出路之感,有如悲剧在叫人流了眼泪以后或者喜剧叫人笑出眼泪以后所给的朗静、轻松、健康、明白。一场乱搅在一起的人欲的全武行。不管胜者败者,由于连淘金也不行,远不如囤积别种更有关国计民生的东西更来得容易发财……大家走在自杀的路上,大势所趋,任他翻得多高,还是迟早都同归于尽。②卞之琳:《读沙汀〈淘金记〉》,《文哨》第1卷第2期,1945年7月。
卞之琳所说的“出路之感”,也许就是《淘金记》这部以通货膨胀为“主角”的小说所内蕴的政治关切:要结束通货膨胀造成的国家不在场的、“人人相互为敌”的自然状态。它从反面确认了能够维持经济秩序、保障人民生活的利维坦——真正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必要性,而这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除了推倒重来的革命,似乎别无他法。
沙汀对大后方通货膨胀的敏感及试图将其显形在小说中的努力,使《淘金记》成为一部独特的作品。小说对现代经济紊乱中生存体验的表达精细入微,揭示了人身处其中退化为“经济人”、丧失了主体性的境遇,也因精细写实现代乱象而使得整部作品呈现表意机制层面的反讽,带上一些现代主义色彩。在文化政治上,《淘金记》对通货膨胀状态中地方的整合问题表达了忧虑,内蕴着民族国家意识,这使它成为典型的抗战文学作品。由对通货膨胀中“人人相互为敌”的自然状态的展示,《淘金记》又从反面证实了革命以建立真正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必要性。这样的深层政治关切,使它并非如看上去那么“客观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