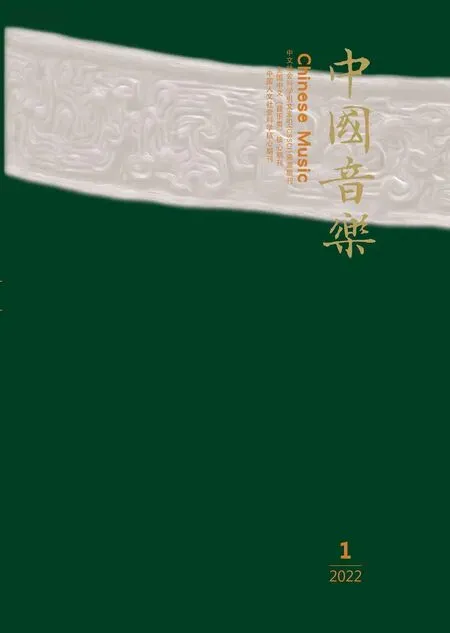旋律学建设笔谈
2022-11-16鲍元恺彭志敏姚恒璐周湘林
○ 鲍元恺 彭志敏 姚恒璐 周湘林
【召集人语】
王黎光教授:音乐创作是音乐文化发展的基石,总观当前的音乐创作,特别是在器乐创作中,把新技术的追求作为首要目标的现象仍然较为突出。殊不知在经过20世纪的新技术探索后,从世界范围看,音乐创作已经从技术追求转向注重内容表现与情感表达。如果回顾欧洲音乐创作的几个高峰,当时的作曲家正是在民族化、大众化与专业性、严肃性上获得了高度的统一。我们曾经创作出把艺术性和大众性很好地统一起来的经典作品,但这种审美追求由于20世纪80年代欧美新音乐的传入而没有得到继续夯实和发展。从科技发展到文明演化,“大道至简”几乎是通则,音乐创作同样遵循这个通则。我们需要将高深的技术,转化成老百姓爱听、爱唱(奏)的永流传的经典。
因此,我们有必要讨论音乐创作中的旋律观问题,更有必要研究如何把几千年来已经融入中国人艺术基因和审美血液中的音乐传统和旋律传统与当前的音乐创作结合起来。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建设基于中国音乐传统、彰显中华民族审美境界,弘扬中国艺术精神的旋律学。
30多年前,有中国学者提出,把旋律学作为“第五大件”来建设。继之,中国艺术研究院倡导并先后举办三次全国旋律学学术研讨会(1998、2000、2014)。这些讨论,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音乐界对旋律学研究与建设的重视。但就目前实际来看,旋律学研究与课程建设依然施施而行,进退无所。
有鉴于此,我召集了鲍元恺教授、彭志敏教授、姚恒璐教授、周湘林教授,共同对旋律学相关问题展开笔谈,期望以此推动旋律学建设。
修炼中国传统音乐的基本功
鲍元恺
民歌是世界上所有民族一代代口口相传的重要的民族文化符号,它以旋律的独特辩识度彰显着不同民族的音乐特征,同时,以高度的可塑性成为人类一切音乐形式的源头。
中国民歌在流传中陆续衍生出了戏曲音乐、曲艺音乐、歌舞曲以及民间的、文人的、宫廷的、宗教的器乐曲。它们与其他形式的传统艺术共生共存,相依相和,构成了我们独特的民族文化遗产。
从1990年开始,我分门别类地对这些传统音乐形式进行重新学习和再度创作,通过现代主流音乐形式,使这些古老旋律获得再生机能,成为一种活的文化形态,在同现代审美情趣的结合中,打开同世界文化隔绝的封闭状态,在文明更替的断层中获得新的生命。这项工作,其意义并不亚于我的个人“原创”。
1991年10月,我的《炎黄风情—中国民歌主题24首管弦乐曲》在天津首演。这部被听众赞为汉族民歌“清明上河图”的音乐画卷,地跨东西南北,情及悲愁喜乐,用绚丽的管弦乐色彩,描绘了炎黄子孙生老病死、婚丧嫁娶、春种秋收、悲欢离合的生活图景。30年来,通过中外乐团的频繁演出,通过飞速发展的各种媒体的高效传播,这部组曲风靡大江南北、海峡两岸,远播东西欧洲、南北美洲。从1995年起,经教育部批准,《炎黄风情》陆续进入了各地中小学音乐课堂。近年来,又以高校的美育通识课、中学的合唱合奏课和小学的音乐剧场课等形式深入不同层次的教育领域。外交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化和旅游部以及中国文联都将《炎黄风情》列为国家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项目。
我在《炎黄风情》里使用这些民歌旋律,不是作为器乐曲整体结构展开基础的“主题”或“素材”,而是完整地保留民歌旋律,并依照原歌词的故事、意境、情感,以严密的多声部结构和丰富的管弦乐色彩深化民歌旋律的表现力。因为,这部组曲的宗旨就是展示民歌。
《炎黄风情》同时使用了中国传统音乐的旋律和西方古典音乐的形式。面对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我的原则是“黑白分明,和而不同”,保持各自的特色和优势,“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中国旋律要尽可能“原汁原味”,西方形式要不怕“洋腔洋调”。“既要土到底,又要洋到家”—不能为了迁就西方音乐结构而破坏民歌旋律的醇厚韵味,也不能为了顺应中国传统旋律而破坏西方音乐的严密结构—东西方的优秀音乐都是“西施”,“金发碧眼”和“柳眉星眼”各有各的美。不要削足适履互相模仿,牺牲各自特点,把西施变成效颦的东施。
《炎黄风情》之后,我又以多部交响乐展现台湾的南管、北管和原住民民歌,京剧的丰富唱腔和河北梆子的苍凉曲调,流传久远的北方鼓曲、福建南音… …这些作品在听众中一次次引发强烈共鸣,原因就在于其中那些具有永恒魅力的古老旋律。
作曲家阿镗先生说:“音乐开始于旋律,精彩于不止有旋律,没落于没有旋律。”
我们的音乐学院作曲教学,本来就缺少旋律的课程设置。而能够为中国作曲家创作旋律提供营养的中国传统音乐课,大部分也从必修课变成了形同虚设的选修课甚至免修课。这是造成当前这一代作曲学子音乐创作旋律贫乏的直接原因之一。
为此,我希望我们的音乐学院切实把旋律创作重视起来,并且从“知其然”的感性认识入手,把中国民歌、戏曲音乐、曲艺音乐和传统器乐曲四项,列为当下音乐学院作曲系至少同西方作曲“四大件”同等重要的课程。同时,在音乐基础(乐理和视唱练耳)课中逐步增加中国传统音乐的内容。
我曾经说过:“旋律靠天赋,和声靠感觉,配器靠经验,对位靠功力。”事实上,写作旋律的天赋,也需要功力的修炼、感觉的培养和经验的积累。而写作展现中华民族精神气质的旋律,尤其需要扎扎实实地修炼中国传统音乐的基本功。
“叫我如何不想她”
彭志敏
汉语旋律一词,也作曲调,西人呼为“麦落地”(melody)。虽其音形义俱全,却不详其词源所出。结构类属动宾,旋者,转也、回也、轮也、变也,一如旋风、旋涡、旋舞、旋宫者是;律者,音高也、音级也。联而缀之,动使于宾,遂有“曲折波动的音高”之意。于是旋律被解释为单个音高横向运动的“曲调线”,至于谱写旋律之工,亦即视为“作曲”(犹且不能“作直”)。旋律一物,绵长隽永,孰能不爱?旋律一词,简重深邃,孰能尽悉?既有论述旋律之书、探究旋律之文、讲授旋律之课、研讨旋律之会,更有专门的旋律之学,重且众矣!然其究竟何谓、何意、何为、何以?鞭辟入里者似不甚多。圣人曰:“必也正名乎!”是以,“叫我如何不想她”!
音乐艺术的时间性,决定了音乐作品的一度性。音乐作品之过程呈现,一是皆以不可停滞、不可逆转、不可中断,唯有前行。而若见诸形态,则有一音接一音、一句接一句、一条接一条、一组接一组的旋律线、旋律群、旋律层、旋律网,绵绵无尽、环环相扣、步步紧跟、滔滔不绝、径直向前。无论民间的歌曲舞曲、乐队的管弦交响,无论古代的琴歌琴曲、当今的摇滚爵士,无论西方的多声音乐、中国的单声曲调,其皆如是,概莫能外。但凡音乐者,孰能无视旋律?孰能无有旋律、不用旋律、弃绝旋律?若将旋律比诸自然,则其如同江河;比诸生命,则其如同血脉;比诸纺织,则其如同经纬;比诸交通,则其如同阡陌。美好的旋律,美丽的线条,美妙地奏鸣,美声地放歌,音乐遂能过程绵延、内蕴充溢、结构生成、魅力绽放。试以问之:音乐中有哪种成分能够独立地匹敌于旋律?有哪种要素能够径直地媲美于旋律?有哪种手段能够超然于旋律之上?有哪种效果能够胜出于旋律之右?苏子曰:“何为其然也?”是以,“叫我如何不想她”!
旋律曾被公认为“音乐的灵魂”。这就意味着,音乐如果没有旋律,就等于没有了思想、没有了灵魂、没有了精神,而只是一副皮囊、一具骷髅、一架空壳。旋律又被比作“和声的表层”,这就意味着,多声音乐的外声部(乃至各声部)进行或构成,如果缺少独立的声部感,缺少独特的旋律性,其和声效果可能会因之失色(故有专为强化声部线性感的对位化和声),即便是一字一音而同节奏进行的宗教经文合唱,或用于训练学生写作的四部和声习题亦然。旋律还被看作“主题的载体”,这就意味着,中外优秀音乐作品的优秀音乐主题,很多都是旋律形式的。音乐作品依其主题而流传,作品主题则依其旋律而表现,旋律之于音乐作品的传远流送之功,亟而大者矣!是以,历史上的伟大作曲家没有不重视旋律者,历史上的伟大作曲家也没有无一两条优秀旋律而传世者。更遑论如柴可夫斯基、拉赫玛尼诺夫、俄罗斯“强力集团”成员、东欧民族乐派大师、肖斯塔科维奇、哈恰图良、斯特拉文斯基等以旋律而成其名作、显其个性、传之于世者。不妨想想贝多芬《田园交响曲》第一乐章贯穿始终的简朴旋律、《第九交响曲》末乐章把民歌颂歌进行曲融为一体的合唱旋律;想想柴可夫斯基《罗密欧与朱丽叶》响遏行云、震撼人心的爱情旋律,《悲怆交响曲》第一乐章协和安详、神圣崇高的副部旋律;想想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第一乐章浩瀚如黑海之波的主部旋律、末乐章宽广如辽阔蓝天的副部旋律;想想肖斯塔科维奇《第七交响曲》第一乐章棱角分明的中部旋律、贝尔格《小提琴协奏曲》用十二音描述夭折少女的主题旋律;再想想《黄河颂》一唱三叹的颂歌旋律、《保卫黄河》精神抖擞的卡农旋律、《游击队歌》俏皮灵活的进行曲旋律、《梁山伯与祝英台》家喻户晓的越剧旋律… …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平心而论,面对如此美妙绝伦的音乐主题,面对如此伟大不朽的迷人旋律,孰能不为之动容、脱帽、折腰、倾倒?欧阳公曰:“胡为而来哉?”是以,“叫我如何不想她”!
进入20世纪以来,西方新音乐的强劲革命和巨大浪潮,摧枯拉朽般地涤荡了共性时期音乐的规规矩矩和条条框框,新音乐逐渐而彻底地放弃了传统音乐的调式、调性、和声、节奏、协和、平衡、主题,也放弃了旋律。新音乐由此进驻了“可怕的盲区”:热衷于非音级音程而音色音响的、非横向连续而断裂发散的、非调性明确而无中心凝聚的、非动机贯穿而非线性点描的音乐比比皆是、占据上峰,效果虽是别开生面、新颖奇异、闻所未闻,但因缺少可聆听、可歌唱、可记忆的旋律声部,缺少动心、感人、煽情的主题进行,一如“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其结果是:作曲家虽乐此不疲地产出,理论家虽不辞辛劳地解析,表演家也不遗余力地奏唱,听众却绝无二致、毫不留情地远离、拒斥、失忆于它们。无乃遗憾至极!须得说明一下,我本人并不反对为创作而创新的任何思想观念和技术方法,因我本人就是新音乐的积极参与者;我所强调的意思是,不要为求新求异而忘记了音乐的基本功能,异化了创新的本来意义。新时代、新发展、新境况、新要求,无疑会有新观念、新语言、新探索、新发现。如若真是为了音乐艺术、为了音乐效果、为了音乐传播和受众,我们的创新求异又何必要以牺牲旋律、牺牲音响、牺牲效果、牺牲受众为代价呢?念昔日之旋律,观旋律之今日,屈子曰:“悲莫悲兮生别离!”幸有王黎光者发动了今次旋律学建设笔谈。是以,“叫我如何不想她”!
旋律学的创建应以音乐风格为引领
姚恒璐
作曲家们常说:旋律是灵感的产物,教学中只能依靠启发,而无法像和声学那样按照某些既定的规则去教。之所以有这样的看法,是因为一旦旋律按照数学般的量化,顾及比例、结构的设计等一系列理性操作,对于创作中感性的启迪、灵活的发挥都会带来不同程度的损失。这大概也是历史上多数论述旋律的理论著作普遍没有得到作曲家们持续、积极回应的原因吧。
东西方对于旋律的认识是截然不同的。从毕达哥拉斯的数理原则中产生的历代艺术之美,从来都是以张扬理性见长的。即使这样,旋律在西方也没有得到如同和声学理论那般的理性重视,因为在西方音乐中“旋律来自于和声”的观念根深蒂固,旋律向来都被看作多声部组织中的附属品。再者,自16世纪功能和声理论问世以来,从诸多教会中古调式中提炼出了“科学的”大小调式体系,调式归类的简化更加强了对这一观念的实践准则。这说明,尽管旋律的教学还是需要某些理论作为作曲实践的指导,但需慎重,原则就是不能因为有了旋律的理论却制约了创作的灵性。旋律在作曲中具有特殊地位,就连西方人的潜意识中都将它归结于多声部理性控制下的“非理性”产物。
中国音乐中的旋律存在着与西方个性不同的因果关系,从各种民族调式和声教材上,我们可以看到频繁出现的一个术语“纵合性五声和弦”,其目的就在于提醒人们:中国民族音乐中的“和声来源于旋律”的观点,取自与西方音乐相反的视角。在中国民族旋律的研究中,“旋法”与“核心音调”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这种独特的研究分类也正是音乐创作中的核心原则。即使是采用同样的七声调式(如七声自然大调式与七声清乐宫调式),由于调式音阶音内部走向习惯的不同,产生出“旋法”上的明显差异,使得“同样的音阶结构样式”产生出“不同的音乐风格品味”。如此看来,我们在旋律学的研究中,一定不能回避音乐风格问题,这是音乐艺术审美的根蒂与要义。解决的办法就需按照中西音乐调式内在规律的不同,去设置不同的研究方法,实践不同的创作结果。
尽管“旋律学”的构建离不开“形态分析”的理性运作,除了单纯旋律线的剖析外,离不开对音乐作品中音阶、音列、音程的种种分析。分析的过程构成不仅反映了“理性因素”,如音程关系构成的不同、音阶音数目的不同、音列组合的不同,更重要的还在于运用音乐的传统构成—调式,来看待创作的结果,即,对音乐生态、音乐风格的取舍,体会截然不同的音乐风格感受。在我国,除了最常采用的五声、七声调式之外,民族调式还有三声、四声、六声、八声、九声(与西方序列组织原则相似的3—9个音),加上音阶中“清、雅、燕”偏音的介入,使得中国民族调式呈现出多彩性、多样化的组织形式。自元代以来,很多理论上已知的六、八、九声调式音阶,清、雅、燕音阶,还有诸如“同均三宫”“唐燕乐二十八调”等曾经流行过的音乐理论和作曲方法,由于极度缺乏创作实践的支持,而逐渐“失传”、无人问津。在20世纪50年代、80年代,全国各地各种民歌集成的“选拔、编辑”工作中,将很多在音乐进行中颇有调式特点的民歌、戏曲、舞蹈音乐及其曲牌淘汰出局,理由就是不够“大众化”“不好听”“不好唱”。这种“主观、任意”的取舍,完全没有专业创作的历史眼光。我们现在创作中所谓的“五声性音乐”,其实就剩下了五个骨干音,反复研究骨干音,理论自然会枯竭,连偏音都不敢用了、也不会用了,民族调式还有什么魅力可言?中国民族调式的特点全在于能否认识到“调式偏音”的价值,认识到“旋法”“核心音调”带来的风格导向。如果看不到这些本质问题,就会导致采用民族素材创作的专业水准越来越低,远远不如一千年前宋代姜夔自创的“自度曲”的水平—精心的音高设计、多色彩的调式风格。我们对七声音阶以外“调式偏音”的感受早就“退化”到可怜的地步了。另外,当我们学习西方现代音乐的种种作曲法时,也会感到十二音体系中的半音化根本代替不了五声性调式旋律中半音化的写作原则,两者间存在着语言表达、风格审美方面的矛盾和隔膜。简言之,西方音乐中的“外音”属于“调式之外”的扩充性半音化;中国音乐中的“偏音”则属于“调式内部”的色彩性半音化,两者间的音乐理论与作曲观念又具有本质差别。假如一切以西方作曲原则为准,终将会使本民族音乐中的固有风格损失殆尽。从单一旋律开始,这一矛盾与差异就已经凸显出来,更不要说多声部写作中的诸多问题了。
审美是音乐教育中的核心问题,音乐审美的一个关键过程是聆听,音乐风格是通过聆听而获得的首要认知能力。音乐教学过程是开发旋律学学科的最前沿阵地,多年来我们缺乏的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旋律写作”课,它是旋律学学科建设中主要的实践阵地。旋律写作+形态分析=旋律学。“歌曲作法”不能代替“旋律写作”,前者受歌词、声乐的局限和制约;后者才能真正囊括旋律写作训练中出现的多种因素:声乐、器乐、有无歌词等。在拙作《作曲的基础训练》的第二章“旋律写作—韵律的升华”中,笔者曾经着力设计过旋律写作的过程。针对大部分作曲学生写旋律的短板,这一章(加上第一章“节奏与节拍—律动的奥秘”),几乎给大一作曲学生训练一个学期的时间。一条旋律可以训练学生的七个方面:1.旋律中调式调性的辨识(主要是民族调式的旋律写作);2.音列与音阶的互通(传统与现代风格的相互理解);3.旋律中节奏节拍的特征;4.以音程的关联为特征的旋律写作;5.旋律写作中的展开手法;6.原型主题旋律的装饰性(加花)写作;7.单一旋律线条中的音色配置(为特定乐器或人声写旋律)。
旋律学学科创建的目的不仅是一种音乐形态的研究,更是对一种“自然生态”下有机体的认识。从生态的角度去看待旋律学,主要是非欧洲、东方民族对待旋律的认识态度。从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与艺术观念出发,对从久远历史沿革中发展而来的民歌、戏曲、舞蹈、说唱音乐,向来给予重视的态度,就是对“原生态”艺术自然有机发展的重视。作曲家写作旋律的个体能力也是依据这种“自然生态”长期积累的结果:生活阅历与体验、形象思维的想象力、内心听觉的判断力,而不是靠多读了几本理论书就能够迅速提升的。这种认知观念反映在旋律学的建设中,中西方也存在意识上的巨大差异。只有在“科学+生态”的平衡与结合中,才能不偏废旋律生成中理性与感性各自参半的实际情况。这也对我们的研究方法提出了新的问题和新的考验,绝不能像看待功能和声那样,以为建立了某种体系就能解决创作问题那么简单直白。由于音乐风格的差异,中西方旋律中的构成方式、各自调式的组织特点一定要分开论述,便于在音乐创作、音乐表演的实践中,打破认识中的模糊界限、提升认知水平。
旋律随想
周湘林
人们普遍认为,旋律是音乐的灵魂,是音乐的首要要素,同时也是音乐创作中最为重要的表现方式之一。在我们珍藏的音乐记忆中,喷涌而出的往往是一段刻骨铭心的旋律,它似乎承载了生命中最珍贵的回忆、最美好的向往、最激情澎湃的岁月。这些流淌着的意味深长的旋律总是那样引人入胜,甚至使人不能自已,到了近乎于膜拜的境地。它为何如此隽永?又为何具有如此魔力?记得一位作曲家赴少数民族地区采风,听到一段奇妙的旋律后发出如此感慨:在这些天籁般的声音面前,作曲家变得苍白无力,束手无策!甚至一些理论家也认为,旋律是天才和灵感的产物,或许都到了无法教、无法学、更难以分析的地步。总之,旋律所蕴藏的独特魅力应该,或者说必将促使作曲家、理论家不断探究其奥秘和玄机,从而对我们的音乐创作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当然,在专业音乐创作中,旋律的“至尊”地位是在共性写作时期形成并得以彰显的。进入个性写作时期,音乐的表达方式如万花筒般呈现出不可遏制的多样性,噪音音乐、简约主义音乐,包括整体序列音乐、电子音乐、偶然音乐等在内的先锋派思潮,以及后来的复杂主义音乐、频谱音乐等,如雨后春笋般地展现在人们的音乐生活中,这些对人类音乐创作方式的探索同样弥足珍贵,并且也产生了诸多标志性的得到较为广泛认同的音乐作品。尽管音乐创作的思维和理念对每一位作曲家来说不尽相同,但是,塑造音乐形象、表达人类情感、体现文化特征等音乐创作的初衷应该是一致的。能够打败时间,穿过历史长河而留下的作品,一定具有极强的延展性与丰富性。喜爱噪音音乐的灵动巧妙、好奇音色音乐的造型衍变,与醉心于旋律的张弛有度、迷恋于旋律的刻骨铭心,二者之间并不矛盾。非此即彼,并不可取。作为音乐创作者,如何准确表达思想?如何使音乐作品与广大听众在情感上产生尽可能多的“共振”?恐怕是每一位作曲家无法回避的永恒命题。既然旋律是音乐中灵魂般的要素,具有挥之不去的强大魅力,我们又为什么要刻意拒绝它呢?看来,在个性写作时期,或者说我们即将超越个性写作到达一个崭新的音乐写作阶段,在专业创作领域一味“去旋律化”的大背景下,重拾旋律学研究这个课题尤为必要。
虽然旋律是“天才和灵感的产物”,但世界万物总是有规律可循。目前来看,关于旋律学相关方面的研究还尚显薄弱。20世纪50年代,我们引进了苏联玛采尔的《论旋律》,改革开放初期也翻译了匈牙利萨波奇·本采的《旋律史》,国内的沙汉昆教授在不同历史时期也刊印了《中国民歌的结构与旋法》《旋律发展的理论与应用》,以及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的《旋律写作教程》,旋律学学术研讨会也召开过几次,20世纪末还成立了旋律学研究会。然而,有关旋律学的研究成果并未形成体系,尤其在高等音乐院校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人才培养方面,关于旋律写作的理念及系统化的技术性训练更是呈现出放任自流的无序状态。虽然个别院校在本科招生及附中入学考试中设置了旋律写作的内容,但由于在入学后的教学计划中并未开设旋律写作的相关课程,致使该内容在作曲主课的教学过程中严重缺失。作曲专业的学生是否能写出一段令人信服的旋律,恐怕只能寄希望于他个人的灵性和造化了。这种窘迫的状态的确令我们这些从业者感到尴尬。因此,旋律写作的相关内容能否系统地纳入教学计划中,值得我们认真探讨。
音与意合,境与声化。完整的文化意义要强调生命力在艺术作品中的自然实现与自然演变。旋律的古朴似一杯清茶,浸润心脾;旋律的悠扬似一片秋叶,撩人乡思;旋律的绚丽似从天洒下的阳光,温暖并照见灵魂。人类对音乐有更多的祈盼,对美好音乐的需求永无止境。若安于现成、凝固之语言,艺术便会随之钝化。重拾音乐之本质,探索语言之更多可能,是真正的作曲家必然的追求。旋律的写作与研究有多种形式,希望未来会有更多旋律学的研究成果,从而使作曲家在创作美妙音乐的过程中得到更多的依靠和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