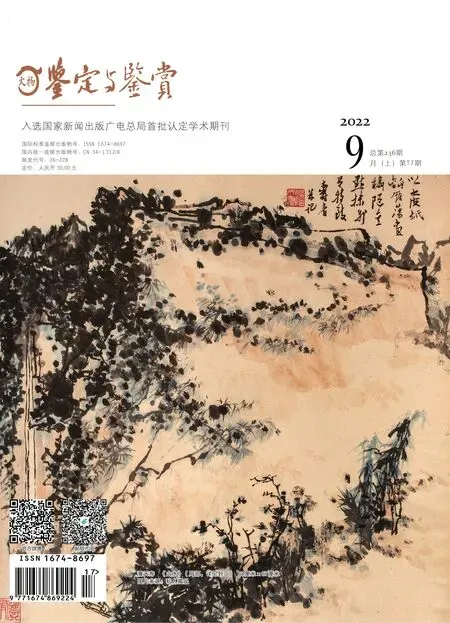琴江满族村民俗文化探析
2022-11-16刘薇
刘薇
(福建省革命历史纪念馆,福建 福州 350014)
0 引言
福州琴江满族村位于闽江下游南岸,距长乐城区4千米,距闽江口15千米,原是清代三江口水师旗营驻防地。三江口水师旗营设于清雍正六年(1728),是清代最早设立的四处八旗水师旗营之一,在成立的180余年里,承担起巡查、讨逆、缉私、戍边的职责,参与了清代所有与福建有关的重大海战。三江口水师旗营既有八旗水师的嫡系部队地位,又有着汉军八旗的尴尬身份;既具有北方地区满汉融合的风俗习惯,又不可避免地受到当地汉族文化的影响。琴江旗人是亦满亦汉的特殊族群,其独特的民俗文化是研究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的珍贵样本。
1 琴江满族村民俗文化形成的历史背景
清初,清廷曾试图以八旗水师为中心建立国家海防体系,福建作为海防前线,理所当然地成了最早的“试点”地。清雍正六年,雍正皇帝正式下旨在洋屿琴江建立三江口水师旗营,其主要职能除了明面上的训练八旗水师旗兵,查拿驻防地上下一带所有盗船、私盐船只外,还有就近监视位于其下游的闽安镇绿营水师。据《福州驻防志》记载,三江口水师旗营成立时,设有协领一员、佐领二员、防御二员、骁骑校六员、兵六百名。此六百兵丁由驻防福州的“四旗壮丁原食将军、总督、巡抚三标兵”三百名,驻防福州八旗中的闲散壮丁二百名及从海坛总兵、闽安副将标下挑选出的谙练水务的充当教习兵的兵丁一百名组成①。之后,原由绿营兵丁担任的教习兵又陆续被老四旗中的“旗下熟练之人”顶补。水师旗营存续期间,旗营额定兵员主要是由汉军八旗构成的。
三江口水师旗营驻防兵丁主要来自福州“老四旗”,祖籍大多在东北,其先人是跟随清军由东北到北京,再从北京南下,经山东、浙江,最后抵达福建的。琴江满族村保留至今的家谱及墓碑是琴江旗人祖籍地的重要证明。例如:琴江许氏家谱记载,其始祖于皇太极执政期间编入汉军镶白旗,后于康熙年间随平定三藩之乱的清军入闽;杨氏家谱载其远祖籍贯辽宁三韩,清初“从龙入关”,又随靖南王转战山东、广东,后驻防福州;琴江现存的墓碑大多刻着辽东、铁岭、三韩、长白、延陵等东北地区地名。皇太极把满洲的“民族特质”概括为骑射、国语、服饰。这些汉军八旗自入旗后便开始接受满洲化,但由于其长期行军、转战多地,满洲化程度不深,尽管最后长驻于福建,但依然保持着许多由祖籍东北地区带来的汉族的语言、风俗、习惯。
清朝统治者为保持驻防旗人的“纯洁性”,避免其沾染驻防地汉俗,采取了一系列防范措施。一是修筑“满城”,实行旗、民隔离政策。三江口水师旗营立营后便陆续建起了城墙,将驻地的衙门、兵房包围起来,形成一座“满城”,旗营中的所有官兵及其眷属一概接受军事化或准军事化管理。久而久之,“满城”内便成了一个封闭、独立且稳定的旗人社区,并开始形成其独特的民俗文化。二是禁止旗、民通婚。三江口水师旗营严格执行清政府制定的旗、民不通婚政策。因水师旗营与福州旗营有一定的距离,琴江旗人的婚配只好以城内通婚为主。三是推行“国语”。对满洲八旗而言,提倡“国语”的主要目的是防止其全盘汉化;对汉军八旗而言,推行“国语”则是对其进行持续满洲化,比如在雍正八年(1731年),福州将军就曾奏准,在水师旗营设清字外郎二名教授官兵满文、满话。然而,“国语”的学习使用始终只停留在官学,并未真正融入日常生活层面。乾隆中期以后,随着满语文逐渐从社会生活中退出,水师旗营中的“国语”学习也渐偃旗息鼓。水师旗营存续期间,“国语”始终未能成为旗营的主要语言,旗人之间主要使用一种以北方官话发音为基础的、被称为“旗下话”的语言。
封闭的“满城”、军事化的管理与不彻底的满洲化,在这些因素的交叉作用下,三江口水师旗营如同一座孤岛,在当地汉族文化包围中始终保持着独立性,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民俗文化。
辛亥革命后,水师旗营就地解散,驻防兵及眷属按原址居住,水师旗营转变为普通乡村聚落(当地称之为“营盘里”),立营一百余年形成的旗人社区、固定的生活模式开始被打破。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琴江人口因战乱大规模流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政策缘故,许多当地汉族居民搬入了营盘里,与旗人后裔混居、通婚,及至原水师旗营的城墙于“文化大革命”时期被拆除,营盘内外无形的族群隔离彻底消失。这一时期,原旗营留下的民俗文化已然发展成型,但也开始了因后继乏人而逐渐式微的过程。1979年,琴江旗人后裔以琴江的清代水师旗营驻防历史、保存良好的旗营建筑、特有的语言及风俗习惯等为由,经过不懈努力,使琴江被确立为满族村,这标志着琴江独特的民俗文化获得了官方认定。
2 琴江满族村保留至今的民俗文化
琴江满族村保留至今的民俗文化绝大部分形成于三江口水师旗营时期,辛亥革命后,“满城”内外开始频繁交流,并发展为混居生活,营盘里的传统民俗文化难免会受到当地汉族民俗文化的影响,但更多体现为吸纳与借鉴,并未发生本质变化。
2.1 语言
三江口水师旗营所使用的“旗下话”至今仍通行于琴江满族村内,通常被学界称为“洋屿话”,其具体形成时间已难考证。据村中老人回忆,至少于清朝末期,“旗下话”便已形成。在水师旗营存续期间,琴江旗人的日常交流只使用“旗下话”,因甚少与当地汉族居民接触,绝大部分旗人是听不懂福州话的,更遑论说了。一直到清朝灭亡、旗营解散,城内城外的交流开始频繁后,旗人后裔才慢慢开始学习、使用福州话,也是在这一时期,福州话的语音开始直接影响“旗下话”的语音,一些福州话词汇也开始出现在“旗下话”中,因此时“旗下话”已基本形成,虽有若干语音特征发生了变化,但基本保留了北方官话的核心特征,受影响有限。
方言是一定地域历史文化的产物,方言词语往往直接反映着某些历史事实和历史现象。从“旗下话”的常用词汇中,也能找到属于三江口水师旗营驻防兵丁的历史记忆。如“麻溜儿”(快点)、“旮旯廓”(角落)、“炕”(床)等,是典型的东北方言用语。又如“昨个儿”(昨天)、“明个儿”(明天)、“晌午顶”(中午)、“窝憋”(憋屈)、“好盖”(很好)、“二五眼”(形容很难看)等,与津京地区方言的用语相近。这些词汇的出现,极有可能是驻防旗兵的先人在跟随清军入关一路南下的过程中,在各驻防地生活时吸纳进自身语言体系的。
2.2 节日
琴江满族村保留至今的节日习俗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类型:
第一种是沿袭驻防旗兵的祖先由北方地区带来的节日习俗,一般与当地汉族习俗有明显区别,如“祭灶”。琴江旗人后裔至今仍然保留着由北方祖籍地带来的习俗,在农历十二月二十三日这一天举行“祭灶”仪式。本地汉族亦有“祭灶”的习俗,但时间定于农历十二月二十四。
第二种是旗人由北方带来的习俗,因受限于驻防地条件,不得不因地制宜有所改变,如“祭祖”。东北地区无论满汉,均十分重视祭祖,尤其是除夕祭祖,被称为“年祭”,是最隆重的,往往要在宗祠、家庙举行。然三江口水师旗营内未立宗祠,旗人祭祖只好在各自家中进行。又由于官兵远离祖籍无法上坟祭拜,据说过去有的人家办“年祭”时,要悬起纸糊的祠堂,密排灵位,有的人家只望空虚设香供,遥祭祖先。此外,如今的琴江满族村旗人后裔还延续着自中法马江海战以来一年一度的,在清明节和农历七月初三举办的抗法和历代戍边阵亡烈士公祭活动。
第三种是接受了驻防地习俗而形成的节日习俗,如“拗九节”。“拗九节”是福州地区独有的传统习俗。据村中老人回忆,水师旗营本没有这个节日,大约是在民初,旗、民开始通婚后,由外嫁的女儿和娶进的媳妇带回了“拗九”的习俗。
2.3 婚丧习俗
三江口水师旗营的婚丧习俗兼具满汉特色。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普遍开始移风易俗,琴江的旗人后裔也不例外,及至琴江满族村成立,旧有习俗已所剩无几了。因此,本部分介绍的主要是水师旗营存续期间及民国初期琴江的婚丧习俗。
琴江旗人只在旗营内部通婚,因此他们的婚俗保留了大量北方地区的习俗,较少受到本地婚俗的影响,体现了满汉两族的特色。琴江旗人的婚姻开始于“相亲”,相看合意后,依次进行“换帖”“合婚”“订婚”。订婚时双方须交换拜帖盒,内放男女双方发绺(此为旗营独有风俗,当地汉族没有)。水师旗营嫁女添箱一般是穿戴应用之物,也有彩丝缠制的装饰品,但最重要的是“三盆火”和“一身热”。“三盆火”指的是烛台、火盆、火笼(也有人家添加水烟袋、熨斗等凑作“五盆火”),“一身热”指的是棉衣、棉裤,这一迥异于当地汉族居民的习俗显然是由北方地区带来的。琴江旗人迎亲多用花轿,但与当地汉族居民在白天娶亲不同,旗人娶亲是在夜里。吉期前夜要“坐高堂”,清晨,迎亲队伍点着火把来到女方家门口接亲。新娘迎出花轿进大门时要先跨过一个木制的马鞍,这是满族的习俗,满族历来有“跨马鞍保平安”之说。又因水师旗营的旗人均是汉军八旗出身,比起满、蒙八旗,多了拜堂的礼节,即拜天地、拜祖宗、拜父母高堂,而后再夫妻对拜,但进入洞房后又遵循满族惯例,不允许闹洞房。
琴江旗人的丧葬习俗带有浓厚的思乡情怀。逝者在咽气之前要拆(蚊)帐,这是由于旗人在北方时原是不用蚊帐的,到南方地区后苦于蚊虫滋扰,不得不使用蚊帐,但是他们又认为蚊帐是“天罗地网”,蚊帐不拆,灵魂就不能离开,因此在逝者咽气之前必须拆帐。入殓前依满俗,由孝子用筷子夹着棉花蘸上净水之后,在死者的额头、下颚、眼圈、鼻尖等处擦拭,称为“开光”。旗人下葬的风俗也与当地汉人有较大差别。如出葬的时候一定要从营盘的北城门出,盖因旗人多数祖籍北方,他们虽然身在他乡,仍期盼魂归故里,便借送葬从北门出,并在北门举行最后一次祭拜,表示对祖籍地的思念和对叶落归根的渴望。
2.4 信仰
三江口水师旗营立营之时,有5座寺庙宇同时落成(天后庙、观音殿、五圣庙、两座毓麟宫)。这5座庙宇被称为水师旗营的“祖庙”。其后,随着旗营人口的增加,又陆续建起了不少寺庙,到民国年间,已有“神祠不下数十座”了。考察这些庙宇所代表的信仰可发现,琴江旗人信仰十分庞杂,除了玄天上帝这类由北方带来的,更多的是驻闽后,出于自身需要,入乡随俗地建立起来的。如信仰妈祖。旗人本无此信仰,但入闽后镇守海疆,为求人身平安、战事顺利,也信奉起妈祖。如信仰临水夫人。临水夫人是福建当地的妇幼保护神,水师旗营五“祖庙”中的两座毓麟宫供奉的就是临水夫人,殿内还同时供奉有许多送子娘娘,反映出琴江旗人对“多子多孙”的渴望。这与水师旗营独特的生活环境有关:对于驻防兵营而言,男丁是一家安身立命的根本,子嗣繁衍直接关系着一个家庭的兴衰。因此毓麟宫两百多年来香火不断,临水夫人在旗人后裔中也拥有广泛的信众。又如信仰西岳华山大帝。村中老人回忆,据传大约是在立营后不久,华山大帝的神像顺水漂至琴江,自此便有旗人开始供奉。关于华山大帝的传说中,说得最多的是他能消灾驱邪、医治百病,在医疗水平低下的过去,能医治难症且药到病除的神灵是最切中民众需要的,因此华山大帝渐渐成了旗人及其后裔心目中的保护神,被尊为“太保爷”。至今,一年一度的太保爷迎会都是琴江满族村最重要的活动之一。
2.5 文娱
除了看戏等较普遍的娱乐方式外,三江口水师旗营还有一项特别的传统文艺活动——“抬阁”。“抬阁”顾名思义,就是人们抬着一个用竹木或铁质材料扎制成的类似“小阁”的架子进行表演。三江口水师旗营的“抬阁”表演一般要在主架上再分上、中、下三架,于每架的分枝上安排固定不同的表演者。安装完成后,由四位彪形大汉抬着游街演出。三江口水师旗营的“抬阁”是旗人从祖籍地东北带来的,既保留了传统的表演形式,又在原来表演所用的东北小调的基础上吸收南音和闽曲,创作出更多的配乐,流传至今的尚有20余首抬阁乐曲,如完全保留北方调的《北调》、闽南调改编的《螃蟹歌》、福州调改编的《四大景》等。“抬阁”曲一般用“旗下话”演唱。据说,在清代,水师旗营的左、右翼各装有一台“抬阁”,一直到民国时,仍不断推出创新剧目,以不同街巷的名义安装表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抬阁”表演渐被人们遗忘,但近年来旗人后裔积极收集资料、整理复原,“抬阁”表演又得以再现,不但恢复了《哪吒闹海》《二度梅》《玉杯缘》《黛玉葬花》等传统剧目,还重新设计了《天女散花》等新节目,深受观众好评。
3 琴江满族村民俗文化的保留与延续
琴江旗人自先祖入旗开始,经历了不彻底的满洲化,后又不可避免地受到驻防地汉族的影响,这使琴江旗人的民俗文化既保有由北方带来的汉俗,又吸纳了满族习俗,同时还有当地汉族文化影响的痕迹,是典型的民族融合的产物。
3.1 民俗文化得以保留之原因
在清朝灭亡、三江口水师旗营解散后的近百年时间里,旗营的民俗文化却大体被保留了下来,这与旗营的历史背景、地理位置有密切关系。
首先,从地理位置上看,三江口水师旗营距福州城有一段距离,来往不便,居住条件和粮饷都不如福州旗营,却也因生活简朴,水师旗营的生活环境相对单纯,其间旗人反不像福州旗营的旗人那样轻易沾染恶习。由于始终保持着较高的战斗力,水师旗营成立后,参加了清代所有与福建有关的海战,立下累累战功,避免了如同期成立的天津水师旗营一般,因丧失战斗力而被清廷裁撤的命运。清亡后,远离城市繁华地段的琴江始终发展缓慢,旗营遗址受现代化进程影响相对较小,历经百年还能基本保持原有建筑格局,水师旗营传下的民俗文化也获得了相对稳定的“容器”。
其次,三江口水师旗营是和平解放的。在水师旗营存续期间,城墙之内的旗人不可务农、经商,因此与周边汉族居民并无实际利益冲突,反因需要从汉民处购买生活必需品而成为汉民的重要主顾。驻防旗兵通常不介入地方事务,与当地汉族居民保持着平和却不亲密的关系。也多亏了这相对和睦的“邻里”关系,使辛亥革命后,水师旗营和平过渡为普通的乡村聚落,驻防兵及眷属自然地完成由旗人向平民的身份转变,不需面对如福州旗营旗人一般被汉人报复仇杀的命运,这是旗营民俗文化得以保留的人员保障。
再次,是水师旗营的城墙长期存在。城墙如同民俗文化形成的襁褓,造就了它的特殊性,同时也是一道屏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限制了当地汉族文化对其的影响,保护了旗营民俗文化的独立性。在旗营解散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也是因为有着城墙的存在,虽有人口流动,但营盘里原有的居住格局基本保持不变,城墙成为原旗营与当地汉族两种民俗文化的分界线,居住在城墙之内的人们依然讲“旗下话”,按着旗营传统民俗文化生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城外汉族居民大量搬入营盘里,一直到“文革”遭遇拆毁前,城墙已不再发挥任何实际作用。水师旗营的民俗文化既然是旗人自我封闭的产物,必然随着封闭的解除,在汉族文化的直接冲击下逐渐式微。
3.2 琴江满族村民俗文化的传承与延续
三江口水师旗营存续期间,琴江旗人依清廷规定,不耕地、不经商,维持生活全靠清廷发放的饷银,因此旗人没有土地、没有商铺,也不像当地汉人一般拥有渔船,可以说,除了营盘里的兵房,琴江旗人在这片土地上再无其他物质根基。营盘如同一艘航船,承载着琴江旗人漂浮在汉族聚居区之中。因此,在从驻防兵营转变为普通乡村聚落后,旗人后裔在当地根本没有可用于谋生的生产资料,只能外出寻求发展机会。一开始,外出谋职的人寄回的收入确实高于曾经清廷发放的饷银,琴江一度看似比作为旗营之时更繁荣一些,然而时日一久,缺乏物质根基的弊端还是暴露了出来。先是遭逢战乱,旗人后裔除兵房祖屋外无甚恒产,可以轻易弃家避祸,许多便就此留居外地不再回来了;而对村中一代又一代年轻人来说,远离市区的琴江,既无法提供生产资料,又缺少发展机会,自然便离家另寻出路,唯留老弱病幼仍在村中,琴江“空心化”一再加重。
1999年,琴江满族村被福建省人民政府授予“省级历史文化名村”称号,2010年又被评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受到各方关注的。不仅是琴江保留的水师旗营遗址,还有它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底蕴。许多学者前来调研、采风,均指出琴江是研究清代水师建设、八旗驻防、民族融合等问题的珍贵标本,应当予以妥善保护。
民俗文化的传承必须依靠一代又一代的人共同努力,而如今的琴江最缺的就是人。民国初年,琴江尚有旗人及后裔2000余人聚居于此,百余年间,旗人后裔四散各地,现在的琴江满族村只有百余户约300多人在此生活,而这些人也并非全都是当年琴江旗人的后裔。如今居住在老式兵房里的人们,除了少数年龄在70岁以上的老者,大多都不会讲“旗下话”,生活习惯也与周边汉族居民没有明显差异了。不少村中的有识之士对此均表现得十分忧心,甚至喊出了“留住琴江”的口号。他们认为,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民族融合是大势所趋,但只要琴江旗人后裔的族群认同没有消失,共同的记忆仍在,琴江的优秀文化传统就有保留下去的可能。因此,当务之急,除了加大旗营遗址的保护力度,留住水师旗营的物质基础外,还应着手编写琴江地方史志,完善琴江八旗博物馆的展陈内容,留住属于琴江的历史记忆;整理收集琴江民俗文化资料,拍摄记录“旗下话”的纪录片,留住琴江的精神符号。
(笔者外祖父母均为三江口水师旗营驻防旗兵后裔,对琴江满族村的“旗下话”及民俗文化较为熟悉,文中所涉风俗习惯资料系作者外祖父母口述或走访村中老者所得。)
注释
①康熙十九年(1680),杭州副都统胡启元率镶黄、正白、镶白、正蓝四旗汉军旗兵移驻福州,后又在原耿精忠部中挑补一千名分派四旗当差,此四旗被称为老四旗,系汉军八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