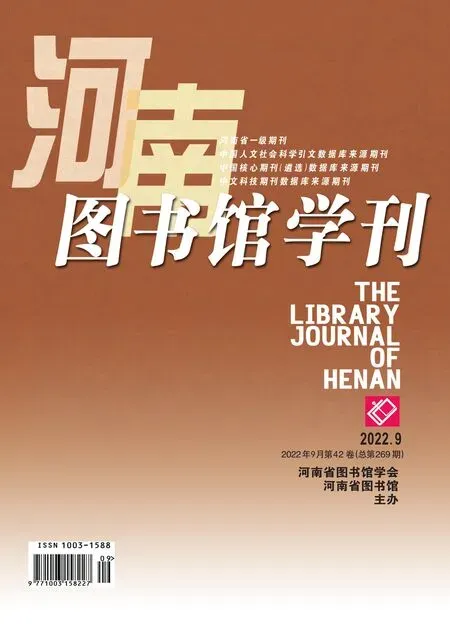丘濬藏书思想探究*
2022-11-08张建媛王小会
张建媛,王小会
(海南大学图书馆,海南 海口 570228)
丘濬(1421—1495),明海南琼山人,景泰五年(1454)进士及第,历任翰林院编修、翰林院学士、国子监祭酒、礼部尚书、户部尚书等职,为明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经济学家,在藏书思想和实践方面颇有建树。目前,关于丘濬藏书思想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具体的藏书措施,笔者对丘濬藏书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个人经历、思想渊源、阶段演进、体系特征等进行了研究,以期全面展现丘濬的藏书理论。
1 丘濬藏书思想的精神内涵
丘濬藏书思想的内涵是作为一个已经将儒学精神内化并进入官僚体系的儒家,对经籍重要性的极端推崇。丘濬认为书籍是儒道及其派生的政治制度、价值体系、人文经济等所依附的载体,“况此儒家经训书籍,乃自古帝王传心之要道,经世之大典,天地、山川、人物风俗之所存,礼、乐、刑、政制度文为之所具”。因此,丘濬赋予书籍无与伦比的重要性,“惟夫所谓经籍图书者,乃万年百世之事焉。今世赖之以知古,后世赖之以知今者”。
明中期,我国古代藏书已历数次书厄与艰难的恢复过程,丘濬怀抱极强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认为保藏书籍以传承义理、文化是当世儒家应承担的不殆之责,“任万世斯文在兹之责,毋使后世志艺文者,以书籍散失之咎归焉,不胜千万世儒道之幸”。丘濬曾任翰林院学士、编修,非常了解中央内阁的藏书情况及典藏职责,向朝廷提出“而我今日不有以修辑整比之,使其至今日而废坠放失焉。后之人推厥所由,岂不归其咎于我哉”的建议。他认为搜求、保藏图书是帝王的首要职责,“是以自古帝王任万世世道之责者,莫不以是为先务焉”。在我国古代图书史上,丘濬是将藏书置于如此高度的第一人。
2 丘濬藏书思想的演进及其阶段特点
丘濬的藏书思想主要体现在《藏书石室记》《大学衍义补·备规制·书籍之储》及《请访求遗书奏》中,笔者以时间为轴对相关内容进行了分析,以期展现丘濬不同阶段藏书思想的演进过程和特点。
2.1 《藏书石室记》与早期藏书实践的情感动机
《藏书石室记》的成书时间最早,是丘濬对早期藏书具体实践行为的记录和情感抒发。明成化五年(1469),丘濬丁忧回到家乡海南琼山,遂利用人生中难得的一段空闲时间实现了其建立藏书室以待后学的夙愿。成化九年(1473),他筑起一座石室,藏书其中,以饷家乡学子,并立碑记录书目规制。在记载这次活动的《藏书石室记》中,丘濬着笔最多的并非是对石室建造过程或藏书理念的阐述,而是对藏书初心的一次回顾。丘濬论述了其爱书之切、求书之艰、藏书以待后进的殷殷之意。对少年治学求书所经历的种种曲折情态,丘濬铭记于心,至数十年后仍然描摹得十分真切生动,“及闻有多藏之家,必豫以计纳交之,卑辞下气,惟恐不当其意。有远涉至数百里,转浼至数十人,积久至三五年而后得者,甚至为人所厌薄,厉声色以相拒绝,亦甘受之,不敢怨怼,期于必得而后已。人或笑其痴且迂,不恤也”。这种一书难求的人生经历构成了丘濬藏书思想和实践的一个底色,是触发丘濬自发、局部的带有实验性质的早期藏书实践的情感动机。
2.2 《书籍之储》与历史藏书制度的调研分析和理论准备
《大学衍义补·备规制·书籍之储》是丘濬对自周至明历朝藏书活动、策略、理论的系统梳理和总结。其体例为分别辑录经典文献中与历朝藏书活动相关的史事,附以名儒先贤议论,并在其后以“臣按”的形式记录丘濬本人对各朝藏书始末的分析、概括和评论。丘濬访求天下遗书的意图在该文中已露端倪,他对隋文帝时秘书监牛弘的访书奏表给予了充分肯定,称牛弘“表请分遣使人,搜讨异本,每书一卷,赏绢一匹,校写既定,本即归主,于是民间异书,往往间出”。《书籍之储》是丘濬对其即将试图推动的大规模藏书实践活动的一次历史调研和理论储备。
2.3 《请访求遗书奏》与藏书的顶层设计
《请访求遗书奏》是丘濬根据历史上的藏书经验,对藏书进行的具体规划设计。弘治五年(1492),丘濬在《书籍之储》的基础上,向明孝宗进《请访求遗书奏》,指出了藏书形势的严峻性,提议访求天下书籍,并提出了极为详尽的操作措施。此时丘濬40余年的仕宦生涯已达到最高峰,并接近尾声。身为内阁大学士、衣冠品秩冠于海南的丘濬选择这一时机,结合石室藏书实践与长期的庙堂思考,将对藏书事业的顶层制度设计提上议事日程,并试图推动一次举中央及地方之力的大规模的图书访求、校勘、收藏活动。
3 丘濬藏书思想的特征
3.1 丘濬藏书思想中的经世情结
丘濬的藏书思想具有较强的实践性,与其早期的人生经历有一定关系,“书又不可得,而求之之难有如此者。乃喟然发叹,自盟于心,曰某也幸他日苟有一日之得,必多购书籍以庋藏于学宫,俾吾乡后生小子,苟有志于问学者,于此取资焉”。丘濬的目光显然已不再囿于乡土,而意欲推广藏书理念,在“天下”实现自身的藏书理想。这种强烈的意愿在很大程度上是其经世思想的反映,历代文人士大夫不乏经世致用情结者,丘濬“少有志用世,于凡天下户口、边塞、兵马、盐铁之事,无不究诸心”。不同的是,作为我国15世纪卓越的思想家,在商品经济日趋繁荣的环境下,丘濬对财货、币制、海运、劳动价值、法律等均有超越前人的独到思考。时人对丘濬的评价为“理学、经济兼而有之”,“北学中国,文章经济,天下仰之如泰山北斗”。“然《大学衍义补》一书,其经济可见矣”,丘濬在《大学衍义补·治国安天下之要》中把“图籍之储”作为“经济”之一端,可见其用意。
丘濬既有经世之志,也重视经世之策,“意谓一旦出而见售于时,随所任使,庶几有以藉手致用”。期待“见售于时”,得以实行,是丘濬对藏书方法和实现路径进行详细规划的原因所在。当丘濬得以入阁参预机务,获得向明孝宗陈献《大学衍义补》书中“所载切要之务”的时机后,便以“图籍之储”的内容为由,呈上一份完整的藏书规划设计。明末,陈子龙将《访求遗书疏》收入其寄以存亡大计的《皇明经世文编》一书中,可见他对丘濬藏书思想的重视。
3.2 丘濬藏书思想的管理思维
丘濬的藏书思想是基于基层实践、历史思考、理论论述及顶层设计的系统化理论,是一种具有管理思维的藏书策略。从《书籍之储》中对汉代藏书策略的分析,可找到丘濬总体藏书路径的渊源所在,即“夫献书之路不开,则民间有书无由上达;藏书之策不建,则官府有书易至散失;欲藏书而无写之者,则其传不多;既写书而无校之者,则其文易讹;既校之矣,苟不各以类聚而目分之,则其于检阅考究者无统矣。后世人主有志于道艺而留心于载籍者,尚当以汉世诸帝为法”。丘濬在《请访求遗书奏》中提出的各项策略及其诗文奏疏关于藏书的表述,涉及访书、建策、誊写、备份、校勘、盘点、目录分类、检索、规制等内容,形成了一套比较科学、系统、完备的藏书体系。
丘濬藏书体系的每一个环节都有具体的措施,注重流程优化和工作效率,如:对于民间进献的图书要“以原本归主,不许损坏不还”;为避免出现重复抄写浪费人力的情况,丘濬提出各地先行开具并进呈书目,“通行各处,互相质对”,重复者只命一处抄录。在提议以监生抄录南京内府书籍副本时,丘濬对字体要求、俸廪支取方式、刷印匠作及纸笔费用的出处、书成装订等进行了明确规定,这些规定具有较强的操作性,显示出曾任国子监祭酒的丘濬对于业务的熟悉程度。丘濬重视书籍抄录、考校的质量,如:指出抄写民间图书时要确保不失真,盘点内阁藏书时须列考校日期、委官于每卷之末,誊抄南京国子监图书副本时要于卷末标记誊写监生及校官的姓名,“立为案卷,永远存照”。此外,丘濬重视内阁藏书管理人员的构成、内外职责、水火盗失安全责任等,考虑极为周详。
3.3 丘濬藏书思想的开放性
3.3.1 书籍典藏结构的广博多元。丘濬对藏书类型的认定展现了其包容和开放的理念,他认为访求图书时,“与凡官府学校寺观,并书坊书铺收藏。古今经、史、子、集,下至阴阳、艺术、稗官小说等项,文书不分旧板新刊及抄本未刻者,但系内阁开去目录无有者,及虽有而不全者,设法搜采,期于尽获无遗”,力求将天下书籍尽数网罗。这种开放典藏理念与其知识结构有关。在书籍严重匮乏的少年求学阶段,丘濬于内外姻戚处遍访图书,“不问其为何书,辄假以归”,求书若渴、来者不拒的态度已隐约可见,《明名臣录》也称其“颖悟绝伦,无书不读”。在当朝士大夫中,丘濬以知识广博著称,《明史》评价说“徐溥以宽厚著,丘濬以博综闻”。丘濬还家承医学,涉猎广泛,撰写了《本草格式》《重刊明堂经络前图》《重刊明堂经络后图》《群书抄方》等医学专著,以及《五伦全备记》等戏剧,因此,何乔新所撰神道碑称丘濬“自六经诸史九流笺之书,古今词人之诗文,下至医卜老释之说,靡不探究,发之文章,雄浑壮丽,四方求者沓至”。这种宏大的知识结构必然需要有大体量的多元的文献储备作为支撑,丘濬身后“行装惟图书数万卷而已”,藏书丰富为其对整个文献典藏结构开放性的认知奠定了基础。这种开放典藏理念还与其多重职业经历的影响有关。丘濬对前代藏书思想中被忽略的档案、谱系、地志等文献类型的关注,与其在翰林院期间的任职有关。丘濬曾任翰林院编修,撰写了高度依存日历、起居注等原始档案的《英宗实录》《宪宗实录》及《宋元通鉴纲目》等史书。他认为玉牒等大事文书、诏册制诰敕书、草捡行礼仪注、应制诗文等项底本、前朝遗文旧事等“可备异日纂修一代全史之用者”,力主将中央档案材料纳入典藏范围,提出了抄录并设立专门场所收藏内府一应文书档案的建议。此外,他还倡议恢复随门阀制度衰落而中断的谱牒撰写和典藏制度,以便官员薄状与私人谱系互相稽考,为撰写人物传记提供可信的证据,“奠系世以知其本所出,辨昭穆以知其世序。凡此皆有书,小史则定而辨之”。总之,丘濬对档案、谱牒二者收藏的重视皆与史撰的基本需求有关。丘濬还曾参与修撰《寰宇通志》《大明一统志》,得以熟悉天下地理、“山川险易,物产登耗,赋税多少,风俗媺恶”,其对志书与地利、边防、资政、教化之间的利害关系颇有认识,因此,他在《书籍之储》中阐述了修撰、收藏地志舆图的古老传统,指出了把郡县图经地志“藏其副于学校,而总收于礼部,藏于内阁”的收藏机制。
3.3.2 书籍的流动性。延续一贯的经济思维是丘濬藏书理念的组成部分,藏书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终点,用才是藏书的目的。“其所储书,非独以存前代之旧,盖将以资儒臣之考阅讲究,以开发其聪明,以为异时大用之具也”,可见丘濬既重视访求遗书,也重视图书刊布和流传。因此,丘濬指出了部分图籍刻板“今皆藏在内阁,天下人无由得见”的弊端,并提请将部分内阁藏书校对后“命工刻梓颁布天下,垂宪后世。俾学校用以教人,科举用以取士”。在奏疏中,丘濬提出的主要刊刻对象是《皇明祖训》《大诰三编》等御制、御注书文,以及儒臣纂成卷帙的《大明帝记》《皇明宝训》《大明宝训》《洪武圣政记》《大明日历》等有关帝王治道的书籍,是对其时其地物力、人力综合考量下的一种较为经济的策略选择,反映出他对官方信息向下的流布总体上是持开放的态度的。针对所谓“圣德神功”赖以传之天下的实录类著作,丘濬并不反对其公开,“今流传民间者多矣,要之本无秘事,不若听其流传也”。丘濬还提出刊刻儒家经训书籍的建议,曾苦求唐代大儒张九龄的《曲江集》和宋代大儒余靖的《武溪集》,亲自抄录并刊行于世,“矧是集藏馆阁中,举世无由而见,苟非为乡后进者表而出之,天下后世安知其终不泯泯也哉”。
4 结语
丘濬的藏书思想是明代藏书发展史上的一个标杆和范本,与其修身治学为官的经历有密切关系。海南大儒郑廷鹄进入庠学时,尚能读到疑为丘濬手定的石室藏书书目,“又读《石室藏书目》,见庠中写本,疑公所自定者”,到海瑞再访石室时,则“藏书已失,石室藏《衍义补》板片”。丘濬耗费心血精心设计的访求天下书籍的策略,虽然“上甚嘉纳”,但终究未能有效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