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群己权界”到“公私德界”
——道德哲学原理的自由儒学之思
2022-11-08郭萍
郭 萍
近来学界对公德私德问题的热议,直接切中了当前中国公民道德建设这一重大而紧迫的现实问题。不过,在笔者看来,目前的讨论仅仅局限于道德行为的实践(the practice of moral behavior),而没有探究道德规范的建构(the construction of moral norm),其实是没有深入到道德哲学原理的层面。因为“道德行为”只是对既有“道德规范”的遵行;而“道德规范”本身何以可能,才是道德哲学要追问的根本问题。这意味着我们在讨论如何培养落实公私道德行为之前,需要先行考察应当建立何种道德价值规范作为现代公民道德行为的基准才是合理的,即要先明确现代公民道德的内涵及其相应的道德模式,否则我们根本无法展开合乎时宜的道德实践。
一、有德无道:目前公德私德讨论的局限
目前的讨论已经形成了两种不同的主张,但双方都是基于某种既定的道德规范之下的思考,也即以既有的“德目”为解答公德私德的自明性前提,而对“道德规范何以可能”,也即“德目”背后所依据的“道”却未加省察,因此这些主张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有“德”无“道”的局限性。
(一)效法传统私德的疑难
一方学者认为,近代学人由于参照现代西方伦理学说而导致中国近代以来重公德、轻私德的弊病,因此建议效法传统的“家国一体”道德模式,即通过个人道德的推扩,直接贯通家与国、公与私,以克服公德私德失衡的问题。其理由是:在“我们儒家的文化立场”上,“治平”之公德与“修齐”之私德都是内在于自身的美德,因此都属于“个人基本道德”,即广义的“私德”,而且“《大学》的‘八目’修身工夫就是有效的实践途径,以人格修养为核心,落实于个人身心,但……对国家、社会也有积极意义”。所以,现代公民道德建设“应是以个人基本道德为核心,从中演绎或推化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形成完整的道德体系”。换言之,提升道德自律,培养以个人修身为核心的私德也就是当前公民道德建设首要而根本的任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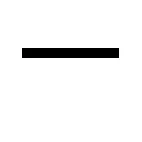
沿此思路,不论公德,还是私德,其内涵实质与传统“家国一体”模式下的“德”无异。因此他们强调,当前培养私德自律的基准就是传统的道德价值规范(礼),其中最基本的内容就是传统的“五常”(仁、义、礼、智、信),其中还有学者进一步提出以传统的“忠孝”观念来培养现代公民道德,主张通过对父母尽孝,转而实现对国家尽忠,进而在“移孝作忠”的意义上强调“孝”是现代公民道德之基。在他们看来,传统儒家道德“完美地实现了民众日常生活和国家意识形态的高度契合,求忠臣必出于孝子之门,在家能孝亲,在朝就能忠君,这……对我们今天也是深有启发意义的”。
事实上,这些学者已经有意无意地将传统道德规范视为恒常不变的道德行为标准,既没有对其合理性进行时代省察,也没有追问规范本身何以可能。这就根本导致他们对现代公民道德建设的理解只是局限于道德行为培养的层面,似乎只要现代公民自觉地认同传统道德价值,自主地遵从传统道德规范,那么现代道德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然而,其中的疑难是:传统道德价值规范作为现代公民道德行为标准的现实合理性何在?传统道德价值规范扎根现代社会的现实可能性何在?进一步讲,基于“家国一体”的传统道德价值规范是否合乎现代社会的价值共识,是否能适应现代生活方式,这都是值得商榷的。
(二)倡导现代公德的缺憾
另一方学者从近代中国谋求现代民族建国的基本事实出发,反驳了前述学者的观点并给出了不同的建议。蔡祥元指出,“家国一体”模式抹去了“大家”与“小家”的区别,导致公私不分,从而使理想的“公天下”沦为了现实的“家天下”。任剑涛指出,一些学者之所以主张将传统伦理直贯现代社会,就在于他们采取了中西之别的静态打量而脱离了古今之变的时代前提;而现代社会的事实是公私分立,私领域(个人、家庭)与公领域(社会、国家)互动关联,但边界清晰,不能直接贯通,因此现代道德需要在个人、社会、国家三层结构下展开:个人道德依靠自我约束,社会公德是靠个人自守和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监督,而国家权力则不应直接干预社会事务与私人事务。进而,他们强调,与私德只关乎个人自身不同,公德直接关乎每个社会成员的基本权益,其核心是社会正义,“倘若社会秩序供给短缺、国家立宪机制有缺,那么个人就无法独善其身,也很难友好相处”。所以当前公民首要的道德素质是要具备良好的公德,这对于公共人物尤其如此;而且公德的维护“不能首先倚重人的‘良知’,而首先需要通过规则来限制和规范人的行为”,因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具有高度道德自觉的人极少,依靠个人自律而实现社会道德理想的可能性极小;而且个人自律也缺乏外在的明确的尺度,最终往往是位高权重者占据道德制高点,这不仅会导致“以理杀人”,而且社会正义无法维系,因此他律才是有效落实公民道德行为的决定性手段。
这些立足现代社会的思考充分考虑了中国社会古今之变的实情,但其反驳与建议主要是以道德实践的现实成效或弊端为理据而展开的,仍然没有深入到道德行为的背后对道德规范本身进行探究。因此,他们一方面缺少对“家国一体”模式下的传统道德规范的学理分析和历史省察,导致相应的反驳并不彻底;另一方面缺少构建道德规范的合理基准和根据,导致其无法提供一种可供参考的现代性道德模式。
综合上述种种问题,当前的讨论有必要深入到道德哲学原理的层面,对道德规范本身进行追问和省察,这也将有助于我们思索现实道德问题更为深层的症结。
二、德有损益:儒家的道德哲学原理
毋庸置疑,任何道德实践都是个人自觉自主的活动,而且其中必然体现着某种人格品质和价值观念,而不论自律还是他律都是引导落实道德实践的有效手段。也就是说,道德实践无不是基于一种内在于“我”自身的道德价值观念而落实为“我”自觉自主的行为活动,其一般逻辑就是:由“我”出发而施于“他者”乃至“群”。在这个意义上,古今中外的道德观念都普遍体现着一种推己及人、由己及群的道德实践逻辑。
但这一普遍的逻辑在不同时代具有根本不同的内涵。因为我们判定一种行为是否道德,实质是在考察一种行为是否合乎某种道德规范,用儒家的话说就是,是否合乎“礼”。这就是说,所谓道德行为(道德实践)必然是对某种道德规范的遵守和践行,即守礼、行礼;反过来说,道德规范就是道德行为的前提和基准,否则根本谈不上行为的道德与否。这意味着有什么样的道德规范就相应地有什么样的道德行为,而道德规范所体现和维护的价值观念决定着一般道德实践逻辑的实质内涵。
然而,如孔子所说“礼有损益”,任何社会制度规范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生活的变迁不断地删改(损)或增订(益),历代的道德规范也不例外。这其中不仅包括具体道德规范的增减,而且包括整个道德价值规范体系的转变,所谓“转变”也就是要解构(损)旧的道德价值规范体系,建构(益)新的道德价值规范体系,此可谓“德有损益”。这意味着道德规范总是有其时代性,而道德行为需要与当下的道德规范相吻合,自然也有其时代性。其中在社会转型期间,由于旧的道德规范尚未消退,新的道德规范还不健全,还会导致“非礼之礼”的现象普遍存在,即某些合乎传统道德价值规范的行为,却并不合乎现代道德价值规范,此时人们对于道德行为的理解常常相互冲突,甚至陷入自相矛盾、手足无措的窘境。这其实正是道德规范时代性转变的集中体现。
当然“德有损益”并不是任意的,而是要合乎“道”。这其实已经涵盖在黄玉顺“中国正义论”所揭示的儒家制度伦理的一般原理中,即“义→礼”,也就是孔子所讲的“义以为质,礼以行之”。更明确地说,“德”的损益与“礼”的损益一样,是要以“义”为根本原则才能合乎“道”。从历代典籍注疏看,“义”作为“礼”的根本原则,既不是一种具体的道德规范,也并非有学者所误解的无关善恶的“价值中立”,而是表达着合理(reasonable)(如《荀子·议兵》曰:“义者,循理”);适宜(fit)(如《中庸》:“义者,宜也”);合适(suitable)(如《论语·学而》邢昺疏:“于事合宜为义”)等意味的基础伦理观念。进一步借助“中国正义论”的归纳,我们还可以推知道德规范所要遵从的两个基本原则:(1)历时维度的适宜性原则,即道德规范的建构要顺应时代变迁,适应当下社会的生活方式;(2)共时维度的正当性原则,即道德规范的建构要以“一体之仁”为出发点,确保有效维护和体现当下社会的价值共识。这就表明,任何道德规范都有其时效性,需要我们根据新的生活方式及新的社会价值共识进行重建。
对此,我们首先要了解:生活方式变迁的核心是组建群体生活的社会基本单元(social primary unit)发生了时代性转变,进而导致一系列社会价值观念及其社会制度的时代性转变。所谓“社会基本单元”也就是社会的经济、政治、道德、文化诸领域生活得以展开的最小单位,而整个社会生活追求和谐有序也就是为了维护社会基本单元的健康,因此这既是社会生活的基础,也是社会生活的根本价值。也就是说,社会基本单元作为一个基本价值单位,是真正的“社会主体”。历史地看,自古至今中国人组建群体生活的社会基本单元由前现代的宗族、家族转变为了现代性的个体(individual),因此形成了前现代的宗族、家族生活方式以及现代性的个体生活方式,同时这也使古今社会(群)体现出根本不同的价值共识,由此便赋予了“我”(ego/self)不同的道德价值内涵。这就要求不同时代的人们根据“正当”与“适宜”的原则建构不同的道德规范,以适应不同的生活方式,维护不同的社会主体价值;而不同时代的“我”施于他人与社会、国家的道德实践也就具有了不同的内涵。具体而言:
西周时期是以宗族为社会基本单位,这既决定了当时社会宗族性的价值共识,也赋予了“我”宗族性的价值内涵,同时由于宗族之间皆依靠自然血缘勾连,因而“兄弟阋于墙”的家事也就是国事,这也就形成了一个家国同构、天下一家的社会。因此,在当时基于自然血缘形成的宗法伦理就是一种合乎“道”的“德”,其基本的道德模式就是《礼记·大学》所记载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一体”模式。相应地,“我”对于这种血缘宗法伦理的践行,就是一个宗族成员理所当然的道德实践,由此维护的也就是家国同构的宗族生活秩序,最终实现的也就是宗族主体价值。但在“三家分晋”之后,真正的家国同构社会便开始瓦解,并逐步转向以家族为基本单元聚族而居的社会。是时,各家族及其与皇族之间渐渐失去了自然血缘的基础,因此直接贯通家与国的伦理系统也随之解体,继之以“门内之治恩揜义,门外之治义断恩”。不过,自西汉以来,占据统治地位的皇族就通过“移孝作忠”重构了“家国一体”的道德模式,所谓“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在此“孝”不仅体现着“父为子纲”的家族道德,而且维系着“君为臣纲”的政治道德,与此相应的制度建构就是以“三纲”为核心的道德规范体系。此时“我”作为一个家族性的存在者也就需要践行忠孝之德,由此体现的是自身作为孝子忠臣的美德,而且在忠孝难两全的现实道德张力中,皇族作为家族之首和国家统治者,实际规训着“我”遵从忠高于孝的道德实践趋向。这种道德规范体系实质性地维护了当时以皇族为首的家族生活秩序及其价值诉求。
随着家族生活方式的僵化衰落和现代性生活方式的孕育兴发,这种道德规范体系便逐步失去了正当适宜性。因为在此规范之下,“我”只是一个非价值自足的个人(person),即“个人总是一定的伦理和政治秩序中的自我,离开了家国秩序,自我将不复存在”。而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是以个体(individual)为基本单元组建而成,“我”也就相应地承载着个体主体价值,并因此成为一个价值自足的存在者。这种古今差异也使得现代族群(包括现代民族国家、社会团体乃至现代家庭)并不同于传统族群,即不再是由非价值自足的个人组成的集体,而是由价值自足的个体组成的联合体。也正因如此,现代社会公民会基于保护个体价值(不仅是自身价值)的目的而共同维护现代族群的利益。
在此情形下,现代社会的道德规范必然要与这种以个体为基本单元的生活方式相适应才具有适宜性,且要以维护和体现个体主体价值为出发点和根本旨趣才具有正当性;与此相应,“我”的道德实践也应当普遍维护个体价值,才能体现身为现代公民的美德。而这都不是“家国一体”模式下的传统道德规范所具备的。正如任剑涛所说:“现代相对于古代发生了根本变化,现代难题无法在传统中求解;现代道德建设难题的解决,只能在现代脉络中来求解,而传统儒家道德若作为可用资源,那就必须在现代性生活方式下进行现代阐释。”其中传统的“三纲”非但不能解决现代道德问题,反而是现代公民道德建设要警惕和剔除的内容。例如,当今我们并不能依靠父为子纲、夫为妇纲来维系由平等个体组建的现代家庭,更不能要求一个现代公民以孝子忠臣的道德意识来承担其社会责任。事实上,在现代社会,即便是“孝亲”也无法以传统方式来落实,这一方面是因为现代家庭的类型日趋多样,甚至存在着某种解体的趋向,另一方面是因为医疗、房产、教育等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合理、不健全对普通民众“孝亲”的意愿和行为造成了严重的挤压和扭曲。再推展一步讲,传统的“五常”同样需要进行现代性的“赋值”,而不能以其前现代的道德内涵充当现代公民道德修养的基本内容。这都意味着我们需要在现代性生活方式下,以个体价值为根本福祉,重建公民个体与家庭、社会、国家的关联,具体到现代公民道德建设方面,就需要我们首先确立一种有别于传统“家国一体”的、现代性的道德模式。
三、公私德界:儒家现代性的道德模式
前论提及现代社会出现公德私德问题本身就是以公私领域的划界为前提的,而现代社会之所以要进行公私领域的划界,以至于现代道德建设之所以要在公私领域划界的前提下展开,其实质是与“群己权界”(the demarcation between private rights and public power)问题相对应。
“群己权界”本身是严复继承儒家“群学”原理对现代自由问题的释义,但其含义并不限于狭义的政治哲学领域,而是表明了一种维护现代主体价值和现代生活秩序的普遍性实践原则,因此严复也将其视为“理通他制”的现代“文明通义”,即广义的伦理实践原则。他曾在《政治讲义》中指出:“仆前译穆勒《群己权界论》,即系个人对于社会之自由,非政界自由。政界自由,与管束为反对。政治学所论者,一群人民,为政府所管辖,惟管辖而过,于是反抗之自由主义生焉。若夫《权界论》所指,乃以个人言行,而为社会中众口众力所劫持。此其事甚巨,且亦有时关涉政府,然非直接正论,故可缓言也。”可以说,“群己权界”乃是关涉着政治与道德的广义的“伦学”思想,而且与中国学术“务为治者”的旨趣一脉相承,可谓是一种“儒家现代群治之方”。事实上,不仅中国学术如此,有学者也指出:“在英语学术界,政治哲学不仅被归于道德哲学之下,而且也通常与法律哲学、社会哲学甚至一般社会理论杂糅在一起”,所以当代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Bordley Rawls)也将其所著的《正义论》视为一部道德哲学的著作。
就此而言,“群己权界”本身就具有道德哲学的意味,或者说在道德哲学的意义上,我们应该把它表达为“群己德界”,更确切地说也就是“公私德界”(the demarcation between private and public morality),而这实质也指示着一种与传统“家国一体”根本不同的道德模式。
与“群己权界”一样,“公私德界”首先意味着在己与群、公与私之间“划界”,即:
使小己与国群,各事其所有事,则二者权力之分界,亦易明也。总之,凡事吉凶祸福,不出其人之一身。抑关于一己为最切者,宜听其人之自谋,而利害或涉于他人,则其人宜受国家之节制,足亦文明通义也已。
之所以要“划界”是因为:现代生活虽然是以个体为基本单元,但仍然是一种群体生活,因此“自入群而后,我自繇者人亦自繇,使无限制约束,便入强权世界,而相冲突。故曰人得自繇,而必以他人之自繇为界”,这就必然需要公权力的维护,唯此才能普遍保护个体价值不受侵害,同时维护群体生活的和谐秩序。因此从积极意义上讲,“划界”是为了在现代性生活方式下,切实有效地发挥群以护己、公以卫私的作用。但要警惕的是,公权力在实行过程中往往偏离或背弃保护个体的宗旨,反倒成为侵害个体的横暴力量,如严复所说:
最难信者亦惟君权,彼操威柄,不仅施之敌仇也,时且倒持,施于有众。……为虐无异于所驱之残贼,则长嘴锯牙,为其民所大畏者,固其所耳。故古者爱国之民,常以限制君权,使施于其群者,不得恣所欲为为祈向。
所以从消极意义上讲,“划界”是为了“裁抑治权之暴横”,防范公权力对私、己的侵害。面对实情,唯有“划界”方能确保个体与群体的两全,所谓“小己之发舒,与国群之约束,亦必有其相剂之道,而无虑于牴牾”。这也就表明“公私德界”并不意味着群与己、公与私的彼此孤立,同时也不存在“家国一体”所蕴含的大公无私,以致以公统私,或者以私害公、甚至“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的极端趋向,而是一种基于公私区分的群己相剂模式。
当然,“公私德界”作为一种道德模式依然遵循着“我”出发推及、施用于“群”(社会、国家)的一般道德实践逻辑,只是由于“我”的内涵发生了时代转变,因此不再是“家→国→天下”的传统形态,而是“个体→社会”的现代形态。其最基本的体现就是“我”作为一个现代公民,通过自主自治而体现出自尊自爱,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哲学上的“群己权界”与道德哲学上的“公私德界”并非二事。从“群己权界”的角度讲,一切权利和权力皆属于社会主体所有,只是在前现代社会,一切权利和权力为宗族或家族拥有;而现代社会一切权利和权力则归公民个体所有,所谓“主权在民”。这意味着“我”作为公民个体的权利不仅是拥有“私权”,而且还拥有“公权”,也即“私权”与“公权”都是“我权”,前者是私人领域的公民个体权利,后者是公共领域的公民个体权利(政府等只是公权力的代理执行机构)。因此,现代公民在政治生活中理应自觉维护和履行公民权利,实现自主自治,而这本身也是现代公民自尊自爱的道德诉求。如梁启超所说,“权利思想之强弱,实为其人品格之所关。彼夫为臧获者,虽以穷卑极耻之事廷辱之,其受也泰然;若在高尚之武士,则虽掷头颅以抗雪其名誉,所不辞矣”,因此“无权利者,禽兽也;奴隶者无权利者也,故奴隶即禽兽也。……且禽兽其苗裔以至于无穷,吾故曰:直接以害群也”。这意味着现代公民的自尊自爱需要以自主自治的个体权利为前提和保障。人们如果缺乏个体权利意识,那么非但难以具备礼义廉耻的道德意识,而且连维护公共利益的资格都没有,其最终会导致社会性的道德败坏。
进一步讲,“我”之权的行使作为“我”之德的体现,其含义如梁启超所概括:“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分而言之:
最基本的私德意味着:其一,自主选择私人生活方式,自行处理私人事务,同时自觉承担相应地责任。如无特殊,公民的“私权”不能、也不应该由他人代劳,否则就是对自身不负责,无异于自暴自弃,徒然增添他人负担;其二,自觉恪守私权的施用范围和边界。在私人领域,但凡是当事人自愿自主选择的生活方式,而且没有侵扰到非当事人的权益,那么就应受到他人和社会的基本尊重。在此情况下,公民个体之间不应侵扰、非议他人的私人生活,不应干涉、窥探他人的私人事务,这既是对他人的尊重,也是自身赢得尊重的前提。
最基本的公德意味着:其一,“公恶不可纵”,即自觉维护公共生活秩序。在公共生活中,任何一个人的权利受到侵害都意味着所有人的权利可能受到同样的侵害,因此对公共权利的侵害是谓“公恶”,此时应以公权力加以干涉“使不得惟所欲为”。这不仅是每个公民公共良知的体现,而且每个公民都有抵制公恶的权利和责任,所谓“不止于恶,以吾身为国民,实且有干涉之权责故也”。其中,对于公职人员而言,尤其应当如此;相反,如果公职人员尸位素餐、玩忽职守、推诿责任,那就不仅是纵容公恶,而且其本身就是一种公恶。其二,“私过可任自繇”,即必须恪守公权力的边界和限度。与私权相反,公权力只能施用于每个公民生活的共同性、公开性的公共领域,而不能涉足其个性化、私密性的私人领域,否则不复为公私相剂之道。因此任何人,尤其是公权力的执行者,绝不应动用公权力来干涉私人事务,而应当奉行“凡事吉凶祸福,不出其人之一身,抑关于一己为最切者,宜听其人之自谋”。这不仅是最基本的公共道德,而且也是维护整个现代生活秩序的底线道德。因为与私权之间的侵扰不同,公权力对私人领域的侵扰,不仅背离了公权力维护个体权益的唯一目的,而且极易成为反制公民权益的横暴力量,使私德丧失现实发展的可能性,如此一来便成了最大的公恶。就此而言,“裁抑治权之暴横”也就是惩治公恶,这本身也是一种基本的公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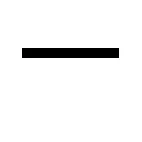
综上所论,道德规范总是随着生活方式的时代转换而更新,其背后依据的是“义以为质,礼以行之”的儒家道德哲学原理,即需要根据“义”的原则,建构新的道德规范(“礼”),以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基于此,我们才能开展合乎时宜的道德实践。据此反观,公德私德问题本身就是以现代社会公私领域的界分为前提,之所以要界分公私,其实质与“群己权界”问题相对应,这其中也指示着一种与现代生活相匹配的道德模式——“公私德界”,而确立“公私德界”的道德模式也就是现代道德规范体系建构的核心内容。这作为现代公民道德行为的前提和基础,乃是现代公民道德建设的当务之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