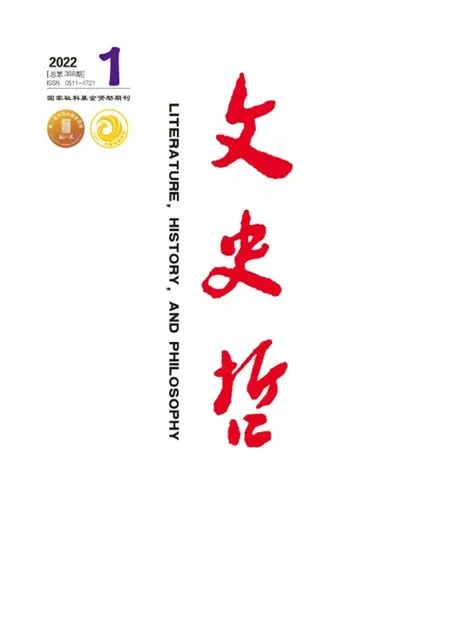禁忌为法律贡献了什么
2022-11-08黄金兰
黄金兰
引 言
德国学者冯特曾指出,禁忌“是人类最远古的法律形式”;卡西尔也强调,“似乎没有一个社会(不管是多么原始),不曾发展出一套禁忌体系”。确实,在更为精细和复杂化的社会控制体系(诸如宗教和法律)出现之前,禁忌曾充当着人类基本的社会控制形式。作为一种在人类历史上较早出现的社会控制机制,禁忌一定给后来的其他社会控制方式提供了某些经验和启示。卡西尔指出,禁忌为道德和宗教提供了很多先天的原则。实际上,禁忌不仅为人类的道德和宗教作出了贡献,很大程度上,它还给法律提供了很多现实的经验和技术支持。
在展开讨论之前,有必要先对禁忌这一社会控制形式作简要交代。所谓禁忌,是基于人们对超自然力量的敬畏而由社会强加的一套责任和义务体系。这些责任和义务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完全是消极的,它们不包含任何积极的理想。某些事情必须回避,某些行为必须避免——我们在这里发现的是各种禁令,而不是道德或宗教的要求”。由此可以看出,禁忌所包含的,全都是消极的禁令,这与道德、宗教和法律有所不同——在道德和宗教中,虽然也存在一些消极的禁令,更多的却是以格言或箴言形式所体现的积极要求;而在法律中,除消极的禁止性规范外,还包括积极的义务性规范,以及赋予人们自由选择空间的授权性规范。然而,也恰恰是在这一点上,禁忌的意义才更加凸显出来。卡西尔指出:“禁忌体系尽管有其一切明显的缺点,但却是人迄今所发现的唯一的社会约束和义务的体系。它是整个社会秩序的基石。社会体系中没有哪个方面不是靠特殊的禁忌来调节和管理的。”的确,作为人类最早出现的行为约束体系,禁忌不仅在人类的幼年时期发挥着重要的社会控制功能;即便到了后来,在道德、宗教、法律等更加复杂的社会控制体系出现后,它仍然在社会控制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这一意义上讲,将禁忌称为“整个社会秩序的基石”,一点也不为过。不仅如此,作为人类最早出现的社会控制体系,禁忌还给后来的其他控制体系的建构提供了诸多启示,本文将主要就它给法律的演化所带来的启示和贡献展开讨论。
在此,我们还需要对本文意义上的“法律”作出简要界定。如所周知,在中外法律思想史上,对于“法律是什么”这一问题,不同学术流派从不同角度给出了不同回答:在价值法学看来,法律是自由、公正等价值原则的现实体现;在实证主义法学看来,法律就是主权者发布的命令;在功利主义法学那里,法律是功利原则的制度落实;在历史法学的眼中,法律是民族精神的产物;而对社会学法学来说,法律就是使社会有序化的社会控制形式;等等。仔细观察便会发现,这些关于法律的不同界定,并非截然对立;它们之间的差异,根本上源于各学术流派所处的立场和视角的不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与其说不同学术流派给法律下了不同定义,不如说他们揭示了法律所具有(或应当具有)的不同意涵。那么,本文是在什么意义上使用“法律”一词呢?本文所谓之法律,主要限于法社会学立场和意义,即将法律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方式来看待。原因主要在于,只有在这一意义上,才能将禁忌和法律放在同一个逻辑序列,并对二者进行比较研究,进而分析前者对后者的启示和贡献。
那么,作为在人类历史上先后出现的社会控制形式,禁忌为法律贡献了什么?
一、自我克制习惯:秩序的行为基础
弗洛伊德指出,“每一种文明似乎都必须建基于对本能的强制和否认之上”,这是因为,“欲望是人的本质自身”。确实,一部人类文明史,一定意义上讲,就是对人的本能予以规范和控制的历史——在人类的先天秉性中,或多或少都存在着某些反秩序和反文化的倾向。正因如此,伽达默尓才强调,“人之为人的显著特征就在于,他脱离了直接性和本能性的东西”。这就是说,一个成熟意义上的人,一定是超越和克服了自身某些本能倾向的人。而这种超越和克服,并不是人们自觉完成的,它需要借助一些外在的机制才可能实现。在所有这些机制中,最早出现的便是禁忌。
人类,无论属于什么种族,生活于什么地域,他们之间都存在很多相似的本能和情感(也即伽达默尓所说的“本能性”)。勒庞指出,尽管人们在智力上差异很大,但在本能和情感问题上,他们却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在这些方面,最杰出的人士并不比凡夫俗子高明多少。滕尼斯也强调,在人的意志里,天生地会对某些事物或活动充满兴趣,而这些源自先天的兴趣也就是人的本能。在这些本能中,一部分是先天于社会秩序有利的,例如爱、怜悯之心、合作倾向等;另外一部分,则是反秩序的,至少是可能引发秩序问题的,诸如自利心、嫉妒心、性本能等。因而,要实现社会的有序化,就不仅需要对那些有助于社会秩序的本能(为行文的方便,不妨称其为“合秩序本能”)予以利用,更重要的还在于,必须对那些不利于秩序的本能(不妨称其为“反秩序本能”)进行规范和遏制。而要做到这一点,却并非易事。可以说,在抑制人的本能这一问题上,人类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禁忌是被人类所最早采用的控制本能的方式。举例说来,研究者发现,在几乎所有的禁忌体系中,都存在着控制人类性本能的一些禁制。性的需要和满足,原本是造物主赐给人类的美好礼物,然而,倘若这种需要冲破了一些必要的限定,便构成对社会秩序的潜在威胁。因此,在不同文化中,人们都设计出一套禁忌体系,来预防类似乱伦和通奸等不恰当的性行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表明,乱伦倾向是隐藏在人类性本能中的危险特点,因而,很多社会都有关于乱伦的禁制。观察者指出,总体上说,越是野蛮的民族,对乱伦的禁忌越严格,尤其在那些裸体的食人野民中,对乱伦的制裁达到了最为严厉和残酷的程度。除乱伦倾向外,人类的性本能中,还存在另一种危险倾向,那就是追求新奇——这种倾向使人们不满足于同固定的性伴侣发生性行为,而是追求性爱对象的多元化和多变性。在人类婚姻制度尚未建立之前,人的这一本能不易引发大的秩序问题。然而,为了保护下一代的利益,婚姻制度终究还是登上了人类历史舞台,婚姻关系一旦确立,夫妻双方对彼此的身体便具有了独占权。婚姻的这一规定性,与人类性本能中追求新奇的倾向严重对立,为了满足这一本能,总有人想要突破婚姻所设定的藩篱,如此,通奸行为便时有发生。通奸的存在,会给婚姻秩序乃至整个社会秩序造成严重破坏(后者主要体现为由性嫉妒所引发的各类恶性事件),为此,人类发明了花样百出的通奸禁忌,来对人的这一本能进行抑制。

由于人是社会秩序的主体,因此,从根本上说,一个社会的有序化,实际上就是指这个社会中人们的行为大多符合社会秩序的要求。前文已提到,在人的本能中,既存在合秩序的一面,也存在反秩序的一面。因而,社会控制的核心就转化为如何有效地引导和利用那些合秩序的倾向,同时对那些反秩序的倾向进行抑制。为此,人类发明了两种体系:肯定性的箴言和否定性的诫命。前者是一种正面引导体系,旨在对人性中那些诸如爱、怜悯、合作等美好特质进行引导和激发,目的在于培养合秩序的美德;后者则是一种反向遏制体系,旨在对人性中那些类似利己、放纵、嫉妒等不良倾向予以否定和遏制,目的在于消除不良或罪恶习性(即反秩序倾向)。可以说,这两种体系并行不悖,共同推动着人类社会不断地向成熟和文明迈进。一般而言,肯定性箴言的主要表现形式是道德格言和宗教箴言,尽管在道德和宗教中也存在少量的否定性禁令。而否定性诫命的表现形式则因时而异,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它几乎完全以禁忌的形式来体现;随着人类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除禁忌之外,其他社会控制方式诸如法律中也包含了大量的禁令。
那么,人类如何从禁忌禁令发展到法律禁令?进一步的问题是,法律中的禁令,其实现如何可能?我们知道,人们对禁忌的服从,依靠的乃是对某些超自然力量的敬畏;但在法律语境中,这种超自然力量通常并不存在(现代世俗国家的法律尤其如此),法律禁令所依靠的,乃是来自国家力量的制裁。然而,就有效性而言,来自国家制裁的威胁显然要大大低于对超自然力量的敬畏——这一点,对于早期的人类尤其明显。法国历史学家古朗士曾指出,在远古时代,“为了将人们纳入一种社会的条例之中,为了建立规范并确保遵守,为了让理性战胜激情……肯定需要某种东西,而这应该是一种比物质力量更强大、比实际的利益更可观、比哲学理论更准确、比习俗更具稳定性的东西,这种东西还应共同植根于人们的心中,并对所有人都具有权威性”。显然,主要作为一种物质力量的国家制裁,并不具有这样的功能,也难以达到这样的效果。于是,问题便出现了,何以在一种更弱的制裁威胁前,人们还是会遵守禁令?可以说,这正是禁忌给法律的第一大贡献。

二、良知与责任:秩序的心理支撑
社会秩序的形成,不仅需要这个社会中的人们养成一种抑制本能的行为习惯,在更根本的意义上,还需要一种对本能进行抑制的内在动力,以及在克服本能失败后的某种不安感,这种内在动力就是人的良知,而不安感就是人的自责。伴随着良知和自责而来的,还有人的责任意识,也即关于什么事情必须做或不能做的自我意识。可以说,良知和责任是秩序形成的重要心理基础。这两种心理对于人类不当行为之抑制作用的有效发挥,很大程度上源于禁忌的实践和经验。

德国学者普芬道夫指出:“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并且知道怎样给自己的主张以确定和无可辩驳的理由的人,被认为是有正确良知的人。然而,一个人也可能对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持有正确的见解,但却不能将其建基于论证之上。他的见解可能来源于他所在社会的一般生活方式,或者来源于习惯,或者来源于权威当局,因而没有理由持有相反的观点。这种人被认为具有潜在的良知。大多数人都受潜在良知的指引,很少有人具有揭示事物原因的能力。”普芬道夫的这一论断,恰好向我们揭示了良知得以形成的经验基础。一个人之潜在良知的形成,并不在于某种基于先天理性而形成的道德命令,而在于他从小所处的生活方式、习惯等给他提供的指令和暗示,什么行为是该做的,什么行为是不该做的。这种指令和暗示,给他划定了一个可为和不可为的清晰界限,一旦越出这一界限,一种不安和自责感乃至罪恶感便油然而生。而关于可为和不可为的界限,最早便是由禁忌所确定的,哪些食物不能吃,哪些话不能说,哪些行为不能做,这些都是禁忌的主要内容。中国古人讲,“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礼记·曲礼上》)。这里的“禁”和“讳”就是指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禁忌,它们给人的行为设定了明确的界限,一旦违背这些界限,就会导致不安和恐慌。至于为什么要这样规定,很多时候也说不出具体的理由,因为“禁忌是不讲道理的,某种语言、某种行为或接触某种人、物与人们认为要降临的恶果之间根本就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
那么,界限如何带来良知和责任呢?这是通过人们在遵守或违反禁忌之后的内心反应来实现的。当行为符合禁忌的要求时,一种内心的安定感随之产生;反之,当行为违背禁忌的要求时,便容易陷入某种忧虑甚至恐慌。为什么会这样?那是因为,任何禁忌体系都伴随着一套报复的威胁。说哪些话会带来不吉利,吃哪些东西容易患病,哪些行为会引发灾难,这些都是禁忌的标准表达方式。而人一旦做了这些事情,便很害怕这些结果会应验。因此,禁忌其实根本上是通过作用于人的心理而实现的——遵守禁忌带来安全和满足,违反禁忌则导致忧虑和恐慌。在休谟看来,正是这两类完全不同的感觉(他将二者化约为“快乐”和“不快”),促成了人类道德感和责任意识的产生:“道德宁可说是被人感觉到的,而不是被人判断出来的;……由德发生的印象是令人愉快的,而由恶发生的印象是令人不快的”;“一个行动、一种情绪、一个品格是善良的或恶劣的,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人们一看见它,就发生一种特殊的快乐或不快。因此,只要说明快乐或不快的理由,我们就充分地说明了恶与德”。休谟的意思是,当一个人做出合理、恰当的行为时,他的心理感觉是快乐的;反之,当他做出不合理、不恰当的行为时,心理感觉则是不快的——这种快乐或不快的心理体验,慢慢造就了一个人关于善与恶的判断;并且,基于这种判断,人们也渐渐养成了一种关于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的责任意识。用休谟的观点来解析禁忌与良知和责任之间的内在关联,我们可以这样说:当人们做出符合禁忌要求的行为时,他会感到安全和快乐;相反,当他违背禁忌时,则感到恐慌和不快。这种快乐或不快的感觉,久而久之,就在人们心中形成了一种关于禁忌的良知,而这种良知会帮助他们养成一种服从禁忌的责任意识。弗洛伊德指出:“什么叫‘良知’?从语言的角度来说,它是和一个人的‘最确实自觉’有关。事实上,我们很难把‘良知’和‘自觉’这两个词在某些语言里区别开来。”弗洛伊德所说的“最确实自觉”,实际上就是指人的责任感。良知和责任感,是一对孪生姐妹,一个有良知的人,内心一定会自觉地要求自己去做或不做某些事情。
良知和责任感,乃是禁忌给法律的第二大贡献。一个具备良知的人,会对公共规则感到敬畏,良知就如同住在他内心的一个“超自然法庭”——康德说,良知“很像影之随形,他想摆脱也摆脱不掉”——在它的作用下,人们会产生一种强烈的责任意识,让自己积极地做出规则所要求的行为,并尽力避免规则所禁止的行为。从这一角度讲,良知和责任实在是社会秩序得以建立的心理根基。我们知道,从外在来看,法律所依靠的乃是来自国家的公共制裁;然而,对于国家制裁及其威慑力,我们不可给予过高的估计。西塞罗指出,“如果只是刑罚,只是对惩罚的恐惧,而不是邪恶本身,才使得人们躲避不道德的生活和犯罪的话,那么就没有人可以被称之为不公正的人,而且更应视恶人为不谨慎的人;进一步说,我们当中的那些并非由于美德的影响,而是出于一些功利和收益的考虑而成为善者的人,就只不过是胆小鬼,而并非好人。因为,对那些除了害怕证人和法官外无所畏惧的人来说,如果无人知晓,他又会走上什么极端呢?”这意味着,仅仅依靠国家制裁,根本不可能形成秩序;一个法律秩序的实现,仰赖于人们积极地履行法律义务。而人们之所以会积极地履行义务,从根本上讲,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必须这样做,也就是说,不是因为害怕制裁,而是基于良知和责任。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普芬道夫才对义务作这样的定义:“‘义务’是指:基于责任,人的行为与法律的命令相一致。”可以说,基于责任的义务,才能够真正形成社会秩序,而这种责任,根本上来自人的内在良知。
三、团体性共识:秩序的产生前提和维护保障
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一定建立在某种共识基础之上。如果不存在基本的共识,则是非标准各异,人人自行其是——可以想见,这样的社会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达致秩序化的。正如《墨子·尚同》所言:“方今之时,复古之民始生,未有正长之时,盖其语曰‘天下之人异义’。是以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百人百义,其人数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而非人之义,故相交非也。内之父子兄弟作怨仇,皆有离散之心,不能相和合。至乎舍余力不以相劳,隐匿良道不以相教,腐朽余财不以相分,天下之乱也,至如禽兽然,无君臣上下长幼之节,父子兄弟之礼,是以天下乱焉。”显然,没有统一的标准和共识,势必天下大乱。而人类最早的共识,便存在于禁忌体系中。
玛丽·道格拉斯指出,“禁忌有赖于某种形式的团体性共谋。团体中的成员如果不遵守它,这个团体就不能存在下去。在那些不要破坏团体价值的警告中,成员们显示了他们的关心”;“单独看一条条禁忌,我们会发现它们是如此地稀奇古怪,以至于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都很难对它们产生信任。我因此而称之为共谋。人们之所以相信是因为他们共同地想要相信”。然而,他们为什么会“共同地想要相信”?这是因为,没有一套共识体系,社会将难以为继。至于这套共识体系是否合乎理性标准,很多时候倒是次要的。如涂尔干所指:“曾经被认作,现在还仍然被认作是犯罪的大量行为实际上对社会并没有产生危害。假如有人触犯了禁忌,触犯了某种不洁的或神圣的动物或人,弄灭了圣火,吃了某种肉,没有向祖坟杀牺献祭,没有字正腔圆地诵读祭文,没有庆祝某类节日,——诸如此类的行为真的对社会构成了危害吗?……社会之所以强迫人们去遵守规范,显然是因为这种严格而又一贯的遵从无论正确与否都是必不可少的,是需要不断强化的。”因此,一套共识体系的存在,其首要功能就在于构建一个社会基本的秩序前提。用现代的眼光来看,也许它们未必都合乎理性原则,但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它能够提供标准,从而使社会有序化。我们不妨举两个例子来进行说明。据人类学家的考察,印度南部的纳亚尔人,女性以性自由闻名,她们没有固定的丈夫,长期与多名男子保持性关系。在这样的社会中,婚姻家庭秩序如何维护?纳亚尔人采用了一种虚构婚姻的方式。在女孩的青春期到来之前,会为她们举行一个婚姻替代仪式,在这个仪式中出现的“新郎”,便是“新娘”未来所生子女的公认父亲。在我们看来,此种虚构婚姻的方式似乎是胡闹,但无论如何,它能够起到维护婚姻秩序稳定及抚育后代的功能。而这再次印证了一点,在早期的人类社会中,一种制度构建本身是否具有合理性尚在其次,更重要的在于,人们在此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另外,据古罗马学者西塞罗称,在斯巴达人那里,人们能够用长矛所触到的所有土地都属于他们自己;雅典人则宣称,凡是生产橄榄和谷物的土地都属于他们。这种看似很粗暴的说法,却慢慢演化成一种共识,其目的在于确定土地的归属,进而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
在复杂精细的法律规则体系尚未出现之前,人们通过禁忌体系来维护基本的社会秩序,而这一套体系之所以能够有效运转,很大程度上源于人们对于禁忌规则所达成的共识或共谋。没有这种共识,禁忌体系将成为无本之木,社会也将难以维续。总体而言,这些共识包含两个部分:一是哪些行为不能做;二是如果做了会有什么后果。以通奸禁忌为例,透过各种不同形式的此类禁忌,我们会发现其间存在着两类共识:一是对通奸行为的共同谴责,也即反对通奸;二是如果通奸行为发生了,人们相信,或者共同地想要相信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其中,第一类共识为人们确立了“不可为”的标准,也即什么样的行为是人们共同谴责的——不妨称其为“标准性共识”;第二类共识则提醒人们,如果违反了这些禁忌,将会面临严重后果——不妨称其为“结果性共识”。可以说,这两类共识相互依存,缺一不可,共同为社会秩序的形成提供基础和保障。标准性共识的功能在于确立行为规范,从而为秩序的形成提供前提条件;结果性共识则对违反规范的行为规定惩罚方式(尽管此种惩罚未必一定会转化成现实的物理性惩罚,但只要人们相信,威慑的效果便能获得实现),从而保障秩序的实现。因此,这两类共识一旦达成,禁忌体系就能够存在下去,社会秩序也就有了实现的保障。
应当说,以一套共识为基础形成社会秩序,并在秩序遭到破坏时予以修复,是禁忌带给人类的第三大贡献。可以看出,后来的法律体系,同样是以一系列共识为前提和保障的。涂尔干将这些共识表述为“共同感情”或“集体意识”。他认为,犯罪行为表面看来是对法律的违反,从根本上讲,乃是对这个社会的宗教情感、家庭情感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传统情感的侵害。这些情感,并不是社会中某些个人的特殊情感,而是为所有社会大众所共同珍视和看重的,它们属于社会中每一位最普通的人;因此,犯罪行为一旦出现,便会遭到社会成员的共同谴责。从涂尔干的论述可以看出,即便在法律的世界里,为人们的行为确立标准的,其实并不是法律本身,而是隐藏于每一个普通人身上的共识性的东西,它们被赋予不同的名称——情感、意识,或是其他什么,并构成了一个社会赖以建立的基本共识体系,离开了这个体系,人类的社会生活将变得不可能;也因此,当这些共识体系被挑战时,所有社会成员都会群起而攻之。斯宾诺莎说,“人类的本性就在于,没有一个共同的法律体系,人就不能生活”。其实,更接近本质的描述是:没有一个共识体系,人类就不可能有社会生活。关于这一点,罗素也曾强调:“在现代技术发明以前,要把一个大帝国团结在一起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帝国全境的社会上层都有了他们由以团结在一起的共同情感。”实际上,无论这种共识被冠以什么名称,它们的功能都是一致的,那就是为社会秩序的建立提供根本性依据;并且,当这种共识被侵犯时,以集体的力量予以谴责,以使社会秩序恢复到原先的状态。
如前所述,在禁忌体系中,存在着两类共识:标准性共识和结果性共识。这两类共识在法律体系中也有相应的存在方式。最典型的就是作为法律规范构成部分的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法律规范中的行为模式相当于禁忌体系中的标准性共识,法律后果则相当于结果性共识。在法律秩序中,人的行为要实现规范化,首先必须有行为标准,这个标准就是行为模式。与禁忌中的标准性共识一样,行为模式也给人类的法律行为提供了界限。所不同的仅仅在于,禁忌中的标准性共识一般表达为“不可为”,而法律行为模式所表达的,除了“不可为”之外,还有“可以为”和“必须为”。表达方式的拓展,并不仅仅是语词意义上的丰富,而且反映出法律作为一种更高级的社会控制方式,在复杂和精密程度上都要高于禁忌体系。而其背后所体现的,就是作为人类标准性共识的知识体系之不断丰富和发展。庞德指出,在人类刚开始出现法律时,道德、宗教、法律,当然也包括更早的禁忌,它们之间是没有明显区分的,在希腊城邦中,“人们通常使用同一个词来表达宗教礼仪、伦理习惯、调整关系的传统方式、城邦立法,把所有这一切看作一个整体;我们应该说,现在我们称为法律的这一名词,包括了社会控制的所有这些手段”。因此,从禁忌到道德、宗教、法律的发展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人类标准性共识体系不断多样化和精细化的过程。

那么,法律体系中的结果性共识又是如何表现的呢?首先,就共识的内容来说,不仅包括对违法(犯罪)行为的否定和制裁,还包括对合法行为的肯定和保护。也就是说,对于符合标准性共识的行为,会给予肯定和保护,而对于违反标准性共识的行为,则给予否定和制裁。这一点,明显有别于禁忌体系,后者只对违反禁忌的行为设定后果,而对于服从禁忌的行为,则不采取任何措施。结果性共识在法律体系中的拓展,缘于人类社会生活的不断复杂化,客观上要求对人类的行为进行更加细化的分离处理。其次,就维护结果性共识的手段来说,法律主要借助于国家的物理性力量,而不是超自然力量。这主要是由于人类认知水平的提升,对自然现象有了更为理性的认识,对人的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联系也有了更为科学的认知——在禁忌体系中,行为与结果之间的联系往往是基于某些错误的假定。例如,在当时的人们看来,通奸与土地不育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或者至少他们愿意相信这种因果联系。这种奇特的假定,除了是因为当时人们认知水平的局限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前面已经提到的,这是一种团体性共谋,它必须这样假定;否则,社会秩序便难以建立。然而,法律体系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世俗化和理性化而来,禁忌体系中的某些观念和做法已经很难获得人们的认可,因而,法律体系中标准性共识的维护,无论是表现为结果性共识之具体内容的设定,还是应对违反标准性共识的外在手段,都不可避免地世俗化和理性化了。最典型的体现是,对于破坏规则者的制裁手段,不再是超自然的或神圣的,而是实在的和物理性的,其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国家制裁。
四、结论:禁忌为法律准备了秩序模型
禁忌不仅是“整个社会秩序的基石”,也是人类通往秩序之路的最初实验。作为人类最早的秩序化实验,它给后来的社会控制带来了很多经验和启示。在此,让我们回到本文标题所提出的问题:禁忌为法律贡献了什么?简言之,它为法律准备了基本的秩序模型。为什么这么说?
一个完整的法律秩序模型,包括三方面的要素。一是规范要素,也即存在一套行为规范体系,告诉人们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事情不能做——这是法律秩序形成的前提条件。二是主体要素,也即社会中的人们从内心普遍认为遵守规范是生活所必须(心理要素),并且大多数人事实上也在践行规则的要求(行为要素)——这是法律秩序形成的主体条件。三是外在保障,也即社会事先准备了一套惩罚机制,以不仅威慑那些试图违反规则的人,也压制和惩罚那些已经违反规则的人——这是法律秩序形成的保障条件。
可以说,构成法律秩序的这三个要素,都可以在禁忌体系中找到。换句话说,禁忌为人类的法律贡献了基本的秩序模型。首先,从规范要素来看,禁忌为社会提供了一套规范标准,告诉人们什么行为是不能做的,这在法律中体现为禁止性规范——人类早期的法律规则,主要以禁止性规范的形式存在;到了后来,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不断提升,义务性规范和授权性规范才逐渐出现在法律体系中。其次,从主体要素来看,一方面,禁忌唤醒并培养了人类的良知与责任,让人们从内心将遵守规则作为自己的义务,从而为法律秩序奠定了主体心理基础;另一方面,禁忌帮助人们养成了自我克制的行为习惯,使他们惯于用实际行动去践行规则的要求,从而为法律秩序提供了主体行为基础。最后,从外在保障来看,禁忌为人类的犯禁行为准备了一整套威慑和惩罚机制:一方面,以结果性共识的形式告诫人们,如果违反规则,将导致怎样的不利后果;另一方面,倘若这些后果没有自动显现,则采取集体报复的方式重申规则的不容挑战。后起的法律将这一套保障机制完整地借鉴过来:一方面,通过在法律规则中设定法律后果的方式,来告诫和警醒人们,遵守或违反规则,将面临完全不同的法律后果;另一方面,当人们事实上违反规则时,又通过警察、法院、监狱等机构实施相应的惩罚。总之,禁忌从规范要素、主体要素和外在保障三个角度为人类法律体系建构贡献了一个基本的秩序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