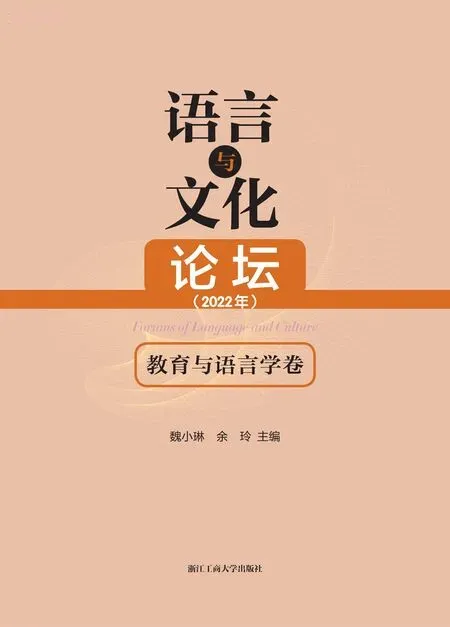阿拉伯亚里士多德学派的哲学思想
2022-11-08程奇
程 奇
1. 前言
阿拉伯人的哲学研究始于伊斯兰教创立之后。在伊斯兰教创立之前,也就是阿拉伯历史上的贾希利亚时期(又称蒙昧时期),阿拉伯人对哲学的认识以形而下的方式出现在他们的神话传说、历史诗歌和偶像崇拜中。由于地理上的相近,古代阿拉伯人在与埃及、两河流域居民的商业往来,以及生活迁徙中,受到了神灵崇拜和命运前定神学思想的影响,于是蒙昧时期的阿拉伯人就以石头、木雕、贝壳等各种物体作为自己的守护神。此阶段他们并没有统一的、形而上的哲学思想,更谈不上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中涉及的宇宙观、灵魂观、形式与质料等若干范畴。
伊斯兰教创立后,阿拉伯人的世俗生活和精神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代替了之前的神灵崇拜,成为阿拉伯哲学的思想之源。伊斯兰教的教义不仅成为世俗秩序的制定准则,也成为阿拉伯人宇宙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基本参照。阿拉伯人在政权及疆域稳定后,开始将重心转移到帝国的文化建设层面,在阿巴斯王朝时期,受益于哈里发的积极鼓励和包容开明,阿拉伯的思想家、文学家和科学家可以不受血统、民族和宗教信仰的限制,进行自由的学术辩论和思想交流,这使得阿拉伯人能在百年内,全面翻译吸收希腊、波斯、印度等哲学思想的精华,哲学一词(古希腊语philosophia,阿拉伯语音译为falsafah)也在“百年翻译运动中被译为阿拉伯语进入伊斯兰教的语言”(马效佩,2011)。阿拉伯学者根据秉承的不同哲学理念可大致分成2种派别,一种是宗教哲学学派,该派又可细分为3类,分别为以正统经院哲学为基础的艾什尔里派,以新柏拉图主义兼具唯理主义为基础的穆尔太齐赖派和以神秘主义为基础的苏菲派;另一种是自然哲学学派,该派坚持伊斯兰教的主导性,提倡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实证研究方法,努力使宗教与哲学融为一体,被称为阿拉伯亚里士多德学派。无论是哪一派的阿拉伯哲学家,以何种理念作为自己哲学思想的理论支撑,他们都相信伊斯兰教的经典《古兰经》,并承认安拉是最高的存在。
2. 阿拉伯亚里士多德学派的诞生与派别
阿拉伯亚里士多德学派萌芽于倭马亚王朝后期,在阿巴斯王朝时期得到蓬勃发展。该派哲学家不但熟谙伊斯兰教义,而且精通多门自然科学,并在医学、数学、天文学、音乐学等某一领域颇有造诣,他们学识渊博、贯通东西,足迹不拘于一隅,并且掌握拉丁文、古叙利亚文或波斯文等一门或多门外族语言。在阿巴斯哈里发马蒙统治时期,首都巴格达成为中世纪阿拉伯东方的科学文化中心,生活在帝国统治下的学者云集于此,用阿拉伯语翻译并研习了希腊-罗马哲学思想及来自东方的印度哲学文化,在此过程中形成了唯理主义的自然观、宗教观及社会历史观。他们对哲学的认知不再像普通民众那样,只满足于表面的形式化的教义诵读,而是力图在宗教信仰中加入理性主义,强调以自然科学和逻辑理性解释哲学问题,用哲学论证的方式自由讨论伊斯兰教义和宗教信条,具有强烈的世俗倾向。
该派哲学家在阿拉伯语中被称为“侯凯玛”派(意为“智者学派”),8—12世纪是其辉煌时期,他们在伊斯兰教正统思想占统治地位的背景下,以唯物论和辩证法为研究方法,同经院派哲学家展开了长期的激烈论战。随着阿巴斯王朝的分裂,该派哲学家在历史时空上大致分为东西两大学派,即分别以巴格达和科尔多瓦(西班牙,当时为后倭马亚王朝首都)为中心的亚里士多德东方学派和亚里士多德西方学派。东方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肯迪(796—873,拉丁名:阿尔金底)、拉齐(864—924,拉丁名:雷扎斯)、法拉比(872—950,拉丁名:阿尔法拉比乌斯)、伊本·西纳(公元980—1037,拉丁名:阿维森纳)、精诚兄弟会(10世纪产生于巴士拉);西方派的代表人物有伊本·巴哲(1095—1138,拉丁名:阿芬帕斯)、伊本·图菲利(1100—1185,拉丁名:亚勒巴瑟)、伊本·路西德(1126—1198,拉丁名:阿威罗伊)、伊本·赫勒敦(1332—1406)。
3. 阿拉伯亚里士多德学派兴起的文化土壤
阿拉伯亚里士多德学派的兴起与阿拉伯帝国的领土扩张、希腊罗马文化的先前浸透息息相关。在四大哈里发和倭马亚王朝的开疆拓土后,阿巴斯王朝的版图横跨亚非欧三大洲,不仅包括整个阿拉伯半岛,还包括地中海东南沿岸的沙姆和埃及等地,波斯、亚美尼亚、怛罗斯(今哈萨克斯坦)乃至印度的西北部。在伊斯兰哲学进入之前,希腊哲学的东渐和东方哲学(阿拉伯人视角下的东方主要指波斯、印度)的西传已经交织存在近百年。其中,希腊哲学对地中海沿岸国家的影响更为深刻。早在公元前4世纪时,马其顿帝国就已征服埃及、小亚细亚、波斯等地,把希腊哲学和文化传播至东方的领土。后来,亚历山大又征服了叙利亚、腓尼基(地中海东岸)、埃及等地,并重新占领波斯,进军印度,推进政治东移,间接促成了东西哲学思想的互通了解。在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安敦尼王朝拥有日耳曼行省、西班牙和高卢行省、叙利亚行省、阿拉伯行省、亚美尼亚行省和亚述行省等;至戴克里先在位统治期间,他把其治下的领土划分为100个行省和作为特别行政区的罗马城,行省的数量达到了极限。
罗马帝国的行省制度推动了希腊哲学的东渐和接受,对东方阿拉伯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地中海南岸的叙利亚、埃及都曾经是罗马帝国内希腊化程度非常深的地区。在翻译、研究希腊经典方面,叙利亚和亚历山大同样赫赫有名,但叙利亚人更喜欢亚里士多德哲学,而亚历山大则偏向新柏拉图主义。杜丽燕(2015)认为,伊斯兰教征服叙利亚以后,首先从他们的被征服者那里获得了希腊哲学的知识,受叙利亚人影响,阿拉伯哲学家从一开始就认为,亚里士多德比柏拉图更重要,他们也像自己的被征服者一样,认为亚里士多德最重要的是逻辑学。段德智(2012)认为,在继承和使用哲学遗传方面,中世纪阿拉伯哲学与中世纪欧洲经院哲学或拉丁哲学一样,所继承和使用的主要是希腊哲学遗产,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遗产。
罗马帝国崩溃后,阿拉伯帝国开始崛起。从伍麦叶王朝后期到阿巴斯王朝后期,阿拉伯学者在研习《古兰经》的同时,将眼光转向了欧洲,当时欧洲古代学者(如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普罗提诺、亚历山大、托勒密等)的经典著作几乎都有阿拉伯文译本。而在阿巴斯王朝灭亡之后,欧洲人又依据阿拉伯文的译本,再把古代欧洲学者的哲学或科学著作重新翻译成拉丁文。刘晓文(2003)认为,古希腊文化在经历东方与非洲的长途旅行后,又回到了欧洲。阿拉伯哲学家在研习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时,融入了自身的思考与注释,使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带有新柏拉图主义和东方感性色彩。马坚先生(1958)认为,伊斯兰哲学的功绩不仅是把希腊哲学保存了下来,而且加以发扬光大……伊斯兰哲学进入欧洲后,黑暗时代的欧洲人才听到亚里士多德的名字,才接触到希腊哲学,对哲学研究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假若阿拉伯人征服波斯、埃及和叙利亚的时候采用了蒙古人征服中亚细亚各国的野蛮方法,那么欧洲的文艺复兴可能会推迟几百年。
4. 阿拉伯亚里士多德学派的代表学说与社会影响
阿拉伯亚里士多德学派的哲学家虽然努力使哲学摆脱宗教教义的束缚而独立发展,但从本体论来看,他们都确信宗教神学的根本存在,但他们也认为,安拉对宇宙万物的作用是间接的,安拉的精神有若干媒介。从认识论来看,他们都倾向唯理主义,认为人类可以通过感性经验和理性认识获得知识,感性经验的对象是个别事物的现象形式,理性认识更接近事物的本质属性。他们的哲学研究是在神学的底座上,以逻辑与实证为支架,构造出人对自然世界、万物之理的认识与理解。
4.1 阿拉伯亚里士多德学派的“灵魂流溢说”与“灵魂净化回归说”
中世纪阿拉伯亚里士多德学派哲学家的“灵魂流溢说”受到罗马时期哲学家普罗提诺(205—270)“流溢说”的影响。普罗提诺出生于埃及,分别在亚历山大和印度研习过希腊哲学和东方哲学,其学说融合了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论、柏拉图学派的宇宙生成说及东方神秘主义的超验说和轮回说。普罗提诺的“流溢说”认为万物从“太一”“理智”“灵魂”3种原初派生,但这三者并不平等,而是存在层级关系。万物先由先验本原“太一”为起点,“太一”是人的认识完全无法达到的;从“太一”漫溢出的第二层本体是“神圣理智”,这相当于柏拉图的“相”和亚里士多德的“纯粹自我观照”;由“神圣理智”再漫溢,产生了第三层本体——“宇宙灵魂”,即世界的主导原则;“宇宙灵魂”虽然位于最低的第三级,但却是具体万事万物的创作者。从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论解释,“太一”是零,不是“一”。
普罗提诺的“回归说”经历的历程和“流溢说”正好相反,他认为,由于灵魂转向自然,同物质接触,这一必经的过程不可避免地使灵魂遭到玷污,使其堕落,而灵魂本质上属于更高的世界,最终它将摆脱对感觉的贪恋,回归“太一”,达到与神同在的境界。灵魂回归“太一”的首要条件是通过净化、与肉体分离,以上升到理智世界,最终达到“如实观照”的神的最高境界。毕哥达拉斯学说和印度哲学都有轮回的概念,不同的是,毕达哥拉斯学派在宣扬灵魂不朽、追求灵魂净化的过程中特别强调“爱智慧”,即爱智的生活方式和教育本质,并认为“数”是最完美、匀称、和谐的智慧。他们把数当作世界的本源,人的灵魂可以在对数的研究或玄思默想中实现净化,使之上升为纯洁的灵魂,摆脱肉体轮回的命运,达到神的境界;而印度教的轮回理论源于对生命世代轮转传承的启发,初期的轮回思想非常朴素,其范围不限于有情的天、人、鬼神及一般动物,也可能遍及植物,轮回思想起于梵书时代,成熟于奥义书时代,是印度各派宗教的共通思想。
阿拉伯亚里士多德学派的哲学家,在研究和继承波斯印度和希腊罗马的东西方哲学遗产上,力图在宗教神学信仰中融入人的理性认知,将自然哲学的研究逻辑与宗教哲学融为一体,进而提出了阿拉伯的“灵魂流溢说”与“灵魂净化回归说”。阿拉伯哲学史上公认的第一位亚里士多德学派的哲学家是肯迪,他曾长期学习过印度婆罗门教的梵的哲学,并写出了论文《真主使者的确证》和著作《依逻辑学家的方式论证先知说》;在受任于哈里发马蒙的指派后,他在智慧宫里翻译了大量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著作,以及普罗提诺《九章集》的第4—6部分,为阿拉伯哲学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肯迪认为,宇宙万物为安拉所创造,万物由它循序流出,物质仅具有精神“流出”的形式。安拉的精神是为一切作用之本原,但安拉对宇宙万有的作用是间接的,二者之间有若干媒介;他把宇宙万有的原始实体划分为5种,分别是物质、形式、运动、时间、空间,它们彼此之间具有普遍的因果联系,运动和变化是一切事物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天体星辰的运动和变换有它本身的规律性。
下一位杰出的亚里士多德学派哲学家是拉齐,他也是杰出的医学家,他的学识深邃广泛,被誉为“穆斯林医学之父”。拉齐在晚年才将重心转移到哲学研究。他认为世界的5种本原由造物主、宇宙的灵魂、原质、绝对的时间、绝对的空间组成,这5种本原同时并存,是世界存在的基础。在“灵魂流溢说”方面,他认为安拉是万物之本,“流溢”出万有,首先流出的是“精神之光”,随后流出理性和“荫”,而荫又构成冷、热、燥、湿4种状态,自然万物便由这四态构成。安拉还赋予了人以感觉和理智,人凭感觉而认识存在,由此证明物质的存在;而理智促使人研究哲学,帮助灵魂摆脱物恋的烦恼,从而上升到更高的智慧世界,复归于安拉。
与拉齐一样,法拉比和伊本·西纳也是著名的医学家兼哲学家,同时,法拉比在中世纪的“三学”(语法学、修辞学、伦理学)和“四知”(算术、音乐、几何、天文原理)上也颇有造诣,是一个全能型学者。法拉比出生于中亚,学术上除了受到罗马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影响,还深受摩尼教、马兹达克教、中亚南部的木鹿学派和中国学术的影响。法拉比兼具自然科学的实证逻辑和宗教哲学的隐喻抽象素养,他将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和新柏拉图主义著作做了详细地区分,并做了深刻、精辟、创造性的注释,从而使其得到“新生”。他受新柏拉图派“流溢说”的影响,认为安拉是宇宙万有第一因和目的因,宇宙万有源自造物主流出,安拉流出了理智、世界灵魂和物质,通过万有表征其存在,外部世界是物质的,是由土、水、火、空气4种物质元素和干、湿、热、冷4个基本特性所构成的物体组成。运动和变化是物体的特性,发展是变化的过程,变化是发展的结果,事物的必然性便是宇宙的规律,宇宙万有同一于安拉的纯粹精神。
伊本·西纳是阿拉伯亚里士多德东方学派的最后一位集大成者,他出生于今乌兹别克斯坦第三大城市布哈拉城附近,青年时任宫廷御医,后辗转花剌子模和波斯。他所著的《医典》是中世纪亚欧地区的主要医学教科书和参考书,因此被尊为神医,同时他也是天文学家、数学家和哲学家,主张世界有意识和物质2个独立本原的哲学二元论学说。他认为,世界的本源是由意识和物质2个实体构成的,肯定物质世界的永恒性、不可创造性,同时又承认真主是永恒唯一,反对灵魂轮回说和死者复活说。“他认为,真主是不可分的太一,是真正的完满,是纯粹的仁慈,是不断活动的原动力的理智,这一理智以流溢来创造宇宙和宇宙间的万物。在太一之中,理智和意志是同一的,因此,太一流溢出宇宙及万物的过程,是太一或真主用思想和精神创造世界的过程。” (杜丽燕,2015)
在亚里士多德东方学派中,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哲学家团体,即精诚兄弟会。精诚兄弟会构建了一种他们认为是可以用来解释宇宙的数学结构(从宏观角度),这种结构可以引导求知者发现自己灵魂的真实本质(从微观角度),也是了解形而上学和神学真理的第一步。(François Beets,2015)精诚兄弟会是组织机构严谨的秘密社团,社员通过撰写有关灵魂、道德、哲学、社会、国家等方面的学术论文进行彼此交流和考察,他们所写的论文首先在内部传阅,在合适的时机才向外部传播。目前,精诚兄弟会流传下来的作品有52篇,内容涵盖数学与逻辑、科学与物质、本能与理性、神学与教义4个方面,毕达哥拉斯的数论是精诚兄弟会的思想哲学基础,他们以数论为学术和哲理研究的本源,结合“流溢说”,充分地论证了伊斯兰教“真主独一”的神学观和以真主为核心的宇宙观。他们认为,真主利用无形也无象的“第一物质”创造了形与象各异的物质世界,就如同数字“一”先于其他数字而存在,然后,天地万物按照先后次序,层层叠叠依次展开,其中天体星辰先于地球的四大元素水、火、土、气而存在,四大元素又先于矿物、植物和动物而存在,这些“物”作为宇宙的组成部分,必须在一个无与伦比的力量支配下,相互依存、彼此维系、协调运转。在灵魂“流溢”产生后,必须经历彻底净化才能复归“太一”,彻底净化必须具备2个前提,一是求知好学、净化自我;二是寿终正寝、肉体死亡。如果戴罪的灵魂没有通过求知和升华的途径净化,肉身死亡后,灵魂也只能坠入黑暗的深渊,继续受到折磨和惩罚。
4.2 阿拉伯亚里士多德学派的“双重真理论”
阿拉伯亚里士多德学派的另一主要学说是“双重真理论”,该学说认为通过理性和宗教都能通达真理,哲学与信仰并不是矛盾对立的。哲学家肯迪开创了阿拉伯“双重真理论”的先河,他的哲学思想深受亚里士多德、新毕达哥拉斯派和穆尔太齐赖派的思想影响,强调哲学和宗教在寻求真理上是一致的,提倡自由讨论教义,用哲学论证宗教信条。肯迪倾向唯理主义,他认为感性经验能接触到的是现象形式,理性认识才能接近事物本质的种和属,现象与本质之间具有联系,人可以通过感性经验和理性认识获得知识,而哲学则有助于人们提高对事物的认识能力,这在一定程度上把神学排除在外。法拉比认为,科学与宗教是不同领域内的知识和真理,哲学和科学是人们探索自然的因果关系和为人类谋求幸福进步的知识,是普遍意义上的真理;而宗教是属于人们的思想信仰和社会道德准则范围内的真理。他认为纯理性的价值高于宗教的价值,科学是人们探索自然的因果关系和为人类谋求幸福进步的知识,是广泛意义上的真理,而宗教是属于人们的思想信仰和社会道德准则范围内的真理,哲学和神学的区分在于逻辑方法。伊本·西那也赞同“双重真理论”,他认为宗教和哲学是可以各自独立的,他承认真主的直接启示,认为它高于认识的真理;但是他又认为,宗教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因此有助于发现真理和获得幸福的哲学,归根结底是高于宗教的。
伊本·路西德是最晚出现,但影响最为深远的亚里士多德学派哲学家。他以研究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著称于西方,仅流传后世的哲学、宗教方面的著作就多达118部,他曾被聘任为地方教法官和宫廷御医,曾奉哈里发之命翻译并注释了亚里士多德的全部哲学著作,他将伊斯兰的传说与希腊哲学,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融合并形成了自己的哲学体系。他非常推崇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把它说成是最高的真理,人类的理解力所能达到的极限。在其著作《哲学和宗教联系的论断》中,他将“双重真理论”学说阐释得最为详尽,认为宗教和哲学二者并不相悖,而是结伴而行,相辅相成。“但他又认为宗教和哲学各有侧重点,信仰和理性是在不同的层面活动的,对于在习惯影响下而形成自己观点的众生来说,有一个绝对信仰的权威就足够了,而哲学则是沿着少数人所能理解的纯粹思辨的道路前进的,他们是吸收抽象的、根据推理得来的真理的人,这些人要求的是探讨未知的真理,因此需要哲学去指示道路。”(蔡德贵,1988)
伊本·路西德认为,宗教真理来自“天启”,是对人们的训诫和约束人们道德行为的规范,旨在止恶扬善,维系世道人心。宗教的基础是真主的启示,因此宗教的真理具有象征性和寓意的形式,宗教是为大多数人所创立的,是群众在习惯中形成的;哲学的真理来自“理性”,是通过纯粹的思辨来理解真理,是供少数人理解的,它是真理的最高表现形式,旨在认识宇宙万物,并推证造物主的存在,哲学理论高于宗教信条。但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哲学与宗教的意见可能会发生矛盾,从哲学的观点来看是真理的东西,从宗教的观点来看可能是错误的东西,反之亦然。因此,一个作者在其哲学著作中可能推翻他在神学著作中的主张,反之,他也可能在其神学著作中否定他在哲学著作中的主张,这是由于各自的认识范围不同。因而,真正的宗教并不反对哲学研究;真正的哲学也不反对宗教,只是排斥宗教对科学和哲学领域的干扰。针对以加扎利为代表的反对派的主张,他写了《哲学家矛盾的矛盾》(又译《驳“哲学家的矛盾”》)一书,对加扎利《哲学家的矛盾》一书中提出的20个问题,采用逻辑论证的方法,逐句逐段进行分析并加以理性反驳。
伊本·路西德主张除了天启的信条,一切事物都应该服从理性的判决,并充分肯定妇女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他认为,妇女之所以不被重视,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制度不允许妇女表现自己的才能,人们觉得妇女生来就是生育和抚养孩子的,这种奴隶地位消灭了妇女做某些更崇高的工作的才能。伊本·路西德的“双重真理说”,不仅在较大程度上恢复了亚里士多德学说的原貌,而且发展了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因素。他继承和发展了亚里士多德哲学思想中科学和理性的倾向,综合了阿拉伯东、西方伊斯兰哲学家的思想成果,并在同正统教义学家安萨里等人的论战中,使哲学摆脱宗教的束缚而得到独立发展。从肯迪开始,阿拉伯哲学家“力图调和哲学和宗教的矛盾,这种折中主义,实际上是‘双重真理’的前奏,他们的努力有时成功,有时失败,伊本·路西德则是系统地和完整地提出了‘双重真理’的理论,并且明确地把哲学置于宗教之上,全力论证这一理论的正确性,使他的敌人无法在理论上压倒他,不得不采用武力镇压他”(李振中,1984)。
12世纪后,伴随着后倭马亚王朝的彻底覆灭,阿拉伯哲学也黯然失色。但是,伊本·路西德有关亚里士多德的研究著作和成果,由西班牙流入欧洲,极大地促进了西欧哲学和科学的发展,并对中世纪基督教的经院哲学起到了重要影响。伊本·路西德哲学思想中的唯物主义观点成为基督教会及神学家攻击的目标,因为他的许多基本观点,都是同天主教正统信仰不相容的,使西欧人耳目一新,为之震撼。但正统经院哲学家把他的学说视为最危险的异端邪说,力图禁止他的著作流传,同时又采纳他的注释式的论证方式和思辨方法,借以维护天主教神学。在欧洲经院哲学内部,反对派则力图通过伊本·路西德来巩固和发展自己的观点,并以此去解释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欧洲学者西格尔等进步的思想家把他的著作改头换面,作为法国巴黎大学的教科书,开创了西方唯理主义哲学的基础,并且以巴黎大学和意大利巴杜亚大学为中心建立了阿威罗伊(伊本·路西德的拉丁名字)主义学派,他的学说在欧洲思想界影响长达400年之久,意义深远。
4.3 阿拉伯亚里士多德学派的社会影响
从阿拉伯亚里士多德学派哲学家的学术观点和社会影响上看,他们在自然科学及哲学方面有深入的研究,强调理性认知与经验总结,并具有强烈的世俗倾向。在一些具体哲学问题上,他们尽力排除神学,用从亚里士多德和新柏拉图主义那里获得的哲学理念,对《古兰经》及伊斯兰教的教义进行种种解释,并得出了支持泛神论或唯物论的结论,给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伊斯兰正统教派很大的冲击。他们的高光时刻往往与政权的需要同频共振,但他们同时又坚持学术的独立性、深刻性和批判性,往往提出与哈里发政权相左的观点,继而又遭到压迫和流放。比如被称为“阿拉伯哲学的先驱”的肯迪,因大力提倡以理性主义调和宗教信仰,自由讨论教义,还对《古兰经》的语言风格、编排次序等内容提出异议和质疑,被正统派教义学家斥为“叛教异端”,他的大部分著作被焚毁殆尽,晚年也因遭谗佞被哈里发穆泰瓦基勒免职;而伊本·西纳,虽然一度官至宰相,但政敌太多且不擅于政治周旋,不得不一个接一个国家的逃亡,以躲避追杀;还有伊本·路西德,在其担任大法官时,因被正统派教义学家“指控”其著作有异端思想而被新任苏丹下令放逐,他的宗教、哲学著作也被付之一炬;至于伊本·赫勒敦,则一生宦海沉浮,既享遍人间富贵,也饱受世事心酸。
到了阿巴斯王朝后期,国家内部矛盾和民族矛盾激化,导致群雄割据、起义不断,阿巴斯的领土已经分崩离析,它与在什叶派在埃及建立的法蒂玛政权、希沙姆之孙在西班牙建立的后倭马亚政权共同存在,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国家的动荡和民生的艰难使得阿拉伯哲学家的关注点更多聚焦在国家、社会、民生层面。比如法拉比在老年时撰写的《高尚城市居民书》一书中,提出了创建高尚社会即“高尚城市”的思想观念,深刻论述了创建高尚城市所必备的道德、教育、政治理念,从国家及政权的宏观视角思索众生实现幸福的途径。而精诚兄弟会则提出了含有一定辩证思想的政治观,他们客观总结了阿拉伯帝国的统治经验,对先知政治、帝王政治、民众政治、家庭政治和个人政治这5个方面做了详细的阐述。他们认为,“先知政治”,就是劝说人们从邪恶的信仰、粗鄙的行为中解脱出来,通过循循善诱,以理服人,引领人们皈依伊斯兰教;“帝王政治”,是以逊奈教派为基础,制定教法教规、树立社会良好风气;“民众政治”,是指为官者要对民众实施有效而适当的治理;“家庭政治”,是指以家庭利益为基础,妥善安排琐碎的家庭事务,构建良好的亲朋关系、主仆关系等;“个人政治”,是指个人要努力提高修养、端庄言行,将自己培养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这5个方面都做好了,人类才能一起把世界建设得更美好。可见,精诚兄弟会的关注焦点已经不满足于深奥的理论研究,而是立足于现实,寄望于以神之名义,约束规范统治阶级,建立一套由神及人的社会治理范式。
阿拉伯亚里士多德学派哲学家的学说为阿巴斯王朝开拓了文化繁荣的新局面,把阿拉伯哲学和科学研究推向了高潮。他们因提倡运用理智来自由讨论伊斯兰教的信条、反对宿命论的前定说,与正统宗教学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哲学研究后期,他们的关注重点由阳春白雪转变到下里巴人,更加注重哲学研究对社会民生的影响。他们在经历了跌宕起伏之后,仍具有积极的共同价值情怀,试图凭一己之力影响或抗议统治阶层的决断,改变社会的面貌,实现众生的幸福。
5. 结语
亚里士多德学派哲学家在遵循天启圣道的基础上,汲取了古希腊罗马学说中有关灵魂与质物、顿悟与理性、流溢与回归的学说,丰富了阿拉伯伊斯兰哲学的理论内涵和逻辑思辨,对摆脱宗教教义的强制束缚和思想枷锁、取得思想解放和科学进步具有积极意义。他们留下了古希腊与古代东方哲学的阿拉伯语译本,这些译本通过西班牙又流回欧洲,进而被重新翻译成拉丁文,给西方学者创造了重新学习和研究古希腊哲学思想的机会,进而推动了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发展,也给世界的文明史留下了宝贵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