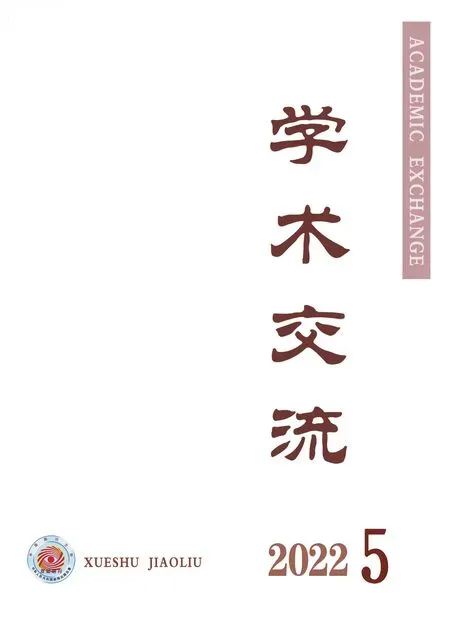数字经济视域内的历史学
2022-11-08张晓校张媛媛
张晓校,张媛媛
(哈尔滨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哈尔滨 150025)
2022年1月中旬,国务院印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对数字经济发展提出具体要求。3月13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加强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数字经济上升为国家战略,不是第一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早在2017年,“报告”就曾经强调“推动‘互联网+’深入发展、促进数字经济加快成长”。作为国家战略的数字经济如火如荼,是疫情时代中国经济率先复苏的动力,预示了“后疫情时代”社会经济发展大势。有论者谓:“数字经济对所有经济领域都产生了影响。”既然影响了各个经济领域,波及历史学是题中应有之意。数字经济伴随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互联网等信息技术、数字化技术发展成长。数字技术影响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数字转向”似乎可视为“前数字经济时代”的先行实践。进入数字经济时代,“转向”升级为“转身”呈必然趋势。
一、数字经济与历史学交集
历史学与数字经济发生交集,决定性因素在于同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存在”,不是数字经济“绑架”了历史学,而是历史学“被镶嵌”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经济是建立在数据、数字技术基础上的经济样态,电子业务、数字服务、平台经济等是数字经济的主要内容,经济向数字化转变,信息和信息技术成为一个国家的重要资源。所有信息转化为数字化形式存在、传递和储存,信息数据是关键的生产要素和新型资源。数字经济和历史学发生联系,或数字经济对历史学产生影响,两者交汇点在于数据和信息。和数字经济一样,数据是数字经济时代历史学的重要资源——既可以是已经数字化的史料源泉,也可是各种学术研究成果的信息发布、资料传递;先前许多以纸质文本为主体的各种学术(教育)文本,陆续实现数字化,速度之快、范围之广、普及程度之高,令人应接不暇。信息时代、网络时代,历史学许多文本文献完成向电子化、数字化过渡,实现了“数字转向”,“数字信息日益丰富”,为历史学发展创造了多于以往的机遇。在数据信息方面,数字经济和历史学异曲同工,殊途同归。数字经济时代,历史学的数字化或数字史学,建立在“前数字经济时代”信息技术基础上。数字经济前期的一系列技术发展与铺垫,历史学一应俱全,信息(数据)资源及其获得方式、路径框定了历史学数字化的存在和发展。人们对数字经济和大数据之间的关系议论颇多,各种信息汇集、汇聚的大数据的基本含义说明大数据同数字经济、数字经济时代历史学之间的天然联系: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的数据量,且还会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大数据一经问世,便对人类的日常生活、科学技术发现与创新等都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成为“创新、竞争的下一个前沿领域”,是“科学技术领域最热门的词汇”,深深浸入日常生活中。信息量增加意味着人类社会知识总量上涨,对于数字经济表现为扩大市场边界,对于历史学则是研究内容增加、知识量增多,扩大了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的边界和容量。信息和数据量增多、飞跃性积累,显而易见的后果是历史学学术研究“体量”增大,知识传播效率大幅度提高。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可以对碎片化信息知识进行整合分类”,能够推进经济发展的创新。对于历史学发展进步,碎片化史料的整合是利好的“福音”。通过整合碎片化史料,诸多零散分布,甚至不易“察觉”、不易发现、不易利用的史料得到发掘使用。实践中,整合碎片化、零散化史料用于系统性专题研究,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现有史料之不足,计量史学研究获得了从前得不到的史料支持。整合碎片化信息数据,历史学获得了新的学术增长点,势必推动历史学走向深入。
共享经济是数字经济的核心内容之一。进入信息时代,诸多历史学文本完成了电子化、数字化,通过互联网传播传递,信息和知识资源的分享与共享成为现实——互联网的开放性打破了知识壁垒,互联网普及程度、数字化普及水准同升共涨。互联网没有森严的“入门条件”,亦无身份要求和限定,“知识形态是平等主义的”,通过互联网实现各种共享。信息共享带给历史学的后果堪称积极,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工作者主动把自己的作品放在互联网上,或及早通过微信推送,乐于和他人分享自己的创新成果。然而,仅有互联网的开放性,尚不足以说明分享与共享的意义,互联网本身拥有的“无数不同来源的巨量信息”,为“分享”创造了“物质条件”,使“分享”有具体内容可“分”可“享”。称互联网为“知识富矿”,或许并不为过。
面对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历史学工作者对数字技术不同把握或运用程度,有学者宣称“许多历史学家已经成为了‘数字史家’”。尽管数字技术对历史学影响深厚,相当数量的历史学家掌握了较为精深的数字技术,但历史学工作者成为真正的“数字史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历史学家更有太多的“功课”要做。
二、传播学意义的考量
数字经济所处时代是社交媒体时代。数字经济和社交媒体相互交汇,反映出数字技术、数字传媒对数字经济的作用。固然不可以把数字经济称为“社交媒体经济”,但是离开社交媒体、互联网,“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的新型经济形态”的数字经济,难免举步维艰。“互联网被想象为一个代替一切旧媒体的新媒体”,是当代名目繁多的社交媒体的“集散地”以及信息数据的集中地。数字经济时代,社交媒体步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历史学 “乘”社交媒体之“船”“出海”,属顺应时代潮流之举。社交媒体之于历史学的价值意义,传播学可以提供佐证:数字经济时代—社交媒体时代是历史学步入的一个全新的传播时代。历史学在传播扩散过程中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传播介质(媒体)决定着历史学传播的数量和质量,以及历史学生存状态和发展的空间,其中大众传媒的贡献不可抹杀。大略而言,历史学传播经历了“口耳相传”——文字传播(包括图画)——纸质文本+机器——数字传播等几个阶段,似可简单归结为“前纸质时代传播”——纸质传播时代——“无纸化(为主)”传播。不同阶段的传播技术手段或载体(介质),决定着历史学发展的规模、档次。“(数字化)改变了历史学家的研究和交流的方式”,创造了从前无可比拟的、超越性特征明显的数字传播,立体化取代了平面化,速度、规模、效应、质量大幅度提升,为历史学平添新的活力。
数字经济充分利用平台模式——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的新型模式。数字经济主动发挥社交媒体平台具有的独特互动性——各种媒介正在从单向传递转变为“互动的媒介”,企业和客户之间、企业和企业之间可以通过平台互动——一种虚拟与现实之间的活动、虚拟之间的互动,世界上多家数字巨头无一不是利用平台做强做大的。平台和数字经济之间的关系、社交平台与历史学的关系存在诸多共性之处,但差异却是本质的。数字经济的平台是交易场所,而历史学的平台是社交场所,主要是信息和知识的传达或传授,各种思想和认识的碰撞。两者之间最为明显的相同之处是:数字经济平台的搭建目的是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历史学借助的平台也有配置资源、优化资源之目的,但这些资源是学术资源、教育资源、知识资源,与市场规律关系甚微;平台本身不生产任何产品,却可以为交易双方提供机遇和空间,历史学借用的平台主要用于思想观点、信息资料、研究动态,乃至学术会议的交流,是思想观点、知识文化的“集散地”。“前数字经济时代”,历史学占比相当多的(纸质)文本、资料(包括音频音像)、信息数据完成了数字化转向,已经介入、利用各种社交平台,数字经济背景下的一些平台是先前平台的延续和发展,历史学传播的数字化时代已是“进行时”。历史学相关的社交平台,对话、讨论、争辩、百家争鸣的功能比较突出,交流与碰撞远比利用平台展示、宣传思想观点重要许多。社交媒体平台改变了以往历史学单向度传播的模式——各阶层受众(大多数时候)被动地接受历史学家“灌输”各种历史知识,人人均可借助平台充当传播者。有人宣称,在(社交)平台上,“专业历史学家和业余历史学家共同建构过去”,强调了平台的开放性以及参与、共享的价值意义。所以,历史学专业的社交媒体平台交流、参与、共享是核心内容。
当下,应用最为广泛、发挥作用最大的媒介及其相关平台是微信,以微信社交平台和各种微信公众号为瞩目,各种学术杂志报纸无一不拥有自己的客户端,学者们把自己的成果及早通过微信推送,各种链接、智能手机为“掌上互联网”创造了物质条件。追根溯源,历史学传播真正的“升级换代”应归功于互联网,实现了“无纸化”飞跃,经济成本降低,真正的规模传播成为现实。互联网将历史学传播带入数字化时代,纸质文本经过数字化技术加工,变身互联网的信息数据,“光速”传播,效率空前。当然,最重要的是,“在互联网虚拟空间之内,历史学得到大批量传播,而且没有放缓的迹象”,且传播主体多样化。和从前任何一次重大传播学技术进步相比,数字技术大获成功,原因之一在于传播成本降低。其中,能够看得见、体会得到的是时间和空间成本降低。人们津津乐道的各种“跨时空”议论,肯定了时空节约的意义。由于诸多纸质文本完成了向数字化的“华丽转身”,历史学工作者充分体会到“简约化”“简洁化”带给历史学研习的便捷。一个人所共知事例是,无论身居何处,只要互联网通达,那些已经“数字化”的文本,即使在大洋彼岸某个图书馆,瞬间到达,不是虚言。数字检索的快捷和优势,似乎让人们遗忘了“书山文海”中寻觅繁复手工劳动之艰辛。数字技术之于历史学传播,节约时间成本的同时,空间成本的节约显示出数字技术、数字化跨时空、“压缩时空”对历史学研习的益处。涉及数字技术和历史学传播的空间,乃至历史学存在空间的关系值得展开研究、分专题研究。
如果仅仅是传播速度的提升,尚不足以全面说明数字技术和数字化带给历史学的积极效应,真正让历史学传播实现规模效应,在宽度广度和深度上的突破,互联网作为传播媒介的革命性飞跃值得考量。历史学传播实现“全天候”“全时态”、全方位、跨时空、立体化传播与传递。电子计算机、互联网正在模糊虚拟世界和有机物理世界的边界,对传统传播的冲击力不难理解。历史学虽然没有彻底告别平面传播,但声音、声像、影像传播陆续“加盟”,数字传播成为“主力”,传播增加了效能,提高了效率,“升级换代”名副其实,绝对优势是从前任何媒介技术无法比拟的。比如,“前数字经济时代”任何规模和档次的学术会议,“现场直播”、不同地域与会者“同步进行”、会议内外同时互动等,都相对困难,尤其是“现场直播”的发射与传输设备不是什么人都拥有的。如今,和电视广播的互动相比,数字化的互动是一种颠覆性的创新,“现场直播”“多方互动”“广泛参与”司空见惯,地理和物理空间阻隔不再构成信息传播意义上难以逾越的障碍。数字技术推动历史学传播快速进步过程中,从传统纸质文本平面化传播,到“有声有色”“声情并茂”立体传播,再到数字技术推动的数字化传播,可以切身感受到数字技术的“各项力量”。信息技术、电子计算机及其信息技术的应用,让历史学传播技术实现了生动形象的“视觉转向”。如果单纯从传播(技术)形式、手段上论及历史学传播及其升级换代,不免低估了由平面传播到立体传播革命性飞跃的价值。与网络化微信为代表的数字化传播相一致的是传播时空自由化,传播载体(纸质与非纸质)多元化,传播主体多元化,传播内容丰富多彩。由此,不难看到这样一个发展规律:简便易行的数字技术,为更多的人传播更多的历史学信息数据创造了参与条件和空间。
历史学传播的核心内容大致为两部分:一是各种史料的传播与传递,二是历史学学问知识信息的传播与传递,此处的知识信息又可分为各种研究成果的发布和流传,以及以历史学教育为主体的历史学传播、各种媒体介绍、传播的历史学知识信息等。在历史学传播升级换代过程中,历史学教育技术手段的跃迁前人无法想象,从电子计算机多媒体,到数字化和“远程教学”“云课堂”“云传播”,内容丰富多彩,用“目不暇接”形容各种数字化历史教育手段,亦不为过。一直处于更新换代的“云课堂”推动历史学教育、历史学知识传播进入新的阶段。在历史学传播史上,图书馆曾是传播历史学思想观点、信息知识的重要场所,作用无可替代。图书馆率先开始数字化步伐,“图书馆正在步入数字化时代,公共图书馆为读者提供在线服务,包括诸多个人没有订阅的各种期刊”。数字化图书馆或图书馆中与日俱增的数字化资源,加快了知识和文化传播,数字“器”之利得到认可。
历史学传播、数字经济的各种传播实现“光的速度”“海一样的容量”,计算机和互联网可以说功不可没。在人类传播史上,任何一项伟大的技术发明,都难以和电子计算机和互联网的技术贡献相提并论。当下,以微信为代表的社交媒体,依赖数字技术,传播触角伸向了社会的各个角落,历史学工作者对于各种信息的获得,微信所占比重甚大。社交媒体时代对史学影响最大的是传播规模扩大,速度提高,具有“全天候”、延时、即时等特征。一些线上课程的互动,即使身处穷乡僻壤、交通闭塞之地,其和大师级学者对话、讨论、分享世界级课程的机会依然均等。数字技术带给历史学传播飞跃式进步的同时,各级历史教学优质资源的分享与共享,让研习者切身感受到了“共享”的益处。
数字经济将推动产业升级,越来越多的企业迈上“云端”,推动历史学持续进步。借助互联网,“线上历史学”似乎正在和“线下历史学”平分秋色:在线学习、在线(远程)学术会议、“云交流”、信息发布、资料传递、课程教学直播等,线上线下相得益彰,“两线并进”得到普遍认同。在抗疫期间,线上课程、远程教学广泛运用,由“两线并进”变成了“一家独大”,证明了数字技术垂直作用于传播的价值。数字经济时代依然会延续先前一些数字化传播,但一定是“升级版”的传播。
三、数字经济与历史学内涵外延之扩大
数字经济是数字化技术发展的结晶,但绝非简单的“数字”+“经济”,不是流于空泛的“交叉学科”。数字经济以数字技术为驱动,注重数字化、数字技术及其服务、产品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地位等。其中,大数据、“云技术”“云计算”、人工智能、互联网等技术的进步对数字经济影响较大。数字化技术不断拓宽数字经济的边界,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大即为表现之一。数字经济时代的历史学,借助数字技术提供的便捷、快捷,扩大学术视野,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在现有“增量”基础上,持续扩大信息数据容量;通过“量的积累”,促进“质的飞跃”,拉动内涵和外延“增容”扩大。各种专业数据库陆续建立,史料及其他信息数据集约化、专门化,对提高历史学学习、研究、教学效率大有裨补,促进某些专题(专项)研究走向深入的拉动作用可以预料。实践中,信息技术、数字技术在多方面为历史学发展贡献了技术支持,某些专业方向迈上了新台阶,世界史即为代表。“和国际接轨”系学术界倡导多年的努力目标,数字技术让学术界开始接近这一目标。借助互联网等数字技术载体,历史学信息跨越“关山阻隔”,走出国门,和国外史学界直接切磋交流,“点对点”“面对面”“点对面”交流、讨论几成常态;一些优质学术资源(会议、讲座、数据库等)、教育资源(在线课程)引入国内,在数字技术搭建的空间内“走出去”“请进来”,“自由出进”。这种和“国际接轨”是历史学内涵和外延扩大的新内容。数字经济内涵和外延扩大是社会经济进步的表现,历史学内涵外延的扩充,表明历史学“体量”——外延扩大的同时,发展质量得到提升——内涵提升。史料的搜集与获得从一个方面可佐证上述观点。笔者曾专门撰文讨论数字技术带给历史学的重要影响之一是(从内容和范围两个方面)扩大了史料边界。首先,史料家族平添“新成员”。数字化技术带来了参与史料“书写”“制作”主体多样化,“参与”的主动性、积极性不亚于职业历史学家。史料种类多元化——“前数字化时代”未曾有的某些信息资料,今天跻身于史料行列;一些不经意之间甚至属于娱乐性的“抓拍”,乃至安置在街头巷尾的“天眼工程”等,各种对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记录,或许可成为解说某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关键资料,改写、重新书写某个历史事件不是虚夸。(包括互联网信息在内的)各种数字化作品成为史料家族的“新成员”不存在太多的争议——对社会现实的记载直观性、真实性不逊于任何形式的文字记录。鉴于数字技术发展的“进行时”,种类增多、边界扩大将是史料未来时段的必然走势。其次,数字技术增加了信息传播渠道和传播路径,由是,历史学的信息量、信息类型、容量随之增多,互联网“绝对优势”的地位将日益巩固。通过互联网、传播的历史学信息,史料仅仅是其中一部分,学术研究信息、教学活动、研究动态、(学术)会议直播或转播、各类学术成果等,均可利用微信发出、扩散,历史学信息来源增多,信息数量的绝对值大幅上涨,历史学学术资源的边界将呈现“动态”扩大的趋势,历史学“总容量”必然随之持续增长。最后,史料边界扩大、历史学相关信息量增加,历史学工作者获得了研判历史多层面的依据,获得了多于此前的发言权,产生新的思想认识,订正原有的结论,推进历史学研究的进步能够预期。此外,史料逐步丰富,研究领域拓宽,传统领域研究走向深入,某些问题的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等等,都属于历史学内涵的充实。例如,传记作家、谱牒学家可以利用关键词,在数据库中得到多于从前的资料,传记书写更趋完善。一系列专题的数据库陆续建立,前所未有地整合、集中了史料,数字技术推动着历史学专题、专项研究迈上新台阶。
与新型、新兴的史料种类增多,以及传统史料日益增多的数字化、电子化相伴随的是新的研究方法、书写模式的问世,数字化书写无疑是历史学应当考虑的书写模式。配合数字经济时代的历史书写,对大数据的作用给予较多关注是必要的。如今,大数据在政府部门决策、“抗击疫情”,以及交通运输、金融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效果甚佳。大数据本身即包括数据的历史积累,“大数据也有自己的历史”。大数据是一种借助数字技术的全新方法——必须经过电子计算机处理的数据才可称得上大数据,适应了数字经济视域内历史学所面临的“信息爆炸”时代的信息数据。总之,与“文献爆炸”相伴随的是信息量猛增,历史学内涵有了更多的积累,甚至是前所未有的积累。实践已经证明,“使用数字资源和数字方法传递新的信息,能够增进对过去的学术研究的理解”,进而产生新的思想观念。
互联网、(智能手机)微信对扩充历史学内涵与外延的作用各有不同,但共性特征是普及程度高,传播效率高、规模大。据2018年的统计数据,全世界95%的人口使用手机,84%的人口使用宽带互联网。今天的统计数字一定会高于2018年的数值。互联网和手机迅速普及,几乎“无网不达”“无微不至”。与数字经济时代的关键词——“数据”关联最为密切的则是互联网和各种媒体社交平台,尤其和历史学密切相关的微信社交平台。历史学各种社交平台、社交账户等不可和数字经济的社交平台混为一谈,但二者之间的共通之处却是鲜明的——公共性和开放性。数字经济,抑或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历史学内涵外延扩大,各种平台特别是微信平台的贡献可谓卓著。
人们从多角度、多侧面议论互联网对人类社会的巨大改变。互联网时代,各种(数字化了的)文本、信息通过互联网阅读交流,引发人们对认识传统历史学“数字化升级”的思考。这种“升级”首先是数字技术的拉动或推动,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历史学“数字升级版”是“被升级版”。其次,对于历史学而言,各种技术不断升级,直接结果是历史学的内涵和外延不断呈现“升级版”的扩大,“扩容”是可以预知的显性后果。至于数字经济时代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大放异彩的数字技术,不仅推动着数字经济的发展进步,自然也会推动历史学进入新阶段。
结语
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一种全新的社会经济形态。和前两种经济形态略有不同的是,数据是一切数字经济活动的动力源泉,重要性堪比石油、钢铁、粮食,远远超出了一般自然资源的价值意义。对数据的认知、把握、使用决定了数字经济的存在和走向。同理,数字时代的历史学,数据、信息等既是重要的资源,也是历史学存在发展的动力。略有不同的是,历史学某些特殊或特定的信息载体时下还没有完成数字化,或者要求历史学所有的信息百分之百数字化,如一些属于孤本、善本的历史资料,一些私人手中珍藏的书画等,几乎不可能。但依据现有的数据资源,数据不仅为数字经济视域内的历史学研究提供强有力的信息支持,而且发挥更大的作用亦值得预期。如世界史学科的各个专业方向,对一些史料性质的域外数据库的依赖,是长期的持续性的。所以,和数字经济相比,数字经济时代的历史学还有面临“非数字化”相关问题,面临数据和“非数据”信息的选择与甄别。
数字经济是历史学进步的“福音”。数字经济及其相关技术为历史学提供诸多技术和智力支持,注入比从前更多的活力。数字化文本及其种类将继续增多、各种传播技术手段升级换代,尤其是大数据、人工智能的长足进步,会给历史学创造新的机遇,乃至产生新的认知。学术界早已有人论证,信息技术、数字化技术给历史学带来了“检索革命”,检索之精准、快捷前所未有。可以预知,人工智能应用于文献检索之后,各种数字化文献“呼之即来”,不再是神话或虚构。历史学对大数据的开发运用,会根据各种数据的整合,对已有或未知的认识检验校正,获得新的观点思想,开辟新的学术领域或将可能。面对数字经济,历史学最主要的任务是适应数字经济,强化自身数字建设。有学者宣称“数字化改变了所有历史学家的工作”。“所有历史学家”言过其实,但“(数字革命)持续不断地改变着历史学家的工作方式”一定是“进行时态”。令人欣慰的是,这种“改变”带给历史学的效应是积极的,促进了历史学发展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