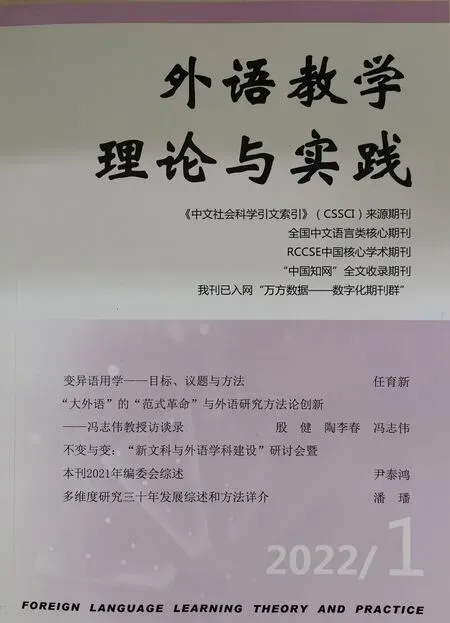“大外语”的“范式革命”与语研究方法论创新*
——冯志伟教授访谈录
2022-11-07南京邮电大学外国语学院陶李春
南京邮电大学外国语学院 殷 健 陶李春
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冯志伟
提 要: “新文科”及“大外语”的理念正逐渐深入人心。现有的相关论述大多来自人文社科领域的学者,而从学科交叉、文理融合的视角展开思考可以增加该领域知识生产的广度与深度。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有幸采访了冯志伟教授,请他就“新文科”及“大外语”发表意见。冯教授是文理兼通的知名学者,他认为“大外语”理念所倡导的是一场“范式革命”。在这一背景下,外语研究需要创新,尤其是方法论创新。广大外语人要直面挑战,更新知识,突出特色,展开文理融合的跨学科研究。
1. 引言
自2019年4月“新文科”建设工程启动以来,广大教育科研工作者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对“新文科”理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也达成了若干基本共识(吴岩,2019;樊丽明,2019;王铭玉,2020;张欣,2020;刘宏,2021)。“大外语”是“新文科”思想落实到外语学科的实践导向。如何深入理解“大外语”的内涵并在教学科研中践行这一理念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到目前为止,对于“新文科”及“大外语”理念,讨论者还是以人文社科领域的学者为主,具有跨学科背景的学者所论尚不多见。学术研究的推进以及教育教学实践的发展需要我们进行多元视角的思考。为此,我们最近对冯志伟教授进行了访谈。
冯志伟教授是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学术委员会委员。作为中国当代跨学科研究的领军学者,冯志伟教授不仅在人文社科领域成果丰厚,也深谙自然科学知识。他“既懂得理科中的数学、物理、化学和计算机科学,又懂得语言学中的古代汉语、现代汉语、文字学、音韵学和普通语言学,深研过汉、英、法、德、俄、日等语言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的自动处理,并把各方面的知识紧密地结合”(赵晶,2010)。冯教授指出,“大外语”理念所倡导的是一场“范式革命”。在这一背景下,外语研究需要创新,尤其是方法论创新。现将冯教授的访谈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2. “大外语”的“范式革命”意义
(下文简称“殷、陶”): 冯先生,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谈。当下,“大外语”是教育主管部门及广大外语学者热议的话题。您具有文理兼通的学术背景,相信您对该话题一定有着独到的见解。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 由于国际国内社会形势的变化,再加上人工智能、自然语言处理、机器翻译等现代技术的快速发展,有学者指出外语学科及专业正面临着巨大挑战甚至危机,您是否赞同这种看法?
(下文简称“冯”): 从学科发展的角度讲,“大外语”理念是中国外语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当下的外语学科正在经历一场“范式革命”,由此带来了外语研究问题域转型与重构的现实需要,相应的研究方法也亟待革新。“大外语”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外语(包括外国语言文学和外语教育)无疑要在新时代文科创新发展中担当大任(刘宏,2021)。一直以来,研究外语的结构和功能是这门人文学科的主要内容。而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技术要素出现在外语学科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之中,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与辩证的思考。例如,现在的机器翻译技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辅助人们从事翻译工作,但我认为机器翻译等语言技术并不能够代替人本身的工作,而主要是为了帮助人类更好地进行语言交流。我早年之所以从事计算语言学研究,就是想借助机器来改进语言研究,促进人与人之间的语言交流。众所周知,语言运用,包括翻译,是非常复杂的智能活动,在这一过程中借助机器能够解决部分问题,比如提高翻译的速度,或者较好地处理某些重复性或纯技术性文本。随着神经网络机器翻译技术的发展,机器翻译的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但也主要以处理一般性的技术类、信息类文本为主,而且其正确率也不能完全满足译文使用的要求,常常需要进行译后编辑。对于语言中普遍存在的修辞、情感、审美等问题,机器翻译就爱莫能助了。人工智能目前还处于初期阶段,比如人脸识别、指纹识别等技术,主要还是处于感知处理的层面,而一旦涉及到认知领域的概念、判断和推理等,就无能为力了。所以语言技术并不能代替人的作用,现在如此,未来也是这样,我在很多场合都表达过这样的观点。
外语专业确实面临着一定的挑战,但不是面临危机。江泽民总书记经常强调各行各业都要“与时俱进”,我想这同样也适用于外语学科。概言之,在新时代,广大外语人要学习使用新技术,要从只会进行主体思辨的传统文人变成用新技术武装起来的新文人。在新技术革命背景下,在人工智能、自然语言处理以及机器翻译技术飞速发展的情况下,外语人要赶上时代的步伐,更新知识,迎接挑战,这倒是一个真问题,也就是我所说的“大外语”的“范式革命”和研究方法论创新。
3. 外语研究问题域的当代转型
确实,外语学科正在面临一场“范式革命”。而面对外语学科所遭遇的挑战,教育主管部门及有关专家提出了建设“新文科”及“大外语”的观点。结合您自身文理兼通的学科背景,您是如何解读“新文科”及“大外语”的? 此外,您作为一个积极主张建立各学科“中国学派”的学者,可否也谈一下“大外语”建设的中国特色问题?
“新文科”之“新”在于学科交叉。造成文理分科的原因之一是教育事业的发展,而从科学本身的角度来讲,文科与理科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古代的很多学者如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苏格拉底等都是文理兼通的。文理分科是随着西方的文艺复兴而逐渐形成的。而随着时间的发展,文理分科似乎愈演愈烈。此外,文理分科也受到了教育政策的影响。比如在我国,从1957年开始,出于更好地培养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发展所急需的各类人才的目的,从中学开始出现文科与理科分开的做法,后来索性就直接分为文科班和理科班,进而规定不同的高考科目,分科录取。这种做法持续至今,自然有它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但也产生了诸多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文理分科环境下培养出来的学生知识面比较狭窄,比如有些理科生的人文素养较差,而文科生则相对缺少自然科学知识与技术。
总体而言,文理分科对于科学的发展是不利的。所以现在教育主管部门提出了“新文科”理念,其中的“新”在我看来就是要用新的方法研究文科,而关键就在于学科交叉。对此,有学者提出外语语言文学各学科内部交叉、外语学科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交叉以及文理交叉这三种不同的学科交叉路径(刘宏,2021),我完全赞同。比如,学外语的人可以学习一点法律,或者文科学习可以与自然科学技术学习结合起来,进行所谓的“跨界”学习。文科和理科在古代是不分的,后来由于科技的发展以及教育的现实需要而分开了,现在我们又重新主张融合发展,貌似回到了原点,其实是否定之否定,是在认识到了错误之后形成的新认识。
“大外语”之“大”在于外语人除了会讲外语之外,还应该具备一些专业知识与技术,比如语料库技术、统计方法、编程技术等。许国璋(1989)教授就曾经批判过在外语教育中单纯进行语言训练的观点及做法,他指出“试想英语好就是学问,那么英国美国街上都是学问家了?”1992年,他又一次深刻质疑“外语界人才,只要求你会外语,此外别无所求”的培养目标(许国璋,1992)。“大外语”之“大”是将一些相关相近的学科及研究方法按照特定的设计及需要进行合理整合、交叉、跨越(王铭玉,2020)。我很高兴地看到,现在已经有了很多这方面的教材,如各类语料库教材、Python教材等,而且部分教材是专门针对文科背景的研究者与学习者的,这些都是新时代外语人更新知识、迎接挑战的宝贵资料。所以“大外语”这个提法很好,它启示我们要借助科学技术进行自我赋能,不要被人工智能、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发展吓倒并将自己与新技术隔离开来,而是要直面挑战与机遇。既要讲好外语,又能掌握技术,从而实现学科交叉与融合,对于外语人而言,也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他们提出的具体要求。
至于“新文科”及“大外语”的中国特色,这是一个国际化和民族化的问题。一方面我们要关注国际学术动态,不要忽视国际学术成就。中国的语言学必须走国际化的道路,闭目塞听不可能做出国际水平的研究成果。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是开放的,是具有国际性的。相同的对象,各国都可以展开研究。对于中国学者而言,我们绝不能忽视国外学术研究成果。有人批评我,说我作为一个研究中文的学者,却整天关注外国学者的研究。这种批评是不成立的。28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中国计算语言学研究的世界化刍议”(冯志伟,1994),其中就提出了“语言研究世界化”这个概念。所以中国的文科人、外语人要有开放的学术视野,做到心怀世界。
另一方面,在关注国际学术的前提下,我们也不能忘记“新文科”、“大外语”的中国特色。作为中国的研究者,面对着中国的语言文字及社会文化,自然需要结合国情展开研究,需要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加快构建具有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特点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樊丽明,2019),语言研究也是如此。早年我在云南昆明五中担任物理教员的时候,就试图通过阅读外文书刊来了解计算机科学的发展情况,并试图将过去学到的语言学知识与计算机技术结合起来。1974年,我通过计算得出了汉字的信息熵是9.65 比特。相比而言,国际上也有学者计算了英语的信息熵为4.03比特。外国学者对中国语言文字了解不深,此类研究只能由中国学者来进行。上个世纪我在从事术语研究的时候,发现术语系统中大多数条目都是词组型术语,单词型术语相对较少,由此我提出了术语系统形成的经济律(冯志伟,2011: 366),此外还有潜在歧义论(冯志伟,2011: 384),也都是基于对汉语的观察而得出的研究结论。再加上从古代一直延绵到现当代的范围广大、特色明显的术语应用实践,我提出了构建术语学研究“中国学派”的主张(殷健等,2018;冯志伟,2019)。当然,科学研究的中国特色并不是要求我们刻意地去盲目追求国别特征,而是要在认真解决所遇到的具体问题过程中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成果。
同理,中国的“新文科”及“大外语”建设也不应该失去中国特色。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日益推进,中国所呈现出的特色会越来越明显,中国与西方之所异将远胜于所同。所以“新文科”建设需要围绕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认识来展开(陈凡、何俊,2020),语言研究也不能脱离这个方向。比如,外语教学中,汉语背景的中国英语学习者在外语习得方面具有什么特点,汉语特殊的分词问题等,都需要依靠中国学者去研究。诚然,科学研究是不分东西方的,但科学家是有国籍和家国情怀的。只要中国学者从自身的时代背景与基本国情出发,我们的“新文科”及“大外语”必然是会具有中国气派与中国风格的。
总之,在建设“新文科”及“大外语”的背景下,我们的外语研究问题域正在发生转型。外语研究既要有世界眼光,致力于解决人类共有的语言问题,也要有本土意识,结合汉语以及中国社会文化的特殊性展开思考。与此同时,语言研究的焦点也正在发生变化,如研究对象从个体语言转向群体语言,研究现象从静态文本转向动态的网络语言,研究内容从侧重语言规范转为强调语言功能等。而借助现代技术开展外语研究便是问题域转型所催生的研究方法论创新。
4. 外语专业师生的技术能力培养
刚才您谈到了外语研究的方法论创新,其中自然涉及到外语专业师生技术能力的培养问题。作为数理语言学、自然语言处理等语言学科与自然科学学科交叉融合的先行者与权威专家,可否请您谈一下外语人才技术能力(尤其是信息技术能力)培养的问题。具体而言,对于国内广大外语教师与外语专业学生而言,他们应该掌握的技术能力有哪些,如何有效培养?
外语人首先要学会新的获取知识的方式,尤其要学会从语料库和大数据中获取更加客观和全面的知识。文科人传统获取知识的方式是用自己头脑中的已有知识来描述对于外部世界与自身的认知,然后形成文字,著书立说。采用这种方法获取的知识叫做“第一人称知识”,基本上采用的是内省方法,其缺陷是主观性太强,往往缺乏客观与实证的依据。另一种获取知识的方式是调查研究。比如查字典,或者进行汉语方言调查,前者是查阅辞书,后者主要是采用诱导的方式进行,比如根据一个方言调查字表让讲该方言的人读某些汉字,然后分析这个方言的语音系统,而研究者或许并不懂这个语言。这种方法同样也有缺陷,比如被调查者的回答可能有误,但却被当成了客观事实,错误的结论便在所难免。
那么,真正可靠的语言知识在哪里呢?在语料库里。语料库有两个特点,一是规模大,少则几十万词,多则上亿词。另一个特点是语料的真实性。从具备上述特点的语料中我们可以获取更全面可靠的语言知识与素材。在积极建设“新文科”与“大外语”的当下,外语人应该学会从语料库和大数据中获取知识。在这过程中,我们需要学会一些语料分析的数学方法,还要学会Python等计算机编程技术。很多人抱怨说Python对文科人难度太大,我看未必。Python的表达方式和英语是很接近的,只要你会说英语,同时具备类似于高中水平的数学知识,再加上努力钻研,掌握基本的技能并不困难。而有了这种编程技能之后,你的语言研究将会如虎添翼,可以根据具体的研究需要改进软件、编写程序等,从而大大提高工作效率。
在技术能力培养方面,我尤其建议文科人要多看一点计算机方面的书籍,不要有畏难情绪。一旦你慢慢进入了语言技术的殿堂,你的语言研究将会取得无以伦比的“加速度”。此外,文科人、外语人要经常关注国内外研究,尤其是语言技术研究的进展,各类学术刊物就是最好的渠道。除了我们经常关注的《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外语电化教学》等刊物之外,特别要多关注文理结合的语言研究刊物,如《中文信息学报》、、等。借助阅读不断更新知识,才能成为一个文理兼通的新文科人和新外语人。当然,新文科不是对传统文科的否定与彻底颠覆,而是在传统文科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拓展和深化。据此,传统的获取知识的方法还是需要的,这是文科人安身立命的基本功。总之,对于“新文科”及“大外语”的建设,其重中之重就是要用新兴的信息技术来武装传统文科,以适应信息时代对于文科的新要求。
5. 外语研究方法论创新的文理结合路径
关于外语研究方法论创新的文理结合路径,有专家指出我们应该坚持“守正创新”与“攻守并举”的原则。那么,在外语学科向自然科学展开“进攻”(即文理结合,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外语研究如何坚守人文学科的“初心”和“阵地”,可否请您谈一下?此外,对于像南京邮电大学这样以信息通信技术为特色的理工科院校而言,其外语学科如何寻找“新文科”及“大外语”与本校特色的共振契合点,可否请您提提宝贵建议?
这个问题的本质涉及到对语言现象的看法。语言既是社会现象,具有社会性与人文性,也是自然现象,具有自然性。在研究方法上,一方面我们不能抛弃传统方法,例如文本细读、内省与思辨等。不管“新文科”发展到什么程度,这些始终是文科的主要研究方法。与此同时,语言也成为了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研究对象,如语音分析、符号分析等,可以用数学的方法来研究。对于语言的自然性,如符号性、离散性、递归性等,传统的文科学人不太了解,所以常常否认其自然性,排斥采用自然科学方法展开研究,这显然是不明智的。使用交叉学科方法来研究语言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我们现在所倡导的“新文科”及“大外语”应该将语言研究的人文视角与自然视角有机结合起来。所以有关学者提出的“守正创新”、“攻守并举”的主张是极富前瞻性的。当然,“创新”的前提是“守正”,我们在采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语言的同时,不能忘记传统的语言研究成果与方法,要守住人文科学的阵地。“新文科”建设并不是要搞一场“颠覆性”的革命,不是要否定传统文科,而是要在“守正创新”的原则指导下持续地促进文科的发展(王铭玉,2020)。
在技术革新突飞猛进的当下,对于人文学者而言,用人文的视角和知识去检验与审视通过自然科学方法得出的结论更是他们义不容辞的时代使命。前年我在《外语电化教学》上发表过“词向量及其在自然语言处理中的应用”(冯志伟,2020)一文,就是想从具有人文传统的语言学角度出发去检验一下词向量这个热点概念,以现在的一些时兴观点与方法来呈现我们传统的语言学思想,让现代技术具有可解释性,我想这就是我在语言学领域所做的“守正”努力。当然,我们也应该坚守文科发展和文科教育对于培养专业人才的重要作用。毕竟,文科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以文化人,对学生进行人文教育以及面向社会、面向全体公民进行基础教育(樊丽明,2019),这是从文科本身的存在意义及功能上讲的“守正”。
从研究方法的角度而言,我们需要妥善处理好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二者的关系。传统的语言学研究主要采用基于规则的理性主义方法。而在当下,基于统计和大数据展开研究的经验主义方法似乎占了上风,理性主义方法被相对忽视,我认为这是不正常的,因为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要洞察事物的本质以及解释事物的原因。如果这种努力被忽视了,只剩下对各种表象的呈现而忽视了对其内在原因的解释与阐发,这是不符合科学的最终目的的。在语言研究中,我们要把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结合起来,而要实现这一目标,人文科学的背景是不可少的。人文学者既要掌握技术,懂一点数学与计算机,更要坚持人文主义的立场,不能让语言研究脱离人文主义的基本特征。也就是说,要学会把经验主义方法与人文方法结合起来,推动学科的发展。虽然当下经验主义占了上风,但我认为未来的语言研究还是会向理性主义回归的,两者紧密结合,共同探索人类语言的奥秘。
自然语言处理等语言技术就像一棵枝叶茂密的果树,果树上挂满了累累的果实,现在有些急功近利的人出于实用的需求,都在争相摘取那些低枝头的果实,那么,如果低枝头的果实都被摘完之后,谁去摘取那些高枝头上的果实呢?究竟怎样去摘取呢?由于自然语言处理的研究对象是语言,当然应当有形式化的语言学知识的支持,因此要想摘取高枝头上的果实,除了依靠计算机技术之外,我们还需要依靠形式化的语言学知识去摘取。语言学家在自然语言处理中是大有可为的。我们要认真地学习语言学的知识,深入研究语言学中的各种规律和规则,同时还要与时俱进,进行更新知识的再学习,学习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学习现代数学知识,学习计算机编程技术,成为文理兼通的新一代语言学家,才有可能摘取高枝头上的果实(冯志伟,2018)。
突出“大外语”特色的另外一个方面是指外语学科要和各个高校的优势学科紧密结合起来,扭转外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千校一面”的不利状态(张欣, 2020)。邮电类高校,比如南京邮电大学的特色与优势显然是信息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而通信就是“communications”,是借助通信技术实现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其中也包括通过语言符号的传递来实现交流。所以信息通信技术研究者与语言文字工作者,包括外语工作者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美国数学家、信息论的奠基者香农曾写过一篇奠基性的论文,叫“通信的数学理论”(A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认为通信工作的任务之一是研究字符串之间的关系,这和对语言符号的研究是密切相关的。理工科高校都有各自的优势,你们南京邮电大学外国语学院也同样如此,应该将外语学科与信息通信科学紧密结合起来。比如,外国语学院可以在学校的统筹安排下与相关院系展开跨学科合作研究,围绕信息通信领域的语料库及术语库建设、专业外语教材开发、垂直领域翻译、国际学术交流、国际产业贸易等做一些具体的工作,形成具有南京邮电大学特色的信息通信外语学科。其他的理工科高校都可以采用这种跨学科合作的模式。这不仅是外语学者的使命,也是自然科学学者的使命。这个使命光荣而伟大,外语学者和自然科学学者都需要为此付出长期而巨大的努力。
6. 结语
新时代的“新文科”及“大外语”建设是一场具有深远意义的“范式革命”。它将带来外语学科问题域的转换以及方法论的革新。面对这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广大外语人如何跟上时代的步伐,看清形势,更新知识,突出特色,展开文理融合的跨学科外语研究,可以从冯志伟教授的上述访谈中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