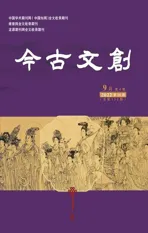“审美化真实” 视野下试析文学价值中美与真的关系
2022-11-01李苏宁
◎李苏宁 武 岳
(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 江苏 徐州 221100)
文学作为认识活动,其本质在于对生活真实的艺术反映。同时作为审美活动,为读者提供审美体验又是文学之为文学的内在根据。真与美构成了文学创作的价值追求,也在碰撞、融合的过程中激发出交相辉映的独特艺术效果。那么,人们应当如何理解文学价值的真与美?二者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本文将主要围绕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展开讨论。
一、文学价值中真、美的内涵分析
(一)“合理”与“合情”
文学价值中的“真”为艺术真实,是创作者主观想法与客观生活真实的辩证统一成果。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较为不同的是,前者主要将实际生活中客观存在的人与事作为直接参照,而后者产生于内蕴自我人格与情感评价的客观对象,是创作者对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进行真实面貌的“诗意揭示”。概括而言,文学价值的“真”蕴含着“合情”与“合理”两个方面。
“合情”意味着文学作品必须反映人们真实、诚挚的感情及意向。如李白所作的“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此句以极其夸张的手法,化沉重的忧愁为三千丈的白发,将其壮志难酬的暮年之悲抒发得淋漓尽致。“合情”的虚构以真实情感将读者带入与现实相离相存的艺术境界,在阅读的思考与回味中达成情、理相融的统一,从而体现了这一虚构的合理性。
“合理”一是指文学作品要符合现实世界的本质性和规定性东西,或是恩格斯所言的人类社会真实的“现实关系”。例如小说《机器岛》,凡尔纳设想了一个名为“标准岛”的人工世界,但在这虚构的岛屿中却蕴含着“合理”的现实性因素:工业发展所带来的社会纠纷、人类面对利益时的信仰沉沦、资本家内部不断尖锐化的矛盾斗争……作品中诸如此类的“诗意揭示”与客观存在的“现实关系”紧密相连,凝结了创作者对工业社会的批判与反思。除此之外,“合理”还意味着与人类积极健康的理想相符合,通过虚构的方式可以表达人在社会规律下的美好心愿。《格列夫游记》通过虚构的幻想展开荒诞离奇的情节叙述,真实地表达了殖民地人民反抗统治者的迫切愿望,以及对无意义的党派斗争等现实世界问题的否定性评价。将“合理”的内容掺入虚构的想象之中,赋予了真实以艺术的表现力。
值得强调的是,这里的“理”不一定达到与现实社会的本质或物理规律完全相合的要求,更多合乎的是人们共通的逻辑与理性能力。换而言之,不是合乎一种既存的事实之理,而是合乎一种人们将如何存在于世的“未来之维”。如米兰·昆德拉的作品,集中探求“人之存在”的问题,蕴涵着人文主义关怀以及对生命存在本质的索解。他运用更加真实并且贴合生活的视角,看待人的精神及行为的存在方式,将存在的真实指向“未来的真实”,而这指向未来的维度即是“理”的所在。
(二)语言的图画美与技巧的创造美
在文学活动中,“美”位于价值功能的核心地位。具体是指文学在真与善统一的基础上,满足人们对美的需求,给予人以精神上的愉悦。从审美角度而言,以语言美、形式美等表现方式具体呈现,通过语言塑造艺术形象并与情感相融,赋予读者美感与理解力。这里本文将针对其中的两个特质进行阐述。
第一,语言的图画美。即为读者提供意趣无穷而又真切如画的生活画面。使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如触其物,如临其境。如《山居秋暝》,王维以朴素平直的笔尖勾勒诗意,通过捕捉事物的光、影、声、色,使其充分自然地表现于诗作中。袁行霈曾这样评析:“自然的美与心境的美完全融合为一体, 创造出如水月镜花般不可凑泊的纯美诗境。”诗句中“空山”“新雨”“明月”等意象的运用,使雨后山间的清新景象跃然纸上。婀娜的荷叶一片片被划到两侧,无数珍珠般晶莹的水珠翻滚着、欢笑着,正如苏轼所称道的“诗中有画”。而这种语言的图画美引人遐想,营造身入其境之感,是艺术美的重要构成因素。
第二,技巧的创造美。宗白华曾言:“艺术家往往倾向以形式为艺术的基本,因为他们的使命是将生命表现于形式之中。”由此可见,形式创造对文学审美价值的实现具有关键意义。而艺术技巧是形式创造的重要表现方式,创作者以翻新出奇的精神与精炼巧妙的艺术技巧进行文学创作,可生成更深厚的审美体验。试看苏轼的这句诗:“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其中跳、乱二字,以珠拟雨,灵动而传神地将骤雨的杂乱无序描绘出来,不得不叹服其技巧之精妙。同时,此诗也可以令人联想起杜甫的“俄顷风定云墨色”以及白居易《悟真寺》中“赤日间白雨”等诗句。苏轼将化用的艺术手法运用得稳妥精当、浑然天成,赋予了作品新的内涵与审美价值,体现了意蕴新生的美学特征。
但技巧亦是需要把握尺度,力撰硬语易露出斧凿之痕而失天籁之自然。正如王国维先生所提出的“隔”与“不隔”之论,形象得不清晰以及技巧的过于强调如“雾里看花”,会增加读者理解时的隔阂,易造成意蕴的流失。但此处的“隔”需要结合话语的蕴藉属性来辩证看待。将技巧与文本的意蕴相结合,纵意所如,不落俗套,可以达到水中着盐的妙境。这种看似“隔”实为“不隔”的高超技巧,使得作品的韵味渐显,以恬然回甘,予以读者更自然的审美感受以及回味的空间。又如修辞、炼字等手法的使用亦使语言表达更为适切,读者于反复的字句推敲中可以感受到意蕴的变化,文学奇巧尖新的魅力也由此体现。
二、关于真、美关系的倾向性观点及其局限
真、善、美作为精神价值的三大基本形式共同构成了相互联系、渗透的价值体系。但在文学史上,因真与美各自价值取向及功用的独立性,关于二者的关系问题产生过不同的倾向性观点。
一是提倡“美胜于真”,将形式、语言等方面的美视作文学价值的重心。例如,罗兰巴特在强调作品的结构之美时曾言:“作品之所以是文学应当体现在其纯粹是结构形式,其核心是‘文学性’。”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森进一步发展了“文学性”观点,将结构主义语言学与诗歌批评相连接,提出“诗歌是自在的词”等结构主义语言诗学理论。罗曼·雅各布森追求将形式之美外化为文本之美,并围绕“以文本为中心”这一重点进行探索。
但另一方面而言,“美胜于真”观点所存在的局限性亦是不可忽视的。雅各布森将文学的语言系统视为较为封闭的符号结构,过于强调形式的规范化和约束力作用。有研究专家对此曾言,雅各布森从不允许他对语言、其他符号系统及其运作的研究涉及社会、文化、意识形态或诗歌效果等。不可忽视的是,文学价值的生成包含两个关键环节,即作家的创作和读者的阅读接受。“美胜于真”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读者“再创造”的文学意义,并使作家失去了相对自由的创作与想象的空间。形式与结构的臻于完美无法替代其内涵的蕴藉性,一味追求艺术美感而脱离真实促使了其内在情、理的流失,难以将真、善、美统一的文学现象诠释完整。因此,“美胜于真”片面强调了语言、形式等方面的审美特质,忽视了知识价值的重要性,具有一定的局限。
与“美胜于真”观点相反的是尊崇“真胜于美”,侧重于文学作品中内容的真实性呈现。老子在《道德经》中论及语言时再三突出“信”的重要意义,如“信不足焉,有不信焉。”并强调语言文辞必须符合自然规律,“希言自然。故飘风不终朝 ,骤雨不终日。”他反对“多言”的观点内蕴着珍重语言,遵从并保持其真实性的思想内涵。在内在逻辑上与其“美言不信”的观点是相一致的,体现了老子对于语言文辞真实性的较高要求。理学家李贽的“童心说”与这种“求真”的思想也较为接近。他将“真”置于理论的核心位置,认为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都只存在于“真心”,自然界是“我妙明真心的一点物相”。
除了宗教学说对“真胜于美”的认可外,中国古典小说也受其影响较深。小说在唐朝之前以“尚实”为主要特征,而在发展后期出现了虚构性的意识并加以自觉提倡的文学现象。例如,叶昼提出“劈空内造”,将虚构与想象视为小说精彩有趣的重要创作因素。金圣叹提出 “以文生事”,强调如果过分拘泥于历史,作者则变成了“官府传话奴才”等,这些观点充分表达了对小说的虚构性所持的肯定态度。
伴随创作的繁荣,明清小说的理论研究也日臻成熟与完善。理论家在营建虚构理论的同时更重视小说的真实性,普遍认为传奇性需要寓居于真实之中。例如理论家毛宗岗所持的“文学匠心为历史还原”的观点,认为历史小说不同于历史著作:历史小说“纪人事”,是“叙一定之事”;创作应以“天然妙事,凑成天然妙文”等,作者要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前提下进行创作,以史实为依据。但不可否认的是“真胜于美”这一观点排斥虚构和想象,机械僵滞地求真,削弱了创作者写作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文学所特有的神秘色彩与艺术魅力的褪色,易使未经艺术处理创造的作品缺少鲜活灵动之美,以至于多样化、丰富化艺术特色的流失。
三、“审美化真实”的概念析解及其具体呈现
真善美虽各自代表了不同的价值取向,引领了不同的文学创作与批评倾向,但人们在具体文学作品中却总是以三者融合的形态去感知它们。尽管在微观的文学创作中各有所侧重,但文学活动作为一种历史性活动,其追求必然体现了三者的内在一致性,形成整体性的价值体系。结合上文所阐述的古今中外的文学事实可得,真、美之间具有不可割裂的统一性,无法相互脱离而独立。将二者文学价值进行分立的文学创作,消减了整体的审美价值。因此,真与美应在整体的价值系统中高度统一,进而达成以真求美、以美启真的审美效果。试举苏轼的此句诗歌为以明之,“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诗人将强烈而自由的感情融入这变化的自然万物,并与含蓄的政治意蕴与人生哲学相结合。这种情理交融的境界正如钱钟书在《谈艺录》中所言:“不泛说理,而状物态以明理。”此诗独特的艺术价值就在于体现了实际生活现象之真、富有哲思启示之善,以及艺术美的气骨与韵味。使读者在真、善、美的浑然一体中,感受到别有理趣的文学境界。
另一角度而言,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审美活动,更多的是要求作品具有审美感受,为读者提供审美体验是其发生的根本。因此,审美无疑是文学实现各种价值功能所围绕的核心。其地位也影响了知识价值,使之成为审美之真,“审美化真实”的文学现象依此产生。具体是指在文学价值系统中,美将真赋予艺术审美化的表现形式,进而构成真美合一的文学价值取向。
文学作品的具体内容往往蕴含了某种对现实之真的价值追求,但这种追求较为内蕴、抽象和主观,需要借助文学的特殊审美形式才能生动、完整、感性地外化出来,即诗意化的语言与形象系统。“审美化真实”作为情、理内容的艺术组织手法,充分发挥了这一诗意化的形式创造作用,具体可划分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指向现实的真实性赋予文学作品鲜活、真切的历史、社会经验基础,使其更具时代与生活之厚重感。以老舍的作品《茶馆》举例,作者选取了裕泰茶馆这个象征着内忧外患的旧中国为观察窗口,通过人物生活的变迁反映整个时代的变迁。该话剧取材于社会生活,浓郁的京文化特色铸就了历史的复现,茶馆里的陈设昭示了在各个特定历史时期中的时代和文化特征。真为美提供了内容的基础,奠定了丰富蕴藉的内涵意义,二者相得益彰,使得《茶馆》在真实地呈现中又不失地域文化的温度。
另一方面,审美形式赋予文学作品更具诗意的形象系统,令作品中的真实超越时空限制,使其富有象征、典型和蕴藉性。创作者透过生活真实的表层,运用主观感知与再创造作出艺术的揭示与表现,突出表现其遵循的审美价值追求。以魔幻现实主义为例,虽然以现实真实为基础,但作者通过极端的夸张手法催生出强烈的艺术效果,将生活真实经由艺术创造转化为亦真亦幻的艺术真实。而这种转化后的“诗意真实”也是文学之真的存在方式之一。例如在《百年孤独》一书中,作者通过巧妙的构思和想象,形成了现实与幻想相结合的独特画面。在虚实交错中,激起读者对创作真实本质的追求欲望,这种对真实的心灵化即为“审美化真实”的运用。
综上所述,文学价值结构的理想宏观形态始终是真善美相统一的,真与美的关系在该系统中表现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方面,指向现实的真实性赋予文学作品鲜活、真切的历史、社会经验基础,使其更具时代与生活之厚重感;另一方面,审美形式赋予文学作品更具诗意的形象系统,令作品中的真实超越时空限制,使其富有象征、典型和蕴藉性。最后,“审美化真实”是真、美关系整体、集中的体现,在追求更高层次的审美感受时,充分理解这一文学现象或许能为人们提供新的启示。
注释:
①(德)恩格斯: 《致明娜·考茨基(1885年11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5页。
②袁行霈:《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37页。
③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5页。
④近代王国维用语。他在《人间词话》中提出:“隔”如“雾里看花”;“不隔”如“豁入耳目”。
⑤Richard Bradford,Roman Jakobson:Life,Literatu re,Art,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4,p.11。
⑥引自《道德经》第23章:希言自然。故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
⑦郝威:《浅析毛宗岗点评〈三国演义〉中叙事意识的自觉与成熟》,《电影评介》2009年第7期,第102页。
⑧黄之栋:《性理风骚一例收——论理学对吕本中及其诗歌的影响》,《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1期,第87-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