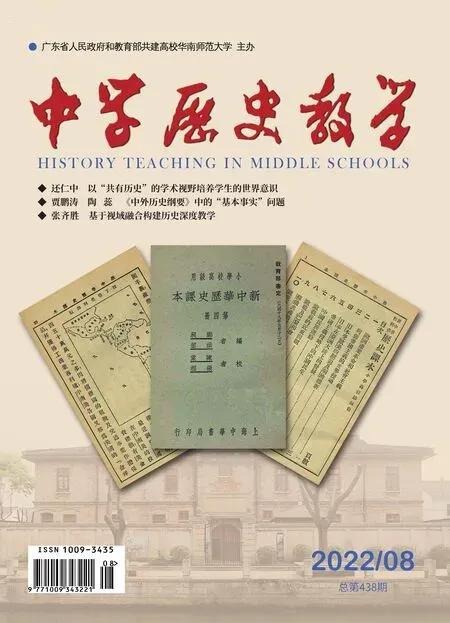《中外历史纲要》中的“基本事实”问题*
2022-11-01贾鹏涛延安大学历史学院
◎ 贾鹏涛 陶 蕊 延安大学历史学院
英国著名史学家E.H.卡尔在《历史是什么?》中将历史事实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一些基本事实,这些事实对于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是相同的,比如黑斯廷斯战役发生在1066年而不是1065年或1067年,发生在黑斯廷斯而不是发生在伊斯特本或布赖顿,历史学家千万不能把这些事情弄错。就像豪斯曼所言“精确是职责,不是美德”。赞扬历史学家在这个层面上事实的精确,就像赞扬建筑师在建筑中适当使用了干燥的木材,合理地运用了混凝土一样。因为,这种事实是历史学家进行工作的必要条件。第二种是史学家在第一种事实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选择和排列,由哪些事实说话、按照什么秩序说话或者在什么背景下说话,这都是由历史学家决定的。在卡尔看来,史学研究有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搞清楚基本事实,这个层面的事实不容有错。第二个步骤是建立在基本事实基础上的选择和排列。显然,如果基本事实都搞错了,那么史学家所建立在基本事实基础上的整个历史事件犹如空中楼阁。由此可见,基本事实在整个史学研究的重要性和基础性。《中外历史纲要》是基于历史学科核心素养和学业质量要求,由教育部组织编写的高中历史必修教科书,它兼具学术性、政治性、教育性和综合性的特征,符合当代教育对中学生历史学习的要求。按道理,在如此权威的历史教科书中,不应该出现“基本事实”的问题。遗憾的是,笔者在阅读《中外历史纲要》过程中却发现了类似问题。现举两例如下:
《中外历史纲要》(下)第18 课“冷战与国际格局的演变”第一个子目下的“历史纵横”板块“凯南的‘长电报’和诺维科夫的‘长报告’”题目下有一段叙述:
随着二战后美苏矛盾的不断激化,双方的态度也逐渐强硬,都把对方视为敌人。1946年2月22日,美国驻苏联大使馆代办乔治·凯南向华盛顿发回一封8000 字“长电报”,提出了美国要依靠实力抵制苏联的扩张,同时又不会引起美苏之间全面军事冲突的主张。这是遏制政策的前奏。同年9月27日,苏联驻美国大使尼古拉·诺维科夫向莫斯科发回“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长篇报告,断定美国战后对外政策的特征是谋求世界霸权,将苏联视为其通往世界霸权道路上的主要障碍,并正在把苏联作为战争的对象而准备未来的战争。由此可见,二战结束仅仅一年,美苏双方的对外政策都从大国合作转向了对抗。
这段叙述中提到“8000 字‘长电报’”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此前学术界是有所争议,但现在已不成为一个问题,学者已有了基本的共识。
在国外,1986年,沃尔特·艾萨克森和埃文·托马斯所著的《美国智囊六人传》一书中曾提到过:“他继而口授了一份5540 个字的、后来被称为‘长篇电报’的分析意见。”研究凯南最权威的学者约翰·加迪斯对这封电报的字数提出了商榷,他在《乔治·凯南:一个美国人的一生》中说:“1946凯南的‘长电报’有一些不准确之处,这封电报并不像他在回忆录中描述的那样‘大约8000 字’长,实际上这封长电报的总字数刚刚超过5000 字。”作者约翰·加迪斯承认了自己多年以来误用“8000字长电报”的说法,并且感谢了尼古拉斯·汤普森对于乔治·凯南“长电报”字数为5540 个字的精确计算。这里的8000 字或者5000 字是就英文单词来讲的。
在国内,冷战史专家沈志华教授在其著作《冷战国际史二十四讲》中说:“凯南很快写出了一份调查报告,这份报告英文单词共5500 多个,译成汉语更是多达8000 字。”针对这一说法,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史教授张小明先生将“长电报”翻译成中文,而结果是10000 多字。这里的8000 字或者10000 多字是就汉字来讲的。
《中外历史纲要》中的“8000 字长电报”是指英文单词还是指汉字?指向不明确。指英文单词的个数,显然5540 字的长电报更准确,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史专家戴超武教授就使用这个数字,他在论文中提到:“凯南在1946年2月 22日向国务院发回了一份长达5540 字的长电报。”指汉字的个数,由于每个学者的翻译标准不一样,翻译出来的字数也不一样,因此有8000 字或10000 字之说。由此可见,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学术界,无论是用英文单词还是用汉字计算,“8000 字‘长电报’”的说法都是有问题的。
那么,如何叙述才不会犯“基本事实”问题,学者们在撰写学术论文时会采用不提具体字数,用“长电报”取代传统的“8000 字长电报”的表述。比如南京大学石斌教授在其《核时代的美国安全观念与战略传统》一文中就运用了“长电报”的说法,而不再提“长电报”的字数问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张小明教授在其论文《“遏制”概念与冷战史研究范式》中全篇使用“长电报”的说法,并在注释中提倡用“长电报”或“长电文”取代“8000字长电报”的说法。《中外历史纲要》似可采用这种叙述,以免出现“基本事实”的问题。
又比如,在《中外历史纲要》下册第17 课“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战后国际秩序的形成”第一个子目“法西斯主义与亚欧战争策源地的形成”中有这样的叙述: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意大利、德国和日本产生了法西斯组织。1919年墨索里尼成立的“战斗的意大利法西斯”,是世界上第一个法西斯主义政党,后更名为“国家法西斯党”。1922年,墨索里尼建立了法西斯政权。1920年,希特勒组建“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简称“纳粹党”,是德国法西斯运动的开始。1921年,冈村宁次、东条英机等日本军人订立密约,要求“消除军阀、刷新人事、改革军制、建立总动员态势”,是日本军部法西斯运动的开始。
在这段叙述中,有“1920年,希特勒组建‘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简称‘纳粹党’,是德国法西斯运动的开始。”一般来讲,“组建”意为组织和建立,它强调的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事实上,该党并非由希特勒建立,而是希特勒受命调查一个社团,这个社团名“德国工人党”。希特勒被邀请去参加该社团的一个会议,会后该党主席邀请希特勒入党。1919年,希特勒加入“德国工人党”。比如,在朱忠武等人所著的《德国现代史1918—1945》一书中有叙述为:“一九一九年九月十六日,希特勒以慕尼黑国防军侦探身份加入德国工人党,成为该党的第七名委员。一九二〇年初,希特勒开始领导该党的宣传工作……一九二〇年四月一日,希特勒将德国工人党更名为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简称为纳粹党)……一九二一年七月,在党内确立‘领袖原则’,希特勒成为了党的拥有独裁权力的唯一领袖。”在乔希姆·费斯特所著的《希特勒传》中也有关于希特勒和纳粹党的描述:“1919年9月12日,也就是收到希特勒这份报告4 天后,梅耳上尉命令希特勒去拜访和考察以下众多激进团体和派系中的一个——德国工人党……几天后希特勒收到了一张不请自来的会员资格卡。”“考虑的结果是他以委员会第7 号成员的身份加入德国工人党。”“在霍夫布劳啤酒馆的会议结束一周后,德国工人党改换了自己的名称。通过借鉴一些相关的德国和奥地利的团体名称,它现在自称纳粹党。”由上可见,《中外历史纲要》中讲希特勒组建“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并不准确。准确的叙述应是:1920年,希特勒改组“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该党简称“纳粹党”。
《中外历史纲要》之所以出现两个“基本事实”问题,笔者认为原因有二:
1.教科书的编写者没有搞清楚基本事实。众所周知,相对于学术界关于某一问题的论述,教科书中的有些论述总是比较“保守”的,有的叙述甚至几十年不发生多大变化。但即使“保守”,似也应该尽可能吸收一些学术界早已达成共识的结论或论述,以保证“基本事实”的准确性。上文提到的“8000字‘长电报’”就是显证,教科书的编者大可以使用英文单词下的表述:凯南在1946年2月22日向国务院发回了一份长达5540 字的长电报。或者使用汉字下的表述:这封长电报译成中文,由于翻译的标准不一致,有8000 字或10000 字之说;也可以借鉴学术界的一些叙述,干脆取消数字,直接使用“长电报”。如此,“基本事实”就准确、清楚了。
2.教科书编写者的叙述问题。刘知畿在《史通·叙事》篇说:“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在具体原则上,又提出:“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要的标准是“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文约而事丰”大概也是历史教科书要追求的一个目标。但是仅仅为了追求“文约”,有时是以牺牲叙事的精准性和准确性为代价的,就像赫克斯特(J.H.Hexter)说:“为了传达一种所增加的知识和意义,真正的历史学原则要求这样一种修辞,它对于唤起能力和范围来说,要以牺牲其普遍性、精确性、控制性和准确性为代价。”而上文所举的“希特勒组建纳粹党”就有最好的例证。如果对于希特勒和纳粹党的关系多两句解释的话,那么就不会出现“基本事实”问题。对于历史叙述而言,准确、清楚是最起码、也是最根本的要求。因此,历史教科书似亦应以叙事准确为第一标准,因为“基本事实”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是必要条件。
[1][英]爱德华·卡尔著,陈恒译:《历史是什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91—93 页。
[2][美]沃尔特·艾萨克森、埃文·托马斯著,王观声译:《美国智囊六人传》,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354 页。
[3]John Lewis Gaddis,George F.Kennan:An American Life.New York:The Penguin Press,2011,p718.
[4]沈志华主编:《冷战国际史二十四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8年,第9 页。
[5]张小明:《重读乔治·凯南的“长电报”》,《美国研究》2021年第2 期,第123 页。
[6]戴超武:《斯大林、苏联外交与冷战的起源》,《俄罗斯研究》2013年第1 期,第45 页。
[7]石斌:《核时代的美国安全观念与战略传统—对两个经典文本的重新探讨》,《史学月刊》2018年第9 期,第105 页。
[8]张小明:《“遏制”概念与冷战史研究范式》,《史学集刊》2020年第4 期,第9 页。
[9]朱忠武等:《德国现代史1918—1945》,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99—100 页。
[10][德]乔希姆·费斯特著,黄婷、马昕译:《希特勒传》,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48、49、52 页。
[11]刘知畿:《史通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52、156 页。
[12]陈新:《当代西方历史哲学读本(1967—2002)》,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8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