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微中的繁荣*
——易县燕下都遗址编磬研究
2022-10-29贾伯男孔义龙
贾伯男 孔义龙
内容提要:战国时期燕国乐器目前仅在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16号、8号和30号墓出土。而编磬的数量在燕下都出土乐器中占据了一多半。燕国“磬乐”的繁荣从战国早期一直持续到战国晚期,并几乎达到了各国不能企及的高度。一方面,燕国“磬乐”在礼乐衰败的战国时期一枝独秀。另一方面,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燕国“磬乐”从早期到晚期也呈衰败趋势。但在规范性和音响性能、材质衰微的同时,其编列规模变大,且出现了繁复的纹饰。可以看出燕国上层社会对于磬乐的喜爱和在礼乐制度中对于编磬的重视从未改变。
磬是流传于我国先秦时期的石制击奏体鸣旋律乐器。《世本》载:“黄帝使伶伦造磬”,“无句作磬”,“磬,叔所造”。《山海经·西山经》曰:“小华之山,……其阴多磬石。”“泾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渭,其中多磬石、青碧。”《尚书·禹贡》云:“泗滨浮磬。”这些古老的传说虽不足为信史,但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磬的久远历史和先民对磬的石材与音色的认知。石磬在新石器时期一直以特磬的形式存在,到商代晚期分化成特磬与编磬两种形制并存的形式,西周以后编磬逐渐取代特磬。编磬在发展过程中虽然历经曲折,但凭借从产生起就具有的礼乐双重身份,使其最终成为周代乐悬制度的核心乐器之一。
河北省保定市易县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史称燕下都。在燕下都故城考古勘查中共发现有墓葬群三处,计31座墓。到目前为止,发掘了其中编号为8号、16号、30号的三座墓,出土了大量的战国时期燕国的文物,同时这三座墓也是目前唯一出土战国时期燕国乐器的墓葬。由于燕国音乐鲜见于文献,而仅有的与音乐相关的记载也语焉不详,所以燕下都遗址出土的乐器对于研究战国时期燕国的音乐文化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燕下都遗址出土乐器跨越战国早期到晚期,共158 件。乐器的种类为金、石两类。其中战国早期16 号墓出土编镈10件,甬钟16件,纽钟9件,编磬15件;战国中晚期8号墓出土编磬24件;战国晚期30号墓出土编镈9 件,甬钟13 件,纽钟19件,铙1件,编磬42件。从出土乐器的数量上看,磬占到总数的一半以上,是这三座墓中唯一一种均有出土的乐器。其中30号墓编磬为陶制明器,而16号墓与8号墓中出土的39件编磬则为石制,这也是燕下都中仅有的实用乐器。如此大规模的编磬出土真实地反映出战国时期燕国磬乐的繁荣。
16号墓编磬(图1)为实用器,其材质为红褐色沉积板岩类石质,大小成序列。倨句角度大多一致,磬底弧曲上收,弧度匀称,曲线协调。编磬多已破碎,大多音律已失。58号磬音哑,10号磬音质较好。

图1 16号墓编磬(作者拍摄)
战国中晚期8 号墓仅出土了一组编磬,大小成序列。其材质为板页岩类石质,石质坚硬,通体无纹饰。编磬呈倨句形,倨句角度较大,磬体多呈上厚下薄,断面呈倒梯形状。鼓端也要比股端稍薄。倨孔一面较大,一面较小,应为单面钻。
30号墓陶编磬共分5组,各组编磬大小相次。
第1组:8件,形制较大,周边正中施朱色纹带,两面周缘施朱色框,内填朱色卷云纹,大部分朱色脱落,仅两件纹饰完整。
第2组:9件,纹饰与第1组基本相同,但卷云纹有较多的变化。
第3组:7件,股博较宽,纹饰与第1组基本相同,但卷云纹有较多的变化,绝大部分磬朱色脱落,仅两件纹饰较完整。
第4组:11件,纹饰与第1组基本相同,但较简单,部分磬的朱绘纹饰保存较好。
第5组:7件,纹饰与第4组基本相同,绝大部分磬体朱绘纹饰脱落,仅1件磬纹饰较完整。
本文将着重对燕下都出土编磬的制作规范、音响性能设计、编列数量和纹饰等方面进行详细的分析,试图了解战国时期燕国编磬的发展情况。
一、从制作规范看燕国编磬的衰退趋势
《周礼·冬官考工记·磬氏》中详细记载了磬成熟时期的了各部分比例及调音磋磨手段,“磬氏为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为一,股为二,鼓为三。参分其股博,去一以为鼓博。参分其鼓博,以其一为之厚。已上,则摩其旁;已下,则摩其端”。即磬氏制作磬,(股、鼓)弯曲的度数为一矩半。以股的宽度作为一,股的长度就是二,鼓的长度则为三。把股的宽度分成三等分,去掉一等分就是鼓的宽度;把鼓的宽度分成三等分,用一等分作为磬的厚度。《考工记》中指出“股为二,鼓为三”,因此当“鼓”与“股”的比值为1.5 时则为正常比值,如果大于1.5则说明“鼓”的长度比《考工记》中记载的要长,反之则短。表1为根据三座墓葬出土编磬股与鼓的数据计算出的比值,通过分析,来了解燕国编磬与《考工记》的关系和燕国是否有着较成熟的制作规范。

表1 易县燕下都三座墓葬出土编磬“鼓”与“股”的比值
8号墓第一组7号磬,30号墓编磬第二组第2件和第4件磬受腐蚀严重,失其股长,所以没有“鼓”与“股”的比值数据。
上述8组编磬均按照形制由大到小排序。8号墓24件编磬大小相次应为一套,第一组整体尺寸大于第二组。其中第一组的12 号磬(XM8FK:3)出土于北墓道方坑,不同于其余23件,因其尺寸数据排列于此处。30号墓中第一、二、四、五组编磬整体尺寸由大到小,第三组7件编磬之间尺寸差距较大,与其余四组稍有变化不同。
16号墓15件编磬的“鼓”与“股”的比值最大为1.49,最小为1.35,比较稳定,其中7号磬比值与《考工记》要求最为接近。平均值约为1.406。
8号墓24件编磬的“鼓”与“股”的比值最大为1.51,最小为1.27,其中第二组3号磬与《考工记》要求最为接近。平均值第一组约为1.398,第二组约为1.372。
30号墓第一至五组平均值依次约为1.224、1.187、1.434、1.353、1.217,其中最接近1.5 的为第三组,但五组编磬比值最大的1.76和最小的1.1也均出自该组,可见第三组编磬制作时规范性不强。
16号墓比值最为稳定,8 号墓次之,30号墓最差。其比值越稳定就代表制作越规范。由此可见16 号墓编磬与《考工记》最为接近,且有自己规范的制作数据。8号墓编磬稳定性不如16 号,制作规范程度上不及16 号,但其数据也比较接近《考工记》。30 号墓稳定性比较差,制作并不规范,工匠并没有把制作的重点放到编磬的规范程度上,而是在磬身上绘制了大量精美的卷云纹。这也与其为陶土所制明器有关,也符合该墓葬其他乐器的纹饰风格。
同时,通过16号墓与8号墓两座墓葬编磬比值可知,大多数尺寸大的编磬更接近《考工记》中的记载。可以看出战国早期到中晚期燕国实用器编磬的制作较规范,且较大的石磬更受重视。
16号墓与8号墓编磬磬身较大,大小有序,30号墓编磬磬身较小,其大小变化较细微。目前所见编磬基本可分为直背型、折背型、弧背型、倨背型四种。燕下都三座墓的磬均属标准的倨背型。16 号墓由于为实用器,红褐色沉积板岩类石质,其制作精良,基本符合《考工记》中的比例要求。8号墓编磬为板页岩类石质,石质坚硬。30号墓的编磬追求纹饰的华美,为泥质灰陶所制,股博较宽。由此可以看出,燕国在战国早期还可以制作比较符合规范的编磬,但到了晚期,因常年的战乱,其乐器的制作工艺和精细程度大不如前,尤其是用于陪葬的乐器就愈发粗糙。但从形制上看基本还是一脉相承的。
值得注意的是,燕下都三座墓葬中出土的编磬只有30号墓为陶制,可能因为时间仓促的原因,来不及制作石质的编磬而选用容易制作的陶编磬代替。战国时期从公元前475年到前221年共255 年,期 间有165年经历战争,而大大小小的战争大约260多场。其中与燕国相关的仅有17场:战国中期3 场、战国晚期到灭国共14场。燕国从战国早期的相对稳定到战国中期开始出现战争,晚期更是大小战事不断。而战国早期16号墓编磬最为规范、中晚期8号墓次之,晚期30号墓制作规范进一步衰落的现象与历史史实相符。总之,三座墓葬出土编磬从其制作的规范程度、形制特征和使用材料出现了由盛转衰的变化,这种变化也是战国时期燕国国力从由盛到衰的映射。
二、从板振动原理看早期燕国编磬的优良音响性能设计
磬的发声原理是一种板振动,当磬的宽与高的比例值越大则低频泛音越多,音高越浑浊,反之则音高越清晰,音质越好。由于30号墓编磬为明器,不存在音质问题,8号墓的编磬因其周边受腐蚀风化严重,其高宽数据与下葬时差距较大而不予采用,而16 号墓编磬虽有断裂,但整体不影响其宽高数据。本文以16 号墓编磬为切入点,通过与周边同一时期编磬的宽高比值的对比来了解战国早期燕国编磬的音质情况,计算得出比值详见表2。

表2 编磬宽高比对比⑨

上表中易县燕下都16号墓编磬的宽高比值平均值为2.42,涉县北关1号墓编磬宽高比例平均值约为2.34,中山王错墓编磬2.41,临淄大夫观编磬甲组2.61、乙组3.09,阳信西北村编磬2.6,临淄商王乙组编磬2.55,临淄淄河店2号墓编磬甲组2.6、乙组2.52,太原金胜村88 号墓编磬3.17,太原金胜村673号墓编磬2.42。通过这些数据可知,易县燕下都16号墓编磬的平均宽高比例在战国时期11组编磬中较小,其音质应更清晰。
按序号横向看,则为各组编磬中通高通长相近的石磬,可以看出易县燕下都16号墓中除9号磬与10号磬没有与之相近大小的磬外,其中有10件的比值在上表中显示最小,两件中等,只有11号编磬比值较大。这说明16号墓编磬的音质在同等大小编磬中也较清晰。
16号墓编磬按序号由大到小排列,其比值也基本依次由大到小,这意味着该组编磬越大音质越浑浊,编磬越小则越清晰,可看出当时燕国制磬技术依据磬身大小而有所变化。
由于16号墓的编磬受损严重,多失音律,仅有一件能发出音色较好的乐音,无法通过测音来研究编磬的音律等问题。但从上述的数据中不难看出燕国编磬制作中对于音乐性能的追求和在当时较高的石磬音响性能设计水平。
因此,通过对同时期编磬音响性能设计的比较可以看出,战国时期燕国编磬设计不论从整体的规范程度还是音乐性能方面,均属当时的佼佼者。
三、从编列数量看燕国磬乐的繁荣
磬作为先秦礼乐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仅具有音乐功能,更重要的是其礼乐功用。到了商代,磬的音乐功能得以具化,其形制进一步固定,为编磬出现创造了条件。两周时期,特磬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编磬进一步发展壮大,这一时期编磬从规模、形制纹饰、音列等方面都到达到了顶峰,之后逐渐衰落。汉代出土的磬已经多为明器。编列数量的多少不仅与其规格相关,更与墓主人对其喜爱程度和对礼乐的追求密切相关。
燕下都与其他地区编磬数量对比见表3。

表3 其他地区出土编磬⑩

编磬由于其取材与制作的相对容易,一直以来都是金石类乐器中出土数量最多的。但像燕下都遗址这样编磬占出土乐器总数的一多半实属罕见,足见编磬在燕国乐悬制度中占有的重要地位。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战国时期燕国编磬在数量上的僭越程度。
由表3可知:编磬在春秋战国之际一般一组为10件左右,其僭越程度在乐器中比较突出。春秋战国时期周边地区编磬数量超越16号墓的有:东周洛阳解放路编磬(23件)、西周中晚期秦公一号大墓编磬(36件)、春秋早期曲村晋侯邦父墓编磬(18件)、战国长治分水岭127号墓编磬(20件)、战国信阳长台关2 号墓木编磬(18件)、战国江陵彩绘编磬(25件)、战国长治分水岭14号墓编磬(22件)、战国早期临淄淄河店2号墓编磬(24件)等,可见燕下都16号墓中的15件编磬僭越的并不十分严重。但在明确断代为“战国早期”的墓葬中,仅有临淄淄河店2号墓编磬(24件)的数量可以超越。而同为“国君级”的墓葬也仅有曲村晋侯邦父墓编磬(18 件)和临淄商王编磬(16件)可以超越。可见,16号墓编磬的数量在春秋战国时期处于中上,但在同时期或同规格的墓葬中是十分突出的。
8号墓作为国君夫人墓,24 件编磬亦为僭越中的佼佼者。而30号墓的42件编磬,其数量超越目前已知的中原地区所有墓葬,其“僭越”程度令人吃惊。
四、从朱绘卷云纹看燕国磬乐的晚期辉煌
燕下都三座墓葬中8号墓与16号墓的实用器编磬为素面,没有纹饰,而30 号墓出土的陶编磬则绘有大量的朱绘卷云纹。战国时期燕国陶器上的纹饰发展得十分成熟,内容丰富且独特,其中兽首、卧兽、鸟形等较为复杂的造型在其他地区是不曾见过的。燕国瓦当上的纹饰,更使其成为战国时期瓦当艺术中三足鼎立之一,尤其是其朱绘卷云纹堪称众多纹饰中的翘楚。30号墓磬身上的纹饰(见图2、图3)在众多出土乐器器身纹饰中最为精美灵动,在战国时期可以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图2 易县燕下都30号墓陶编磬第1、2组线图⑯

图3 易县燕下都30号墓陶编磬第3、4、5组线图⑰
现存实用器编磬中存在纹饰的较少见,主要有周原召陈乙区遗址夔纹编磬、舒城九里墩编磬、江陵彩绘编磬等。但是这些有纹饰的编磬,没有一例绘有通体卷云纹。30号墓编磬上的卷云纹,十分生动形象,根据磬身大小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变化,它们已经不仅仅是一批随葬的明器,而是成型的艺术品。这种写意的手法在其他地区十分少见,与燕国相邻的赵国(图4)和中山国(图5)也有这种写意趋势的纹饰,但较少。可见这种纹饰在燕国成熟,并影响到周边地区。

图4 涉县北关1号墓编镈鼓部纹饰㉑

图5 中山王错墓铎舞部的纹饰㉒
云纹被古人赋予尊贵、吉祥的含义,此外云纹与原始信仰图腾有关。所以云纹在历朝历代器物纹饰的应用上十分广泛。燕下都除30号墓出土乐器中见到了大量的卷云纹外,在墓葬区已经发掘的三座墓葬器物上也出现了大量的云纹,尤其是这种朱绘卷云纹在三座墓葬中均有发现。(见图6、图7、图8)

图6 16号墓铜合页纹饰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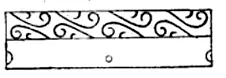
图7 8号墓圆柱形器上的卷云纹㉔

图8 30号墓方壶上的朱绘卷云纹㉕
其中编磬上的纹饰与8 号墓圆柱形器、16号墓铜合页和30号墓方壶等器物身上的卷云纹十分相似。可见卷云纹在燕下都出土器物中为一脉相承的关系。
通过燕下都出土器物卷云纹的形态可知,在簋、方鼎等较高级别礼器上均有出现,所以卷云纹饰在燕国的上层社会中也是一种比较高级的纹饰,亦可见燕国上层贵族对于编磬的重视。
结语
燕下都作为战国时期燕国都城,其音乐生活亦是燕国音乐文化的缩影。三座墓葬出土的编磬从制作的规范程度、形制特征和使用材料均出现了由盛转衰的变化,这种变化也是战国时期燕国国力从由盛到衰的映射。三座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礼乐器,其中只有16号墓编磬和30号墓编磬为实用器,其余均为明器。编磬直到战国晚期才作为明器出现在燕国墓葬中:一方面是由于编磬制作相对容易;另一方面则是燕国磬乐十分繁荣和燕国人对其喜爱的表现。
燕下都出土的编磬在音乐性能设计方面是战国时期的佼佼者。不论是全套编磬,还是单个石磬,都体现出燕国当时高超的石磬设计水平,也可看出燕国人对磬乐音响性能的追求。
燕下都共出土编磬81件,占据燕下都出土乐器的一多半,其数量也是战国时期北方出土编磬最多的墓葬。尤其是30 号墓出土了42件编磬,数量超越了目前已知的中原地区所有墓葬。
从战国早期、中晚期编磬磬身无纹饰到晚期绘制通体变形朱绘卷云纹,可看出燕国磬乐发展的繁荣。30 号墓磬身的卷云纹在已知出土的磬上从未出现过,但在出土乐器的早期16号墓,中晚期8号墓和出土该套编磬的30号墓中均出现了类似的纹饰。且这种纹饰在燕国墓葬中出土的簋、方鼎等较高级别礼器上均有出现,可以看出在燕国的上层社会中卷云纹是一种比较高级的纹饰,亦可见编磬在战国晚期的受重视程度进一步加深。
总之,燕国“磬乐”的繁荣从战国早期一直持续到战国晚期,并几乎达到了各国不能企及的高度:一方面,燕国“磬乐”在礼乐衰败的战国时期一枝独秀;另一方面,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燕国“磬乐”整体也呈衰败趋势,但在规范性和音响性能、材质衰微的同时,其编列规模变大,且出现了繁复的纹饰。可以看出燕国上层社会对于磬乐的喜爱和在礼乐制度中对于编磬的重视从未改变。这也使得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战国晚期礼乐最后的辉煌。
①[汉]宋衷注,[清]秦嘉谟等辑:《世本八种》,商务印书馆,1957,第659页。
②同①,第360页。
③同①,第361页。
④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23页。
⑤同④,第34页。
⑥[清]阮元校:《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中华书局,1980,第148页。
⑦[清]孙诒让撰,王文锦、陈玉霞校点:《周礼正义》,中华书局,1987,第3350-3356页。
⑧以上数据根据杨宽所著《战国史》中的《战国大事年表》统计。
⑨此表格以燕下都16号墓编磬为标准,横向展示的比值均为与其高宽最近者。
⑩文中数据来源于《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各卷和发掘报告,其中各墓规格主要来源于发掘报告,所选取多为可以判定规格的墓葬,其中有少量规格不明确,但用乐数量较多的墓葬也收录进来。
⑪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安徽蚌埠双墩一号春秋墓发掘简报》,载《文物》,2010年第3期,第4-18页。
⑫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凤阳县文物管理所:《凤阳大东关与卞庄》,科学出版社,2010。
⑬安徽省文物工作队(执笔者:杨鸠霞):《安徽舒城九里墩春秋墓》,载《考古学报》,1982 年第2期,第229-242页。
⑭出土地址为山西。
⑮安徽省六安县文物管理所(执笔者:许玲):《安徽六安县城西窑厂2 号楚墓》,载《考古》,1995年第2期,第124-140页。
⑯吴东风、苗建华主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Ⅱ·河北卷》,大象出版社,2008,第83页。
⑰同⑦,第85页。
⑱西周中晚期墓葬,共15件,出土于陕西,纹饰为阴刻夔纹、阴线重环纹、阴线鳞纹。
⑲春秋晚期国君墓,共5件,出土于安徽,纹饰为朱色雷纹。
⑳战国时期墓葬,共25件,出土于湖北,纹饰为1-3只凤鸟。
㉑图4见同⑯,第9页。
㉒图5见同⑫,第49页。
㉓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燕下都》,文物出版社,1996,第653页。
㉔同⑭,第680页。
㉕同⑭,第69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