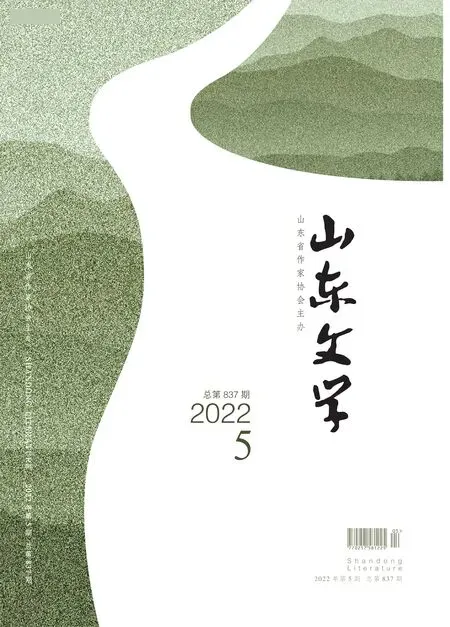来燕堂砚话
2022-10-29刘凤桥
刘凤桥
大连得砚
今年的中秋节,我休假在沈阳。节后,应友人之邀,到大连一游。有四五年没来大连了,风景依旧似昔时。还是我心中那座洋味十足的城市。旧地重游,风景已不重要,他乡遇故知,与老朋友相聚则是最快乐的事情了。然旧雨新知欢聚之余,我照例要逛逛当地的古玩市场。按照仰宋堂赵胥兄的指点,第二天下午,我们来到坐落在市区东关街的良玖古玩城。
从一楼转到三楼,感觉好一点儿的店我都进去瞅瞅,确实如胥兄所言,没有能相上眼儿的东西。略感失望之际,朋友说上面还有一层,于是我们来到四楼。在电梯边上有一家名曰“老古玩”的店铺,从橱窗中文玩古籍之类的陈设看,挺有品位的。我们走进店里后,原先在店里看东西的几个人就陆续出去了。我则抓紧时间一边看东西一边和店主聊天,得知店主姓王,这个店是今年八月十五刚开的,这两天来看东西的人比较多。王先生从小就喜欢收藏,经手了不少好东西。他收东西比较讲究,古玩之类的必须与文人沾边,也就是说偏重于文房类藏品的收藏。这很对我的趣味,所以我们聊的投机,王先生人也很诚实爽快。他有很多藏品我都喜欢。我在他的店里逗留了大概两个多小时,最终买了两件藏品,一件是姚鹏图的书法册页,临了两通《兰亭序》,其他的也都是小字,原装旧裱,甚是精彩。姚是清末名士,金石学家,词人,留存的墨迹不多。我有他题铭的一方井田砚,购买时做过一些功课,所以对他有些了解。王先生说这本册页是山东省图书馆一位老先生的旧藏,他从老先生家里收了不少好东西。姚鹏图是山东省图书馆的缔造者之一,清末民国年间,在山东很有名望。这本册子出自山东省图书馆的一位老先生家里,也算渊源有自了。
买的另一件藏品是石质的金蟾形小镇纸,随形雕琢,遗貌取神,简略有趣,特别是包浆古厚莹润,色泽极美,既可做镇纸,案头赏玩,又可在伏案之余握于掌中舒筋活血。先贤雅趣于兹可见一斑。朋友们开始不理解我为什么要买这么一块石头,后经我一番描绘,这才恍然大悟,连连称妙。惟赵胥兄一见曰“好”,解人也!
其实,在王先生的店里我还看上了几件东西,有一件日本的竹制文房盒,做工精致极了,枣红色的漆面,光亮润泽,极是惹人怜爱。还有一支日本“得应轩”制作的竹杆毛笔也不错,但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抓我心的是一方“汝奇作”的九如灵芝纹随形老端砚。这方砚配有清代楠木盒,正面平池,刻一阳一阴两枝灵芝纹饰,背面横刻一枝根壮叶茂的大灵芝,在大灵芝的两侧又分别浮雕了六枝小灵芝,有阴有阳,顾盼生动。前后共雕九枝灵芝,故称“九如”砚。整个画面浑然一体,古拙大方,很见气度,处处用刀却不留刀痕,线条流美,气韵生动,一看就是大师妙手所为。灵芝主干上刻有行草书“汝奇作”三字款,用刀松弛如挥毫,笔画行云流水般舒展自如,灵动活泼。这种以刻当写的铁笔功夫,绝非等闲之辈所能,也非嘉道以后金石刻手所为。砚台石质温润细腻,砚面略有墨垢,然包浆自然,旧气开门,真是难得的一方佳砚、美砚!
由于时间关系,又因对方心气较高,我当时没有还价,只是拍了几张该砚的图片,说回去研究研究。晚饭后,我又对着照片仔细研究了一下,感觉这方砚台无论是制作水平,还是款识书法、铁笔功夫皆臻上品,无可挑剔。盒子虽不是名贵木材(楠木刷漆),但也素朴大方,与此砚相伴相依至少也有一二百年了。
同时,我也参考了朋友发来的一方“汝奇”款砚(民间所藏),无论是砚台工艺还是书法水平,与我所遇到的这方“汝奇作”砚台,直如天渊之别,高下立判。史书记载,谢汝奇“善草书,波折清遒,得涪翁法。”又说“工怀素,大者尤苍劲“。“至端溪砚石,一经琢磨即成佳制”云云。这样的记述,在我所遇见的这方端砚上都可得到印证。我又特别对谢汝奇的书法做了一番比较,确定无疑之后,我便约王先生第二天再见面聊聊,并询问了这方砚台的底价。
第二天大连有小雨。吃过早饭后,我们又如约来到古玩城王先生的店里。我又看了些昨天没来得及细看的东西,当然这方砚台仍是重点。我的夫人一直跟在我身边,她也上手仔细看了看这方砚台,并私下告诉我她感觉这是一方好砚,“应该是真品”。
夫人这些年跟我出入古玩市肆,耳濡目染,对字画古玩很有些鉴赏能力,我们经常会对一张画一方砚台有同样的审美感受。所以,有时候,我对她的意见是很重视的。对这方砚台,我和夫人的感觉很一致,遂决定购买。最后由夫人和王先生商量价格。王先生见我们夫妇如此诚心,又给了一些优惠,并将我昨天相中的那件日本竹盒赠送给我们作为纪念。我们告辞走出小店,刚一出门,见展柜里有一清末三层粉彩文盒很是漂亮,便又折回店里,请王先生取出来细看,果如王先生所说“一点毛病没有”“绝对是文房佳品”,遂又问价收藏了。这次,我也很爽快,没再跟王先生讲价。我和王先生互相加了微信,相约以后多联系多交流。
大连之行虽然只有短短两天,但见了老朋友,认识了新朋友,又得到了几件心仪的宝贝,真是收获满满,不虚此行啊!特别是参观了赵胥兄的山上美术馆并亲见他半斤酒后仍能为我砚拓题跋,小行书隽永潇洒,一丝不苟,真佩服这家伙是个人才!
回到沈阳后的第二天,我在怀远门古玩城和一位玩古高手孙先生喝茶聊天,他看了我买的寿山石纸镇还有端砚的照片,对这两件东西都极为称赏。他说他虽然不懂砚台,但一看那刀工,绝对是顶级的。这可能就是古玩人的敏感吧!孙先生对好东西的敏感度极高,在这古玩城里拣了几件很上档次的宝贝,有的还被选入了工具书,成了标本。
最后,再来谈谈这方砚台的制作者“汝奇”吧。汝奇即谢士骥(生卒年月不详,乾隆十二年尚在世),他是康乾年间文人砚的代表作家,出生于福建侯官(今福州),字汝奇、宏卿。能诗善书,精篆刻,擅长琢砚,“鉴赏家珍如圭璧”(引乾隆年间侯官秀才郑杰所撰《注韩居诗话》)。汝奇诗书底蕴深厚,为人潇洒疏淡,被黄莘田誉为嵇康、阮孚一类人物,所以为艺境界自然高远,真气弥漫。坊间有人将其与另一大家顾二娘比较,认为顾二娘琢砚以俗雅胜,谢汝奇制砚以文雅胜。顾氏制砚,我没有上手把玩过,不敢妄评。但汝奇作的这方九如砚,却可置之案头,晨夕品鉴,确实有“郁郁乎文哉”之感,雅韵欲流,信非凡品。
谢汝奇制作的砚台存世极罕,上海博物馆藏有他制作的《赤壁图端砚》,有“环翠楼”篆书印,曾经为清初藏砚大家黄任收藏。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有他制作的《云月端砚》,也有黄任的题铭,为馆藏重要文物。至于民间私藏,则稀如星凤矣!
沁香阁遗砚
河北老张原来在文物店工作,后来辞职不干了。在程田古玩城开了一爿古董店,经营的多数是从日本回流的东西,也有一些古砚。我偶尔到他店里坐坐,喝喝茶,聊聊天,遇到喜欢的文房件也买买。我收藏的那对罗复堪题字的紫檀篏银丝镇纸就是从他手上买的。砚台一共买过五方,一方菊花石椎圆形小砚,砚背刻有“沁香阁”印款,是清末著名小说家李涵秋的遗物。是老张从“瘦西湖”那里买的。我收藏后,请郭师傅做了一个红木砚盒,又请著名文艺评论家陈丹晨老先生题了砚铭,镌刻在盒盖上。题的是“四壁烟霞古洞天”,这是石楚青赞美李涵秋沁香阁的诗句,陈老移来题砚,也是很恰当的。
李涵秋(1874-1923),名应漳,号韵花、别署沁香阁主人,扬州人。12岁习古文辞章,17岁设帐授徒,20岁中秀才。1921年,李涵秋赴上海主编《小时报》,兼为《小说时报》及《快活》等报刊撰写小说。据《扬州历史人物辞典》记载,李涵秋一生著作颇丰,计著有长篇小说36部,短篇小说20篇,诗集5卷,笔记杂著25篇,遗著有《沁香阁游戏文章》。
李涵秋被誉为民国第一小说大家。代表作《广陵潮》,以扬州社会为背景,以恋爱故事为线索,反映自中法战争到五四运动这一阶段的社会百态,布局巧妙,通俗幽默,受到当时文艺界称誉。如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认为,在“现在的小说”中,《广陵潮》是属于“上等的”,但同时又认为它“不配在新文学上占一个位置”。瞿秋白在《鬼门关以外的战争》中认为,在“新出的白话小说”中,《广陵潮》是属于“坏一点的”,但同时又承认它“至今还占领着市场”。无论如何,《广陵潮》在辛亥革命之前就已经问世,而在八十年以后的今天仍拥有大量读者,这不能不说它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正如张恨水在《广陵潮·序》中所说: 《广陵潮》是三十年前的作品了。第一,我们不能用文艺尺度来量它,这是要紧的。认定了这一点,我们可认为李先生在当年下笔,对社会现状有很好的反映。写出来,虽然是中国一个角落,那也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是个什么状态。他虽没有强调革命的意识,在许多地方他是反封建的。当年除了《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和《官场现形记》,没有第三部书能够这样对旧社会猛加抨击。而且以上二书,有些地方夸张过甚,倒不如《广陵潮》写一角落,还比较能把握现实。根据《鲁迅日记》的记载,鲁迅也曾经购买和阅读过《广陵潮》这部小说。
1923年5月,李涵秋因“脑溢血”而去世,同乡兼好友张丹斧撰挽联:“小说三大家,北存林畏庐,南存包天笑;平生两知己,前有钱芥尘,后有余大雄。”
李涵秋的逸事很多。据说他每次去上课,总是骑着一头毛驴到学堂去,优哉游哉,令人想起在驴背上觅诗的古代骚人。他喜欢养鸟,认为鸟鸣可以助其文思。他初次到上海时,友人领他乘电梯,他惊讶地说:“这房间怎么这样小?”每逢友人相聚会餐,别人吃西餐时,他总是单独要一份中餐。他的眼睛高度近视,有一次去访周瘦鹃,晤毕告辞,但一二分钟后又折回原处,因为他看不清楼梯。有一次,涵秋在一部小说中偶然涉及某公司产的糖果,该公司因此销路大增,盈利数倍,为感激作家,这家公司特地备了最高级的糖果,装以锦匣,恭敬地送给涵秋。涵秋本是无意,不料得到意外口福,便将糖果分赠给朋友。涵秋文思敏捷,有时能够同时做五六种小说。周瘦鹃在《李涵秋》一文中就曾回忆说,有一段时间,涵秋同时为《新闻报》写《镜中人语》,为《时报》写《自由花范》,为《晶报》写《爱克司光录》,为《快活》写《近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为《小说时报》写《怪家庭》,还为《商报》写一部名字不详的小说。这种超人的精力,是一般人难以望其项背的。据说,当年的报纸都以登载涵秋的小说为荣,时人甚至有“无郑不补白,无李不开张”之谚。前一句谓报纸的补白必须郑逸梅,后一句谓副刊的开张必须李涵秋。
李涵秋涉猎深广,诗书画印俱佳,只是为小说名所掩。1923年,江都贡芹孙编著,由上海天忏室出版部出版的《李涵秋》中第二编是《涵秋艺术》,其中介绍了李涵秋的文、诗、书画、金石,并附有四幅书法作品、两幅绘画作品和数枚自镌图章。他的书法宗王右军,肥瘦秾纤,弥所不宜。郑逸梅在《人物和集藏》中说:“(李涵秋)所作柬札,秀劲有致,曩年给我的书信,凡若干通,自经浩劫,仅留其一,我心瑰宝视之。”
李涵秋绘画精研工媚,若出闺秀手。喜作花鸟画,且擅画菊,设色清妍,墨致浑脱,若不腕力者。当他在扬州设立私垫时,贡少芹持一白纸扇来访,李涵秋看见,便自告奋勇,磨墨濡笔,为作山水,即题云:“少芹不索我画,我偏要画,且泼墨画远水遥山,自谓尺幅中有千里之势,盖我非画前人之画,乃画我之画?”李涵秋绘画笔法疏宕,充满文人画风格。李涵秋有时画菊,有时画秋柳,画鸣蝉,也都脱俗可人。扬州中学老人忆及,先生执教时,凡学生作文成绩特佳者,乃作书画扇为奖励品。学子得获,辄视若珍宝。一次,扬州军政分府的都督徐宝山以扇面请涵秋作画。适兴至,涵秋饱蘸赤朱于笔,立成蟹二。另涂墨作残菊二三枝,横卧于地,盖正持螯赏菊时也。细玩之,笔致苍劲,神韵饱满。徐得之喜,将设宴以报。不料徐中仇人之计被炸死。涵秋闻之叹曰:“横行将军果就烹矣,吾画岂为预兆乎。”
李涵秋也擅长篆刻。早年他收藏前人印谱甚多,经常观摩。时间长了自己也就能操刀治印。据贡少芹的《李涵秋》一书中载有他的13幅印章,其中有“李应漳印”“涵秋”“江都李氏”“涵秋翰墨”“著书时代之涵秋”“李涵秋印”等,以及“二十四桥明月夜”“学然后知不足”“纸墨相发偶然欲书”等闲章。它们有白文,有朱文;或刚健浑厚,或稳当自然,可见他运刀熟练。据郑逸梅《清末民初文坛故事》中云:“经少芹搜罗了一些,复乞助于涵秋弟镜安,涵秋夫人薛柔馨,钤成一册,或和著《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李伯元的《芋香室印存》媲美。”可惜这本李涵秋的印谱已散佚,我们已不能看见更多的涵秋印章。万幸的是,这方小砚上尚有李涵秋所刻印章一枚,或可聊慰遗憾之怀。
李涵秋的沁香阁在扬州宛虹桥,屋虽三楹,然结构殊为雅致。室内有吕凤子所书对联及古碑拓片,室外小圃有花木扶疏,且蓄各种鸣禽。郑逸梅曾专门写有沁香阁的文字:民国初年名小说家李涵秋,时居扬州,我常与之通信。涵秋应狄平子之聘,来沪编《时报》副刊,始得与之把晤,其扬州之书斋沁香阁,闻之而未一至也。顷见友人张翼鸿有《李涵秋先生传略》,谈及沁香阁,爰摘录之以窥一斑:“沁香阁,后名韵香旧馆,为宛虹桥江都烟业会馆之东屋。屋仅三楹,结构殊雅致,为涵秋早年设馆,后充著作室之用。壁悬吕凤子所书对联,余为石拓之古碑帖。石楚青夫妇往谒,曾有句云‘四壁烟云古洞天,师门同叩李青莲’。可见其环境之清幽。室前有小圃,杂莳花木,檐前有鸽棚,养鸽十余头,系铃高飞,声闻九霄。”
这方砚虽然没有什么雕饰,但小巧可爱,与沁香阁的幽雅还是蛮配的。
陈方恪“璞砚”
这方砚也是河北老张让与我的。他收藏了很多年,一直没舍得卖。两年前老张让我赏玩了一次,从此,一见钟情,记在心里挥之不去了。庚子年,我砚兴大发,相继收藏了几方好砚,遂乘胜追击,向老张展开了凌厉攻势。几番较量下来,老张终于被我的痴情打动,同意让了。尽管开出的价格超出我的心理价位不少,但人家肯让,已经是很大的情面了,区区几沓钞票又算得了什么!何况,好东西向来是无价的。能见到,已是眼福不浅,如果条件允许,机缘巧合能藏为己有,那得是冥冥中多大的福报啊!我一直相信很多事情是有前因的,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事儿!
所以,我还是要深深地谢谢老张!
这方砚保存的非常好。原配的红木盒,枣红色包浆一流。砚是随形的老坑端石所制,很厚。石质细腻,触手即润,呵气凝露。砚堂平展,上方开一圆形小砚池,其它皆随形简单修饰。砚背阴刻篆书铭文曰:“厚重端介,悃款无华。含贞吐耀,安室宜家。彦通制铭并篆。”镌阳文“方恪印”阴文“彦通”两方小印。砚一侧刻隶书“殢香馆藏砚”,一则刻篆书“璞砚”,另有楷书跋语曰:“乙丑孟冬得此砚于杭州梅花碑,既铭之复谥曰璞。彦通。”镌阳文“方恪印”一枚。
从铭文和印章可知,这方砚是陈方恪1925年冬天(乙丑孟冬),在杭州的梅花碑得到的。
案:梅花碑是杭州市的地名。东起城头巷,西至佑圣观路,南通道连长寿弄,北通道连水亭址。长210米,宽6米。梅花碑的所在地原为南宋德寿宫的一部分,明代在这里设有署理木税的南关工部分司。明末,潞王来杭居于南关分司内。当时该署庭院内有梅树和芙蓉石等景物,因而议事厅有“梅石双清”的题额;厅南有一石碑,上面刻有明代著名画家蓝瑛和孙挞画的梅花和石,称为“梅花碑”。后来乾隆帝来杭,见后十分喜爱,将碑移至北京圆明园内,另摹一石留在杭州。民间遂称此处地名为梅花碑。
陈方恪非常喜欢这方砚台,把它列为“殢香馆藏砚”,还亲自制铭,赞美它“厚重端介”,虽然做工简单,但“悃款无华”,至诚而不虚浮。特别是质地温润丰富,“含贞吐耀”,像文章一样华美。并为这方砚起了一个名字曰“璞”,形容它天真淳朴,像未经琢磨的玉石一样,有着天然的美质。
爱重之诚,于兹可见!
陈方恪(1891—1966),字彦通,斋号屯云阁、浩翠楼、鸾陂草堂、殢香馆等。江西义宁(今修水)人。清末民初著名诗人陈三立(散原老人)第四子,著名画家陈师曾、著名学者陈寅恪胞弟。光绪十七年(1891年)在祖父陈宝箴于武昌的湖北布政使衙署内出生。
幼承家学,习诗词文章,传承散原老人文脉。师从陈锐、周大烈、王伯沆等名士,又得梁鼎芬、沈曾植、樊增祥、朱古微、郑文焯、陈衍、郑孝胥等诗词名家点拨,年少时即形成清醇婉约、造句险峻、意境深远的诗词风格。其诗名在衡恪、隆恪、寅恪等诸兄弟之上,故散原老人常对人曰:“做诗,七娃子尚可。”汪辟疆编写的《光宣诗坛点将录》与钱仲联编写的《近百年词坛点将录》均将陈方恪入列其中。称其诗“绝世风神,多回肠荡气之作”(钱仲联语)。前辈朱祖谋则盛称其慢词“情深意厚。”
陈方恪交游广泛,一生传奇。1910年秋,他毕业于复旦公学,1912年冬,应狄葆贤之邀,陈方恪到上海任《时报》编辑。后又经梁启超介绍,进入上海中华书局,任杂志部主任。还在商务印书馆、《民立报》及《时事新报》做过编辑。1920年秋,南下江西南昌淘金。在此后几年之中,得到赣省多任督军眷顾,先后担任江西图书馆馆长、景德镇税务局局长、田亩丈量局局长、釐金局局长以及地方关口税务局等肥差,职务调动频繁,日进斗金,宦囊充溢。1924年春,江西境内局势不稳,归南京。之后,又应唐文治聘请,重回沪上,任教于无锡国学专修馆分校,教授古典诗词课程。同时又在暨南大学、持志大学、私立正风学院等校兼课。
解放后,陈方恪已失业,困守在南京城南饮马巷的两间旧房里。1950年,陈毅在一次专门招待南京文化名流的宴会上,闻知漏请了散原老人之子陈方恪,就立即派人登门请他赴宴。不久,在南京市政府的安排下,陈方恪一家迁往四卫头54号居住,生活才算是安定了下来。1959年,陈方恪家又迁到了牯岭路26号的小洋楼里,陈本人也被安排在《江海学刊》杂志社任编辑,继续研究诗词、治版本目录学并提携后学,贡献颇大。1966年1月3日,陈方恪逝世于南京,享年75岁。后人辑有《陈方恪诗词集》。
陈方恪翩翩贵公子,文采过人,生活风流,在与名士交游过程中,沾染上阿芙蓉癖,一生为之所累。又曾随报界同仁拜过洪帮老头子,加入帮会,且在洪门中有较高辈分。
郑逸梅写有一篇《陈彦通与花雪南》的文章,可见陈氏的文采风流:
散原往矣,其子也具美才。长衡恪,字师曾,擅艺事,物故有年。次方恪,字彦通,今尚健在。彦通诗,得石遗老人称誉,许为名贵一流。其人名士气殊重,风流自赏,好声色,作冶游,尝有感于京师南妓,撰《梁谿曲》三首,最为予所爱诵。如云:“曲罢真能服善才,十年海上几深杯。不知一曲梁谿水,多少桃花照影来。”“休言灭国仗须眉,女祸强于十万师。早把东南金粉气,移来北地夺胭脂。”“镫痕红似小红楼,似水帘栊似水秋。岂但柔情柔似水,吴音还似水般柔。”末一首尤足寻味无穷。闻彦通于民初在海上眷校书花雪南。花雪南开香巢于跑马厅之东,初本幺凤也。叶遐庵物色得之,以语人,遂有幺二大王之号,于是连裀接席,无虚日。彦通亦座上客,觉花雪南婉娈多姿,其媚在骨,为之欲仙欲死。时陈英士遭袁项城忌,为醇酒妇人之信陵君,亦一见倾心。然花雪南却喜侣文士,与彦通订啮臂盟。顾彦通窘于资,适其乡人以巨款托散原为之生息,散原固不事家人生产者,以款交彦通存之钱庄。彦通正如枯鱼之得水,遂暂移之以应急需。既而花撤其艳帜,随彦通北上,家津沽间。日久而彦通于灯红酒绿间别恋一妓,大事报效,且以花之金钗钿合付诸质库。花大不怿,乃绝彦通而南,重堕风尘。后彦通深悔之,奈已无可换回矣。
陈方恪后来曾对自己年轻时荒诞之举有所反思,颇感悔意:“予频年以来,飘萍南北,青眼未逢,黄尘何极!独优伶倡伎之中不少激楚流连之子,渐成倾盖之交,感缔蕴袍之约,纬繣至今,负人者多矣。”
陈方恪虽然不是什么专门的鉴赏家,但他出身簪缨之家,书香门第,见多识广,被作家章品镇称为“金陵最后一个贵族”,眼界自在高处,这方砚台由他鉴赏,并亲自撰铭命名,又收藏于他人生最快意的民国初年,想必会有很多故事附丽也未可知。如今,物是人非,名士的风流早已云烟缥缈,只剩下这方砚台仍完好无损地供于来燕堂的案头,透过凝脂似玉的包浆,我仿佛能依稀看见那旧时的明月,前辈的风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