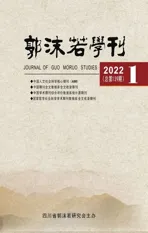论黄现璠对奴隶社会肯定论的批判与先秦社会形态理论重构*
2022-10-28周书灿
周书灿
(苏州大学 社会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一、《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兼论世界古代奴及其社会形态》一书的著述背景、中心观点、框架结构、论点体系
《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兼论世界古代奴及其社会形态》(以下引用是书文字随文标出页码,不再一一详细作注)为黄现璠先生遗作。该书的中心论点即“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1981 年12月,黄氏在该书《自序》中说:
余早就认为,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汉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少数民族历史也没有奴隶社会,这在拙著《广西壮族简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57 年6 月)及之后相继发表的拙文《侬智高起兵反宋是正义的战争》(《广西日报》1962 年4 月2 日)和《土司制度在桂西》[《壮瑶族史科学讨论会论文集(壮)》,第一集,1962 年7 月]中皆有论述。(《自序》P1)
在该书《绪论》中,黄氏又说:
余于新中国成立之前长期坚持中国古史“存在奴隶社会发展阶段说”,只是因为思考尚未成熟,研究尚未透彻,一直无意草率撰文公表,参与社会史大论战。1949 年12 月,余任广西大学中文系主任,兼讲《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一段时间,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入研究,余开始对郭沫若先生一贯主张的中国历史存在“奴隶社会发展阶段说”产生怀疑,自己原来的认识和观点逐步动摇。(《绪论》P2)
综上可知,1949 年前后,黄氏对中国先秦社会形态,尤其是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奴隶社会问题,历经长期深入思考,有一个从有到无的180 度大转弯的变化过程。黄氏强调,促成其在中国历史上有无奴隶社会这一问题的认识发生重大转变的动因在于“精研马列”(《绪论》P2),但从甘文杰执笔撰写的《黄现璠传略》可知,黄氏一生,“工于史学、民族学、民俗学、语言学、壮学,博通中英日壮侗瑶语”(《黄现璠传略》,P7)及前揭《自序》中“皆有论述”的篇章可知,促成黄氏对中国历史上有无奴隶社会这一重大问题的认识发生深刻变化,可能还是缘于其对民族史尤其壮学的深入研究,而受到若干启发。
兹列举以下数证,略加申论。早在1957 年,黄氏在《广西僮族简史》一书中即较早通过对壮族古代社会组织的考察和研究后指出:
此后,在《侬智高起兵反宋是正义的战争》一文,黄氏对学术界有些学者认为“隋唐以来,桂西壮族地区是奴隶社会”的观点进行反驳:
黄现璠史学研究涉及的领域颇为广泛,可谓纵贯古今,毕其一生,对当代学术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对壮学的开拓性研究和积极倡导“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说。自20 世纪50 年代中期开始,黄氏对中国历史分期与社会形态诸问题曾进行过长期深入的思考,黄氏言及,《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之探讨》一文连刊于《广西师范学院学报》1979 年第2、3 期和《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兼论世界古代奴及其社会形态》完稿之前,黄氏已陆续完成“起草于1955 年10 月3 日的一稿《我国古史分期应该重新估定》、修改于1974 年5 月8日的二稿《我国历史分期必须重新估定》、修改于1976 年3 月2 日的三稿《我国古代历史没有经历过奴隶社会》、修改于1977 年12 月6 日的四稿《中国古代史没有奴隶社会初探》和修改于1978年11 月30 日的五稿《我国古史分期应该重新估定——古代没有奴隶社会》”(《绪论》P2)。综上可知,黄氏“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说,总体上是在20 世纪50 年代以后中国古史分期大讨论的背景下,通过长期深入学习马列经典著作,并从对桂西壮族历史发展的道路和社会形态的探讨中获得启发,逐步建立起来的。
《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兼论世界古代奴及其社会形态》共分为四编:
第一编《汉文“奴”》,分设六章,分别从语言学角度对汉文“奴”、“隶”、“奴隶”、“众”、“民”等的语义进行考察。
第二编《外文“奴”》,分设四章,分别考察了苏美尔、古巴比伦、古印度、古希腊文献中“奴”的等级身份。
第三编《奴役制》,分设两章,重点讨论奴隶的定义、来源及家庭奴隶制等相关问题。
第四编《先秦社会形态》,分设四章,重构新的先秦社会形态理论,对先秦社会发展阶段重新进行划分。
全书围绕着“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这一中心论点,层层展开,在对“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这一中心论点进行论证的同时,黄氏亦重新构建起独到的先秦社会形态理论,并由此建立起互为关联、勾连贯通的论点体系:
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中国古代史的发展衍变轨迹应该是“尧舜时代的族国→夏禹时代的氏国→殷商时代的城国→周代的王国→秦代的帝国”这样一个演进过程,与此相应的社会形态为“原始社会→上贡社会→领主封建制社会(雏形)→领主封建社会(典型)→地主封建社会”(P583)。
二、黄氏对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奴隶社会肯定论的反驳与批判
自20 世纪30 年代起,长期坚持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论指导下研究古史分期与先秦社会形态的郭沫若,在漫长的学术生涯中,虽然有关中国古史分期的论点不断发生变化,但其始终坚持奴隶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并肯定中国古代经历过类似古希腊、罗马的奴隶社会的观点。为积极申论“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这一中心论点,黄现璠从文字语义、逻辑推理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理论公式化、教条化、生搬硬套等方面,对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有关中国奴隶社会肯定论进行了激烈的反驳和严厉的批判。兹仍择其要者,举证如下:
当战俘或俘虏被俘后被反缚其双手直接用为人牲,他们未经过“被奴役”的过程,何来“奴”之“身份或称谓”?即便这些被反缚其双手的俘虏未被立即当作“人殉人祭”或“人牲”而关押时继续被反缚其双手,同样非奴也。因为沦为奴者(奴婢或奴隶),是要被奴役的,所谓“受奴役”,意味着就没有自由只被使唤的人供主人随便使唤和处置,而供人随便使唤意味着就要干苦力,干苦力者不可能被反缚其双手(P12)。
在郭先生认识的奴隶社会中,没有自由人,没有农民,一切民众皆是奴隶。按照这种“郭式想象造史法”及其思维逻辑推论,我国数千年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广袤农耕地上世世代代从事耕种的农夫或农民,全都可以被视为“奴隶”,又何止于先秦三代焉。(P60)
黄氏以下对郭氏的批判,言辞颇为激烈。许多带有讽刺挖苦口吻的废话,大大超出了正常学术批评的范畴:
郭先生的政治意识太强,对奴隶先入为主之见根深蒂固。为了满足自己构建先秦奴隶社会的主观愿望,他不惜从“太阳下耕作的农民”中挖掘“奴隶的痕迹”,先将在“太阳下耕作的农民”形容为“农民在日下从事苦役”。苦役往往与奴隶相提并论,如此一来,“奴隶的痕迹”呼之欲出,继而补充点郭式文学笔墨和其他牵强附会的史据,再盖上一顶自以为正统的“历史唯物主义”大帽,农民便等同于奴隶了。这种三段式逻辑在以郭沫若先生为代表的主张中国存在奴隶社会的学者中普遍可见。事实上,郭先生已经正确地认识到“殷末周初称从事耕种的农夫为‘众’或‘众人’”,但他为了满足“五种社会形态说”,非要从农夫中去寻找“奴隶的痕迹”,无异于无中生有削足适履多此一举(P64—65)。
此外,黄氏还批评“郭氏杜撰的所谓众人或庶人一类耕种奴隶的来源为夷人俘虏,纯属虚构。至于所谓‘夷人奴隶兵’的‘前途倒戈’,更是荒谬绝伦”(P417)。
郭先生对金文“民”字之解,则具有郭氏三段式逻辑的特征,即所谓“民之为言萌也,萌之为言盲也”,民盲每通训,则盲其一目为言奴隶也(前提),金文“民”字“均作一左目形而有刃物以刺之”而盲其左目(前提),故金文“民”字为奴隶之总称(结论)。问题在于:郭氏三段式逻辑推理总是前提存在问题,结论自然难以成立或存在错误(P67)。
黄氏指斥郭氏“疑民人之制实始于周人”是“误识”(P69),批评郭氏“对词语、术语和概念的区别,向来是粗枝大叶或混为一谈,可谓思虑过浅”(P69)。黄氏批评郭氏议论荒唐:
郭沫若先生向来是对古文词语、术语和概念不加具体区别的,自然对词义的演变不屑一顾,由此便会错误地以汉代文献之《贾子·大政下篇》说“民之为言萌也,萌之为言盲也”来解释周初之金文“民”字义,从而得出“今观民之古文,民、盲殆是一事然也。然其字均作左目,而以之为奴隶之总称”这样十分荒唐的推论(P70)。
黄氏不厌其烦地批评郭氏:
实不知郭先生依据为何又以何据从金文“民”字形义中想象而看出了奴征?假如郭先生解金文民之说成立,商王盘庚岂不是在“恭承瞎奴之命”,周康王治下的万民岂不都成了万名瞎奴,全国周民一片瞎奴,这与史料记载的事实相距甚远。以史为据,郭先生解“民”为“盲眼奴隶”之说,从史料记载上难觅蛛丝马迹,实可谓无中生有、荒诞不经,可以休矣(P73)。
与此同时,黄氏批评郭氏将奴隶概念模糊化倾向:
在郭沫若先生看来,西周的农业生产者皆为奴隶。他认为古文献上记载的连同土地封赐的“臣”、“鬲”或“人鬲”皆是奴隶,而庶人则是下等的奴隶;至于《诗》、《书》中的农人、农夫、和周初分封的“殷民六族”、“殷民七族”、“怀姓九宗”、“殷顽民”等,在郭沫若先生看来都是为周族统治者生产的奴隶和种族奴隶。这类将“战俘奴隶”与“受剥削的当地居民生产者”视为一体;将“奴隶”、“农奴”、“耕奴”、“农民”等概念混为一谈,实为概念不分,混淆史实(P199)。
黄氏还批评郭氏在先秦奴隶社会产生这一问题上的单纯化和教条化倾向和“郭沫若式”反复无常的主观论证(P225),并一一举证如下:1.郭沫若先生将奴隶制等同于奴隶社会,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此为一误(P220)。2.郭沫若先生将被奴役者一律视为奴隶,并认为由此造成社会发生质变,从而由原始公社制转变为奴隶制,此为二误(P220)。3.(郭沫若先生)是按照斯大林同志“规定”的条条框框认识奴隶制度的,这就难免有教条主义倾向,实为三误(P221)。4.(郭沫若)所谓中国的“五种社会生产方式”和“五种社会形态”说,是对马克思学说的曲解,当为四误(P223)。5.以郭沫若先生为代表的主张中国存在奴隶社会的一大批学者,大多数都以阶级斗争理论为纲,将中国乃至世界古代社会存在的所谓奴隶社会简单地划分为“奴隶主与奴隶”两大对抗阶级,实为五误(P224)。6.郭沫若先生将夏、殷、周三代的生产力方式断定为奴隶制度,只是在用自己主观设定的“五种社会形态”套用于历史,当为六误(P225)。
此外,黄氏还批评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主张奴隶社会存在论的学者混淆恩格斯所区分的“古典古代的劳动奴隶制”和“东方的家庭奴隶制”,“将科学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生搬硬套于中国古代社会”(P230)。
综上可知,黄氏对郭氏“众”、“众人”奴隶身份说的批判,的确暴露出郭氏奴隶社会肯定论中若干严重的缺陷和不足,这对于推动学术界对相关问题作更进一步周密的思考和研究,显然是有一定的启发意义的。
不惟如此,黄氏对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奴隶社会肯定论的反驳与批判过程中,在证据和方法运用方面,也存在一系列突出的问题。如黄氏大量使用默证,兹以其第一编《汉文“奴”》为例,黄氏结合语言学材料,屡屡论及,“奴”字的本义为罪人,殷代是否有罪人为奴者,未见于甲骨卜辞文例(P13);甲骨卜辞中可能无“奴”字,……甚至怀疑殷人是否有“奴”或“奴婢”的意识或观念(P14—15);“奴”在《说文》中所释的本义是指古之罪人,而非奴隶(P15);隶人、徒隶、隶仆、流隶、贱隶、隶役、隶臣妾等称谓大多始于秦代之后(P36);中国先秦社会没有“奴婢”“奴仆”“奴隶”等连称(P47)等。事实上,无论以上论述能否成立,都很难为其“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中心论点提供证据支持。从论证方法上,这显系极不健全科学的默证法。黄氏的推论,很容易被驳倒,同样,我们可以反问,甲骨文中没有“民”,是否也意味着商代没有“民”的存在?甲骨卜辞中没有记载的人物和事件多得去了,我们能说只要未见卜辞记载,就意味这些人物在商代就不存在?这些事件在商代就没发生?
在对郭沫若奴隶社会肯定论的激烈反驳与严厉批判和先秦社会形态理论重构过程中,黄氏对改革开放前中国学术界在马克思主义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主导下的古史分期与社会形态研究成果,几乎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戴帽子、打棍子、上纲上线、以偏补偏,以左纠左的论述,贯穿于全书。如黄氏批评郭氏:
他将古文字学识用于研究古代史时,习惯于教条主义,并配以丰富的文学想象力,对古代史来一个张冠李戴的重塑。由此自然难免漏洞百出,许多观点或结论呈现出浅思浅虑强词夺理的特点,完全经不起推敲。……郭氏于史料上找不到直接有力的证据用以自圆其说时,便习惯于拿出得心应手的“奴隶转换套用概论法”,抛弃严格科学的概念和定义,抛弃历史科学法则,甚至置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法于不顾,从不对奴隶作具体论证,似乎认为仅凭自己的学术地位和声望只要概说几句:殷周时代的“民、庶、众、鬲、臣、黎、工、农”都是“奴隶”,然后登高一呼,响应者便会蜂拥而至。果真不出所料,中国文人的“身重言重”传统陋习以及以往的“阶级斗争”需要伴随着“郭沫若效应”,开始急速恶性膨胀,以至于三十多年来众多参与者制造的奴隶“层累说”呼之欲出,并渗透到中国当代学术界的各个角落。(P507)
此外,黄氏论著中,诸如“揭开以郭沫若先生为代表的主张中国存在奴隶社会的学者们一些杜撰和虚构史事的面纱”(P415)、“郭沫若先生的‘殷周奴隶社会’伪说”(P508)、“以郭氏、范氏为代表的‘奴隶层累宣教说’的荒诞不经”(P386)、“我国主张奴隶社会存在论的学者们习以为常又津津乐道的谰言”(P500)、“揭示出当代教条主义学奴虚构古史的面目”(P427)及“郭氏空想论证法”、“范氏幻想罗列法”(P384)、郭氏“文学虚构臆断法”(P417)、“郭沫若史学的奴仆”(P519)、“胡言乱语的曲解”(P504)、“没有任何具体论证的信口开河”(P505)、“欺世盗名”(P320)、“添油加醋,大放厥词”(P418)等情绪宣泄类的抱怨和反右、文革时期目空一切、唯我独尊、盛气凌人乃至人身攻击的表述,比比皆是。这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对郭沫若奴隶社会肯定论反驳与批判的学术品质,也大大降低了论著的学术质量和价值。限于文章篇幅,本文对以上问题,仅仅点到为止,不作全面展开和进一步的深入论述。
三、对黄氏重构先秦社会形态理论的几点思考
综上可知,黄氏论著的中心论点即“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而欲论定“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说成立,黄氏所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即要彻底否定马克思主义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主导下的各种古史分期学说。从《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兼论世界古代奴及其社会形态》一书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由于该问题固有的复杂性,黄氏四面出击,无的放矢,不惟批判郭沫若,可以说见奴即批。综观黄氏论著,则不难发现,黄氏把中国奴隶社会肯定论的学者,如范文澜、吕振羽、侯外庐、周谷城、日知、尚钺、金景芳、孙作云、王玉哲、于省吾、束世澂、赵光贤、童书业、岑仲勉、王承祒等几乎全部批判了一遍。然而在对中国奴隶社会肯定论的批判过程中,黄氏很难抓住问题的关键,论证杂乱无序,不仅达不到各个击破的目的,反而使得其对先秦社会形态理论的重构陷入破立两难的困境。兹仅就黄氏所重构之先秦社会形态理论,作一番深入思考,略陈以下管见。
1.“族国”、“氏国”等概念术语的使用是否妥当?
2.“上贡社会”是否可以构成先秦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阶段?
较之于其他持“中国历史无奴隶社会”说的学者,黄氏对先秦社会形态的理论建构最独特之处,即认为原始社会和封建社会之间的夏代,是一个“上贡社会”。黄氏论及:
虽然夏代部落公社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具有二重性,但支配生产资料的阶级是贵族统治阶级,他们不仅决定着直接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而且决定着分配关系、交换关系和消费关系。这种生产关系概而言之就是上贡关系,具体的表现形式为部落公社黎民与部落公社贵族的从下贡上的经济关系。这种上贡的生产关系在生产发展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具体表现形式。上贡制的产生以私有制和父权制的形成为基础,从奉公制演变而来,它几乎贯穿着夏代社会生产领域的各个层面,因而余认为,夏代社会是一个上贡社会,即上贡制社会。(P319)
综观黄氏论著,不难发现,黄氏判定夏代为“上贡社会”的主要文献依据即《尚书·禹贡》中“任土作贡”和《周礼·天官·冢宰》中“九贡”的记载,与此同时,黄氏又一再强调,“殊不知《尚书·禹贡》所记贡赋之法而对夏禹时代的附会描述”(P310);“《周礼》中所记九贡、九赋并非完全是周代之事,甚至许多学者认为《周礼》是伪书,因而《周礼》所言不可全信”(P312)。既然《禹贡》、《周礼》所记“任土作贡”、“九贡”和夏代乃至西周时期均无关系,不知黄氏为何在“夏代之贡”一节不厌其烦地对《禹贡》、《周礼》“任土作贡”、“九贡”大做文章!此外,颇为费解的,黄氏一方面说,上贡制的生产关系“几乎贯穿着夏代社会生产领域的各个层面”,同时又说:“夏禹时代的贡尚处于初级形态,为‘贡无定期,物无定品,品无定数’之贡,这与夏代正处于国家初级形态的部落联盟制国家相适应。到商代,贡仍处于初级形态,只是到了周代,贡似乎始有了一定的定期,即岁贡。至于贡之定品、定数,还要到春秋战国时代。”(P312)这里暂且不说,贯穿于黄氏全书中的“周代”是否包括春秋战国时期,既然夏代乃至商代,“贡”均处于初级阶段,换言之,夏商时期,“贡”尚未成为具有普遍和典型意义的制度,那么,为何夏代被单独称为“上贡社会”?根据黄氏的前后论述,则似乎西周、春秋战国时,更应称之为“上贡社会”!既然如此,“上贡社会”是否可以构成先秦时期社会形态发展的一个阶段,自然就颇为值得怀疑!
3.“封建”一词的滥用及领主制、地主制“封建社会”阶段划分的逻辑疑难。
黄氏力主“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但其并不否认中国历史有封建社会。在黄氏重塑的古史体系中,虽然有领主封建社会和地主封建社会的区分,但却屡屡将周代的分封制和西语中的“封建”互为混淆。诸如黄氏屡屡论及:“殷之所谓封,实际上不过是所封子姓或异姓同族诸侯名义归服于殷而已,并非殷用武力灭之而行封建也。故余将其称为领主封建社会雏形,有何不宜乎”(P379)。“商代虽有封建之制,然而土地既非商城国所有,又非商王一人所有,而是商王和方国、各诸侯国之王分别所有,商王所谓分封,仅为分封称号以及承认各诸侯国之王自有的土地而已,此谓‘有封无建’也。而对各诸侯各国君王而言,他们拥有土地以及对土地上生活的平民百姓拥有征兵、征役等绝对统治权,此为初期领主封建制的特征之一,亦为与后世的地主只拥有土地所有权而无征兵、征役等权力的地主封建制的本质区别所在”(P451)。与此同时,黄氏又批评主张西周封建论的童书业、岑仲勉“过于强调古之‘封建’含义而忽视了其生产关系”(P451)。黄氏所强调的“封建”究竟是什么,似乎其自己也说不明白。
在黄氏论著中,黄氏一方面强调说,“商代并存的氏族公社、部落公社和地域公社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具有二重性,但支配生产资料的阶级是王公贵族或封建领主统治阶级,他们不仅决定着直接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而且决定着分配关系、交换关系和消费关系。这种生产关系概而言之就是领主式的土地关系”(P450-451),“在商代生产关系中占主导地位的便是封建领主制”(P451),既然领主制的生产关系在商代已经占“主导”地位,却不知黄氏为何又将商代社会称为“领主封建制社会(雏形)”?这种文字表述上的自相矛盾,让人屡屡感到困惑不解。还有,黄氏将周代社会视为封建领主制的典型时期,黄氏著作第四章第五节标题即为《周代无井田制》,按照人们通常理解的周代,自然应包括西周和春秋、战国长达八百余年的历史,而黄著《领主封建社会(典型)》一章,则写至西周末年宣王时期,突然收笔。春秋、战国的东周时期究竟应归入黄氏所划定的“领主封建社会(典型)”阶段还是“地主封建社会”阶段,只能令人猜谜式地进行推测了。
黄氏长期被视为改革开放以后“无奴说”的开创者和“无奴学派”的领袖,黄氏《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兼论世界古代奴及其社会形态》一书曾被部分学者称之为“无奴说”的集大成之作。黄氏对于中国先秦社会形态的理论重构,是有着筚路蓝缕的开拓之功的。然由于时代的局限,无论其对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中国奴隶社会肯定论的反驳与批判,还是对“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申论,以及对先秦社会形态理论的重构,都存在诸多严重的缺陷和突出的问题。本文无意全盘否定黄现璠先生的学术贡献,对黄氏学术研究中若干缺陷与问题的全面揭露,则在于唤起学术界,在新的学术背景下,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引领下,批判继承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积极探寻这一对于学术界早已兴趣锐减但却永远不会过时的重大理论问题探讨获得新的突破的崭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