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书写中的黑人民主之路
——试论格温朵琳·布鲁克斯的创作
2022-10-27刘立平
刘立平
(天津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
一、布鲁克斯的生平和创作
格温朵琳·布鲁克斯(Gwendolyn Brooks,1917-2000)是美国第一位获得普利策奖和第一位成为美国国会图书馆顾问的非裔女诗人。她于1917年6月17日出生于堪萨斯州的托皮卡,她的父亲虽然是一名普通的门卫,但是多才多艺,擅长唱歌和讲故事;母亲是小学教师,会弹钢琴,在发现布鲁克斯有写作才能后积极为她创造条件,带着她去见两位著名的黑人作家休斯(Langston Hughes)和约翰逊(James Weldon Johnson),在父母的影响和支持下,布鲁克斯从小就树立了成为作家的理想。布鲁克斯在创作诗歌方面有极高的天赋,沃克(Alice Walker)曾经在一次访谈中说:“如果有人生来就是诗人,那么这个人就是布鲁克斯。”(Baym et al.,1994:2518)在母亲的鼓励下,她7岁开始写诗,13岁时在《美国童年》杂志上发表了第一首诗歌《黄昏》(Eventide),此后她的诗歌陆续发表在《哈珀斯》《诗歌》《耶鲁评论》《星期六文学评论》和《黑人故事》等杂志上。
1936年布鲁克斯在威尔逊专科学校毕业后,先后做过清洁工和打字员,但她始终没有放弃诗歌的梦想。1940年在参加了南岸艺术中心的一个诗歌工作坊之后,布鲁克斯的创作技巧突飞猛进,创作的作品也日益得到人们的认可。约翰逊评价道:“从来没有一位像她这种水平的白人诗人会被如此低估,这样的作品无人问津是不可饶恕的,作为一位杰出的女性诗人,她应该得到尊重,她和那些已经成名的诗人——亚当斯(Leonie Adams)、毕肖普(Elizabeth Bishop)、莱维托芙(Denise Levertov)——同样重要,艺术水平也许更高。”(Melhem,2001:163)与其他黑人女性作家相比,布鲁克斯是幸运的,在1945年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布朗兹维尔的一条街》之后,她声名鹊起,不但在1968年接替桑德堡(Carl Sandburg)成为伊利诺伊州的桂冠诗人(1968-2000),而且获得了美国诗歌协会的奖章以及美国50多个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
她的主要作品包括诗集《布朗兹维尔的一条街》(A Street in Bronzeville, 1945)、《安妮·艾伦》(Annie Allen,1949)、《吃豆子的人》(The Bean Eaters,1960)、《在麦加》(In the Mecca,1968)和《暴动》(Riot,1969)。除此之外,她还出版过一本儿童书籍《布朗兹维尔的男孩和女孩》(Bronzeville: Boys and Girls,1956)以及小说《莫德·玛莎》(Maud Martha,1953)。
布鲁克斯的创作风格发生过几次重大的变化,她曾经把自己的创作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作‘表达自我’,因为我写周遭的一切,我想要表达自己。第二个阶段是‘种族融合’,我想让黑人和白人或者说所有人能够共存,他们大多数人似乎并非如此。第三个阶段的创作宗旨是60年代末黑人诗人所提出的‘黑人诗歌是由黑人创作的,关于黑人的,同时也是写给黑人的’。”(Saber,2010:15)布鲁克斯对自己创作风格的归纳基本涵盖了其创作的不同阶段。
第一阶段是20世纪40年代,以她出版的处女作《布朗兹维尔的一条街》为标志,作品主要描写了芝加哥黑人聚居区贫民窟的体验。这一时期她主要以模仿为主,还没有形成自己独有的风格。贝克(Houston Baker,1974:43)认为:“布鲁克斯的诗歌有张力,复杂而且有节奏感,包含了玄学派邓恩的复杂和阿波利奈尔、庞德和艾略特的词语魔法……有着‘白人’的风格和‘黑人’的内容——在一个黑人的身体中包含着两种敌对的理想。”布鲁克斯初期创作时学习的对象是邓恩、狄金森、艾略特、庞德和南方逃逸派诗人,她学习白人的写作模式和语言,而表达的内容却是黑人在贫民窟的痛苦生活。
第二阶段是20世纪40年代末到60年代初,这一时期她出版了《安妮·艾伦》《莫德·玛莎》《吃豆子的人》。布鲁克斯在这一阶段的作品中呈现了种族融合的理想,同时她的思想开始倾向左翼,作品中出现了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形象。《安妮·艾伦》反映了她在种族融合方面的探索。这首长诗主要写一位黑人女性从童年到成年的成长历程,这是一首从天真之歌走向经验之歌的长诗。她认为,黑人应该在保有民族特性的同时携手实现种族融合。布鲁克斯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她是美国有色人种协会的成员,曾在芝加哥和作家泰勒(Margaret Taylor)一起参加了反对私刑的街头抗议。她的诗集《吃豆子的人》和小说《莫德·玛莎》中包含了大量以工人阶级为描写对象的抗争诗歌。
第三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80年代,这一阶段的作品表现了她对于黑人艺术运动明确的支持态度,她的作品开始谈论革命暴力,并在作品中努力寻找黑人解放的出路。语言上不再使用标准的英语,而是运用更加贴近黑人的日常语言,更多采用自由体,同时融入了黑人的音乐形式。她开始为黑人写作,并脱离了纽约的出版商,让作品由非裔美国人创办的出版社出版。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有《在麦加》《暴动》《家庭照片》(Family Pictures,1970)、《黑人初级读本》(Primer for Blacks,1981)、《戈特沙尔特和塔兰泰拉舞曲》(The Gottschalk Grand Tarantelle,1988)等。
本文将从布鲁克斯三个阶段的代表作品《布朗兹维尔的一条街》《莫德·玛莎》《吃豆子的人》和《在麦加》入手,呈现黑人群体的日常生活图景和种族生存困境,探讨布鲁克斯为改变困境寻求黑人解放所作的探索和努力。
二、《布朗兹维尔的一条街》:黑人群体困境
1945年,布鲁克斯出版了她的第一本诗集《布朗兹维尔的一条街》。她想要在这部作品中展现生活在布朗兹维尔的小人物的不同性格、他们生活中的悲欢离合以及在贫穷艰难的生活和种族歧视的环境中为保持尊严所做出的努力。居住在这里的人们有一种共同的特征,即无法得到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满足,这些人中有缺乏沟通的老年夫妇、堕胎的妇女、得不到尊重的布鲁斯歌女、不被承认的黑人英雄和被男人抛弃的女人等。从诗歌形式来看,布鲁克斯并没有采用先锋的诗歌实验形式,而是使用了传统的歌谣、蓝调、三节诗、四行诗、十四行诗等形式。
布朗兹维尔是当地记者给芝加哥黑人贫民窟起的名字。这个地方位于芝加哥南部,南北从29街到69街,东西从科蒂奇·格罗夫街(Cottage Grove)到州府街(State Street),如今仍然是非裔美国人的生活聚居区和文化中心。作为黑人聚居区,布朗兹维尔的生活环境极其糟糕,压抑的环境让人们无所适从,人们在生与死的边缘挣扎,梦想在窘迫的现实下失去了光辉。在《合租房》(kitchenette building)①一诗中布鲁克斯(Brooks,1987:20)写道:
我们是干枯的时间和偶然计划的产物,
进入灰暗、灰暗,“梦想”发出让人眩晕的声音,不如
“租金”“养妻子”“满足男人”的声音强烈
然而透过洋葱的油烟,
它的白色和紫色,与油炸土豆搏斗,
昨日的垃圾在大厅中成熟,
梦想可能从其中摆动双翼,或者在这些房间中唱咏叹调
即使我们愿意让它进来
有时间温暖它,让它整齐美观,
期待一个信号,让它开始?
我们想知道。但是不行!一刻也不行!
因为现在第五个已经从浴室出来,
我们想到温水,想要进去。
布鲁克斯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描写人物,合租房糟糕的居住环境和艰难的生活在布鲁克斯的笔下生动地展现出来。这里的合租房是指租给从南方移居过来的非裔美国人的破旧的老房子,居住在里面的黑人们每天要为维持最基本的生活而忙碌,男人要满足一大家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女性除了要承担繁重的家务以外,还要取悦男人。然而,在这样的生活压力下,他们仍然没有忘记梦想。诗中出现的紫色和白色这种比较鲜明的颜色与灰色形成对比,生活是灰色的,而梦想仍然是亮色,但是在“洋葱冒出的油烟、炸土豆和腐烂的垃圾中如何实现梦想”。在诗歌的结尾,梦想已经大大缩水,她的期盼就是能够洗上热水澡,梦想的翅膀被残酷的现实无情斩断,最终无疾而终。
这首诗不仅让人想到了休斯的《延误的梦想》(Dream Deferred),诗中运用一系列比喻,将梦想比作风干的葡萄、化脓的伤口和腐烂的肉。梦想随着时间的推移干瘪、破碎,甚至成为一种负担。在诗歌的最后,作者写道:“它可能会爆炸”,言下之意是未实现的梦想甚至成为了一种危险的因素,可以摧毁一个人。如果说休斯的诗歌更具象征意味,布鲁克斯的诗歌意象则更加生活化,土豆、洋葱、油烟、垃圾让理想与琐碎的现实形成鲜明的对照,反差更加强烈。
在这本诗集里布鲁克斯讨论最多的就是女性的形象。《赛迪和莫德》比较了赛迪和莫德两姐妹的人生,虽然她们对自己的人生作出了不同的选择,但结局却都以悲剧收场。全诗共22行,每一行只有四五个词,仿佛象征着她们的人生如诗句一般随着叙述逐渐缩短,直到画上句号。赛迪未婚生子,独自抚养两个孩子,这给她的家庭带来了羞辱。
赛迪生了两个孩子
都随她娘家姓。
莫德、爸和妈
差点羞愧死。(Brooks,1987:32)
莫德虽上了大学,但循规蹈矩,生活缺乏活力,找不到生存的意义,最终孤独终老。赛迪与男人建立了关系,然而这种关系却并不长久,她只能独自抚养孩子;莫德则没有机会与男人建立任何关系。两个人的共同之处都是孤独、痛苦与不幸,她们都无法获得她们想要的爱情,或是拥有幸福的家庭。
贫困的生活甚至剥夺了黑人女性做母亲的权力。《母亲》一诗讲述了因为生活所迫而不得已数次堕胎的黑人女性的故事,全诗采取了戏剧独白的形式。诗中母亲的名字并没有出现,这样更具有普遍意义,这不是一位黑人母亲的命运,而是许多黑人母亲共同的命运。
若是我剥夺了你的好运气,
让你的人生无法到达应有之地,
若是我偷了你的生日,你的名字,
你孩子的眼泪和游戏
你矫揉造作或者愉快的爱情、你的烦乱、
婚姻、痛苦和你的死亡
如果我毒害了你最初的呼吸
相信我即使我这样做了,也是迫不得已。(ibid.:21)
母亲意识到她剥夺了孩子生存的权力,同时也没有机会与这个小生命共度亲子时光。只有想象孩子长大的样子才能填补一点心灵的空虚,而这种想象又让扼杀孩子生命的母亲愈加痛苦。她强调她不是有意要伤害这个孩子,而是要让他免于苦难的命运。诗句生动的描述中透露出深深的自责、撕心裂肺的痛和最深沉的爱。
你不会忘记堕胎。
你会记住你怀过却没有活下来的孩子,
那个小小的、湿漉漉的、有一点头发或者没有头发的果肉,
没有面世的工人或者歌唱家。
你无法忽视或者处罚他们,
为他们买糖果或是沉默。
……
相信我,我爱你们中的每一个。(Brooks,1987:21)
结束与自己身体紧密联系的小生命对于母亲来说是无法承受的,这种痛苦也是无法忘记的,而且这种痛苦不止一次,每一次都是无可奈何的选择,同时也反映了母亲无奈却深沉的爱。“她意识到她让那些没有出生的孩子免于面对严酷的现实,同时也承认她剥夺了他们可能在人生中获得的快乐。她不知这样做正确与否。”(Guy-Sheftall,2001:237)她认为自己是罪魁祸首,但是一句“迫不得已”却从侧面反映了这个社会的不公,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让这些孩子早早夭折,并且剥夺了黑人女性做母亲的权力。
黑人男性同样实现不了人生的价值与梦想。诗歌《赛坦-莱格斯·史密斯的周日》共159行,是诗集《布朗兹维尔的一条街》中最长的一首,描写了一位叫赛坦-莱格斯的黑人周日一天的生活。“布鲁克斯笔下的黑人男性通常没有稳定的工作和家庭,没有爱他的妻子和无忧无虑的孩子,他们以一种非传统的方式来藐视压迫。”(Saber,2010:48)这位黑人男性虽然生活在布朗兹维尔,然而他对自己的外表却非常在意,穿着时髦的佐特服②,并且想在周日的时候也能去看电影,与一位美女共进晚餐,获得身心的满足。这让他觉得自己并不是一个被社会抛弃的人,一样可以获得人的尊严。
诗歌描写了他周围的环境,“人们是如此贫困,需要帮助。/人们需要多少他们不知道的东西。”在这种环境下,赛坦-莱格斯却渴望拥有一个种满了康乃馨、天竺葵、紫鸢、玫瑰、木兰的花园,然而这是无法实现的,他能拥有的只有田野中的蒲公英。他周围环绕的是卷心菜和垃圾桶以及“领子上羽毛做的假花”。
……可能他最幸福的选择
(你想)无非是
有着连续传统及
美好味道的上等人的花园?也许是这样
不过你忘了,或者说你可曾了解,
他的遗产是卷心菜和发辫
熟悉的是小巷和垃圾桶,
深入到南方腹地(然而总是美丽的)
那里玫瑰绽放出红颜(据说是)
木兰的香气胜过了香奈儿
而他所拥有的只是插在领子上羽毛做的假花(Brooks,1987:43)
诗中详细地描述了他的壁橱,壁橱里不是白人所拥有的珠宝、银器和珍珠,而是花里胡哨的衣服和遮风挡雨的帽子。他在努力创造自己的世界,他热爱音乐,但不是格里格、柴可夫斯基和勃拉姆斯的音乐,而是黑人们最熟悉的布鲁斯音乐。布鲁斯音乐为他带来了希望,成为他现实生活的精神支柱。在诗歌的最后,与他共进晚餐的并不是一位贵妇,而是一位妓女,但这足以给他带来满足和安慰。
她的身体是一碗蜂蜜
等待的蜂蜜丰厚又热烈。
她的身体就像夏日的土地
接纳、柔软、绝对(ibid.:47)
赛坦-莱格斯无意识地创造了一种自我防御系统,他选择对周围熟悉的环境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因为他太熟悉这一切了,他选择有意识地逃避这一切,努力突破这里的空间和氛围,生活在自我的世界中,只追随自己的想法,他似乎创造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这个人物特点鲜明,从他的壁橱、他看的电影、他对音乐的热爱到他每个周末与妓女度过良宵,可以看出他是非典型的穷苦黑人中的一员,他想冲破自己的社会阶层过一种自认为体面的生活。然而,在作者冷峻的笔下,他是一个在夹缝中生存的人,他的做法是掩耳盗铃,无法得到理想中美好的一切。
三、《莫德·玛莎》:知识改变认知
布鲁克斯1944年开始创作她的小说《莫德·玛莎》,这也是她发表的唯一一部小说。这部小说的出版并不顺利,她曾于1946年和1947年两次向《哈珀斯》杂志投稿,但是编辑拒绝刊发这部作品。但布鲁克斯并没有放弃,反复修改,直到1953年小说得以发表。这部作品共34章,讲述的是1924-1945年在芝加哥发生的关于一位工人阶级黑人女性莫德的故事。小说描写了她从六七岁到二十七八岁的生活以及她周围工人阶级社群的生活。黑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形象在美国小说中鲜有出现,因此这部小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这部小说所展示的不是惊天动地的事件,而是一位黑人女性如何在诸多小事中与社会抗争,并能够生存下来的故事。主人公莫德是普通人,如同住在布朗兹维尔街的其他黑人一样,也在贫困线下挣扎。她是一名档案管理员,每周赚10美元;她的妹妹海伦是打字员,每周赚15美元,她们的收入比当时的最低工资还要少。结婚以后莫德和丈夫搬到了一个三层楼的公寓,“里面有两个小房间,一张铺着油布的桌子,几把折叠椅,一个褐色的木制冰箱;洗手间要与四个家庭共用,厨房里的三个炉盘,只有一个炉盘可以用,蟑螂是家里的常客,而房东不会做任何的改进,夫妻两个只能忍受这种现状”(Washington,2014:184)。在这样恶劣的居住环境下,莫德却在努力摆脱种种束缚,追求精神自由。她热爱阅读,喜欢音乐,有着良好的艺术修养。她在艰难的生活中仍然能保持自己的尊严,不仅没有随波逐流,而且有着自己的审美,并想方设法改变周遭的一切,这与她是一位知识女性不无关系。
布鲁克斯笔下呈现的莫德形象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热爱文学,阅读不仅给予她精神的滋养,同时也让她能够追求自由;二是独立思考的能力和批判意识,她认为,仅从外表来判断一个人的价值是荒谬的;三是她在种族歧视的环境里试图改变人们对于黑人的刻板形象;四是虽然居住的环境很恶劣,她却从未放弃对幸福生活的追求。
莫德与其他小说所描写的工人阶级人物不同,她喜欢文学,比如她提到一本非常重要的文学著作维农·帕林顿(Vernon Parrington)的三卷本《美国思想主流》,这本书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文学专业研究生的必读书目,囊括了1620-1900年的美国作家,这样广泛的阅读开阔了莫德的视野。不仅如此,阅读还充实了她的人生,慰藉着她的心灵。她在卧室的读物是《人性的枷锁》,这本书中主人公菲利普的遭遇让莫德决心冲破种族、性别和肤色的束缚,获得身心的自由。虽然她的居住环境是灰暗的:“与这座石头公寓相联系的每个人和每件事物都陷入灰色所代表的一切:污秽、隔绝、延迟的梦想、死亡。不论来到这儿的人之前是多么干净,多么明亮”(Richardson,2002:141),阅读却让莫德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她努力提高自己的学识修养,成为一个关爱别人的人,一个正直的人。
莫德认为,不应该以肤色来判断一个人的内在价值,这体现在莫德和她丈夫保罗之间的关系。保罗与莫德之间的关系很微妙,保罗很爱莫德,但是却无法完全接受莫德,因为他接受了“白即是美”的观念。莫德认为,这样仅从外表来判断一个人是荒谬的:“他喜欢的是内在的我,真正的我。但是他一直在看我皮肤的颜色,那像一堵墙,他必须翻过这堵墙才能接触我,了解真正的我。他要跳得足够高才可以,他厌倦了这种跳跃。”(Brooks,1987:229-230)这其实也是黑人群体内部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很多如保罗这样肤色稍浅一些的黑人对于深色皮肤的黑人也存在歧视,而跨越这堵墙的关键在于拥有知识。莫德知道问题的症结所在,她呼吁黑人内部应该突破这种障碍,认识到人的内在价值与尊严。
她从不向种族、经济和性别歧视低头,而且努力改变人们对黑人的刻板印象,赢得应有的地位和尊重。有一次她在美容店做头发,听到一位白人销售员对黑人店主说:“我像一个黑鬼一样赚几个臭钱。”黑人店主对此默默忍受,甚至变得有些漠然。莫德则认为,对这种贬低黑人的态度不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必须要纠正这种错误的观点,改变这种现状。在她的丈夫失业以后,莫德去给一位白人太太做饭,当她被告知不能从大门出入,而要走后门的时候,她毅然决然地辞去了这份薪水还算丰厚的工作。在世界剧场,她和丈夫保罗是“那里唯一的有色人种”。在保罗因为向一位白人女士询问而感到胆怯的时候,她感到非常愤怒。在灯光暗下来的时候,她体会到了平等的感觉,但剧目结束后她想与白人交流看剧的感受时,却没有人愿意与她对话。在市中心的百货商店,当白人扮演的圣诞老人忽视了她的小女儿博莱特(Paulette)时,她的女儿问:“为什么圣诞老人不喜欢我”,莫德一时语塞,因为她不想让女儿的心灵受到伤害。尽管她不能改变这一切,但“她不要在特定的地点让特定的人进一步地剥夺自己的人性”(Lattin & Lattin,2001:141)。
莫德虽然生活在恶劣的环境中,却从未放弃对幸福生活的追求。这体现在她对于家的珍视和乐观的生活态度。“家对于莫德来说则是一个避难所,是她童年寻求安慰的地方。”(ibid.:137)成人以后她极力维护着自己的家园不受侵害。莫德最喜欢的是最寻常不过的蒲公英,“那么普通的植物也能开花让人觉得安慰,她觉得她在花中发现了自己”(ibid.:138)。她喜欢在买来的二手桌子上铺上白色的桌布,放上白色的杯子和碟子,给妈妈准备姜饼和一杯可可。她在痛苦的遭遇中不断成长,始终没有放弃希望:“小说中的主人公拥有双重的意识,这让她可以在丑中见到美,死亡中看到新生,以及在面对压倒性的负面力量时保持自尊和创造力,秉持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ibid.:137)即使在最艰苦的环境中,她依然乐观向上,认真地对待生活,并且努力寻求改变。
布鲁克斯是一个与工人阶级家庭和社群保持紧密联系的作家,她塑造的形象不是简单的黑人工人阶级女性,而是一位精通文学艺术的知识分子,突破了以往人们对于黑人女性的刻板印象。文学与艺术为莫德提供了审视生活的新视角,为她积极生活下去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源泉和力量。《莫德·玛莎》以其独特的创作方式、高度的美学价值和深刻的思想成为黑人文学的经典之一。
四、《吃豆子的人》:暴力催生觉醒
1958年12月,布鲁克斯将《吃豆子的人》③投到《哈珀斯》,这是一本薄薄的册子,包括35首诗。不同于《莫德·玛莎》,这部作品很快被编辑接受了。这部作品是她创作生涯中的一个转折,诗歌体现出较强的社会性和政治性,特别是涉及她与左翼的联系。比如,《杰克》一诗中的杰克极有可能指的是布鲁克斯的左翼朋友杰克·康罗伊,他是著名的左翼作家,与黑人作家联系紧密。他和黑人作家邦当(Arna Bontemps)共同创作了《他们寻找一座城》等几部作品,影响了包括布鲁克斯在内的很多黑人作家。在这部诗集中,她讨论了种族歧视、性别歧视、阶级差别、暴力、战争和民权等主题,创作背景还是同样的贫民窟。布鲁克斯尤为关注种族隔离所引起的暴力事件和黑人的反抗。
《一位布朗兹维尔的母亲在密西西比徘徊。与此同时,一位密西西比的母亲烤焦了培根》是这本诗集中最长的一首诗,这首诗是对一个真实事件的反思。芝加哥的14岁男孩提尔和她的母亲去密西西比探访他的叔叔,在一家杂货店购物的时候,收银员布莱恩特太太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认为提尔对她有不良企图,告诉了她的丈夫布莱恩特。布莱恩特和他的兄弟米莱姆劫持了提尔,并且将他杀害,肢解后腐烂的尸体在塔拉哈奇河中被人发现,而这两个杀人凶手不但未受到法律的惩罚,反而被无罪释放。
这首诗从白人女性布莱恩特太太的视角出发,描写了在她的丈夫杀害提尔之后她的反应。“布鲁克斯独辟蹊径,走进这位妇女的内心世界,假想她的良知觉醒,不仅运用她在文学叙事中的在场弥补她在历史叙事中的缺场,而且,也以诗性正义来弥补现实社会中公平和正义的缺失。”(黄怡,2016:119)她在厨房里为无罪释放的丈夫和孩子做早餐时想到了提尔的死和后来的庭审。她相信南方的种族主义神话,觉得私刑处死这位孩子是必要的,然而她也意识到所谓的坏人其实非常弱小,只是一个孩子,她无法说服自己接受提尔被杀害这个残酷的现实。
这种乐趣受到了干扰,几乎消失了
这个黑皮肤的坏人不过是个十四岁的孩子,
那双眼睛年轻而又清澈,
一张柔软的嘴
现在已变得僵硬。(Brooks,1960:20)
这位少年刚刚到达人生最美好的阶段,却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被杀害,“这个孩子一定很吃惊!/因为他们是成人。/成人应该是明智的。”然而,事实正好相反,成人做着最野蛮、最没有理性、最可怕的事情。她的眼前浮现出提尔被绑架杀害,尸体被抛入河中的景象,“她的培根烧焦了。/她迅速地把它藏进垃圾桶。”她无法说服自己这件事是合理的,内心难以平静。
这首诗运用了民谣的形式,布莱恩特太太想要通过王子救公主的故事来创造一个幻觉逃避现实:“她自己,乳白色的姑娘/歌谣中温柔的姑娘,/被黑皮肤的坏人追赶,/王子救了她/从此幸福永远。”布鲁克斯解构了美好的童话故事,主人公变成了黑人男孩和白人姑娘。在传统故事中,坏人总是高大强壮的,然而现实中的这个坏人不过是一个14岁的孩子,而杀害他的人则是强壮的成人。布鲁克斯刻意打破了黑人诗歌传统来强调白人母亲的困惑,而且呈现了一个混乱的世界,这个颠倒的世界不仅允许私刑处死一个14岁的孩子,而且犯罪者还能被无罪释放。提尔和凶手之间的对比恰好表现出了童话的美好期许和冷酷无情的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美梦很快转成了噩梦,伴随着对提尔使用的暴力,母亲的困惑也到达了顶点。“发生了这么多事,她不记得敌人做了什么/对她不利的事情,或者做了任何事情。”在毫无缘由的情况下,这个孩子就被处死了,她则成了这桩罪恶事情的共犯。这一切让她无法承受,她走到镜子前面,想要补一下妆,但是镜子中的美丽面容也无法掩盖丑陋的现实。
诗歌的后半部分出现了她的丈夫,他看到了北方报纸上对这一事件的谴责,他貌似对此不以为然,叫嚣着“什么也阻挡不了密西西比”,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和内心的优越感跃然纸上,然而他对孩子的暴力行为暗示了他内心的脆弱与不安,而且再一次对“弱小的罪犯”(他的孩子)施加了暴力,诗歌中的讽刺不言而喻。白人母亲也对这位“王子”彻底灰心,认为他不仅是杀人凶手,而且还在家庭中对孩子施加暴力,她甚至无法保护自己的孩子。白人母亲最后说:“对他的恨生出了美丽的花朵”,暗示了这位母亲的觉醒,她根深蒂固的南方种族歧视意识开始改变,并且这也预示着密西西比的土地上也将发生改变,白人内部也同样孕育着变革的力量,而这种力量不是来自男性,而是来自女性。
在另外一首诗《艾美特·提尔的民谣的最后的四行诗:谋杀之后,葬礼之后》中她的重点集中到了黑人母亲身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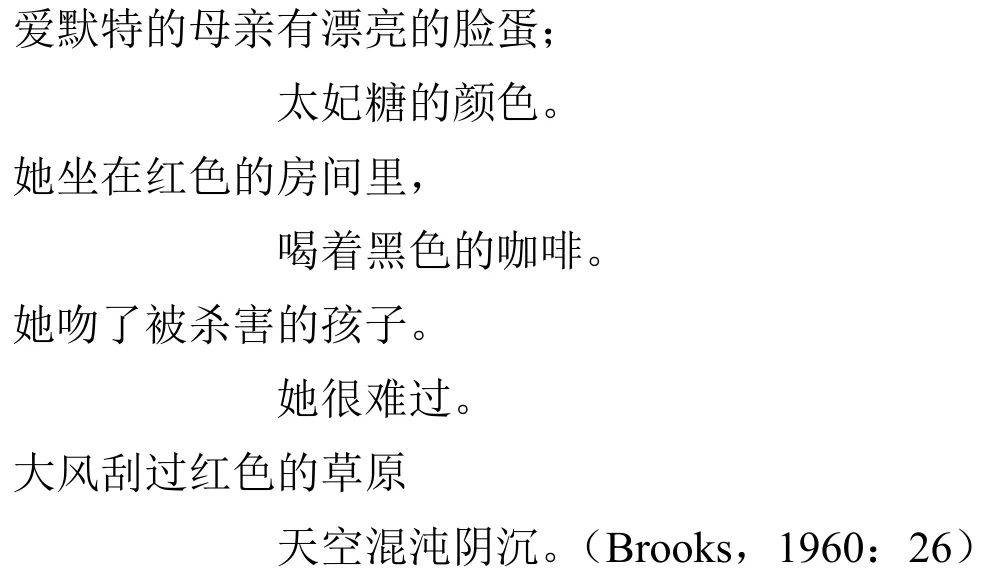
这首诗出现了红色与黑色的对比,黑色咖啡的苦涩暗指黑皮肤所遭遇的悲惨命运,让读者产生了更进一步的联想,阴沉的天空暗示了母亲绝望的心情以及对未来生活的迷茫。这首诗结束于对一片孤寂的红色草原的描写之中,红色既指提尔的被杀所喻示的种族暴力与性别暴力,也指“密西西比红色的土壤是用私刑处死的人的血所灌溉,才开出了木兰花”(Saber,2010:130),而这片土地孕育着反抗的种子,终有一天会改变这片荒原。
布鲁克斯不仅展现了白人对无辜的黑人所施行的罪行,而且还描写了黑人的暴力反抗。在《鲁道夫·里德的歌谣》一诗中,里德(Rudolph Reed)想要拥有一所体面的房子,可是白人邻居却对他充满敌意。这首诗共16节,主人公里德的名字意为芦苇,诗的第一节在形容里德一家时又用了oaken(橡树)一词。这两个词暗示了芦苇的韧性和橡树的忍耐,这些特性都反映在了里德的身上。他有勇气跨越种族界限,居住在白人生活的社区,那里不再有那么多噪音,也不会再有蟑螂。但他搬到这里却发现这里无法接受他,他很快就感受到了邻居的敌意:“第一天晚上,一块石头,有两个拳头那么大。/第二天晚上,有三个拳头那么大。”里德保持了足够的克制,但是在第三天晚上,当破碎的玻璃伤到了他的小女儿梅布尔时,看到女儿额头上流的血,他决心要反击。
我们的鲁道夫·里德站了起来
用力握了一下他妻子的手,
……
冲出门外(Brooks,1960:64)
里德出去之前用力握了握妻子的手,这个动作表明他是知道后果的,然而他决心要战斗。在打伤了四个白人后里德被枪杀,他的白人邻居们看到他的尸体,踢了一脚说:“黑鬼——”,他的生命就这样被剥夺了。他“在平凡的家庭生活中对抗种族隔离和压制,宣称了黑人对于参加社会公共交往以及保障平等公民权利的诉求,这无疑是黑人英雄主义最有意义的体现”(史丽玲,2016:114)。在里德死后,里德的妻子没有离开这所房子,也没有责备她的女儿,里德的尊严与力量传递给了下一代。
一直以来,布鲁克斯秉持着种族融合的理想,想让白人接受黑人并且承认他们享有与白人相同的权利。融合(integration)与同化(assimilation)及调和(accommodation)不同,同化意味着永远失去自己的种族身份,同时放弃自己的文化和传统,融入主流文化。布鲁克斯所强调的融合是在保留种族自尊的前提下,跨越种族界限,实现种族和解,结束种族排外,有一种理想主义和不切实际的成分在其中。充满暴力的种族冲突催生了布鲁克斯的觉醒,她清醒地意识到在种族压迫下黑人是无法维持种族尊严的,如果不进行真正的政治变革,黑人就永远没有自由和平等的希望。
五、《在麦加》:死亡孕育新生
《在麦加》是布鲁克斯写作生涯中最长的一首诗,最初的形式是小说,但是出版商认为她的作品更像诗歌,而且认为她用诗歌的形式创作更好,因此布鲁克斯把它改成了一首2 000行的诗歌,之后精简为807行,于1967年完成,1968年出版,并受到了读者的好评,同年9月和11月分别印刷了两次。1969年2月,这一作品还获得了国家图书奖的提名。这首诗创作于20世纪60年代,“死亡”是当时的一个关键词。1963年6月12日,美国有色人种协会的领导人艾佛斯(Medgar Evers)被杀;1965年2月21日,黑人领袖马尔科姆(Malcolm X)被敌对的黑人穆斯林教徒暗杀。1965年8月11日至16日,洛杉矶的黑人聚居区瓦茨发生暴乱,造成35人死亡以及严重的财产损失。这首诗虽然不是反映这些现实事件的,但是诗中所描写的黑人小女孩的死的确影射了黑人内部的暴力。这首诗不仅呼吁人们关注居住在贫民窟的黑人处境,也反思了死亡对社会和人们的影响:死亡不只带来负面的结果,也可能孕育着新生的希望。
麦加是“四层楼的砖制结构,楼顶是一个烟囱,破旧而丑陋……庭院里散落着报纸、易拉罐、牛奶盒和碎玻璃”(Brooks,1987:404)。这里是芝加哥黑人的聚居区,也是典型的贫民窟。麦加曾经一度富丽堂皇,最初是为白人修建的,装修很考究,门厅放有鱼缸,楼梯上铺有地毯。一战期间北方的黑人开始移民于此,经历了1919年的芝加哥暴乱和之后的经济萧条,这座建筑物辉煌不再了。麦加大楼共有176间公寓,能够安置2 000人。1941年,芝加哥理工学院买下了这座建筑,并于1952年彻底拆除了这座建筑物。布鲁克斯之所以选取这座建筑物为题,一是她早年曾居住在麦加,有亲身体验,当时她给一个药品代理商做助理,诗歌中的“预言家威廉斯”片段就是对这段经历的回忆;二是麦加象征着美国北方城市的贫民窟,代表了它所有的优点与缺点,“即使它不复存在,这种令人窒息的气氛和各种压迫的形式仍然在 60年代的非裔美国人的生活中挥之不去,布鲁克斯想在诗歌中表达人们在这种环境中所进行的反抗和为了改变生活所做出的努力。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她让这座建筑超越了当时的历史。”(Saber,2010:156)此外麦加也有着象征意义,因为麦加原本是穆斯林的圣城,是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出生地,是穆斯林朝圣的地方。诗歌第一页的左侧写着“这是通往麦加的路”,让人想起《圣经》中《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第十一节中提到的麦加是“耶稣基督出生的方向”。这为全诗增加了几分宗教的意味,同时诗歌中也蕴含了再生的力量。
在作品的扉页,布鲁克斯将这首诗献给三位著名的黑人作家:兰斯顿·休斯、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阿米里·巴拉卡(Amiri Bararka)和一位黑人教育家麦克·亚力山多夫(Mike Alexandroff)④,表达了对他们的敬意。诗歌的开头暗示了麦加所带来的希望与失望:“坐在阳光腐化面孔之地。/密斯·范·德·罗⑤的(建筑)优雅不在。/美丽的传说没有好的结果。”阳光虽然美好,但紧跟着“阳光”的词是“腐化”,阳光成为加速事物腐烂的原因。光本来应该指救赎之光,就像叶芝的《二次圣临》一样,我们所盼望的拯救之光并未到来,所得到的只是腐蚀我们、带来负面结果的光线。原文中的fair(美丽的)与白皮肤相关联,只有金色的头发、白色的皮肤才被认为是美丽的;fable既有传说、寓言之意,也暗示着这种传说只是谎言和虚构的,黑人显然与这种美丽无关。密斯设计的伊利诺伊理工学院就在麦加的对面,却早已失去了昨日的光辉,美国梦也是昨日的神话,一切都没能得其所愿。
诗歌的第一部分围绕一个四五岁的黑人小女孩帕皮塔的失踪展开,她的母亲莎莉是富人家的女佣,一共有九个孩子。她对主人家的孩子有着非常矛盾的态度,希望自己的孩子和主人家的孩子能够互换角色,因为那个孩子所拥有的物质享受是她的孩子无法得到的。她爱她的孩子,但是她能给他们提供的食物只有甘薯和玉米面包。她没有时间思考人生的出路,因为她必须努力工作,为九个孩子提供食物。虽然“清洁工如同外交官/一样高贵”,然而她的工作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日复一日的工作就只有一个简单的目的:活下去。
诗歌的第二部分讲述了帕皮塔的失踪,这是这篇诗歌的核心内容。莎莉回到家中发现自己最小的孩子帕皮塔失踪了,她的失踪使原本就艰难生存的家庭雪上加霜。诗中用大写字母突出了母亲的恐惧和焦虑:“SUDDENLY, COUNTING NOSES, MRS.SALLIE SEES NO PAPITA. WHERE PAPITA BE?(突然,莎莉太太数了数孩子,发现少了帕皮塔,帕皮塔去哪了?)”这让她内心崩溃,难以相信和接受这一事实。这一部分的叙事从对话转为内心的独白。对于帕皮塔的寻找不仅仅是物理意义上的寻找,并且具有一定的象征意味。莎莉太太疯狂地在麦加这座建筑物里寻找,每敲开一扇门她都听到了一个充满恐惧与压抑的悲伤故事,她求助的人本身也需要帮助。这样故事就延伸到了许多居住在这座建筑物里的人物,最后这首诗扩大了叙述的范围和领域,从帕皮塔的故事转而叙述寓居在麦加大楼的黑人的梦想、斗争和经历的挫折。在寻找帕皮塔未果的情况下,莎莉太太选择了报警,可是这完全没有给她带来希望,因为警察代表着白人的世界,他们只是麦加的局外人,“无法为黑人很快地找到/一名女性”。警察的工作仅仅是阻止黑人暴力,并且对犯罪的黑人进行惩罚,对于黑人母亲寻找孩子的诉求,他们无动于衷。白人世界的反应并不令人吃惊,黑人自己的漠然和道德扭曲反而更可怕。比如,哈依那深陷于白人的审美标准,看不到黑皮肤、黑头发的任何好处,这导致她不仅排斥自己的同胞,也排斥她自己。为了与白人相同,她将头发染成金黄色。这种自我憎恨包含了内在的暴力,让她和其他黑人之间产生了不能逾越的鸿沟。她对帕皮塔不仅没有同情,反而充满了恶意。“痛苦、贫穷、肮脏、不公撕碎了麦加居民的心灵。”(Melhem,1987:163)
居住在麦加的黑人居民与白人社会疏离,而且彼此疏远,寻找帕皮塔又重新让他们聚在一起。他们的痛苦都是来源于种族主义、贫穷和压迫,尽管他们讲述的方式不同,但是都同样令人震惊,使人悲伤。每个人都在寻找失去的帕皮塔,她象征了破碎的承诺和人们所依赖的模糊希望。麦加的故事充斥着各种各样的体验:被奴役、暴力、疯狂、孤立、受骗、自我憎恨、家族仇杀与背叛,这让莎莉太太在寻找女儿的过程中也同样痛苦。爱是沉重的负担,希望带来的只是失望。
故事以悲剧结尾,警察找到了帕皮塔的尸体,上面爬满蟑螂,她已经被人杀害了。谁是杀害帕皮塔的凶手,是黑人还是白人?这将为本诗带来不同的结局。如果凶手是白人,那就能归罪于种族歧视,但是杀害他的凶手是来自牙买加的黑人爱德华。这是内在的暴力,而不是来自外面的迫害。“与巴拉卡的民族主义主张暴力不同,帕皮塔之死给读者带来了一个严肃的启示,暴力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是我们总要从两方面来看。”(Saber,2010:164)暴力并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并不能制止暴力。帕皮塔是种子,是希望,但是这粒种子却被黑人的脚所践踏死亡,联想到黑人领袖马尔科姆的死亡,布鲁克斯很明显在谴责种族内部的暴力。在诗歌的结尾,诗人写道:
她用微小的勇气在与这个世界搏斗
像知更鸟一样挣扎!
这种微小的挣扎很奇怪
同样奇怪的还有切断的啁啾。
知更鸟具有死亡和再生的双重喻义。在基督教的传说中,知更鸟从受难的耶稣的荆棘王冠中拔出荆棘时刺穿了自己的胸膛,因此它胸前的羽毛是红色的。知更鸟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它却用尽自己的力量给受难的人以安慰。在欧洲,知更鸟的出现则意味着漫长的冬天已经结束,春天已经来临。
莎莉太太在寻找帕皮塔的过程中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物,面对生活的不幸,他们从开始的无动于衷到后来的愤怒、呐喊,体现了积极的变化,但最后以帕皮塔之死结尾,表达了布鲁克斯最终仍然没有找到一个明确的方式来解决黑人的问题。“然而,虽然帕皮塔的人生结束了,但是帕皮塔不可侵犯的灵魂变成了鸟,永不屈服。”(Melhem,1987:175)死亡孕育着新生,通往自由的路充满着荆棘和曲折,黑人用鲜血和泪水在探索一条通往自由的道路,希望最终实现真正的民主与自由。麦加的遭遇给人们带来了失望,同时也促使黑人群体不再盲从与互相伤害。如果想得到自由,必须消除内部的暴力,麦加的居民必须成为一个共同体,建立一种集体的黑人意识,以此来进行抗争,才有获得自由的可能。
莎莉太太在寻找的过程中所遇到的人虽然有的很冷漠,对于黑人本身的遭遇无动于衷,但也有一些人对黑人的解放作出了积极的探索,这让破败的麦加孕育了重生的希望。特别是阿莫斯、莫根、唐李和阿尔弗雷德,他们采取了不同的方式来冲破美国社会对于黑人的枷锁,尝试改变黑人生活的窘境,从而获得新生。布鲁克斯对这四个人物的描写体现了黑人在受压迫、受奴役的过程中始终没有放弃获得解放的努力,他们的探索恰好呈现了三个阶段:“预言、毁灭和建构。《在麦加》经历了从表达到阐释、从提问到行动的过程。”(ibid.:164)阿莫斯预言了暴力方式是获得自由的途径,莫根拿起武器进行反抗,而唐李和阿尔弗雷德想要打破旧世界,建立新国度的想法则孕育着获得新生的萌芽。
阿莫斯的名字取自《圣经》中的人物,他为受压迫者代言,认为人们无论贫富都应该被公正对待。他预言只有通过暴力,用血和愤怒来对美国进行洗礼,才能撕开美国民主和平等的面具,让其恢复纯洁。“用美丽的血为她洗浴。/这种洗浴可以让她得到净化。”他认为,白人长期“用他们的手鞭打黑人,/黑人流血他们却以此为乐”。然而,他的复仇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并未付诸行动。而莫根则拿起了枪,他要复仇,因为他的妹妹在密西西比被白人暴徒强奸,他准备通过武力进行反抗。
阿尔弗雷德是麦加的一名知识分子,他是莎莉太太遇到的最后一个人物。他想要找到一个黑人可以追寻的模式,而他开始也是一个逃避主义者,想从白人世界寻找答案。他阅读赫胥黎、莎士比亚、乔伊斯、波德莱尔、勃朗宁、聂鲁达等人的作品,希望从中找到答案。而这种追寻并没有给他带来希望,在唐李的影响下,阿尔弗雷德摒弃了白人知识分子的模式和他过去相信的白人信条,去除了自己先前的迟疑和消极的逃避,因为:
在麦加有什么一直
在召唤!无影无形,然而却如同山峰,
河流和海洋;如同风吹过的
树木。坚定地
保持清醒的头脑,虽是黑人却不气馁
才成就了报道与救赎。
强烈的疏离。
事物崩溃后
才能建构。(Brooks,1987:433)
保持清醒就是要认识到在多年的压迫和不公之后,积极响应反抗的召唤。事物崩溃就是让融合和平等的神话分崩离析,在这种毁灭人的环境里黑人要认清自己,从而“为一整套的社会秩序形成新的民族精神”(Melhem,1987:173),建构起黑人自己的道德观和价值观。
唐李比阿尔弗雷尔的探索更进一步,不仅要建构黑人的道德观和价值观,而且他觉得必须要建立一个新的国度。
唐李想要的
不是一个多样的美国
唐李想要的
是一个白手起家的
新国家;
逐渐增加的光
想要
新的艺术和安魂曲;想要
在太阳下嘶吼的音乐。
他所提到的“逐渐增加的光”表明随着黑人的努力,微小的希望之光在逐渐放大。唐李“主张在政治、文化、艺术等方面独立于欧洲中心,建立现实和想象层面的‘黑人国度’”(史丽玲,2014:86)。这种主张反映了布鲁克斯所受到的黑人国家主义的影响。“1967年在费斯克(Fisk)大学召开的第二届黑人大会改变了布鲁克斯,她遇到了一些年轻的诗人正在支持一种新的黑人文化国家主义,特别是巴拉卡(那时候叫 LeRoi Jones)。布鲁克斯感觉自己醒来了并进入了‘某种神秘与不安的奇妙境界’。”(Ramazani,2003:141)1967年后她将自己归入激进的黑人作家,脱离了纽约的出版商,将自己的作品交给非裔美国人的出版社出版,并归属于非裔美国人的团体。她认为,黑人作家应该求助于他们的黑人文化,准确定位自己的身份。他们不但要拒绝被白人同化,而且要恢复黑人的自尊,复兴黑人的文化,甚至建立黑人自己的国度。可以看出,《在麦加》明确地表达了布鲁克斯已经放弃了种族融合的幻想,开始探索建立“黑人国度”的可能性。
六、结语
布鲁克斯在诗歌中描写了城市中各行各业的黑人,展现了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的全景,直面城市中黑人男性和女性所面临的种种不公,讽刺白人虚伪的民主,表达了黑人的政治诉求。她以独特的观察视角展现了暴力、死亡、身份认同、两性关系、战争、扭曲的社会关系等方方面面的主题,并对黑人未来的出路进行了探索。
《布朗兹维尔的一条街》呈现了黑人群体的日常生活图景和种族生存困境。为了改变黑人艰难的生活处境,获得民主与自由,布鲁克斯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莫德·玛莎》塑造了一位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形象,她热爱阅读,追求精神自由,从未放弃对幸福生活的追寻。在《吃豆子的人》中,布鲁克斯又把眼光转向种族暴力事件,黑人群体诉诸暴力的行为模式体现了其对于社会公共权利的诉求,同时也催生了白人内部对于种族歧视的质疑。在《在麦加》中,布鲁克斯通过帕皮塔之死谴责黑人内部的暴力,在寻找帕皮塔的过程中探索建立“黑人国度”的可能性。
布鲁克斯笔下的人物有着自己鲜明的个性与特征,她充满同情地描写了黑人的生活困境、他们的种族主义斗争和破碎的梦想。他们所处的外界环境是一样的,虽然对于生活的态度各异,却都无法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在她的叙述中,黑人女性无法与男性建立稳定的关系,甚至无法拥有做母亲的权力;黑人男性渴望拥有幸福的生活,获得做人的尊严,但是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获得身心的满足。
她所描写的是具有真实情感、在痛苦生活中保持自己尊严的个体。布鲁克斯的描写是发自内心的,描摹的是苦难深重的黑人同胞。她还描绘了一些知识女性的形象,无论是《安妮·艾伦》中的安妮还是《莫德·玛莎》中的莫德,她们在艰难的人生中从书籍和音乐中汲取力量,不再将自己的命运寄托于爱情和婚姻,而是有了更高的精神追求。这突破了以往对于传统黑人女性的描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布鲁克斯还具有兼容性的种族观,认为黑人首先要实现内部的联合,赢得社会的普遍尊重,在保有民族特性的同时跨越种族的差异,努力实现种族和解。她认为,黑人要直面现实,用行动去改变社会。她想要在非裔美国人的社群中进行一种改变,同时响应黑人艺术运动的呼唤,呼吁黑人建构自己的道德观和价值观。种族歧视是可怕的,而黑人内部男性对于女性的压迫、自我贬低以及追求同化更加可怕。布鲁克斯追求的是实现黑人内部的平等,让黑人团结起来,实现自身的价值,获得外界的肯定,从而才能实现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平等。
注释:
① 这部诗集中所有题目的首字母都没有大写,仿佛暗示着他们卑微的身份与悲惨的命运。
② 佐特服(zoot suit)流行于20世纪40年代,裤腰高,裤口狭窄,搭配大翻领、厚衬垫和宽肩的长上衣。
③《吃豆子的人》选自诗集中的同名诗作,因为罐装豆子非常便宜,是穷苦黑人的主要食物。
④ 麦克·亚力山多夫是芝加哥哥伦比亚学院的院长,布鲁克斯在那里获得了第一份教职。
⑤ 德裔美国建筑师,伊利诺伊理工学院的设计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