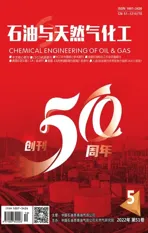地下含水层储存氢气的可行性分析
2022-10-24崔传智任侃吴忠维姚同玉徐鸿邱小华
崔传智 任侃 吴忠维 姚同玉 徐鸿 邱小华
1.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石油工程学院 2.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氢是自然界乃至宇宙中最多且最常见的元素,氢气相比于其他燃料,其燃烧产物最清洁,基本只产生无污染的水,可用于循环制氢。因此,氢能被认为是当前最具吸引力的清洁能源之一,有效利用氢能可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此外,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波动性可能导致需求和供应之间的暂时不匹配,因此,为避免可再生能源的浪费,需要将储能技术与电网系统相结合[1],把剩余能源通过电解水转化为氢气储存在地下,以达到平衡这一能源缺口的目的。从地质学的角度来看,地下空间适合储存氢气,可以将其用作能源生产过剩时的储存介质,然后在能源需求高峰期时进行利用[2]。储存氢气的主要地质构造包括盐穴、枯竭油气藏和含水层等[3]。其储存方法为向地质构造中注入垫气(缓冲气体,如氮气和二氧化碳)和注入氢气。氢气地下储存的目的及意义主要体现在能充分利用地下空间、节约土地资源、有效降低氢气的储集成本、提高氢气的经济效益,以及保障能源供应和能源安全等[4]。
氢气地下储存的潜力已通过HyUnder项目所论证[5],德国的InSpEE项目编制了盐穴储氢库的标准,并估算了北德盆地的储存潜能[6]。此外,许多国家也进行了氢气地下储存的地质调查[7-27],众多的研究表明,全球正在开启氢能开发和地下储存的探索之路,因此,了解地下储氢以及对此展开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在诸多地下储氢研究中,大多为盐穴型储氢库,含水层储存纯氢的现场案例暂未见报道,因此,需要论证其可行性,以期将多余能量转化为氢能储存于地下含水层中。目前,在氢气地下储存的实例中,地下含水层储存容量比盐穴大几个数量级,位于美国Spindletop油田的一个盐丘型储气库,气体中含有体积分数为95%的氢气,容积仅为906 000 m3,而位于法国Beynes的一个含水层储气库,其储存气体由体积分数分别为50%的氢气和50%的甲烷组成,容积达到3.3×108m3[28]。
本文在对国内外文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主要对氢气常温常压以及高温高压下的物理化学性质和地下含水层储存氢气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总结了部分含水层储存氢气的模拟案例,为地下含水层储存氢气的实施提供参考依据。
1 氢气的物理化学性质对储存的影响
在地球大气中,氢气的质量浓度极低,大约为1 mg/L[29]。与甲烷和二氧化碳相比,氢气具有不同的物理性质。氢的相图如图1所示[30],氢在-262 ℃下表现为密度为70.6 kg/m3的固体,图1中阴影部分为液体,在地层条件和标准条件(20 ℃,101.325 kPa)下氢都是以气体状态存在。

表1列出了氢气、甲烷和二氧化碳的物性参数[28,31],在常温常压(20 ℃,101.325 kPa)下,甲烷和二氧化碳的密度分别为氢气(0.083 75 kg/m3)的8倍和22倍,因此,储存同等质量的氢气需要更大的压力。由图2和图3可以看出[32]:与甲烷和二氧化碳相比,氢气的黏度和摩尔质量最小,这表明氢气的流动性更高;氢气的密度和黏度随温度和压力的变化甚小;三者中氢气的扩散系数最大,这可能是地下储存氢气损失的原因[33]。因此,地下储存氢气对地质结构的要求更高,以防止氢气逸散。

表1 氢气、甲烷、二氧化碳的物理化学性质对比


当氢气储存在含水层中时,其溶解度的影响非常重要。与甲烷和二氧化碳相比,氢气的溶解度较低,这可以看作是地下含水层储氢的一个优点,因为溶解而产生的氢气损失较少。在标准条件下,氢气在水中的溶解度要比在地层条件下小得多,如图4所示。在319 K和0.678 MPa时,氢气在水中的溶解度为0.000 085 6 g/100 g[34];而在323 K和7.9 MPa时,氢气在水中的溶解度为0.001 03 g/100 g[35]。

2 氢气地下储存模拟案例
充满盐水的深层含水层具有巨大的容量,广泛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沉积地层中,可以储存大量的气体,这是季节性氢气地下储存较好的方案。尽管没有在含水层中储存纯氢的例子,但是有很多数值模拟的研究论证了地下含水层储存氢气的可行性。
Pfeiffer等[37-38]利用油藏数值模拟软件Eclipse E300对德国Schleswig-Holstein的一处背斜结构中含水层储氢进行模拟,共布5口井。第1阶段,以56 625 m3/d/井的速度注入缓冲气体氮气,持续710天;第2阶段以155 000 m3/d/井的速度注入氢气,持续210天;第3阶段,模拟4个储存循环周期,每个周期包括采出氢气7天、注入氢气50天以及关井30天。其中,采出和注入速度分别为1000 000 m3/d/井和150 000 m3/d/井。通过模拟得到平均每口井的采出速度由第1个周期的4 537 663.45 m3/d提高到第4个周期的4 937 376.33 m3/d,增幅为8.81%;平均每口井的采出气体中的氢气体积分数也由最初的52%增至85%,可见效果较为理想。同时,从优化结果来看,在储层刚开始填充缓冲气体后到关井一段时间,可以提高氢气的注入能力,进一步提高储存性能。
Luboń等[39]对波兰Suliszewo地区一个深层含水层建立静态地质模型,并使用PetraSim TOUGH2软件进行氢气注入模拟,以此评价季节性循环储氢的可行性。先向地层中注入氢气24个月(第1个月注入速度为0.34 kg/s,接下来23个月注入速度为0.51 kg/s),接着注入和采出(采出流量为3 kg/s可使采出气体中的氢气流量约为0.51 kg/s)分别为6个月。第1个循环采出氢气8 404.95 t,仅为注入氢气的25.41%,但经过5次循环后,采出氢气41 807.43 t,占注入氢气的59.19%。
通过上述数值模拟可以看出,虽然注入-采出循环初期采出气体中的氢气含量较低,但是经过4~5次循环后,氢气体积分数均超过50%,有的甚至达到85%,取得了较好效果。
3 含水层储氢影响因素分析
3.1 缓冲气体影响
将地下含水层转为储氢库时,由于地层压力低,很难在短周期内采出适量的氢气,需要对储层进行加压,一般是通过注入缓冲气体(如氮气和二氧化碳)来实现[40]。同时,缓冲气体的注入可以降低重力偏析的影响,从而提高氢气的回收率。缓冲气体的作用是增加储层压力,使得工作气体(氢气)更易采出。在采气过程中不采出缓冲气体,而是将其保留在地层中。能否作为缓冲气体,关键是看气体的压缩性强弱,压缩性强的气体作为缓冲气体时效果越好[41]。氢气储存在含水层时,注入气中大部分为缓冲气体,其体积分数可达80%,见图5[42-43]。由此可见,缓冲气体是影响含水层中氢气储存的关键因素。

从热力学性质和碳封存方面考虑,二氧化碳作为缓冲气体具有很大的优势[44],但其与氢气的混合始终存在问题[45]。Tek[46]认为,氢气和缓冲气体之间的混合来源于扩散,包括分子扩散和机械扩散。谭羽非[47]通过研究二氧化碳作为缓冲气体的混合机理,指出影响二者混合的因素包括黏度差、密度差、注入速率和注入强度。Wang等[48]基于标度理论,通过二维垂向数值流动模拟,对缓冲气体二氧化碳在氢气中的流动展开研究,认为气体捕捉效应和毛细管力不是影响氢气采收率的重要因素。Mu等[49]从二氧化碳的较高压缩性、二氧化碳和甲烷的密度差异导致分层从而减少两者混合这两个角度,论证了二氧化碳作为含水层储气库缓冲气体的可行性。氢气密度较甲烷密度小,因此二氧化碳和氢气的分层更明显,二者的混合效果相应减弱。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二氧化碳作为缓冲气体的可行性。
Pfeiffer等[37-38]通过对5口井进行含水层储氢模拟得到,当氮气作为缓冲气体时,第1个周期(每个周期包括采出氢气7天、注入氢气50天及关井30天)采出的气体中,氢气体积分数最高为55%,最低仅为5%。经过4个注采周期后,5口井的采出气体中氢气的平均体积分数为85%。因此,一般需要经过数个周期才可以达到理想的状况。
Kim等[50]通过数值模拟,对氮气和二氧化碳分别作为储气库缓冲气体进行比较发现,氮气的生产指数降低幅度大于二氧化碳,因此,二氧化碳作为缓冲气体比氮气作为缓冲气体对含水层储存氢气更为有利。谭羽非等[51]通过计算得出:在5~13 MPa下用二氧化碳作为缓冲气体,二氧化碳极高的可压缩性允许更多工作气体注入;同时,二氧化碳具有较高的黏度和黏度变化率,注采时可限制二氧化碳与工作气体混合。但是,Iloejesi等[52]认为,盐水层中注入二氧化碳后,降低了pH值,导致碳酸盐和铝硅酸盐矿物的溶解,为次生矿物的沉淀创造了有利条件,进而改变储层的渗透率,如果有大量二氧化碳参与反应,采气时会导致压力差降低,从而降低储氢库的工作效率。
Heinemann等[53]利用商业储层模拟器GEM得到,在含水层储氢库的条件下,较高的储层渗透率和较深的储层所需缓冲气体的量更少。
综上所述,虽然在理论上二氧化碳和氮气都可以作为缓冲气体,但是由于地质条件的复杂性,在实施工作前应先进行诸多数值模拟研究,以期达到理想状况。此外,在中国进行“双碳”目标重大战略决策的当下,应着重进行二氧化碳作为缓冲气体方面的研究。
3.2 润湿性影响
由于黏土矿物的润湿性,氢气可以吸附在黏土矿物中,从而有利于在富有黏土矿物的储层中储存氢气[54]。Yekta等[55]通过半动态毛细管力和压汞法,测得氢气-水系统中接触角的余弦值分别为0.93和0.82;界面张力分别为0.051 N/m和0.046 N/m,进一步从实验角度证明了地下储存氢气的合理性。
Al-Yaseri等[56]通过倾斜板法测量氢气与高岭石、伊利石和蒙脱石黏土矿物之间的润湿角[57]。实验结果如图6所示,所有黏土矿物-气体的接触角都随压力的增加而增加,这是因为在高压下,黏土矿物表面和气体之间的分子间相互作用增加,因此密度较低的气体润湿角θ0也低(θ0,He≤θ0,N2<θ0,CO2)。总之,这3种黏土矿物在黏土矿物-氢气-水系统中水湿都较强,θ0,H2基本低于40°,蒙脱石的润湿角大于伊利石,高岭石的润湿角最小。

由于这3种黏土矿物都是水湿的,因此在黏土矿物存在的情况下,氢气可以吸附在黏土矿物中,有助于抑制地下储层中氢气的逸散。其次,氮气、二氧化碳的润湿性都强于氢气,可以作为缓冲气体来稳定储层压力。
Al-Yaseri等[58]通过实验验证了玄武岩对于地下储氢是有利的,并且同样验证了氮气作为缓冲气体的合理性。Hashemi等[59]使用捕获气泡法对Bentheimer砂岩进行润湿角测量,得出砂岩-氢气-盐水系统中的润湿性不受温度、压力和盐度的影响,且润湿角为21.1°~43°。同时,Iglauer等[60]通过倾斜板法亦得到砂岩-氢气-盐水系统的润湿性,润湿角最大不超过48.3°。Ali等[61]通过实验研究云母(在页岩、火成岩、变质岩和沉积岩中大量存在)-氢气-盐水系统的润湿性得到相同的结果,并提出为保证地下储氢的有效实施和安全性,应考虑有机酸的影响。
上述研究表明,在常见的矿物中,矿物-氢气-盐水系统都属于亲水的,且润湿角不超过50°。因此,就润湿性而言,地下储氢是可行的。
3.3 微生物影响
微生物能够在-15~121 ℃和pH值为0~11的非常极端条件下生存。地下的微生物多种多样,主要包括细菌和古细菌这两种单细胞群[62]。在地下2 000 m左右发现了微生物的存在,Dutta等[63]通过基于定量聚合酶链反应(quantitativ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qPCR)的方法确定细菌和古细菌 16S rRNA 基因拷贝数,以此来描绘微生物的垂直分布,得到每克岩石中的细菌数和古细菌数各约为104个和108个[64]。Magnabosco等[65]估计整个地表以下有(2~6)×1029个微生物。
从以上分析可知,含水层中微生物含量丰富,既有地层中固有的,又有人类地下活动(如钻井、注水或酸化处理等)引入的。为了保持自身活性,微生物需要特定的环境和维持生命的基本物质,即水、能量和许多必需元素(碳化物、氮化物和无机盐以及微量元素)。目前,氢气被认为是地下岩石自养微生物生态系统(即没有光合作用参与的生态系统)的主要能量来源[66-67]。氢气与这些微生物反应复杂(表2)[68],这些反应将不利于氢气在含水层中的安全储存。

表2 储层微生物与氢气发生的反应
Eddaoui等[69]通过数值模拟软件 DuMux建立了孔隙堵塞模型。利用该模型,向含水层中注入氢气进行模拟,最终认为微生物堵塞孔隙虽不可避免,但并非十分严重,甚至可能是有益的。微生物在氢气饱和度高的地方积累,迫使氢气向不同的水平方向运移,并且毛细管力增强了这种运移,使得储存在含水层的氢气在各个方向上均匀分布。
由于地层中缺少氧气和硝酸盐,因此好氧氢的氧化、反硝化和氨化作用只有在含水层受到污染时(例如钻井液的侵入)才会变得显著。烃分子中的氢原子被卤素原子取代后生成卤代烃(如氟代烃、氯代烃等),虽然卤代烃在含水层中很常见,一般由污染物或沉积物中的自然过程引起,但是这些化合物的浓度极低,在170~1 000 m的含水层中,氯氟代烃(由氯、氟取代烷烃中的氢所形成的各种卤代烃的总称)的质量浓度≤1.1 μg/L,对于原始含水层氯代烃质量浓度为0.003~0.007 μg/L,因此,卤代烃对于地下储氢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70]。在消耗氢气方面,捷克共和国Lobodice地区储存在含水层中的城镇天然气中,有体积分数为45%~60%的氢气在35 ℃下被微生物转化为CH4和H2S[71]。因此,氢气在地下含水层的储存需要着重考虑氢气与微生物反应所造成的消耗。
上述研究表明,微生物对于地下储氢的影响不大;但实际案例表明,氢气在微生物作用下的甲烷化程度非常明显。因此,这些化学反应(甲烷化、乙酸化、硫酸盐还原等)都是影响氢气地下储存的因素,对不同地层既要考虑相应的化学反应,还要进行大量储层环境下的实验,以最大程度降低微生物的影响。
3.4 地球化学反应影响
注入地下储层的氢气会破坏地层水、溶解气和岩石基质之间的化学平衡。由此产生的地球化学反应可能导致以下情况:①氢气的大量损失;②产生其他气体(如H2S等)污染环境;③矿物溶解或沉淀导致注入能力的减弱;④矿物溶解破坏盖层的严密性。这些反应均会影响地下储存氢气的安全性和有效性[33]。
在地下储存期间发生的反应为氢气促进的与含铁矿物(如赤铁矿、针铁矿等)的氧化还原反应,具体反应如式(1)所示[72]。如果砂岩储层中颗粒间的含赤铁矿的胶结物减少,这种反应可能会改变岩石基质的机械强度。盖层中的矿物溶解可能会产生新的渗流通道,从而影响盖层的密封性。


(1)
除了矿物溶解对孔隙度和渗透率的影响外,反应中还会产生H2S,不仅对环境造成污染,同时还降低了氢气的质量。由于天然气行业在生产富含H2S的天然气方面具备丰富的经验[73-74],因此地下储氢过程可以解决H2S问题。
Flesch等[75]通过模拟地下条件(40~100 ℃,10~20 MPa)对储层砂岩进行实验,结果表明,碳酸盐和硫酸盐胶结物的溶解,导致与氢气接触期间的储层孔隙度增加。但是,石英和长石等骨架矿物并不受氢气的影响。因此,碳酸盐和硫酸盐矿物的溶解非常重要,这可能导致储层岩石或盖层的密封性受到破坏,进而导致氢气的逸散。
Yekta等[76]将法国Buntsandstein地层的砂岩作为测试样本,分别在地层条件(①温度100 ℃和200 ℃,压力10 MPa;②温度100 ℃和200 ℃,压力1 MPa)下,测试氢气在水存在下对砂岩的影响。结果表明,氢气的存在与否对于石英、长石和云母的溶解影响甚微。
Bo等[77]通过数值模拟得到:①温度和压力在氢气损失中的作用可以忽略不计;②储层和盖层不含方解石的地质条件更适合地下储存氢气。
上述研究表明,选取合适的地质结构对于地下储氢至关重要。盖层中方解石的存在会导致储层的致密性受到破坏,研究认为,储层为砂岩是较为理想的选择。
3.5 储层温压系统及孔渗特性
储氢库一般包括盐穴、枯竭油气藏和含水层3种类型,不同储存环境下的储层温压、孔渗特性各不相同,尤其含水层储氢库相较前两者差别较大。
含水层作为储氢库,其深度建议为 500~2 000 m[78],温度为 17.5~70.0 ℃,压力为 5.3~21.0 MPa,在含水层中还应注意注入和采出速度,防止指进现象的发生[79]。
含水层作为储氢库比盐穴和枯竭油气藏更为复杂,地下储氢含水层的设计容积取决于孔隙体积,含水层必须具有高渗透率和高孔隙度,适合储氢的含水层岩石渗透率应大于100×10-3μm2,孔隙度应大于10%[32]。
为了尽量减少氢气沿着边界扩散和迁移产生的影响,需要低渗透率和低孔隙度的盖层。因此,盖层最好是不透水页岩或碳酸盐岩的背斜结构或者穹窿结构[32],储层可以是透镜状砂岩含水层[80],最小盖层厚度应为6 m。
总之,与枯竭油气藏型储氢库相比,含水层的筛选需要更为详细的现场考查,包括地球物理学、盖层和储集层的实验室评估,以及地下水条件的物理和化学分析。
4 结论
(1)含水层储氢库大概需要体积分数为80%的缓冲气体,为适应当前碳减排要求,二氧化碳可以作为缓冲气体。需要根据储层的实际条件,优化缓冲气体与氢气的注入质量比和缓冲气体用量。
(2)从润湿性的角度分析,在富有黏土矿物的储层中储存氢气是有利的。碳酸盐和硫酸盐胶结物含量低的砂岩以及不含方解石的盖层更适合地下储存氢气。
(3)不同区块的地下微观环境各不相同,地下含水层储氢需要着重考虑氢气与微生物反应造成的氢气消耗以及对储集层或盖层密封性的破坏,并且还需进行大量的储层环境下的实验,以保证将微生物的影响程度降到最低。
(4)目前没有地下含水层储存纯氢的实例,但是相关的数值模拟研究和影响因素分析论证了含水层中储存氢气的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