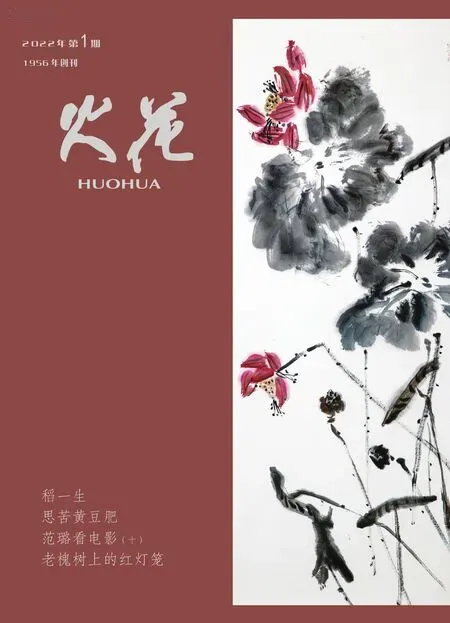思苦黄豆肥
2022-10-22徐玉向
徐玉向
每一年播下的种子,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黄豆,但是,在这片土地上播种的人,却早已似收割后的黄豆秧,换了一茬又一茬。黄豆地东南角的那座小山已被铲平,黄豆地中突然竖起一片高楼。小山里的石块被碾成了沙子,运到了很远的建筑工地上,黄豆地中的高楼则是用混凝土浇筑而成。于是,黄豆地里再也没有了黄豆,小山成了一个秃顶的山包,高楼呢,既没有家乡小山的骨血,更无黄豆地的魂魄。冷峻的用混凝土浇出来的怪物,则成了村子拆迁之后故乡人的栖身之处。而我,只能在记忆深处寻找那片曾经生机勃勃的黄豆地了。
一
大自然孕育出很多奇妙的生物,寄生在黄豆秧中的黄丝藤就是一种。黄丝藤是故乡人赋予菟丝子更形象的别称,它的出现,仿佛是黄豆成长过程中的一次劫难。
黄丝藤通体金黄色,或呈黄褐色,无叶无根,仅仅是些相互缠绕在一起的细丝。所以,有些地方也称为无根草。它没有叶绿体和叶绿素,不能进行光合作用,完全靠寄生存活。就算是寄生,它竟然有自己的选择。对于一般植物,它是看不上的,唯有豆科、菊科或者番茄是其所爱。从它的幼苗钻出地面起,便无时无刻不在空中摆动,借助风的力量,以期搜到宿主。虽属初生,其性情却无比刚烈,倘若没有找到它中意的植物,宁肯殒命也不随意攀附。
故乡一年两季收成,主要涉及三种作物。秋收之后所有的地种小麦;端午到中秋之间,水田就种稻子,旱地种黄豆。1980年,家乡开始分地之后,我们每人分得不到一亩半的耕地。鲍家沟向西是连成片的旱地,这其中就有我们家的一亩多。每年夏秋两季,这里就是黄豆的海洋,所以,它也理所当然地成了黄丝藤的倾身之处。
黄丝藤有一项其它寄生植物所不具备的特异功能,它凭嗅觉在风中寻找中意的植物。豆科、菊科或者番茄会散发一种化学物质,这让它沉醉其间。即使相隔甚远,它也千方百计地越过一切障碍,向着心中所爱慢慢接近。
黄丝藤表面上给人以柔柔弱弱缠缠绵绵的感觉,所以古人把它当作爱情的象征,自古到今留下了许多关于它的爱情诗句。《古诗十九首》:“与君为新婚,菟丝附女萝。菟丝生有时,夫妇会有宜。”诗仙李白亦有“君为女萝草,妾作菟丝花”的诗句。
黄丝藤的生命中充满侵略性。虽然无根,它却靠吸盘如水蛭一般深入黄豆秧体内吸收水分和养料。但凡出现一株,不久就会连成一片一丛,成为黄豆地的噩梦。但凡被它盯上,不要说拔节结荚了,就连存活都成了问题。
听人说,黄丝藤身体里吸收和储存的都是别的植物精华,具有滋补肝肾、固精止泻等功效,是一味不可多得的中药。
可是,仍然靠天吃饭的故乡人只认庄稼。天不作梗,人不偷懒,地不服输,谁影响口粮的收成,那它一定就是大家的公敌。种庄稼的人家过日子,难道天天要拿中药来填肚皮吗?但凡被收拾出来的黄丝藤,绝对不会摊上好脸色,要么被丢在马路上,要么被捎回家给猪打了牙祭。
二
以秋露为甘泉,广袤的黄豆地为青蟒尖提供食之不尽的嫩叶。它们自出生即埋首豆茎上,不分昼夜地啃食豆叶,每天以肉眼看得见的速度长大。
相较黄丝藤,青蟒尖对黄豆的伤害更大。每年临近中秋,正是黄豆地里青蟒尖泛滥之时。故乡人称豆青虫为青蟒尖,主要是畏其个头大,危害严重。常常,当我们发现它们时,青蟒尖的身体已快赶上小拇指粗,细的也粗过豆秸的主茎。成虫体长有的同掌心,小的五六厘米。它们所过之处,豆秧一片零乱。有的黄豆叶仅被吞食一个小孔,有的只剩下不到三分之一的残叶,严重一些的一株豆秧只剩下光秃秃的茎和孤零零的豆荚。缺少了豆叶的光合作用,豆荚也会停止生长,造成大面积减产。
青蟒尖却从不关心黄豆秧的死活,自入侵伊始便为非作歹。饱餐之后,惬意地用几对短足吸住茎杆,而上半身则探在空中,或弓起腰身注视远方,或反身贴向尾部。尾部延出的细细尖角让人很容易辨识头尾。缓缓地蠕动,慢慢地攀行,似一个沉稳的王者,周边的一切皆臣伏身下。唯那一身裹在肥胖身躯上的青袍,看着有些瘆人。正是那身青袍,使它匿于碧叶之下时极不易被发现。
逮青蟒尖的人靠近豆秧,用短棒挑翻层层豆叶之时,一束光射在笨拙的身体之上,它们仍毫无慌乱之意,慢吞吞地向着阴暗处退去。故乡人便连着叶子一起剥进柳条筐或瓷盆里。即使被捉住,它们仍不放过每一刻进食的机会。最终,被人们丢在地头的马路上,任车辆辗压其躯,任鸟雀啄食其尸,任烈日暴虐其魂。
村里有见过世面的人,说青蟒尖可以吃。“看着头皮都发麻,怎么吃?”听者便要说话的人自己先尝尝。一片哄笑声中结束了劳作后的闲聊。
多年之后,我在距故乡几百里外的苏北做项目时,接风宴上竟邂逅青蟒尖。只不过,它已改名换姓成了豆丹,且成了席间最贵的一道美食。
三
秋风轻轻一吹,豆荚就变黄了。再等上几日,豆荚变成褐色时就可以收割了。
故乡人趁着太阳高天气好,早早下到豆地里。一把镰刀,一块毛巾,最多再加一顶草帽,收割就开始了。
黄豆秧除了顶上几片叶子是青色,豆茎、豆荚早就改变了形象,恍如公社干部的脑袋,四周已一片光亮,唯有中间几络黑发在迎风招展。弯下腰时,黄豆秧便齐了大半个身子。埋首期间,一股豆香沁入心脾。攥住几株豆秧的上端,镰刀向前虚顶一下再顺势向身后一带,一把黄豆应声脱离了根基,地面只剩下几截尖尖的茬。连续几刀下来,三四把黄豆秧便堆成一小堆。也有性急的豆荚,似要保卫豆秧不受侵犯,镰刀无意间碰到它便轻轻炸裂,豆粒急飕飕地滚向大地。
黄豆地早已被枯黄的豆叶厚厚地垫了底,蟋蟀、土狗连同鸟雀各自惊慌地寻活路去了。偶然有小鸟飞在半空不停尖叫,那下面一定会有一小窝鸟蛋。稻田里常有蛇出现,但大都无毒,黄豆地里最常见的是被我们乡下人称为“土鬼蛇”的,身上带着暗斑,脑袋略显三角。大人们都说被这种蛇咬上一口不得了,轻些的会身上发麻,严重的直接倒下去。其实这些蛇是很少主动攻击人的,它们主要猎食田鼠和小鸟。大人们又说,蛇咬了人之后它自己也不会好受,有些也会死去,好像是遭到报应受到上天的惩罚一般。
我仿佛又想通一个道理,故乡人辛苦打理的黄豆不仅仅是为自己提供口粮,还养活了许多我们知道的和不知道的、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东西。经常说的一句话“众生平等”,我想这众生不仅是生命,还应该包括生态,人与其它生命、人与自然环境是一种相依相存的关系。
在大河与小山之间,赐予故乡人这么一大片珍贵的土地。故乡人经过多少年的摸索,又选择了黄豆作为这片土地的主宰。春天种下黄豆,到了秋天收获了黄豆。大片的绿色豆秧本身就是改善空气的好原料。黄豆供人食用后,残渣成了改善土地养分的上等肥料。供养黄豆的豆秧则成了豆秸,被当作柴禾,贡献完热量后化为灰烬,终又被洒入大地。在这一轮回过程中,人鸟兽虫都得以休养生息,各得其所,且相安无事。
清晨的露珠,仿佛就是这片土地的表情。总在夜深人静之时,大地细细将白天发生在眼皮子底下的事情一件件过一遍的时候,仿佛牛儿在反刍一般。露珠是素日看似鬼灵其实是最傻的一个孩子。挂在草叶尖,躺在豆叶间,倚在豆荚上,直到太阳在顶上不断催促,它们才悄悄地渗入大地之中。露珠其实是最懂母亲的一个孩子,但它善良过早地把母亲的心思暴露了出来。心思这个东西,若是掩在心中,一般人是不知道的。常常,对面走来一个皮肤晒成了大地颜色的老汉,从裤腰上抽出旱烟袋,往地头一蹲,两眼直勾勾地扫向黄豆秧,任烟袋锅噗嗤噗嗤地闪着火星。你知道他在想啥?你又知道他想干啥?
秋风吹熟了黄豆,之后便不知躲哪消遣去了,只剩下黄豆地里的无比闷热。镰刀不住地挥动,汗滴不住地落在大地上,身后的空地越来越敞亮,隔三差五的豆秧堆成了星罗棋布的小岛。
收割黄豆,乡下的妇女老人和半大小孩都可以胜任,而运输则要靠青壮年了。好在车子可以直接下到旱地,不似水稻收割时要一挑一挑沿着细窄的田埂先运到路上。
一头牛,一驾架子车,一把三股铁钗早已停在地头。待豆秧堆凑够几十把的时候,车子被拉进豆地,一铁钗下去,地上一块豆秧堆就被叉起,再一扭身送到架车上。车上的豆秧越码越高,待高过一个成年汉子的头顶时,几人开始用长麻绳把车上的豆秧码得严严实实。套上牛,一人在前面把着车,其他几人在后面推。等架车出了豆地上了马路,推的人回来继续收割,把车的人独自驾车向打谷场上赶去。
在收获黄豆的日子里,原本并不宽敞的马路仿佛一个流水线上的传送带,一头连着黄豆地,一头接着小山脚下的打谷场,每一辆码紧黄豆秧的架子车仿佛就是传送带上的产品。
每一株看似普通的农产品,无不凝聚着勤劳的故乡人大半年的辛苦。每一棵黄豆从被播进土里那一刻起,就要面对无数的自然劫难,唯一守护在它们身边的只有播种它们的故乡人。每一年播下的种子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黄豆,但是,在这片土地上播种的人,却早已似收割后的黄豆秧,换了一茬又一茬。
四
秋收时节,也是我们乡下孩子最幸福最值得回忆的时光之一。且不说山边上开荒地里的芋头个儿大汁水多,也不提田边地头的花生一拔一大窝,单是那大片大片的黄豆地已让我们费尽琢磨。
当黄豆秧子由绿变微黄时已被我们盯在眼里,可是这时绝不会下手。在黄豆完全成熟时,大人都忙着抢收,我们这群孩子帮不上大忙,就提着篾篮下一块刚割完的豆子地,装模作样地来拾豆子。
常常,在篾篮的底刚被黄豆秧铺满时,我们便凑在一处稍平整的地面开始烧豆子了。柴禾是不需找的,茅草和脱落的焦黄的豆子叶要多少有多少,从各自篮子里抽几根缀满豆荚的黄豆秧轻轻铺在柴禾上,划着洋火,再轻轻吹上几口气,慢吞吞的火苗煎熬着我们急切的心情,袅袅盘起的青烟飘荡在围坐成一圈的孩子们的顶上。那时吃烧豆子有一个铁定规矩:不允许爬锅台!谁要是爬了锅台不但豆子吃不上,脸上还要被抹上黑灰。
火越来越旺,烟越来越少,我们的耳边不时听到豆子蹦出豆荚的脆响。火光越来越黯,香味越来越浓,我们脸上的笑意也越来越多。把烧火用的荆条轻轻拨开灰烬,火光终于消散,一堆黑灰里隐着烧得焦黄的豆子。我们不约而同地伸手,向眼前的这堆黑灰里频繁地伸手。黑灰里的烫烫在手指,嘴里豆子的烫烫在舌尖,于是手指是黑的,嘴唇是黑的,唯有眼角有一点点湿润。可是没有一个人因为烫而停手,越烫越捡,边捡边吃,且吃且笑。烧豆子的味道全不同于铁锅内炒熟的那种,又因是新下的豆子,脆中带着一股天然的油香。
烧豆子须等很久,吃豆子几分钟就结束了。有没尽兴的提议再来一锅,立刻得到众人附和。
一场烧豆子之后,提着空篾篮来的我们依旧提着空篾篮回。可是谁又知道,那空荡荡的篾篮里却填满我们烧豆子的欢乐呢?
五
黝黑壮实的三股铁钗将黄豆秧卸到打谷场上,再一钗一钗地将它们均匀地散开。摊得太薄,既占地方也容易让黄豆粒被碾伤,太厚了又压不透。铁钗在黄豆秧的缝隙中起起落落,反复地摆弄着。一个中午的烈日,足以晒干豆秧上的露水,下午两三点便进入打黄豆的程序。
打场这件事对于黄牛来说仿佛是世间最残忍的事。在收割黄豆时,它可以趁着主人不注意,叼几口黄豆秧顶上的青叶子,或是嚼几棵看起来不算太老的豆荚,即使主人看见他们也不会在意,彼时大家都忙着收割、装车,谁会在黄豆地里在意一两颗黄豆秧的去向呢?可是,在打谷场上却完全不同了,黄牛被套上了笼头,只好一边拉着沉重的石磙磨洋工一般慢慢转悠,一边低着头瞅瞅脚下散发着浓郁豆香的黄豆秧。
故乡的人对于打场一向格外重视,非行家里手不可胜任。我们家打场的一般是祖父,他去世之后才轮到父亲。父亲去世之后我常年在外,听母亲说是家乡的叔伯用拖拉机帮忙,有几回别人家忙不过来就花钱雇人打场。
在故乡,无论是牛牵还是拖拉机,打黄豆如打小麦打水稻一样,都离不开石磙子,仿佛豆秧离不开土地一样自然。听说其他地方有用连枷打黄豆的。那么个小东西,一下一下砸在黄豆上,又费力又慢,哪里有磙子碾来得快?
笨拙的石磙不紧不慢地打着圈,在黄豆秧上反复折腾。它经过的地方,原来支楞八煞的家伙们立即变得服服帖帖,偶然有调皮的豆子也会“啪啪”地怪叫几声,最终,与其它黄豆粒一起乖乖地伏在光滑的场上。
脱离了豆荚的黄豆粒大都非常饱满,虽然个头不大,但精气十足。古人说撒豆成兵,我觉得主要还是称赞它们的精神头儿。无数黄豆堆成一堆时,那就是黄灿灿的一片,就是乡下人心中的金山。
起豆秸,推豆粒,扬场,扫去浮物,打场的任务基本完成了。若第二日不用场或天气好,就把黄豆粒堆在场上,晚上安排人看着即可。
看场是个有趣的活儿,但看场的人一定还要有胆量。且不说打谷场四周很多坟地,夜晚一两个人分居在十几个连在一起的场上,中间还隔着一堆堆小山一般的稻草堆豆秸堆。打谷场向南,一层一阶向上升起,直延到小山的顶。窑厂下夜班的人老远打着手电筒。蟋蟀叫醒了月亮,它慢慢攀上小山的脑壳。野鸡在空稻田里咯咯直叫,猫头鹰偶尔也会远远地打趣,搞得看场人头皮发麻。
一床棉被,垫在稻草上面,铁钗就放在手边。关于看场,故乡有很多有趣的传说。据说有一人在看场时,睡梦中感觉有东西咬了自己一下,他以为是蚊虫,连眼也不睁一下,朝手心吐了口唾沫就按向疼痛处,接着继续睡。第二天一早醒来,发现身边有一条蛇已死得直妥妥的。自那以后,故乡人便相信自己的唾沫可以战胜一切虫毒。若有蚊子叮了包,手心一口唾沫是少不了的,在故乡,这个常识连三岁小孩也都知晓。
至于看场时梦见精灵鬼怪的也有不少,但都没有实例。自从播了《聊斋》之后,再去看场总想摸把手电筒别在身上。
看场最恼火的事莫过好不容易熬到半夜,刚打了会儿盹,忽被一阵阴风惊起,紧接着就是劈头盖脸地往下砸雨点。没有准备的只好慌乱地往场中的粮食堆上盖稻草,甚至棉被。事先有准备的则可从容地盖上塑料,再压一层稻草或豆秸。但这样的情况不多见,庄稼收获的季节,乡下人宁肯少吃一口饭,也要摸清天气情况。
六
几天前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中断了对作物的抢收,也让忙碌数日的故乡人稍微喘了口气。然而,人闲了下来,但心一直记挂着地里没有收割完的作物。
大雨来时,大人们把刚碾下来的黄豆装进了蛇皮袋,而豆秸却被草草地码在一边。侥幸逃逸于农民粮袋之外的黄豆粒,趁着温润的雨水和依然热情的阳光,终于有了一次再生的机会。一天,我去打谷场上背柴禾时,发现有人在挑黄豆芽。
踩过泥泞的场角,我赶紧丢下粪箕去掀自家的豆秸堆。孰知第一把就扑了个空,到第二把时我才瞅见一根带着湿气的豆芽。那豆芽也真是急性子,连胞衣都没褪尽就探出了头,一根嫩白的茎顶着两片还没有分开的豆瓣,没有见到阳光的缘故,豆瓣并没有市场上卖的那种苍白的黄,而是微微泛着青。
伸手去挑,我却发现那豆芽透过胞衣居然有少许根须盘上了点泥土。轻轻地捏着这枚小小的豆芽,我心中却生出一点感慨,又多了几分欣喜。这个小小生命,从田地里千辛万苦地长成,再被运到打谷场上,躲过了石磙的碾压,跳出了豆荚,却趁着带着温度的雨水滋润抽出心底的希望。不要小看了白嫩的触角,这既是它们吸收营养的嘴,又是寻找生存之处的脚。
雨后能挑到豆芽有时还要碰运气的。我的眼前立刻浮现出豆芽炒肉丝、凉拌豆芽、豆芽炒细粉。那个年代,家中来客时,待客之物少不得一盘黄豆芽。黄豆营养丰富,听村里的赤脚医生说,每次吃七颗黄豆,是和吃一个鸡蛋的营养价值差不多。长辈们则常举出上世纪困难时期的事情,说人们吃不饱,就水肿,到单位医务室看病,大夫不给开药,人们就想办法搞点黄豆吃,不久病情就好转了。在那个年代,黄豆可是个十分珍贵的东西呢。
现在,一般家庭一年之中吃了多少黄豆,任谁也没法统计。黄豆换的豆油是一家生活必不可少之物,至于黄豆换来的豆腐及零花钱之类更不在少数。冬天,嘴里实在闲得慌,一把炒黄豆也嚼得满屋生香,或是一堆人猫冬闲扯之际,某人“嘭”地放个响屁,边上的人一定嘲笑他黄豆吃多了。至于豆奶、豆浆之类,对于乡下人来说一点也不实惠,所以很少去问津。
接连掀了几处豆秸,均收获或多或少的几根豆芽。左手已塞不下了,就卷起汗衫的前襟,一只手提着汗衫一只手扒拉豆秸。掀完堆角散落的豆秸,我又到附近几处没人看管的豆秸堆下继续寻找。
豆秸堆虽然比散落的豆秸难翻,但是一翻就能寻到一堆的豆芽。这些豆芽好像一窝生出来的一般,根齐齐地扎在一处,芽瓣似伞状分布。我却再顾不得欣赏,一把一把地抓到汗衫里,就连刚从豆荚里才冒出一根小芽的也没放过。
多年之后,我一直怀念着那个美妙的傍晚。小山伏着脑袋,宽敞而又充实的打谷场上,高低不平一座挨着一座的豆秸堆,如浮在大海中的一座座岛屿。此时的我,忽似躲在自家场角一粒不起眼的黄豆粒,焦急地等待着人生中的第一场雨水。
回家的路上,灿烂的晚霞追赶着一个少年的背影,而我的手中正捏着整整一兜的黄豆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