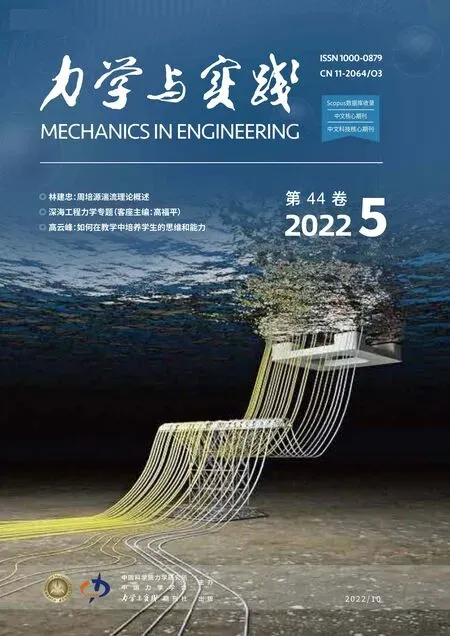往事越卅年
——写在周培源先生诞辰双甲子之际
2022-10-21林建忠
林建忠
(宁波大学机械工程与力学学院,宁波 315210)
(浙江大学航天航空学院,杭州 310027)
1 行为心役
在20世纪70年代的中后期,我们国家迎来了教育和科学的春天。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刊发了有关高校招生重大改革的消息,我国将恢复中断了11年的高考制度。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会上明确指出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为配合当时的形势,报告文学家徐迟接连发表了几篇歌颂科学家的报告文学,其中有关于地质学家李四光的《地质之光》、数学家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植物学家蔡希陶的《生命之树常绿》以及力学家和物理学家周培源的《在湍流的涡漩中》。
《在湍流的涡漩中》发表于1978年4月,该文以1976年10月初粉碎 “四人帮”前夕的时段为背景,描写了时任“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周培源处于政治斗争涡旋中的心理活动。文中将政治斗争洪流中的涡旋与周先生所研究的自然界的湍流穿插叙述,用自然界中紊乱无序、变化莫测的湍动涡旋,烘托出当时政治斗争的复杂与凶险以及当时形势下周先生在大是大非面前的爱憎分明与情操大义。当时有一位福建的上山下乡插队知青被这篇报告文学吸引,文中那一连串自然界的湍动涡旋波谲云诡、目乱睛迷,这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并由此产生对其探究的想法。就在同一年,这位知青参加了高考并被浙江大学录取,在填写专业志愿时,他选择了与湍动涡旋相关的力学专业,在大三选专业方向时又选择了与湍动涡旋更相关的流体力学。在相继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并留浙大工作后,1988年他又报考北京大学周先生的博士研究生,直接进行湍动涡旋的研究,实现了10年前的意愿,这位当年的知青就是我。
三年的读博时间使我有了与周先生近距离接触的机会,因而能感受到周先生大处动中肯綮,小处细致入微的风格。
2 动中肯綮
周先生的湍流研究生涯能抓住问题的关键,把握研究的走向。
2.1 立论有道
在一次与周先生的交谈中,他认为一个新理论的建立必须具备三个基本特征,一是能描述旧理论所能描述的客观现象;二是能描述旧理论所不能描述的客观现象;三是能预见新的客观现象并能被实验证实。周先生湍流理论的建立正是具备了这三个基本特征,基于该理论得到的结果不仅能较好地符合以往理论所给出的结果,如湍流场的平均量和脉动速度二阶统计关联量;而且还能给出以往理论所不能给出的结果,如脉动速度的高阶关联量;同时还能预见新的结果并被实验证实,如均匀各向同性湍流从前期到后期以及一般剪切湍流的湍能和微尺度的衰变规律。
2.2 纲挈目张
周先生在漫长的研究生涯中始终都有明确的目标指向,这种指向贯穿时空,使不同时期的工作浑然一体、丝丝入扣。在湍流研究中,周先生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脉动速度方程和各阶脉动速度关联函数是研究湍流的重要环节,从20世纪30年代末开始基于脉动速度方程建立脉动速度高阶关联函数的方程,到五六十年代寻求与脉动速度相关的涡元解,最后到八九十年代的基于求解脉动速度方程的逐级逼近法的建立,都紧紧围绕这一环节进行。
2.3 数理融合
周先生认为描述湍流场的动力学方程是非线性偏微分方程,直接从数学上求解这些方程很困难,所以他注重将物理规律融入到对湍流场数学方程的求解中,认为要在认清湍流运动本质的基础上,根据物理条件对数学方程予以简化,然后对方程进行求解。周先生在均匀各向同性湍流中提出的相似性理论、准相似性理论到一般湍流场提出的广义准相似性理论,以及将湍流场的物理量分成快变量和慢变量进行分别处理就是典型的例子。
3 细致入微
或许有人会认为周先生这样高龄又身兼数职,日理万机,指导研究生只是挂个名而已,其实不然。周先生对研究生的培养,从论文选题、进度、撰写一直到答辩都会给予具体的指导。
3.1 面授定题
第一次与周先生见面是请教有关学位论文选题的事,只见他鹤发松姿,虽年至耄耋,却精神矍铄。他思路清晰,从湍流研究发展的历史到现状娓娓道来,从湍流研究的模型到方法如数家珍,对提到的公式、数据更是信手拈来。他认为论文的选题应考虑难度、价值性与可行性三要素。周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末曾推导得到了湍流场三阶脉动速度关联方程,该方程中出现的四阶脉动速度关联和其他新未知项使方程不封闭而无法求解,为此他当时提出将四阶脉动速度关联项用三个二阶脉动速度关联乘积之和再乘上一常系数表示,但受限于测量仪器和技术,该系数的值一直无法确定。因此,我的学位论文内容之一就是由实验确定不同自由剪切湍流场中该常数的值。
3.2 三阅文稿
1991年初,我的学位论文初稿完成后交给周先生审阅,他看了一遍后给我来信(图1),信中指出了3个问题,表示准备再看一遍,并约好3月份返校后再当面细谈论文的事。记得讨论我的学位论文初稿是在一个大雪的日子,当时恰逢全国政协会议召开,周先生抽空和我谈了两个多小时,表明了具体的修改意见。后来又再次给我写信(图2),了解论文的修改情况,并嘱咐论文付印之前让他再看一遍。他对论文逐段斟酌,亲手推导验证有关公式,对标点符号、图注、目录和页码都仔细校核。

图1 周先生1991年2月21日的信件

图2 周先生1991年4月3日的信件
3.3 亲临现场
1991年5月30 日是我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的日子,这天一大早周先生专程从北太平庄的住处赶到北京大学力学系大院参加我的答辩。这应该是周先生最后一次参加研究生答辩,参加答辩的还有梁在潮、是勋刚、崔尔杰、陈耀松、魏中磊、凌国灿、黄永念等老师(图3~图5)。答辩过程除了就论文内容展开问答外,还就国内外湍流研究的动态进行了讨论。答辩前,周先生与老师们进行了交流(图6),谈到了北京大学湍流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发展乃至我国流体力学研究的现状。

图3 答辩现场(左起:是勋刚,周培源,梁在潮,崔尔杰,本人)

图4 答辩现场(左起:本人,梁在潮,崔尔杰,魏中磊,陈耀松,周培源)

图5 答辩现场(左起:凌国灿,是勋刚,崔尔杰,周培源,梁在潮)

图6 答辩前的交谈(左起:魏中磊,崔尔杰,周培源,梁在潮)
3.4 抱恙提点
我将博士毕业时,周先生希望我留在北京大学继续湍流的研究,考虑到当时浙大的需要和家庭的情况,我回到了浙大,但仍继续保持联系。当时周先生的逐级逼近法刚提出不久,用该方法不仅可以求出湍流平均量和脉动量的二阶关联函数,还可以便捷地计算高阶脉动速度关联值,避免求解高阶脉动速度关联方程的困难。我回到浙大后将逐级逼近法用于对平面湍尾流场的求解,论文完成后将初稿寄给了周先生,当时他生病住院,病愈返家后回信给我(图7),信中表示很高兴我开展的研究工作,并对后续事宜做了安排。这封信写于他去世前不到1年半的时间。

图7 周先生1992年7月17日的信件
先生已逝,幽思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