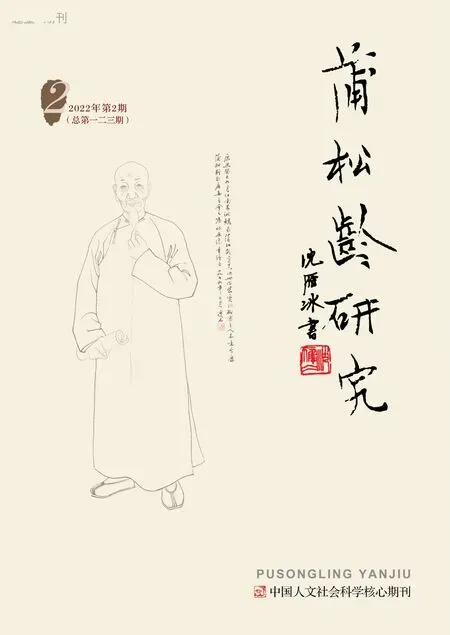《品花宝鉴》中异化的才子佳人模式
2022-10-21李雨薇
李雨薇 舒 乙
(1.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山东 青岛 266580;2.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品花宝鉴》成书于清中叶男风大盛的时期,狎优成为雅好龙阳者的时尚。在此背景下,作者陈森以士族公子梅子玉与男优杜琴言的同性恋情为中心,反映了京师的梨园生活和盛行于社会各阶层的男风现象。在这一时期,虽然发轫于明末,盛行于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有所衰落,但《品花宝鉴》的创作依旧不可避免的受到了影响。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一方面将《品花宝鉴》归类为狭邪小说;另一方面也指出其未脱才子佳人模式之旧套。因为其中的“伶如佳人,客为才子,温情软语,累牍不休”依旧是才子佳人小说的思想内容。但鲁迅也承认其中的“佳人非女”是“他书所未写者”。这涉及到品花宝鉴以士优同性恋情为主体的思想内容。才子佳人模式限制了《品花宝鉴》对于同性恋情的现实描写,但同性恋情在书写的过程中也不断地冲击着才子佳人模式,形成了异化的才子佳人模式。以梅杜恋情为例,梅子玉与杜琴言的恋情从最初的品评色相、一见钟情的才子佳人模式到最后发展为趋于友情双方平等的知己之交,这一变化过程就展示了一种异化的才子佳人模式。
一、性别倒错下的“才子佳人”
才子佳人小说在明末清初大量涌现,其最大特点就是具有明显结构特征的固定模式。尽管这种被曹雪芹称为“千部一腔,千人一面,且终不能不涉淫滥”的小说受到了历代文人的批判,正统文人认为其“淫荡人心,败坏世道”,非正统文人则从小说艺术价值的角度对其进行批判,但它依旧在文坛上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繁荣趋势。从明末清初到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模仿者纷起。尽管《品花宝鉴》是以清代士优之间的同性恋情为题材,但陈森在写作《品花宝鉴》时也不可避免的陷入到才子佳人的小说模式中。
对于贯穿于才子佳人小说中的固定情节模式,许多人都对其做过阐述与界定。鲁迅是最早对才子佳人小说进行系统研究的,他在对才子佳人小说进行了明确界定的基础上,初步阐释了才子佳人小说共同具备的情节特点,“至所叙述,则大率才子佳人之事,而以文雅风流缀其间,功名遇合为之主,始或乖违,终多如意”。范烟桥对此进行了更明确的界定,“大多以才子佳人为经,以功名利禄为纬,且往往‘否极泰来’,以快其意”。在此基础上,郭昌鹤总结了才子佳人模式通备的五个特点“一、有一个真才子必生一个真佳人;二、姻缘是天注的,而结合的形式是不违礼教的真恋爱;三、初会多在后花园或庙宇中;四、好事多磨;五、结果是大团圆”。从历届学者对其的界定可以看出,固定的角色模式、恋情发展的千篇一律以及最后的大圆满结局是才子佳人模式的三个主要特点。由于《品花宝鉴》中有一种奇异的性别倒错,使得其中士优恋情的发展都体现了这三个特点,从而造就了《品花宝鉴》中的士优恋情与才子佳人模式的契合。
首先是名士与才子、优伶与佳人角色的完美契合。在士优的同性恋情中,士子群体作为恋情的一方,他们都是才华横溢的才子,其中多数都家世显贵,这符合一贯对才子的定义;而恋情的另一方优伶虽是男身,他们身上却出现了一种性别倒错现象,表现出更多的女性特质,相对于男性身份而言,他们在小说中的形象反而更加贴近才子佳人模式中的“佳人”形象。
从小说的描写可以看出,《品花宝鉴》中处于被动一方的伶人都被刻意强化女性气质,这具体体现在他们的容貌、姓名和气质性格上。以梅杜恋情中的男优杜琴言为例,子玉第一次看到琴言时,他眼中的琴言是“以玉为骨,以月为魂,以花为情,以珠光宝气为精神”,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女性化的审美描写。作者不仅让琴言在容颜俨若女子,在心理与思想上也赋予了琴言女性的特质。在小说第二十一回中,杜琴言因魏聘才恶意诽谤子玉而心神不安,在短短的半天里他的情绪几度起伏,并且动不动就“滴下泪来”。据统计,这段并不长的情节叙述,杜琴言总计六次落泪。相对于男子身份而言,杜琴言的表现更符合中国古代对于女子“柔弱”“温顺”的要求。
在梅杜恋情中,杜琴言在性别倒错下填补了“佳人”角色的空白,再加上梅子玉的才子身份,从而形成了才子佳人的角色模式,梅杜恋情也顺势陷入了才子佳人小说的惯常套路。梅子玉为才子,杜琴言为佳人,二人一见倾心,继而徐子云以假琴言试探,证明梅子玉非“狭邪人”,二人始正式定交,情投意合。但此后便聚少离多,中又有小人诽谤,遭遇诸多煎熬。细究梅杜恋情的发展过程,其中所体现的依旧是一见钟情、小人挑拨、好事多磨等才子佳人模式的典型特征。
在小说的最后,尽管梅子玉需要遵循传统的伦理道德娶妻生子,但作者为其安排的妻子琼花小姐的面貌却又与杜琴言十分相似。琴言与琼华小姐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组特殊的“镜像”:
皇天可怜子玉一片苦心,因琴言是个男子,虽与子玉有些情分,究竟不能配偶,故将此模样,又生个琼华小姐出来,与琴言上妆时一样,岂不是个奇事?
梅子玉娶面貌酷似琴言的琼华小姐为妻,这也可以看做琼华小姐代替琴言与子玉达成了传统意义上的大团圆结局,从而完成了才子佳人模式上的最后一环。这一情节在另一位名士田春航和男优苏惠芳之间也出现过,田春航在金榜题名后所娶的妻子苏浣兰不仅与苏惠芳有“九分相似”,连姓氏都一样。这种“镜像”在本质上是小说中男旦们性别倒错的隐喻,小姐们是男旦们身上女性特质的具现化。
在以梅杜恋情为中心的名士群体与男旦群体的恋情中,男旦们身上体现的性别倒错贯穿于恋情发展的始终,引导着小说情节向才子佳人模式发展。这种奇异的性别倒错并不是偶然出现的,而是作者陈森精心设定的,对此他甚至借小说中的人物之口直接发声:
只有相公如时花却非草木,如美玉不假铅华,如皎月纤云,却又可接可玩,如奇书名画,却又能羽而非言,如极精极美的玩好,却又有千娇百媚的变态出来。
从作者的叙述中可以看到,他试图用一种唯美主义的论调调和男女性别的天然差异,在某种程度上甚至颠覆了传统的伦理观。但这种审美主义的论调,本质上依旧体现着男权中心主义的思想,是将男旦与美人和花草放在一起,用一种鉴赏的态度来进行品评和玩味。《品花宝鉴》中的“花”指的是在作者有意的性别倒错下,如花一般美丽的名旦,而“品”则指的是名士们对男旦物化后的品评鉴赏。
在传统的情爱结构中,只有女性处于被把玩鉴赏的地位,进而成为男性情欲寄存的对象。因此在士优交往的过程中,那些被迫承担着女性角色的男旦,是被视为与女人并列的第二性,逃脱不了被窥视,被展示的命运。男旦们的男性身份被忽略,其所扮演的女性化角色被追捧,他们展示出的女性化魅力甚至成为了男男恋情中激发情欲的关键性要素。即使“风骨高绝”的梅子玉,初见琴言时的动心,也是由于其“惊艳绝伦”的女性化容颜。这种对于男旦身上女性特质的追求,展现着士子们在同性恋情中对于感官刺激下“欲”的追求。
二、不稳定的“佳人”角色与“爱情”的消失
《品花宝鉴》中的士优恋情虽然没有脱离才子佳人的模式,但这其中也出现了一定的僭越。一方面,小说中的“佳人”角色并不是由男旦们的性别决定的,而是由其职业的特殊性及其低下的社会地位造成的,当男旦们的身份地位出现变化时,“佳人”的角色也就呈现出消解的状态;另一方面,如果说才子佳人模式下的小说结局是“爱情的胜利”,那《品花宝鉴》的最后结局则表现的是爱情的消失,或者说爱情在潜移默化之间转变为友情。
关于佳人角色的消解,可以梅杜恋情中的杜琴言身份变化为例。杜琴言的身份变化经历了从常人到贱民,再从贱民到常人,最后从凡人到绅耆子弟的三重变化。
从常人到贱民的阶段,指的是琴言因父母双亡,被其婶婶卖入梨园,琴言从此由常人变为贱民,沦落到社会的最底层。在梨园从业时,琴言与梅子玉相恋。但在梅杜恋情的初始,琴言是被卖身的男旦,在性别关系和社会结构中都处于被支配的低下地位;而梅子玉则是出身官宦人家的名门子弟,且满腹经纶,不仅在等级制度中占据上层地位,而且在性别关系结构中占有霸权地位,这就导致了在才子佳人模式下的梅杜恋情中,作为主动方的梅子玉占据了才子的角色,作为被动方的琴言被迫承担起“佳人”的角色。从贱民到常人的转变指的是徐子云为琴言赎身,琴言脱离梨园从而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和等级可变性。最后,琴言实现社会等级的提升,从常人到缙绅子弟的转变则是通过扶乩认父的这一事件来实现的。怡园扶乩,上仙断出琴言与屈道翁有前世的父女渊源,徐子云又进行说和,琴言拜屈道翁为义父,改名屈勤先。此事之后,琴言也成为官宦子弟。此时,杜琴言与梅子玉社会等级身份已基本相同,这使得梅杜二人在恋情中的角色模式也趋于平等,在这种情况下,琴言在梅杜恋情中所承担的女性化的“佳人”角色也就转变为更平等纯挚的“知己”角色。
从杜琴言到屈勤先的变化过程反映的正是杜琴言社会等级地位的变化,这种变化导致了他在性别结构关系中的变化。杜琴言所承担的“佳人”角色就在这种变化中逐步的消解了。
“佳人”角色在恋情中的不稳定性,体现出《品花宝鉴》对于才子佳人模式的僭越,除此之外,这种僭越还体现在对于士优恋情大圆满结局的处理上。
在一般的才子佳人模式中,主人公们都会为爱情而奋力抗争,最后达成“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大圆满结局。但以梅杜恋情为代表的士优恋情却呈现出“爱情消失”的结局。当梅子玉考中翰林进入仕途彻底地融入正统的人生轨道,他与杜琴言之间的同性恋情就开始被逐渐地消解、淡化,这种同性恋情逐渐向着友情转变。在杜琴言成为屈道翁的义子后,他又辗转变成梅子玉的伴读,子玉本人也有了品貌双全的妻室。梅杜二人之间很明显隐藏着爱情的种子,但当这种爱情受到传统的伦理道德和婚姻制度的制约时,它在潜移默化之中转变为友情。
梅杜恋情的变化体现着作者贯穿于小说中的“主情克欲”的原则。“情”指的是符合封建伦理道德的情,当同性恋情与士人的道德追求相违背时,它便转化为君子之交的知己之情。需要克制的“欲”,一方面指的是肉欲,另一方面指的是士人受男旦们女性化特质的吸引而衍生出的情欲。在梅杜恋情的初期,子玉还受到琴言容貌的吸引,用一种女性化的视角看待琴言,称赞其温顺柔弱、贞洁自守的品质;但在梅杜恋情的后期,作者通过一次扶乩认父,使得琴言进入士族的行列,梅杜二人的关系由才子佳人的恋情变为君子之交的知己之情。在清代社会,纵欲思想蓬勃发展,男风的盛行对传统的家庭伦理道德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品花宝鉴》中的梅杜恋情从掺杂有情欲因素的同性恋情发展为更为平等纯洁的知己之情,实际上就是儒家“克己复礼”思想的体现,反映了作者思想中的儒学痕迹。
三、情与欲的冲突———作者矛盾的书写状态
在小说中,梅杜二人的相恋情节作为小说中的主线,具有串联起其他名士与男旦们恋情的作用,集中体现了《品花宝鉴》士优恋情的特点。因此,对梅杜恋情进行分析,可以透析作者对于《品花宝鉴》中士优恋情的书写心态。
从梅杜恋情展现的异化的才子佳人模式中可以看到,作者在书写《品花宝鉴》的士优恋情时体现出一种矛盾的状态,这种矛盾主要集中在“情”与“欲”的冲突上。作者对于“欲”的渴求,主要体现在小说花费大量笔墨来实现男旦们的性别倒错,对于男旦女性化特质的大力刻画与追捧。在将男旦转换为“佳人”后,其女性化的容貌和温顺的特质使得人们获得视觉上的感官刺激与男性霸权心理的满足,进而成为投射情欲的载体。而作者所追求的“情”,在小说的第一回就可见一斑。他将缙绅子弟和名旦分为十种,皆是一个情字,最推崇的就是梅杜二人的“情中正”与“情中至”。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及:“《品花宝鉴》中的人物,大抵实有,就其姓名而言,推之可知。惟梅杜二人皆假设,字以‘玉’与‘言’,则‘寓言’之谓,盖著者以为高绝,而已无人足供影射者矣。”这表明梅杜二人的恋情是作为一种寓言存在的,寄寓着作者理想化的同性恋情模式。这种理想化的同性恋情,作者在小说的最后将其转化为一种符合礼教与伦理道德的“恋情”模式,细究这种恋情的本质,可以看到,比起恋情,作者所追求的这种情实际上更偏向于同性之间互相欣赏的知己之情,而作者在这种对于同性恋情的处理过程中无意间实现了对于才子佳人模式的僭越。一方面,作者追求符合礼教伦理的同性恋情;另一方面,作者又投注大量笔墨对于男旦的女性特质进行重复的描写与细致的刻画,暴露了其对于美色带来的感官刺激的恋恋不舍,这两者体现出作者矛盾的创作心态。
这种矛盾的创作心态是由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清代的狎优风气和“主情”“重情”的文艺创作思潮都对作者的创作产生了影响。而作为主流的儒家文化对于男风的态度以及中国男风传统所独具的一些特点也影响了作者对于士优恋情的态度。
中国古代的男风传统源远流长,受时代的更替和地域的差异的影响,呈现出盛衰变化的迹象。在明清之际,中国古代的男风文化达到了顶峰。相对于前代而言,清代男风呈现出的最大的特点就是狎优风气的盛行。此时的士人们多好歌童而不好名妓。咸同年间的士人黄均宰在《金壶遁墨》中曾描绘过这种景象:
京师宴集,非优伶不欢,而甚鄙女妓。士有出入妓馆者,众皆讪之。结纳雏伶,则扬扬得意,自鸣于人,以为某郎负盛名,乃独厚我。
以描写士优恋情为主要内容的《品花宝鉴》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清代狎优风气的兴起,需要从明末社会强调个性解放与肯定人欲的风潮中追溯其源流。在晚明时期,王阳明的心学兴起,反对宋明理学对人性的戕害,强调人欲和个性解放。但当文化思潮过度强调人欲时,整个社会都弥漫着纵欲的气息,人们道德观念开放的同时,性爱观也呈现出极其复杂的状态,这种背景下男风应运兴起。晚明男风的兴盛一直延续到清末。同时由于明清二代禁止官吏狎妓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官宦们不得不在男性优僮身上寻找替代性出路。随着清代戏曲的发展,大量伶人自乾隆时期开始汇聚京城。在当时的男风背景下,戏剧的兴盛带动了狎优文化的兴起。男旦们所独有的“儿女英雄一身兼”“名士倾城合一身”雌雄同体的性质受到了当时好男风人士的追捧。对此,梁绍壬有诗为证:“软红十丈春风酣,不重美女重美男。婉转歌喉袅金缕,美男妆成如美女。”但在受追捧的同时,戏子由于自身卑贱的社会地位和职业的娱乐性质,也常常成为身份比自己高的观众的狎玩对象,甚至被以“倡优”待之。
士人们对于男风的追捧,展现的是一种恣意纵欲的心态。在狎优风气盛行的男风背景下,男旦们由于其出众的容貌与低贱的社会地位从而成为士子们情欲寄托的对象。而陈森在写作《品花宝鉴》时也不可避免的受到了这一时代风气的影响。
关于陈森的重情思想,小说的第一回就有具体的体现,“事不出于理之所无,人尽于情之所有”“先将搢绅中的子弟分作十种,皆是一个‘情’字”“再将梨园中名旦分作十种,也是一个‘情’字”。在小说的初始,作者便将“情”作为评判标准,而在小说的最后作者尽力摈除了梅杜恋情中的狎昵成分,使其变为“至纯”“至正”的知己之情。陈森在小说中始终体现着对于“情”的探索与追求。这种创作思想一定程度上受当时“主情”“重情”的文艺创作思潮的影响。清初在诗文领域出现了性灵文学思潮。性灵派文学要求诗人在写作诗歌时要具有“真性情”。这一理论在达到极盛之后,也影响了小说的创作,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提及《品花宝鉴》的思想内容深受《红楼梦》的影响,而这一时期出现的峰巅之作《红楼梦》,所秉持的正是“大旨言情”的创作主张。无论陈森所追求的“情”与性灵派文学所追求的“情”是否一致,他“重情”的理念贯彻于小说的始终,在小说中借梅杜恋情展现了自己理想中的同性恋情。
除了时代背景的影响外,作者矛盾的创作心态与还与中国古代男风的特点以及儒家主流文化对于男风的态度有极大关系。
施晔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同性恋书写研究》中对中国古代男风的特点进行了概括,认为:
中国古代同性恋者之间存在着固定、鲜明的权力架构,年长、富有、权高者充当主动方,反之则为被动方,绝少角色互换的例子。中国的男风组合大多是异性恋组合的戏拟,是一种‘亚异性恋’,是男尊女卑现象在男人内部的复制,同性爱不过是异性爱的模仿,缺乏独特性和自足性。
而陈森在处理士优恋情时,不自觉地将被极力强化了女性特质的男旦们作为士子们情欲寄托的对象,正是基于中国古代同性恋者之间存在的固定、鲜明的权力架构。在士优恋情中,士子们是霸权男性的代表,是主动方;男旦们则处于被动方的地位,是被雌化了的男性,性特权不仅存在于男性对女性中,还存在于霸权男性对被雌化的男性中。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士子们是将男旦们视为与女子无异的情欲寄托对象。
《品花宝鉴》以士优恋情为题材,一方面对“用情守礼的君子”与“洁身自好的优伶”之间的同性恋情极力描摹,表现出赞赏推崇的态度;另一方面,小说的结局却又极力淡化同性恋情的痕迹,将士优恋情转变为更符合传统礼教的知己之情。这一矛盾的表现形式也与占据主流地位的儒家文化密切相关。
儒家主流文化对男风一直持一种温和的反对态度,这主要归因于儒家文化中始终贯彻的中庸之道。子曰:“中庸之为德也,甚至已乎!民鲜久矣。”儒家的中庸之道具有包容、理性、稳健的特色,强调宽纳包容、和而不同。施晔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同性恋书写研究》中阐述了儒家的中庸之道对于中国古代男风的影响:
首先,儒家主流文化这种接近中立的温和反对态度,为同性恋者创造了一个宽松的生存环境。同时,中国古代同性恋也以中庸之道行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摒弃完全逆转的性取向,不排斥异性恋,在性生活中阴阳同体、双性皆可。
儒家主流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男风温和的态度,是陈森对于士优同性恋情推崇赞赏的思想基础。但由于社会和宗族的压力,绝对的同性恋在中国古代没有生存空间。《品花宝鉴》中也只是将同性恋情作为夫妻敦伦、男女性爱的补充。因此,在小说最后,作者让梅子玉、田春航等士人在功成名就后娶妻生子,男旦们也出了“旦党”,以普通人的身份做起了生意,士优之间的同性恋情向纯洁的友情转变。一方面可以认为作者所追求的理想的同性恋情正是这种纯洁无欲念的感情,但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作者在小说中所安排的结局也体现着对现实伦理道德的妥协。儒家主流文化对于男风所持的温和的反对态度极大地影响了陈森的创作观。
《品花宝鉴》异化的才子佳人模式反映了陈森在小说书写过程中的思想矛盾。他在《品花宝鉴》中力图呈现一种用情守礼的同性恋情,但又不可避免的受清代男风文化中最典型的狎优风气和女性化审美影响。在追求纯挚的“情”的过程中,小说中的士优恋情呈现出一种雅正的君子之交,体现着儒家克己复礼的思想。然而,作者又难以割舍美色下“欲”的感官刺激,不断强化小说中男伶们的女性特质,用一种奇妙的性别倒错,消解男旦们的男性特质,将其转化为可供士子们进行情欲投射的“第二性”。陈森的这种思想矛盾既受时代风气的影响,也受根植于其思想中的儒家文化的影响。“透过情欲冲突的表层,异化的才子佳人模式中隐藏的是小说作者面对男色时既躲闪又渴望的矛盾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