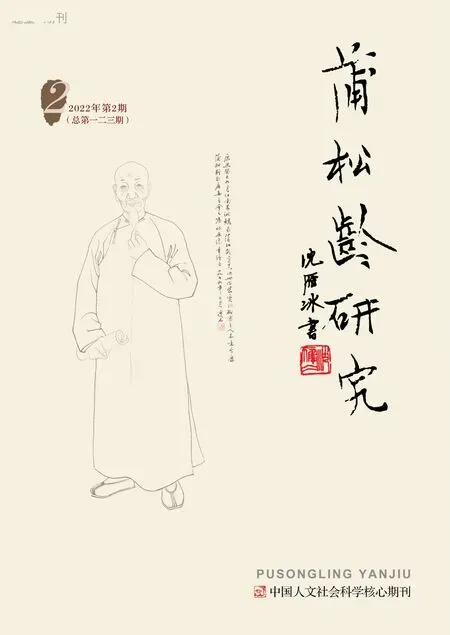《聊斋志异》在西班牙语世界的翻译与传播
2022-10-21李翠蓉赵智利
李翠蓉 赵智利
(贵州财经大学 外语学院拉美研究中心,贵州 贵阳 550025)
一、《聊斋志异》的西译版图
根据罗一凡《创造中国怪异:Rafael de Rojas y Román首译〈聊斋志异〉西班牙语译本研究》一文,《聊斋志异》的首个西译本为西班牙翻译家Rafael de Rojas y Román 所译《志异故事》(Cuentos extraños,1941),距今,西译史已达八十年。已有数十个译本,包括改编画册、选译本、节译本;英语、法语、德语等欧洲语言转译本与汉语直译本交互,西班牙语世界译入与中国译出并进。
(一)西班牙持续译入
西班牙对《聊斋志异》的翻译始于巴塞罗那,Rafael de Rojas y Román翻译的插图版《志异故事》包括10篇:《龙飞相公》《画壁》《西湖主》《劳山道士》《书痴》《宦娘》《聂小倩》《汪士秀》《红玉》以及《恒娘》,26幅插图,由加泰罗尼亚20世纪最重要的插图画家Joan d’Ivori绘制。同年,也在巴塞罗那,佚名译者翻译彩色插图西译本《中国故事》(Cuentos chinos),选译《宦娘》与《书痴》等5篇,这个版本1951年再版。
20世纪80年代共4个译本:1个选译与3个节译,均在马德里出版。选译本为Isabel Cardona与博尔赫斯从英语转译的《报恩虎》(El invitado tigre,1985),共16篇,其中14篇选自《聊斋志异》;第一个节译本是Carmen Salvador转译《罗刹海市》(Los fantasmas del mar,1982),选译 4篇;第二个节译本是Laura A.Rovetta与Laureano Ramírez从汉语直译的《聊斋志异》(Cuentos de Liaozhai,1984);第三个节译本是 Kim En-Ching 与 Ku Song-Keng 从汉语直译的《聊斋志异:真正的中国经典故事》(Extraños cuentos de Liao Chai:auténticos y clásicos cuentos chinos,1987)。
Rovetta为乌拉圭籍专业译者,除母语西班牙文之外,还通晓中文、英文及法文,曾任职于墨西哥驻华使馆,口、笔译经验丰富。Ramírez为西班牙著名汉学家,目前在西班牙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翻译学院任教,译作丰富且皆为经典文本。他们合译的《聊斋志异》遵循乾隆十六年的铸雪斋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版;译本的插画则取自1866年的广百宋斋版本;选译105篇,附引言、脚注与三篇附录:科举制度、中央政府及地方的行政工作分配与中国传统文学作品。2004年5月与10月重印两次。
译者将中国古典故事的发展(《聊斋志异》之前)分为四个阶段:产生、童年、成熟与没落。“产生”对应秦汉,寓言与传说极为丰富,故事创作基于现实、寓言、传说,融入想象,甚至夸张元素;“童年”对应东汉北魏六朝,故事创作范围扩大,普通大众以及非正统文人都融入其中,鬼魅、超自然事件也被纳入其中;“成熟”对应唐朝,故事创作的文学含金量逐渐增加,唐传奇篇幅增长,描述更加细化,结构更加缜密,语言更加精良;宋明时期对应“没落”阶段,因为话本对古典故事的冲击,唐传奇故事主题的无限重复,导致中国古典故事的衰退。译者在此基础上定位《聊斋志异》,认为它是“短篇故事”的扛鼎之作,原因有二:一是蒲松龄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描绘:封建主义最后阶段的社会冲突与明清过渡阶段的社会动荡、变革。二是从蒲松龄个人的角度阐述,他作为一个社会个体,作品反映了他个人的生活状态,他也通过文学来实现了宣泄与倾诉。
译者清楚地交代翻译策略以流畅易懂为原则,根据古孟玄在《〈聊斋志异〉西译本与中西文化差异》中的论述,此译本是从沟通的角度去翻译,“西方文化在文字游戏、单位词、神话、传说、文化遗产等方面,和中华文化落差极大,《聊斋志异》译者 Rovetta及 Ramírez灵活应用西语读者的文化背景和习惯,搭起两文化间的沟通平台”。
20世纪90年代,西班牙有一个节译本、一个选译本。1992年,Imelda Huang Wang与Enrique P.Gatón从汉语直译《一位爱艺者的神奇故事》(Historias fantásticas de un diletante),选译 31 篇《聊斋志异》故事,在马德里出版;德国著名传教士汉学家卫礼贤著有《中国故事》(Chinesische Märchen),1958年在慕尼黑出版。此译本由Paz Ortega Montes转译为西语:《中国故事I——〈柳毅传〉与其他中国神话传说》(Cuentos chinos I.La princesa repudiada y otros relatos de la mitología china,1997)与《中国故事II——〈婴宁或笑美人〉与其他中国民间故事与传奇故事》(Cuentos chinos II.Yingning o la belleza sonriente y otros cuentos populares y fantásticos,1998),在巴塞罗那出版,共 100 个故事,选译有《劳山道士》《种梨》《画皮》《娇娜》《小猎犬》《蛰龙》《白莲教》等 15篇聊斋故事。这个译本在西语世界影响颇大,在西班牙分集、合集、选集反复出版,2009年、2012年在巴塞罗那合集再版;2019年在马德里分四集出版;2020年在马德里节选再版。
2003 年,RolandoSánchez-Mejías从汉语直译《中国神奇故事选集》(Antología del cuento chino maravilloso),选入部分《聊斋志异》故事,在巴塞罗那出版。2009年,Clara Alonso从英语转译《中国微型小说》,选译41篇微型小说,以现代小说为主,但选译3个古典篇目,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蒲松龄的《申氏》与干宝的《李寄斩蛇》,在马德里出版。
(二)西班牙语美洲分散译入
相对于西班牙的持续译入,西班牙语美洲对《聊斋志异》的译入则较为分散,体现在时间上的断代与空间上的零零星星。从时间上来看,早在20世纪40年代,西语美洲便产生相关选译本,但此后直到21世纪,才重新出现新的译本;空间上则主要是阿根廷与墨西哥有相关译入文本。
西班牙著名汉学家黄玛赛(Marcela de Juan,1905-1981)是首位从汉语直译中国古典文学的译者,她的译作丰富,译风精准,在西语世界影响深远。1948年,黄玛赛译《中国古代传统故事》(Cuentos chinos de tradición antigua),在阿根廷出版,选译宋元明清四个朝代共9个故事,《聊斋志异》最为突出,共4篇:《罗刹海市》《促织》《成仙》《娇娜》。黄玛赛简述蒲松龄的生平、作品以及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与《聊斋志异》的重要地位,“《聊斋志异》毫无疑问是最被中国人珍视的书,也是认识、了解中国民俗习惯与生活方式的最佳向导”。
黄玛赛的翻译质量是值得信赖的,但她也阐述了自己认为翻译过程中所丢失的一些元素:“显然,它们(聊斋故事)风格迥异且语言类型丰富,古文,白话文,俗语甚至口语尽囊其中,遗憾的是,这些细节在翻译的过程中已经遗失。”这个译本颇受欢迎,首版是1948年3月31日出版,在同年的9月18日就又刊行了第二版,相隔时间还不到半年。而黄玛赛对《聊斋志异》的偏爱也在后续的译作中得到沿承,比如,1954年黄玛赛再译《〈古镜记〉与其他中国故事》(El espejo antiguo y otros cuentos chinos),共 8个故事,再次选译《促织》《娇娜》与《罗刹海市》三篇。
《中国古代传统故事》后,西语美洲对《聊斋志异》的译入开始断代,直到21世纪,才又出现新的译本。墨西哥学院的亚非研究中心成立于上个世纪60年代,是西语美洲成立时间最早、研究成果最多、学术水准最高的有关中国的研究中心。他们的西班牙语学术期刊《亚非研究》(Estudios de Asia y áfrica)1966年1月始发,至今,已不间断发行近200期。期刊的主要板块为书评、论文与译作。《亚非研究》2012年第1期载《娇娜》(Jiao Na)西语译文,Radina Dimitrova与Pan Lien-Tan从汉语直译。2014年第2期两位译者再译三篇:《瑞云》(Ruiyun)、《书痴》(El lector obsesionado)与《丑狐》(La zorra fea)。
关于《聊斋志异》最为新近的一个节译本在阿根廷出版。2014年,Julio Miranda译《中国魔幻故事》(Cuentos mágicos chinos),共 18篇,全部选自《聊斋志异》,如《洞庭主》《瑞云》《劳山道士》《书痴》《恒娘》《林四娘》与《红玉》等,此译本无前言,无注释,无附录,也未点名蒲松龄与《聊斋志异》这两个关键词,大概是译者希望读者更多地从文学欣赏的角度去看待这部故事集。
(三)中国集中译出
中国对《聊斋志异》的译出呈现“集中”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出版社集中,主要是外文出版社与朝华出版社;二是均从属于某一些出版系列。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就注重向世界表达自我,开启主动译出的历程,早期的译介以文学作品改编为主,连环画、儿童画册最为常见,民间故事与经典文学作品是改编的重要对象。从西班牙语译本来观照,《西游记》画册最多,《聊斋志异》次之。20世纪80年代,外文出版社与朝华出版社发行西语版彩图画册共8本:《仙人岛》《白练秋》《红玉》《劳山道士》《阿宝》《促织》《莲花公主》《婴宁》。装帧精良、绘图优美、故事简洁。画册署名编者、绘画者、装帧设计者,但并无译者,这在一定程度上无法保障翻译质量,翻译水平且不谈,拼写错误就常见,比如,在《婴宁》的封里,“Extran os Cuentos de Liaozhai”中的“Extranños”就拼写错误。
《大中华文库》致力于系统、准确地将中华民族的文化经典译成外文,编辑出版,介绍给全世界,1994年开启,选择110种图书,是一项国家层面推动的大型系统出版工程。得到季羡林、任继愈、叶水夫、袁行霈、丁往道、韩素音等多位学者和翻译家的支持与指导,已有外文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等18家出版社参与该项目图书的编辑与出版工作。《大中华文库》涉及两种类型的翻译,一种是语内翻译,即将古代汉语翻译成现代汉语;另一种是语际翻译,即将汉语翻译为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德语、俄语、阿拉伯语、日语和朝鲜语共8种外语。其中,汉语——西班牙语对照本的出版计划分三批,共25册,《聊斋志异》属于第二批。
2014年,《大中华文库》系列的西语版《聊斋志异选》(Selecciones de Extrañ os Cuentos del Estudio Liaozhai),外文出版社发行,译者为古巴翻译家María Teresa Ortega与Olga Marta Pérez,采用张友鹤辑校本,共选译216个故事,汉西对照,分四册,近2000页。前言称“《聊斋志异》成为一部驰想幻域而映射人间、讽喻现实、表现世情的‘孤愤之书’”。并将这些故事大致分为两类:“这些多姿多彩的奇幻表意之作,又可大致分为两类:美情小说与讽喻小说。前者歌赞人性的善、人情的美,特别是爱情之美;后者针砭社会的丑,世态的恶,特别是官场的丑和恶。”
二、《聊斋志异》的西译风格
在横向地大致勾勒《聊斋志异》的西译版图之后,纵深地通过对比译本来观照译风。《娇娜》是各个译本选译较多的篇目,以此为例。袁行霈《中国文学史》认为《娇娜》带有对两性关系的思索性内涵,“玩味小说情节和夫子自道,可以认为作者是用了并不确当的语言,表达了他感觉到的一个人生问题:得到‘艳妻’不算美满,更重要的是‘腻友’般的心灵、精神上的契合,不言而喻,美满应是两者的统一”。袁行霈认为蒲松龄在《娇娜》中描述了理想的男女关系,或者是男人对女人的完美幻想:“艳妻”与“腻友”统一,但他点到即止,并未深入探讨。
在《〈聊斋志异·娇娜〉中的第四种关系》中,叶润青立足文本分析,体悟作者意图,定位孔生与娇娜之间是第四种关系,即“腻友”关系,他认为,在两性关系的范畴中,文学中的描绘不外乎三种主要类型:纯洁至真的友情、灵肉结合的爱情和血肉相连的亲情。“这种关系可以说是前三种关系的交叉、临界和边缘,既复杂又纯粹。而维系第四种关系的重心是两人之间心心相照的‘知契’感应。因此这种情愫的微妙、多义和潜在的力量赋予了其独特的美学内涵与永恒的审美价值”。
其实,《娇娜》中关于两性关系的总述主要体现在最后的“异史氏曰”:“余于孔生,不羡其得艳妻,而羡其得腻友也。观其容可以忘饥,听其声可以解颐,得此良友,时一谈宴,则‘色授神与’,尤胜于‘颠倒衣裳’矣。”我们比较三个汉语直译本对此段的翻译:
Rovetta译本(2004):
En lo que a mí respecta,admiro más a la maravillosa amiga de Kong que a su bella mujer.Dicen que a uno se le quitaba el hambre nada más verla y que oír su voz era una bendición para los oídos.No me cabe duda de que charlar y comer en compa ía de una amiga así,sintiéndose compenetrado en todo,supone un placer mucho mayor que el mantener con ella unas simples relaciones carnales!
Dimitrova译本(2012):
No envidio a Kong Xueli por tener una bella esposa,sino por encontrar una cordial amiga.Al ver la cara de un amigo,uno se olvida del hambre;al escuchar su voz,la sonrisa sale sola en el rostro.Al tener un amigo tan próximo con quien de vez en cuando conversar o comer juntos,el espíritu se regocija frente a la faz querida!Y aquellos líos que acaban con la ropa de ambos en desorden ni de lejos se pueden comparar con la verdadera amistad.
Ortega译本(2014):
Lo que admiro del erudito Kong no es que se casara con una mujer bella,sino que también tuviera un buen amigo cuyo rostro pudiera hacerle olvidar el hambre y cuya voz le trajera dicha y deleite.Tener un buen amigo como ése con quien hablar y comer y beber significa un flujo y una fusión en la esfera espiritual.Una amistad tal supera al amor entre esposo y esposa.
首先,观照“得艳妻”与“得腻友”两者之间的关系。虽然从表面看两者是“非此即彼”的并列关系,但根据后文的“色授”可知,“腻友”是在“艳妻”的基础上增进了“魂与”,即“腻友”首先也是美丽的,其次还是能够成为知己,类似于现代的“红颜知己”,首先要保证颜值。所以,从内涵上讲两者是递进的。观照三个译本的翻译:Rovetta译本译作递进关系,相比艳妻,更加“倾慕”腻友,递进关系恰当,但直接“倾慕”,而不是羡慕孔生“得”,意义的准确度上有所欠缺;Dimitrova译本与原文亦步亦趋,用的是“不是……而是……”的并列关系;Ortega译本用了强调的并列关系:“我羡慕孔生的不是……,而是……。”
其次,我们观照“腻友”的翻译,“腻友”在文中是有具体指射的,即娇娜,即使将孔生与娇娜的关系抽象出来,也是独特的男女关系,在西语中仍然应该用女性朋友“amiga”,Rovetta译本在整段中均用“amiga”,翻译贴切;Dimitrova译本在“而羡其得腻友也”采用“amiga”,但后文所有关于“腻友”的指射都抽象为“朋友”(amigo),突出友情,忽略男女之间的特殊关系;Ortega更是从头至尾都用“朋友”(amigo),将“第四种关系”狭隘地解读为友情。
三、《聊斋志异》在西语世界的传播缘由
由上可知,《聊斋志异》西译本众多,蒲松龄在西语世界也颇有影响。2001年,José Manuel Pedrosa Bartolomé作《口述与书写——亚瑟王传奇与蒲松龄对博尔赫斯与胡安·戈伊蒂索罗的影响与交汇》(Oralidad y escritura:Influencias y convergencias〈de la literatura artúrica y Pu Songling a Borges y a Juan Goytisolo〉),论述“口述”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但以西方的文论、作家为主,涉及蒲松龄之处,仅短短三段。引用《聊斋自志》:“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编。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夥。”借此分析《聊斋志异》的“口述”源头,但并未将蒲松龄和两位作家联系起来,所以,更多地是借作一个噱头,但也能侧面揭示蒲松龄与《聊斋志异》在西班牙语世界的名气。
博尔赫斯在《报恩虎》(1985)西译本的前言指出:“《聊斋志异》在中国的地位就等同于《一千零一夜》在西方的地位。”这个比较看似无意,其实道明了《聊斋志异》在西语世界广泛传播的两个原因:一是灵活的短篇形式;二是无穷想象力。短篇故事是西方文学的重要形式之一,西班牙语文学也不例外,古有《卢卡诺尔伯爵》,与蒲松龄时代接近的有Juan Pérez de Montalbán,Chen Xinyi在《中国文学与西班牙文学的比较研究:17世纪的胡安·佩雷斯·德·蒙塔尔班与蒲松龄的短篇故事》(Estudio Comparativo entre la literatura española y la china:relatos cortos del siglo XVII de Juan Pérez de Montalbán y Pu Songling)中将两者作比,但研究并不深入也不具体,不过作者在文章中提及自己的博士论文是涉猎这两个作家的比较研究,有待以后深入梳理。西班牙语美洲近现代文学的短篇故事佳作更是数不胜数:Juan Rulfo《烈火平原》、Horacio Quiroga《爱情、疯狂和死亡的故事》、Juan José Arlt《寓言集》等,西语读者对短篇故事的接受度高。从翻译实践来看,短篇故事灵活,易于选择,从上述译入译出的作品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到,《聊斋志异》各类西译本从一个、几个、十几个再到百来个、两百余个的选译都具有可操作性。
《聊斋志异》承志怪与传奇,袁行霈论道:“《聊斋志异》……就文体来说,其中有简约记述奇闻异事如同六朝志怪小说的短章,也有故事委婉、记述曲微如同唐人传奇的篇章。……《聊斋志异》里绝大部分篇章叙写的是神仙狐鬼精魅故事,有的是人入幻境幻域,有的是异类化入人间,也有人、物互变的内容,具有超现实的虚幻性、奇异性,即便是写现实生活的篇章,如《张诚》《田七郎》《王桂庵》等,也往往添加些虚幻之笔,在现实人生的图画中涂抹上奇异的色彩。”[
《聊斋志异》的无穷想象力是它在西语世界受到青睐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仅从书名的翻译便可见一二,有一些译本会删减“聊斋”,或者直接用音译,但“异”字从来都是译者刻意突显的重要因素:黄玛赛用了“extraño”;Imelda Huang Wang 用了“fantástico”;Rolando Sánchez-Mejías 用了“maravilloso”;Julio Miranda用了“mágicos”,均突出了《聊斋志异》的无垠想象力。
不光是题目,在各个译本的前言中,也不无突出作品想象力的。《聊斋志异选》就在前言中厘清了关于女性人物塑造的无穷想象力:“蒲松龄笔下的狐女形象甚多,婴宁、青凤、娇娜、小翠、莲香、青梅、凤仙、红玉……,鬼女(连琐、宦娘、晚霞、小谢、巧娘、聂小倩、伍秋月、公孙九娘、辛十四娘)、花女(葛巾、香玉、黄英、荷花三娘子)、仙女(嫦娥、翩翩、蕙芳、芸萝公主)、鸟女(竹青、阿英)、蜂女(绿衣女)、龙女(织成)、蛙女(十娘)、鼠女(阿纤)、獐女(花姑子)、扬子鳄女(西湖主)、白鳍豚女(白秋练)……”
其实,想象力丰富只是表层,内里是幻象、幻境的叙述方式,不少评论都认为蒲松龄营造的世界,幻象与真实界限淡化,两者交叉互融。Rovetta就认为,“当他给我们讲述怪物或狐女时,并不将其作为一种文学手段,而是真实地相信它们的存在”。其实,对于这种用“平常口吻”叙述“奇像”的独特叙事方式,并非蒲松龄独有。善于讲故事的拉美作家也深谙此道,比如墨西哥作家Juan Rulfo在《佩德罗·巴拉莫》中用平静的口吻讲述鬼魂故事,又比如1982年诺奖得主加西亚·马尔克斯,他在惊世之作《百年孤独》中,用寻常的口吻讲述人物飞升空中、持续四年的雨季、猪尾巴婴儿等一系列奇怪的故事,这与《聊斋志异》叙事口吻相映成趣。
除了短篇形式与无限想象力,《聊斋志异》在西语世界受到青睐的第三个原因则是它对彼时“中国现实”的呈现与批判。从文学作品中去“见中国之像”一直都是西方读者了解中国的重要途径,尤其是离我们遥远的古代社会现实,中国古典文学为此提供了合适的窗口。蒲松龄收集民间故事,在此基础上创作《聊斋志异》,所以它经历过采集民间声音的过程,使得它对现实的反映增加了不少“可信度”。也是因此,《聊斋志异》中人物众多,有访仙道士,奇异鬼魅,严肃公务员,可怖恶魔,佛家和尚与花妖狐女等,蒲松龄以不同层次、不同生活圈的人之口、非人之口,以及他们的生活经历来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主要描绘两种“社会之像”:一是他自身的感悟与体会;二是对社会的观察与深入。大部分篇章的故事与书生、文人的生活境遇休戚相关,“联系作者蒲松龄一生的境遇和他言志抒情的诗篇,则不难感知他笔下的狐鬼故事大部分是由他个人的生活感受生发出来,凝聚着他大半生的苦乐,表现着他对社会人生的思考和憧憬。就这一点来说,蒲松龄作《聊斋志异》,像他作诗填词一样是言志抒情的”。但是,蒲松龄写自己,但并不局限于自己,“在那个时代,官贪吏虐,乡绅为富不仁,压榨、欺凌百姓,是普遍的现象。位贱家贫的蒲松龄,有一副关心世道、关怀民苦的热心肠,又秉性伉直,勇于仗义执言。抒发公愤,刺贪刺虐,也成为《聊斋志异》的一大主题”。
Rovetta也认为,蒲松龄的文学创作价值就在于他的批判精神。秘鲁著名汉学家吉叶墨(Guillermo Dañino,1929-)在西班牙语版的《中国文化百科》中如此解释《聊斋志异》的现实指射:“这部作品也是对当时某些社会现实的一种揭露与批判:贿赂、专政、科举的不公正、官员的腐败、地主阶层的专横。每一个故事的夫子自道也揭示了这种批判与控诉意图,他同农民共同生活过多年,他自己也曾艰难度日,所以深知那个时代的各种不公,所以他的很多故事都描述了统治阶级对民众的剥削。”Chen Xinyi在《中国文学与西班牙文学的比较研究》中具化了三个批判对象:一是官员;二是科举制度;三是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道德体系。总之,《聊斋志异》以其灵活的短篇形式、无限的想象元素以及深刻的批判精神,受到西班牙语世界译者、读者的青睐与喜爱,传播深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