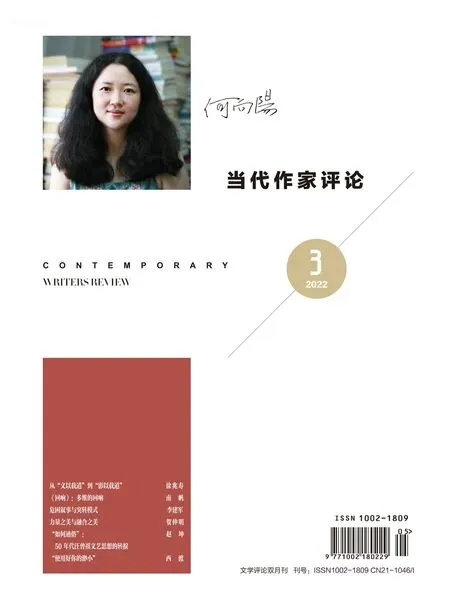女性之笑与日常情感的政治
——英语世界杨绛研究述评
2022-10-21潘莉
潘 莉
作为“世纪老人”,杨绛的百岁人生铭刻着现代中国不同历史阶段的印记,因此,杨绛研究具有独特的意义。而发掘英语世界里杨绛研究的历史,则为我们把握杨绛在海外的传播状况,观察英语世界如何经由杨绛来理解现当代中国的文学、文化及其历史的复杂性,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入口。本文将在充分占有海外杨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全面梳理英语世界杨绛研究的历史,为国内学界提供一份较完整的英语世界杨绛研究图谱。
一、作为事件的80年代杨绛作品英译与研究
80年代英语世界产生的杨绛作品译介热,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一个“文学事件”。单说《干校六记》在5年内出现3个英译版本这一现象,就殊为少见:历史上甚少有哪部文学作品(除经典名著)会被同一种语言翻译成多个版本,更不用说在短短几年内接二连三地吸引不同的译者为之付出心力。这种对同一作品不约而同的兴趣与选择,体现了西方译介者背后共同的文学品味与价值取向。这种品味和价值取向在当时,与中国正在兴起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思潮有某种契合。《干校六记》可以说是一部典型的书写知识分子“伤痕”的作品,西方对《干校六记》重复的译介行为,产生了通过外部力量使该作品成为“伤痕文学”潮流经典的客观效果。
耿德华和葛浩文可以说是英语世界最早的杨绛研究者。一方面,耿德华接续夏志清,注重发掘被忽视、“被冷落”的边缘文学作品,进一步助推了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影响下的80年代后期“重写文学史”的潮流;另一方面,以葛浩文为代表的杨绛“文革”作品译介研究,则昭示着英语世界对中国“伤痕”“反思”等文学潮流发展的关注。耿德华着眼于杨绛早期戏剧的“反浪漫主义”和葛浩文关注杨绛晚年作品的日常性与情感性,成为英语世界研究杨绛的最早切入口和理论定位点。不仅如此,某种程度而言,耿德华和葛浩文为后续英语世界杨绛作品研究开辟了两种研究路径,甚至不经意间指明了两大研究方向。
二、“女性之大笑”“低调的欢愉”或“暧昧讽刺”
不同于主流话语中将女性描绘为承受着文本暴力的受难者形象,或作为家国民族叙事的工具性存在,杨绛通过塑造“大笑的女主角”(the laughing heroine),赋予女性主角(如李君玉和张燕华)“大笑”之能量,将女性从家长制的可悲受害者梯队中解救出来,并且拒绝幼稚的“女超人”观念。与此同时,杨绛重新考察这两部喜剧中的男性角色(特别是资产阶级家长如张显甫和现代浪漫主义求爱者如周大章)的作用。由此,杨绛不仅将喜剧发生的重要之地“客厅”从家庭恶作剧和浪漫阴谋的场所,转变为女性被剥削和客体化的场所,还将其用作对压迫和解放等重要观念的意义进行协商的场域。最终这两部戏剧所呈现的喜剧远景,远非一种独立而琐碎的娱乐形式,而是开始迈入波德莱尔所说的“绝对喜剧之阈”(the realm of absolute comedy),即喜剧被视为颠覆现状的政治手段。总之,杜爱梅认为,在为大众提供娱乐的同时,杨绛将其“女性主义风俗喜剧”的创作作为一种批判主流性别论述和建构一种新的具有欢笑能力的女性角色的途径与方法,为性别议题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具体论述中,习恬指出,按常理来说,讽刺作品通常期待通过幽默来传达道德信息,谴责那些偏离社会习俗之人,但杨绛对原本应是讽刺对象(如《弄真成假》里的周大章)的模棱两可的描绘,挑战了读者和观众对讽刺对象的反感/反对;此外,虽然杨绛嘲弄并揭示社会中的邪恶,但并没有给出替代性的“高尚”行为和活动。总之,暧昧的叙事和修辞使得读者无法清晰辨别作者的信息,读者可以对故事进行不同的理解和反馈。其次,身处新旧之交的社会,“爱情”“婚姻”“家庭”等概念被赋予新的内涵,但这种赋能过程还处在形塑之中,统一的概念、固定的框架尚未建立,因此,杨绛讽刺的暧昧或模棱两可性的一部分原因,也来自其作品所涉及概念的模糊和流动性,即读者和观众对于概念的理解的多样性会导致对杨绛作品理解的多样性。然而,习恬认为,这并不意味着杨绛的作品不再具有讽刺性,事实上,即使缺少一个稳定的指涉框架,杨绛仍有着自己坚定的价值体系,杨绛的个人生活成为她讽刺爱情和婚姻的基本参照系。最后,习恬指出,杨绛的“暧昧讽刺”书写其实是对文学传统的嘲弄,是关于爱情和婚姻的文学类型和话语的“元讽刺”(meta-satire),例如《小阳春》重叙三角恋故事,解构“才子—佳人”神话,《Romanesque》则是对言情、侦探和古典聊斋故事的戏仿。
对于杨绛作品讽刺内涵的歧义性和复杂性的阐明,是习恬论文最重要的发现。这一发现提醒我们注意,杨绛作品内涵的丰富性需要读者与受众的参与,读者与受众不同的解读可以对文本产生不同的认识。这种强调“积极受众”的主动参与,注重读者/观众与文本之间形成的互动与联系,成为杨绛研究不可忽视的方面。
三、“亲密公众”“文学世界主义者”与翻译的政治
总之,方哲升的研究强调杨绛作品中与个人和身体相关的情感维度,这种情感因素延伸至作品的传播与接受层面,形成共享价值观与情感共鸣的“亲密公众”社群。方哲升的研究提醒我们重视文学的情感维度,在以往的研究中,情感维度很少成为国内学者研究杨绛的有效视角。在“情动理论”(affect theory)日益盛行的当下,情感视角可成为我们深入理解杨绛作品的另一维度。
有必要指出的是,方哲升的论述突出的是杨绛的个人性情感,关注的是这种情感超越或疏离于特殊政治立场的普遍性意义。与这种对杨绛作品中的个体性情感的普遍性理解同一逻辑的,是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系雷勤风教授(Christopher Rea),他进一步将杨绛(包括钱锺书)理解为“文学世界主义者”(literary cosmopolitans)。“文学世界主义者”的理解不但强调杨绛作品中人性和情感的普遍性,还进一步将杨绛的作家生涯、智识生涯理解为具有普遍意义。
不过,无论是注重普遍的个人性情感的“亲密公众”,还是超越特殊文化传统的“文学世界主义者”,其隐含的意图都是试图建构一种人为的普遍性(这种人为的普遍性通常以西方现代性为核心),以便包纳中国的特定文化、政治实践。因而,“非政治化”的“亲密公众”和“文学世界主义者”的解释,都是具有特定的政治内涵的。正是在这种“非政治化”与“政治化”交织的坐标系里,美国杜克大学东亚系罗鹏教授(Carlos Rojas)将杨绛的翻译工作视为一种政治实践。
结 语
总的来说,英语世界的杨绛研究一方面揭示杨绛作品的女性主义喜剧性与讽刺性,一方面关注杨绛生活和创作的日常性、情感性、世界性及其内在的政治性。这两种路径,自耿德华和葛浩文在80年代初开展杨绛研究和译介以来,就被持续地深化,直至今日。我们或许既需要清醒地意识到两种研究路径一以贯之的那种将杨绛纳入英语世界的文学、文化和价值秩序的理解方式,意识到这种理解方式所必然带来的误差和意识形态裹挟,也不妨将这两种研究路径及其具体成果引为必要的参照,以促进国内的杨绛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