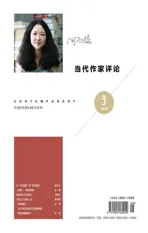非虚构写作的文学性维度及可能面向
——以熊育群《钟南山:苍生在上》为例证的思考
2022-10-21刘艳
刘 艳
作家熊育群的《钟南山:苍生在上》,15万字,由花城出版社2020年6月出版。中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守护人民生命健康方面堪称全世界的榜样,正应了钟南山在这本书的扉页上所言:“一个人在他的岗位上能够做到最好,这就是他的最大政治。”中国在2020年成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之后的几年时间里,在国际上做到了最好的抗疫成绩,这是中国最大的政治,更是中国不言自明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形象的表现。
《钟南山:苍生在上》这本书,没有因为它的纪实性和即时性而事过境迁,即使今天读来,仍然会被其中的真实性和真性情所打动,不能不引发我们更多的思考。就像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以及近年众多的非虚构作品一样,这本书在出版体例上被归为“纪实文学”。不仅如此,由于所记之人、所记之事自带极强的客观真实性,这本书要比很多非虚构作品更加“严格”地遵循客观真实、材料真实等“真实”维度的写作伦理和叙事策略。但这些来自事件真实性和人物真实性等方面的严苛的叙事要求,并没有影响或者降低作品本身的文学性、艺术性和可读性。作品本身含蓄蕴藉、意蕴深远,于字里行间自如生长的文学性和艺术性,向读者展示着纯“纪实类”的非虚构作品的文学性维度及其可能面向。
一、对虚构的反拨:重申“真实”维度的写作伦理
中国文坛近年来方兴未艾的“非虚构”写作热潮,被论者指认为是对“真实信念”写作伦理的重申。21世纪以来,文学一度不能不面对的一种情况是:越来越多的作家安于书斋式写作,远离现实,远离生活,过于依赖文学虚构性想象,甚至仅仅是根据新闻素材来创作虚构性小说,这样的写作方式难以避免会对写作本身产生伤害——其所反映往往是一种表象化的现实,作家在作品中所追求的“艺术真实”,越来越呈现面目可疑之状,越来越令读者不能认同其具有贴近生活的艺术真实性。当远离生活真实的作品越来越多甚至是泛滥的时候,“非虚构”写作势必会作为一种反拨——或者对表象化反映现实,或者对新历史主义式地书写历史的虚构文学做一种自觉的反拨,从而受到写作者和读者的重视与青睐。
对于《钟南山:苍生在上》这部非虚构作品而言,作家没有采取如上的写作者以自己的采访为主线串联起所见所闻的惯用手法。熊育群没有将自己置于各个叙事现场的核心位置,也未将自己的采访行为做主动展示,更未做主观观念意图的呈现。该书有两条叙事线索:一条线索是以钟南山这位现实中的人物为书写对象,这种为当世人作传本身就极具写作难度。当然,作家深谙其中的本意并非单纯为钟南山作传,他更大的叙事雄心是揭示出钟南山在两次疫情及其人生当中,所体现的医者与知识分子的一种精神,一种担当,即勇于付出、甘于奉献、无惧艰险的知识分子风骨与精神。另一条线索是以钟南山挺身而出、力挽疫情险局、拯救芸芸众生的作用不可被忽视的两个历史事件——他在2003年的“非典”期间与2019—2020年之际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历史性贡献为核心,来尽可能真实地全方位地展现这两次时隔十七年的重要的抗击疫情的历史性事件。
在普遍被指认为以亲历性和在场性为典型特征的“介入性”写作姿态,成为非虚构的写作姿态、写作指征的情况下,熊育群独辟蹊径地选择了作家创作主体的貌似不在场、不亲历,选择了将自己的主观观念隐匿起来,来表现历史事件历史记忆的真实与当下抗击疫情的真实,不可谓不煞费苦心。此书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后短短两三个月的时间里完成的,而此书的出版是在2020年6月份,《收获》发表更早,2020年5月即已刊发。也就是说,这本书既要写出现实真实——刚刚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中的种种现实事件和钟南山在其中所起的扭转危局的作用,又要写出历史真实——2003年那场“非典”疫情中钟南山所起的巨大的历史作用。而对于钟南山家世和成长经历及至当下在本职工作中的情状的书写,作家又在很大程度上试图努力真实还原一位知识分子的成长史。作者在历史真实和现实真实双重维度上,皆体现了非虚构写作对于真实信念写作伦理的不懈坚持与孜孜追求。
《钟南山:苍生在上》面对的素材和写作对象,无不对“真实”维度提出了更高的写作要求。梁鸿的“梁庄”系列非虚构作品,所写关于梁庄的客体真实,外界对其知之不多,更多要依靠写作者的寻访、采访、交流与记录,来读解梁庄人的生存景象和梁庄乡土社会结构的变迁。而像王树增等作家对于历史战争的书写,陈徒手的《故国人民有所思》等非虚构写作,都可以在大量的历史资料、档案资料的比照和对读中,重构寄寓作者思考的历史现场,历史真实有着各方面材料的有效支撑。至于何为历史真实?读者完全可以将自己代入到作品当中,像作者一样去解读和触摸历史真实,做同位思考。2003年“非典”疫情当中的很多事件、历史现场,相较于武汉当时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来说已经“尘埃落定”,诸多历史事实已有定论。而对于《钟南山:苍生在上》的写作来说,疫情仍在,还存在许多不甚明晰的现实真相,这对作家的写作提出了更为严苛的在真实维度的写作伦理要求。如最先报告不明原因肺炎的张继先医生的情况,以及围绕她的发现所记录的所有最初的病例事件真相;钟南山的学生之一管轶在2003年就协助过钟南山抗击“非典”,2020年初武汉发现不明原因肺炎也同样引起了管轶的高度关注,他现身武汉街头却遭到误解,只能匆匆离开武汉等。这些情况作家都给予了最为贴近事件真相的书写,没有因为笔触有失允当而让所写的人物与事件经受不住时间的考验。作家甄别事件真相的能力与写作中对价值立场的坚守,都是作品能经受住现实真实性严苛考验的重要保证。而敢于触碰和选择这样的选题和素材,作家是基于自己多年来丰厚的写作经验的累积,并对纪实类、非虚构写作有着深入思考与对叙事手法有深入探究的。
《钟南山:苍生在上》所采取的其实也是一种在场性、亲历性为指征的“介入性写作姿态”,只不过,作家选择了创作主体的消匿和隐匿姿态——写作者并不在事件现场,作家也完全不表露自己的采访与寻访,不标注素材和材料来源,看不到作者主动给出自己进行现场记录的主观意图的流露和展示。事件和现场全靠身在现场的人物来引发、推动和展示。钟南山和身在现场的人物,是最为重要的“叙述因子”,人物的视角、眼光和所见所闻,决定着事件过程、事件真相的展示。作家创作主体的主观意图不越界或僭越到作品叙事当中,这样切近事实和现场真实性的手法,反而让作品现场感十足。阅读者不必受制于或者说是被写作者的主观意念牵绊影响,他可以只关注事件本身,有关当下事件或者历史事件以及事件中的人物都是重要的叙述因子,迅速推动着事件发展形成较为迅捷的叙述节奏。剔除了先入为主的主观意图的影响,一切的客观真实和事件真相,都获得了更加原生态的呈现,这或许也在更深层的意义上贴近了非虚构写作关于“真实”维度的写作要求。比如这本书一开篇,就是紧急事件的发生——钟南山被国家卫健委紧急派往武汉,电话一催再催,都是通过钟南山助手苏越明的视角来叙述的。春运高峰中钟南山与助手好不容易赶上了赴武汉的高铁,在途中,疫情进展紧急,钟南山随时关注疫情并对疫情做出及时的研判。相关情节的叙述节奏密织紧凑,快速的叙事节奏烘托出了当时令人紧张不安的情境。
二、文体的兼容性:纪实文学对叙事散文与小说文体特征的汲取
《钟南山:苍生在上》以作家尚在事件现场,与事件以及事件中的人物零距离,要即时性地表现和书写刚刚发生和正在发生着的事件——所写的一切都尚在变动不居甚至尚无定论的情况下,要写作出极为接近客体实存之“真实”的非虚构作品,还要经受住时间的考验,不能因言之偏颇或者判断有失允当而让作品“过时”、立不住脚。在这样的写作要求之下,作家不能不在作品叙述和文体方面,做出精心的考量与叙述手法的巧用选取,作家自觉或者不自觉地需要让作品呈现一种文体兼容性状态,在非虚构的写作体例上,尽可能参鉴叙事散文甚至是小说的一些叙述手法和文体特征。这也让这部作品,呈现出与一般的非虚构作品不尽相同的写作特质。
非虚构作为对于传统的虚构文体的反拨样态而出现。但该如何令非虚构写作创造出更具感染力的“艺术真实”呢?我们应该打破虚构和非虚构之间决然分明的文体界限,让非虚构文体具备兼容性——涵容和汲取叙事散文与小说的文体特征,打破束缚在非虚构写作之上的对作家创作主体创造力和艺术想象力的桎梏,在一种较为开放的视域和文化意蕴中,探索更多的人性的可能性、生活的可能性。就如米兰·昆德拉对小说的强调一样,让非虚构写作也能如小说般在更多层面实现对于存在的可能性的勘探。非虚构自身的局限性和文体自带的局囿与限制表现在:在少数作家可以专注于现实书写或者历史书写的非虚构写作之外,大多数作家对于非虚构写作仅仅是浅尝辄止。保持开放性文化语境,充分调动创作主体的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让非虚构写作少些文体束缚,尽量保持开放性的写作姿态和文体兼容性,注重对叙事散文尤其是虚构小说叙述手法的兼容并包,是这种文体继续生长、获取更新以及促使非虚构经典作品生成的重要因由和途径。
随着非虚构写作的不断发展,虚构和非虚构两种文体界限越来越不分明,两者都需要创造“艺术真实”。事实性和虚构性看似对立,其实也是关联甚深的两个概念。在所有的文学类别中,事实性似乎都是在逻辑上先于虚构性的,但事实性和虚构性何者为重或者哪一个受到更多的重视,或许恰恰是非虚构和虚构的的一种区分方式。即便如此,不能否认的是,虚构小说中也要有纪实和写实的成分,非虚构作品中也要有虚构的场景和虚构还原出的“真实”的故事来支撑,因为即使是采用在场性、亲历性写作姿态的非虚构写作者,也并不能保证自己在事件和场景中的全程“在场”。具体的场景和情境,也只能通过类似小说虚构的艺术手法加以还原和呈现,一味图解客体真实、缺乏艺术真实创造力的写作者,注定是不成功的,这就对非虚构写作者的艺术想象和艺术虚构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对于钟南山在2003年抗击“非典”中的那些真实的故事,作家只能借助自己的艺术想象力和艺术创造力,对当时的情境进行合理的艺术虚构来加以还原和呈现。这本书里最具感性和艺术性的叙事段落,应该是第四章“挫折 强者之阶”和第五章“负笈英伦”。作者笔法灵动,不急不缓、淡然悠远、绵意深远却又不乏激情地叙述着钟南山的父辈家世、身世与他从出生到童年、少年、青年乃至中年一路走来的经历,故事性与可读性很强。叙述不仅不枯燥乏味,反而有着近乎虚构性小说的可读性;但由于故事和事件皆基于真实的人物和事件,作者叙述确也简洁朴素,亲切感人,所以时时引人心灵共鸣或者发人深思……作家在非虚构这一文体类别里,不动声色地对小说叙述手法和小说虚构性写作手法予以借用,让作品艺术真实性元素倍增。钟南山的人生经历和故事,展示了更多生活的可能性、人生的可能性与人性的可能性。书中引用了钟南山在抗击“非典”时期对记者说过的一段话,这段话蕴含着人生哲理:
三、兼顾文学性维度:非虚构的叙事探索及可能面向
熊育群一反其他非虚构写作强调写作者自己的在场性、亲历性或随时随地记录自己的所见所闻、介入性地全方位呈现所掌握的所有史料材料等的常态,而不明言自己的在场和亲历,几乎全部采用钟南山和其他人物的视角来叙述,坚持采用写作者看似“不在场”但却是时时在场这样一种更加深隐的介入性写作姿态。因此全书的叙述策略也呈现新质:即纪实类、非虚构类文体能够实现对于叙事散文与小说文体叙述手法的兼容并包、多有借鉴并作经验的汲取。
强调非虚构是“行走”的文学,强调非虚构需要作家全程参与到写作所涉及对象的每个环节,强调要广泛搜集材料、认真采访和寻访,强调如实记录自己的所闻所思所感,熊育群做到了。作为优秀的小说家和散文家,基于多年积累的小说与散文写作经验,他无师自通地在书里几乎是隐身了。虽然所有材料的剔抉用弃,皆由他做主,他的价值观判断、感知、兴趣、好恶等写作者的“视点”也左右着他的取舍……但他在叙述上获得了彻底的解放,不拘囿于类乎深度新闻报道式的写作束缚,而是将不同文体的叙述手法兼容并包,从而最大程度地调动他掌握的叙事资源,也令作品呈现很好的故事性、可读性,展现创作主体丰沛的艺术想象力与艺术创造能力。
2003年抗击“非典”与2020年初开始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围绕钟南山和其他医生、病患的所有事件、故事及场景,都要靠作者的艺术想象力和一定的艺术虚构能力,才能如实而又生动地还原和呈现。而整本书当中,写作得行云流水,如小说如叙事散文一样婉然悠远好读并且吸引读者的章节,当属第四章和第五章,其中讲述了钟南山早年的经历、上山下乡以及回广州工作后负笈英伦访学进修的经历。所有的故事与场景,作家不可能一一实地到访,这就要从所掌握的材料和采访记录里提炼出来,做艺术上的生发和创造。
本书对于钟南山早年成长经历的叙述是作品最吸引人的地方。早年的经历,也是钟南山后来能够在国家和人民危难之时挺身而出,体现一名医者和知识分子的勇气、判断、责任与义务担当的前提与先决条件。1964年底,钟南山被学院派往胶东乳山下乡,两年后回到学校,又被安排烧锅炉,进行“思想改造”。艰苦的环境中,钟南山的心态却总是积极向上的,烧锅炉的情景被描写得生动真实。面对这些场景,作者并未采取口述实录方式、未作主观性介入,而是尽量地节制创作主体的思考、分析和判断,让场景、事件、人物作为“叙述因子”,忽略人物的心理描写,像写作小说一样,把故事和现场还原呈现出来。这样反而令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更加贴近客体真实,呈现出一种既符合客观真实性又别具艺术真实性的叙述效果。
本书当中,作家巧于叙事结构的安排。对于实地采访和对人物采访所得的大量材料这些叙事资源,作者也没有拘泥于客观材料的束缚,而是精心取舍和加以安排,让客观的数据材料和事件材料,具有温暖人心的温度。材料的取舍与安排使用,本身也是对非虚构写作者写作眼光、写作经验与写作能力的切切实实的考验。据熊育群介绍,目前这本书已有14种译本正在翻译当中。它所展示的不仅是钟南山在两次疫情中的担当作为,也不仅是钟南山这个人物的生平,而是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形象和中国力量。而钟南山这个人物身上,所体现的医者和知识者那些可贵的精神品质以及他的人生经历,都在显示更多生活的可能性、人生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带给我们无尽悠远深厚的审美回味,也让文本呈现立体而丰赡的艺术品质。
能够成功挣脱特别具体的客观存在和那些繁复的物化外观材料的束缚,挣脱非虚构难以避免常常要拘泥于作家的所见所闻的具体实录的牵绊,在非虚构这样一种文体的写作当中,令文学想象力的翅膀得以自由飞翔,《钟南山:苍生在上》这部作品,算得上是作家熊育群在非虚构领域新的建树。这本书对中国人乃至全世界的人,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同时它也将是非虚构写作的一个经典文本,它预示着非虚构写作是一种具有文学性维度新的生长点的文体,它的无限可能性尤为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