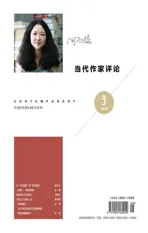游走于语境和文本之间
——对近年来女性文学研究的反思
2022-10-21王妍
王 妍
女性文学研究的关注点往往在于如何精准地把握和分析女性形象,着力挖掘其客观的人性特点以及角色本位。这一方面有利于理清作者的叙事脉络;另一方面能够熏陶读者,形成积极健康的审美情趣。然而,综观近年来女性文学研究,存在着诸多问题:其一,批评视域明显地游走于语境和文本之间,或此或彼,摇摆不定,男权主义意识处于女性文学研究的主流地位,使得批评物化为观赏。其二,过分凸显解构男性中心秩序时所造成的张力,使得批评出现了语言暴力倾向,“偏执少女”“骁勇悍妇”“雌性的魅惑”等词语在女性文学研究论述中随处可见,格外刺目,男性特质被过分夸张,而女性形象则被严重扭曲。这些都值得研究者认真反思。
一、游离语境凸显文本的女性文学研究
通常而言,语境既是言语行为发生的环境,也是话语理解的环境,其往往作为内在化的认知结构赋予人对客观存在进行解读的能力。而作为作品本身的文本则是凝固静止了的语篇,其和语境的关系恰如丹纳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所阐释的,是相辅相成的,绝不能有所偏废。因此,女性文学研究也离不开语境这一要素,一旦游离语境来凸显文本——在批评分析过程中单纯地针对作品文本本身,便容易出现概念多元、批评视域单一和角色定位模糊等一系列问题,从而导致偏颇。
首先是概念多元与批评视域单一的冲突。作为学术术语,女性文学涉及的层次是多元化的,具体关涉到性别概念、学科概念,乃至文化概念。性别概念是界定女性文学的理据,决定着对女性形象的批评究竟是建构还是解构,其关键词是“女性”;学科概念指明了女性文学的范畴,是对文本性质进行的确认,其关键词是“文学”;文化概念则是就批评视域而言的,具体指的是研究女性文学的方法。综上可知,女性文学研究是“性别概念”“学科概念”“文化概念”整合而成的批评体系,必须统筹兼顾,不能有所偏废。否则就容易出现偏颇,造成概念多元与批评视域单一的冲突。从近年来女性文学研究的现状看,由概念多元与批评视域单一所造成的冲突,较易导致两个方面的偏颇:一个是对于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定位,另一个则是相关学科归属。
一般说来,对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进行定位需要以性别概念作为准绳。然而,由于批评视域单一导致游离语境凸显文本这一偏颇现象的出现,往往研究者在批评分析时过于强调类型的划分而相对忽视了对于典型的确认,这就不可避免地走向了群体归类模式。以“类”为标识的“某某(受难、逃离、黑人、自审者、嬉戏者、东方)女性形象”便是如此。当然,出于研究工作的实际需要,对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进行归类无可厚非,可是这种带有标签性的定位如果缺乏统一的标准,就很难做到科学而合理。这样的情况就使得归类的结果明显典型性不足,而类型性又过于强势,从而偏离了作者在作品中塑造女性形象寓意的初衷。可见,女性文学研究的范式如果过度在意类型的划分就容易导致对女性形象特征的解读出现偏颇,其体现在语用上的直接影响就是概念模糊。
此外,概念多元与批评视域单一的冲突在学科归属方面也有所体现。由于游离语境凸显文本,所以女性文学研究经常出现“超文本”解读现象,也就是出于凸显批评视域的新颖而忽视文本的主体性,热衷于所谓的“深度”挖掘。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把作者和作品中的人物混淆甚至等同起来加以分析阐释,从而陷入类似于《红楼梦》研究过程中的“索隐派”泥淖。然而,需要加以说明的是,过于强调学科归属也同样可能会误入“考证”歧途,其显现结果便是容易把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割裂开来。例如,一段时间以来,研究者在解读女性形象时,对“女性意识”的考据和挖掘出现了泛滥,喧嚣一时,几乎成为解读女性文学形象的“万金油”,似乎没有“女性意识”就不会有女性文学。殊不知,所谓“女性意识”当中的“孤独意识”“围城意识”“逃离意识”“黑夜意识”“自审意识”等绝非女性专属意识,即便是在男性中也会广泛存在,且并不是所谓“哪一方更为突出”就能作为划分标准的依据。由此可见,女性文学批评如果任由概念多元与批评视域单一发生冲突而不去进行整合,自然会出现游离语境凸显文本这样的偏颇。为了避免这一现象的出现,女性文学研究就需要基于批评视域来展开性别概念、学科概念综观式的形象批评,以确保研究方向不会陷入孤立与静止的境地。
值得注意的是,概念多元与批评视域单一的冲突还容易形成对批评者认知域方面的禁锢,也就是刻板印象的生成。作为文学批评的一种,女性文学研究也是审美评价的一种类型。所以,真正意义上的女性文学研究要做到统筹兼顾,不能顾此失彼。如《白鹿原》当中的田小娥,若是单纯地把她界定成“封建制度的反叛者”便显然失之偏颇,容易出现以偏概全的问题。依据维柯的观点,田小娥短暂的一生经历了四体演进的全部过程。在其人生过程中,她分别在不同时段和场合扮演了渴望美好生活的“凡人”、反抗压迫的妇女主任(“英雄”)、以肉体换取庇护的“颓废者”、死后被乡民敬畏和修建镇妖塔来防止其复仇的冤魂(“神祇”)四种角色。所以,若是把她界定成“封建制度的反叛者”,则仅仅是就其角色形象中的“英雄”这一属性而言的,如此评价田小娥有悖于陈忠实创作该女性文学形象的初衷。如此定性也自然削弱了人物形象应有的道德批判力度。总之,女性文学形象研究需要注意概念多元与批评视域单一存在的矛盾,以整合的眼光进行批评。
其次是概念多元造成了女性文学定位的模糊性。在女性文学研究上,性别概念是一切的初始,它具体关涉到两方面范畴:一个是作者,另一个是作品里的女主人公或者女性陪衬人物。这样就使得女性文学存在着狭义与广义的区别。狭义上的女性文学指作者和作品的主人公都是女性,二者存在同一范畴所指,如曾经风行一时的“小女人”散文和“千禧一代”女性小说等。相形之下,只要满足上述两个范畴中的任意一项便是广义上的女性文学。据此可知,女性文学从诞生起就存在着定位及由作者身份属性带来的模糊性问题,这在目前依然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在实际研究过程当中,女性文学范畴上的广狭义之别造成的定位模糊无疑对女性文学的研究范式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这具体体现在研究究竟是作者中心观还是作品人物中心观的确认上。从当前的研究现状来看,以作者中心观替代作品人物中心观是女性文学研究的基本范式。这种通过人物形象分析再到作者溯源来探究作品意义的研究方法无疑是作者中心观的表征。然而客观存在的问题是,基于女性叙事视角的男性作者及其作品,基于男性叙事视角的女性作者及其作品,能否也采取该类方式进行解读,这还有待进一步探究。
与性别概念的初始性相比,学科概念在指明女性文学所指范畴的同时,还能够对文本的归属进行科学定位。体现在文体上,女性文学可以具体划分为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不同的艺术种类。这在理论上是非常明晰的,然而一旦涉及具体的研究工作时,则常常出现语用模糊现象。各种冠以“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现当代文学”“晚清文学”“唐前文学”字样的限制,使得研究的范畴被显著放大,而这一状况的直接结果就是在研究范式上出现了以局部替代整体、以次要人物取代主要人物之类的断章取义式的偏颇。如有的研究者对《雷雨》中繁漪这一人物形象的解读,其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繁漪的命运悲剧性上,得出的结论自然是“三不”,即不幸福的妻子、不美好的恋人、不完整的母爱等。殊不知繁漪只是《雷雨》里面的一个功能性的推进剧情发展的人物,她的出现能够进一步彰显周朴园的自私、虚伪和冷酷。因此,研究繁漪就需要把她和周朴园关联在一起,孤立地、静止地看待和分析这一人物形象本身,显然是没有考虑到学科概念这一要素,有脱离主体之嫌。
相比之下,文化概念关涉的则是批评视域,也就是女性文学研究所采用的视角。作为方法论,借助文化概念来解读女性文学形象的时候,需要符合相应的语境信息关联,即作者创作的时代背景、创作目的等一系列背景要素。忽视这些要素就容易造成牵强附会之类的偏颇,得出来的结论也并非是人物角色固有或性格发展变化的产物,而是成为一种理论上的强加。这样的情形一旦出现,就会使得女性文学形象的研究存在过度解构的现象,使得对女性文学形象阐释与解读严重偏离社会现实而演变为研究者的杜撰。如对《水浒传》女性形象的研究就有观点指出,作者施耐庵的创作带有“反女性”倾向,他是以鄙视甚至仇视的态度来描述女性的。如果去除时代背景这一要素,这种结论无疑是合理的,然而,在元末明初那个男尊女卑观念依然盛行的封建时代,作者的创作观念显然不应以今时的男女平等理念去解读。
二、游离文本凸显语境的女性文学研究
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类型,女性文学批评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它通过文本把作者和读者有机地关联在一起。因此,女性文学批评是建立在文本这一基础之上的文学审美活动。然而,需要关注的是,任何一部文学作品的生成都离不开时代背景,既包括作者生活的时代,也涵盖作品反映的时代。此外读者本身也是一种客观性的现实存在,有其固定的生活时期和社会认知。因此,研究女性文学形象自始至终都离不开对语境的关注。这里所说的语境,具有三个方面的意涵指向:一是作品所反映的时代背景;二是作者所处的年代;三是读者所生活的时代。由此可见,文本的语境是一个带有时间关联的集合体,具有立体属性。在功能上,语境在具体解读女性文学作品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综观近年来女性文学研究的现状,游离文本凸显语境的女性文学批评几乎成了一种主流,这自然会为相关研究带来诸多弊端。
受此创作观的深刻影响,部分女性文学研究者混淆了私人化创作与个性化批评之间的界限,进而影响了女性文学批评的健康发展,导致偏离现象的出现。一些女性文学研究者从私人角度出发对文本进行私人化解读。有的研究者在所谓发现真相和书写真实的驱动下,把女性文学创作看成是“分裂意识”的表征,是对男权传统文化的叛离。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纵观我国历代文学创作情况,女性作者屡见不鲜。从《诗经》里的许穆夫人,到东汉的蔡文姬,再到唐朝的薛涛,及至宋代的李清照,这些女性作者及其作品如果也使用“分裂意识”予以解读的话,是否还能够得出相同的结论?这是让人备感疑惑的事情。毕竟私人化创作有着固定的群体和指称对象,因而不能泛化,也不能把研究者的个性化解读与私人化创作等同起来。因此,女性文学研究做私人化处理是不恰当的一种研究方法。
由于私人化创作观强调个人化写作的颠覆性与解构性,所以被引申应用到女性文学研究领域后,也随之出现了过度解构的现象。某些批评者甚至抛弃文本和学科概念,紧紧抓住文化概念不放,把文本里的女性形象看成是符号标识物,并据此仅仅关注文本中女性的生存状态,对女性形象作出了种种扭曲式的描述与阐释,致使角色反动现象泛滥一时。如在当代青年女性的角色认同与社会基础视域下,某些研究者在解读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时,把“女汉子”强加于女性身上作为其性格特征的标签。与盛行于20世纪60年代的“铁姑娘”相比,“女汉子”叙事视角显然是男权主义中心观在作祟。同时,把“独立自强”“自由自主”“自信乐观”等没有性别区分度的词语附着在文学作品中的女性身上,显然也有失偏颇。可见,使用“女汉子”这样的词语来对女性文学形象进行描述,无疑是在进一步彰显与固化男权主义话语权力,不符合女性文学研究的发展趋势。
与女性文学形象研究过程中的颠覆与解构相比,在具体批评过程中的建构性则略显不足。笔者随机从知网上抽取60篇(部)有关女性文学研究的文章(论文),经过简单的数字统计后可发现大约71.3%的文章(论文)对女性文学形象进行的是负面描述与研究。可用作表征的关键词有“不幸福”“不完美”“女汉子”“悍妇”“物品”“他者”“魅惑”“依附”“逃离”“受害者”“卑鄙”“女骗子”等,不胜枚举。这些明显带有语言暴力倾向的词语一旦作为标签被附着在研究与批评对象身上,其颠覆力是不言而喻的。相形之下,可用于建构女性文学形象且带有褒义色彩的词语则非常少见。即便使用,往往也是传统认知观念的折射,缺乏当代意识,如“坚忍”“顽强”“无私”“真情至性”等,不一而足。由此可见,近年女性文学研究的偏颇也体现在解构有余而建构不足上。
其次是各种西方文论对女性文学批评建构的冲击。文学创作离不开语境,因此,研究女性文学形象也自然不能脱离语境而单纯地使用理论进行过度阐释。纵观近年来女性文学研究的现状,形形色色的西方文论对女性文学批评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这是造成偏颇的原因之一。
从学术交流与互动的角度讲,适当引进西方科学性较强的文艺理论解读我国女性文学形象效果很好,可以与时俱进,达成理论创新之举。可客观事实则是,研究者关注的焦点依然只是表层上的新奇特氛围的深度营造,创新深度明显不足。20世纪80年代中期,西方盛行的“女性主义”学说登陆我国学术界。改革开放初期,特定的历史阶段使得引介来的“女性主义”本土化理论,往往基于女性是受压迫受歧视的群体,从而把传统认知与现实有机地关联在一起。时代在变化,性别秩序也不是不可更改的。于是有研究者便采用这一观点来解读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批评矛头直接对准男权秩序以及生成该秩序的文化传统。值得注意的是,引介来的“女性主义”在本土化过程中,又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变异。有的研究者把“女性主义”和“女权主义”等同起来,结果在具体批评某部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时存在着语用模糊现象,从而发生一定程度的偏移。从偏移的程度来看,当关注的视角是“性”的时候,就会围绕女性意识的觉醒进行深度挖掘,得出来的结论自然是屈服于“性”压力之下的女性的种种痛苦和不幸,这种情形被看成是“欲望”与“自我认同”。而当关注的中心是“权”的时候,就会以女性反抗男权社会为话题进行系统阐释。以此暴露社会黑暗面,这本无可厚非,可是当把女性对命运和现实的反抗界定为“女性形象的异化”就或多或少有些偏颇了。
综观研究现状,在女性文学形象批评过程中,跨学科理论的引入也助推了偏离现象的生成。当下,学科交叉已经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女性文学形象研究当然也不能例外。然而,在实际应用时,如果没有掌握好分寸这个度,就会出现过度解读现象。如基于心理学、社会学的视角对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进行研究,在探讨女性分裂意识时,是人格分裂、心理分裂或多重分裂就值得商榷。如《祝福》中的祥林嫂,在她走向死亡的过程中,絮絮叨叨的碎语显然是心理分裂的表征。然而,由一个完全能够自食其力的劳动妇女蜕变为末路乞丐,还能简单地界定为人格分裂吗?所以,跨学科研究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需要确定出原点,切忌拔高批评,出现定位偏差。
女性文学形象研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学术话题,需要在研究过程中注重语境和文本,而不能有所偏废。游离语境凸显文本的女性文学批评以及游离文本凸显语境的女性文学批评都是一种解构过度的批评行为,缺乏文学研究应有的建设性,这样的女性文学批评是不符合文学批评发展规律以及文学自身要求的。此外,建设性的批评一旦出现缺失情形,也会伤害到健康向上审美情趣的养成。当下,学术界在进行女性文学研究时,需要围绕“女性”展开“形象”批评,批评的方法既要符合语境,又要契合文本,从而保证批评方向的科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