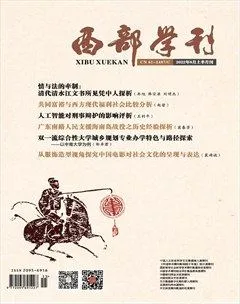二十世纪上半叶小说批评派对王熙凤形象接受倾向浅探
2022-10-21张彦芸
张彦芸
一、引言
二十世纪上半叶,《红楼梦》研究开启了新的篇章,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红学、以胡适为代表的考据派红学和以王国维为发端的小说批评派红学成为《红楼梦》研究的三大学派。小说批评派始于国学大师王国维,他是运用文学批评的方法来探讨《红楼梦》文本本身价值的第一人,他的这一研究方法开创了小说批评派的红学研究之路。
接受美学认为,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存在于历时态读者的阅读与接受中。接受美学理论的首倡者尧斯认为:“在阅读过程中,永远不停地发生着从简单接受到批评性理解、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接受、从认识的审美标准到超越以往的新的转换。”自《红楼梦》诞生之日起,各个历史时期的各类读者对王熙凤形象的接受正体现了这样的审美接受规律。二十世纪上半叶,时代巨变,西学东渐,多种多样的思想观念导致读者们的接受思维更加多样和丰富,限于篇幅,本文主要考察这一时期小说批评派对王熙凤形象接受倾向的特点。
二、季新:社会政治立场下的功利阐释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我国正处在内忧外患交作、民族危机深重的时代,改革救亡的政治主题成为当时的中心话题,这种强烈的政治意识也渗透到学术研究领域。1898年“戊戌变法”的失败让梁启超等人感到从思想上唤醒民众的重要性,因此发起了一场“由下而上”的“新民”运动,“小说界革命”正是这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严峻政治形势的触动下,在“小说界革命”的影响下,很多激进人物都认为文学要揭露旧社会,抨击旧制度。革命派文论家天僇生认为《红楼梦》主旨就是“哀婚姻之不自由”这一社会问题,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封建婚姻制度。
这种社会政治角度的阐释在“五四运动”爆发前后进一步发展,成为当时红学研究领域的主流批评模式。新文化运动吹响了反对封建制度、封建礼教,拥护科学与民主的时代号角。季新的《红楼梦新评》正是在这种时代语境下诞生的。该文认为《红楼梦》是“中国之家庭小说”,并认为专制是中国国家组织和家庭组织的特点,封建礼教则是专制的辅翼,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礼教则造就了一个虚伪的社会。用这样的观点来解读《红楼梦》中的人物,他认为凤姐就是一个典型的“假孝假慈假友假悌之人”,“若凤姐者,承欢色笑,宜若能尽妇道者矣,然其心但以能博老祖宗之欢喜,为一己颜面上之光荣,益得以遂其揽权专制之志云尔。”他将凤姐作为当家人的弄权行为阐释为“揽权专制”,连被一些封建文人所称赏的凤姐对贾母“斑衣戏彩”的封建孝道行为也被其看成是凤姐“揽权专制”的手段。在季新看来,凤姐就是封建制度、封建礼教的执行者和帮凶。
季新对凤姐的解读是立足社会政治立场的功利阐释。这种接受视角首先和我国经世致用的文化传统有关。我国古代的政治家与先进士大夫都把文学的教化功能放在第一位。梁启超弘扬小说的宗旨也是让小说为政治服务,让小说成为改造国民、唤醒民众的政治工具。这种强烈的政治意识影响到古典小说研究领域,使得人们在解读《红楼梦》时往往立足于社会政治立场。他之所以采取这样的一个接受视角,还有其深刻的时代因素。这篇文章发表于1915年,正是“五四运动”爆发的前夜,国内政治形势严峻,各种进步的政治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文学要揭露旧社会,抨击旧制度,反抗专制,倡扬民主成为这个时代文学界的主流价值趋向。因此,季新对凤姐没有进行传统的忠奸善恶的道德评判,而是将其理解为旧社会中某类人的代表加以批判,其斗争的矛头最终指向旧的社会制度。
三、王国维、牟宗三:悲剧论视角下的审美观照
二十世纪上半叶,西方的各种文化思潮开始进入中国学人的视野和学术研究领域,这股西学东渐的狂飚也影响到了当时的红学研究。晚清学者王国维正是在西学东渐之风影响下的一位学人,他所接纳的思想是多元的,这种复杂的期待视野为他的《红楼梦》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1904年,王国维发表了《红楼梦评论》,该文在《红楼梦》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他用德国叔本华的哲学对《红楼梦》进行了一次系统的解读。在此文中,王国维援引了叔本华的悲剧观,认为世间的悲剧分为三种:“一类是伦理悲剧,由极恶之人制造悲剧;另一类是命运悲剧,盲目的命运造成悲剧;还有一类就是存在悲剧。”在王国维看来,《红楼梦》属于“存在悲剧”,这类悲剧的根源不在于道德层面或命运层面,而是由于小说中各种人物的位置、关系所造成的,悲剧的根源在于生活本身。王国维认为宝黛的爱情悲剧并非极恶之人肇祸,而是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因为各人的立场、境遇的不同而导致的必然结果。由此推之,贾母、凤姐等人并不是千方百计破坏宝黛爱情的恶人,他们只不过是站在自己的立场行为处事的普通人而已。在悲剧论视角的观照下,王国维没有将凤姐视为大凶大恶之人进行谴责,而是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理解与宽容。
王国维对《红楼梦》的哲学、美学阐释在红学界引起了某些人的共鸣。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牟宗三发表了《红楼梦悲剧之演成》一文,重点剖析《红楼梦》悲剧产生的根源。该文认为《红楼梦》悲剧形成的原因不是由于善、恶与灰色这三种人相互攻伐,而是因为书中人物“性格之不同,思想之不同,人生见地之不同”造成。由此,他认为《红楼梦》里面,“没有大凶大恶的角色……”小说里的人物“在为人上说,都是好人,都是可爱……”基于这个前提,他认为凤姐“是一个治世中之能臣,不是一个乱世中之奸雄”“……至于宝黛的悲剧,更不干她事,她不过是一个工具而已。”牟宗三从悲剧论的视角出发,也没有将凤姐解读为大凶大恶之人,且在对凤姐表现出理解与宽容的同时,多了一份赞赏和肯定。
在西学东渐的狂飙席卷下,晚清的思想界出现多元并存的局面并影响到学术研究领域。王国维作为一名前清遗老,眼看着清王朝的土崩瓦解,深感前途渺茫,因此他选择了叔本华的哲学,并将叔本华的悲观主义与虚无主义同《红楼梦》的悲剧精神相结合,从而表达他悲观厌世的情怀。牟宗三之所以采取悲剧论的视角解读《红楼梦》,除了在学术方法上受王国维的启发之外,更多的是对当时政治功利解读方式泛滥的不满。晚清以来,随着政治形势的日趋严峻,国内对《红楼梦》的政治功利研究居于主流地位,政治索隐派和社会政治阐释派大行其道。这些非文学性的解读立场引起了一些学者的不满,如牟宗三就认为索隐红学和考证红学都不属于文学批评的范畴,都属于《红楼梦》鉴赏的“圈子外的问题”。因此,他呼吁《红楼梦》研究要摆脱政治功利意识,回归文学性研究立场。王国维、牟宗三都以一种系统的美学理论为参照系来阐释凤姐,他们的接受态度散发着理性和美学意味的光辉。
四、李辰冬:抽象人性论视角下的文学性解读
“五四运动”之后,尽管国内政治局面处于军阀混战的动荡状态,但文化思想的开放程度是前所未有的,西方各种文化思潮的引入为人们审视《红楼梦》提供了新的参照系。当时的很多学者纷纷用西方的文艺思想观念来诠释《红楼梦》这部经典之作,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便是其中的一例。
李辰冬于1928年赴法留学,留学期间,他就非常喜欢法国哲学家兼批评家丹纳的思想并在其影响之下撰写《红楼梦研究》一文。他对凤姐的看法见于该文的第三章《红楼梦重要人物的分析》。李辰冬是抽象的人性论者,这种人性观无视时代、阶级等历史性因素。从这种人性观出发,李辰冬认为《红楼梦》中的人物大都象征着一种普遍的、世界性的人性。关于凤姐,李辰冬认为作者塑造她的目的“是让她来象征着人类的才干和阴险”。他认为:“王熙凤之所以喜欢做事,系一种恃强欲在那里冲动着。……是我们青年气壮力强,野心勃勃时代所有的通性,”“喜奉承,好虚荣本是喜欢做事人的通病,也是我们人类的天性。”在抽象人性论的观照下,李辰冬将凤姐的“才干和阴险”“恃强欲”“野心勃勃”“喜奉承,好虚荣”等个性特点理解为人类普遍的天性,没有对她进行道德层面的褒贬,在保持与审美对象一定距离的前提下作出了具有美学意味的观照。
李辰冬还从文学创作方法的角度去解读《红楼梦》中的人物。他认为曹雪芹是“极端的自然主义者”,“他写王熙凤的才干,并不是想赞美她,写王熙凤的阴险、毒辣、贪财……也不是骂她,他的目的只在创造这一类人的一个典型罢了。”李辰冬认为在《红楼梦》里,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贾雨村和薛蟠这六个人物是“最富时代性”的人物形象,贾宝玉、薛宝钗、林黛玉是“才子佳人”的代表,王熙凤、贾雨村和薛蟠则是“一般人的性格”的代表。他将凤姐明确列为一种具有时代性和普遍性的艺术典型。这种解读方法实际上是对作者如何塑造人物方法的探讨,本质上属于文学研究。
李辰冬对凤姐的解读是抽象人性论视角下的文学性研究。抽象人性论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有着一定的学术背景。以鲁迅为代表的作家们认为艺术是为人生服务的,艺术应当反映人生,因而人性是有阶级性的;以梁实秋为首的却认为艺术与人生没有直接关系,艺术是超功利的,应当为艺术而艺术,这一派多赞成普遍的人性论。李辰冬赞同后者,提倡“为艺术而艺术”的文艺观。因而,李辰冬对凤姐的解读摈弃了人物的社会历史内涵,从艺术创作的角度对人物作出了超功利的文学性解读。
五、吴宓:跨文化语境下的道德批判
新文化运动之后,中西文化的交汇给《红楼梦》研究带来开阔的跨文化视野。1919年,吴宓的《红楼梦新谈》就是一篇用西方文学理论来评论《红楼梦》的专论。该文采用美国哈佛大学G.H.MAGNADIER博士的小说学理论中关于评定小说杰作的六大标准来衡量《红楼梦》的文学价值。吴宓对人物的看法体现在对《红楼梦》宗旨的理解中,他认为《红楼梦》的宗旨正大主要表现在其写情之深,《红楼梦》写了四个层面的情,且四种情分别以贾宝玉、林黛玉、王熙凤和刘姥姥为代表。吴宓把作品的宗旨同某一人物联系起来,这种解读人物的视角有一定的新颖之处,但他在具体的阐述中又回归到清代评点家常用的道德批判立场,如认为凤姐是“弄权好货之贻害大局”的奸雄,其“桀鸷自逞,喜功妄为,聚敛自肥……”,直接导致了贾府的衰败。
1945年,吴宓撰写了一篇人物专论《王熙凤之性格》,这是他采用跨文化语境解读《红楼梦》的延续。这篇专论采用多重标准对凤姐进行解读,具体阐述如下:其一,从文学典型塑造和作者的情感态度出发,吴宓认为“十二金钗……乃指我(贾宝玉)一生所见,最可爱之女子……,举例以代表之(今语曰人物典型)”。其二,吴宓按照基督教中将人分类的标准,对宝、黛、钗和凤姐进行了分类。他认为宝、黛属于上等人——天界的神仙,其立身行事本于真理和爱情,王熙凤则是下等人——物界的魔鬼,其对人成功专凭机诈、势力。其三,吴宓根据佛教将人分为“贪、嗔、痴”的标准,认为凤姐在三类人中“属于贪之一类”“又兼带嗔,但并无痴之成分”。其四,吴宓还认为:“王熙凤为霸道之政治家,即柏拉图《理想国》书中所描写之霸主或暴君Tyrant是也。”在这篇专论中,吴宓首先从文学创作的角度出发将凤姐认定为一个艺术典型,接着分别运用基督教、佛教和柏拉图的思想等作为标准对凤姐来了个大杂烩式的评价,但其实质仍是传统的道德批判。
吴宓虽然将对凤姐的解读置于跨文化的语境之下,显示出一定的独特性,但最终仍指向道德批判。他的解读方式既带有鲜明的跨文化色彩,又打上了深深的传统烙印。这种独特的接受视角和他本人的生活经历、学术信仰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吴宓生长于陕西一个比较富裕的官绅家庭,自幼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在美留学期间,吴宓崇奉美国新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的思想,认为中国儒家的人文主义传统是中国文化的精华。他曾说:“我的一言一行都是遵照孔子、释伽牟尼、苏格拉底和耶稣基督的教导。”由此观之,吴宓思想的核心是儒家文化,加之受到其他西方文化思想的浸染,从而形成其独特的思想体系。在文学观上,吴宓始终提倡以文学来提高人的道德水准,净化作家和读者的灵魂。吴宓的世界观、道德观和文学观在解读凤姐这个人物时得到了充分的运用和体现。
六、结语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社会走进动荡不安的变革时期,新文化运动举起“科学”和“民主”的大旗,反传统、反礼教成为这一时期主流的价值观。在此语境下,季新和佩之等人对凤姐的解读带有强烈的政治功利色彩和社会批判意识。二十世纪上半叶也是一个西学东渐的时代,一批深受资产阶级文艺思潮浸染的知识分子对《红楼梦》的接受开始向文学性回归。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引用叔本华的悲剧观来阐述《红楼梦》中的人物,在红学史上具有开创意义。以牟宗三、李辰冬、吴宓为代表的学者们,则厌恶学术为政治服务,追求学术的独立地位。他们大多用西方美学理论或跨文化视角来解读凤姐,与社会政治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综观二十世纪上半叶小说批评派对凤姐形象的接受,我们看到了中国的文学批评经历了从感性走向理性,从全面借鉴西方到中西兼收并蓄的历史过程。